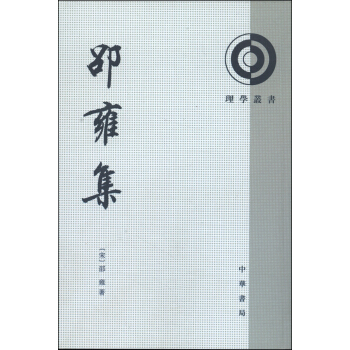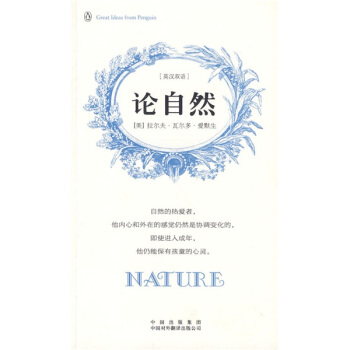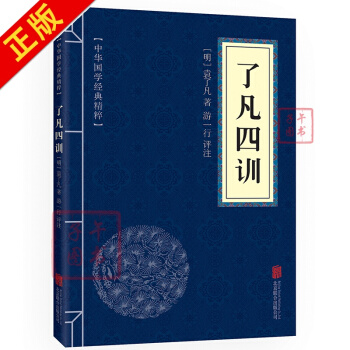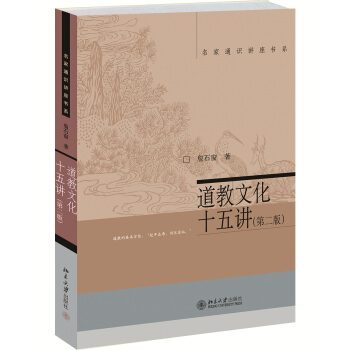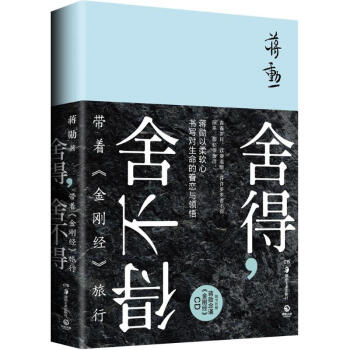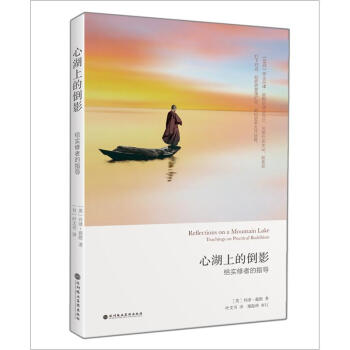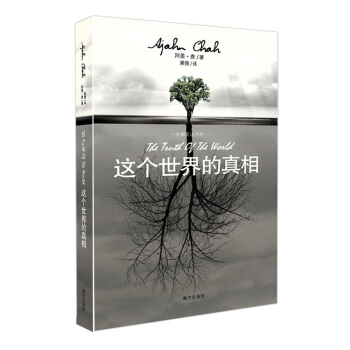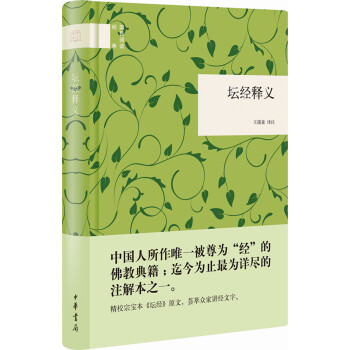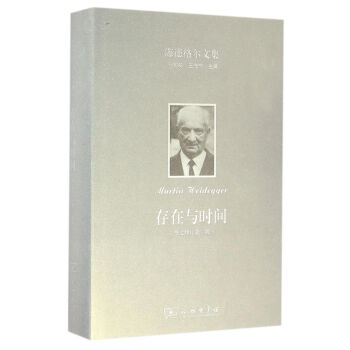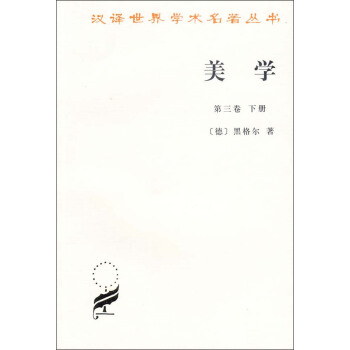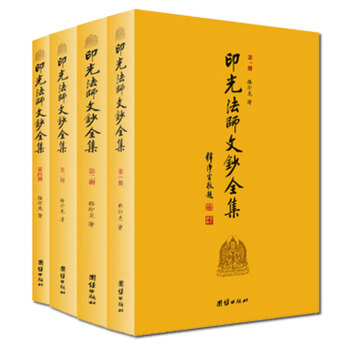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徐复观全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是台湾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的重要著作,它与《中国思想史论集》一起,完整地反映了徐复观一生的思想历程和主要学术观点。在书中,徐复观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问题等,作出了独具慧眼敏锐深刻的阐释。同时,还继承了《中国思想史论集》考证严密、思想深邃、立论卓特、文风雄健等特点。《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初版。九州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书时增入曾作为单行本印行的《公孙龙子讲疏》一书。
相关视频:
作者简介
徐复观,原名秉常,字佛观,一九〇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琂坳村。著名学者,曾任香港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台中农学院教授,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华侨日报》主笔。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目录
前言
自序
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
由《尚书?甘誓》、《洪范》诸篇的考证看有关治学
的方法和态度问题—敬答屈万里先生.
与陈梦家、屈万里两先生商讨周公旦曾否践阼称王的问题
有关周公践阼称王问题的申复
有关周初若干史实之考证
答陈胜长先生“《周官》非古文质疑”
释“版本”的“本”及士礼居本《国语》辨名
帛书《老子》所反映出的若干问题.
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
先秦名学与名家
公孙龙子讲疏.
附录:有关公孙龙之若干资料
释《公孙龙子?指物论》之“指”有关中国思想史中一个基题的考察
—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
中国自由社会的创发
释《论语》“民无信不立”—儒家政治思想之一考察.
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
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为纪念一九七九年孔子诞辰而作.
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中国的治道—读陆宣公传集书后
程朱异同—平铺的人文世界与贯通的人文世界.
王阳明思想补论.
“清代汉学”衡论.
释《论语》的“仁”—孔学新论.
精彩书摘
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
现在再看五行方面的情形。《史记·历书》谓“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这是以五行起于黄帝,当然是附会的,不足置论。传统上认文献中出现“五行”一辞最早的是《尚书》中的《甘誓》,其次是《洪范》。这留到后面,另作研究。《尚书》中的《周书》中,无五行的名词、观念。整个《诗经》中,同样的没有。在《左传》、《国语》中,才有五行的名词、观念。一般所说的五行,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原素,有同于印度佛教之所谓“四大”。但对五行观念的运用,却主要是放在由这五种元素的相互关系,即所谓相生相胜的相互关系上面,以说明政治、社会、人生、自然各方面现象的变化。以下,看《左传》、《国语》中的五行,是否与上述的观念相应。再推上去考查《甘誓》、
《洪范》中的五行观念。
《左传·文公七年》:“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杜《注》:逸书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以上《夏书》之文,下乃郤缺之解释)。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火水木金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按上引《夏书》之文,见今伪古文《虞书·大禹谟》,而杜《注》则以为系逸书,则郤缺之所谓《夏书》,当然与伪古文
《尚书》之《大禹谟》无涉。谷为生活之重要资材,此处之水火金木土与谷并列而为六府,其并为民生所不可或缺之生活资材可知,正因为如此,故与正德利用厚生,同为政治设施上之重大目标,故合称为“九功”。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罕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孰能去兵”,古人因手指为五,所以好以五为事物之定数,而六府中之谷,实为土所产生,因此,六府亦去谷而称为“五材”。就其为人所蓄聚而言,故称为“府”;就五者之功能而言,故称为“材”。五材为生活所通用而不可缺,故又称为“五行”。
《论语》“子张问行”,“行”乃通行无阻之意,五行者,乃五种通行应用之资材,所以别于一般的资材,以见其特别重要。由五行亦可称为五材之事观之,其原始为五种实用资材,盖毫无疑义。
《左传· 昭公十一年》晋叔向答韩宣子“ 楚能否克蔡” 之问,有谓“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杜《注》:“金木水火土,五者为物用,久则必有敝尽。”据此,则此处之五材,其为人所用之实用资材,亦无疑义,否则不会有“力尽而敝之”的情形。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答赵简子问礼:“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按“生其六气”,是就“天之明”来说的;“用其五行”,是就“地之性”来说的。此处,分明以五味、五色、五声为六气所出,而未尝以其为五行所出;因五行为地所生之五种实用的资材,故人得而“用”之。不过,因为这是五种最重要、最基本的资材,所以便把它作为地生万物的代表。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蔡墨答魏献子“虫莫知于龙”之问中有“……官宿(安)其业,其物乃至……故有五行之官,是为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杜《注》:‘正,官长也。’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此文以五正言之,则为古之官名,非神名也’,甚是),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按依蔡墨所说的原文,社稷五祀,分明是对于主管木、火、金、水、土、稷的几个成绩特别好、有功德于民的几位好官员,死后加以祭祀,这种死后的祭祀,与生前的“列受氏姓,封为上公”,同样是崇德报功的意思,与天神地祇毫无关系。而此处的五行,都是民生不可缺少的实物,与“稷”是民生不可缺少的实物,完全是一样。这和后来的五行观念,全不相干,所以才说“实能金木及水”,即是能把金木及水的资材培植管理得很好,等于柱和弃能把“稷”培植管理得很好一样。把五行当作五种天神,这到秦以后才渐渐形成的。但过去的注释家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此处的杜《注》说“五官之君长,能修其业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神”,这真与原文离得太远了。后来环绕“五祀”所发生的论争,都是因没有历史发展观念而来的盲人摸象的争论。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顺焉……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贰也……”按史墨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魏献子所问之蔡墨。五行若作为生物元素的气,即不应仅属于地。所以董仲舒便说“天有五行”(《春秋繁露·五行对》三十八),和此处之与天相对之“地有五行”,恰可作一明显的对照。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罕所
说的“天生五材”的天,乃兼天地而言。
……
前言/序言
去岁十一月间,复观先生自港来函,谓三十年来所写学术论著,除出版专书者外,其单篇论文,在五十年代所作者,已印为《中国思想史论集》,由学生书局出版。六十年代以后,拟再予整理,以“续篇”为名付梓。嘱询时报出版公司意见。当商诸高信疆兄伉俪,即荷承诺。乃复书先生,旋接来示,至表欣慰,并谓俟整理后约三月间交稿。盖是时先生精神充沛,体力正旺,贯注于研究学术及论衡时事,固不因宿疾未瘳而有所芥蒂也。今岁二月五日,忽接先生快函,谓因筋骨痛急欲来台,嘱代办入境证及治疗安排,经顺利完成。先生偕夫人于二月八日下午搭华航班机自港启程,余迎之于中正机场,见先生步履尚健,神态如常,惟时以手抚背,盖剧痛也。行箧殊简约,仅所携小手提箱,须臾不离,意者其中必为细软或随身用品。迨至海关检查,启而视之,则别无他物,只书稿一束而已。即《中国思想史论集
续篇》也。先生抵台后,即入台大医院,住九○七病房。翌日检查,诊断为癌细胞扩散,即照钴六十。越三日,忽感足部麻木,自踵至股。二月十四日,余得电话,谓先生有事须面谈,当即赶往,先生在病榻上,握余手,曰:“经询医师‘下肢麻木,是癌细胞侵入神经否’,答曰‘有此可能’。‘此项现象,将继续扩延否’,答曰‘有此可能’。恐旦夕间口不能言,爰将《思想史续篇》稿先行交代。整理工作,仅及其半,余将委之于曹永洋、陈淑女诸生,并
烦君作一序冠诸篇首,述其经过。”余方欲辞以不敏,先生亟止之。重以先生嘱咐之殷,不敢再言。自先生入台大医院治疗以来,瞬将两月。先生病况,时有起伏,或谈笑自若,或剧痛难忍。先生谓余曰:“纵令全身麻木,但求脑子不废,仍可将沉思所得,吐而出之也。”其忧时爱国,播学传薪之志业,溢于言表。余以清人吴锡麒寿袁随园八十文中“病到难回之日,又懒升天”之句慰之(今年农历正月初三日为先生八十整寿),先生为之莞尔。《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都六十万言,经时报出版公司同仁尽力编校,历时仅月余而全书杀青。以之持献于先生病榻之前,庶期先生见心血所瘁之作,得以问世,色然而喜,瞿然而愈。此则馨香祷祝者也。至于兹书内容,精深博大,如海如渊,浅学如余者,固不敢赞一词矣。
后学杨乃藩谨记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用户评价
我必须承认,初次接触这部学术巨著时,心中是带着一丝敬畏的,毕竟面对的是一位公认的大师倾注毕生心血的结晶。然而,在深入阅读后,这种敬畏很快转化为一种强烈的共鸣感——那是一种智者与智者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体验。作者在批判前人观点时,措辞极为审慎,既不失批判的犀利,又饱含对先贤探索精神的理解和尊重,这种平衡的艺术,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我特别欣赏他那种“不轻易下定论”的学者风范,很多时候,他会详细铺陈两种对立观点的合理性,然后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张力所在,而不是单方面地灌输某种既定的结论。这种开放式的引导,反而更能激发读者的主动思考,让人感觉自己仿佛也参与到这场历史性的思想辩论之中,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最终判决。
评分这部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初次接触时,那种厚重而典雅的气质扑面而来,让人立刻感受到内容的非凡分量。纸张的质感处理得非常考究,阅读时指尖的触感是沉静而舒适的,这对于长时间沉浸在思想的海洋中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内页的排版布局极为清晰流畅,字体大小和行间距的设置都达到了艺术与实用的完美平衡,使得那些复杂的概念和深邃的论述,在视觉上也不至于显得过于压抑或晦涩难懂。装帧的细节之处,比如扉页的设计和章节的起头样式,都透露出一种对传统学术精神的尊重与现代审美的融合,绝非市面上那种草草了事的版本可比拟。这种对物质载体的用心,潜意识中也在为读者建立一种阅读的仪式感,让人在捧起它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收敛心神,准备迎接一场严肃的智力对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光是把这本实体书放在书架上,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品味的陈设,无声地宣告着主人对深度思想的追求与珍视。
评分对于希望系统性构建自己国学知识体系的严肃学习者而言,这套书无疑是一块坚实的基础磐石。它的结构性非常严谨,每一章的论证都建立在前文的基础上,层层递进,如同精密的钟表构造,少一个齿轮都无法精确运作。我个人尝试将其作为我周末深度阅读的首选材料,发现其极高的信息密度要求我必须保持高度的专注力,这在充斥着碎片化信息的今天,是一种难得的“智力锻炼”。相较于那些只关注某一小块主题的专著,本书的优势在于其广博的覆盖面,它像是一部高分辨率的地图,标明了中国思想地理上的主要山脉与河流走向。即使是那些看似已成定论的议题,作者也能挖掘出新的切入点,或提出精妙的重估,这使得即使是老读者,也能从中咂摸出新的意味。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需要时间去消化的“慢读”经典,但其所提供的思想养分,足以支撑长久的学术探索。
评分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极为宏大且连贯的“编年史”式的视野,将那些原本看似零散的哲学思潮,串联成了一部有机的、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以往阅读类似题材的书籍,常常会感觉不同学派的观点像是一堆孤立的岛屿,而这部作品则像一座坚实的桥梁,清晰地勾勒出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压力下进行自我调适、碰撞与衍变的。特别是作者在论述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哲学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共生关系时,展现出一种惊人的洞察力。他不仅仅是在梳理理论本身,更是在挖掘理论赖以产生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语境,这使得那些抽象的义理之辨,瞬间变得鲜活起来,充满了历史的重量感。这种全景式的叙事,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中国思想史的整体理解框架,不再局限于某家某派的教条,而是开始关注思想的“流动性”与“适应性”。
评分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勉强啃下了其中关于“理”与“气”形上学基础的几篇核心论述,那种感觉,就像是深入一个极其精妙但结构复杂的古代迷宫,每走一步都需要极度的专注和反复的推敲。作者的文字风格是典型的旧学大家的风范,笔力雄健,逻辑链条严密得几乎没有可以被攻击的缝隙,但与此同时,也要求读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学术背景和耐性。这不是那种让你读起来轻松愉快的“入门读物”,它更像是一套精密的学术工具箱,里面装满了经过千锤百炼的分析工具和概念框架。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对照着其他辅助材料去理解某些关键转折点,比如他对宋明理学某些细微流派区分的界定,简直可以用“锱铢必较”来形容,这种对内涵的精确把握,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力。对于那些期待快速获得结论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会显得有些门槛过高,但对于真正想要探究中国思想脉络深层结构的人而言,这种“难读”恰恰是其价值的佐证,因为它拒绝一切浮光掠影的解读。
评分参加满减还是非常实惠的。收一些来读。经典著作
评分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但也不遑多让,塑封也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
评分不错的书呀不错的书不错的书呀不错的书
评分的书卷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写文章就才思敏捷
评分《西游记(套装共36册)》包括《猴王出世》《龙宫借宝》《齐天大圣》《蟠桃宴》《寻访取经人》《紧箍咒》《收白龙马》《黑风山》《高老庄》《黄风岭》《流沙河》《万年人参果》《波月洞》《平顶山》《真假唐僧》《火云洞》《黑水河》《除三怪》《大闹通天河》《金兜洞》《女儿国》《真假孙悟空》《三盗芭蕉扇》《伏龙寺》《小雷音寺》《七绝山》《计盗紫金铃》《盘丝洞》《智战三魔》《比丘国》《无底洞》《连环洞》《悟空斗狮精》《玄英洞》《天竺国》《灵山参佛祖》共三十六册。《西游记(套装共36册)》是一套吴承恩《西游记》共36本的连环画。天产石猴,得了日月精华,即变成仙猴。他五官俱备,四肢齐全,就如人一般。他漂洋过海,在须菩提祖师处得名为孙悟空;他在师祖处学成七十二般变化,回花果山水帘洞后逍遥自在,只因缺少兵器,大闹了龙宫,获得如意金箍棒。从此,孙悟空便有一番大作为。
评分就是力量。” 不错,多读书,增长了课外知识,可以让你会感到浑身充满了一股力
评分期盼已久的宝贝儿,趁着活动,果断拍下,终于如愿。包装精美,物流很快,非常满意。
评分商品是否给力?快分享你的购买心得吧~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