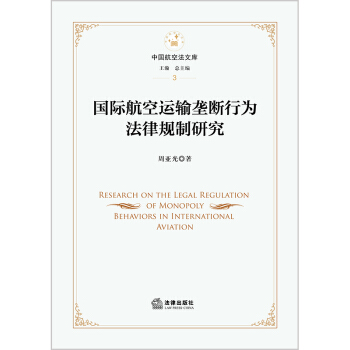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医疗 法律与生命伦理(套装上下册)》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今世界人们普遍关注、尤为媒体特别关注的医疗法律与伦理问题,资料丰富,视角开阔,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共13章:1导论、2脑死论议、3死亡习题、4终末医疗、5器官移植、6人体试验、7生育控制、8人工生殖、9复制生命、10基因技术、11变性手术、12同性婚姻、13艾滋病。《医疗 法律与生命伦理(套装上下册)》既立足于法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又能深入浅出地解释和引用大量科学技术、生物伦理的相关理论,结合时事新闻、著名案例,作者跟踪国外立法、判例的不同发展阶段,综合性强,适于一般大众与从事法学研究、医疗法律实务工作人员阅读。
目录
上册代序
第一章导论
--医学与生命伦理
一、医学的两个面向
(一)面向生命
(二)面向医学
二、医学的多元性
(一)巫医的故事
(二)两个科学属性
三、医学的人文精神
(一)概说人文主义
(二)医学以人为本
(三)守护"爱"的医学
(四)商业利益挂帅
四、医学的主要职能
(一)生命的延长
(二)社会的复归
五、审视科学的哲学
(一)概说两种思维
(二)科技悲观主义
(三)科技研究自由
(四)小结
六、关于生命伦理
(一)概说
(二)历史回顾
(三)明确的定义
(四)"生"的现实论
(五)"死"的现实论
(六)伦理委员会
(七)基本原则的出现
七、人的核心价值
(一)概说
(二)关于人的尊严
(三)不同时代的定义
(四)人性尊严的特质
(五)人性尊严的损害
(六)人的尊严的核心
八、基本伦理原则
(一)自主性原则
(二)生命价值原则
(三)有利无伤原则
(四)行善原则
(五)公平正义原则
(六)小结
九、结语
第二章脑死论议
--死亡定义的转变
一、死亡的问题性
二、如何定义死亡
(一)生物学上的死亡
(二)临床上的死亡
(三)定义的不确定
(四)法律上的死亡
(五)反脑死的呼喊
三、死与生的区别
(一)死亡的过程
(二)生与死的交错
四、判定精确化原则
五、脑死说的层次
(一)脑死说的直面
(二)全脑死说
(三)脑干死说
(四)大脑死说
六、脑死之伦理性
七、不宜明文规定
八、脑死与死亡时点
九、脑死之诊断
(一)美国
(二)芬兰
(三)挪威
(四)瑞典
(五)丹麦
(六)瑞士
(七)奥地利
(八)德国
(九)英国
十、判定程序
(一)判定标准的演变
(二)哈佛大学判定标准(1968年)
(三)明尼苏达大学判定标准(1971年)
(四)日本判定标准(1985年)
(五)英国判定标准(1976年)
(六)德国判定标准(1982年)
(七)瑞士判定标准(1983年)
(八)葡萄牙判定标准(1998年)
(九)大陆判定标准(2002年)
(十)台湾地区判定标准
十一、判定医师
十二、宣布脑死亡
十三、脑死之误诊
(一)误诊之陷阱
(二)不同的脑干病变
(三)误判的三种形态
十四、脑死与尊严死
十五、脑死与器官移植
十六、脑死与植物状态
(一)植物状态
(二)临床诊断标准
(三)脑死与植物状态
(四)治疗义务
(五)复苏可能
十七、结语
第三章死亡习题
--有死亡权利吗
一、死是生命的轴心
二、死亡观的再飞跃
(一)再提死亡话题
(二)死亡学是显学
三、能被管理的死亡
(一)安乐死
(二)自杀
(三)协助自杀
(四)医助自杀
(五)可逆转的死亡
四、有死亡的权利
(一)模糊的"死亡权"
(二)从自杀的观点而言
(三)自我决定的观点
(四)协助自杀的观点
(五)就道德权利观点
(六)小结
五、再论安乐死
(一)古典意义的安乐死
(二)现代意义的安乐死
六、安乐死的类别
(一)自愿的安乐死
(二)非自愿的安乐死
(三)无意愿的安乐死
(四)主动的安乐死
(五)被动的安乐死
(六)其他分类
七、安乐死的民意调查
八、断种与安乐死
九、安乐死论的系谱
(一)生命神圣
(二)自我决定
(三)社会观点
(四)滑坡理论
(五)医学观点
(六)其他观点
(七)小结
十、安乐死在英国
十一、安乐死在美国
(一)安乐死立法运动
(二)延命拒绝权扩大
(三)加州自然死法案
(四)代行判断之拟制
(五)统一末期病患权利法案
(六)医助自杀的动向
(七)沃克诉奎尔案
(八)泰莉?夏佛案例
十二、安乐死在澳大利亚
十三、安乐死在荷兰
十四、安乐死在比利时
十五、安乐死在瑞士
十六、安乐死在法国
十七、安乐死在日本
(一)案例一
(二)案例二
(三)案例三
(四)案例四
(五)案例五
(六)案例六
十八、安乐死在以色列
十九、安乐死在回教世界
二十、植物人与安乐死
(一)谁有权剥夺生命
(二)植物人是活人
二十一、实行程序
二十二、重残新生儿与安乐死
(一)问题所在
(二)几个不同的观点
(三)几个案例
(四)问题解决的方向
(五)延命治疗的中止
(六)早产儿
二十三、终末期与医助自杀
(一)合法化的动向
(二)伦理的分析
(三)指导原则
(四)相关案例
二十四、总结
第四章终末医疗
--尊严死的选择
一、终末期病患
(一)终末期的定义
(二)终末期病患
二、终末期医疗
(一)一个案例
(二)延命医疗
(三)缓和医疗
(四)两者的不同
(五)问题之所在
三、生命质量
(一)坚持生命质量
(二)尊严死的提倡
(三)与安乐死不同
(四)相关伦理争议
四、自我决定权
(一)自主性的界定
(二)自主性的落实
(三)自主性的扩张
(四)人权保障的催生
(五)技术主义的回响
(六)与隐私权的交错
(七)与法益的放弃
(八)家属的决定权
五、预立医疗指示书
(一)历史考察
(二)事前指示
(三)书面指示
(四)口头指示
六、维持生命的手段
(一)手段的意义
(二)手段的基准化
(三)标准的公式化
(四)原则的再解释
七、执拗的治疗行为
(一)良心条款的导入
(二)概念的现代化
八、双重效果原则
(一)双重效果原则
(二)双效原则的适用
(三)双效原则的再补充
九、安宁疗护制度
(一)历史考察
(二)安宁疗护的内涵
(三)四全的照顾理念
(四)家属的精神关怀
(五)与安乐死不同
十、拒绝执拗医疗
(一)拒绝与中止不同
(二)拒绝权利的根据
(三)执拗的医疗措施
(四)拒绝权的行使
(五)有尊严的善终
(六)尊严死的实现
十一、中止延命医疗
(一)容许中止延命医疗
(二)行使中止延命医疗
(三)中止的行使要件
(四)中止医疗的内容
(五)中止要件之分析
(六)道德问题与争论
十二、中止行为的性质
(一)作为说
(二)不作为说
(三)分析与检讨
十三、中止行为的刑法评价
(一)概说
(二)两个相关的案例
(三)中止行为的定性
(四)中止行为正当化
第五章器官移植
--人间至爱主义
一、移植的概念
二、历史回顾
(一)神话阶段
(二)实验阶段
(三)临床阶段
(四)发展阶段
三、移植类别
(一)同种器官移植
(二)异种器官移植
(三)其他器官移植
四、移植现状
(一)角膜移植
(二)心脏移植
(三)肾脏移植
(四)肝脏移植
(五)胰脏移植
(六)肺脏移植
(七)骨髓移植
(八)眼球移植
(九)头颅移植
(十)子宫移植
(十一)卵巢移植
(十二)睾丸移植
(十三)肢体移植
(十四)颜面移植
五、移植梦魇
(一)移植梦魇
(二)供不应求
(三)排斥反应
(四)抑制药物
六、器官属性
(一)活体器官
(二)尸体器官
七、器官的来源
(一)活体器官
(二)尸体器官
(三)胎儿器官
(四)无脑儿器官
(五)人造器官
(六)复制器官
八、器官捐献模式
(一)器官捐献卡
(二)标准捐献模式
(三)活体交叉捐献
(四)连锁性捐赠
九、冷冻器官
十、器官买卖
(一)从卖血说起
(二)器官市场
(三)伦理争议
十一、移植之适法性
(一)摘取器官
(二)移植器官
十二、动物器官
(一)异种供体
(二)病毒风险
(三)排斥风险
(四)人体基因猪
(五)知易行难
(六)伦理争议
(七)异种器官管理
十三、移植立法例
(一)日本
(二)美国
(三)英国
(四)丹麦
(五)法国
(六)西班牙
(七)中国
(八)新加坡
(九)德国
十四、移植费用
十五、移植与性格
十六、器官分配
十七、商品责任
(一)器官瑕疵
(二)瑕疵责任
十八、移植地点
十九、总结
下册
第六章人体试验
--一把"双刃剑"
一、一把"双刃剑"
(一)科学实践之父
(二)试验的必要性
(三)恶性的一面
(四)无可逃避的宿命
二、人体试验与常规医疗
三、晚近的人体试验
四、人体试验类型
(一)天然试验
(二)自我试验
(三)自愿试验
(四)研究试验
(五)治疗试验
(六)其他分类
五、人体试验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
(二)第二阶段
(三)第三阶段
(四)第四阶段
六、人体试验的方法
(一)盲性试验
(二)随机化试验
(三)安慰剂试验
(四)对照组试验
(五)多中心试验
(六)小结
七、人体试验项目
八、试验的伦理规范
(一)纽伦堡准则
(二)赫尔辛基宣言
(三)日本厚生省原则
(四)美国医师协会伦理纲领
(五)贝尔蒙特报告
(六)国际伦理指引
(七)优良临床试验准则
(八)欧洲理事会公约
(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
九、审视试验伦理
十、相关试验伦理
(一)自主原则
(二)善行原则
(三)公正原则
十一、知情同意
(一)概说
(二)信息的揭示
(三)信息的理解
(四)自愿的同意
(五)同意的能力
(六)族群与社区的同意
十二、试验利益
(一)利益冲突
(二)损益评估
十三、对象的选择
(一)以儿童为对象
(二)以孕妇为对象
(三)精神障碍者
(四)以病患为对象
(五)小结
十四、跨国双重标准
十五、试验管制方式
(一)研究自由
(二)确立许可制
十六、人体试验适法性
十七、费用负担与补偿
(一)费用负担
(二)损害补偿
十八、动物试验
(一)动物试验
(二)跨物种伦理
(三)动物解放论
(四)动物权利论
(五)反动物权利
(六)替代方案
(七)选择动物
(八)人道主义
十九、结语
第七章生育控制
--优生的社会
一、优生的社会
(一)优生概念
(二)优生运动
(三)新优生学
二、绝育手术
(一)结扎目的
(二)强制绝育
(三)奖励绝育
(四)绝育与断种
(五)法制变革
(六)伦理争议
三、关于避孕
(一)怪异的避孕法
(二)避孕药的发明
(三)安全套的使用
(四)允许避孕的理由
(五)主要的伦理问题
四、性别鉴定
(一)性别形成
(二)伦理问题
五、产前诊断
(一)产前诊断
(二)伦理问题
六、着床前基因诊断
(一)受精卵的遗传检查
(二)问题性与伦理争议
七、不当出生与不当生命
(一)不当出生
(二)不当生命
(三)不当怀孕
(四)过失致畸
(五)侵权诉讼
(六)小结
八、人工流产
(一)历史考察
(二)从犯罪到权利
九、美国堕胎法的变革
(一)限制堕胎时期
(二)法制变革时期
(三)划时代的案例
(四)三阶段堕胎理论
(五)罗伊一案的余波
(六)转趋保守的判决
十、立法模式的转变
十一、其他立法例
(一)英国立法状况
(二)德国立法状况
(三)其他立法状况
十二、西方文明的缺憾
十三、胎儿的生命权
(一)胚胎的地位
(二)母亲身体的一部分
(三)有感觉的生命
(四)胎儿是人吗?
十四、妇女的决定权
十五、残疾新生儿
(一)治疗界限
(二)道德观的变化
(三)谁来决定
(四)决定基础
第八章人工生殖
--奇妙的新世界
一、生殖技术
二、生育自由
(一)生育权利
(二)子女利益
三、人工生殖方式
四、人工授精
(一)在配偶之间
(二)非配偶之间
五、精卵的捐赠
(一)精卵的定性
(二)精卵的筛检
(三)捐赠的限制
(四)互盲原则
(五)误植精卵
六、冲击与挑战
(一)伦理冲击
(二)实施对象
(三)多胎问题
(四)胚胎买卖
(五)亲子关系
(六)子女知情权
(七)器官的来源
(八)婚姻效力
(九)小结
七、冷冻胚胎
(一)精卵冷藏
(二)胚胎孤儿
(三)胚胎的归属
八、死后生殖
(一)死后取精
(二)各种事例
(三)遗腹胚胎
(四)伦理争议
(五)相关立法例
九、胚胎的使用
(一)胚胎的处分权
(二)禁止试验研究
十、代孕母亲
(一)典型的孕母
(二)代孕与生育权
(三)商业性代孕
(四)相关立法例
(五)出现人造子宫
十一、代孕契约
(一)M女婴案例
(二)Calvert 诉Johnson案
(三)女同志代孕
(四)契约当事人
(五)契约相关内容
(六)子女交付义务
(七)确定母子关系
(八)相关伦理挑战
(九)小结
十二、结论
第九章复制生命
--从花园到实验室
一、划时代的突破
二、什么是复制?
三、复制的魔盒
四、治疗性复制
(一)概说
(二)国际研究现状
五、干细胞研究
(一)干细胞类别
(二)神奇价值
(三)相关的伦理争议
(四)美国研究现状
(五)英国研究现状
(六)加拿大研究现状
(七)德国研究现状
(八)日本研究现状
(九)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六、复制的梦魇--生殖性复制
七、技术的突破
(一)人类胚胎的复制
(二)伦理争议
(三)祸福难料
八、复制设想
(一)受精卵
(二)复制器官
(三)复制自己
(四)历史人物
(五)优生复制
九、复制人大事纪
(一)桃莉诞生前
(二)桃莉诞生前后
(三)桃莉诞生后
十、立法趋势
(一)英国
(二)日本
(三)美国
(四)法国
(五)加拿大
(六)俄罗斯
(七)世界卫生组织
(八)欧盟
(九)意大利
(十)联合国
十一、法律疑义
十二、反对意见
(一)从宗教的观点来看
(二)从生物医学角度来看
(三)从人类进化角度来看
(四)从伦理学角度来看
(五)从性别比例失调来看
(六)从遗传问题来看
(七)从优生学的观点来看
(八)从人的本质来看
(九)从科学探索的观点来看
(十)从其他观点来看
十三、赞成意见
十四、折衷看法
十五、地下市场
十六、结语
第十章基因技术
--医疗的未来
一、从基因的发现--到基因组
(一)基因的发现
(二)人类基因组
二、基因决定论
(一)概说
(二)基因决定论
(三)环境决定论
(四)双重决定论
三、基因组计划
四、基因组的价值
五、基因风险
六、基因治疗
(一)基本原理
(二)基因诊断
(三)治疗类别
(四)历史轨迹
(五)治疗风险
(六)伦理问题
(七)立法管理
(八)专利争议
七、基因检测
(一)检测与筛查
(二)遗传检测
(三)知道好吗?
(四)新生儿检测
八、基因干预
(一)基因干预
(二)产前基因干预
(三)胚胎植入前的基因检测
(四)婚前基因检测
(五)设计婴儿
(六)伦理守则
九、基因普查
十、其他问题
(一)基因优生
(二)机会不均
十一、基因隐私
(一)基因信息
(二)基因隐私
十二、基因歧视
(一)概念
(二)保险与基因歧视
(三)人种与基因歧视
(四)职场与基因歧视
(五)立法趋势
(六)小结
十三、专利争议
十四、国际规范
十五、转基因生物
十六、基因与司法鉴定
(一)亲子鉴定
(二)刑事鉴定
(三)其他身份鉴定
(四)基因组照片
(五)小结
十七、结语
第十一章变性手术
--捕错灵魂的躯体
一、上帝也困惑
二、变性欲的特征
三、变性手术--拯救被扭曲的灵魂
四、手术的条件
(一)事实与争论点
(二)法院判决结果
五、立法现况
前言/序言
代序科技与伦理的遇合
——从斯诺的两种文化说起
一
有两本书,一本是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年)斯诺是20世纪的英国名人。1956年在《新政治家》杂志发表短文《两种文化》,1959年又发表以此为题的著名的瑞德演说,1963年发表《再论两种文化》,以后结集为一本小书并有过若干次增订。斯诺那篇一个多小时的瑞德演说,至少做成了三件事:一是拋射出了一个词汇、一个概念(两种文化),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二是阐述了一个问题(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文化分裂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三是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参见龚育之:“科学与人文:从分隔走向交融”,载http://www.csc.pku.edu.cn/art.php?type=4&sid;=1583。将其于1959年在康桥大学所做著名的瑞德演讲(Rede Lecture)讲稿正式出版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另一本是美国学者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的《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说的就是由于教育背景、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的诸多不同,有两个群体即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之间相互不理解、互不交往,久而久之,或者大家老死不相往来,虽相互鄙视却相安无事,或者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甚或相互攻击。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斯诺命题。这种两种文化割裂的现象,早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就现端倪并被一些敏锐的思想家观察到。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美人文主义传统在英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的马修?阿诺德(M. Arnold,1822~1888年),也提出过类似两种文化的观点。他在1869年那篇享有盛名的论文《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中,对英国人所“尊崇的机械与物质文明”和使得“人性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的文化之间作了一番对比,认为人类“对机器的信仰已经到了与它要服务的目的荒谬地不相称的地步……好像机器本身或其作为目的就存在一种价值似的。”他认为现代文明更应该珍视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主义理想,因为“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在的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参见刘钝:“斯诺命题今昔和科学史的文化功能”,。斯诺宣称,存在不兼容的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它们之间有着一条危险的鸿沟。“第三种文化”说的是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谁最有发言权?谁更有发言权?是人文学者?还是科学阵营的思想家?指出科学文化向人文领地的“入侵”,是科学家直接向人文学者“争夺”公众话语权。不用奇怪的是,很多科学家把人文科学看作是“对科学家是没有帮助作用的,正如鸟类学对于鸟类来说不相干一样”。苏珊?哈克(Susan Haack):“既非神圣亦非骗局:批判尝试主义的宣言”(Defending Science-Within Reason: Between Scientism and Cynicism,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2003),收录于刘大椿、刘劲扬主编:《科学技术哲学经典研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因此,科学被认为是与人的精神相左,人文精神的丰富多彩已被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遗传学抹上一层罪恶的阴影。
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实际上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路。那就是科学与传统价值观的沟通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对技术和科学所持的态度。有一些人虽否认鸿沟的存在,认为科学本身是立于人的价值观并委身于人的价值观,科学运用本身是一回事,如何运用科学又是另一回事。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的人文传统过于深厚,因此斯诺曾经“恼火地”问人文学者:“你们中间有几个人能够解释一下热力学第二定律?”斯诺很替科学家抱不平。而在布罗克曼的“第三种文化”中,人文学者的傲慢和自负依然故我。就在科学家们努力创建完备的科学体系、科学显露出繁荣曙光之际,两种文化的分裂,形成传统人文价值对科学的反动。研究人文学科(liberal arts)的人文学者轻视科学家,认为科学属于机械技艺(mechanical arts),因此有些已被科学家接受为已知事实或客观性证据或诚实探究的东西,也常常被认为并非如此。又科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分子,对社会有其应负的伦理道德义务,从事科学研究不能不遵循一定的科学伦理,对于有悖伦理的研究项目,不能甘冒高度的风险,而伤了人类的利益,脏了自己的双手。遗憾的是,科学家们有些并不承认人文及社会科学也是真正的科学,科学家们甚至相信,科学中没有重大的伦理问题。一些科学机构认为科学研究中固然有所谓“科学不当行为”,但将不当行为界定为研究中出现的捏造、伪造和抄袭,并不包括违背不伦理的行为。论者因此认为这些定义在思考或讨论科学研究中的伦理议题时,并不特别有用。更认为如果科学中的伦理问题可以黑白分明,轻松了解,便不需要写一本科学伦理的书,也不需要像学科学的学生教授伦理。参见David B. Resnik著:《科学伦理的探索》(The Ethics of Science),向画瑰译,台湾伟伯文化国际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95页。总而言之,科学家虽然生活在人类社会,却不解科学的成功何以会被认为与人文是相冲突的,因此科学研究不断地在传统伦理道德藩篱中突围,科学家不问科学行为是否违背伦理的原则,一心想把人类带到一个科学的新天地里,这正好显示出科学与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剧烈冲突。
按照斯诺的看法两种文化冲突的原因,是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是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人文领域的好就像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年)所说: “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之最完美的表达”(the best that is known and thought in the world),因此有教养的人文学者无须关注科学的细节。可以说人文学者的观点都具有反科学的态度,持这种态度有如下含义:重心在人不在外力;强调情感和道德而不是仪器计算;使用解释的而非定量的方法;思想上赞同一种和技术与实证科学的危险作斗争的“道德的”社会。但人文学者不能否认的是,科技的力量是深不可测的,人类生活的不断改善,来自于技术的不断发明。而迄今为止的几百年来,人类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功,毫无疑问地也是体现在科学领域。科学有卓越性也具有实用性,也使人类的实际生活更具多样性,是唯一能够促进我们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活动。我们认为科学家对人文的无知不一定存在,人文学者对科学的傲慢也未必,如果说有的话,更多地也是科学对人文的傲慢,这种傲慢的存在常常源于科学发展的特质——“双面刃”。换句话说,科学研究有局限性这是科学家难以忍受的,因此科学家在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与追求知识的同时,只强调科学是“强有力的、值得信赖的、是好的”的主张,就不会把科学看成是文化的一部分。科学的研究不能不考虑一切人类价值,以生命科学为例,一方面使人类对生命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现象和高度统一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却也提出许许多多的社会、法律难题,并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严峻的挑战。
我们认为善与美是伦理道德的重要元素,科学如只偏执求真,忽略科学的善与美,如只计利害不问是非,任令道德思维滞后与科学现实,科学与伦理的冲突必然产生。毋庸讳言,冲突的现实已将科学家与伦理学者逼向进退两难的境地。状况的改善必须寻求一个融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两者都不能把自己装在过于主观的意识形态的盒子里。2014年3月27日一位80岁英国退休教师安妮,感叹自己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加上无法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在孙女的陪同下到瑞士安乐死。她认为“现代高科技社会,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每个人都像机器人,缺少人性。《苹果日报》2014年4月8日A18版。”其实无论科学方法如何地被视为人文的敌人,科学的发展已为伦理提供存在及力量的实质支持。来自哈佛大学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威尔森(James Q Wilson)在他1993年的经典著作《道德感》(The Moral Sense)一书中,选择广泛的研究题材,他不仅研究演化论、人类学、犯罪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他的结论是,无论知识分子如何争辩,某些普世的、引导性的道德本能确实是存在的。对于伦理与科学的冲突,他建议我们,“无论科学方法如何的被视为是道德的人,科学的发现其实为道德提供了存在及力量的实质支持。”麦可?迦萨尼迦著:《伦理的脑》(The Ethical Brain The Science of Our Moral Dilemmas),吴建昌等译,原水文化2011年版,第282页。威尔森的建议凸显伦理道德确实已浮上科学的台面,伦理道德是“真实”的存在,科学的发展一定要有伦理道德的元素。换言之,强调科学发展的重要,绝不能舍弃人文的想象,无视人文的炫目耀眼。
对于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斯诺认为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才不至于偏颇、忽略甚至于离题,一件是以人文学者熟悉的方式向他们讲述科学的故事,让他们理解科学的人文意义,而不是把科学当成一个有害传统伦理道德的东西。另一件是向科学家阐述科学的形象,唤起科学家的人文自觉,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文价值的建设者,也是伦理道德的捍卫者。我们要指出的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除了双方都要有如斯诺所说的自觉之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明智而公正地处理双方的冲突?亦即如何控制具有潜在爆发力的科学研究的使用和应用而使之不背于伦理道德,不致造成“科学巨人,道德侏儒”的扭曲现象,不致成为美国总统生物道德委员会主席卡斯(Leon Kass)所称之“嫌恶的智慧”,这才是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共通的使命。能够有个起始点当然是好事,但前方的路又是另一回事,如何调和科学与人文这两种不同特性、不同领域的学科,在日益复杂的科学研究中,科学研究者能否反身性地做到,才真的是崎岖且漫漫的一条长路。
有件事是清楚的也是存在的,即普世伦理是依存人性(being human)而建立的,科学研究是一项社会、政治、法律及其他秩序脉络下所从事的活动,如忽视人性的特质脱离人性的轨迹,当然会引发伦理议题以及争论。纯粹客观的科学是个神话,是某些人为了逃避令人困惑、苦恼的争议性问题而瞎编出来的神话。伦理上的两难道德两难的例子俯拾皆是。哈佛大学神经哲学家贾书华?葛林(Joshua Greene)提出两个常用的例子。比如说你正独自开着你的新车并且你看到路边有一个人。他发生了意外并且浑身是血。你可以带他就医拯救他的生命,但你会把你的新车弄得血淋淋的。弃他不顾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吗?或者在另一场景中,你在一封信当中接到一个请求,说如果你寄去100美元,你就可以救10个挨饿的小孩。不寄钱过去是可以的吗?麦可·迦萨尼迦(Michael S.Gazzaniga)著:《伦理的脑》(The Ethical Brain The Science of Our Moral Dilemmas),吴建昌等译,原水文化2011年版,第288页。及伦理议题可能出现在科学中,也是科学成为伦理的对象之后人类必然要面对的课题,因此科学研究必须进行除法律之外的伦理道德的规范。David B. Resnik著:《科学伦理的探讨》(The Ethics,of Science),何画瑰译,台湾伟伯文化国际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页。科学技术在证伪中不断进步,牛顿、托勒密或许已经过时,但科学技术原本是人的权力的表现,是行为的一种形式,因此无论有多少天才不断地超越前人,他们的一切行为当然仍须受到伦理道德的检验。1942年现代科学社会学的开山鼻祖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发表一篇题为《民主秩序下的科学与技术》的文章,提出四个科学的精神特质的构成要素,其中两个是公有性和无私利性(另外两个是普遍主义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公有性强调要把科学中的产权削减到最小限度;无私利性是由公有性延伸,要赋予科学成果更更广的社会实用性。因此,科学家在其行为举止中,必须优先保证大众的利益,可能产生的个人得失则要让位。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Saint John Perse,1887~1975年)在他令人难忘的领奖辞中也说:“科学家也好,诗人也罢,应该表彰的是他们思想的无私。”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著:《拉丁美洲的孤独》,李静译,南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这是科学研究制度上必要的伦理规范。
在国际上常因伦理上的考量,对于医疗科技新技术的发现,大多以法规排除不予专利,唯排除的范围大小不同,有完全排除者、部分排除者,甚至全面开放者。在制度方面,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对于人类的贡献日渐增加,因此有日趋开放而给予较广之专利保护的趋势。但2003年12月13日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萨尔斯顿于2002年与英国的布雷内(Sydney Brenner)、美国的霍维茨(H. Robert Horvitz)同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评审委员会表彰他们发现了在器官发育和“程式性细胞死亡”过程中的基因规划。程式性细胞死亡是细胞一种生理性、主动性的“自觉自杀行为”,这些细胞死的有规律,似乎是按编好了的程式进行的,犹如秋天片片树叶的凋落。又称为细胞凋亡。程式性细胞死亡在生物发育和维持正常生理活动过程中非常重要。参见程书钧、潘锋、徐宁志编著:《话说基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萨尔斯顿(John Sulston)到台北访问,在以“社会与人类基因”为题的座谈会中,萨尔斯顿大声疾呼,表示有关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信息不应成为私人所有,也不应过度专利保护,而应开放所有人自由使用。这表示现代科学是世界范围的,个人的私利应该让位,与罗伯特?默顿的说法不谋而合。萨尔斯顿说:“人类应该注意专利等障碍造成悬殊的贫富差距,最终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当被问到作为一个科学家,何以如此坚持平等、消弭贫富差距时,他又说:“以前只做科学研究,从未思考过研究对社会有何影响,直到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也看到人类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他发现“不平等与不人道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人们赞美科学的理论成就,欢迎改善人类生活的技术发展,但人们也发现科技的自由成为一种不受抑制的权力意志(will-to-power)而造成人们堕入虚无的焦虑深渊时,人们才感到沮丧并对于科学家的傲慢自大感到烦心。当发现科学中的造假、不端行为和无能为力时,科学如何造假,请参见霍勒斯?弗兰里?贾德森著:《大背叛——科学中的欺诈》(The Great Betrayal:Fraud in Science),张铁梅、徐国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人们又会大失所望。我们可以这么说,科学可以造福人类,科学可以毁灭人类,是造福是毁灭,问题不在于科学,是在科学家。萨尔斯顿上面这一段话,让我们惊喜于科学家的自觉,终于促成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美好结果。
历史上诞生过的奇迹不计其数,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当属令人瞩目的科学发展,那固然是另一个照进现实的伟大梦想。不过,在科学乐观的全面发展中,并不是没有另类的声音。晚近在研究领域上,人类人伦思想、社会公益道德、哲学上的价值论、公益论已开始进入高新科技的领域,学者们纷纷提出各种新一系列的伦理观察,可说是对于科学发展的伦理反思。在对科学的发展进行伦理反思时,必须解决科技发达中所面临的深陷人心的伦理困惑。这种伦理困惑不仅在于科学技术恶意的滥用,在出现恶意滥用的意图时,即便它被善意地利用到本来的和最合法的目的,科学技术仍不免有其危险的一面。例如避孕药丸的发明是基于善的目的,但药丸不加区别地供应,在一个本来就是享乐主义的社会,无异助长了性泛滥,怂恿了性与生殖和爱情的异化。人们终于惊觉现代科学发展,在它以飞快的脚步前进中,人们竟已面临这样一个困局,就是科学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功,却也对人们形成巨大的威胁。解决科学发展中对于深陷人心伦理的困惑,还须理解科学不能只是科学家的科学,伦理也不能只与伦理学者有关。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在《致千禧年》一文中就说:“科学只有科学家有关的想法是反科学的,正如诗歌只与诗人有关的想法是反诗歌的。”点出科学与人文之间相融合的道理。科学与人文之间有很多共通的语言,偏执其一科学就不是真正的科学,人文也就不成其为人文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科学、教育、文化的表述不清,让人误以为科学、教育、文化是三码事(其实是一码事)颇有微词,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著:《拉丁美洲的孤独》,李静译,南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也就不觉得突兀了。
在过去科学与人文都势不两立的情况下,人们自己反而早在科技发展“善”的光环中冲昏了头脑。在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时,人们从未想到要将人文思维吸收进科学的成就。例如,人们只知核电有益于现实人生,却不知核废料将贻祸几代子孙,核武器更可能使地球回到最初的原点。人们在智识大开猛然醒悟之后,终于看到摆在无限制的科学研究的前方竟是如此凶险万状,人们也已知道科学就像一把“双刃剑”,意外的是这样的觉醒竟成为人们挽救自己的一线曙光。人们认识到自己才是可能酿成灾难的始作俑者,人类既是可怕的肇事者,但也是潜在的拯救者。但对于科学思维有新的反省,并不容易彻底解决科学造成的规范失序与祸害苍生的现象。人们应该认知,除了科学家自救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救世主会挺身而出,这是科学家们当仁不让无可推卸的义务。质言之,科学家们必须重新进行自我调整,另行确立以“人类利益至上”、“以人的需求为本”的新的价值观,在科学研究中重新诠释“至善”、“义务”以及“罪恶”的意义,一改过去只热衷战斗(研究)却漠视应有崇高道德修养的骑士精神。而拜科学家的自觉和学科分类的专业化思潮,各种科学伦理学科如“地球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生命伦理”、“医学伦理”等规范性的伦理学门,也迅速地发展成新一轮学术网络聚焦的光点,从而开启了伦理学史上的新篇章。
生命伦理原就是伦理学的一部分,如今更成为当代极为重要的论题。尤其随着生物科技的一日千里,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老、病、死展现强烈的干预与操纵,各种困惑人心的尖端医疗萦绕每个人的身边,如人工流产、脑死判定、安乐死以及与这有关的生前预嘱、健康照护的有效法定代理人,以及代理孕母、生殖技术与复制技术、基因改造设计婴儿、同性恋等问题。这些问题可都是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但归根结底,生命伦理牵涉的最核心课题,仍是千古以来伦理学乃至于哲学的根本议题——人的基本价值,即“人是谁”?人有何生命的特质、价值与意义?常言道,生命的本质是一切实在的本质,如将生命尊严作为整体成为考察的资料和知识的背景,一切医疗科技和理论、知识和方法、功能等都得重新评价。因此,要解决科技应用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要想拨云见月,除却人类心灵的茫然与困惑,维护人的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我们就必须回到生命伦理思维的最根本之处,亦即人的主体性,去建立对真理、对生命的基本认识与了解。换言之,就是表现以同理心、悲悯心在各种纷扰不已的伦理争议中做出平衡的判断。值得提出的是2013年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以其非凡的方式,对于堕胎、同性恋、避孕等棘手问题,不执着于“眼光狭窄的规定”,强调以同理心处理让自己成为世界良知的新生因,而在仅就任几个月获选为“时代”杂志封面风云人物。可预见的是一种天主教的新伦理观将影响世界。
在生命伦理与医学领域中,埃德蒙?佩莱格林诺(Edmund D.Pellegrino)认为医学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构筑了一座独特的桥梁:“医学是科学学科中最人道的科学(the most humane of sciences),是最经验主义的技艺,是人文学科中最富有科学性的学科”。“医学人文主义已获得了其救世主的地位。这个地位赦免了当代医学的可以察觉到的罪恶。这些罪孽的罪名很长,五花八门,有时互相矛盾:什么过于专业化、技术主义、过于职业化,对个人的价值和对社会文化价值缺乏感知(麻木不仁),对医师的作用的解释过于狭隘,治疗多于关怀,对预防、患者参与,以及对患者的教育强调不够。医术讲得多,人文关怀讲得少,行为科学不足,经济诱因太多。”佩莱格林诺这段话正充分地反映出医学与伦理学之间方方面面的冲突。在生物科技生命伦理冲击的议题上,日本生命伦理学学者森冈正博教授提出一个“没有根据的樊篱”概念,他认为纵使因科技介入而有助于某些人的治疗,但仍然希望人类的生命中有一个绝对不可侵犯及介入的地方,而这样的信念就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樊篱”,这种“没有根据的樊篱”乃源自一种“根源性安全感”,一旦科技过分介入人类的生命,科技将不知不觉、有系统地剥夺我们的“根源性安全感”。森刚正博:“‘没有根据的樊篱’与‘根源性安全感’论基因科学的规制”,载基因科技伦理、法律与社会议题国际研讨会,台湾大学日本宗和研究中心,2001年5月26日。我们常说,在医学的实践及医学人文的面向,人文关怀的核心问题是去关怀我们自己以及别人,有德性的医师会在医疗行为中培养出对于病患爱的情怀、关怀性的关系,自然不会只专注于医疗技术的运用,不会关注于医疗的成就和功绩,而也会遵循医学伦理道德原则。
实际上,伦理学本来就是人文科学之一,其内容涉及道德,涉及风尚,涉及有道德价值的所有东西,并被视为是人的行为准则。在医学领域中,与生命攸关的问题如能离开单纯的技术环境,在伦理学的范围内,比如在道德的、哲学的、历史的以及文学观念中重新被捕获,就不至于迷惑于乐观主义对医疗科技功能的期待,而置人文关怀于不顾,也不至于自陷于科技悲观主义者一味地反对科技的深层发展,如此之下,当能建立医疗科技与伦理之间有机与稳定的关系,而臻于一种理想境界,这个境界用个最普通的字眼,就是“善”。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出版,简直是给所有医疗从业者和对生命伦理议题感兴趣的普通人送上了一份厚礼。我是一名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的护士,日常工作中,法律问题和伦理困境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以往,我们更多是凭经验和院内的指导方针来处理,但总觉得不够系统,也担心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合规和合乎伦理。这套书,尤其是上册,系统地梳理了医疗纠纷中常见的法律条文和案例,让我对患者知情同意、医疗差错的处理、隐私保护等方面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下册关于生命伦理的部分,更是触及了医疗最前沿也最棘手的难题,比如临终关怀、辅助生殖技术、基因编辑等等。作者的论述逻辑严谨,引用的案例既有现实意义,又发人深省,很多时候读来让人不禁停下来思考。这本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罗列,更像是一次与法律和伦理专家的深度对话,引导我们去理解这些复杂议题背后的价值冲突和社会共识。它让我深刻体会到,在救死扶伤的同时,我们也肩负着维护法律尊严和尊重生命价值的重任。这套书,绝对是我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参考宝典。
评分我一直对医学的进步及其可能引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感到好奇,所以当我看到这套《医疗 法律与生命伦理(套装上下册)》时,立刻被它所涵盖的范围吸引了。作为一名对科学和人文都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我尝试着去理解那些在医学领域看似冰冷的技术背后,蕴含着怎样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价值判断。这本书上册关于医疗法律的探讨,虽然涉及一些专业术语,但作者的解释深入浅出,让我对医疗事故的界定、医患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了全新的认知。尤其是关于医疗信息的公开和患者的知情权,书中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患者的权益。而下册的生命伦理部分,更是让我大开眼界。从“安乐死”的争议到“试管婴儿”的伦理挑战,再到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设计婴儿”问题,作者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并引介了不同的伦理学派观点,使得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充满着复杂的权衡与考量。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生命、对医学、对社会责任的理解都有了更深层次的升华,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扇打开思想大门的钥匙。
评分我对生命科学和哲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总觉得在科技飞速发展的背后,一定隐藏着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伦理和社会议题。《医疗 法律与生命伦理(套装上下册)》这本书,恰好满足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欲。这本书的上册,从法律的视角切入,深入剖析了医疗领域中存在的种种风险和挑战。它并非仅仅是枯燥的法律条文的罗列,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案例,展现了法律在保障医患权益、规范医疗行为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医生的责任边界到患者的权利边界,都得到了细致的阐述。而下册则将目光投向了更深层次的生命伦理领域。书中对“生命”本身的定义、对“尊重生命”的多种解读,以及在科技干预下,如何界定人类的伦理底线,都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例如,关于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关于辅助生殖技术背后的伦理争议,以及关于“尊严死亡”的争论,都引发了我强烈的思考。这本书让我明白,医学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它是一次深刻的智识之旅,也让人对生命的奥秘和人类的未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评分我是一名律师,专门从事医疗领域的法律事务。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数量逐年攀升,涉及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复杂。在处理这些案件时,我常常感到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医疗实践中遇到的伦理困境,因为法律条文的适用往往与伦理原则紧密相连。这套《医疗 法律与生命伦理(套装上下册)》正好满足了我的这一需求。上册对于医疗法律的解读,非常系统和权威,不仅涵盖了医疗事故责任、医疗合同、侵权责任等核心法律问题,还对最新的医疗监管法规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的专业性毋庸置疑,许多案例的分析都非常到位,为我处理实际案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下册关于生命伦理的探讨,更是让我看到了法律与伦理交叉领域的广阔前景。关于生命权、生育权、死亡权等基本人权的界定,以及在科技进步面前如何进行伦理的边界探索,都写得鞭辟入里。尤其是一些关于新生儿伦理、遗传伦理的讨论,对我启发很大。这本书让我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医疗行为背后的法律和伦理逻辑,从而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也为推动医疗领域的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评分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我深知理论知识的扎实对未来职业生涯的重要性,而《医疗 法律与生命伦理(套装上下册)》这本书,无疑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坚实的知识体系。在学校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更多地关注医学本身的原理和技术,对于法律和伦理的探讨,往往是零散的、碎片化的。这套书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上册详细地介绍了医疗法律的基本概念和实践应用,从医患沟通的法律要求到医疗差错的法律责任,再到患者的权利保障,内容十分丰富。作者通过大量真实案例的解析,让我们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法律条文在实际医疗情境中的运用,避免了枯燥的理论说教。下册关于生命伦理的部分,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挑战的未来图景。从生殖伦理到临终关怀,再到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困境,书中涉及的议题都极具前瞻性,能够激发我们对医学发展方向和人文关怀的深入思考。这本书不仅是课本的补充,更是我们职业素养提升的指南,让我对未来成为一名负责任、有担当的医生充满了信心。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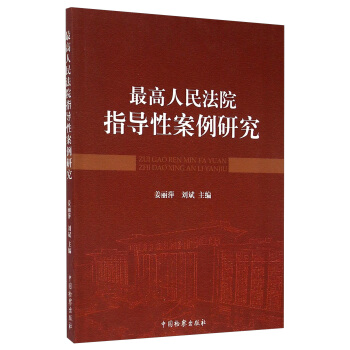




![刑法(总论)案例教程 [Casebook on Criminal Law(General Provisio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83871/58131c95N16c8b2e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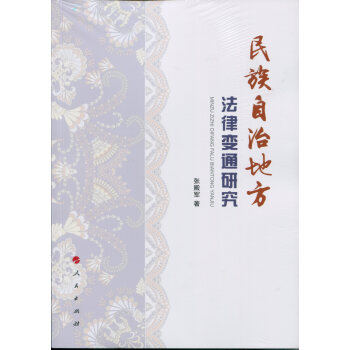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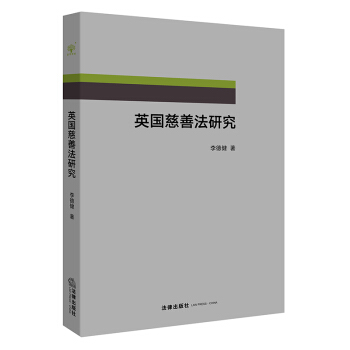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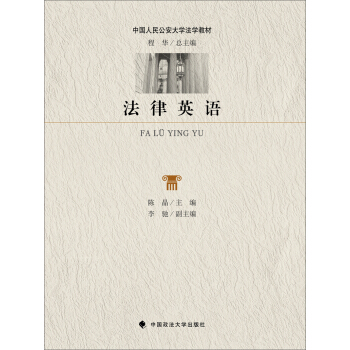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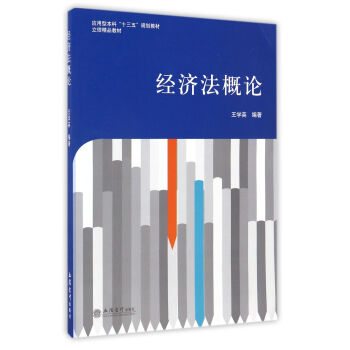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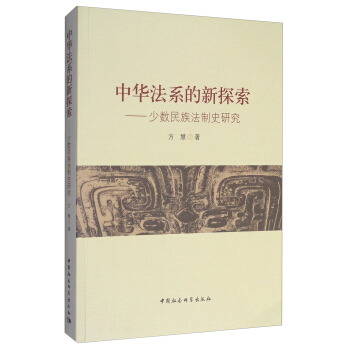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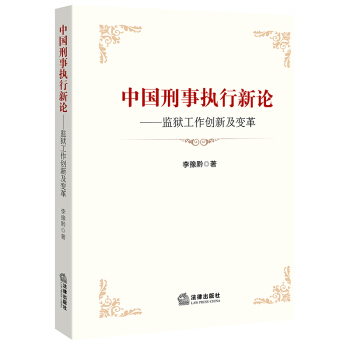
![中国知识产权审判实务与案例评析 [TRIAL PRACTICE AND CASE STUDI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43682/59f30c10N4e9f710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