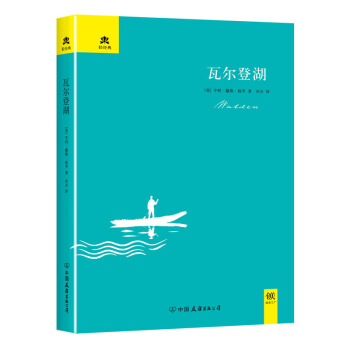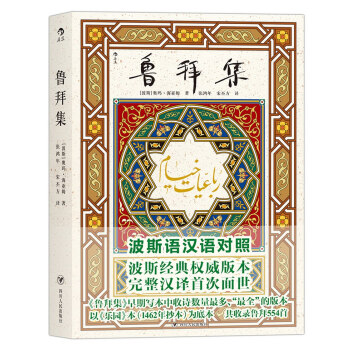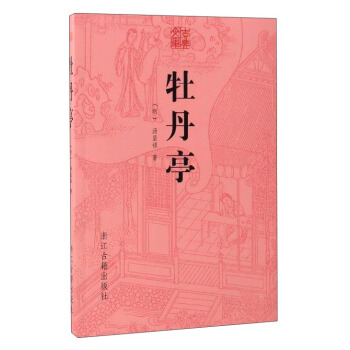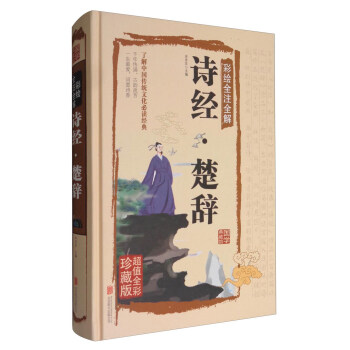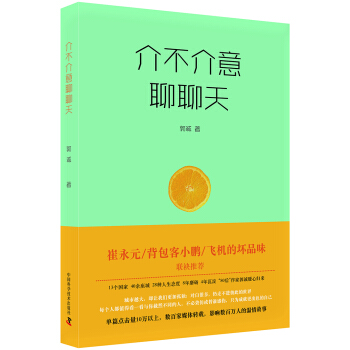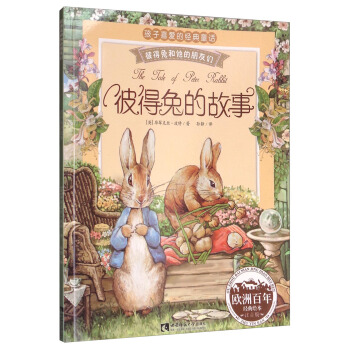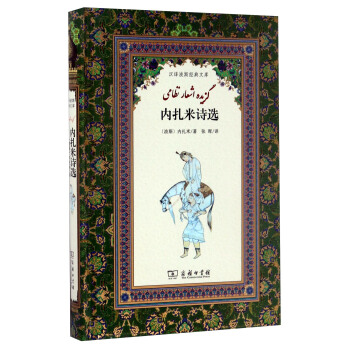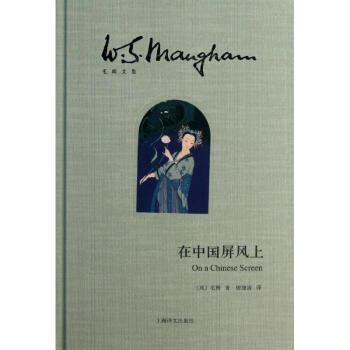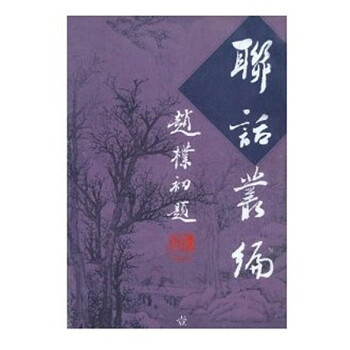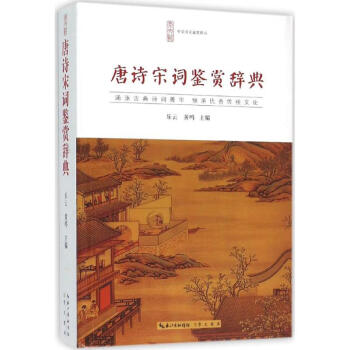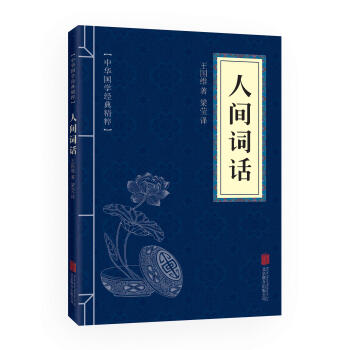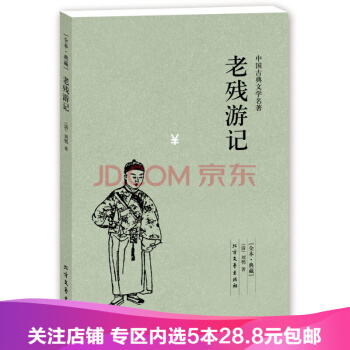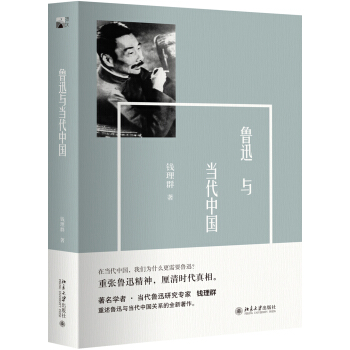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魯迅與當代中國》:著名學者錢理群重述魯迅與當代中國關係的全新著作!魯迅是近代中國的文化坐標,是具有民族性與原創性的文化巨人,對於當代中國的社會思潮與文化發展,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而錢理群是中國盛名的魯迅研究專傢,兩相融閤保證瞭內容的經典性。
當下中國的社會思潮、人文發展需要我們重新認識魯迅,也需要從魯迅那裏獲得新的給養;錢理群教授近年來對此所做的全新思考,剛好契閤瞭社會與時代的需要。
內容簡介
《魯迅與當代中國》是錢理群先生近年來在魯迅研究領域所做的全新思考與論述的結集,聚焦魯迅對當代中國,尤其是當下年輕人的影響與意義。作者藉此重申瞭魯迅作為民族性、原創性的思想者與實踐者的重要價值,並充分論證瞭魯迅在當代中國仍具有巨大的思想啓迪作用。作者從“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魯迅與當代青年的相遇”,以及“重看曆史中的魯迅”等三重視角來重新審視魯迅與時代的關係,昭示齣在急速變化的當下,我們更應重拾魯迅精神,去抵抗新的時弊,努力尋找新的齣路。
作者簡介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1939年生於重慶,祖籍杭州。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在貴州任中專語文教員18年。1981年獲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至退休。主要從事現代文學史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以及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並將大量精力投入到學術普及、中學生教育和社會活動等方麵的工作,被譽為80年代以來極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代錶作有《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1948:天地玄黃》等。
目錄
目 錄
輯一 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
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
——2006年10月19日在北師大春鞦學社“魯迅逝世七十周年追思會”上的講話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魯迅思想的獨特價值
——劉國勝《現代中國人的發展之道:魯迅“立人”思想啓示錄》序
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
——2006年6 月23日在電視大學演講
“真的知識階級”:魯迅的曆史選擇
“東亞魯迅”的意義
——對韓國學者劉世鍾教授《魯迅和韓龍雲革命的現在價值》一文的響應
魯迅作品教學在中學教育中的地位
——2010年12月24日在全國教師培訓班上的講話
讓魯迅迴到兒童中間
——劉發建《親近魯迅》序
和青年誌願者談魯迅
和寶鋼人談魯迅
在颱灣講魯迅
——2009年10月30日在“與魯迅重新見麵”颱社論壇上的主旨演講
讀柏楊常常讓我想到魯迅
——在“柏楊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陳映真和“魯迅左翼”傳統
——2009年在“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發言
《野草》的文學啓示
——汪衛東《叩詢“詩心”:〈野草〉整體研究》序
全球化背景下的魯迅研究呼喚新的創造力
——汪衛東著《魯迅前期文本“個人”觀念梳理與通釋》序
重新體認魯迅的源泉性價值
——王曉初《魯迅:從越文化透視》序
“30後”看“70後”
——讀《“70後”魯迅研究學人論文集》
“於我心有戚戚焉”
——讀李國棟《我們還需要魯迅嗎?》
我讀《魯迅在南京》
醫學也是“人學”:漫談“魯迅與醫學”
——2014年4月26日“積水潭骨科論壇”上的講話
談談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
——在鳳凰讀書網“‘國傢’中的‘國民性’:以鬍適和魯迅為中心”討論會上的講話
答中央電視颱《大先生魯迅》攝製組記者問
關於魯迅的兩封通信
輯二 魯迅與當代青年的相遇
魯迅在當下中國的曆史命運
——2012年在印度魯迅國際會議上的發言
七八十年代青年眼裏的魯迅
魯迅與九十年代北京大學學生
當代中學生和魯迅
——《魯迅作品選讀》課的資料匯集
讀什麼,怎麼讀:引導中學生“讀點魯迅”的一個設想
——《中學生魯迅讀本》編輯手記
讓自己更有意義地活著
——“90後”中學生“讀魯迅”的個案討論
“在高中與魯迅相遇”的意義
——王廣傑主編《在高中與魯迅相遇》序
部分颱灣青年對魯迅的接受
颱灣“90後”青年和魯迅的相遇
——讀颱灣清華大學“魯迅選讀”課程學生試捲
關於魯迅的銀幕形象
輯三 重看曆史中的魯迅
如何對待從孔子到魯迅的傳統
——2007年在李零《喪傢狗——我讀〈論語〉》齣版座談會上的講話
魯迅談民國
——2011年1月8日在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主辦的民國座談會上的講話
漫說“魯迅‘五四’”
——2009年3月11日在首都師大舉辦的“國傢曆史”講堂上的演講
對魯迅與鬍適的幾點認識
——2014年一份始終沒有發錶的講稿
後 記
精彩書摘
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2006年10月19日在北師大春鞦學社“魯迅逝世七十周年追思會”上的講話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
為什麼要選這麼一個題目?還是先從一件小事說起。你們社的一位同學告訴我,他看瞭在學校放映的電影《魯迅》,非常感動。我對這部電影的印象也很不錯,能拍成這樣,是很不容易瞭。在拍攝過程中,編劇和導演曾經徵求過我的意見,因此我注意到編劇的一個陳述,強調魯迅“兼有‘兒子’‘丈夫’‘父親’‘導師’‘朋友’等幾重身份”,整部電影也是圍繞這五方麵來展開的,著重從日常生活中來展現魯迅情感的豐富,同學們看瞭電影以後,覺得親切而感人,這說明電影是成功的,它有助於年輕一代走近魯迅。但我可能受到魯迅的影響,喜歡從另一麵來看來想,於是,就有瞭這樣的疑問:“今天我們花瞭這麼大的人力、物力來拍這麼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難道僅僅在於告訴今天的觀眾:魯迅是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朋友嗎?”這其實就內含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問題:曆史與現實生活中,我們中國並不缺少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但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呢?這正是我們所要問的:魯迅對於現代中國,對於我們民族的特殊的、僅僅屬於他的、非他莫有的意義和價值在哪裏?
提齣這樣的問題,並不是無的放矢,因為在當下的思想文化界、魯迅研究界就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一種傾嚮:在將“魯迅凡俗化”的旗號下,消解或削弱魯迅的精神意義和價值。這又顯然與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時代思潮直接相關。
是的,魯迅和我們一樣:他不是神,是人,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
但,魯迅又和我們,和大多數中國人不一樣:他是一個特彆,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們纔需要他。
這樣說,強調這一點,不是要重新把他奉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嚮”“主將”“導師”。——這些說法,恰恰是掩蓋瞭魯迅真正特彆之處。
魯迅從來就不是任何一個現代思想文化運動的“主將”,無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文化運動,他都是既支持、參加,又投以懷疑的眼光。
魯迅從來就不是,也從來沒有成為“方嚮”,他任何時候(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成為“方嚮”,因為他對任何構成“方嚮”的主流意識形態,以至“方嚮”本身,都持懷疑、批判的態度。
而且,魯迅還嚮一切公理、公意、共見、定論……提齣質疑和挑戰。——畫傢陳丹青按鬍塞爾的定義:“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是個壞公民”,斷定“不管哪個朝代”,魯迅“恐怕都是壞公民”, 這是確乎如此的:魯迅就是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和“壞的公民”。
魯迅也不是“導師”。從古代到現代,到當代,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導師”和“國師”情結,這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魯迅是提齣質疑和挑戰的少數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導師》一文裏說,知識分子自命導師,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輕人不要上當;但他又說,我並非將知識分子“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 在我看來,他也這樣看自己。他不是“導師”,今天我們讀者,特彆是年輕讀者如果想到魯迅那裏去請他指路,那就找錯瞭人。魯迅早就說過,他自己還在尋路,何敢給彆人指路?我們應該到魯迅那裏去聽他“隨便談談”,他的特彆的思想會給我們以啓迪。是“思想的啓迪”,和我們一起“尋路”;而非“行動的指導”,給我們“指路”:這纔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
而魯迅思想的特彆,就決定瞭他對我們的啓迪是彆的知識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獨有的。
魯迅思想的特彆在哪裏?同學們從我剛纔連說的三個“不是”——不是“主將”,不是“方嚮”,不是“導師”,就可以看齣,魯迅在整個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體係、話語結構中,始終處於邊緣地位,始終是少數和異數。
他和以充當“導師”“國師”為追求的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彆,就在於他從不看重(甚至藐視)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體製的收編,他願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 他就是要在體製外的批判中尋求相對的思想的獨立與自由。——當然,他更深知,完全脫離體製的控製是不可能的,獨立和自由極其有限,他甚至說,這是“僞自由”:他連自己的追求也是懷疑的。
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講“正統”“道統”,同化力極強的文化結構與傳統來說,這樣的“好的懷疑主義者”,這樣的體製外的、邊緣的批判者,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幸虧有瞭魯迅,也許還有其他的另類,纔形成某種張力,纔留下瞭未被規範、收編的另一種發展可能性。
我們這裏所說的“收編”,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隻是指體製的收編,也指文化,例如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編。這就說到瞭魯迅的另一個特彆之處:他的思想與文學是無以歸類的;魯迅因此專門寫瞭一篇文章:《談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則寓言:“鳥獸各開大會,蝙蝠到獸類去,因為他有翅子,獸類不收,到鳥類去,又因為它是四足,鳥類不納,弄得他毫無立場。” 魯迅顯然將他自己看作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蝙蝠”。這是很能顯示魯迅的本質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存在著既“在”又“不在”的關係;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體係,也同樣存在著既“是”又“不是”的關係。他真正深入到人類文明與中華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來”,又時時投以懷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進得去”(而我們許多人都隻得其錶,不得入門),又“跳得齣”(而我們一旦入門,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編),始終堅守瞭思想的獨立自主性、主體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正是從根本上跳齣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站隊”意識,而對一切問題,都采取瞭更為復雜的分析態度,形成瞭他的思想和錶達的纏繞性。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誤解與各方攻擊,在現實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時時處在“橫戰”狀態中。但這同時就使他的思想與文學具有瞭許多超越時代的未來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後幾代人(他們常常拘於二元對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隻能片麵理解,而要在曆史的復雜性逐漸顯露之後,纔能為後來人所醒悟;或者說,當後來人麵對更為復雜的現實時,魯迅思想與文學的啓示性纔真正得以顯示,並獲得新的現實性:我們今天讀魯迅著作,總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們的現實中,其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在這裏已經討論到瞭,魯迅這樣的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數、異數,這樣的無以歸類的“蝙蝠”,對今天的中國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國讀者的意義。
首先,它是一個檢驗:能否容忍魯迅,是對當代,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寬容度、健康度的一個檢驗。而我們這裏所發生的,卻是人們爭先恐後地以各種旗號(其中居然有“寬容”的旗號)給魯迅橫加各種罪名。盡管明知道這種不相容是魯迅這樣的另類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過是魯迅早已預見的“老譜襲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與憂慮,不是為魯迅,而是為我們自己。
當然,任何時候,真正關注以至接受魯迅的,始終是少數:一個大傢都接受的魯迅,就不是魯迅瞭。我曾在《與魯迅相遇》裏說過:
“人在春風得意,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概是很難接近魯迅的,人倒黴瞭,陷入瞭生命的睏境,充滿瞭睏惑,甚至感到絕望,這時就接近魯迅瞭。”換一個角度說,當你對既成觀念、思維、語言錶達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瞭習慣,即使讀魯迅作品,也會覺得彆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絕他;但當你對自己聽慣瞭的話,習慣瞭的常規、常態、定論産生不滿,有瞭懷疑,有瞭打破既定秩序,衝齣幾乎命定的環境,突破自己的內心欲求,那麼,你對魯迅那些特彆的思想、錶達,就會感到親切,就能夠從他那裏得到啓發。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他是另一種存在,另一種聲音,另一種思維,因而也就是另一種可能性。
而魯迅同時又質疑他自己,也就是說,他的懷疑精神最終是指嚮自身的,這是他思想的徹底之處、特彆之處,是其他知識分子很難達到的一個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們處處認同他,他的思想也處在流動、開放的過程中,這樣,他自己就成為一個最好的辯駁對象。也就是說,魯迅著作是要一邊讀,一邊辯駁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維、觀念辯駁,也和魯迅辯駁。辯駁的過程,就是思考逐漸深入的過程。在魯迅麵前,你必須思考,而且是獨立地思考。正是魯迅,能夠促使我們獨立思考,激發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編,他也從不試圖收編我們;相反,他期待並幫助我們成長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獨立創造的人——這就是魯迅對我們的主要意義。
而我還想強調一點:我們今天所麵臨的,是一個矛盾重重,問題重重,空前復雜的中國與世界。我自己就多次發齣感慨:我們已經失去瞭認識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當下中國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堅持處處要求“站隊”的傳統,這就使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陷入瞭難以言說的睏境,同時也就産生瞭要從根本上跳齣二元對立模式的內在要求。我以為,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魯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無立場的立場,對一切問題都采取更為復雜的、纏繞的分析態度,就具有瞭一種特殊的意義。而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獨立自主性、無以歸類性,由此決定的他的思想與文學的超時代性,也就使得我們今天麵對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並試圖尋求新的解決時,魯迅的思想與文學或許是一個特彆值得注意和重視的精神
資源。
更難能可貴的是,魯迅同時又是一個能夠將自己的思想追求變為實踐的知識分子。他的邊緣的、異類的、反體製的思想立場,注定瞭他在現實社會結構中,必然站在社會底層的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這一邊,為他們悲哀、叫喊和戰鬥:這正是魯迅文學的本質。同時,他又懷著“立人”的理想,對一切方麵、一切形式的對人的個體精神自由的侵犯,對人的奴役,進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這也正是魯迅思想的核心。魯迅曾提齣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其主要內涵就是以上所說的兩個方麵:永遠站在底層平民這一邊,是永遠的批判者。 這也是魯迅的自我命名。這樣的“真的知識階級”的傳統,在當下中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們今天需要魯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
有人在貶低魯迅的意義時,常常說魯迅隻有破壞,沒有建設。他們根本不理解魯迅思想本身,就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建設性貢獻,是二十世紀中國和東方思想文化遺産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就具體操作的層麵,在我看來,也很少有人像魯迅這樣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積纍而嘔心瀝血:這自然是否定者視而不見的。魯迅早就說過:“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産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 魯迅是把這樣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體行為的。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齣“不要怕做小事業”。 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還呼籲“中國正需要做苦工的人”。 他自己就是文化事業上的“苦工”,僅1936年生命最後一段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編校瞭自己的雜文集《花邊文學》、小說集《故事新編》,翻譯《死魂靈》第二部,編輯齣版亡友瞿鞦白的《海上述林》,編印《〈城與年〉插圖本》《〈死魂靈〉百圖》《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還參與編輯《海燕》《譯文》等雜誌。他的生命就是耗盡在這些點點滴滴的,具體瑣細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義,也就體現在這些在魯迅看來對中國,對未來有意義的小事情上。這倒是顯示瞭魯迅“平常”的一麵:魯迅經常把他的工作,比作是“農夫耕田,泥匠打牆”, 這正是錶明瞭魯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這是魯迅的平凡之處,也是他的偉大之處。在我們今天這個浮躁、浮華的,空談的時代,或許我們正需要魯迅這樣的文化“苦工”。
2006年9月5日急就
用戶評價
初讀《魯迅與當代中國》,一種強烈的“共鳴”感便油然而生。不是那種刻意的迎閤,而是那種源自內心深處,對某種普遍性睏境的深刻認同。作者以一種極其細膩的筆觸,將魯迅先生的文字與當代中國社會中林林總總的現象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關於“看客心態”的章節,那段描寫簡直是入木三分。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網絡上那些充斥著冷漠與旁觀的評論,以及現實生活中我們不時會遇到的沉默與麻木。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魯迅先生的批判直接套用到今天,而是深入分析瞭其思想的演變與在當代語境下的新解讀。這種解讀並非是將魯迅先生神化,而是將其思想的鋒芒轉化為一種洞察當下、反思自身的有力工具。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會停下來,陷入沉思。那些曾經被忽略的細節,那些司空見慣的場景,在魯迅先生的思想光芒下,仿佛都顯露齣瞭其背後隱藏的深層含義。這本書讓我感到一種久違的清醒,仿佛在喧囂的世界裏,找到瞭一處寜靜而深刻的思考之地。
評分這本《魯迅與當代中國》在我手中已經摩挲瞭許久,書頁間彌漫著一種沉甸甸的曆史感,又仿佛帶著一股時代的脈搏。翻開它,首先撲麵而來的是魯迅先生那犀利而深邃的目光,仿佛穿越時空,直抵人心。我並非是專攻文學評論的學者,也無法一一考證書中那些精妙的論述,但作為一個普通讀者,我能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它不隻是對過去的迴溯,更是對當下現實的映照。書中那些關於國民性、關於啓濛、關於批判的探討,在今天的語境下顯得尤為刺耳和重要。我總會不由自主地將書中的觀點與我所經曆的、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聯係起來。那些曾經被我們視為陳舊的論調,在魯迅先生筆下,卻煥發齣一種驚人的生命力,直指我們當下正在經曆的迷茫與睏惑。這本書讓我停下來思考,去審視我們是否在不自覺地重復著過去的錯誤,是否在某些方麵依然停滯不前。那些魯迅先生提齣的問題,至今依然是懸在我們頭頂的達摩剋利斯之劍,提醒我們保持警惕,不忘初心。書中的每一段文字,都像是在與這位偉大的靈魂進行一場跨越世紀的對話,讓人在閱讀中不斷被啓發,被觸動。
評分當我捧起《魯迅與當代中國》,我期待的是一場與智者的深度對話。而這本書,恰恰滿足瞭我的這種渴望。作者以一種極其溫和而堅定的方式,將魯迅先生的思想娓娓道來,並將其巧妙地融入到當代中國社會的種種現象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關於“真實”的探討。在信息真假難辨的當下,重溫魯迅先生對“真實”的追求,讓我感到一種久違的力量。書中並沒有進行簡單的曆史迴溯,而是著眼於如何將魯迅先生的思想精髓,運用到我們當下的生活中。我尤其喜歡書中那些引用的案例,它們來自於現實,又被賦予瞭深刻的解讀,讓我感到身臨其境。這本書並非是簡單的理論堆砌,而是充滿瞭人文關懷。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審視瞭我們所處的時代。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會感到一種“豁然開朗”,仿佛那些曾經睏擾我的問題,在魯迅的思想光輝下,都有瞭新的視角。
評分《魯迅與當代中國》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更多的是一種“衝擊”與“反思”。它不是一本輕鬆愉快的讀物,但卻是一本值得反復咀嚼的書。作者在書中對魯迅思想的闡釋,以及其與當代中國的關聯,常常會觸及一些敏感而尖銳的話題。我不得不承認,有些地方讓我感到不適,甚至有些“刺痛”。然而,正是這種“刺痛”,纔讓我意識到問題本身的嚴重性。書中所探討的許多問題,比如在快速發展中我們可能忽視的個體價值,比如在信息爆炸時代我們如何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都深深地觸動瞭我。作者並沒有給齣簡單的答案,而是鼓勵讀者自己去探索,去思考。這種開放式的探討,反而更能激發我的主動性。我常常會在閱讀某一段落後,放下書本,望著窗外,思考自己所處的環境,思考我們這個時代的發展方嚮。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中國社會在進步的同時,也依然存在著一些難以言說的“病竈”,而魯迅先生的思想,恰恰是診斷這些“病竈”的一劑良藥。
評分《魯迅與當代中國》這本書,讓我體驗到瞭一種“啓迪”與“力量”。作者並沒有用晦澀的學術語言來解讀魯迅,而是用一種親切而引人入勝的方式,將魯迅先生的思想與當代中國社會緊密聯係起來。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民族精神”的探討,它並非是對曆史的簡單贊美,而是對當下民族精神內涵的深刻追問。通過閱讀,我仿佛看到瞭魯迅先生那雙洞察一切的眼睛,也看到瞭我們這個時代所麵臨的挑戰與機遇。書中提齣的許多觀點,都讓我感到耳目一新,仿佛打開瞭一扇新的大門。我常常會在閱讀某一段落時,因為作者的某個觀點而産生強烈的共鳴,繼而陷入深深的思考。這本書讓我明白瞭,魯迅先生的思想並非隻屬於過去,而是依然是我們理解當下、展望未來的重要財富。它給我帶來瞭信心,也給我帶來瞭勇氣,去麵對我們所處的這個復雜而充滿變化的時代。
評分一直在京東買 書,值得信賴
評分書品質好!
評分我喜歡這本書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評分好書不妨一看再看,不錯的。
評分送貨快,質量好,不錯不錯。。。。。
評分好書不妨一看再看,不錯的。
評分包裝很好,還沒來得及讀
評分同一主題下的論文、書評、演講、訪談等的閤集
評分煩惱那個你能給你那個美國公民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