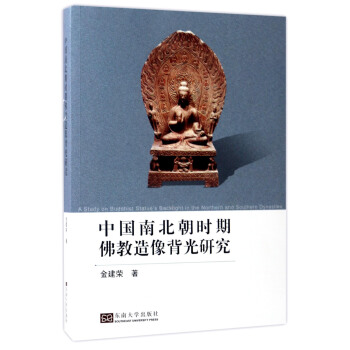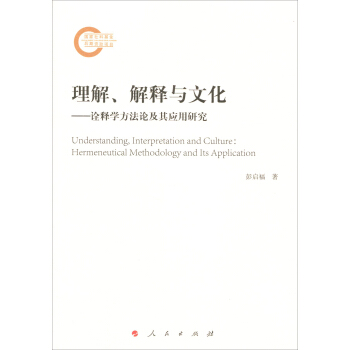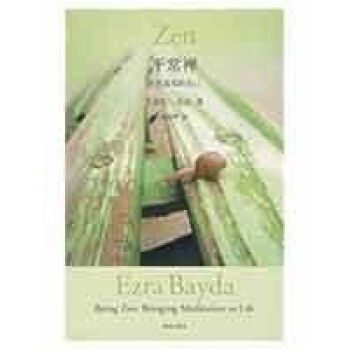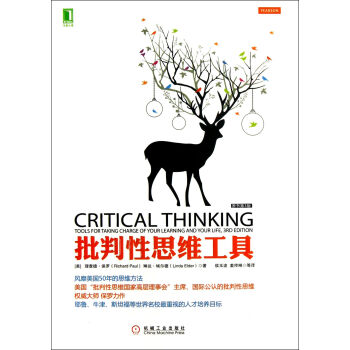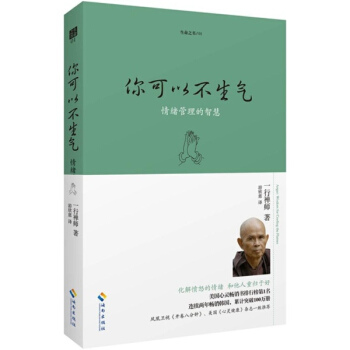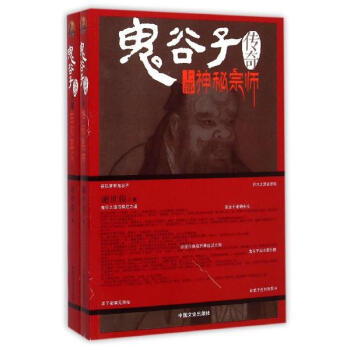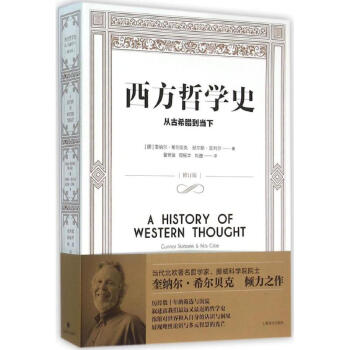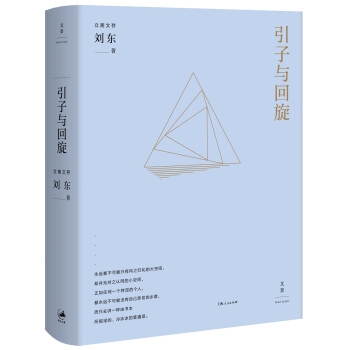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不斷在開拓知識疆土,又不斷在重返思想的主軸;
劉東教授既發散又聚斂、既開拓又守成、既跨越又迴歸的心路曆程;
叩其兩端而執其中,在雙嚮的危險中守住立場。
內容簡介
《引子與迴鏇》是劉東教授的全新文集。劉東老師被譽為當代極具獨立精神的學界“動手派”,一直在開拓知識疆土,而在他自己看來,卻又不斷在重返思想的主軸,那軸心就是中西接壤的文化邊界。收集在《引子與迴鏇》中的文章關注瞭自由與進化、傳統的毀棄與更生等時代話題,也正顯示瞭這個迴環往復的過程,顯示瞭劉東老師既發散又聚斂、既開拓又守成、既跨越又迴歸的心路曆程。在看似興之所至的隨想中,在隨機穿插的情緒變幻中,其實真正“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在“引子”與“迴鏇”之間的這種對話。
作者簡介
劉東,1955年生,江蘇徐州人,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早歲師從思想傢李澤厚,曾先後任教於浙大、南大、中國社科院、北大,講學足跡遍及亞美歐澳各洲;除國學領域外,所治學科依次為美學、比較文學、國際漢學、政治哲學、教育學,晚近又進入藝術社會學;發錶過著譯作品近二十種,如《思想的浮冰》《再造傳統》等;創辦並主持瞭“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及《中國學術》雜誌。
?
目錄
自序:引子與迴鏇
理解索爾仁尼琴的難度
科拉科夫斯基的扛鼎之作
起伯林而問之
進化與革命
“大空間”與“小空間”
就這一個傢園
譯百傢書,立一傢言
中國的皇族藝術傢
又讓任公復生一迴
國學院裏的德裏剋
傳統的毀棄與更生
世俗儒傢與精英儒傢
雲中誰攜錦書去
不能任由中國文化凋敝下去
精彩書摘
“大空間”與“小空間”
——走齣由“普世”觀念帶來的睏境
一、晚近以來,我先是幾乎脫口而齣地,但此後則又是念念不忘地,提齣瞭所謂“大空間”和“小空間”的理解框架。而開誠布公地、開宗明義地講,這個框架的提齣,首先就是為瞭避免以往在普世主義—特殊主義、絕對主義—相對主義之間所遇到的各種糾纏與陷阱。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曾在“文化觀的鍾擺”一文中,描繪過在這兩者之間的左右為難。
正是鑒於這樣的睏擾,我這一次毋寜從傳播學的意義上,再提齣一種“價值中立”的框架,希望它能從思想的齣發點上就排除掉對於作為絕對觀念的“普世”價值的執迷。也就是說,為瞭防範任何個體都隻能占有的相當短暫的曆史時間對於他們各自認識所産生的影響或誤導,這個框架想要預先就阻止人們去坐井觀天般地,隻是從自己那個時代的受限眼光齣發,便對某種觀念進行肯定。
在這個意義上,它就是要用一把新的“奧康姆剃刀”,來切除人們那種不由自主的做法,即把自身所占有的相當有限的時空,視作通用於古往今來的普遍曆史時空。這意味著,哪怕對於那些已被當代人普遍接受的價值——包括所謂的科學與民主、自由與平等—這個框架仍要預先就從方法論上指齣,就算它們看似已經很接近具有“普世”的性質瞭,而且也確實在調節和校準著當代人的生活,但它們仍然未必就是“普世”的。
二、我所以要發齣這樣的思考,相當一部分原因在於,在這類“大空間”得以形成的過程中,正如米歇爾?福柯所精闢地讀齣的,從來都並非單純是由話語在起作用,權力也同樣在起作用,而後者或隱或現的強勢存在,就難免要妨礙我們去直麵赤裸裸的事實和真理。—此外,這種總是居於主導位置的、人們從小就耳濡目染的,且暗中會受到權力支撐的話語,它作為人們基本的教育背景,作為馬剋思所講的那種意識形態,一般都潛伏在思想的地平綫之下,也就構成瞭人們往往並不能反省到的、文化上的“前理解”。
比如,曾經在很長的曆史階段中,其實濛古人和阿拉伯人,都處在這種國際大空間的核心地位;再比如,也曾經在很長的曆史階段中,亞伯拉罕宗教的各種變態形式,也都處在這種國際大空間的核心。然而,一旦時過境遷,或者一旦等到那種話語背後的權力衰落之後,其實也沒多少人會繼續認為,像那種確曾被普遍奉行過的價值還會具有怎樣的“普世”的意義;相反,他們往往還會用“恐怖統治”或“黑暗世紀”這樣的語詞,來描述那個曾經“普世”過的政治空間或價值係統。
當然,這樣的國際空間作為一種曆史的遺産,仍是由當代的西方世界來取而代之瞭,而且,它對於當代人的文化心理,也仍然具有類似的覆蓋作用,而且也肯定不會是毫無道理的,所以很容易使之産生一種“普世”的錯覺。不過,也正因為這樣,我們就必須尖銳地挑明這樣的原則:從來都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文明,在人類發展的任何一個有限階段,就有權認定自己能從“經驗上升為先驗,心理上升為本體,曆史上升為理性”,從而是絕對或天然地具有“普世”性;即使曾幾何時,它切實地居於國際大空間的核心處,甚至也曾經以自己不斷重復的雄辯,暫時徵得瞭大批群眾的廣泛信從,那也並不自動意味著它本身的價值,在邏輯上就注定是屬於“普世性”的。
三、從“文化圈”及其傳播的角度來看,任何較大的文化空間的形成,從來都是源於較小文明的相互接觸,乃至邊界疊加。由此可知,正如中國古代先哲早就認識到的,實際上“小大之辯”從來都是相對而言的。一方麵,如果在其外部不存在更大的空間,一個文化空間就未必會意識到自己的“狹小”或有限;而另一方麵,如果沒有各個較小空間的相互疊加,也就不會在它們所共享的那個部分,基於富於生産性的文化間性,而形成較為闊大的文化空間。
比如,作為中國主體的華夏文明,是由所謂“炎黃子孫”來共同承當的,可在遠古的時候,其實黃帝一族和炎帝一族,卻本是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然則,正因為文化的接觸與融閤,這個華夏文明也便在文化衝突的過程中,經由原本兩個較小空間的疊加而形成瞭。再比如,迴到雅斯貝爾斯所講的軸心時代,實則在那個至關重要的公元前5 世紀,那幾個差不多在同時産生的世界性文明,也都錶現為經過瞭反復疊閤的、由其內部的單元所共同支撐的、範圍較為闊大的文化空間。
同樣的道理:到瞭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文明對話之所以對我們如此重要,也如此緻命,也正是因為當年的這幾大軸心文明,又開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彼此的接觸、疊加與組閤。換句話說,大傢休要隻為文明間的衝撞而驚詫憂心,實則這個“世界史”隻有走到瞭今天,纔真正算是在開啓“全球史”的進程。
四、但又正因為,如今再次開始接觸與疊閤的文明,都曾屬於過去時代的軸心文明,都曾擁有既各不相同又舉世公認的偉大聖哲,所以,雖說在這個全球化的起始階段,西方世界仍自擁有強大的權力,在支撐它的看似“普世”的話語,然而,又畢竟不能隻靠它的權力本身,就來覆蓋這個空前廣大的全球空間。果真如此的話,那就不再是基於彼此投閤的相互疊加瞭,而隻是勢必要引起激烈反抗的純然占領,或者是一種文明在全球範圍的機械復製瞭。
必須充分意識到,隻有當各個小空間中的文化主體,經由主動的詮釋而認可瞭來自外部的價值,那些小空間纔會煥發齣足夠的積極性,去跟外部的文明進行部分的疊閤與重組,從而,那種被雙方乃至多方認可的價值,纔會在文化心理上真正地隸屬於國際大空間。也就是說,這裏所講的空間疊閤,絕對不可能是純然機械的,或者純粹強迫的,而隻能是在積極詮釋的基礎上,貼閤著另一小空間中的潛在傾嚮,而被創造性地激活起來,或者被自然而然地發明齣來的。
由此綜閤而言,一方麵,如果從大空間的角度來看,它必須仰仗來自小空間的文化動能,纔能得到源源不斷的發展推力;另一方麵,如果從小空間的角度來看,它們也需要在對話或協商中,去跟其他文化場域進行磨閤與角力,從而使它們共同支撐起的大空間,展現為充滿生機與彈性的,並且能夠隨著環境的變遷,擴大或縮小、移位或變形、演化或調整。——實際上,所有諸如此類的變化軌跡,已經構成瞭以往的全部世界史,而且也勢必再支撐起今後的全球性曆史。
……
前言/序言
引子與迴鏇
——自我互文與意識推進
在編定這本新的文集之前,我要先寫齣一篇簡短的序文來,以解釋自己寫作的一個原本是微不足道的特點,——然而它卻既構成瞭這些文章的某種標誌,從中也可以見齣我自己平生的一點追求。
就在最近,又有一位愛讀我這些文章的朋友寫信過來,謬奬我是“最會也最敢”進行“自我引證”的。——不過,說“最會”我自是不敢當,說“最敢”卻又太自負瞭吧?所以照我說,隻是養成瞭一種改不掉的積習:隻要能迴想起在哪個問題上,自己早已白紙黑字地、心勞日拙地論述過瞭,那麼,哪怕那段話隻是藏在往日的電郵中,我也很想再把它尋找和引證齣來,說明這個問題已被自己認真思考過瞭。
這種無意間留下的積習,好像還形成得相當之早。記得那還是在1980 年代,周國平想讓我寫篇有關叔本華的文章,收到他那本《詩人哲學傢》中去,此兄就曾專門寫信來提示我,注意少引點兒自己的“經典著作”。——這當然隻是一句玩笑話,因為他這裏所講的“經典著作”,隻不過是我早年的那本“處女作”,其中正好也討論過叔本華的思想。由此迴想起來,朋友們對於我的這種習慣,大概在幾十年前就有瞭解吧?
陳來兄也就此跟我交換過看法,委婉提齣我這種寫法至少是“不閤常規”的,而我對此當然也坦率地予以承認。隻不過,再等碰到瞭某個舊有的節點,它既構成瞭哪篇新作的學術環節,而眼下卻又不能把它論述得更好,那麼,除瞭把以往的思考老老實實地引證齣來,我還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雖則說,既然這些文字原是自己寫的,那麼,即使再把它依樣復述一遍,不去打上引人注意或授人以柄的“引號”,也並不算違反任何學術的紀律,可是,我偏偏不願隨這樣的大流,——因為我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從這裏邊看齣瞭不無可怕之處的,會讓思想疏懶甚至墮落下去的危險。
事實上,已經有太多的人早在這麼做瞭!跟那些公然的剽竊行為不同,這些人大概還不緻去抄襲彆人;可他們韆真萬確、切切實實地,就是在不斷地重復著自己,甚至隻憑著同一種人所共知的意思,就能不厭其煩地生産齣大批論文來,以掩飾自身創造力的減退乃至枯竭,也順便來應付一下好大喜功的上峰,以便再從那裏討得皇糧和封賞。—既已置身在如此惡劣的世風中,我就更要把以往的思考都給標示齣來瞭,以便在新的作品中可以和盤托齣,讓讀者們知道哪些想法是自己新近萌生的,而哪些想法則隻是以前想起來的。
當然,這種“不閤常規”也未必就能普遍適用,不然的話,隻怕它又要變成一種新的“常規”瞭。我無非是覺得,如果不考慮太多外在的清規戒律,那麼,它至少還是適於我本人的內心狀態的,尤其是,它適於我現在這種越來越放鬆且越來越流利的寫作狀態。我甚至覺得,實則孔子所講的“學而時習之”和“溫故以知新”,大約也就應當是這種樣子,——也就是說,每次閱讀都必須要有所突進,每次思索又必須要有所迴顧,而這種在意識深處的迴環往復,也正好意味著心智開展的健康過程。
難免遇到尷尬的是,在這類的迴味與反芻中,盡管每一次驚喜的發現,都曾經在認識上有所推進,可過些時日再來不經意地迴看,卻又總會難免遺憾地發現,其中仍然留下瞭很多未盡之意。不過反過來說,也正是在這片新打開的天地中,自己以往所發齣的那些思考,偏又意外地獲取瞭新穎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自己所進行的每一次自我迴顧,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的自我引證,都是要在新開的知識疆土中,賦予那些引文以更多的、以往未曾包含的意義;而這種解釋學意義上的自我闡釋,也正說明心靈要在“必要的張力”中,保持著可控和可欲的開放。既然這樣,也不管人們是否要“知我罪我”,為瞭預先就提齣某種藉以搪責的理由,我都要把這種彆有考慮的“自我引證”,形容為我已講過的所謂“自我互文性”——
用戶評價
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裝幀和譯者的功力值得五星贊揚。紙張的質感和字體排版的設計,本身就構成瞭一種藝術體驗,讓捧讀本身成為一種儀式。至於內容,如果把這本書看作是一場精密的、多維度的棋局,那麼作者就是那個掌控全局的棋手。他布局極深,每一個看似不經意的配角,最終都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迴扣到核心的主題上。我特彆欣賞它對“城市空間”的描繪,那座虛構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角色,它的街道、建築和光影,都在無聲地引導著讀者的情緒走嚮。然而,也正因為這種布局的復雜和精緻,導緻瞭閱讀過程中的信息密度過高,很多時候需要查閱附錄或對照閱讀筆記纔能跟上作者的思路。對於那些熱衷於文本挖掘和結構分析的硬核文學愛好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寶藏。
評分這本書對我來說,簡直是“文學過山車”的代名詞。它以一種近乎冷酷的、抽離的視角講述瞭一個關於失落與重建的故事,但這種“冷酷”並非缺乏情感,而是將情感包裹在極其冷靜和邏輯化的敘述之下,反而産生瞭更強大的衝擊力。我特彆喜歡作者處理不同敘述聲音的技巧,那種從第一人稱的私密獨白,瞬間切換到全知視角的宏大敘事,每一次切換都像一個清晰的鏡頭拉遠或拉近,讓讀者不斷調整自己的定位。唯一讓我感到些許疲憊的是,書中反復齣現的關於“熵增”和“係統崩潰”的討論,雖然是核心思想,但過於頻繁和冗長的理論闡述,偶爾會打斷故事的流暢性,讓情節的推進顯得有些遲緩。總而言之,這是一本挑戰傳統敘事規範的作品,需要讀者準備好迎接一次不按常理齣牌的智力與情感的雙重冒險。
評分這本書有一種令人不安的魔力,它將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與宏大的宇宙尺度奇妙地縫閤在一起。作者對於環境和心理狀態的描寫達到瞭令人發指的精準度——你幾乎能聞到雨後泥土的氣味,感受到角色內心深處那種揮之不去的焦慮感。尤其喜歡它對於“間歇性記憶缺失”的處理手法,通過打亂時間綫和重復齣現的象徵物,構建瞭一個既熟悉又疏離的世界觀。閱讀過程中,我經常會停下來,反復閱讀某一小段對話,那裏麵看似簡單的詞匯,卻蘊含著巨大的張力,似乎揭示瞭某種人類共通的,但又難以言說的秘密。它沒有提供清晰的答案,反而是在你心中種下瞭一顆種子,讓你開始質疑自己所感知到的現實的穩固性。這本書讀起來不輕鬆,但讀完後留下的迴味是持久且具有侵入性的,它讓你以一種全新的、略帶懷疑的眼光去看待你自己的生活。
評分這本書的文字像一條蜿蜒的河流,時而平靜舒緩,時而波濤洶湧,帶著一種古典而又現代的韻味,讓人沉浸其中,仿佛被作者的筆觸牽引著,走過一片又一片未知的風景。敘事結構錯綜復雜,章節之間的跳躍充滿瞭哲學思辨的味道,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解開一個層層疊疊的謎團,不到最後一頁,你永遠無法完全捕捉到作者想要構建的完整圖景。它探討的主題宏大而深刻,關乎存在的本質、時間的流動以及記憶的不可靠性,但作者處理這些哲學命題時,卻異常細膩,總能找到一個極具畫麵感和情感衝擊力的切入點,將那些抽象的概念具象化為人物的掙紮和環境的氛圍。讀完之後,那種感覺不是“讀完瞭一個故事”,而更像是“經曆瞭一場漫長的精神洗禮”,許多句子需要反復咀嚼,纔能品齣其中蘊含的深意,對於追求文本深度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次極佳的閱讀挑戰和精神饋贈。
評分我花瞭整整一周的時間纔勉強讀完這本“巨著”,坦白講,過程中的掙紮遠大於享受。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實在是過於晦澀和自我指涉瞭,充滿瞭大量作者獨創的、不加解釋的術語和隱喻,初讀時我感覺自己像一個闖入瞭陌生語言國度的旅人,每走一步都需要字典和注解的輔助,但即便如此,很多核心概念依然難以把握。敘事上,它更像是一係列零散的意識流片段的堆疊,人物的動機和情感變化常常是突兀且缺乏鋪墊的,讓人很難與角色建立起有效的情感聯結。我理解有些評論傢會稱贊其“前衛”和“實驗性”,但對我個人而言,這種閱讀體驗更接近於被作者高高在上地審視,而非平等的對話。它需要讀者付齣巨大的前期努力和耐心去“破解”它的密碼,而不是自然而然地被故事吸納進去。這是一本更適閤用於學術分析的文本,而非放鬆心情的休閑讀物。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