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手 [LA CHIAVE A STELLA]](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33526/59e73649N632a5c10.jpg)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扳手》獲意大利項斯特雷加文學,是萊維文學成就的突齣展現。★普裏莫·萊維重返日常生活的主題,詮釋另一種理想人生。
★普裏莫·萊維是意大利國寶級作傢,奧斯維辛極為重要的記錄者和見證者。
★卡爾維諾評價萊維是:我們時代極重要、極有天賦的作者之一。 索爾·貝婁說:“在普裏莫·萊維的作品中,沒有一句話是多餘的,每個字都不可或缺。”萊維的思想和文學成就,已經獲得西方學者、作傢、媒體普遍的贊譽和推崇。
內容簡介
獲意大利項斯特雷加文學奬,是奧斯維辛見證者和記錄者普裏莫·萊維文學成就的突齣展現。他在本書中重返日常生活的主題,詮釋另一種理想人生在這本詼諧的小說中,萊維將目光聚焦在普通人的生命經驗上。體格健壯、經曆豐富的裝配工利貝蒂諾·福索內嚮敘述者——一位作傢、化學傢——分享瞭一係列令人著迷的人生故事,他熱愛工作、享受勞動,以職業為冒險,從平凡中獲得瞭自由。這些故事串聯起一個又一個通常被忽視的瞬間,令人時而會心一笑,時而黯然神傷,為人類的智慧與局限,也為生命的偉大和渺小。
“萊維作品”係列還包括《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他人的行當》《這就是奧斯維辛:1945—1986年的證據》《不定的時刻:萊維詩選》《休戰》《若非此時,何時?》《緩刑時刻》《記憶之聲:萊維訪談錄 1961—1987》《與你們交談的我:萊維、泰西奧談話錄》等。
作者簡介
普裏莫·萊維(Primo Levi)意大利猶太人,作傢,化學傢,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
1919年,萊維齣生於意大利都靈;1944年,他因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被捕,後被遣送至集中營。戰爭結束後,他迴到故鄉都靈生活。在此後的人生中,他從事工業化學這一行當30年,同時作為一位作傢,寫作瞭“奧斯維辛三部麯”(《這是不是個人》《休戰》《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以及其他基於其化學傢身份和大屠殺幸存者經曆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作品。1987年4月11日,萊維從他齣生的房子墜落身亡。
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索爾·貝婁曾評價說:“在普裏莫·萊維的作品中,沒有一句話是多餘的,每個字都不可或缺。”
精彩書評
我們時代極重要、極富有天賦的作傢之一。——卡爾維諾
在普裏莫·萊維的作品中,沒有一句話是多餘的,每個字都不可或缺。
——索爾·貝婁
歐洲極高尚、不可或缺的作傢之一。
——《洛杉磯時報》
如果一位化學傢可以寫齣這樣的作品,上帝幫幫那些作傢們吧。
——《衛報》
普裏莫·萊維是偉大的大屠殺迴憶錄作傢……也是我們時代文字傑齣、優雅而動人的作傢
之一。
——《新共和》
他將歐洲猶太人的兩極生活放在一起作對比,萊維先生的小說形成瞭一種無可抵擋的、史
詩般的氣質,這成就瞭他*好的作品。萊維又一次呈現瞭我們在他所有作品中都能找到的
特點——對全人類的悲憫。
——《紐約時報》
一位傑齣的作傢已經齣現,而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他的正直、他的尊嚴、他的人性,以及他那嚴格的標準。
——H·斯圖爾特·休斯《紐約時報》
目錄
“蓄謀”與世隔絕
幫手
大膽的姑娘
提瑞西阿斯
離岸
打銅
酒和水
橋
沒有時間觀念
錐齒輪
鳳尾魚一
姨媽
鳳尾魚二
精彩書摘
“蓄謀”“不,不,我不能什麼都告訴你。我要麼跟你說說那些國傢,要麼跟你說說我經曆瞭什麼事。但對於你,我還是告訴你我經曆瞭什麼事吧,因為這是個挺好的故事。然後你要是真想寫齣來,就花點兒心思,好好打磨、修邊兒,把它敲錘成形,這樣你就能寫齣一個好故事。雖然我年紀比你小,但我經曆過很多,有很多故事。或許你能猜到那些國傢的事,那也沒所謂。但我要是跟你說瞭那些地方在哪,我就會惹上麻煩:那裏的人雖然好,但他們也有點兒難搞。”
我跟福索內纔認識兩三個晚上。我們是在食堂裏碰巧遇上的,那是我們所在的偏遠工廠專為外賓設的餐廳,我作為一名塗料化學師,因為工作需要到瞭那裏。那兒唯有我們兩個是意大利人。他纔來三個月,但他曾因為其他事在那一帶待過,所以他對當地語言掌握得不錯,此外,他本來還會四五種語言,雖然說話時語病頗多,但很流利。他約莫三十五歲,高而瘦,近乎禿頂,皮膚曬得黝黑,鬍子總是颳得很乾淨。他麵相嚴肅,錶情相當凝重,沒什麼變化。他講故事不是特彆擅長。相反,他的語調變化不多,時常輕描淡寫,頗為簡略,仿佛擔心人傢覺得他誇張。但他也時常放任自己,於是,不知不覺地,他真的有些誇張。他詞匯量有限,又頻頻用那些爛大街的詞句錶達自己,但他自己似乎覺得這些錶達新穎又機智。要是聽故事的人沒有笑容,福索內就會把那些詞句重說一遍,就像在跟傻子說話似的。
“……就像我跟你說的,我會在這個行當裏,從一個工地到另一個工地,到世界各地的各種工廠和港口,並不是偶然: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所有的小孩都夢想進入叢林、深入沙漠、遊曆馬來亞,我也有這樣的夢想,不過我想要自己的夢想能夠實現;否則,它們就會像某種你終生患有的病痛或某場手術留下的傷疤,一旦天氣陰潮,又會復發作痛。擺在我麵前有兩條路:我可以一直等到自己富瞭,然後做觀光客;我也可以做裝配工。所以我就成瞭裝配工。當然還有其他的路可走:你或許會說,可以去做走私犯,或者諸如此類的行當。但這些不適閤我。我想遊曆異國,但我也一樣是個普通人。到如今,我已經有瞭一種沒法安分的性子,一旦被迫安定下來,我就會害病。要是你問的話,我會說,這世界很美麗,因為它總是不同。”
他麵無錶情地看瞭我一會兒,眼睛無神,卻稍有異樣,接著又耐心地說瞭一遍:“一個人待在傢裏,或許平靜安穩,但這就像吮吸一個鐵做的乳頭。這世界很美麗,因為它總是不同。所以,就像我說的,我去瞭許許多多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奇遇,但最離奇的故事還要算過去這一年在那個國傢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不能告訴你它在哪兒,但我可以告訴你,它離這兒很遠,離我們的國傢也很遠,我們在挨凍,但那裏十二個月裏九個月都熱得跟地獄似的,剩下三個月會颳風。在那兒的時候我在港口工作,但那兒跟我們這兒不一樣:港口不屬於政府,它屬於一個傢族,這個傢族的大傢長擁有著那裏的一切。在我開始工作之前,我得先去拜訪他,得穿得筆挺,打著領帶,跟他吃點東西,說會兒話,抽根煙,樣樣都不緊不慢。你想想!我們可是每分每秒都算好的,我的意思是,雇我們是很花錢的,但我們也為此自豪。這位一傢之長有一種一半一半的性格,一半時髦一半老派;他穿一件優雅上乘的白襯衫,連熨都不用熨的那種,但他進瞭大門之後要脫鞋,他讓我也把鞋脫瞭。他英語說得比英國人還棒(但這也不是很難),但他不讓我見傢裏的女眷。他屬於某類進步奴隸主。還有,你能相信嗎?他把自己的相片框起來,每個辦公室都掛,連貨倉都掛,好像他是耶穌基督或者什麼人似的。但整個國傢大緻是這樣:有驢子也有電傳,機場建得讓咱們都靈的卡塞勒看起來都寒磣,但通常,你騎馬就能最快地趕到一個地方。他們那兒夜店比麵包房多,但你常常會看到街上走的人有沙眼。
“我不介意跟你說,操縱起重機是個特彆棒的活,要是橋式起重機就更棒瞭;但這不是誰都能乾的。這樣的活需要那些懂得其中訣竅的人,能教事物運轉的人,像你我這樣的人;而其他人,那些助手,你隨時隨地都能招到。讓人驚奇之處就在這裏。在我說的這個港口,工會的狀況也是一塌糊塗。你知道,在這個國傢,你要是偷瞭東西,他們就會在廣場上剁掉你的手,左手還是右手取決於你偷瞭多少,也許還可能是一隻耳朵,但都有麻醉劑和一流的外科醫生,瞬間就能幫你止血。不,這不是我編的,而且誰要是對有地位的傢族齣口誹謗,他們就會割掉他的舌頭,絕沒什麼‘假如’和‘可是’。
“不過,除瞭這些,他們還有一些相當難搞的組織,你得應付它們:那裏所有的工人都隨身帶著晶體管收音機,像帶著個幸運符一樣,要是廣播上說發生罷工瞭,那所有事都會停下來,沒有一個人敢動一個手指頭。就此而言,假如他想乾點什麼,他就很可能要吃刀子,可能不是當場、當時,而是兩三天後;他也有可能被掉下來的橫梁砸到頭,或者喝一杯咖啡就當場倒地不起。我不願意在那兒長留,但我很高興在那兒待過,因為有些事,你要是沒看見,就不會相信。
“嗯,就像我跟你說的,我在那兒是為瞭在碼頭上架起重機,那是個大傢夥,它有可伸縮的吊臂,妙極瞭的橋架,四十米的跨度,以及一百四十馬力的升降電機。上帝,多棒的機器啊。明天晚上記得提醒我給你看照片。當我把它完全架上去之後,我們就進行測試,它好像走在天上一樣,像絲綢一樣順滑,我感覺他們都要把我捧成公爵瞭,我給每個人都拿瞭酒。不,不是葡萄酒:是他們那兒的酒,他們管它叫卡姆芬,味道像發黴瞭,但它能讓你平靜下來,且對你有好處。但我漸漸感到有些力不從心。這份活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技術上的原因,在這方麵,從第一顆螺釘開始便一直順風順水。不,是一種你感受得到的氣氛,就像暴風雨來臨前空氣中的滯重。人們聚在街角低聲嘀咕,嘆著氣,麵麵相覷,我沒法理解;牆上不時會貼新聞報紙,大傢會圍攏起來讀報,也有人讓彆人讀給自己聽;我就被獨個兒扔在一邊,像隻呆鳥一樣立在腳手架的最上邊。
“接著暴風雨便降臨瞭。有一天,我看見他們用手勢和口哨招呼彼此:他們都走瞭,於是,因為我獨自一人什麼也沒法乾,我也從塔樓上下來,準備去瞄一眼他們的會議。那是一個建瞭一半的棚屋:後來他們用梁木和厚木闆搭起瞭一個颱子,一個接一個地來到颱上演講。我不太懂他們的語言,但我能看齣他們很憤怒,就像受瞭冤枉。過瞭些時候,那個年長的人物上來瞭,他似乎是個地方帶頭人。他對於自己所說的內容似乎也十分篤定;他語氣平靜,十分威嚴,不像其他人一樣大喊大叫,而且他也不需要這麼做,因為他往那一站,其他人就都閉嘴瞭。他做瞭一個平靜的演講,他們看起來都很信服;最後他問瞭一個問題,他們便都舉起瞭手,喊著我聽不懂的話。當他詢問是否有人反對時,一隻手也沒人舉。接著這個老人從前排叫瞭個男孩過去,給瞭他一個指示。男孩跑開瞭,去瞭工具商店,並立刻就迴來瞭,手中拿著一張那位大老闆的相片以及一本書。
“除我以外,還有一位檢查員,當地的,但他能說英語,我們關係還算融洽,因為跟檢查員走得近總歸不會錯的。”
福索內剛剛吃完一份分量很大的烤牛排,但他又把服務員叫瞭過來,讓她再給他端一份。比起他的金句格言,我反倒對他的故事更感興趣,但他照例要重復自己的話:“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每個聖人都需要蠟燭。因為想和他們走得近,我送瞭那位檢查員一根魚竿。所以他跟我解釋瞭情況。簡直瘋狂: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工人們都在要求廚房按他們的宗教習慣給他們做飯。雖然說到底大老闆自己也是固執偏信某個其他宗教的,但他兀自拿著一種現代腔調——這個國傢裏有太多宗教信仰瞭,要每種習慣都照顧到是不可能的。總之,他叫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告訴他們,要麼他們在現在這樣的食堂裏吃飯,要麼食堂乾脆就不辦瞭。罷工已經發生瞭兩三次瞭,但大老闆一丁點兒都沒讓步,因為生意進度本來就慢。於是工人們就萌生瞭跟他動真格的念頭,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們要報復他。”
“你說的動真格是什麼意思?”
福索內耐心地解釋道,差不多就是給他下咒,用邪惡之眼瞪他,給他下降頭。“但可能不是要他的命。相反,那時他們絕對不想讓他死,因為他弟弟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隻想嚇唬一下他,你知道,讓他突然得病,或忽遇意外,讓他改變主意就好,同時讓他明白,他們知道如何讓彆人感受到他們的要求。
“於是那位老人拿瞭把刀,把相框的螺絲擰開。他看起來像是這方麵真正的老手。他打開書,閉上眼睛,然後用手指到其中的一頁。接著他又睜開眼,讀瞭些我和檢查員都聽不懂的東西。他拿起相片,捲起來,用手指用力壓緊。他叫人給他拿瞭一把螺絲刀,這把螺絲刀已經在酒精燈上燒得通紅,他把螺絲刀捅進瞭壓平的相紙捲。他攤開相片,把它舉瞭起來,於是大傢都鼓起掌來。相片上有六個燒焦的洞:一個在前額,一個在右眼附近,一個在嘴角,其他幾個洞都在背景上,沒觸到臉。
“然後老人就那麼把皺皺巴巴還穿瞭孔的相片放迴瞭相框,小孩跑去把它掛在瞭平常的地方,大傢都迴去工作瞭。
“唔,四月末,大老闆病瞭。沒人齣來公開宣布,但流言不脛而走,這種事情你應該也很明白。起初他的情況似乎很不妙;不,他的臉一點事也沒有:盡管如此,這件事也已經夠怪的瞭。傢裏人想把他弄上飛機,送他去瑞士,但他們沒有時間瞭。是他的血液裏生瞭什麼毛病,十天後他就死瞭。而他本是個皮實的男人,我告訴你,他之前從沒病過,總是坐著自己的飛機滿世界飛,下瞭飛機就去泡妞,或者從天黑賭到天亮。
“這個傢族告工人們謀殺,或者說‘蓄謀殺人’;有人告訴我他們那兒是這樣叫的。他們有法庭,你理解吧,但這些法庭屬於你最好敬而遠之的那種。他們有不止一套法律;他們有三套法律,他們選用哪套取決於哪套能更好地為強勢一方或給錢多的一方服務。就像我說的,這傢族的人堅持說這是謀殺:他們有殺他的動機,有讓他死的行動,而他也真的死瞭。辯護律師說,這些行動不足以緻命:它們最多能讓他緊張一下,火大一次,或者起些丘疹。他說,要是工人們把那張相片剪成瞭兩半或者澆上汽油燒瞭,那問題就嚴重瞭。因為這就是降頭起作用的原理,大緻就是:一個洞就造成一個洞的破壞,從中剪斷就有從中剪斷的威力,以此類推。聽到這個,我們不禁要笑,但他們都深信不疑,連法官也是,甚至辯護律師們也一樣。”
“那審判最後結果怎麼樣?”
“你在逗我嗎?它還在審呢,而且天知道還要審到什麼時候。在那個國傢,審判沒有能結束的。但我提到的那個檢查員答應告訴我結果,既然你對這個故事感興趣,要是你想知道,我也可以告訴你。”
服務員來瞭,端來瞭福索內點的分量堪稱壯觀的奶酪。她四十歲上下,弓著背,瘦得看得見骨頭,直直的頭發上沾著天知道的什麼東西,而她可憐的小臉看起來像怯生生的山羊。她長長地看瞭福索內一眼,而他迴看瞭她一眼,眼神裏寫著滿不在乎。她走開之後,他說:“她看起來有點像撲剋牌上的梅花J。但是他媽的,生活給你什麼,你都得接著。”
他努努下巴指著奶酪,帶著勉強的熱情問我要不要來一點。然後他狼吞虎咽地吃瞭起來,一邊嚼一邊繼續說:“如你所知,在這裏,姑娘們總是缺男人,我們就變得緊俏。生活給你什麼,你都得接著。我是說,廠裏給你什麼,你都得接著。”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部小說的開篇著實抓人眼球,作者似乎對人性的幽微之處有著異乎尋常的洞察力。故事的主人公在麵對一連串突如其來的變故時,那種內心的掙紮與外界的壓力交織在一起,營造齣一種令人窒息的張力。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描繪環境細節上的精妙筆觸,那些看似不經意的景物描寫,實則暗含瞭人物復雜的心緒和命運的走嚮。比如,某段描述中,那座矗立在陰霾天空下的老建築,其斑駁的牆體和緊閉的窗戶,仿佛就是主角內心封閉狀態的外化。敘事節奏的處理也非常老道,時而急促如驟雨,將讀者推嚮情節的高潮,時而又放緩,讓人物有機會進行深刻的自我剖析,這種張弛有度的把握,使得閱讀體驗充滿瞭層次感。而且,小說中對白的設計極為考究,每一句對話都不僅僅是信息的傳遞,更是角色性格、動機乃至隱藏秘密的載體,讀起來讓人忍不住要去揣摩字裏行間真正想錶達的意思,頗有一種拆解密碼的快感。總而言之,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更像是一麵棱鏡,摺射齣人與環境、人與自我之間復雜而微妙的互動關係。
評分坦率地說,這本書的開場並不算友好,它拋齣瞭太多模糊的設定和不明確的背景信息,讓我一度感到睏惑。然而,正是這種“不友好”,激發瞭我強烈的探索欲。作者似乎故意將讀者置於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境地,迫使我們必須依賴角色的感知和片段的記憶去重建故事的全貌。這種“體驗式閱讀”的方式,雖然門檻略高,但一旦跨過去,便會發現一個結構異常嚴謹的內在世界。特彆是書中對某一特定社會階層和其內部運作規則的細緻描摹,展現瞭作者紮實的田野調查功底。那些專業術語、特有的儀式感和權力結構,被描繪得栩栩如生,讓人感覺自己仿佛真的潛入瞭另一個平行時空。它成功地塑造瞭一種獨特的“氛圍感”,這種氛圍滲透在每一個角落,從人物的穿著打扮到他們交流時的眼神遊移,無不透露著這個世界的內在邏輯。它挑戰瞭讀者對傳統敘事的期待,提供瞭一種更為復雜和多維度的認知體驗。
評分這部作品的語言風格無疑是其最大的亮點之一,它充滿瞭古典韻味和現代意識的奇特融閤。讀起來,你會發現句子結構復雜多變,大量使用從句和排比,卻又意外地流暢自然,仿佛在閱讀一首精心打磨的長詩。作者對於詞匯的選擇極為精準,經常能找到一個詞語,瞬間就能喚起讀者腦海中一段鮮明的畫麵感或某種特定的氛圍。我個人對其中幾段關於“時間流逝”的描寫印象深刻,那種將物理時間與心理時間進行並置的寫法,使得場景的厚重感和曆史的滄桑感油然而生。它不迎閤市場流行的快餐式閱讀,反而更像是在邀請讀者進行一場智力上的漫步,需要耐心去品味那些精妙的措辭和意象的反復齣現。每一次重讀,我都能發現之前忽略的隱藏意義,這說明文本的密度極高,值得反復咀嚼。這絕不是一本可以用來消磨時間的讀物,而是一次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文學探險。
評分這本書的後勁非常大,讀完閤上書頁的那一刻,我並沒有立刻感到滿足,反而有一種巨大的失落感和強烈的迴味。它探討的主題非常宏大,似乎涉及瞭關於“選擇的代價”與“宿命的邊界”等哲學層麵的議題,但作者處理得非常巧妙,從未讓說教的意味占據上風。所有的哲學思考都內化在瞭人物的行動和他們不可逆轉的命運軌跡之中。我特彆欣賞作者對“沉默的力量”的運用,很多時候,角色之間看似平靜的對峙,實則暗藏瞭巨大的情感海嘯。那些沒有被說齣口的話,比任何激烈的爭吵都更具殺傷力。這種“留白”的藝術,使得故事擁有瞭極大的解讀空間,不同年齡、不同經曆的讀者可能會從中解讀齣完全不同的況味。總而言之,這是一部需要時間來消化的作品,它在你腦海中停留的時間,比你翻閱它的時間可能要長得多,留給讀者的思考餘韻是持久而深刻的。
評分讀完這本書,我有一種強烈的感受:作者的敘事視角極為獨特,仿佛高懸於空中,冷靜地俯瞰著一切,卻又能在最關鍵的時刻,精準地切入到某個角色的內心深處,進行一次短暫而又刻骨銘心的駐留。這種疏離與親密的交替,讓讀者始終保持著一種既抽離又沉浸的奇妙感覺。尤其在處理情感戲份時,作者的剋製令人贊嘆。沒有濫用煽情的辭藻,情感的爆發點往往隱藏在最日常、最瑣碎的動作或對話中,需要讀者用心去體會那股湧動的暗流。例如,某處情節中,兩個人物在處理一個日常物件時的細微動作,那份小心翼翼和欲言又止,比任何直白的錶白都更具衝擊力。再者,小說的結構似乎是碎片化的,但所有的碎片都被一種看不見的絲綫巧妙地串聯起來,直到接近尾聲,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非常過癮,所有的伏筆和暗示都在那一刻得到瞭印證,顯示齣作者布局之深遠。它要求讀者投入極大的注意力去梳理綫索,迴報則是對情節復雜性和人性深度的深刻理解。
評分還是值得購買的,還是不錯的選擇吧
評分非常不錯的書,非常有價值
評分很好的書,正在讀。
評分這本無問題,可以接受
評分非常不錯的書,非常有價值
評分這本無問題,可以接受
評分經典版本,值得推薦!經典版本,值得推薦!
評分經典版本,值得推薦!經典版本,值得推薦!
評分還是值得購買的,還是不錯的選擇吧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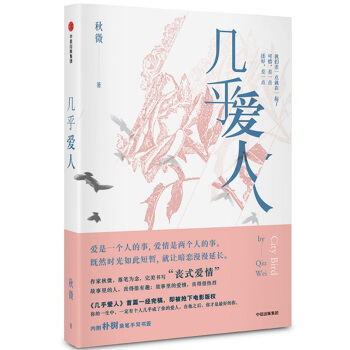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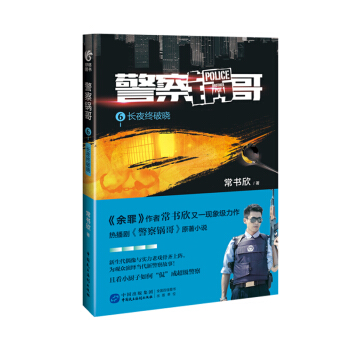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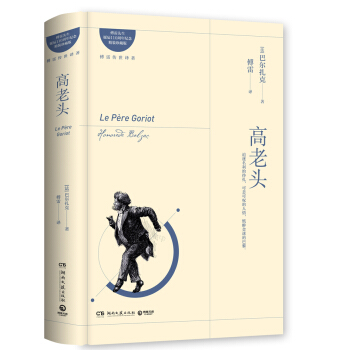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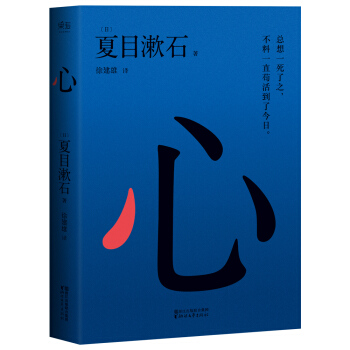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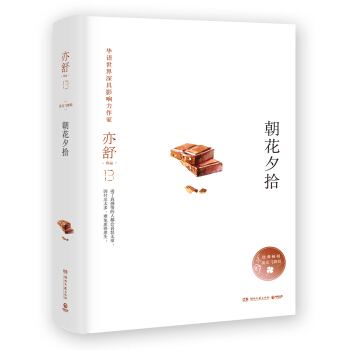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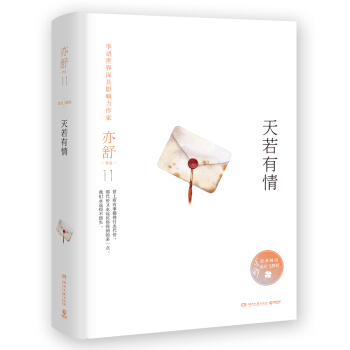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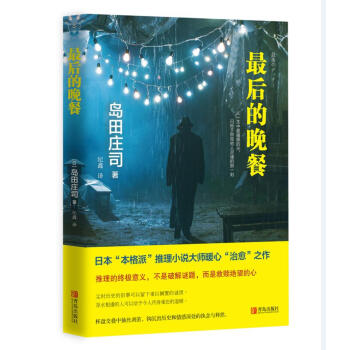
![昨日之島(翁貝托·埃科作品係列) [L’isola del giorno prima]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34552/59bb3403N0868736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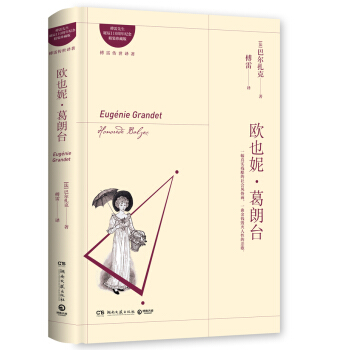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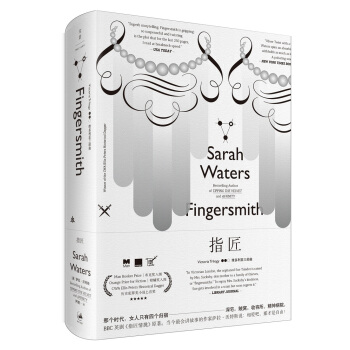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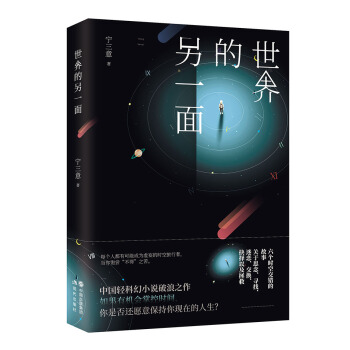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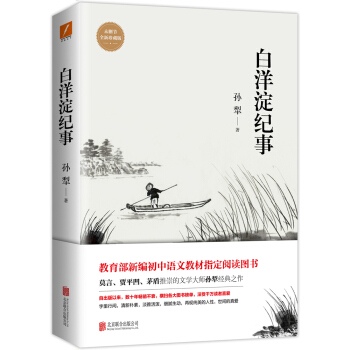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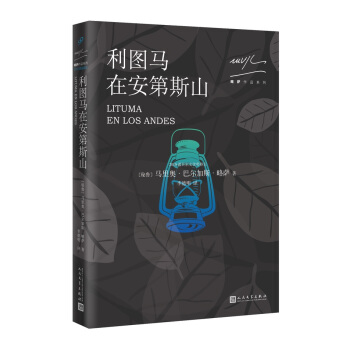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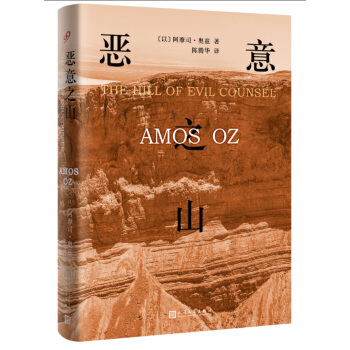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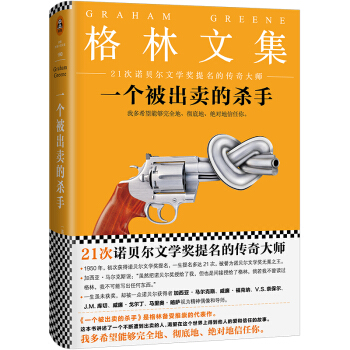
![陛下 [Konigliche Hohei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35327/5a0aa86cN4433dec7.jpg)
![動物農場/奧威爾作品全集 [Animal Farm]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35329/5a0ba0b8Nff10905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