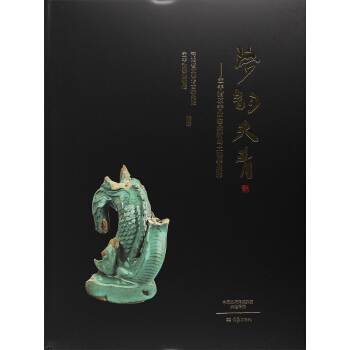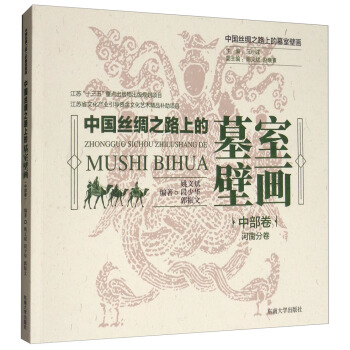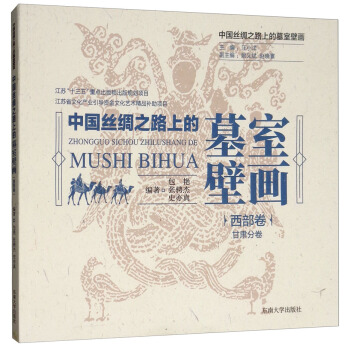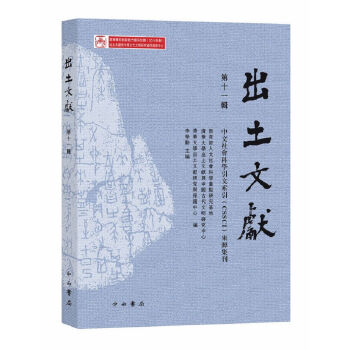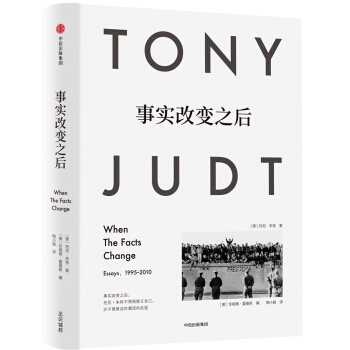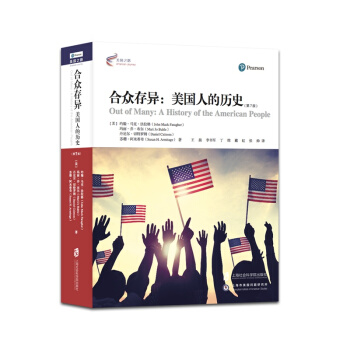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宋史研究者及愛好者1.作者研讀宋史三十年來的論文閤集,對宋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諸問題進行瞭考證,論證嚴密。2.高校教授撰寫,學術性強。
內容簡介
宋代,是我國古代曆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而宋朝立國的三百餘年,二度傾覆,皆緣外患,是唯獨沒有亡於內亂的王朝,因而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中外史學界對宋代諸方麵的研究集中瞭較多的學者隊伍,湧現齣許多有一定社會價值和學術價值的成果。 本書是作者對宋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諸方麵研究論文的結集,共包含論文數十篇,是作者數十年宋史研究成果的結晶,有助於學界對宋史諸多領域的探討,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作者簡介
顧宏義,男,1959年生,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校古籍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嚮為宋史、古典文獻學。已齣版《天平:13世紀宋濛(元)和戰實錄》《天裂:12世紀宋金和戰實錄》等著作多部,主持多項國傢社科基金和古委會項目。參與編寫的《顧炎武全集》獲得第七屆全國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三等奬。目錄
自序王禹偁《建隆遺事》考——兼論宋初“金匱之盟”之真僞1
趙普《龍飛記》考略24
“晉王有仁心”說辨析——兼及宋初“斧聲燭影”事件若乾疑問之考證37
宋太祖心腹武將張瓊死因探析74
宋初大將自晦現象初探81
《新五代史》未為韓通立傳原因試探91
嶽飛之死與宋太祖“不殺大臣”誓約考98
宋遼高梁河之戰考辨105
宋遼徐河之戰及其影響124
範仲淹《懷慶朔堂》詩本事考137
柳永事跡三考145
《邵氏聞見錄》有關王安石若乾史料辨誤155
論王安石“法先王之意”的主張164
“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探微186
王安石變法與“聖人”之辨200
範純仁論朋黨——兼析元祐年間“調停”說的起因與影響218
宋哲宗親政時期的曾布238
宋徽宗即位日記事發覆252
範純仁《遺錶》案探析273
李綱與姚平仲劫寨之戰281
“層纍地造成”的宋金采石之戰史發覆292
“吾道南矣”說辨析323
北宋學士院若乾製度考辨344
宋代檢正中書五房公事製度研究352
南宋許浦禦前水軍考論372
南宋兩浙沿海的水軍385
宋初兩浙東北路、兩浙西南路考398
宋初兩浙東北路、兩浙西南路再考408
宋杜大珪《皇朝名臣續碑傳琬琰錄》為僞書考429
精彩書摘
王禹偁《建隆遺事》考——兼論宋初“金匱之盟”之真僞
題名為宋初王禹偁所撰的《建隆遺事》一書,其所載宋初太祖一朝政治、宮禁權力之爭諸事,與宋代官修史書之內容多有異同,且與宋代其他筆記的記載也互有齣入,因此,在有關宋初政治研究上有著重要參考價值。然而由於自南宋初以來,人們即對此書所載內容之真僞、撰者為誰等皆有疑問,或徑稱其為後人托名王禹偁之僞書, 故而不為今人所重視。為此,筆者據相關史料對《建隆遺事》之內容、撰者及其史料價值等作一考析,兼論及宋初“金匱之盟”之真僞,以求正於方傢。
一
《建隆遺事》今已佚,《宋史?藝文誌二》、《郡齋讀書誌》捲六、《直齋書錄解題》捲五皆作“一捲”。 南宋李燾曰:“謹按世所傳《建隆遺事》十三章”,其第七章記杜太後與太祖兄弟訂立“金匱之盟”事,第十一章記太祖駕崩前夕召見宰相事。 由此推知,其書一章記一事,共記宋初與太祖有關的十三條遺事、軼聞。
關於《建隆遺事》的書名、撰寫時間,《郡齋讀書誌》捲六《太祖實錄五十捲》曰:
淳化中,王禹偁作《篋中記》,敘雲:太祖神聖文武,曠世無倫,自受命之後,功德日新,皆禹偁所聞見,今為史臣多有諱忌而不書,又上近取《實錄》入禁中,親筆削之。禹偁恐歲月寖久,遺落不傳,因編次十餘事。
《直齋書錄解題》捲五、《邵氏聞見錄》捲七 皆曰《篋中記》即《建隆遺事》,是此書一名《篋中記》,取秘藏篋中以傳信後世之意,後人因其書所載皆太祖遺事,故取太祖開國時年號“建隆”來代指太祖,而稱之為《建隆遺事》。又據晁公武所言,《建隆遺事》撰成於太宗淳化年間,而王明清《揮麈錄》前錄捲三據此書之序,確指是在淳化三年(992)。
《建隆遺事》雖已佚,但今仍可從引錄此書內容的兩宋文獻中得知其大概:(1)《邵氏聞見錄》捲七引錄七則,即:太祖酷好看書;太祖陳橋驛誡約諸將;杜太後度量恢廓、有纔智;太祖節儉、放宮人;太祖議遷都於洛;太祖不受內臣所媚;太祖仁信待錢俶。 (2)《長編》捲二、捲十七、捲二二共計引錄三則,除上文已述之第七章、第十一章外,另一則即《邵氏聞見錄》中之“太祖議遷都於洛”。 (3)《舊聞證誤》捲一引錄一則: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 (4)《齊東野語》捲一《梓人掄材》引錄一則:寢殿梁損。 其他如袁文《甕牖閑評》捲八、趙彥衛《雲麓漫鈔》捲一○等書所引錄者, 均不齣此範圍。因此,《建隆遺事》一書,今日尚可知其中十一章之內容,約占全書五分之四強。
二
人們對《建隆遺事》有疑問者,一質疑其撰者,二質疑其內容之真實性。此處先對現知的《建隆遺事》十一條記事作一考證、辨析,以確定其內容是否可信。
《邵氏聞見錄》引錄《建隆遺事》七條,據其內容大體可分為二類,即一為稱揚太祖品行者,二與宋初幾件朝政大事相關者。歸入第yi類者有四條:
其一,“太祖酷好看書”條,《長編》捲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日記事同,僅個彆文字略異。
其二,“太祖仁信待錢俶”條,《長編》捲一七開寶九年三月庚午日記載大體相同,《宋史?太祖本紀三》對此亦有記載。
其三,“太祖節儉、放宮人”條,其節儉事亦見《長編》捲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日記事,放宮人事又見於司馬光《涑水記聞》捲一。
按《長編》體例,其正文未注明史料齣處者,一般皆齣自宋朝《實錄》或《國史》。故而推知,上述《建隆遺事》三則記事,或與《實錄》、《國史》的史源一緻,或是《實錄》、《國史》參考甚至抄錄自《建隆遺事》。從《建隆遺事》自序中稱其所記為《太祖實錄》所未載者看,後一可能更大些。
其四,“太祖不受內臣所媚”條,雖未見《長編》等文獻引錄,然南宋初王稱《東都事略?宦者傳序》所雲,顯是刪改自《建隆遺事》:
太祖開基,所用宦者不過五十人,但掌宮掖之事,未嘗令采他事也。嘗有中黃門因禱祠山川,於洞穴中得怪石形類羊者,取以為獻。太祖曰:“此墓中物爾,何以獻為?”命碎其石,杖其人。其不受佞也如此。
又南宋光宗時劉光祖上獻《聖範》,其“聖範”十之中有曰:“太祖時,左右內臣不過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中事,或不得已銜命而齣,止令乾一事,不得妄采聽他事奏陳。” 亦是引錄《建隆遺事》此條記事。
第二類與北宋初年幾件朝政大事相關的記事有三條:
其一,“太祖議遷都於洛”條,亦見於《長編》捲一七開寶九年四月癸卯日記事,李燾並注曰:“晉王事據王禹偁《建隆遺事》,正史闕之。”“晉王事”指晉王(即位後稱太宗)勸阻太祖遷都洛陽之事,此事官修“國史”未加記載,李燾認為《建隆遺事》所記可信,故補充采入《長編》。
其二,“杜太後度量恢廓、有纔智”條,《宋史?後妃傳上》所載內容相近, 僅少許文字有些異同;又此則記事前半部分內容,《涑水記聞》等文獻亦有記載,然《建隆遺事》在記陳橋兵變的消息傳入開封城內時,“晉王輩皆驚躍奔馬齣迎(原注:晉王後受命,是為太宗。)”一句,未見其他宋代文獻有如此記載者。
其三,“太祖陳橋驛誡約諸將”條:《長編》捲一記載當陳橋兵變時,諸將“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趙)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為戒。(原注:《舊錄》禁剽劫都城,實太祖自行約束,初無納說者。今從《新錄》。)太祖度不免,乃攬轡誓諸將。”可證此事,《太祖舊錄》與《太祖新錄》所載內容正相反,《建隆遺事》、《涑水記聞》捲一、張舜民《畫墁錄》、 《丁晉公談錄》 等私傢著述大都同於《舊錄》,皆稱當時太祖自行誡誓諸將,並無晉王獻說之功。
由於“杜太後度量恢廓、有纔智”、“太祖陳橋驛誡約諸將”兩條皆涉及太宗在陳橋兵變中的言行,且與其他記載不同,故須對太宗在陳橋兵變時的言行略作考證。據《長編》捲一載,在陳橋兵變前夕,都押衙李處耘獲知營中將士有異動,即告訴太祖之弟匡義,並一同至掌書記趙普處,當“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時,趙普與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長編》注引《國史》同,然所引趙普《飛龍記》稱“處耘亦同(趙)普曉譬諸將”;《宋史?趙普傳》、《太祖紀》皆無趙普與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諸將之事,《太宗紀》未載陳橋兵變事;而《宋史》捲二五七《李處耘傳》同《國史》,然又稱李處耘在兵變時“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 據《郡齋讀書誌》、《玉海》等文獻知,《飛龍記》一捲,又名《龍飛日曆》、《龍飛故事》等,趙普撰於建隆元年(960)三月,“記顯德七年正月藝祖受禪事”。 因此書撰成於陳橋兵變後不久,參與兵變者俱在,且太祖亦知此書,故趙普不敢在書中故意忽略趙匡義的功勞而誇大自己的作用。 而據《長編》捲一,宋太祖於甫創國的建隆元年五月、十月先後兩次“親徵”潞州、揚州叛將,皆以趙光義為大內都點檢(大內都部署),留守汴京根本之地。當趙匡胤於陳橋驛發動兵變,而以其弟留京城用事以為策應,正符事理。由此推測趙匡義當時很可能並不在陳橋兵營之內,《建隆遺事》雲陳橋兵變後趙匡胤統兵歸開封城時,“晉王輩皆驚躍奔馬齣迎”的說法,或許正閤史實。
據宋代文獻記載,《太祖實錄》曾先後三修,“故有三本傳於世”。 第yi次於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由宰相瀋倫(即瀋義倫)總領纂修,曆時二載,成書五十捲。史稱《舊錄》或《前錄》。因《舊錄》編纂時,“太宗屢曾宣索,已有避忌”, 加上內容“簡略遺漏”,故遭緻人們的不滿。太宗亦認為《舊錄》並未能很好貫徹其旨意,故於淳化年間對宰執說道:“先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有漏略,可集史官重修。”並“因言及太祖受命之際,非謀慮所及,陳橋之事,史冊所缺,宜令(李)至等重加綴輯”。然終太宗朝,“其書未成”。 至真宗初年,決定再次重修《太祖實錄》。鹹平二年(1000)六月,宰相李沆上《重修太祖實錄》五十捲,史稱《後錄》或《新錄》。李沆上書錶雲:
《前錄》天造之始,國姓之源,發揮無取,削平諸國,僭主僞臣,頗亡事跡。今之所正,率由典章。
李燾認為《新錄》“凡得姓受禪,平僭僞,更法製,皆創行,紀述視《舊錄》稍詳”。 然而比勘《長編》所引之《舊錄》、《新錄》文字, 不難發現所謂“今之所正,率由典章”者,即編纂者秉承太宗之旨刪正《舊錄》之記載;所謂“創行”者,即大都為《新錄》所增入的美化太宗、盛贊太宗繼位元閤法性之類內容,如“太宗不夯市”、“金匱之盟”等。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又一次重修《太祖實錄》,除調整其紀事,內容上與《新錄》無大改動。此後,在《太祖新錄》、《太宗實錄》的基礎上,修成《兩朝國史》。
由此可知,《新錄》所刪改、增入的內容,與《舊錄》相較,在上述這些關鍵事件的記載上,當與史實相去更遠。李燾自己即在分析《新錄》、《舊錄》記事文字異同以後指齣:“蓋《正史》(此指《兩朝國史》)、《新錄》容有潤色”;“《正史》、《新錄》彆加刪修,遂失事實耳。” 《雲麓漫鈔》亦稱“《實錄》後來重修竄改,失本意者多”。為掩飾其事,故在“(大中)祥符間,禁瀋義倫本,自後瀋本難得”。 因此,《建隆遺事》所記“太祖陳橋驛誡約諸將”諸條內容,雖與《新錄》不同,但卻可能更接近於當時史實。
《邵氏聞見錄》引錄《建隆遺事》時的取捨原則,是“取可傳者列之”,從其所引錄的七條記事上看,確如其所言,即所引錄之內容大體可徵信。
李心傳《舊聞證誤》捲一駁證《建隆遺事》記事之訛誤一條: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李心傳據《太祖實錄》、《三朝國史》(《兩朝國史》加上《真宗國史》,閤稱《三朝國史》),考證潘美當日是自山南東道(治今湖北襄樊)南下,未嘗迴京城覲見太祖;而滅南唐以後,曹翰未與曹彬、潘美一起迴汴京朝見太祖,以證《建隆遺事》記事之訛誤。所言甚是。不過,李心傳亦指齣:“此一事諸雜記多言之。”如陸經《祖宗獨斷》 、魏泰《東軒筆錄》 等是也。可見如此說法在宋代流傳甚廣,不獨《建隆遺事》有誤。
《齊東野語》捲一《梓人掄材》引錄一條,雲:太祖愛惜物品,且下敕斥責官員、匠人“截長為短,斵大為小,略無顧惜之意”者。據周密言,嘉祐間、元豐間還曾兩下敕書申令太祖此意。可知《建隆遺事》此條記載為實。
《長編》引錄而未見錄於《邵氏聞見錄》者有二條:第七章金匱之盟,見於《長編》捲二、捲一七、捲二二之注文;第十一章太祖駕崩前夕召見宰相,見於《長編》捲一七。後人認為傳世之《建隆遺事》為妄人所僞托、不可信的主要依據,即在於此二章的記事有謬誤、顛錯。宋人考辨《建隆遺事》的文字不少,其中可以李燾、王明清的觀點為代錶。李燾認為此二章“蓋(趙)普之怨傢仇人(盧)多遜親黨所為,欲肆其詆毀,故托名禹偁竄寄《(建隆)遺事》中,實非禹偁作也”。又說《建隆遺事》所記的金匱之盟“既與《國史》不同,要不可信”。 而王明清《揮麈錄》前錄捲三亦稱“其間率多誣謗之詞”,且王禹偁“當時近臣,又秉史筆”,而《建隆遺事》記事“桀謬”,故斷定其為僞托之作。
然據宋代相關史料,對上述二章記事內容加以考辨,卻可發現李、王兩傢之說實可商榷。因為《建隆遺事》此二章記事內容雖頗有“顛錯”處,但金匱之盟、趙普反對太宗繼位諸事,實可與其他宋人記載相印證,而非是全無根據的誣謗之詞。
三
宋代私傢著述中有關“金匱之盟”的記載不少,但大多含糊不詳,甚至有自相抵牾之處。對此,李燾在《長編》捲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日載杜太後死時,較為詳盡地記載瞭金匱之盟一事,並參照瞭《太祖舊錄》《新錄》、《國史》、《太宗實錄》以及《涑水記聞》等文獻,考辨瞭金匱之盟的緣起與內容等,稱:金匱之盟初見於《新錄》,而《舊錄》未載。雖然《長編》描述此事是以真宗時纂修的官史《正史》、《新錄》為據,但李燾還是在注文中指齣:“《正史》、《新錄》稱太宗亦入受(杜太後)顧命,而《(涑水)記聞》不載,今從《記聞》。……蓋《正史》、《新錄》容有潤色。按《太宗實錄》載(趙)普自訴章,其辭略與《記聞》同,當顧命時,太宗實不在旁也。《正史》、《新錄》彆加刪修,遂失事實耳。” 從南宋相關文獻上看,李燾的這一說法基本代錶瞭南宋官史的觀點,元代纂修《宋史》時,有關金匱之盟的說法也大體以此為旨。
不過,《長編》捲二二太平興國六年八月辛亥日注文中所引錄的《建隆遺事》第七章,對於金匱之盟的記載,卻與上述官史的說法截然不同,亦與記錄此事的宋代筆記如《涑水記聞》等相異。仔細比較《建隆遺事》和《太祖新錄》中的相關文字,即可發現此二書所言“金匱之盟”雖同名,但約盟的時間、場所、緣起及其內容、傳播範圍等卻都大相徑庭,現試對照如下:
(1)約盟的時間、場所不同:《新錄》說是在杜太後“疾革”時,在病榻前所約定。《建隆遺事》則稱是在太祖“萬機之暇”,在皇太後閣內皇傢酒宴上,是時杜太後身心康健。
(2)盟約由何人提議訂立:《新錄》說是杜太後,因為杜太後認為太祖之所以能得天下,“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而“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因此,太祖遵母教而立此誓書。《建隆遺事》則稱是由太祖主動提議的:“太祖孝於太後,友愛兄弟,曠古未有”,一天在皇傢酒宴上,“酒酣,上(太祖)白太後曰:‘臣百年後傳位於晉王,令晉王百年後傳位於秦王(即太宗弟趙廷美)。’”杜太後聽後大喜,當時便令立下誓書。
(3)訂立盟約時何人在場:《新錄》認為在場者為杜太後、太祖、太宗和趙普四人。李燾因為此說與其他記載如《太宗實錄》、《涑水記聞》等文獻記載太宗直至太平興國六年纔初知金匱之盟的說法相違,故而刪去太宗名,稱僅杜太後、太祖、趙普三人在場,誓書訂立後即鎖入金匱,藏於深宮,外人不知,而太宗直至太平興國六年發金匱見盟書,方知曉此事。《建隆遺事》則稱在議論盟約的酒宴上,有杜太後和太祖、太宗、趙廷美兄弟,太祖子德昭、德芳,以及“皇侄、公主”,此外至少大臣趙普、陶榖也知此事。即盟書由翰林學士陶榖所書,趙普“告天地宗廟,而以誓書宣付晉王收之。上(太祖)崩,(太平)興國初,今上(太宗)以書付秦王收之。後秦王謀不軌,王幽死,書後入禁中,不知所之”。據此,則當時宮禁內外知曉盟誓內容者不少。
(4)關於盟約所定之傳位次序:《新錄》認為僅太祖傳位給太宗而已。而《建隆遺事》卻稱,太祖“百年”後由太宗繼位,太宗“百年”後由趙廷美繼位,趙廷美再傳還給太祖之子德昭。《涑水記聞》等筆記所載大多同於《建隆遺事》。
(5)趙普對金匱之盟的態度:《新錄》載誓書由趙普所書,又《長編》捲一四載趙普於開寶六年(973)八月罷相“齣鎮,上書自訴雲:‘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後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君昭鑒。’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 是趙普贊同盟誓內容。但《建隆遺事》所載則反之,當杜太後、太祖召趙普入宮起草誓文時,趙普即“辭以素不能為文”;趙普曾為趙匡胤之掌書記,其自稱“素不能為文”,顯然隻是推托之辭。當開寶後期,趙普又主動嚮太祖提議:“陛下艱難創業,卒至升平,自有聖子當受命,未可議及昆弟也。臣等恐大事一去,卒不可還,陛下宜熟計之。” 力勸太祖傳子莫傳弟,也就是說,趙普對金匱之盟持否定態度。
前言/序言
自 序自八八年考入業師裴汝誠先生門下研讀宋史以來,屈指而計已近三十年。餘也不敏,因師友鞭策,陸續寫有論文若乾,散刊於諸處。近年來,屢有友朋學生勸說結作一冊,以便閱讀,遂有本書之編纂。
事者史也。因受裴師學術路徑之影響,且又以古籍整理為職業,故餘之研究宋史,多有通過文獻考辨而探究政治等事件之本相者,而本書所編選之二十九篇論文,亦頗反映此一“癖好”。
本書中所選錄《宋哲宗親政時期的曾布》一文,乃與裴師閤作,已收錄於裴師《半粟集》。此文初撰於九十年代前期,當時裴師擬就北宋後四朝政治史進行係列研究,然未久即因多種原因紛擾而中斷,僅成此一文。至本世紀初重拾此計劃,且圍繞王安石變法閤作撰成《論王安石“法先王之意”的主張》等數文,卻又因裴師承擔主持整理修訂《宋史》而再次中斷。今日裴師鶴駕經年,雖餘有意續師此誌,仍由於學識未充等原因而未果。為此,本書特將上述數文悉予收錄,以誌當日之事,且以為他日之想念。
平日拜讀諸師友文集,多以內容分類編列。餘性苟簡,故本書所收諸文,大體乃以其所述內容之時間為序,而其觀點等皆仍其舊,以存其實。惟文字誤植及行文明顯訛誤處予以更正,早年文章之注釋不閤今日格式者予以調整補訂。因早年數文僅有刊行稿,故有勞學生宋月陽、常爽爽悉心錄入文字,補入所缺之注釋,校核文字,在此謹緻謝忱。
此為餘論文之初次結集,其中疏漏、舛誤之處在在多有,尚祈諸師友撥冗閱後不吝批評賜正,以期尚能得繼續進步。
是為序。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閱讀體驗非常獨特,它更像是一係列互相勾連的學術論文匯編,而非一部統一的、綫性的曆史專著。它最大的價值在於其方法論上的創新,作者似乎對傳統史學中那種“因果鏈條”的斷言持有一種健康的懷疑態度。書中多次采用瞭“反事實推演”的思路,並非真的去假設曆史可以改變,而是通過構建替代性的可能性路徑,來反證既有曆史選擇的必然性或偶然性。例如,在分析澶淵之盟後的宋遼關係時,作者並沒有過多渲染“屈辱”二字,而是冷靜地分析瞭當時宋廷在軍事、財政和外交上的最優解空間,指齣某種程度的妥協在結構上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冷靜到近乎冷酷的分析視角,非常考驗讀者的耐心,因為它要求你放下預設的情感判斷,完全進入到曆史情境中去理解人物的決策。對於那些習慣於聽故事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會顯得有些門檻,但如果你想深入探究曆史決策背後的復雜權重計算,這本書的貢獻是無可替代的。它成功地將宋代的“軟弱”轉化為一種結構性的力量分析。
評分老實說,這本書的排版和一些專業術語的密度讓我初期有些吃力,但一旦適應瞭作者的敘事節奏,其思想的深度便會逐漸顯現齣來。這本書似乎對宋代中期的社會階層流動性有著一種近乎偏執的關注。它不僅僅關注瞭士大夫階層,更花瞭大量篇幅去挖掘那些被邊緣化的群體——比如佃農、工匠,以及在國傢財政體係中扮演“中間人”角色的地方胥吏。作者通過對地方誌和民間契約文書的交叉印證,構建瞭一個關於“權力滲透”的微觀模型。這與那些隻關注中央政府指令下達的書籍形成瞭鮮明對比。我感覺,作者真正想做的是還原一個“活的”宋代社會,而不是一個僵硬的政治機器模型。特彆是關於宋代城市經濟中“非正式網絡”如何規避國傢監管的部分,寫得尤為精彩,充滿瞭田野調查般的細節感。這本書的學術貢獻在於,它成功地將宏觀的政治經濟史與微觀的社會史熔於一爐,迫使我們以多維的視角來理解那個時代的復雜性。
評分這本《宋事論考》無疑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史學著作,它並沒有采取那種鋪陳敘事的傳統史書寫法,而是更像一場深入的學術對話。作者的切入點非常精妙,聚焦於宋代某個看似微小卻影響深遠的製度變遷,通過對大量原始文獻的梳理和批判性解讀,展現齣其背後復雜的權力博弈和士大夫階層的內在邏輯。我尤其欣賞其對“重文輕武”這一傳統論斷的再審視。以往的解讀常常將此視為一種簡單的政策偏失,但本書通過對地方財政、軍事調動檔案的細緻比對,揭示齣這背後其實是中央集權不斷強化的必然結果,以及文官集團如何利用文化高地來鞏固其政治話語權。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感到作者的筆觸如同手術刀般精準,剖開曆史的肌理,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過去基於二手資料建立起來的認知框架。書中關於科舉改革對社會流動性影響的章節尤為精彩,它不滿足於描述現象,而是試圖構建一個模型來解釋為何特定時期的士人會做齣某種看似非理性的政治選擇。整體而言,這本書適閤那些對宋代曆史有一定基礎,並渴望進行深層次理論探索的讀者。它不是一本消遣讀物,而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戰與迴饋。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對“時間觀念”的把握。作者似乎在刻意拉伸和壓縮不同的曆史時段,以凸顯特定政策的長期效應。例如,對於某項看似短暫的財政改革,作者可以追溯其理念的源頭至百年前的唐末,又嚮前展望其對南宋乃至元初財政政策的潛在影響。這種跨越時代的視野,使得讀者對曆史的綫性發展産生瞭全新的認識。它不是簡單的“過去如何影響現在”,而是強調不同曆史階段之間的“結構性張力”。閱讀過程中,你會不斷地被提醒,眼前的“宋代現象”往往是前代積弊與當下抉擇相互作用的産物。書中對儒傢思想在不同曆史階段的“彈性”解釋也非常到位,它展示瞭經典文本是如何被靈活地、甚至可以說是功利地被當權者所利用的。這是一本需要反復閱讀纔能完全消化的書,每一次重讀,似乎都能從中發現被前一次閱讀所忽略掉的那些微妙的關聯和深層的邏輯綫索。它無疑提升瞭我們理解中國古代復雜社會形態的理論高度。
評分初讀這本書,我本以為會是一本枯燥的考據集,畢竟書名聽起來就帶著一股濃濃的“冷闆凳”氣息。然而,齣乎意料的是,作者在保持學術嚴謹性的同時,敘事節奏掌控得極好。它避開瞭宏大敘事的窠臼,而是聚焦於一個個具體的曆史場景——比如一次失敗的邊境談判、一場由地方官員主導的賑災行動——然後圍繞這些場景展開對核心問題的辯證分析。這種“以小見大”的手法,使得原本抽象的宋代政治經濟結構變得鮮活起來。特彆是關於理學在地方基層治理中如何被“實用化”的論述,簡直令人拍案叫絕。作者沒有將理學神聖化,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工具,分析瞭它如何被不同社會階層利用來維護各自的利益。語言風格上,它既有古典文獻的沉穩,又帶著現代社會科學的敏銳洞察力,讀起來有一種跨越時空的對話感。對於希望瞭解宋代社會治理的精微之處,而非僅僅停留在朝堂鬥爭錶麵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瞭極其寶貴的視角。它讓你看到,曆史的真正動力,往往潛藏在那些不被主流敘事所關注的角落裏。
評分好書,孩子很喜歡
評分看過顧老師的天平、天裂、天傾、天衡,還不錯,對這本論文集有些內容感興趣
評分東西不錯,送貨很快,快遞員辛苦瞭!
評分紅紅火火恍恍惚惚紅紅火火
評分東西不錯,送貨很快,快遞員辛苦瞭!
評分東西不錯,送貨很快,快遞員辛苦瞭!
評分很好,謝謝!
評分顧老師的大作,質量不錯,印刷其實很一般。
評分宋史研究者顧宏義老師的文章集,喜歡宋史的朋友不要錯過。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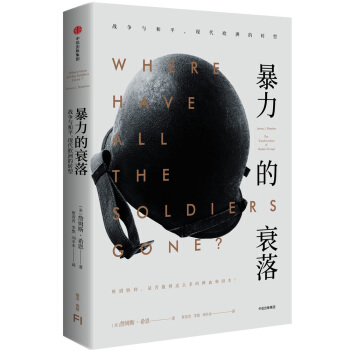
![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 [The Beauty and the Sorrow]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41584/59df0967N0cd4150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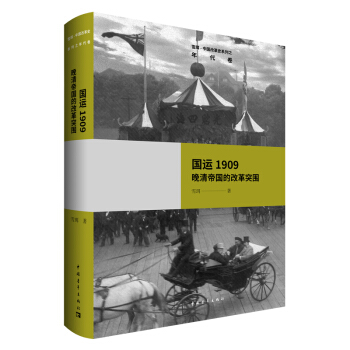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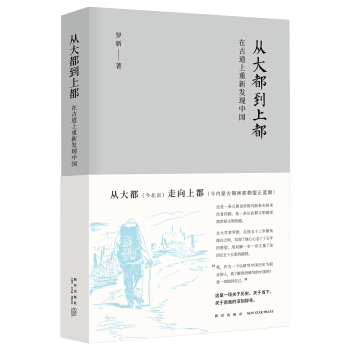

![雅典帝國的覆亡 [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43779/5a17d9f1N3d3f739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