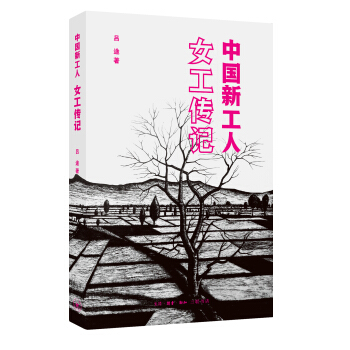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黄裳,原名容鼎昌,1919年生,山东益都人。曾做过记者、编辑、编剧。20世纪4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并熟于版本目录学。结集有《锦帆集》《关于美国兵》《旧戏新谈》《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银鱼集》《翠墨集》《清代版刻一隅》等,辑有《黄裳文集》六卷,译有《猎人日记》等。
作者简介
本书由一组主要是回忆梅兰芳、盖叫天和周信芳三人的文章组成,精彩呈现了三人在戏剧领域的艺术成就,生动记叙了一些名角们的生活轶事,并在叙述中融入了作者深挚的感情。另有一篇回忆许姬传和两篇回忆俞振飞的文章也十分精彩。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戏可分为剧本与表演,伶亦可分为人品与艺品。以黄裳先生的见闻之广,四十余年间,收入《漫忆》的名伶,不过数位,足见作者取舍之功。——张一帆
目录
《宇宙锋》——看梅兰芳的三出戏之一
关于剧本
关于表演
《醉酒》——看梅兰芳的三出戏之二
附:《醉酒》小记
《穆柯寨》——看梅兰芳的三出戏之三
《别姬》
继往开来的艺术大师
《忆艺术大师梅兰芳》序
许姬传
忆许姬传
盖叫天
和盖叫天先生在一起(上)
和盖叫天先生在一起(下)
祝贺盖老舞台上的花甲生日
谈《快活林》
重演《恶虎村》——湖上的哀思
忆盖叫天
周信芳
周信芳先生的艺术成就
怀周信芳
周信芳之死
俞振飞
“正是江南好风景”
江南俞五
精彩书摘
《宇宙锋》——看梅兰芳的三出戏之一《宇宙锋》
——看梅兰芳的三出戏之一很早就想对梅兰芳先生所表演的几出重要作品做点分析记录的工作,可是因为看戏不多,能力限制,这工作始终没有进行。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困难:记录什么?怎样记录?这两个问题始终不能解决。经过一年多以来的思索,在我自己说来,总算逐渐有些眉目了。
首先是记录什么的问题?要选择哪几出戏呢?
梅先生几十年来演出的节目,将近一百出。有很多出是我根本没有看过,或虽看过也已事隔多年,印象淡薄了的。要在这许多节目中间,选出代表作来,的确也不是容易的事。
如果从青衣、花衫、刀马旦、时装、古装、昆曲这些方面来着眼分类,自然也不失为一个方法。不过这方法多少有些“形式主义”,很难从中抓住梅先生在中国京戏舞台上达到的高度成就的精粹。
梅先生今天还经常上演的,大约有十个节目。经过仔细的思索,事实上这十个节目也就主要地概括了他几十年的舞台实践。让我们来看一下,从角色的身份说,有贵妃、丞相之女、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传奇性的女英雄,一直到市井妇女以神话人物面貌出现的白蛇。这,就主要地概括了封建社会中各个阶层的妇女人物。
再从角色的年龄来看,有十八怀春的少女,有浸淫在幸福的新婚生活中的少妇,也有十分成熟了的女性,有的还是以久历风霜、有着充足的社会经验的寡妇身份出现的。
虽然他所表演的角色如此广泛、复杂,可是这一连串人物,就她们的精神生活来说,几乎完全是一致的,她们都是在封建社会中遭受无情迫害的人物,她们都对封建社会抱着坚决反抗的心情,虽然由于出身、环境的不同,表现出来的反抗方式彼此并不一样。
这就是梅先生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的伟大的地方。他真正继承并发扬了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古典戏剧的传统,他用具体的舞台实践概括地表现了中国妇女勤劳、勇敢、热爱自由、坚韧的性格。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选择代表作的工作也许就并不十分困难和茫无头绪了。
其次,就是怎样记录的问题。这是个具体的技术问题,是更为复杂、困难也更多的。
几百年来,曾经流传下来不少曲谱(或工尺谱),是记录演员唱腔的;也流传着一些身段谱,特别是梨园抄本的曲子中间,保留的这种身段谱最多。这是记录舞台上的动作的,是专家的工作,也是戏剧工作者(内行)的工作。在我们外行说来是困难的。
我曾经尝试过仔细进行记录身段的工作,结果并不理想,顾此失彼,记录不完,最后终于达到了“眼花缭乱口难言”的地步,在最丰富多彩的地方往往没有留下一字。演后追忆,只有惘然。先前总以为是看得少,就多看几遍,其实也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追寻得愈细腻,发现得也就愈多。
曾经想向几位看梅先生戏最多的他的学生请教,结果发现这些学生也是在困惑的情况当中。因为她们都是专家内行,身段地位摸得熟了,却每每在再看一遍的时候,又发现了不同的地位与表情,很使她们无从捉摸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很好地说明了梅先生现在的表演是已经达到充分掌握了规矩,因此,突破、活用了规矩的地步。换句话说,今天他在台上,已经不完全是在演戏,他充分地使用了多少年来掌握的熟练技巧,自如地在创造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了。
自然,在许多次表演当中,不可能是完全一丝不动的。
一张照片可以复印多少张,完全不变,可是一张艺术作品,就不可能有同样的多少张,有时候看见画家展览在作品上声明可以订件,照样再画若干张的情形,总觉得非常奇怪。莫非这位画家已经改行做摄影家了吗?同样,如果要求一位表演艺术家在他每次完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时完全不走样,岂不也是同样天真的要求吗?
有一次和梅先生谈天,朋友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代表学生说出了困惑的所在。梅先生笑了,他说了很可宝贵的意见。 自然,他是不习惯用我们批评家的术语的,他说得自然、生动极了。我在台上作戏,并不能扣准了说准做到哪儿,有时候,做到了那个地方,非笑出来不可了,就笑了;有时候逼到那儿,不禁不由得就要笑,我可没有记住到这地方非笑不可。 有时候没有笑,那是当时台上的情形能早收住就早收住了。其实并不是我觉得该严肃了。他说的是《醉酒》里面一个极为细微的地方,是他的一个非常细心的学生看出来的。这正好说明了他最近演出的《醉酒》,已经不是演员在演杨玉环,而实在是杨玉环在舞台上了。我当时觉得非常感动。这岂不就是他自己说明了已经进入了角色完全浸入在角色的精神生活里面了吗?底下他又提到另外的一点:在台上演戏,有时候得看对方(指同台的演员)怎么样,有时候他使劲了,我才能用出力量来;要是他没使什么劲了,我倒拼命用力,那就不对了。他的这一段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这是说舞台上的谐和。演员必须注意这种谐和,才能替演出带来真实的感觉,不会使观众感到哪个是在突出地作戏。自然,他是不赞成某些演员的松弛的,因为这就会把整个的演出给拉下来,可是他也不能自顾自地突出,说这是前辈艺术家的风度自然可以,更应该着重的是他对现实主义表演的体会与掌握,和他对演出的整体的尊重。
这两段话对许多学习他的艺术的人说来,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已经应该在一腔一字、一个身段、一个笑靥之外,更多地注意他对整个戏剧、人物的掌握,摸索他的现实主义表演的轨迹了。
自然,这并不是否认基本动作的重要性,正相反,只有充分掌握了这样的武器之后才有条件谈到进一步的学习。这些,想在后面较详细地提到。
前言/序言
导读
张一帆
2003年,我即拜读过黄裳先生的《旧戏新谈》(开明出版社1994年8月版,以下简称“《新谈》”),近日北京出版社将黄裳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谈戏文字辑为《伶人漫忆》(以下简称“《漫忆》”),并命我撰作导读,因而找来“大家小书”版《新谈》参考,赫然发现其新序竟是黄老宗江先生所写,不觉大惊。宗江老见多识广,才情横溢,又与黄裳先生自少年同窗起,即诗酒唱和七十年,尽可随笔挥洒,尚且将其新序谦称为“佛头沾粪”,于我,则不禁更是战战兢兢,手足无措。不过,出冷汗亦能起到使人冷静思考的积极作用:宗江老的《新谈》新序写作之时,恰是我负笈京华追随周育德、钮骠、周华斌诸师研治中国戏剧史之始;以迄今积十余年之功,勉力为读者写一点自己读《漫忆》的心得,亦是对宗江先生和缘悭一面的黄裳先生的追怀与汇报吧。
一
近现代的戏剧评论能够在当时获得重大影响,至今仍然流传,与其载体是公开发表的文章有必然联系。而发表的阵地当时只有是在近现代传媒的第一种形式——报刊上,才能具有相当的受众面。而能在报刊长期发表评论的主要是报人。因此,平面媒体与报人对于近现代的戏剧评论发展乃至整个近代戏剧学科建设,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至徐凌霄、刘豁公、周剑云,下至黄裳、张之江、金庸等,兼报人与剧评家这两种身份,皆可谓既本色又当行。不知从何时开始,在戏剧界有两种极度缺乏调查数据支持的说法甚嚣尘上:年轻人不爱(懂)看戏,媒体为了追求时效而缺乏对戏剧的深入追访、人云亦云。可是上述这些近现代剧评家里,哪一位不是从少小时期就看戏、爱戏、品鉴戏、研究戏的?又有哪一位名记,不曾有自己极具个性的独立思考?黄裳先生显然是这当中继往开来、极具代表性的一代。
《新谈》原系《文汇报·浮世绘》副刊中专栏之结集,发表时黄裳先生笔名“旧史”,年尚未及而立;写作时常以正史与戏文合参,旁征博引,融通大传统与小传统,认为将“大约未必是实事”的,“写进戏中,倒也不失为绝妙的题材”,这令人想起终身热爱历史的金庸先生也说过类似的话:有的事,历史学家不喜欢,但是小说家喜欢。虽谈旧戏,且笔法老辣,但仍难掩青春元气,用句北京话来说:多少有点儿冲(音去声)。内容重在“新谈”,因为还常常结合时势,作振聋发聩之讥刺,至今垂七十年,很多感叹竟常读常新。《漫忆》的文笔更添沉稳,文风依旧犀利,完全可视作《新谈》的续篇。因此,有兴趣的读者最好是将《新谈》与《漫忆》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起来读。《新谈》写于1946-1947年,《漫忆》中的文章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文革后,这也正好代表了作者对“旧戏”(以京剧为代表)看法的三个阶段,并且,一直都在向更理性的方向发展。
中国传统戏剧,常常戏是戏,伶是伶,换言之,剧本是剧本,表演是表演,两者之优劣不可混为一谈、互相替代。黄裳先生的前辈徐凌霄认为:
因为中式戏剧的演员,负有双层表演之任务,一方面为演戏者(戏的情节意义,戏中之人之品行行为言动),一方面又为演技者(口眼身步,唱做念打,文武昆乱等)。于是新旧间之怀疑,内外行之争执,知识之多寡,功夫之深浅,相标榜相菲薄,皆为此界限不清关系不明之所致。徐凌霄�毕酚爰吉本缪г驴�,1932,4��
因而章泯先生在《新谈》首版序言中认为“只取意识,说不上懂戏”,显然,黄裳先生也是深谙此理的。当然,最为优秀的作品往往两者均好;一般来说,行家常常分而论之。《新谈》戏伶并提,尤重于谈戏与戏中人物,心中既存为普通观众提供知识之念,亦有本人心境之流露;析戏情戏理,再云对名伶表演的期待;参以时局,可谈者甚夥,因而数月之间即积成数十篇。《漫忆》主要谈伶人,且专写与之有过深入交往或深切关注的伶人,内容可与《新谈》互为补充;遇到因时势所生与舞台相似之处,同时也是作者所愤的部分,总要表达些感叹,这样的写作习惯则二著皆有,贯穿始终。
二
戏可分为剧本与表演,伶亦可分为人品与艺品。以黄裳先生的见闻之广,四十余年间,收入《漫忆》的名伶,不过数位,足见作者取舍之功。
《新谈·饯梅兰芳》中云“我想象这一个历经沧桑的人物,从《金台残泪记》时代经历若干年的风险,到现在的艺人,受多少人崇敬,盖非无因”。诚哉斯言,《新谈》的终止是由于报馆被查封,不过《文汇报》复刊后,仅时隔两年,经主编柯灵提议,编辑黄裳落实组稿,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许源来整理的我国第一部表演艺术家的自传《舞台生活四十年》得以在《文汇报》连载了一百九十七期。因之这样的前后机缘,黄裳先生对“梅派”代表作《宇宙锋》《醉酒》《穆柯寨》《别姬》的分析,不但延续了《新谈》以史征戏的传统,并且他自己还曾说过:凡是已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间提到的地方,为避免重复,不再涉及。在内容上,显然也是他在与梅兰芳先生的当面交谈以及细读《舞台生活四十年》后的绝好心得。比如,谈到梅先生说在与搭档演对手戏时:
对方这时好像有一股力量向你扑过来,使你不能不也拿出相似的“力”来和他取得平衡。和前辈演员演出,最容易提高,那道理就在此。
再比如:
梅先生现在的表演是已经达到了充分掌握了规矩,因此,突破、活用了规矩的地步。……他充分地使用了多少年来掌握的熟练技巧,自如地在创造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了。
因为“充分掌握了规矩”,所以“突破、活用了规矩”,且还常使得梅兰芳先生的学生们“无从捉摸”,这不正是“从心不逾矩,移步不换形”的又一诠释吗?
众所周知,梅兰芳先生的“移步而不换形”说在1949年秋冬之际给他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黄裳先生看来,梅兰芳的水袖、圆场,还有对小动作的讲究这些“运用得非常巧妙的程式化动作”,是“值得宝贵的经验,如果把这些看作形式主义,事实上就是给艺术创造加上偏狭的桎梏,成为不折不扣的‘封条主义’了。”(《〈宇宙锋〉——看梅兰芳的三出戏之一》)尽管这些观点是1954年发表的,但即便是到了1981年,黄裳先生的看法一仍其旧:
50年代初实际事件发生1949年11月。,他(编者按:指梅兰芳)曾试图总结多年成功失败的经验,归纳为‘移步而不换形’几个字。对此,是曾经有过不同的理解和争论的。照我的体会,他提出的是一个有群众观点的切实的改革方法。改革必须顾及群众能否接受,改革也不是推倒重来。有时表面看来缓慢,但却切实的措施反而更能收到实效。梅兰芳在这里表现了他的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稳扎稳打,决不莽撞。摘自《继往开来的艺术大师》,原载于1981年8月30日的《光明日报》。
对于“移步而不换形”说,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自可以有各自的解读,黄裳先生的“体会”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重要的参照。
由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组稿工作,使得黄裳先生与许姬传、许源来兄弟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对许氏兄弟的回忆,当然不属于“伶人漫忆”,但因为他们是长期生活在梅兰芳先生身边的文化人,即便是“琐细的小事,也只是想说明他们是生活在怎样一种文化气氛中,这是培养、滋育艺术家的十分必要的条件。”(《忆艺术大师梅兰芳》序),唯其如此,方可“使读者清晰地接触到艺术家的全人,而不只是他在舞台上的献身,同时也感染到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忆许姬传》)。
《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组稿工作可以说对黄裳先生一生的谈戏文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对周信芳,还是对俞振飞,他都主张抓住一切机会对他们珍贵的舞台经验、表演范例,“即使是一鳞片爪”(《江南俞五》),也应进行记录并流传下去。这也与他早年所云“旧戏菁英,需要多少年的淘洗,才能得到本身之精炼”构成了严密的因果关系。
三
黄裳先生惯于只写他见过、交往过的伶人,《新谈·后记》中就明确不写谭鑫培、龚云甫等当时已不在世者。作为电影《盖叫天舞台艺术》的编剧,黄裳先生与盖老的交往经历是极为难得的:《和盖叫天先生在一起》中对盖老故居燕南寄庐原貌的记实,今天的读者可在去重修后的故居凭吊时相参照;入金沙港拜访盖老,未见其人,即有引人入胜之铺垫,竟颇见京派风格;亲历盖老生圹的建设过程亦令人神往;文字是很难记述表演艺术之精妙的,而黄裳先生对盖老舞棍时的描述,硬是用他的生花之笔,在我们眼前展示了如摄像机镜头用推拉摇移、快慢切换之法般记录的立体运动影像,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并忍不住要大篇幅引用,提前以飨读者:
起初他舞得很慢。棍在他手掌里转动,在前身转动,交叉着转动。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的手腕是怎样扭转的;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棍是怎样服帖地在他的五指中间盘旋。从右手交到左手,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着旋舞的棍影,有背花,有穿过跳跃的脚步的抡动,有大的旋转。像一把折扇,可以打开,可以闭拢。自然,旋律是愈来愈快的,棍影包围了他的全身, 组成了一个浑圆的个体。(我想,飞机的螺旋桨发动起来以后就会造成这种印象的吧。)
随着棍的飞舞,身体的各部位自然也有着激烈的变化,可是我的注意力却完全没有被引导到这方面去,只感到棍的旋律和舞棍者身体的转动是糅合在一起的,这已经完全成为一整体。节奏的控制极为自然,每一个段落的开始和终结,都衔接得恰好。像看一幅名画似的,跟随着棍影的回旋,堕入了沉醉当中。
此后诸多细节的回忆还给今天留下了极有历史价值的资料:不但记录了盖老对戏曲电影的思考以及对表演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还还原了拍电影时,本计划拍摄《洗浮山》,后改为《七星聚义》,以及《恶虎村》则完全被“慎重”地“暂时不宜拍摄”的过程,在梳理这些问题的原因时,黄裳先生即便到了花甲之年,仍然保持着写作《新谈》时坚毅的锐气:
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笼罩着文艺界的那种无形的压力。有勇气突破它的人是很少的。不过今天还能听到一种说法,一些老艺人解放后因为思想觉悟提高,所以自动放弃了一些“不良剧目”。这是不能为世人感到奇怪的,至少是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盖老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用亲身经历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的并不确切摘自黄裳写于1979年7月的《重演恶虎村——湖上的哀思》。。
四
无论是《新谈》,还是《漫忆》,都能看得出,作为剧评家的黄裳,十分尊重伶人,其实,这也就是尊重剧评家自己。剧评家可以是伶人之师,但更好的角色是与伶人相互尊重、信任,能与之说真话的诤友。宗江老曾说“真有这样的感觉:一位师友去世了,像是自己的一部分,跟别人谁也说不清的一部分,和他一起死去了,但似乎又有他的一部分活在了自己身上,也难为人细道了。火种萧军//黄宗江�币帐跞松�兮�北本�:中华书局,2008�薄蹦盐�人细道的是哪一部分呢?可能是指记忆、精神、创作方法等不易随肉体陨灭而消失的东西。从一个方面理解,可拿梅兰芳的代表作《贵妃醉酒》为例,“经过几十年的加工,《醉酒》已不再是他从师傅那里接下来的《醉酒》了”(《继往开来的艺术大师》);从另一方面理解,梅兰芳、盖叫天、周信芳、俞振飞等已逝,他们活生生的艺术经验与为人之道,有黄裳之《漫忆》记之;黄裳已逝,后人仍可读其《漫忆》并生可慕、可思,大约这样也是一定意义上的薪尽火传。
黄裳先生曾这样总结盖叫天对待文化艺术遗产的态度:首先,他热爱、尊重前人的劳动;其次,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再次,有着高度的艺术欣赏水平。“这种对待文化遗产的朴素态度是值得佩服的。”(《和盖叫天先生在一起》)这不仅是盖叫天的态度,也正是黄裳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对于今人而言,这种态度,不仅值得佩服,而且值得深思:假如不尊重前人劳动,假如没有多方面的兴趣,假如缺乏高度的艺术欣赏水平,会是什么结果?与其说是态度,不如说是成为合格艺术家与剧评家的必备素质。
从事专业戏剧研究的人们自然会对黄裳先生笔下涉及戏剧的文字格外感兴趣,其实,这些既优美,又平实的文字不但也可为大众带来知识,还能带来美的享受。
2016年10月31日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极具张力,像极了一场精心编排的戏码,高潮迭起,却又在最关键处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尽的回味空间。我发现,作者对于人物心绪的捕捉,达到了近乎残忍的精准。那些伶人在台上光芒万丈,台下却常常是孤独的。书中有一段关于一位武生在戏班解散后,如何努力适应现代生活的描写,那种从“一呼百诺”到“无人问津”的巨大落差,被作者用极其克制的语言写了出来,没有煽情,但字里行间全是叹息。它迫使读者去思考,当一个人的全部价值都被定义在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上时,一旦角色消失,他本人还剩下什么?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回忆录”范畴,更像是一部探讨“身份认同危机”的深度小说。我喜欢这种不把话说死的写法,它尊重读者的智力,允许我们自行去填补那些留白之处。读完后,我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不断回放那些模糊不清的旧照片般的场景。
评分坦白说,这本书的结构稍微有些跳跃,不像传统传记那样线性叙事,它更像是散落的、被时间冲刷的珍珠被重新串联起来。这种“漫忆”的方式,恰恰是它迷人之处。它没有刻意去构建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而是展现了人性中各种复杂的面向——有光辉的艺术成就,也有私德上的瑕疵与挣扎。特别是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戏曲艺术如何被卷入时代洪流的描述,视角独特而犀利。作者似乎对“失语者”群体抱有深切的同情,那些在历史转折点上不得不放弃自己毕生所学的艺术家们,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挣扎,被这本书细致地记录了下来。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查阅历史背景资料,因为书中提及的事件和人物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这本书与其说是在记录伶人,不如说是在用伶人的命运折射一个时代的变迁,厚重而深刻。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风格是极其考究的,透露出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但又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书卷气。它像一壶陈年的老茶,初品可能觉得味道有些酽,但细品之下,回甘悠长,韵味无穷。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作者在描述唱腔和身段时,大量运用了非常形象化的比喻,使得不熟悉戏曲的我也能“听见”和“看见”那些繁复的动作和高亢的声调。比如形容某位老生的嗓音时,用了“仿佛是枯木逢春后,深埋地底的泉眼被重新凿开”这样富有画面感的句子。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整本书的质感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它不是那种快速消费的读物,更像是需要静下心来,在一个阳光洒落的午后,伴随着一杯热茶慢慢品味的精品。读完之后,我甚至开始对一些老戏的唱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便是阅读一本好书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收获。
评分这本书成功之处在于,它打破了我们对“名角儿”的刻板印象。在世人眼中,他们是舞台上的神祇,但在这部作品里,他们首先是活生生的人,有着对柴米油盐的焦虑,有着对爱情的渴望,有着对生死的恐惧。作者没有采取歌颂的笔调,而是采用了近乎纪实的手法,记录了他们生命中那些不那么光鲜亮丽的时刻。这种真实性,赋予了整本书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关于师徒关系的那几章,关于学艺的艰辛,关于初登台的青涩与惶恐,读来让人感同身受,甚至能感受到那种透骨的寒冷和对成功的近乎偏执的追求。这本书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艺术道路的残酷性与崇高性并存的复杂面貌。它不是轻飘飘的怀旧,而是对特定群体命运的深刻探究,读完后留下的震撼是长久且富有启发的。
评分翻开这本《伶人漫忆》,最初的感受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历史烟尘感。它没有那种刻意为之的宏大叙事,反倒是将笔触细腻地投射在那些舞台边缘、幕布之后的人生切片上。作者似乎拥有洞察时代的敏锐,却又选择了一种近乎旁观者的冷静视角,描摹着旧日梨园行的种种光怪陆离与辛酸不易。我尤其欣赏其中对于“行当”之间微妙关系的刻画,那种同行之间的惺惺相惜,偶尔夹杂着的嫉妒与倾轧,都处理得恰到好处,真实得让人心惊。读着那些关于技艺传承的段落,仿佛能闻到老戏台上木地板被汗水浸润的气味,耳边响起咿呀的腔调。它不是一本单纯的戏曲理论书籍,更像是一部关于“时间”和“角色”的哲学探讨。我们总以为戏子是活在虚假世界里的人,但这本书却让人看到,正是那些极度的“假”,才铸就了他们生命中最真实、最无法替代的价值。整体而言,这本书的文字有一种老电影的质感,色彩浓郁,对白精妙,值得反复咀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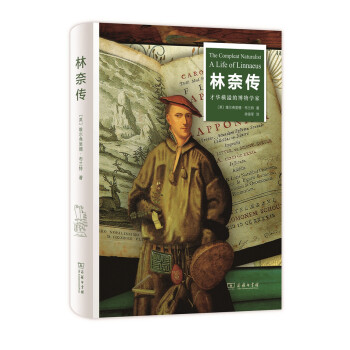





![世界上伟大的法学家/世界法学名著译丛 [Great Jurists of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77530/5a40a6a9Nac6edaa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