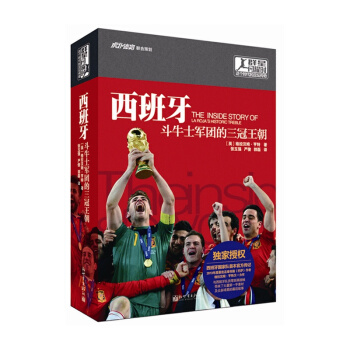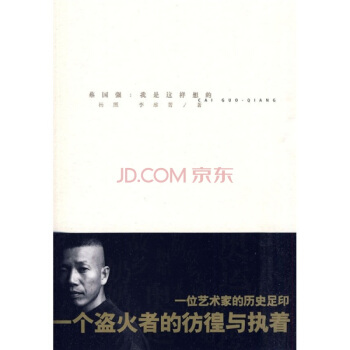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纽约占根海姆美术馆视觉艺术展参观人数的展览:2008蔡国强火型回顾展“我想要相信”。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1至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1986年赴日留学,1995年移居纽约至今。
蔡国强是国际当代艺术领域中受瞩目和具备开拓性的艺术家之一,艺术表现涉及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多媒体艺术等多个领域,尤擅以火药创作作品,对西方艺术世界产生巨大冲击力,西方媒体称之为“蔡国强旋风”。
蔡国强的艺术足迹几乎遍及所有国际大展以及著名的艺术宫殿,主要火药草图及大型装置作品也为众多优秀美术馆长久收藏。曾获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1999)、美国欧柏特艺术奖(2001)以及第20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9)等,连续多年被英国专家艺术杂志A,IRevieu,评为世界艺术界有影响力的一百位艺术家之一。
蔡国强曾受邀主持国内多项大型庆典的视觉及焰火设计,包括2001年上海APEC大型景观焰火表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视觉特效艺术演出及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焰火庆典,其中为奥运会所作的“大脚印”创意令人尤为印象深刻。
内容简介
《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内容简介:关于风水:一个人若选择相信风水,那么在相信风水的同时,等于他选择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存在。总体上我比较信仰看不见的世界,我是迷信的人。关于故乡:我总是在自己的历史中拿东西,几个资源不断地开发,像是泉州的资源,如帆船、中药、风水和灯笼。故乡是我的仓库。关于作品
做成的作品像天上出现的焰火,没有实现的只是黑夜而已。这对于艺术家来讲都是作品,都是他的人生。问题是人们仰望夜空,为的是看到绚丽的焰火,而非黑夜。
关于艺术
艺术的问题不能靠艺术解决,艺术的问题终还是要靠艺术来解决。
关于艺术家
好的艺术家不是教育的结果,好的艺术家就像好的野兽。他们知道该躲藏在树林里的哪一个角落,才能捕捉到好的猎物并且不让猎物察觉。
作者简介
杨照,本名李明骏,1963年生,作家、文化评论家。2009年任《蔡国强泡美术馆》展览总顾问。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总主笔。作品有长篇小说《大爱》、《暗巷迷夜》等,中短篇小说集《吾乡之魂》、《独自》等,文化评论集《流离观点》、《理性的人》等。李维菁,台湾大学农经系、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毕业,长期投入当代艺术观察与评论,著有《文物名家鉴藏》、当代艺术大系《商品·消费》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世界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家。——《纽约时报》
全世界有创意的一百位人物。
——美国商业杂志Fast Company
世界艺术界有影响力的一百位艺术家。
——英国艺术
目录
代序草船与借箭/陈丹青
你的风水怎么样
形势宗与理气宗/少年时期与马列/怎样变成一位艺术家呢?/去日本/去美国
奶奶
火药与创作观
寂寞
与前辈艺术家的对话
艺术家vs.当代艺术家
作品中的群众参与性,雅与俗
工作室团队
马文
失败的作品是无缘的梦中情人
策展人
女生
与台湾的缘分
艺术可以乱搞
我给自己作品的分类
蔡国强大事记
精彩书摘
“风水这件事情并不迷信。”他说过,一个人若选择相信风水,那么在相信风水的同时,等于他选择相信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存在。多数人一旦相信看不见的世界的存在,往往便会担心害怕,怕这世上有鬼,也担心不知道鬼怪会做出什么事情。蔡国强的观念不同,他对这种事情竟也有分乐观。他相信,人要相信有鬼,就必然要相信有神。
“既然有鬼,也必然会有神,不然这个世界的力量就无法获得平衡。你相信有鬼,就应该相信有神,因此不需要恐惧鬼,担心鬼的捉弄。因为你同时相信有神,便会感受到神对你的支持,行得正,自然会有感受。”
从中国到日本,再移居美国,蔡国强在国际上崛起,在日本、欧洲及美国陆续引起旋风,四处旅行参加不同国家与不同城市的展出。尤其九。年代是国际艺坛上双年展最为风行的时期,大大小小的双年展、各式各样关于文化现象的探索与宣言,频繁地出现。同样这个年代,中国艺术家的兴起又是艺坛特别关注的现象,国际策展人看好并且邀请中国艺术家广泛地参与双年展。蔡国强当年主要行程就是参加各地的国际双年展,或接受美术馆邀请去发表作品。
前言/序言
1998年,我在纽约P.S.1当代美术馆中国专展上初见《草船借箭》。它被高高悬挂在狭小的、布满砖墙的空间,木质船体的每一缝隙密密麻麻插满带着羽毛的竹箭,粗暴,沉默,而且好看。傲慢的纽约。那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有规模地被接纳、被展示,而《草船借箭》的出现,使这件制于泉州的大装置显得触目而冥顽,浑身带着彻头彻尾的陌生感。它的材质全然是异国的:一架废弃的南中国木船,一簇簇仿制的古中国的箭,那么“土”,那么“草根”,与纽约无数装置的材质——金属、塑料、泥土、石块、垃圾、纺织物、电子废料、凝固的汁液、腐朽的生命物——大异其趣。现在,犹如野蛮的闯入者,它被悬挂在纽约,像是一场被主动邀请的挑衅;而作者的思路,或者说,动机,尤其对西方主流艺术构成陌生感。日后在《纽约琐记》一份稿件中,我试图解析《草船借箭》的狡诘与攻击性:它来自纽约语境难以测知的另一维度,是一份因果置换的文本,一场角色变易的游戏,古老的传说,船与箭,巧智交作,在蔡国强手中,也在纽约,成为一则正喻而反讽的寓言。
此前,此后,我以为,蔡国强的几乎所有作品大约均可视为不同材质、不同场域、不同版本的《草船借箭》。但我不想说,蔡国强的精彩缘自谋略。是的,这一伟大的典故为他所借,然而他并不是以智谋取胜的诸葛亮;幸亏他不是。
迄今,关于蔡国强的议论与评说,包括他的自述,大抵将他的实践归结为中国资源的借取与活用。诚然,这是显而易见的,但玩弄中国牌不是他的专擅。近二十多年,太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以种种过于聪明的——抑或廉价的——方式搜刮所谓“中国资源”,并竭力探触更为广泛的西方资源,使之利用或被利用,期以兼收“船”“箭”之效,而居然奏效,果然奏效了——当我在庞大的《草船借箭》前徘徊不去,我所属意的不是作者的智谋,而是罕见的秉性,一种如今我愿称之为异常专业的“业余感”:在我所知道(而且佩服)的中国同行中,蔡国强可能是唯一一位自外于西方艺术庞大知识体系的当代艺术家。
在线试读
《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作品相关 在这本书中,我以为最可珍贵的不是艺术与观念,而是农民式的表白。除了书写者的词语,我们在蔡国强的陈述中找不到西方文论的缘引(这类被转译的话语充斥中国当代艺术文本和研讨会),不出现哪怕一位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文论家(这些人物的汉语译作是八五运动的初期圣经兼实用手册),他也不提起譬如杜尚或波依斯这样的人物(他或许从未想起他们,更不曾由知识的层面认真拜祭这些西方实验艺术的祖宗,而他供在奥运会办公室的偶像,是一具岭南的观音)。除了大量创作过程的交代,蔡国强有关艺术的陈述全都近乎业余,包括陈述的方式。用户评价
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作者的叙事方式并非线性,也不是那种按部就班的流水账。他似乎更倾向于通过一系列的“瞬间”来构建他的艺术世界,这些瞬间可能是一个闪光的想法,一个意外的发现,或者是一次深刻的体验。他没有刻意去追溯某个作品的每一个创作细节,而是更侧重于那个“想”的过程,那个灵感迸发的源头,以及这个想法如何在心中逐渐成形,最终转化为我们所见的震撼人心的作品。这种碎片化的叙述,反而更像是在解剖一团火焰,我能感受到其中涌动的热量和不规则的形态,而并非是在看一幅燃烧的地图。这种“想”的逻辑,是一种直觉式的、跳跃式的,但又充满了内在的必然性,让我仿佛置身于艺术家的大脑中,一同经历那些曲折而充满惊喜的思考路径。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本身就透露着一种沉静而强大的力量。封面没有使用过于花哨的色彩或者具象的图像,而是以一种非常简洁、抽象的方式呈现,仿佛在引导读者进入一个思考的深层空间。触感上,纸张的质感温润细腻,拿在手里,会有一种沉甸甸的、值得细细品味的仪式感。即使还没有翻开书页,光是封面和整体的触感,就已经让我对接下来的内容充满了期待。我想,这一定不仅仅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艺术画册,更像是一份精心准备的邀请函,邀请我去探索艺术家内心深处的风景,去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但却真实存在的艺术能量。我很好奇,在这样一种内敛的包装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创作哲学和生命感悟?这是一种静水流深的力量,让人忍不住想要去触摸、去感知、去解读。
评分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于“意外”和“不确定性”的探讨。蔡国强先生在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时,并没有回避那些计划之外的变数,反而将它们视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似乎并不害怕失控,而是拥抱那些在火药爆炸瞬间产生的不可预测的痕迹。这让我联想到生活本身,很多时候,我们越是试图精确地控制一切,越是会显得僵硬和死板。而书中展现的,是一种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让我在感受艺术家创作的张力的同时,也反思了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否过于追求完美和稳定,而忽略了那些偶然带来的可能性。这种对于“意外”的拥抱,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智慧,更是生活哲学的一种启示,让人看到了一种更加自由和充满生命力的存在方式。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它不仅仅是一次了解艺术家创作过程的途径,更是一次关于“思考”本身的深刻探索。蔡国强先生的语言简洁有力,充满了哲学意味,但又并非晦涩难懂,而是能够触及到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某种共鸣。他让我看到,艺术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最终呈现的作品,更在于那个孕育出作品的、复杂而充满智慧的“想”的过程。这种“想”,包含了对世界的好奇,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命本身的深刻体悟。这本书就像一个引子,让我更加渴望去深入了解这位艺术家,以及他那些充满东方哲学和普世关怀的伟大作品。
评分在阅读到关于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关系的段落时,我深受触动。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一种单向的输出,而是期待与观众之间产生一种共鸣和对话。他对于作品被解读的方式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甚至鼓励观众在作品面前进行自己的想象和联想。这种“不设限”的态度,让我觉得他的艺术不仅仅是视觉的呈现,更是一种精神的连接。他似乎在用作品搭建一座桥梁,邀请我们跨越时空,进入一个共享的感受场。这种对待艺术的态度,让我觉得非常平等和人性化,仿佛艺术家在邀请我们一同参与到一场盛大的思考和感受的仪式中,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评分代序
评分了解大牛现代艺术家的心理和创造不可错过的书哦
评分我想遇见你的人生 我想遇见你的人生¥29.30(7.6折) 做父亲的关注女儿生命的每一步是如何展开,女儿生命的每一步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父亲对自身生命的感悟和反思,母亲提供了他们父女俩生命历程中的点滴瞬间的照片,这一切都构成了人间最美的画面。 ...
评分不错 ,是本值得看的好书
评分蔡国强是国际当代艺术领域中最受瞩目和最具开拓性的艺术家之一,艺术表现涉及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多媒体艺术等多个领域,尤擅以火药创作作品,对西方艺术世界产生巨大冲击力,西方媒体称之为“蔡国强旋风”。
评分京东双十一依旧能够保持快速送达,牛
评分读了一周不到就读完了 很通畅感觉 没有难懂的东西 读起来像是在喝大米汤 甚好
评分梅塞德斯是马尔克斯的妻子。
评分书很不错,值得一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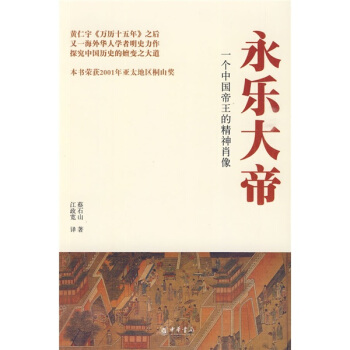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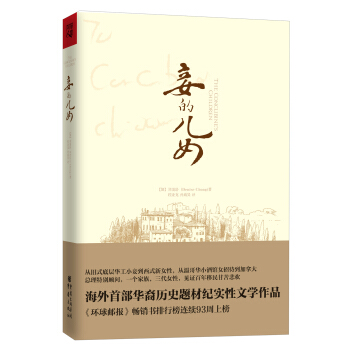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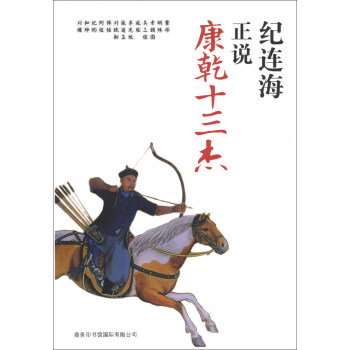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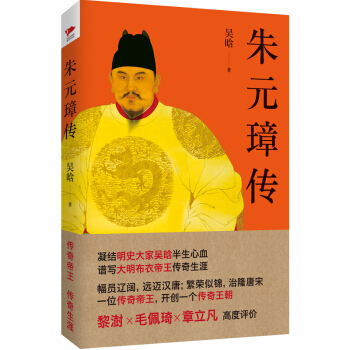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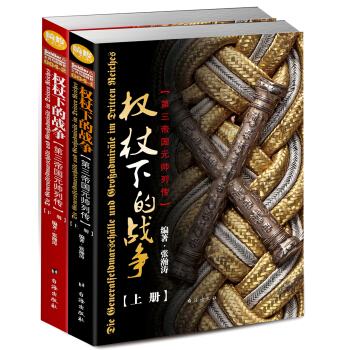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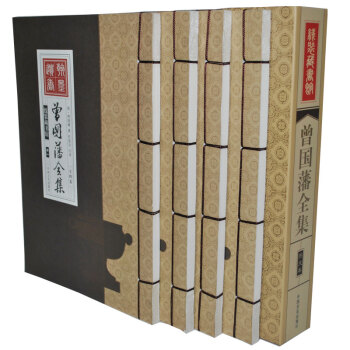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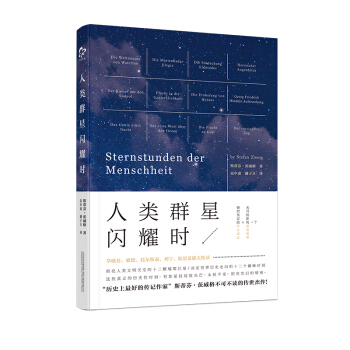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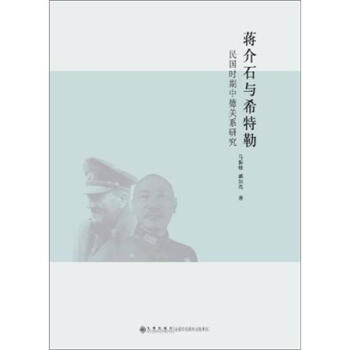
![安迪·沃霍尔自传及其私生活 [The Autobiography and Sex Life of Andy Warhol]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69306/rBEhUlKmiksIAAAAAAimcWKjbVwAAGl_ADTulEACKaJ03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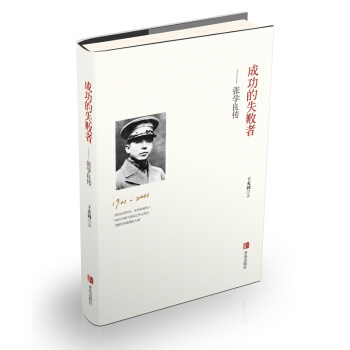
![霸王的春秋:一匡天下齐桓公 [从放纵逍遥的浪子,到叱咤风云的首霸,带您探索齐桓公“霸术”的奥秘]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45288/56a87566N529a0b5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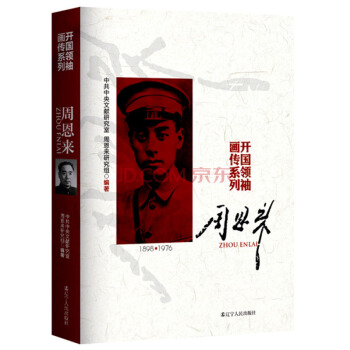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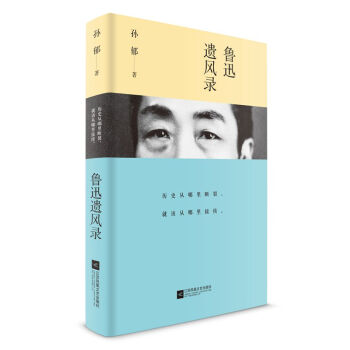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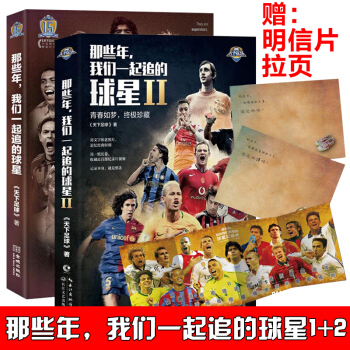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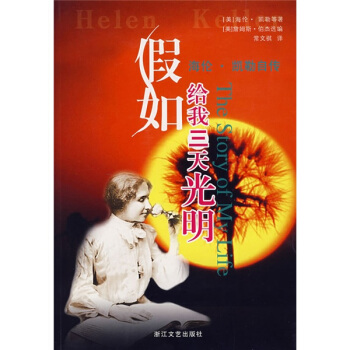
![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的人生王道 [The Last Samurai:The Life and Battles of Saigo Takamori]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317970/5fa96823-a3da-4907-af06-b0aafc25f1c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