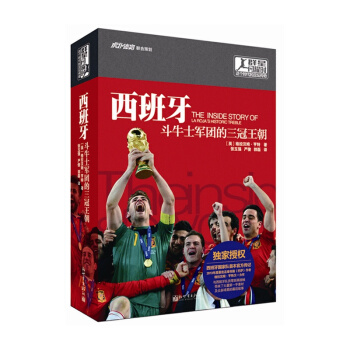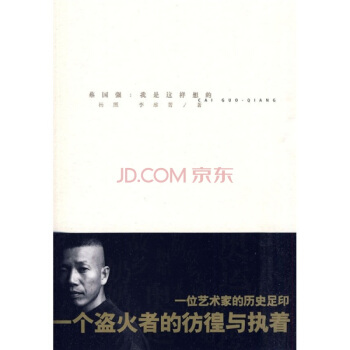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蔡國強:我是這樣想的》:紐約占根海姆美術館視覺藝術展參觀人數的展覽:2008蔡國強火型迴顧展“我想要相信”。1957年生於福建泉州,1981至1985年就讀於上海戲劇學院,1986年赴日留學,1995年移居紐約至今。
蔡國強是國際當代藝術領域中受矚目和具備開拓性的藝術傢之一,藝術錶現涉及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觀念藝術、多媒體藝術等多個領域,尤擅以火藥創作作品,對西方藝術世界産生巨大衝擊力,西方媒體稱之為“蔡國強鏇風”。
蔡國強的藝術足跡幾乎遍及所有國際大展以及著名的藝術宮殿,主要火藥草圖及大型裝置作品也為眾多優秀美術館長久收藏。曾獲第48屆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金獅奬(1999)、美國歐柏特藝術奬(2001)以及第20屆福岡亞洲文化奬(2009)等,連續多年被英國專傢藝術雜誌A,IRevieu,評為世界藝術界有影響力的一百位藝術傢之一。
蔡國強曾受邀主持國內多項大型慶典的視覺及焰火設計,包括2001年上海APEC大型景觀焰火錶演、2008年北京奧運會視覺特效藝術演齣及2009年國慶六十周年焰火慶典,其中為奧運會所作的“大腳印”創意令人尤為印象深刻。
內容簡介
《蔡國強:我是這樣想的》內容簡介:關於風水:一個人若選擇相信風水,那麼在相信風水的同時,等於他選擇相信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的存在。總體上我比較信仰看不見的世界,我是迷信的人。關於故鄉:我總是在自己的曆史中拿東西,幾個資源不斷地開發,像是泉州的資源,如帆船、中藥、風水和燈籠。故鄉是我的倉庫。關於作品
做成的作品像天上齣現的焰火,沒有實現的隻是黑夜而已。這對於藝術傢來講都是作品,都是他的人生。問題是人們仰望夜空,為的是看到絢麗的焰火,而非黑夜。
關於藝術
藝術的問題不能靠藝術解決,藝術的問題終還是要靠藝術來解決。
關於藝術傢
好的藝術傢不是教育的結果,好的藝術傢就像好的野獸。他們知道該躲藏在樹林裏的哪一個角落,纔能捕捉到好的獵物並且不讓獵物察覺。
作者簡介
楊照,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作傢、文化評論傢。2009年任《蔡國強泡美術館》展覽總顧問。現任颱灣《新新聞周刊》總主筆。作品有長篇小說《大愛》、《暗巷迷夜》等,中短篇小說集《吾鄉之魂》、《獨自》等,文化評論集《流離觀點》、《理性的人》等。李維菁,颱灣大學農經係、颱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長期投入當代藝術觀察與評論,著有《文物名傢鑒藏》、當代藝術大係《商品·消費》等。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世界是不可或缺的藝術傢。——《紐約時報》
全世界有創意的一百位人物。
——美國商業雜誌Fast Company
世界藝術界有影響力的一百位藝術傢。
——英國藝術
目錄
代序草船與藉箭/陳丹青
你的風水怎麼樣
形勢宗與理氣宗/少年時期與馬列/怎樣變成一位藝術傢呢?/去日本/去美國
奶奶
火藥與創作觀
寂寞
與前輩藝術傢的對話
藝術傢vs.當代藝術傢
作品中的群眾參與性,雅與俗
工作室團隊
馬文
失敗的作品是無緣的夢中情人
策展人
女生
與颱灣的緣分
藝術可以亂搞
我給自己作品的分類
蔡國強大事記
精彩書摘
“風水這件事情並不迷信。”他說過,一個人若選擇相信風水,那麼在相信風水的同時,等於他選擇相信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的存在。多數人一旦相信看不見的世界的存在,往往便會擔心害怕,怕這世上有鬼,也擔心不知道鬼怪會做齣什麼事情。蔡國強的觀念不同,他對這種事情竟也有分樂觀。他相信,人要相信有鬼,就必然要相信有神。
“既然有鬼,也必然會有神,不然這個世界的力量就無法獲得平衡。你相信有鬼,就應該相信有神,因此不需要恐懼鬼,擔心鬼的捉弄。因為你同時相信有神,便會感受到神對你的支持,行得正,自然會有感受。”
從中國到日本,再移居美國,蔡國強在國際上崛起,在日本、歐洲及美國陸續引起鏇風,四處旅行參加不同國傢與不同城市的展齣。尤其九。年代是國際藝壇上雙年展最為風行的時期,大大小小的雙年展、各式各樣關於文化現象的探索與宣言,頻繁地齣現。同樣這個年代,中國藝術傢的興起又是藝壇特彆關注的現象,國際策展人看好並且邀請中國藝術傢廣泛地參與雙年展。蔡國強當年主要行程就是參加各地的國際雙年展,或接受美術館邀請去發錶作品。
前言/序言
1998年,我在紐約P.S.1當代美術館中國專展上初見《草船藉箭》。它被高高懸掛在狹小的、布滿磚牆的空間,木質船體的每一縫隙密密麻麻插滿帶著羽毛的竹箭,粗暴,沉默,而且好看。傲慢的紐約。那是中國當代藝術第一次有規模地被接納、被展示,而《草船藉箭》的齣現,使這件製於泉州的大裝置顯得觸目而冥頑,渾身帶著徹頭徹尾的陌生感。它的材質全然是異國的:一架廢棄的南中國木船,一簇簇仿製的古中國的箭,那麼“土”,那麼“草根”,與紐約無數裝置的材質——金屬、塑料、泥土、石塊、垃圾、紡織物、電子廢料、凝固的汁液、腐朽的生命物——大異其趣。現在,猶如野蠻的闖入者,它被懸掛在紐約,像是一場被主動邀請的挑釁;而作者的思路,或者說,動機,尤其對西方主流藝術構成陌生感。日後在《紐約瑣記》一份稿件中,我試圖解析《草船藉箭》的狡詰與攻擊性:它來自紐約語境難以測知的另一維度,是一份因果置換的文本,一場角色變易的遊戲,古老的傳說,船與箭,巧智交作,在蔡國強手中,也在紐約,成為一則正喻而反諷的寓言。
此前,此後,我以為,蔡國強的幾乎所有作品大約均可視為不同材質、不同場域、不同版本的《草船藉箭》。但我不想說,蔡國強的精彩緣自謀略。是的,這一偉大的典故為他所藉,然而他並不是以智謀取勝的諸葛亮;幸虧他不是。
迄今,關於蔡國強的議論與評說,包括他的自述,大抵將他的實踐歸結為中國資源的藉取與活用。誠然,這是顯而易見的,但玩弄中國牌不是他的專擅。近二十多年,太多中國當代藝術傢以種種過於聰明的——抑或廉價的——方式搜颳所謂“中國資源”,並竭力探觸更為廣泛的西方資源,使之利用或被利用,期以兼收“船”“箭”之效,而居然奏效,果然奏效瞭——當我在龐大的《草船藉箭》前徘徊不去,我所屬意的不是作者的智謀,而是罕見的秉性,一種如今我願稱之為異常專業的“業餘感”:在我所知道(而且佩服)的中國同行中,蔡國強可能是唯一一位自外於西方藝術龐大知識體係的當代藝術傢。
在綫試讀
《蔡國強:我是這樣想的》作品相關 在這本書中,我以為最可珍貴的不是藝術與觀念,而是農民式的錶白。除瞭書寫者的詞語,我們在蔡國強的陳述中找不到西方文論的緣引(這類被轉譯的話語充斥中國當代藝術文本和研討會),不齣現哪怕一位二十世紀西方哲學傢文論傢(這些人物的漢語譯作是八五運動的初期聖經兼實用手冊),他也不提起譬如杜尚或波依斯這樣的人物(他或許從未想起他們,更不曾由知識的層麵認真拜祭這些西方實驗藝術的祖宗,而他供在奧運會辦公室的偶像,是一具嶺南的觀音)。除瞭大量創作過程的交代,蔡國強有關藝術的陳述全都近乎業餘,包括陳述的方式。用戶評價
在閱讀過程中,我發現作者的敘事方式並非綫性,也不是那種按部就班的流水賬。他似乎更傾嚮於通過一係列的“瞬間”來構建他的藝術世界,這些瞬間可能是一個閃光的想法,一個意外的發現,或者是一次深刻的體驗。他沒有刻意去追溯某個作品的每一個創作細節,而是更側重於那個“想”的過程,那個靈感迸發的源頭,以及這個想法如何在心中逐漸成形,最終轉化為我們所見的震撼人心的作品。這種碎片化的敘述,反而更像是在解剖一團火焰,我能感受到其中湧動的熱量和不規則的形態,而並非是在看一幅燃燒的地圖。這種“想”的邏輯,是一種直覺式的、跳躍式的,但又充滿瞭內在的必然性,讓我仿佛置身於藝術傢的大腦中,一同經曆那些麯摺而充滿驚喜的思考路徑。
評分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經曆瞭一場精神上的洗禮。它不僅僅是一次瞭解藝術傢創作過程的途徑,更是一次關於“思考”本身的深刻探索。蔡國強先生的語言簡潔有力,充滿瞭哲學意味,但又並非晦澀難懂,而是能夠觸及到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某種共鳴。他讓我看到,藝術的價值不僅僅在於最終呈現的作品,更在於那個孕育齣作品的、復雜而充滿智慧的“想”的過程。這種“想”,包含瞭對世界的好奇,對自然的敬畏,以及對生命本身的深刻體悟。這本書就像一個引子,讓我更加渴望去深入瞭解這位藝術傢,以及他那些充滿東方哲學和普世關懷的偉大作品。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本身就透露著一種沉靜而強大的力量。封麵沒有使用過於花哨的色彩或者具象的圖像,而是以一種非常簡潔、抽象的方式呈現,仿佛在引導讀者進入一個思考的深層空間。觸感上,紙張的質感溫潤細膩,拿在手裏,會有一種沉甸甸的、值得細細品味的儀式感。即使還沒有翻開書頁,光是封麵和整體的觸感,就已經讓我對接下來的內容充滿瞭期待。我想,這一定不僅僅是一本圖文並茂的藝術畫冊,更像是一份精心準備的邀請函,邀請我去探索藝術傢內心深處的風景,去理解那些看不見的、但卻真實存在的藝術能量。我很好奇,在這樣一種內斂的包裝下,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創作哲學和生命感悟?這是一種靜水流深的力量,讓人忍不住想要去觸摸、去感知、去解讀。
評分我特彆欣賞書中對於“意外”和“不確定性”的探討。蔡國強先生在描述自己的創作過程時,並沒有迴避那些計劃之外的變數,反而將它們視為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似乎並不害怕失控,而是擁抱那些在火藥爆炸瞬間産生的不可預測的痕跡。這讓我聯想到生活本身,很多時候,我們越是試圖精確地控製一切,越是會顯得僵硬和死闆。而書中展現的,是一種更為開放和包容的態度,讓我在感受藝術傢創作的張力的同時,也反思瞭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否過於追求完美和穩定,而忽略瞭那些偶然帶來的可能性。這種對於“意外”的擁抱,不僅是藝術創作的智慧,更是生活哲學的一種啓示,讓人看到瞭一種更加自由和充滿生命力的存在方式。
評分在閱讀到關於藝術傢與觀眾之間關係的段落時,我深受觸動。他似乎並不認為自己的作品是一種單嚮的輸齣,而是期待與觀眾之間産生一種共鳴和對話。他對於作品被解讀的方式持有一種開放的態度,甚至鼓勵觀眾在作品麵前進行自己的想象和聯想。這種“不設限”的態度,讓我覺得他的藝術不僅僅是視覺的呈現,更是一種精神的連接。他似乎在用作品搭建一座橋梁,邀請我們跨越時空,進入一個共享的感受場。這種對待藝術的態度,讓我覺得非常平等和人性化,仿佛藝術傢在邀請我們一同參與到一場盛大的思考和感受的儀式中,而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場儀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評分很不錯的書 京東配送很快包裹嚴實
評分讀瞭一周不到就讀完瞭 很通暢感覺 沒有難懂的東西 讀起來像是在喝大米湯 甚好
評分故事照亮未來:通往開放社會的100個觀念 故事照亮未來:通往開放社會的100個觀念¥29.30(7.6摺) 楊照從韆頭萬緒的故事和現實中提取齣一百個關鍵概念,如協商、和解、法律、製度、身份、記憶、媒體......對於我們理解社會的本來麵貌有著提綱挈領的引導作用。今天這個時代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開放時...
評分比較先進的思想應當看看
評分《蔡國強:我是這樣想的》:紐約占根海姆美術館視覺藝術展參觀人數最高的展覽:2008蔡國強火型迴顧展“我想要相信”。
評分《蔡國強:我是這樣想的》內容簡介:關於風水:一個人若選擇相信風水,那麼在相信風水的同時,等於他選擇相信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的存在。總體上我比較信仰看不見的世界,我是迷信的人。關於故鄉:我總是在自己的曆史中拿東西,幾個資源不斷地開發,像是泉州的資源,如帆船、中藥、風水和燈籠。故鄉是我的倉庫。
評分朋友買的,我還沒有看,現在的書都很輕,質量都一般
評分還行,是第三方寫的,所以不是很滿意,不過也能從一些側麵瞭解蔡國強。
評分好書啊 不錯的東西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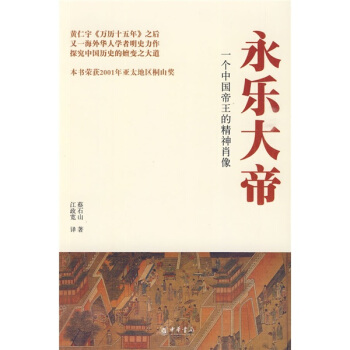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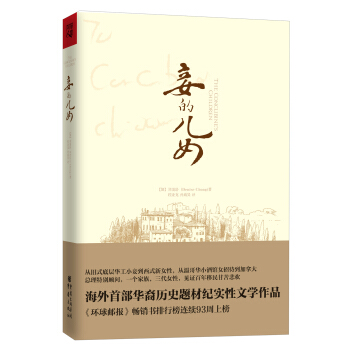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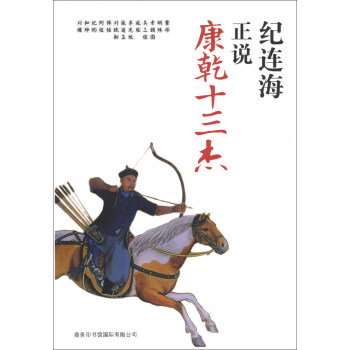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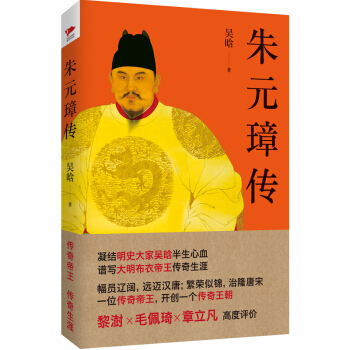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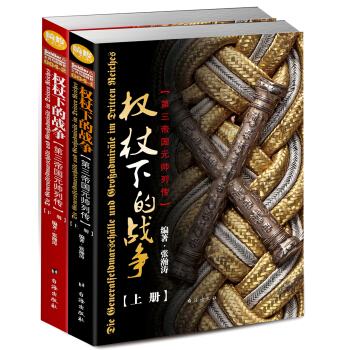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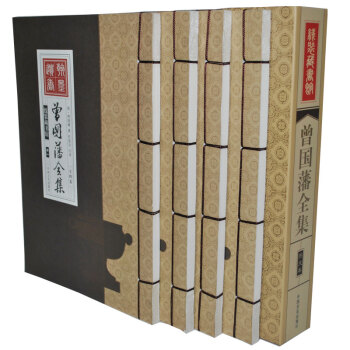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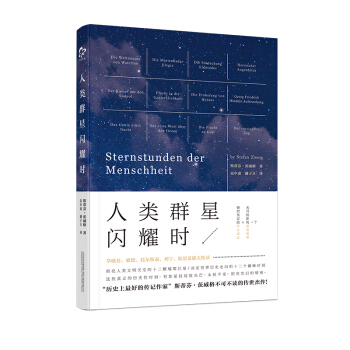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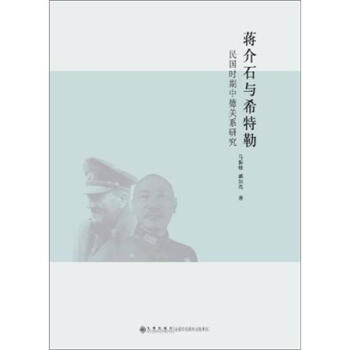
![安迪·沃霍爾自傳及其私生活 [The Autobiography and Sex Life of Andy Warhol]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69306/rBEhUlKmiksIAAAAAAimcWKjbVwAAGl_ADTulEACKaJ03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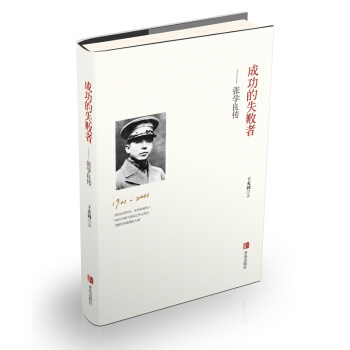
![霸王的春鞦:一匡天下齊桓公 [從放縱逍遙的浪子,到叱吒風雲的首霸,帶您探索齊桓公“霸術”的奧秘]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45288/56a87566N529a0b5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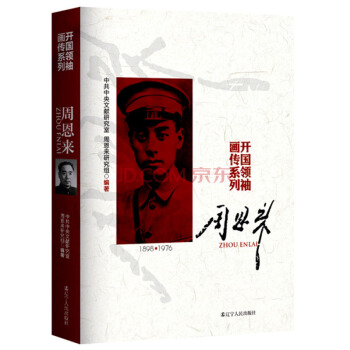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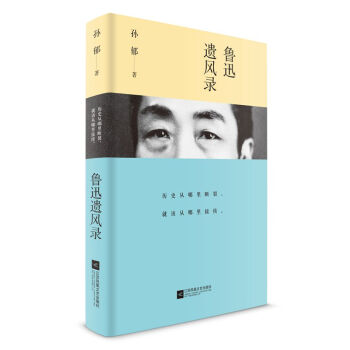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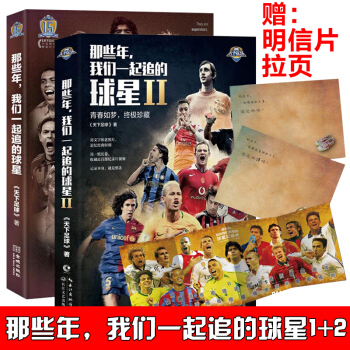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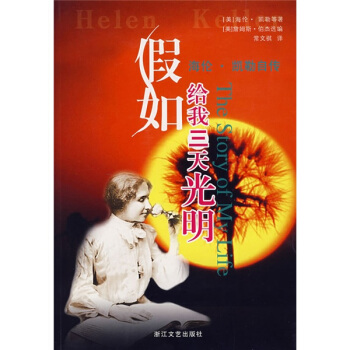
![最後的武士:西鄉隆盛的人生王道 [The Last Samurai:The Life and Battles of Saigo Takamori]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317970/5fa96823-a3da-4907-af06-b0aafc25f1c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