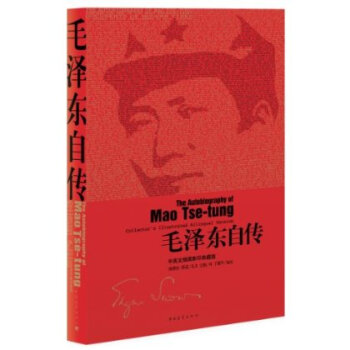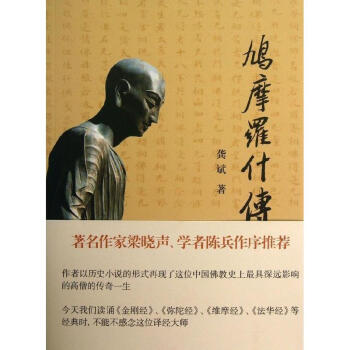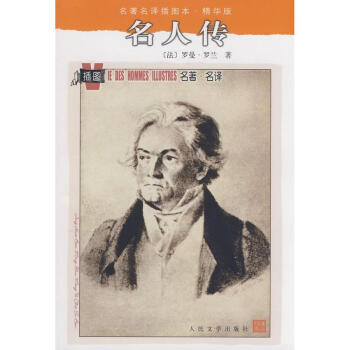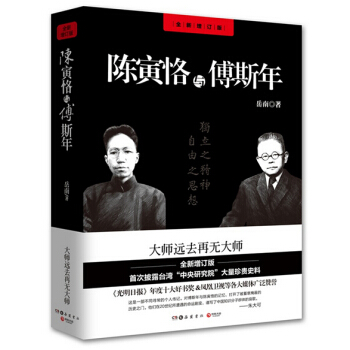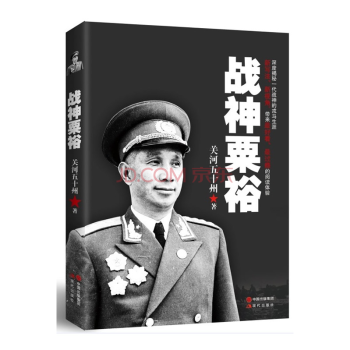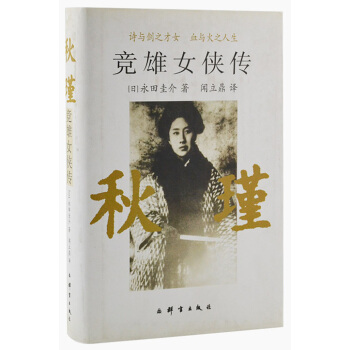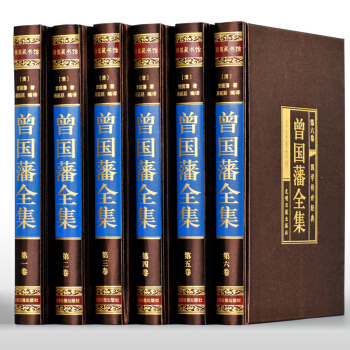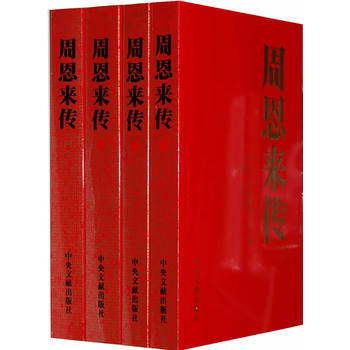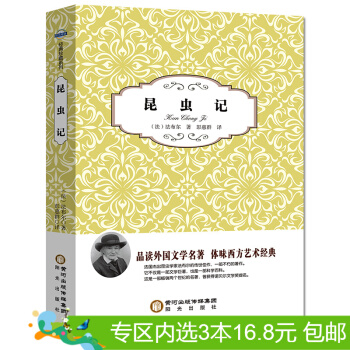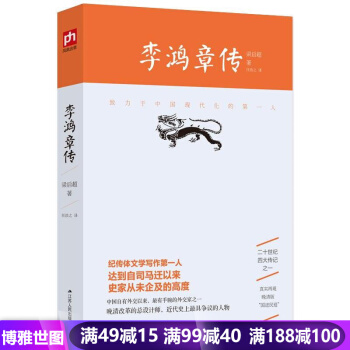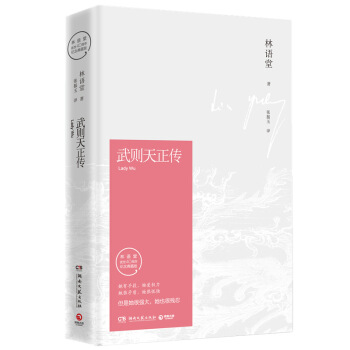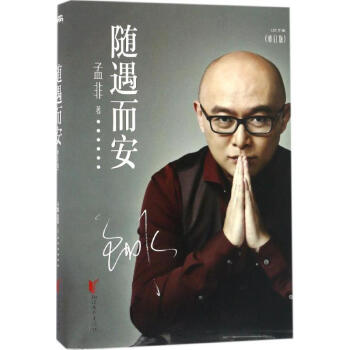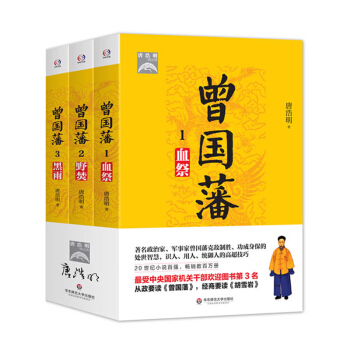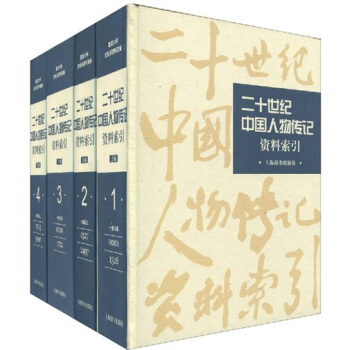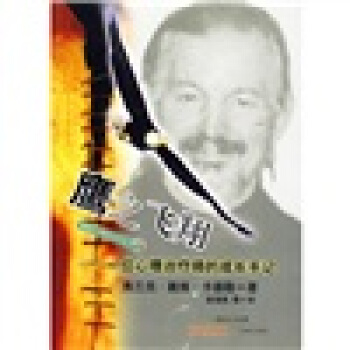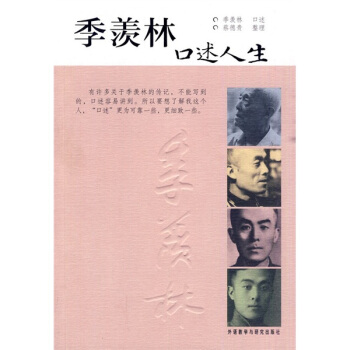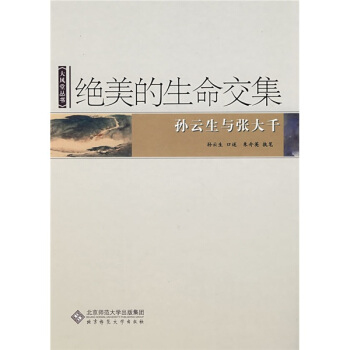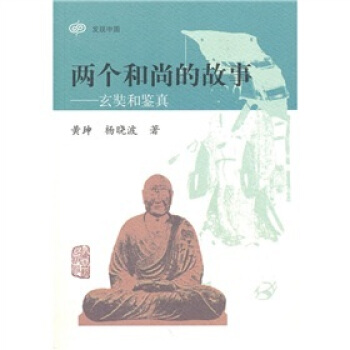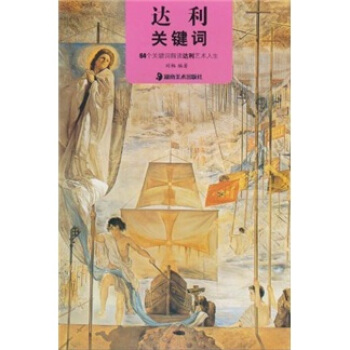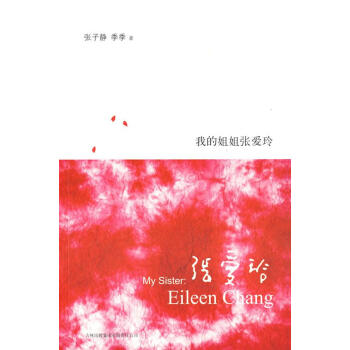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同一个秋千架上的童年,截然两种的人生旅途,张爱玲唯一的弟弟回忆姐弟身世,家庭变故,人世沧桑……内容简介
《我的姐姐张爱玲》是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先生,以亲历亲闻的特殊身份,回忆姐姐张爱玲的家庭、生活经历和所接触的人和事。同一个秋千架上的童年,截然两种的人生旅途,张爱玲唯一的弟弟回忆姐弟身世,家庭变故,人世沧桑……姐姐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得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姐姐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姐姐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无解之谜。(张子静)
想起张爱玲,总是想起钻石。因为张爱玲的光芒,是一种钻石的光芒。钻石棱角分明,也耀眼迷离、昂贵稀有,也夺人魂魄。张爱玲无须佩戴钻石,她本身就是一粒钻石……一粒钻石了政治魔障,穿越了时光隧道,在写过《封锁》也被封锁过的中国大地,再度熠熠生辉……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她的钻石光芒,我看到的,是那地层之下的无尽煎熬。(季季)
作者简介
张子静,1921年生于上海市,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肄业,曾任职中央银行扬州分行、无锡分行,1949年后在上海浦东郊区任小学语文教师及中学英文教师,1968年底自黄楼中学退休。季季,本名李瑞月,台湾省云林县人,1945年生。1963年省立虎尾女中毕业,放弃人学联考参加救国团文艺写作研究队,获小说组比赛冠军。1964年3月月开始专业写作,6月成为一批皇冠基本作家。专业写作十四年。1988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作家。1978年进入新闻界服务。曾任《联合报》副刊组编辑;《中国时报》副刊组主任兼《人间》副刊卡编;时报出版公司副总编辑;《中国时报》主笔。2005年2月自《中国时报》退休。出版小说《属于十七岁的》、《异乡之死》、《拾玉镯》;散文《夜歌》、《摄氏20-25度》;传记文学《我的姐姐张爱玲》(张子静合著)、《休恋逝水——顾正秋回忆录》等十余册。丰编1976年、1979年、1986年、1987年年度小说选(尔雅版),1982年台湾散文选(前卫版)等十余册。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姐姐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得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姐姐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姐姐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无解之谜。——张子静
想起张爱玲,总是想起钻石。因为张爱玲的光芒,是一种钻石的光芒。钻石棱角分明,也耀眼迷离、昂贵稀有,也夺人魂魄。张爱玲无须佩戴钻石,她本身就是一粒钻石……一粒钻石了政治魔障,穿越了时光隧道,在写过《封锁》也被封锁过的中国大地,再度熠熠生辉……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她的钻石光芒,我看到的,是那地层之下的无尽煎熬。
——季季
目录
前言如果我不写出来
一章 家世
张家、李家、黄家、孙家
第二章 童年
成长与创伤
第三章 青春
逃出我父亲的家
第四章 早慧
发展她的天才梦
第五章 成名
命中注定,千载一时
第六章 盛名
约稿被拒始末
第七章 萎谢
悲壮与苍凉
第八章 永别
离婚与离国
第九章 故事
《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
第十章 结局
败家与解放
附录一 我与张爱玲的垃圾
附录二 张爱玲生平?作品年表
初版后记
寻访张子静,再见张爱玲
新版后记
梦幻城堡仰望钻石城堡囝
张爱玲为什么要销毁《小团圆》
精彩书摘
一章 家世·张家、李家、黄家、孙家“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浑沌。”
——张爱玲《烬余录》(一九四四年二月)
以前评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提到她的显赫家世。这可能因为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家世比她更显赫。我们的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我们的祖母李经(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李鸿章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无日不在要津。签订《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都是这位北洋大臣的“功绩”。中外人士提起清末政治人物,李鸿章的知名度,可说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要详析我姐姐的家世,不应止于父系的张家和李家。母系的黄家——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孙家——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也都间接或直接地对我姐姐有所影响。或许因黄、孙两家较不为人知,评介我姐姐的文章几乎从未提到他们。我们要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就不能有所偏差,留下缺憾。所以,开头的一章,我要介绍张家和李家,也要介绍黄家和孙家。
张佩纶才大心细,词锋可畏,可惜性格躁进。
我的祖父张佩纶(一八四七—一九○三),字幼樵,原籍河北丰润。他才思敏捷,自视甚高;有笔如刀,恃才傲物,因而在官场得罪了不少人,弄得中年罢官,抑郁以终。
祖父早年生活贫困,苦读出身。我的曾祖父印塘(一七九七—一八五四),字雨樵,曾任安徽按察史。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于一八五三年返回安徽办团练,"与印塘曾共患难"。这是我祖父后来成为李鸿章东床快婿的原因之一。
一八五四年,印塘因积劳成疾,逝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那一年“佩纶方七岁,转徙兵间十余年,操行坚卓,肆力为经世之学”;一八七○年(二十三岁)中举;次年登进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一八七五年升侍讲,任“日讲起居注官”,直谏朝政,声誉日隆。后来并擢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内则不避权要,外则论议锋厉,满朝侧目。
我祖父看到清末的政治腐败,一心为国;个人则为官清廉,生活穷困,常吃稀饭。据曾朴在《孽海花》中所述,他在大和殿大考,一挥而就,首先交卷。不日发榜,名列榜首。当时京中对他的批评是“词锋可畏,是后起的文雄”;“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他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洪钧登门道贺,家中竟没米煮一锅干饭待客,只得叫仆人拿棉袍去典当,买些菜、饭回来。
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息者惟佩纶一人。
洪钧未上门之前,本就有米店来讨债,弄得狼狈不堪。受此刺激,他想到“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哪一点儿不如人,就穷到如此?”又听说“浙闽总督纳贿买缺”,“贵州巡抚侵占饷项”;还有“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便夹着一股愤气,写了一封奏折。次日消息见报,轰动满京城。
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采,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刻六部,那回刻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
——《孽海花》
那时慈禧垂帘听政不久,为了树立开明君主的形象,广开言路,博采众议,笼络人心。我祖父的犀利文笔,得到当时军机首辅—恭亲王—奕和另一位军机李鸿藻(李石曾之父)的赏识,逐步升至侍讲署佐副都史。
《清朝野史大观》里说,当时京中和祖父一样勇于直谏的还有张之洞、陈宝琛、潘祖荫、宝廷、黄体芳、刘恩溥、邓承修等人:“号曰清流……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巩带夕褫,举国为之震竦……丰润喜着竹布衫,士大人争效之……”他们并在明儒杨福山的故宅“松筠庵”设了一个"谏草堂",有什么论列就集合在那里讨论。
我祖父当时参奏的案子,轰动的是户部尚书王文韶核准云南报销受贿六百万两和另一位京官大员万青藜昏瞆颟顸,滥竽朝政。结果王文韶被罢官回原籍,万青藜也被免职。
另外他也上了很多有关军事、国防的奏折。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
但祖父与“清流党人”的勇于直言,到底得罪了很多人,埋下他日后被罢官的祸根。
赴马尾上任,“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
一八八四年中、法军在越南起冲突,我祖父与清流党人竭力主战。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不愿轻启战端,委曲求全仍然交涉失败。法国不仅侵占了越南,而且窥伺台湾,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以为威胁。山西、北宁陆续失守之后,国威大损,慈禧震怒,就撤了奕的军机首辅之职,改以她的妹婿醇亲王奕任军机首辅。其中的一位军机大臣孙毓汶就向奕出谋划策,把清流党的几位主将都派到外省任官,以免他们的直言在京干扰朝政。张之洞被派为广东总督,陈宝琛也以南洋大臣会办海防事宜派到广东。我祖父则以三品钦差大臣会办海疆大臣的名义被派到福建马尾督军。
又有一说是李鸿章很赏识这位故旧之子的文采,见他时常发表有关军事、国防的高见,以为他能文又能武,想借此机会厚植他的实力,以为来日北洋大臣的继任人选。祖父出京前去向慈禧叩别,聆听圣训,慈禧也对他的才干训勉有加,寄予厚望。所以“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
“以词臣而任军机”,不战而败,颜面尽失。
那时我祖父正当英年(三十七岁),踌躇满志,“以词臣而任军机”,也颇想有一番作为。
但他并无军事、国防的实务经验。放言高论和实际执行到底有一段距离。他带着慈禧的圣训和李鸿章的厚勉南下,志得意满,眼高于顶,没把那些地方官放在眼里。对于福建巡抚张兆栋、船政大臣何如璋的实务建言不予理睬,仅靠北京来的上谕和李鸿章的电报作为他布置战守的依据。终致中法之战马尾一役,不战而败,张佩纶"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海上失了基隆,陆地陷了谅山",颜面尽失。《孽海花》里对此有如下之描述:
仑樵左思右想,笔管儿虽尖,终抵不过枪杆儿的凶;崇论宏议虽多,总挡不住坚船大炮的猛,只得冒了雨,赤了脚,也顾不得兵船沉了多少艘,兵士死了多少人,暂时退了二十里,在厂后一个禅寺里躲避一下。等到四五日后调查清楚了,才把实情奏报朝廷。朝廷大怒,不久就把他革职充发了。
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猪蹄,别来无恙。
关于马尾败战的羞辱,直到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还有唐振常先生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张佩纶徒事空谈》的文章。文中有言:“战之先,佩纶尝作大言,谓败当以三钱鸦片殉难。及败,携猪蹄途中大嚼。于是时人为联曰: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猪蹄,别来无恙。”
这段话是否属实,只有留待史家考证。作为张家的后代,看到时人撰文仍如此嘲讽祖父,我的感觉自是很难堪的。
回到天津未及半月就订妥姻缘。
一八八四年我祖父被发配到边寨张家口,继室边粹玉与元配朱芷芗(卒于一八七九年)所生之子志沧、志潜(仲照)并未随行。他在塞上读书著述自遣。当时所读多为汉晋隋唐诸子百家,并写成《管子学》二十四卷。一八八六年,边粹玉在京病逝,一八八八年戍满,李鸿章于二月十七日“分俸千金,以资归葬”。我祖父乃于四月十四日返抵津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致函台湾巡抚刘铭传,提到我祖父与其女的婚事:“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由是观之,我祖父返津未及半月,就与李鸿章的女儿李经(菊耦)订妥姻缘。那年我祖父四十一岁,祖母二十二岁。
《孽海花》里说,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为了他要把有才有貌的女儿许配给一个相差十九岁的“囚犯”做继室,曾经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哭闹着不愿认这门亲。但李菊耦对母亲说:“爹爹已经许配,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他的夫人也只好罢了。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曾朴在《孽海花》里,形容我的第三祖母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编按:指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并引了两首我祖母作的诗来印证她的才华,说我祖父就是见了这两首诗,对她倾倒不已。
一首
基隆南望泪潜潜,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璋谁教使狄山;
宵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第二首
痛哭陈辞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前言/序言
张爱玲散文集《流言》的一篇文章是《童言无忌》,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的《天地》月刊。那篇文章共有五个子题:钱、穿、吃、上大人,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叫,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进:“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篮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2
张爱玲笔下的那个“很美”而“没志气”的弟弟,就是我。
我今年七十四岁,住在上海市区的一间小屋里;是个退休十年的中学英文教员。
我姊姊发表《童言无忌》那篇文章时,二十四岁,是上海红的专业作家;我二十三岁,因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尚未正式工作。那时看到姊姊在《弟弟》里对我的赞美和取笑,并投有高兴,也没有生气。甚至看到文章的结尾:“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那时,我也没有悲哀。
我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姊姊,当然更没有她的聪慧和灵敏。到了二十多岁,许多事也还是鲁钝的;没有大的快乐,也没有深的悲哀仿佛只是日复一日麻木地生活着。在那上海“孤岛时期”的末期,我中断学业,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有的只是永远烟雾迷蒙的家:—堆仆人侍候着我那吸大烟的父亲,以及我那也吸大烟的后母。我那时心情的茫然和苦闷,是难以言说的。所以,对于姊姊在文章里的取笑,除了麻木以对,又能如何?在我们那个没落了的、颓靡的家里,是看不见—点儿希望的。而我姊姊,一九三八年逃出我父亲的家后就昂首阔步,有了她的自我世界,也终于有了她的名望——只有她,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3
一九九五年中秋次日,从太平洋彼岸传来我姊姊离开人世的消息。那几天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时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来。后来我找出《流言》,一翻就是那篇《童言无忌》。
重读《弟弟》,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汩汩而下了!“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了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姊姊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父亲早在一九五三年过世,和姊姊比较亲的母亲一九五七年逝于英国;姑姑也于一九九一年走了。就是和我们不亲的后母,也于一九八六年离世。但我心里并不孤独,因为知道姊姊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读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觉得亲。
用户评价
这本书名《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下子就勾起了我对文学传记的无限遐想。张爱玲,这个名字本身就自带一种传奇色彩,她的作品,她的人生,都仿佛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我的姐姐”这个视角,则让这份传奇增添了亲切感和独特性。我很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位姐姐,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张爱玲,或者说,又是怎样一位姐姐,能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这位文学巨匠?是她在张爱玲的创作道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默默支持,还是她本身也拥有着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我期待书中能够揭示她们姐妹之间的深层联结,不仅仅是血缘上的亲密,更是在精神层面的互相影响。是否她的姐姐也对文学有着独到的见解,或者在张爱玲的某些作品中,能够找到她姐姐的影子?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挖掘她们共同的成长经历,那些童年时代的点滴,那些在家族变迁中的相互扶持,那些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所共同经历的挣扎与选择。从一个至亲的视角来审视张爱玲,无疑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多元、更加真实的面貌,打破我们以往对她可能存在的单一印象。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像一幅细腻的水彩画,徐徐展开一段关于亲情、关于才情、关于那个时代的动人画卷,让我能够沉浸其中,感受那份属于姐妹之间独一无二的情感。
评分读到《我的姐姐张爱玲》这个书名,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各种可能性。作为一本文学传记,它显然会聚焦于张爱玲这位传奇女性。但“我的姐姐”这个前缀,却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奇。这究竟是张爱玲本人的视角,还是她的某位亲近的女性,以姐姐的身份来讲述张爱玲的故事?如果是前者,那么这本书无疑会是张爱玲对自己人生的深刻反思,是对自己与姐妹之间关系的梳理,可能会揭示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如果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那么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的姐姐是怎样一个人?她是如何看待张爱玲的才华,又是如何与这位才情横溢的妹妹相处的?书中的内容,是否会侧重于她们的童年回忆,那些共同经历的岁月,那些在战乱年代的相依为命?或者,她姐姐的视角会更加侧重于张爱玲在创作上的某个时期,某个重要作品的诞生过程?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解读视角,不落俗套,能够从一个非常亲近、非常个人的角度,去触碰张爱玲生命中那些柔软的、不为人知的瞬间。我想象着,在她的姐姐眼中,张爱玲也许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文学巨匠,而是那个需要照顾、需要陪伴的妹妹,是那个有着自己烦恼和快乐的普通女性。这本书,或许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具人情味、更接地气的张爱玲,一个被亲情温暖过的女人。
评分《我的姐姐张爱玲》这个书名,瞬间点燃了我对文学传记的好奇心,特别是当主人公是张爱玲的时候,这份好奇更是被放大到了极致。张爱玲,一个自带光环的名字,她的作品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而“我的姐姐”这个视角,则像是在这片星空中投下了一束来自近处的灯光,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亲近、更人性化的角度去审视这位伟大的女性。我非常想知道,在这个“姐姐”的眼中,张爱玲是怎样的?是那个在乱世中坚持创作的才女,还是那个在生活中有着细腻情感和独特见解的普通女子?书中是否会描绘她们童年时期共同度过的时光,那些细碎而美好的回忆,那些在家族变迁中相互扶持的画面?或者,她的姐姐会着重描写张爱玲在创作上的某个重要阶段,例如《倾城之恋》的构思,亦或是《半生缘》的情感刻画,而姐姐又是如何参与其中,或者扮演了怎样的倾听者和支持者的角色?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展现出,亲情与才情在张爱玲的人生中是如何交织的,她是如何在亲情的滋养下,绽放出耀眼的文学光芒。我想象着,这本书会像一幅精心绘制的人物肖像,通过姐姐的笔触,勾勒出张爱玲最真实、最动人的神情,让我们感受到,即使是文学巨匠,也终究是一个有着亲情羁绊、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女人。
评分这本书名《我的姐姐张爱玲》立刻抓住了我的眼球,让我产生了极大的阅读冲动。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巨匠,她的作品和人生本身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元素。而“我的姐姐”这个视角,更是为解读这位传奇女性增添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处理这种“姐姐”的叙事角度的?是张爱玲本人以姐姐的口吻来回顾自己的人生,还是她的某位真实的姐姐,以她独特的视角来讲述这位文学才女的成长历程?无论哪种情况,都必然会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如果是我自己,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从一个至亲的视角来审视一位伟大的作家,往往能挖掘出更深层、更隐秘的情感连接和人生轨迹。我期待书中能够描绘出,她的姐姐是如何看着张爱玲一步步走向文学巅峰的?她们之间的日常互动是怎样的?姐姐是否也曾经嫉妒过张爱玲的才华,或者更加自豪于她的成就?书中是否会触及张爱玲生活中的一些敏感话题,比如她与胡兰成、赖雅的感情纠葛,或者她晚年的孤独生活,而她的姐姐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更具象、更具温度的张爱玲形象,让读者不再仅仅是仰望一位文学神祇,而是能够走近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感波动的女性。我期待书中能够描绘出,亲情在张爱玲的人生中,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评分这本书真是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当我翻开第一页,就仿佛被一股温暖而又带着些许忧伤的力量所吸引。姐姐,这个词语本身就承载了太多情感——守护、陪伴、榜样,甚至是某种程度上无私的奉献。而张爱玲,一个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名字的女性,她的故事被置于“姐姐”的视角下,无疑会带来一种全新的解读。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在那个充满着动荡与变革的社会里,她的姐姐是怎样一位女性?她是如何看着自己的妹妹步入文坛,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她是否也曾有过文学的梦想?她与张爱玲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亲情羁绊?是惺惺相惜,还是有着无法言说的隔阂?我期待书中能够细致地描绘出她姐姐的生活片段,那些不为人知的日常,那些隐藏在著名作家光环背后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我想象着,也许在她姐姐的眼中,张爱玲不仅仅是那个才华横溢的“大作家”,更是那个需要疼爱、需要理解的妹妹。或许,这本书会通过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一个更立体、更鲜活的张爱玲,一个不再是符号化的文学巨匠,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羁绊的普通人。我希望能够在这本书里,找到关于亲情、关于成长、关于时代的独特印记,看到那些细微之处流淌出的真实情感,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评分很好
评分很好
评分满意
评分一直喜欢张爱玲,喜欢她独特、富有韵味的文字,想看看在弟弟眼中,她是怎样的一个姐姐
评分很好
评分很好
评分满意
评分很好
评分一直喜欢张爱玲,喜欢她独特、富有韵味的文字,想看看在弟弟眼中,她是怎样的一个姐姐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