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死去的家 [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41688/rBEQYVGe3XEIAAAAAAOL0zXXWTgAAB5QgJ1eOQAA4vr229.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 东野圭吾自信力作,日本销量突破60万册
★ 我是个不会笑的孩子,仿佛被孤零零丢弃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 儿时的我,已经在那个家里死去了,之后一直在等待着我回来。
★ 《从前我死去的家》是我的自信之作,却遭到了冷遇。从此,我开始以怀疑的目光看待评论家。——东野圭吾
海报:
内容简介
沙也加对小学以前的童年毫无印象。为找回记忆,她和前男友来到父亲生前常独自前往的、神秘荒凉的别墅。种种迹象表明,这幢别墅的的人似乎在二十三年前的某一天全部消失,再也没有回来。
当看到一架钢琴的时候,沙也加禁不住喃喃自语:从前我来过这里。
作者简介
东野圭吾,日本著名作家。1985年,凭《放学后》获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开始专职写作;1999年,《秘密》获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此后《白夜行》、《单恋》、《信》、《幻夜》先后入围直木奖。;2008年,《流星之绊》获第43届新风奖;;2012年,《浪矢杂货店的奇迹》获第7届中央公论文艺奖。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东野并没有描写残酷的场面,但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怖感始终包围着作品。
——东野圭吾粉丝网站
包含恐怖小说要素的、让人痴迷的杰出作品。
——推理小说盛典网站
一部没有凶杀情节的悬疑小说,但值得推荐给真正的推理小说狂热读者。
——洋泉社MOOK《名为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
精彩书摘
第一章我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一切的开始。
一听声音我便辨出了对方是谁。那带着几分稚气的独特嗓音,让我内心一阵激荡。但我还是刻意用例行的口气问:“请问您是哪位?”本来是想在她面前逞点强,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样做未免太无聊。
“噢,我是中野。”她报的不是原来的姓氏,而是结婚后改的夫姓。看来她也在以她特有的方式逞强。
“中野?”我继续装作想不起来的样子。
“啊,不好意思。我是仓桥,仓桥沙也加。”
“是你啊!”我一副终于反应过来的口气,演技拙劣。
“前几天的聚会上多承你关照了。”说完,她陷入了沉默,仿佛不知道如何接口。这也难怪,“前几天的聚会上多承你关照了”——这句寒暄本身就与事实相去甚远。_
我对着话筒轻笑了一声。“话说回来,那天我们几乎没怎么聊过呢。”
‘‘是啊。”沙也加似乎也放松了不少,“你只顾着和男同学说话,都不来我这边。”
“你还不是一样,一直在躲着我。”
“没那回事。”
“是吗?”
“是啊。”
“呵……”我拈起桌LID自动铅笔,咔嚓咔嚓地按出笔芯。难堪的沉默持续了几秒。“算了。”我说,“那你今天打电话过来是为了什么事呢?纯粹的闲聊?”
“才不是。”话筒里传来沙也加的呼吸声,虽然很轻微,但我还是察觉到她的气息有些紊乱。她下定决心似的开口道:“我有事要和你见面,你有时间吗?”
我有些惊讶,没想到她会主动提出见面。望着铅笔芯,我问道:“什么事?”
她顿了一下,回答:“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耳朵贴着听筒,我不禁开始浮想联翩。脑海里涌现出若干好似三流言情小说的故事情节,但我实在不相信沙也加会为那种事打电话找我。不过我还是问了一句:“这件事和我们俩有关系吗?”
‘‘和你没关系。”她立即否定,“是我自己的问题。不过我希望跟你谈谈,还要请你帮个忙。”不等我回答,她又抢先说道,“你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
我内心涌起强烈的好奇心,但还是按捺着继续问道:“这件事你丈夫知道吗?”
“他现在不在。”
“不在?”
“他去美国出差了。”
“这样啊。”我用食指将铅笔芯推了回去。
“不过你别误会,”她的呼吸又有些紊乱,“即使他在也无济于事。”
我沉默了,完全摸不着头脑。但从她的I〕I气里,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看来需要谨慎对待。
“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我舔了舔嘴唇,“其实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不是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见面非常危险,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是深思熟虑后才拜托你的。”
“可是……”
“求你了!”她艰难地说。我仿佛看到了她固执的模样:眼睛定定地望着远方,眼圈也泛红了。
我叹了口气,略显生硬地说:“明天下午我有空。”
“谢谢。”她回答。
从高二到大四这六年时间里,我和沙也加是一对恋人。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炽热的情话,也没有特别浪漫的回忆。不知不觉中,就已交往六年了。
为我们的关系画上句号的,是沙也加。
‘‘对不起,我喜欢上别人了。”
她没有说出‘‘我们分手吧”,只是沉默地垂下视线。但一切已尽在不言中了。我们曾经约定过,彼此不束缚对方,不向对方撒娇,想结束关系就坦白挑明。所以我虽然恋恋不舍,却也无法开口挽留。
“我知道了。,’面对低头不语的她,我只回了这一句。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重逢是在七年后的初夏,在新宿举办的高二同学会上。不可否认,我选择出席有期待见到沙也加的因素。
在会场上,我一边和长了岁数的同学们谈笑风生,一边用眼角余光寻觅她的身影。正如我期待的那样,她也来了。过去我们交往时她那纤瘦的身材,如今已有了几分女性的圆润,化妆技巧也高明了许多,成功塑造出沉稳的气质。但不经意一瞥间,我发现她依然透着少女般的危险气息,与和我交往时一般无二。确认T~--A,我终于略感安心。因为这才是沙也加的本质,失去这种特质的沙也加是无法想象的。她与人群稍稍拉开距离,保持着自己的独立领域,警惕的眼神不动声色地扫视着四周。
我感觉到她向我投来了目光。如果我当时迎上她的视线,也许我们就会攀谈起来。但我假装没注意。
同学会的气氛漸渐热烈起来,大家开始轮流发言。轮到沙也加时,我低下头,望着手上兑了水的酒杯。
四年前结了婚,现在是全职太太,这就是沙也加的近况。丈夫在贸易公司上班,很少在家一一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以前根本无法想象从她口中会听到如此平凡的话题。
“有孩子吗?”以前当过班委的女生问,这也是照例要问的问题。我喝了一口兑水后稀释的酒。
“嗯……有一个。”
“男孩吗?”
“不,是女孩。”
“几岁了?”
“快三岁了。”
“那正是最可爱的时候呢!”
对于前班委的话,沙也加没有立刻搭腔,停了片刻后,才以比刚才更轻的声音回应道:“嗯,是啊。”我不由得抬头看了她一眼,因为感觉到她的声音里隐藏着很深的痛苦。但除我之外,谁也没有发现她那轻微的不自然,下一位同学紧接着开始了发言。
沙也加取出手帕,轻按在额头上,仿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她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我又凝视了她片刻,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视线,转头望向我。这是我们那天第一次目光交会。
但只对视了片刻,我就低下丫头。
结果我和沙也加始终未交一言。回到家解开领带时,我忍不住问自己:跑这一趟究竟是为了什么?同时我也有种预感,今后恐怕再也见不到沙也加了。
但一个星期后的今天,她给我打来了电话。着不算宽敞的大厅,心里嘲笑着自己。比约定的时间整整早到了十分钟,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即将出现在这里的,已经不是那个女大学生沙也加了,她早已成为一个贸易公司职员的太太。
内心另一个声音又在反驳:不,我并没有抱任何期待,只是听到她沉重的声音,来替她排解心事而已。她不是也说过,我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
原来的声音立刻反唇相讥:这话好像让你很飘飘然,在心里反复回味嘛。连对丈夫都不能说的话,却愿意告诉我,即使已经嫁为人妇,内心依然爱着我——你不就是这样期待的吗?快死心吧!做这种无聊的梦,只会落得自讨没趣。
我根本没想那种事,我只是——
四点五十五分,沙也加出现了。
看到我,她胸口不易察觉地起伏了一下,然后走了过来。她身穿清新的浅绿色套装,内搭一件白衬衫,裙子短得让人感觉她才二十三四岁。剪的短发也很适合她,随便拍张照片就可以直接上主妇杂志封面。
“我还以为是我先到呢。”她站在餐桌旁说道,脸上泛起一丝红晕。
“我前面的事情提前结束,就先过来了。你别站在那儿,坐呀。”
她点了点头,在我对面落座,向经过的服务生点了一杯奶茶。我喝咖啡,她喝奶茶,一如当初。
“你家住在这附近?”她望着餐桌问,不时偷眼觑我。
“不是,搭电车过来要换两趟车。不过也不算很远.”
“那为什么要约在这里见面?”她转了转眼珠,打量了一下大厅。
“我只是想找个我们俩住处中间的地点,不过还是离我更近一些啊。你现在是住在等等力吧?”
听我这样一说,她不禁微微瞪大眼睛,应该是对我知道她的住处感到意外。其实这是前几天她在同学会上说的,我听后便记在了心里。这时她似乎也想起了这件事,唇边露出一抹微笑。
“我还以为我讲话的时候你没听呢。”
“那我讲的话你没听吗?”
“听了,你好像正在积极打拼啊。”
说到这里,沙也加点的奶茶送过来了。等她喝了一口,我问道:“我家的电话号码你是从哪儿打听来的?”
“是工藤告诉我的。”
“我猜就是。”
工藤是同学会的组织者,那家伙从前就很热心,一到节日盛会更是活跃。他也知道我和沙也加过去交往过,这回沙也加找他要我的电话,难免会让他浮想联翩。这一点沙也加不可能想不到,但她依然不管不顾,看来果然有很要紧的事情。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放到她面前。
“你住在练马区?”她端详着名片问。
“因为我想离大学近一点嘛。”我任职的大学位于丰岛区。
“理学院物理系第七讲座“……和那时候一模一样呢。”
“唯一的长进就是多了个助教的头衔。”我自嘲地哼了一声。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探讨了“家”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存在的空间,更是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载体,甚至是某种原罪的见证所。故事中构建的世界观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你不得不相信,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里,那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是真实发生过的。角色们面对的困境,与其说是外部的灾难,不如说是源自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我个人尤其喜欢那种宿命感,那种清晰地知道结局可能并不美好,但角色依然义无反顾地走向它的悲剧美学。它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恐怖”之外的“不安”,那种源自生命本源的对未知的敬畏与恐惧,让人在合上书本后,会下意识地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
评分坦白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它拒绝提供廉价的娱乐性。它更像是一场对读者心智耐力的考验。情节推进缓慢,大量留白的处理方式,要求读者必须主动参与到故事的建构中去。如果你期待的是那种一气呵成的快节奏叙事,可能会感到不耐烦。但如果你愿意沉浸其中,与那些幽暗的氛围和模糊不清的真相共处,你会发现它回报给你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它成功地在“叙事性”和“氛围营造”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让故事在保持其神秘性的同时,也拥有了足够的情感重量。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细嚼慢咽才能体会其深意的作品,绝对不是可以随意翻阅的背景读物。
评分从文学技法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语言是极其考究的,带着一种古典的韵味,但又不失现代的锐利。它不像某些作品那样追求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追求每一个词语的准确性和画面感。作者善于运用意象,比如特定的光影、某件器皿的残缺,来象征人物内心的某种状态或某种命运的转折点,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达到了极高的水准。阅读的过程需要一定的专注力,因为很多关键信息都不是通过对话直接传达的,而是隐藏在环境描写和角色内心独白之间的缝隙里。初读时可能会觉得有些晦涩,但一旦抓住作者设置的“情绪脉络”,便会发现其精妙之处。它更像是一部需要被反复品味的艺术品,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感悟。
评分这本小说的开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座迷雾笼罩的老宅,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陈旧气息。作者对于环境的描摹简直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每一个角落、每一件家具,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那种压抑、沉重却又带着一丝奇异的吸引力,让人忍不住想深入其中一探究竟。叙事的节奏处理得非常巧妙,时而缓慢得像是滴水穿石,让人能充分体会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与不安;时而又骤然加速,抛出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悬念,让你心跳加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张弛有度的叙事手法,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沉浸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尽管故事的基调略显阴郁,但字里行间又流淌着一种对“记忆”与“存在”的深刻探讨,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思考,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
评分读完这本书的感受,颇有一种在迷宫中穿行的体验,不是那种单纯的路线错综复杂,而是情感和时间线索的交织错位。叙事者似乎总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游走,用一种近乎诗意的、略带疏离的笔触描绘着那些被时间磨损的片段。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那些细微的情绪波动,那些未曾说出口的遗憾,都被捕捉得淋漓尽致。这不是那种直白地告诉你“这个角色很痛苦”的小说,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场景和潜意识的流动,让你自己去感受那份深入骨髓的孤独和迷茫。每一次翻页,都像是在解开一层又一层包裹着核心秘密的薄纱,但每一次揭开,似乎又引出了更深层次的疑问。它探讨的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一种关于“失落”的哲学命题,读完后劲十足,久久不能散去。
评分东野其实应该相信一下日本那些评论家。。这故事写的好生平庸。中间有一段想走一下黑暗路线,感觉好生硬,非常没看头。东野圭吾的书我从来都不是当做推理小说来看的。而对我来说,推理也只不过是阅读中的副业,要表达的更重要的东西,是随着推理的深入而一步步明了的。从看《嫌疑犯X的献身》开始我懂得了看东野圭吾小说的要义。作为推理小说,一开始就把凶手写出来,当然不是再让读者去找出凶手。甚至比起找出凶手,读者更不希望的是真正的凶手被找到。那个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杀掉无辜之人的冷血无情的石神,和那个为了保护所爱之人不惜自己犯下重罪甚至扮演跟踪狂的石神,都让我惊讶。这个人到底是有爱,还是没有爱?
评分用了几个小时就一口气看完了~日系伦理推理,很不错!
评分非常好!物流也挺快的!慢慢看认真体会
评分满意
评分喜欢看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
评分现在成了京东的忠实粉丝了,吃的呀用的呀一般都在京东买了,都不用出去逛啦,省了很多事。最喜欢京东的物流,快呀,有些东西就算贵一点,也在京东买了,京东的快递小哥服务还蛮不错的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nice
评分女儿喜欢东野圭吾的书,她特意买的。好评满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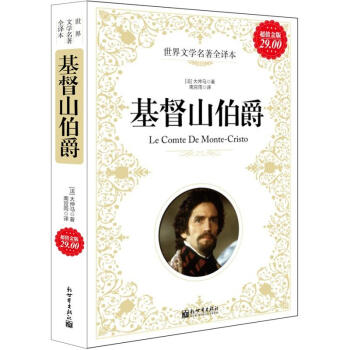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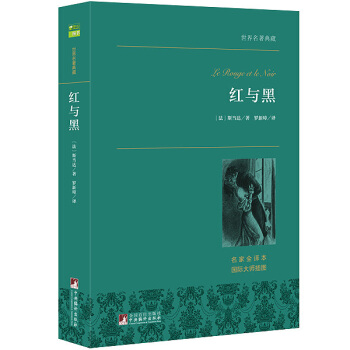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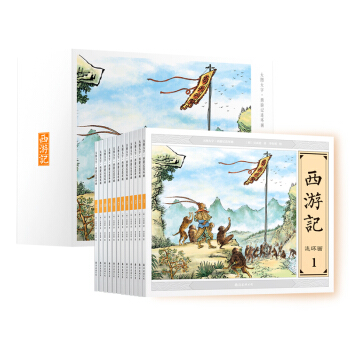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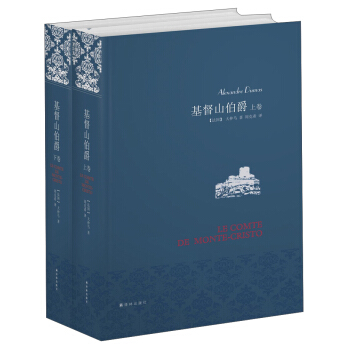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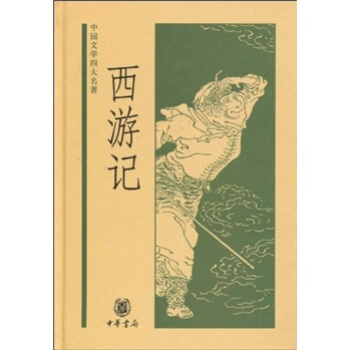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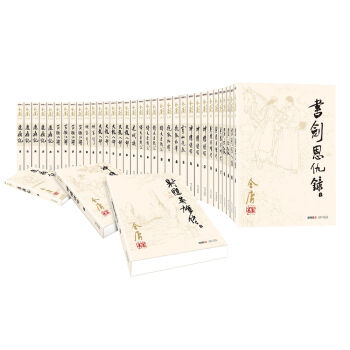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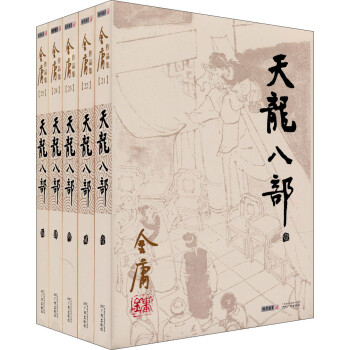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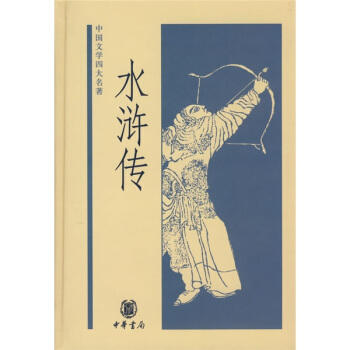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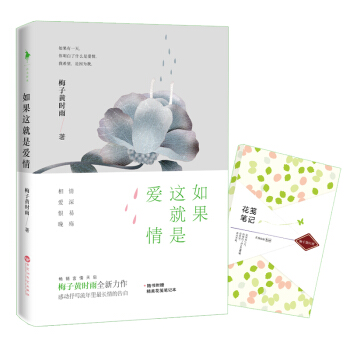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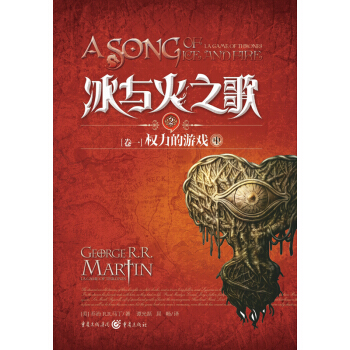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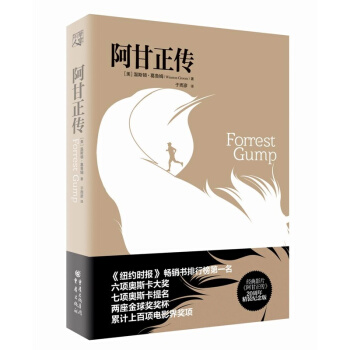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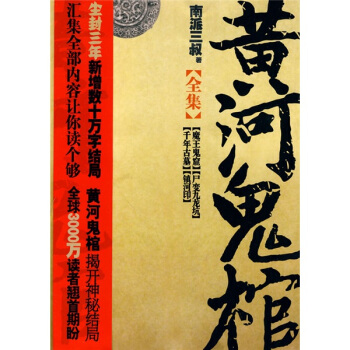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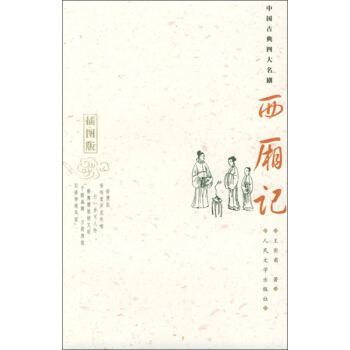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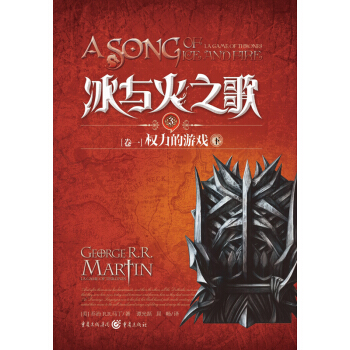

![孤儿列车 [Orphan Trai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75704/552e2952N3fb67a94.jpg)

![译文经典:一九八四 [Nineteen Eighty-fou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16272/55079ce7N29451ee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