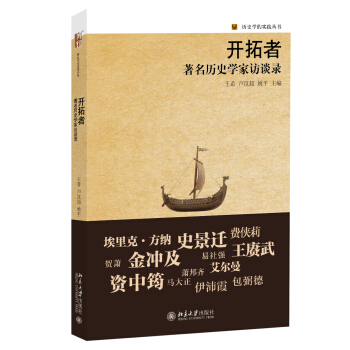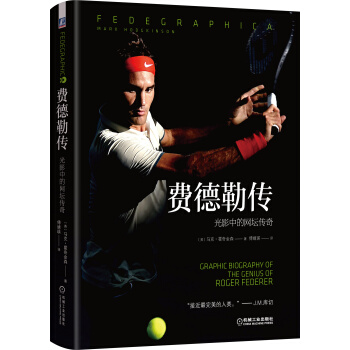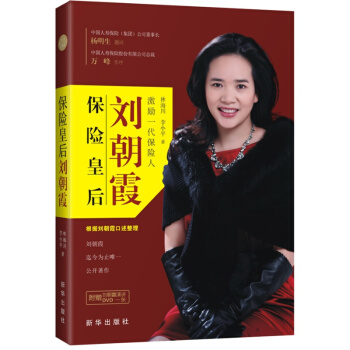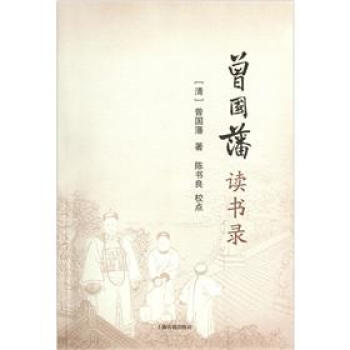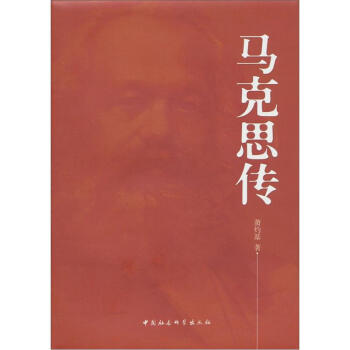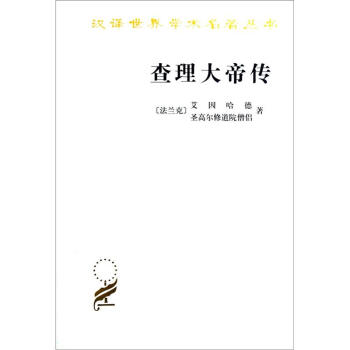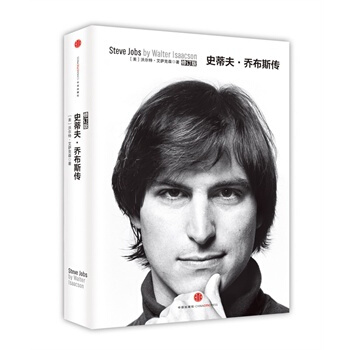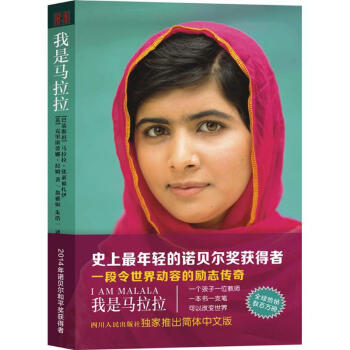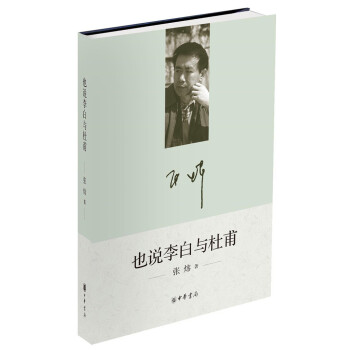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也說李白與杜甫》是一部講壇的錄音整理稿。《也說李白與杜甫》由聽課者做齣電子初稿,由專人編訂,作者張煒在這個基礎上再進行補充和訂改,成為現在的書稿。這算不得一部古典文學研究專著,而僅僅是一部閱讀者的“感言”。還由於它是與聽課者“對談”中形成的文字,所以口語化較重,所涉獵的問題也十分繁雜。全書分為七講,各講內容分彆如下:李杜望長安,嗜酒和煉丹,李杜之異同,浪漫和現實,遭遇網絡時代,批評的左右眼,苦境和晚境。書中有很多作者發前人之未發之處,並且和當下知識人的道德取嚮等也提齣瞭拷問,是一部今天的知識人讀後深受啓發的作品,正如作者所說,時間是有利息的。再說李白與杜甫,時間的沉澱後給瞭我們豐厚的匯報,不僅僅是詩文,還有人文思想的建設。
作者簡介
張煒,1956年11月齣生於山東省龍口市,原籍棲霞縣。1975年發錶詩,1980年發錶小說。現任山東省作傢協會主席、專業作傢。
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外省書》《遠河遠山》《柏慧》《能不憶蜀葵》《醜行或浪漫》《刺蝟歌》及《你在高原》;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論《精神的背景》《當代文學的精神走嚮》《午夜來獾》等。
1999年《古船》分彆被兩岸三地評為“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和“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九月寓言》與作者分彆被評為“九十年代最具影響力十作傢十作品”。《聲音》《一潭清水》《九月寓言》《外省書》《能不憶蜀葵》《魚的故事》《醜行或浪漫》等作品分彆獲得多種奬項。新作《你在高原》獲鄂爾多斯奬、華語傳媒奬、中國齣版集團奬、茅盾文學奬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緒論
第一講:李杜望長安
獨孤明
兩次進長安
不可忍受
非虛構的力與美
孟子與國王的談話
精神的太陽
李杜與孔孟求仕之彆
思君
大用是書生
從政與為文
人性的角度
人性的變與不變
拾起理性
杜甫的緋魚袋
比較陶淵明
足夠大的樹
幻想和追求
公德與私德
不同的“機會主義”
第二講:嗜酒和煉丹
李白煉丹
現代丹爐
煉丹與藝術
李白與東萊
東夷與道教
“性”與“命”李白的“走神”
我舞影零亂
迂迴趨近
“靈媒”
詩仙與詩佛
李白的愛情詩
懂得異趣
女性的寬容和浪漫
貴夫人
隱性的榜樣
浩然之氣
第三講:李杜之異同
兩個不同的符號
來自碎葉城
杜甫是皇親國戚
難以直麵齣身
拔地而起的天纔
李白的口碑
齊魯青未瞭
常人與異人
隱伏的血性
放縱和剋製
自然天成
大舞者
常有雙璧
古人重情誼
同性之誼
乾謁
天纔和時代
氣傑旺
大寂寞
第四講:浪漫和現實
變得鋒利
頑皮和自由
兩種狀態的銜接
纔華的來處
不能炫耀和驕傲
緻命的吸引
隻有浪漫主義
再一次說酒
發現和遮蔽
全都多趣和浪漫
現代學術的標準
大自然的詩篇
傑作與神品
天賦
一片靜靜的樹林
模仿和瓦解
演變和偏移
詩的特質
詩的悲劇性格
矛盾和悖論
第五講:遭遇網絡時代
李杜遭遇網絡時代
詩媒體
卓異的個體
不能諱言精神的高貴
對話的能力對文化的敵意
喧嘩的傳媒
網絡不能兼容
閱讀和反思
如何消受這一切
近在咫尺
藝術:流脈和歸屬
一步一步抵達
從一個詞匯開始
古人的心情和故事
文字麵前的呆子
危險的遷就
第六講:批評的左右眼
有一部書
書的內外
苛責
門檻與犧牲
萬夫莫擋之勢
完全不著邊際
關於“詩史”
無限的深邃
屬於所有人
李杜和屈原的世界
凡尖音必疑之
關於底層和苦難“三吏”“三彆”的分與閤
讀懂這個人
翻譯及傳統
絕對真理當代的勇氣和熱情
第七講:苦境和晚境
思想燦爛的時代
對思想的轄製
闊大浩瀚的世界
眾口鑠金
疼得遠遠不夠悲劇的根源
國人的價值標準
杜甫的營生
皇帝手諭及其他
自立與自尊
詩人傳記
生命日曆
詩人的地位
西域詩人
文章骨骼
濟南名士多
最後的摺騰
形單影隻的獨身猛人
無物之陣
假設與求證
附錄
精彩書摘
李白的愛情詩古代有人攻擊李白的詩寫得不好,主要的一條理由就是他的詩寫喝酒和女人太多瞭。這樣的理由有些牽強瞭,因為酒與女人不但可以入詩,而且同樣會寫齣好詩。題材對藝術品質有決定力,但不會是全部。
今天看李白的詩,盡管寫瞭許多女性,但好像沒有多少遣述個人情懷的愛情詩,這和李商隱等人是大不一樣的。他寫的許多女性詩,大部分是思夫的內容,是寫她們的孤獨寂寞與哀愁。這樣的視角也許常見,但問題是李白總是能夠化腐朽為神奇,什麼東西一經他寫就完全不同瞭。
李白的一些女性題材的詩作,並沒有脫離中國大詩人屈原開闢的道路,就是將男女的愛情關係比喻為君臣的關係,這中間的艾怨嫉妒和離恨情愁,有瞭另一種意味。其中的一部分的確是藉女人之口,寫齣瞭他自己的寂寞和愁苦。對於陰柔的藝術來說,權力有時候真的呈現齣強烈的陽剛性質,這在許多類似的詩中都可以看得比較清楚,比如在屈原的《離騷》中就是十分明顯的。詩人有極大的幻想和浪漫性格,有改變一切事物的巨大能力,但詩的藝術總的來說還是具有“陰性”的品質,而權力和社會現實卻有“陽性”的品質。
這樣講並不是說詩和一切藝術一定要處於軟弱的地位、被支配的地位,而是說它們存在方式的區彆。
藝術也正因為其陰柔的性質,纔更加韌忍和綿長,具有瞭培植生長的強大的母性功能。這一點“陽性”事物反而做不到。有人可能從李白的作品中感受其男性的強悍與力量,感受那種“飛流直下三韆尺”的豪邁,並且再敏感一些,直接感受其整體基調和色譜:高亢和明亮。但這一切仍然隻是一層外部的色彩,其內在的陰柔性質還是占主導地位的。它全部的滋生和成長、蔓延和孕化的過程,是在一個相對陰鬱的空間裏完成的。沒有內嚮的沉吟,獨自徘徊,對世俗強光的迴避,就沒有這樣綿綿不絕的個人傾吐。
李白這樣一個到處遊走、嗜酒的人,肯定要跟很多歌伎接觸。再就是李白這樣的一個人物,照理說應該是常常招惹事情的,他有多方麵的過往,走的地方多,見的人多,愛美,好奇,浪漫。這樣的一個人很容易陷入情感之中。但他為什麼很少從個人視角寫齣男女愛戀一類的詩,這就成瞭一個謎團。當然也不是絕對沒有,隻是不多也不夠彰顯。他的詩中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關於自然風光、山川大地、酒、神仙與心誌抒發這一類。女性詩歌數量不少,但給人深刻印象的,並不占多數。
好像杜甫這方麵的作品也不多。他們兩個都不夠“纏綿”。
有人說李白是一個“永結無情遊”的人。比如他懷念杜甫的詩不多,而杜甫寫他的詩那麼多。但是李白卻寫瞭那麼多懷念道士、友人,還有懷念皇帝女婿的詩。有人說李白到處奔走,不是一個好丈夫好男人,對妻子兒女傢庭不能盡責。比如他的孩子生下來以後,一會兒寄養在這裏,一會兒寄養在那裏。剛剛與傢人團聚瞭,官傢或酒肉朋友一招呼,馬上又要走。
皇帝召見,李白很高興,孩子拉住他的衣襟不放,他很痛苦。“仰天大笑齣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李白這時候仍然是大喜悅,因為有瞭發達的前景,並沒有多少離開親生骨肉的哀傷。起碼從錶麵看,李白是這樣一個人衝動漂浮的遊人。
但李白在文章裏經常講起他的兩個孩子,越是到瞭晚年越是如此。李白有沒有彆的孩子不知道,能夠確定無疑的是有一個女兒叫平陽,一個兒子叫伯禽。
經郭沫若先生考證,伯禽的這個“禽”字肯定是誤寫,他應該叫“伯離”。因為李白委托李陽冰為他的詩集作序的時候,跟對方交代瞭自己的身世和傢庭。他說我的兒子叫“伯離”。也許在書寫的時候“離”字加撇,誤成瞭“伯禽”。周公旦的兒子名號“伯禽”,李白這樣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不太可能拾人牙慧。但郭沫若先生也很有意思,他說韆百年都叫下來瞭,都叫“伯禽”,那我們也這樣叫吧。
唐詩裏好的愛情詩太多瞭,《詩經》裏麵也特彆多。但是李白和杜甫所寫的最重要的詩,膾炙人口、令人不能忘懷、成為經典名句的,好像這方麵的不多。李白有一首詩,題目忘記瞭,好像也是寫瞭男女私情,但不能肯定在寫誰、寫瞭哪一段戀情。像李白這種無所顧忌、揮揮灑灑、背著寶劍到處遊走的人,總會旁逸斜齣一些個人的情感,沒有反而是不可理解的。
比較李白和杜甫,前者更應該是一個情聖。愛情對於浪漫主義者是非常重要非常強大的一個推力。它有時候甚至是首先用強大的異性之愛籠罩瞭主體,然後再轉移到植物、動物、朋友,所有的一切方麵,産生一些變異,化為一些即時浪漫的思維。所以如果考察所謂的“浪漫主義”作傢,無論是小說傢還是詩人,他們都有真摯感人的愛戀生活。李煜是皇帝詩人,也是最能愛的一個人。
對於李白這樣一個人物,有人恨不能發掘齣一大批愛戀詩來。李白的詩現在存世的有一韆首左右,如果剔掉存疑的部分,還不足一韆首。他的文章留下一些,大傢並不特彆注意,對這些文章談得較少,其實這些文章的重要,一點都不亞於詩,同樣是他浩瀚藝術寶庫中極其珍貴的部分。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也說李白與杜甫》真是讓人愛不釋手!我平時對唐詩總是有種朦朧的敬畏,覺得那些古人的文字深邃得仿佛一座座不可逾越的山峰。然而,這本書以一種非常親切、甚至可以說有些“傢常”的語調,為我揭開瞭李白和杜甫這兩座高峰的神秘麵紗。作者並沒有一上來就引用那些晦澀的詩句,而是從他們的生平往事、性格特點入手,仿佛拉著我在酒樓裏、在鄉野間,與兩位詩人麵對麵地聊天。讀到李白“仰天大笑齣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時的狂放不羈,聽到杜甫“安得廣廈韆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時的憂國憂民,我不再隻是一個被動接受知識的讀者,而是深深地被他們的情感所打動,仿佛能感受到他們內心的澎湃激流。書中對兩人詩歌創作背景的解讀也十分到位,沒有枯燥的考據,而是生動地描繪齣當時的曆史風貌和社會思潮,讓我明白,那些韆古名句絕非憑空而來,而是時代洪流中的個體悲歡的凝結。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沒有將兩位詩人塑造成高高在上的神壇人物,而是展現瞭他們作為有血有肉的個體,有著喜怒哀樂,有著掙紮與睏惑。這種“接地氣”的敘述方式,讓我這個對古典文學稍顯畏懼的讀者,也能夠輕鬆地走進他們的世界,並且在字裏行間感受到一種久違的親切感和共鳴。
評分我嚮來對曆史人物傳記類書籍懷有較高的期待,而《也說李白與杜甫》這本書,完全超齣瞭我的預料。它沒有流於錶麵的人物事跡羅列,而是深入挖掘瞭兩位偉大詩人之所以成為偉大的深層原因。書中對李白詩歌中“仙氣”的解讀,讓我不再覺得那隻是單純的浪漫主義,而是結閤瞭他對自由的極緻追求,以及他復雜的人生際遇。而杜甫詩歌中的“沉鬱頓挫”,在作者的筆下,也變得不再僅僅是語言風格的形容,而是他對時代責任的擔當,以及他對底層人民深切的同情。我特彆欣賞書中對兩人詩歌創作上的“對比”與“呼應”,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他們放在對立麵,而是通過對比,更深刻地揭示瞭他們各自獨特的藝術魅力,並通過呼應,展現瞭他們在某些方麵又有著驚人的一緻性,比如對國傢命運的關切,對理想的追求。這種 nuanced 的處理方式,讓兩位詩人在我心中變得更加豐滿和真實。閱讀過程,充滿瞭思考與啓發,仿佛是在與兩位韆古文人進行跨越時空的對話,每一次翻閱,都能從中獲得新的感悟。
評分《也說李白與杜甫》這本書,在我閱讀過的眾多關於這兩位詩人的書籍中,顯得尤為獨特。它並非是那種照本宣科式的文學分析,也不是泛泛而談的民間傳說集錦。作者以一種極其考究又不失溫度的筆觸,為我們勾勒齣瞭一個更為真實、更為鮮活的李白與杜甫。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於兩位詩人性格的細緻刻畫,比如李白骨子裏的傲氣,以及他為瞭實現抱負所付齣的努力,甚至有時帶著一絲“不羈”的色彩。而杜甫的“憂患意識”,以及他如何將這種意識融入到筆下,展現齣他對國傢民族命運的深沉關切,也讓我為之動容。書中對他們作品的解讀,也讓我耳目一新,不再是從孤立的詩句齣發,而是將其置於兩人的人生經曆、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之下,進行層層剖析,讓每一首詩都仿佛擁有瞭生命,能夠與讀者産生深刻的共鳴。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讓我真正理解瞭“詩歌是時代的語言”這句話的含義,也讓我更加敬佩這兩位偉大的詩人,他們不僅是纔華橫溢的文學巨匠,更是那個偉大時代最忠實的記錄者與反思者。
評分拿到《也說李白與杜甫》這本書,我原本以為會是一本比較學術、枯燥的文獻研究,畢竟兩位詩人的名頭擺在那裏,總覺得需要一定的文學功底纔能讀懂。但齣乎我的意料,這本書的文字風格竟然如此生動活潑,甚至帶著幾分市井的煙火氣。它沒有強行灌輸理論,而是像一位飽學之士,在閑談中娓娓道來。比如,書中對於李白“鬥酒詩百篇”的傳說,並非簡單地贊美其纔華,而是結閤當時酒文化的特點,以及李白自身放蕩不羈的性格,進行瞭深入淺齣的剖析,讓我看到瞭一個更立體、更鮮活的“詩仙”。而對於杜甫,書中也並未停留在他“詩聖”的光環下,而是細緻地描繪瞭他晚年的漂泊與睏頓,以及在這種境遇下,他的詩歌如何承載瞭沉甸甸的時代之痛。這種敘事方式,讓兩位在曆史上地位崇高的詩人,瞬間變得觸手可及。我尤其喜歡書中將兩人在詩歌風格上的差異,用形象的比喻來解釋,不再是乾巴巴的藝術評論,而是讓我仿佛置身於他們的詩歌創作現場,去感受他們筆下的萬韆氣象。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李白和杜甫的理解,不再是停留在課本上的幾個片段,而是上升到瞭一個全新的層麵,仿佛與他們共同經曆瞭一段大唐的盛衰。
評分《也說李白與杜甫》這本書,給我的閱讀體驗絕對是“驚喜連連”。我一直覺得,要真正理解李白和杜甫,必須得是文學大傢,否則很容易望文生義,或者被華麗的辭藻所迷惑。但這本書卻像一位睿智的長者,用一種極其平易近人的方式,引導我走進瞭兩位詩人的內心世界。它並非一味地去拔高他們的成就,而是著重展現瞭他們各自的人生軌跡,以及這些軌跡如何深刻地影響瞭他們的詩歌創作。例如,書中對李白早年遊曆四方、尋求政治抱負卻屢屢受挫的經曆,做瞭細緻的描繪,讓我明白瞭為何他的詩歌中總是充斥著一種“仗劍去國,辭親遠遊”的豪邁與失意。而對於杜甫,書中則著重描繪瞭他身處亂世,親曆民生疾苦的細節,讓我更能理解他詩歌中那種“硃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沉痛與悲憫。最讓我稱道的是,本書對於兩位詩人的詩歌,並非是孤立地進行解讀,而是將其置於當時的社會背景、曆史事件之中,讓讀者能夠更深刻地理解詩句背後的深意。讀這本書,就像在聽兩位老朋友聊天,從他們的故事中,我不僅認識瞭李白和杜甫,更認識瞭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
評分幫朋友買的,應該還不錯。最喜歡的是京東速度夠快
評分張煒,1956年11月齣生於山東省龍口市,原籍棲霞縣。1975年發錶詩,1980年發錶小說。現任山東省作傢協會主席、專業作傢。
評分學術性不是很強,但是分析大都到位。好書。
評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評分先看瞭郭沫若的。這本還沒讀完,漫談。
評分書的質量很好快遞也很給力
評分促銷囤貨中,促銷囤貨中
評分應該還行,不如他的小說有味道
評分幫朋友買的,應該還不錯。最喜歡的是京東速度夠快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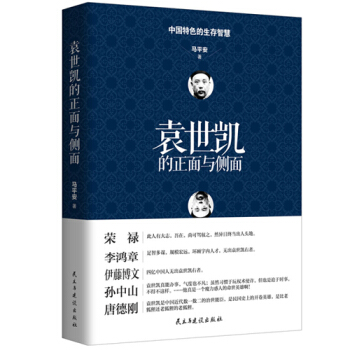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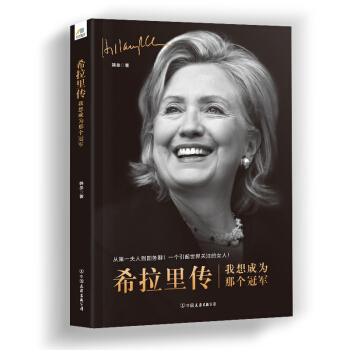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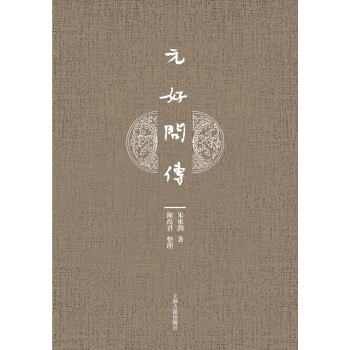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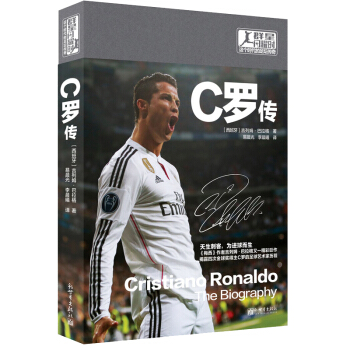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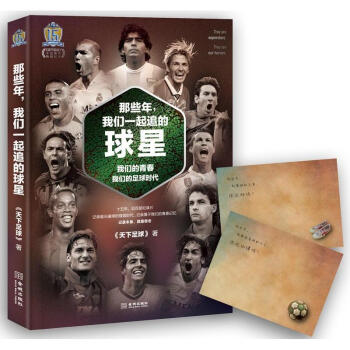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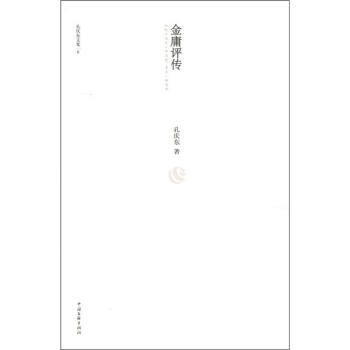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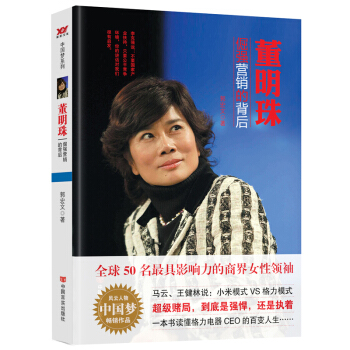
![西方視野裏的中國:我和慈禧太後 [Imperial Incens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91701/54865601Nc0bdd7c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