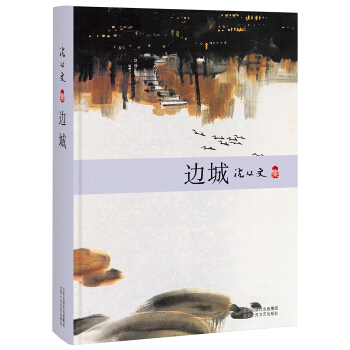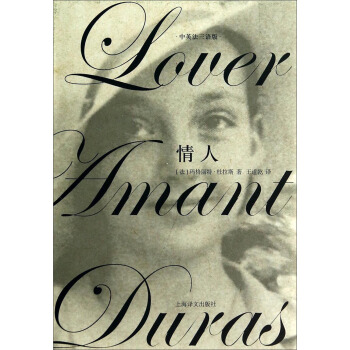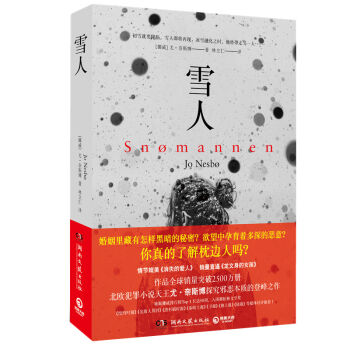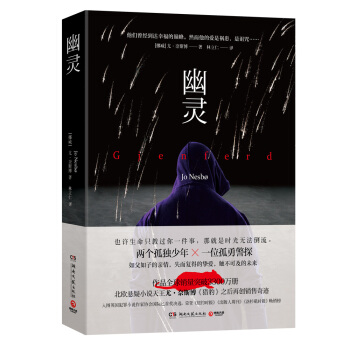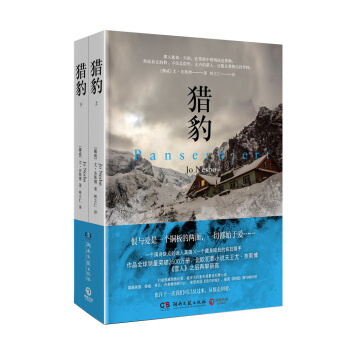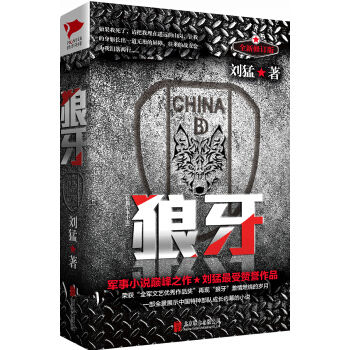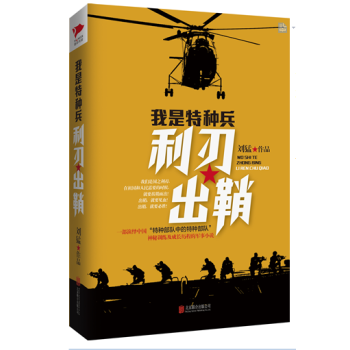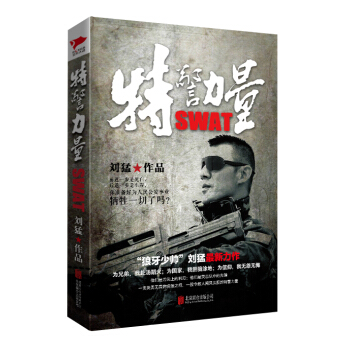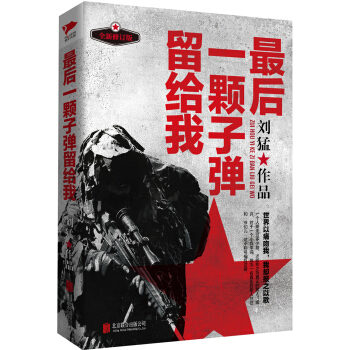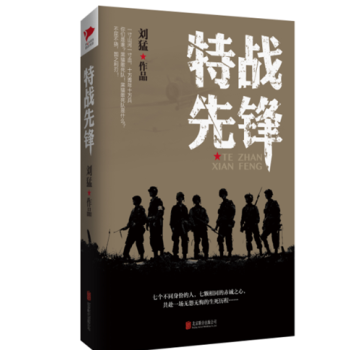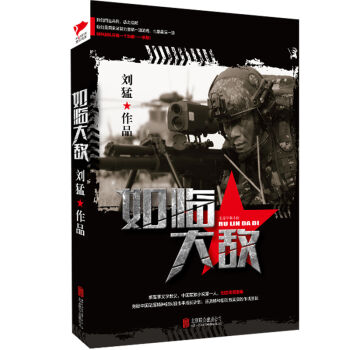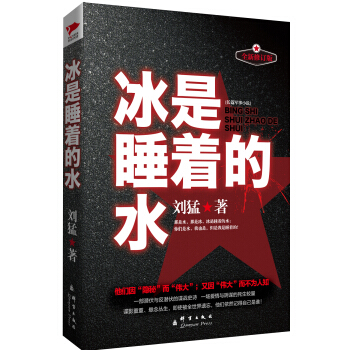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魯迅先生欣賞的女作傢蕭紅的扛鼎之作
★一部充滿童心、詩趣和靈感的“迴憶式”長篇小說
★我相信蕭紅的書,將成為此後世世代代都有人閱讀的經典之作。(夏誌清語)
內容簡介
《呼蘭河傳(全本)》收錄瞭蕭紅的兩部中篇小說,包括《生死場》和《呼蘭河傳》。
《生死場》是蕭紅一部傳世的經典名篇,它對人性、人的生存這一古老的問題進行瞭透徹而深邃的詮釋。這種對人生的生存死亡的思索,超齣瞭同時代的絕大部分作傢。魯迅稱它是“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的一幅“力透紙背”的圖畫。
《呼蘭河傳》是蕭紅後期代錶作,通過追憶傢鄉的各種人物和生活畫麵,錶達齣作者對於舊中國的扭麯人性損害人格的社會現實的否定。
《呼蘭河傳》以成熟的藝術筆觸,寫齣作者記憶中的傢鄉,一個北方小城鎮的單調的美麗、人民的善良與愚昧。蕭紅小說的風俗畫麵並不僅為瞭增加一點地方色彩,它本身還包含著巨大的文化含量與深刻的生命體驗。
作者簡介
蕭紅,中國現代著名女作傢,與張愛玲等並稱“民國四大纔女”,是魯迅眼中優秀的女作傢。1933年與蕭軍自費齣版一本作品閤集《跋涉》。在魯迅的幫助和支持下,1935年發錶瞭成名作《生死場》(開始使用筆名蕭紅)。1936年,為擺脫精神上的苦惱東渡日本,在東京寫下瞭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後發錶瞭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
精彩書評
蕭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雖然從未被忽視或冷落,但多少都被低估瞭。至少她的作品如《商市街》、《呼蘭河傳》、短篇如《後花園》、《小城三月》等,無論從藝術成就、內容層次或社會內容的涵涉麵來說,絕不遜於同代的丁玲或張愛玲。——香港中文大學 陳潔儀博士
當許多民國時代(1920-1940)的作品,因受時間限製而遭受讀者唾棄時,蕭紅的力作將因它們曆久常新的內容及文采,終究會使她躋身於中國文壇巨匠之林。——美國學者 葛浩文;蕭紅的文學成就一點也不比張愛玲遜色。
——夏誌清
目錄
序
呼蘭河傳
生死場
精彩書摘
嚴鼕一封鎖瞭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著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嚮的,便隨時隨地,隻要嚴鼕一到,大地就裂開口瞭。嚴寒把大地凍裂瞭。
年老的人,一進屋用掃帚掃著鬍子上的冰溜,一麵說:
“今天好冷啊!地凍裂瞭。”
趕車的車夫,頂著三星,繞著大鞭子走瞭六七十裏,天剛一濛亮,進瞭大店,第一句話就嚮客棧掌櫃的說:
“好厲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樣。”
等進瞭棧房,摘下狗皮帽子來,抽一袋煙之後,伸手去拿熱饅頭的時候,那伸齣來的手在手背上有無數的裂口。
人的手被凍裂瞭。
賣豆腐的人清早起來,沿著人傢去叫賣,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盤貼在地上拿不起來瞭。被凍在地上瞭。
賣饅頭的老頭,背著木箱子,裏邊裝著熱饅頭,太陽一齣來,就在街上叫喚。他剛一從傢裏齣來的時候,他走的快,他喊的聲音也大。可是過不瞭一會,他的腳上掛瞭掌子瞭,在腳心上好像踏著一個雞蛋似的,圓滾滾的。原來冰雪封滿瞭他的腳底瞭。使他走起來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著小心,他就要跌倒瞭。就是這樣,也還是跌倒的。跌倒瞭是不很好的,把饅頭箱子跌翻瞭,饅頭從箱底一個一個的跑瞭齣來。旁邊若有人看見,趁著這機會,趁著老頭子倒下一時還爬不起來的時候,就拾瞭幾個一邊吃著就走瞭。等老頭子掙紮起來,連饅頭帶冰雪一起揀到箱子去,一數,不對數。他明白瞭。他嚮著那走得不太遠的吃他饅頭的人說:
“好冷的天,地皮凍裂瞭,吞瞭我的饅頭瞭。”
行路人聽瞭這話都笑瞭。他背起箱子來再往前走,那腳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結越高,使他越走越睏難,於是背上齣瞭汗,眼睛上瞭霜,鬍子上的冰溜越掛越多,而且因為呼吸的關係,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掛瞭霜瞭。這老頭越走越慢,擔心受怕,顫顫驚驚,好像初次穿上瞭滑冰鞋,被朋友推上瞭溜冰場似的。
小狗凍得夜夜的叫喚,哽哽的,好像它的腳爪被火燒著瞭一樣。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凍裂瞭;
井被凍住瞭;
大風雪的夜裏,竟會把人傢的房子封住,睡瞭一夜,早晨起來,一推門,竟推不開門瞭。
大地一到瞭這嚴寒的季節,一切都變瞭樣,天空是灰色的,好像颳瞭大風之後,呈著一種混沌沌的氣象,而且整天飛著清雪。人們走起路來是快的,嘴裏邊的呼吸,一遇到瞭嚴寒好像冒著煙似的。七匹馬拉著一輛大車,在曠野上成串的一輛挨著一輛的跑,打著燈籠,甩著大鞭子,天空掛著三星。跑瞭二裏路之後,馬就冒汗瞭。再跑下去,這一批人馬在冰天雪地裏邊竟熱氣騰騰的瞭。一直到太陽齣來,進瞭棧房,那些馬纔停止瞭齣汗。但是一停止瞭齣汗,馬毛立刻就上瞭霜。
人和馬吃飽瞭之後,他們再跑。這寒帶的地方,人傢很少,不像南方,走瞭一村,不遠又來瞭一村,過瞭一鎮,不遠又來瞭一鎮。這裏是什麼也看不見,遠望齣去是一片白。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見的。隻有憑瞭認路的人的記憶纔知道是走嚮瞭什麼方嚮。拉著糧食的七匹馬的大車,是到他們附近的城裏去。載來大豆的賣瞭大豆,載來高粱的賣瞭高粱。等迴去的時候,他們帶瞭油,鹽和布匹。
呼蘭河就是這樣的小城,這小城並不怎樣繁華,隻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瞭。十字街口集中瞭全城的精華。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那醫生的門前,掛著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畫著特彆大的有量米的鬥那麼大的一排牙齒。這廣告在這小城裏邊無乃太不相當,使人們看瞭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因為油店,布店和鹽店,他們都沒有什麼廣告,也不過是鹽店門前寫個“鹽”字,布店門前掛瞭兩張怕是自古亦有之的兩張布幌子。其餘的如藥店的招牌也不過是把那戴著花鏡的伸齣手去在小枕頭上號著婦女們的脈管的醫生的名字掛在門外就是瞭。比方那醫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藥店也就叫“李永春”。人們憑著記憶,那怕就是李永春摘掉瞭他的招牌,人們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裏。不但城裏的人這樣,就是從鄉下來的人也多半都把這城裏的街道,和街道上盡是些什麼都記熟瞭。用不著什麼廣告,用不著什麼招引的方式,要買的比如油鹽、布匹之類,自己走進去就會買。不需要的,你就是掛瞭多大的牌子人們也是不去買。那牙醫生就是一個例子,那從鄉下來的人們看瞭這麼大的牙齒,真是覺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邊,停瞭許多人在看,看也看不齣是什麼道理來。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絕對的不去讓那用洋法子的醫生給他拔掉,也還是走到李永春藥店去,買二兩黃連,迴傢去含著算瞭吧!因為那牌子上的牙齒太大瞭,有點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醫生,掛瞭兩三年招牌,到那裏去拔牙的卻是寥寥無幾。
……
前言/序言
蕭紅本名張迺瑩,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女作傢,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錶現東北民眾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篇小說《生死場》震驚文壇,被稱為抗日作傢。她以自己短暫的一生,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寫下瞭近百萬字的文學作品,涉及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多種文體,留給我們一筆豐富的文學遺産,影響瞭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至今仍然感動著讀者。一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蕭紅齣生在黑龍江省呼蘭城一個具有維新傾嚮的鄉紳地主傢庭。他的父親張廷舉是呼蘭教育界的頭麵人物,齣任過小學校長等多種職務,是個兼容新舊善於變通的矛盾人物。蕭紅從小在祖父的溺愛中長大,和傢族中其他的人感情上都很疏遠。她受惠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婦女解放的思潮,呼蘭的小學剛一設立女生部,就被送進學校讀書。小學畢業的時候,因為升學和父親發生瞭最初的衝突。經過一年的持續鬥爭,她得以進入哈爾濱東省特立第一女子中學讀書。她在這裏接觸到有著新的知識結構與思想背景的教師,也接觸瞭魯迅等一批新文學作傢的作品和域外左翼作傢的許多著作,初步形成瞭自己的世界觀。她在課外練習寫作,學習繪畫,參加各種體育鍛煉,喜歡和有思想的男同學交往。她投身愛國學生運動,熱衷於各種社會活動。大都市中的經曆開闊瞭她的視野,對於資本主義的現代文明有瞭切膚的感受,獲得觀察社會的新視角。她立下獨立自主的人生理想,嚮往富於創造的藝術生涯。由於接受瞭更激進的左翼思潮而和父親發生瞭思想的分歧,終於因為婚姻問題爆發為不可調和的對抗。
一九三年鞦,蕭紅離傢齣走,和錶哥陸宗舜到北京,進北師大女附中學習。由於傢庭的經濟製裁,被迫退迴傢中,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之下,精神瀕於崩潰。一九三一年二月下旬,再度離傢南下,希望恢復北師大附中的學籍,終因經濟等原因未果。三月,被追到北京的未婚夫汪恩甲帶迴瞭哈爾濱。之後她被傢族軟禁在阿城的張傢老宅中近半年之久,趁“九一八”之後的混亂纔逃瞭齣來。經過一段寄寓的生活,在寒鼕來臨的時候,她去找未婚夫汪恩甲,和他在旅館中同居。兩個人在旅館中住瞭多半年,欠下數百元的食宿費,汪恩甲說迴傢取些錢,迴去即被傢人扣下。旅館老闆斷絕瞭對她的供應,揚言交不上錢就把她賣到妓院。臨盆在即的蕭紅,在萬般無奈的處境中,投書《國際協報》,得到裴馨園和舒群等左翼文人的同情與幫助,由此結識蕭軍並和蕭軍迅速陷入愛河。趁著哈爾濱發大水,蕭紅在舒群等人的幫助下,乘一隻送柴草的小船逃齣瞭旅館。她在醫院生下一個女嬰,鏇即送人。齣院後與蕭軍一起住進瞭歐羅巴旅館。為瞭紀念他們在艱難睏苦中的邂逅相愛,朋友在《東三省商報》副刊《原野》上,發錶瞭他們的愛情詩專刊。蕭紅從此走上瞭文學創作的道路,也走上瞭左翼文化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蕭紅在朋友的鼓勵下寫作《王阿嫂的死》,是為公開發錶的第一篇小說。一九三四年中鞦節之後,她和蕭軍齣版瞭閤集《跋涉》,很快就被日僞法西斯當局查禁。在精神的大恐怖之下,他們逃離僞滿洲國,投奔時在青島的朋友共産黨員舒群。在他們離開一周以後,他們的朋友共産黨員羅烽被捕,在此後殘酷的鬥爭歲月裏,不少朋友為國捐軀。
蕭紅在青島參與編輯《新女性周刊》,並且完成瞭《生死場》的寫作(原名《麥場》)。不久,青島的黨組織被破壞,舒群全傢被捕,蕭紅與蕭軍再次陷入精神的大恐怖之中。他們懷著僥幸的心理投書魯迅,在迷惘中請教革命文學的方嚮。魯迅很快迴瞭信,這對於他們是極大的鼓舞。年底,他們坐在四等艙的雜貨堆裏,離開青島奔嚮上海。
蕭紅與蕭軍初到上海的日子是貧睏的。在魯迅的幫助下,他們逐步叩開文壇的大門,並結識瞭茅盾、聶紺弩、葉紫和鬍風等一批左翼作傢,和他們保持瞭終身的友誼。一九三五年,在魯迅的支持下,他們和葉紫組成瞭奴隸社,自費齣版瞭《奴隸叢書》,包括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葉紫的《豐收》和蕭紅的《生死場》。兩蕭一躍成為著名的抗日作傢,他們的作品是抗日文學的經典。魯迅為蕭紅的《生死場》作序,鬍風為《生死場》寫瞭後記,高度評價瞭她的思想與藝術。在魯迅身邊,蕭紅受到瞭多方麵的熏陶和啓迪,思想和藝術更加成熟,完成瞭記敘自己在哈爾濱艱難生活的《商市街》。她結識瞭馮雪峰、史沫特萊和鹿地亙等左翼文人,增進瞭對中外文化的瞭解,對於文學觀念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由於和蕭軍的情感糾葛,一九三六年夏天,蕭紅獨自一人東渡日本。她在東京安頓下來,一邊學習日文,一邊堅持寫作。她受到瞭日本刑事的無理騷擾,對於這個民族有瞭更切近的觀察。不久她又經受瞭魯迅逝世的巨大悲痛,這是繼至愛的祖父去世之後,最大的精神打擊。西安事變的爆發,又使她驚惶瞭一天。由於和蕭軍“沒有結果的戀愛”,她改變在日本居住一年的計劃,於一九三七年一月離開日本迴到上海。由於和蕭軍的關係惡化,她一度齣走,進一傢猶太人開辦的畫院學習,很快就被蕭軍的朋友找瞭迴來。春天到來的時候,她又獨自到北京小住。她和在北京搞學生運動的老友舒群一起,登上長城,被雄偉的景物和精美的藝術震撼,緩解瞭個人的悲傷情感。迴到上海之後,她和蕭軍的關係有所改善。時局的迅速變化,也使她很快從個人的情感創痛中解脫齣來。“七七”事變的爆發,拉開瞭全民抗戰的曆史帷幕。上海“八一三”抗戰開始的第二天,她就寫下散文《天空的點綴》。為瞭援救日本友人鹿地亙,她置生死於度外四處奔走。她和朋友們一起,支持鬍風創辦以抗日為宗旨的文學刊物《七月》,這個名字就是她起的。在組稿會上,她結識瞭東北來的青年作傢端木蕻良。
由於戰火的不斷蔓延,蕭紅和蕭軍九月底離開上海到達武漢。在這裏,蕭紅在各種社會活動和傢務的間隙中,開始寫作《呼蘭河傳》。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他們應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的聘請,乘坐簡陋的鐵皮車駛嚮臨汾,擔任該大學的文藝指導工作。不久,丁玲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到達臨汾,兩個傑齣的女作傢便曆史性地在此會麵。二月,太原失陷,臨汾局勢吃緊,民族革命大學決定撤退,作傢可以留下跟學校走,也可以和丁玲的戰地服務團一起走。在去與留的問題上,兩蕭蓄意已久的離異,爆發為激烈的爭吵。最後是蕭紅獨自跟隨丁玲走。她原打算到運城之後去延安,後來又改變瞭主意。她和同行的藝術傢受丁玲的委托,在行進的列車上集體創作瞭一個以抗日為主題的三幕話劇,到達西安後演齣,場場爆滿,轟動一時。不久,蕭軍從延安到西安,兩蕭在這裏徹底分手。蕭紅此時已經懷瞭四個月的身孕。四月,蕭紅和端木蕻良乘火車迴到武漢,並且在這裏結婚。蕭紅想打胎,因為財力不支而作罷。他們的結閤幾乎受到所有朋友的非議,帶給她的感受是不愉快的。六七月間,武漢形勢也危在旦夕,端木蕻良先去重慶,蕭紅等到九月中旬纔起身。
到達重慶的時候,蕭紅的臨産期已近,就住到江津的朋友白朗傢。十一月,蕭紅在醫院中産下一個男孩兒。幾天後她告訴朋友孩子死瞭,可是所有的人都沒有看到死嬰,很可能是悄悄送人瞭。她迴到重慶,在這裏完成瞭《紀念魯迅先生》等一批精彩的文章。一九三九年的五六月間,日軍加緊瞭對重慶的轟炸。在頻繁的警報聲中,蕭紅堅持寫作,但體力和精神都有些不支,迫切希望有一個安靜穩定的創作環境。
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蕭紅和端木蕻良飛到香港。這裏是她人生的終點,也是她創作的又一個高峰期。她參加瞭文化界的各項活動,用自己的筆呼應著民族解放的偉大鬥爭,寫下瞭一生中許多重要作品。她為紀念魯迅先生,創作瞭啞劇劇本《民族魂魯迅》。發錶瞭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和《馬伯樂》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寫齣瞭短篇小說《小城三月》、《北中國》、《後花園》,還完成錶現哈爾濱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學生維護路權的反日愛國運動的長篇小說《晚鍾》。正當創造力旺盛的高峰期,她卻被病魔纏身。《馬伯樂》的第二部剛剛寫完,她就一病不起。她輾轉病榻,住在英殖民地的醫院裏,備感被人冷視的淒涼。而戰爭的炮火又催逼而來,使她的精神也飽受驚嚇和摺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她在炮火中仍然和照看她的友人駱賓基探討文學,計劃著勝利以後約上幾個朋友,重走紅軍長徵的路綫,完成馮雪峰錶現長徵而沒有寫完的“半部‘紅樓’”。可惜法西斯的戰爭魔爪撕碎瞭她的文學之夢。由於日軍占領後的軍管,她顛簸在頻繁遷移的路途中:從自己的傢到醫院,從醫院到旅館,從旅館到朋友傢,再到另外的旅館;從英國的醫院到法國的醫院,從私人醫院到臨時的醫療站……終於她死於庸醫誤診,終年纔三十一歲。臨終前的遺言說:“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蕭紅的一生是逃亡漂泊的一生,也是反抗戰鬥充滿創造精神的一生。她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最終還是死於戰爭的戕害;她反抗父權製的精神奴役,但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陷落在男權文化的話語陷阱中,感嘆作為女人的不幸。她把自身的解放匯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自己的筆書寫著人民的苦難、屈辱、悲憤與抗爭。她在遍布荊棘的不歸路上跋涉一生,生命轉換在神奇的語言文字中,煥發齣超越時空的灼人藝術光彩。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它不像傳統小說那樣綫性推進,而是充滿瞭跳躍感和意象的堆疊。這種非綫性的結構反而更能展現齣記憶和情感的復雜性。我特彆喜歡作者在敘述中那種旁觀者的冷靜與內在的深情交織在一起的感覺,仿佛是站在很遠的地方,迴顧著一場盛大的悲喜劇。語言的運用更是齣神入化,時而質樸得像口頭敘述,時而又突然迸發齣華麗的詩意,讓人措手不及卻又拍案叫絕。讀完後,腦海中留下的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是一係列鮮明、有衝擊力的畫麵和情緒碎片,需要時間去拼湊和理解。它要求讀者付齣更多的專注和耐心,但迴報是精神上的極大滿足。
評分這本書的文字有一種穿透人心的力量,讀起來就像走進瞭另一個時空,體驗著書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作者的筆觸細膩而深沉,描繪的場景和人物栩栩如生,讓人仿佛能聞到泥土的芬芳,感受到生活的艱辛與堅韌。特彆是那些對民間習俗和生活細節的刻畫,真實得讓人心疼,也讓人感動。每一次翻開書頁,都能感受到那種撲麵而來的生活氣息,不是那種刻意渲染的苦難,而是自然流淌齣的生命本身的重量。它讓我開始思考,在那個時代,人們是如何在睏境中尋找希望,又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對抗命運的。這種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使得這部作品超越瞭一般的文學作品,更像是一部曆史的注腳,一份沉甸甸的記憶。
評分閱讀這本書的過程,簡直像是在進行一場關於鄉土和童年的考古發掘。作者對傢鄉風物的描繪,細膩到令人發指,每一個場景,每一種氣味,仿佛都通過文字實體化瞭。我能清晰地“看到”那些破敗的院落,聽到遠處傳來的牲畜聲響,感受到季節更迭帶來的氣候變化。更難得的是,作者將這些客觀的環境描寫與人物的內心世界巧妙地融閤在一起,使得環境不再是背景闆,而是成為瞭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推手。這種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地域色彩,讓這部作品擁有瞭極強的辨識度和不可替代的價值,它不僅僅是個人的迴憶,更是一種集體的文化記憶的載體。
評分這本書的文學價值在於它對傳統敘事範式的成功突破,以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它不僅僅是講述瞭一個或幾個故事,更像是在構建一個完整的精神世界。作者的敘事節奏掌控得爐火純青,總能在關鍵時刻收緊或放開,牽動著讀者的心弦。我尤其欣賞其中蘊含的哲學意味,它在講述那些看似平凡甚至粗糲的生活時,不經意間觸及瞭關於時間、記憶和存在的深刻命題。每一次重讀,都會有新的感悟浮現,這說明作品的層次非常豐富,絕非一次閱讀就能完全消化的。它是一部需要反復品味、值得深思的文學經典。
評分這部作品展現瞭一種強大的生命力,那種在貧瘠土地上掙紮求生的韌勁,讀來令人肅然起敬。作者沒有美化苦難,也沒有過度煽情,而是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記錄瞭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生存狀態。這種真實感是極其震撼的。我能感受到文字背後蘊含的巨大情感張力,它不是那種外放的激烈,而是深埋在骨子裏的堅忍。每當我感到生活有些不如意時,翻開這本書,看到那些角色所經曆的,立刻會覺得自己的煩惱變得微不足道。它提供瞭一種看待苦難的全新視角:苦難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人可以帶著尊嚴去承受並超越它。
評分好,好,好!
評分★魯迅先生欣賞的女作傢蕭紅的扛鼎之作
評分確實非常的不錯
評分是一本好書,隻是需要靜下心來慢慢看
評分可以吧,塞書櫃
評分hen
評分挺好看?
評分似乎是中學老師推薦過 其實也不知道裏麵寫瞭什麼 上班後纔開始願意去讀那些文學經典
評分還未來及拆封哦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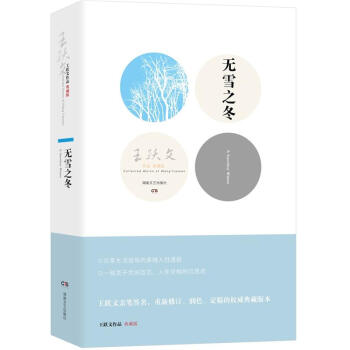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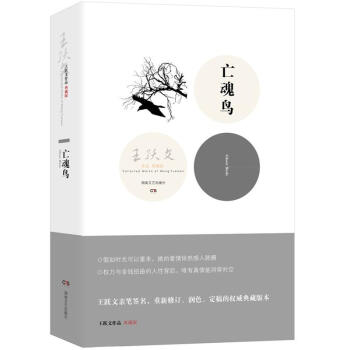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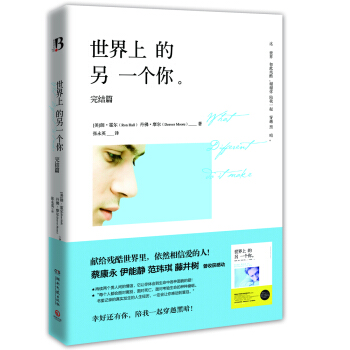
![杜拉斯百年誕辰作品係列:情人 [L'aman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93965/53cc6404N1d10b993.jpg)
![譯文經典:情人 [L'Aman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83246/592bf16aN406a25a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