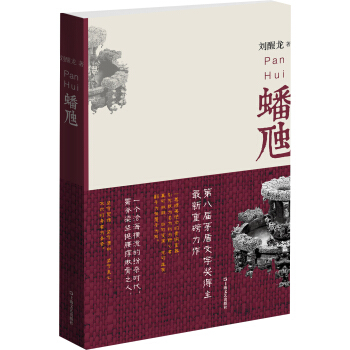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生死场》创作于1934年,萧红成名作,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小说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里行间描摹着中国人于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被誉为是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作者简介
萧红(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著名女作家,原名张迺莹,1911年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7年在哈尔滨就读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接触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萧红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内页插图
目录
《生死场》校订记 章海宁
序言 鲁迅
一、麦场
二、菜圃
三、老马走进屠场
四、荒山
五、羊群
六、刑罚的日子
七、罪恶的五月节
八、蚊虫繁忙着
九、传染病
十、十年
十一、年盘转动了
十二、黑色的舌头
十三、你要死灭吗?
十四、到都市里去
十五、失败的黄色药包
十六、尼姑
十七、不健全的腿
读后记 胡风
精彩书摘
《生死场》校订记章海宁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阅读萧红,如果绕开《生死场》,是不能算读懂萧红的。
上世纪70年代,早在葛浩文先生的英文本《萧红传》出版之前,夏志清先生便评价萧红的《生死场》,“将中国古老农村刻划之深刻,实在胜过鲁迅的《呐喊》、《彷徨》。”夏先生将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并提,认为它们都是“了不起的作品”。[1]这样的评价,虽然不是出现在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但也足以让中国读者感到惊讶。
萧红创作完成《生死场》时只有23岁,当初她给这部小说命名为《麦场》。《麦场》共17章,其前两章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上(简称“初刊本”)。[2]1934 年6月,因《跋涉》被伪满当局查禁引发的恐慌,萧红、萧军出走青岛。在青岛,萧红编辑《新女性周刊》之余,大部分时间用于续写《麦场》,同年9月9日,《麦场》完稿。萧红曾把《麦场》的片段朗诵给同在《青岛晨报》工作的梅林听,梅林感觉萧红的笔触“清丽纤细大胆,好像一首牧歌”,但小说的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3]与鲁迅通信后,二萧将《麦场》的复写稿连同他们的第一部文集《跋涉》一起寄给了鲁迅。鲁迅对《麦场》的出版倾注了全力,先是将稿子投给生活书店,当局的书报检查委员审查了半年没有通过。鲁迅又将书稿转到《文学》杂志,希望它能在《文学》上连载,但《文学》不愿意冒险,因为《麦场》写到了东北民众的抗日,在当时,抗日的言论是被当局明令禁止的。鲁迅还不甘心,再将它转到黎明书店,期待它有一线的生机,结局同样令人失望。此路不通,只能另辟蹊径。一次饭局上,叶紫、萧红、萧军想成立一个“奴隶社”,自行印刷自己的作品。鲁迅对这个想法很赞同,分别给叶紫和萧军的书写了序。待萧红的《麦场》出版时,鲁迅改让胡风作序,但萧红反对,鲁迅只好另写一篇序言,胡风写好的序言改作《读后记》。根据胡风的建议,《麦场》改名为《生死场》,1935年12月24日,“奴隶社”以“容光书局”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简称“初版”)。《生死场》的出版,在当时的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年内6版,至萧红离世前,已出11版。即使在抗战胜利以后,《生死场》也一直畅销,大连文化界民主建设协进会、生活书店、鲁迅文化出版社、东北书店等多家出版单位重印此书。甚至它还被改编成连环画[4]。应该说,《生死场》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出版策划,文豪鲁迅的序言、著名左翼文学评论家胡风的评论、文学新锐萧红的“越轨”的文字使这本新书卖点十足。鲁迅多次向萧红索书转赠友人,在当年的江浙和北平,还出现了盗版的《生死场》,该书的影响可见一斑。萧红凭借《生死场》跻身上海滩名作家行列,这是她人生的重要转折。如果没有《生死场》,萧红能否被上海文学界接纳尚未可知。
像《生死场》这样一部经典,因为语言的变迁,阅读者与创作者身份、文化、认知等方面的差异,阅读的感受会千差万别。即使在专业的文学批评家那里,也同样如此。
鲁迅在评价《生死场》说,“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不少明丽和新鲜。”[5]鲁迅认为萧红对北方土地上挣扎着的人群的描写是“力透纸背”的,他称萧红的文字有“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胡风对“力透纸背”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胡风认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地方揭示生殖与死亡的意义。“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6]所以他将小说命名为《生死场》。对走投无路的抗日民众的描写,胡风也很欣赏,既“看到了女性的纤细”,也看到了“非女性的豪迈”。在这些方面,鲁迅与胡风的看法是大致相同的。鲁迅和胡风在《生死场》的人物描写方面都对萧红对提出了批评,鲁迅委婉地说《生死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胡风说,“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和加工非常不够。”[7]胡风还批评萧红“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的迫力”。[8]对《生死场》的“语法句法”,胡风认为它“太特别了”,并且认为产生这种印象的重要的原因是“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9]鲁迅和胡风的评价,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对《生死场》的阅读定势。客观地说,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阅读是有局限的。《生死场》在它问世的近半个世纪里,一直被作为“抗日文学”来阅读。萧红与东北作家群其他作家一样,都来自沦陷的“满洲”,由于当时政府对抗日言论的钳制,国人对失去东北的愤懑之情无处发泄,而《万宝山》、《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恰好满足了这种阅读期待。鲁迅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强化了读者对该书“抗日功能”的解读。而蕴于“抗日”文字之外的诸多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屏蔽。其实,该书的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日无关,而是写东北乡村极度的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人的生活退化为动物式的生存,而这挣扎的人群描写的重点是乡村的女性,如麻面婆、王婆、月英、金枝等,她们的命运,很多时候与自己是否勤劳、美丽没有多大关系,除了自然和经济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她们身边的男性。她们感受的苦难,与其说是来自“自然的暴君”,还不如说是与她们一起生活的男性。萧红在《生死场》中对男权世界的激烈的批评男性批评家是视而不见的,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萧红的性别批评立场才得到极大的关注,《生死场》才从“抗日小说”跳出,以另一种面目被读者重新阅读。
鲁迅、胡风包括后来很多的批评家,对《生死场》的结构是持批评的意见。文学批评家摩罗称《生死场》是一个“断裂的文本”[10]。这与此前萧红研究者葛浩文的观点相接近。萧红为什么要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写残酷的“生、老、病、死轮回”的乡村女性,难道仅仅是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 [11]?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葛浩文在他的《萧红传》出版30多年后,修正了他的看法,“我本来对书中风格和主题的豁然改变表示不满,以为全书统一性给破坏了。后来我推翻我自己的看法,觉得这种看法忽略了小说后半部的主旨,即描写当时的女性之如何间接的经历战争。”[12]葛浩文从“文本断裂”跳出来,将萧红小说前后的主旨连贯了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小说读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文字的张力实在惊人,那种深入骨髓的压抑感和生命力的迸发交织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来。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细致入微,即便是最微小的挣扎、最隐秘的欲望,都被毫不留情地剥开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尤其欣赏它对时代背景的捕捉,那种粗粝、原始的生存状态,仿佛能透过纸页感受到泥土的气息和汗水的咸涩。故事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好,时而如山洪暴发般激烈,时而又沉淀下来,像凝固的琥珀,让人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的复杂人性。读到某些情节时,我甚至会忍不住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富有哲理的对白,它们像一把把锋利的刻刀,直指人性的幽暗与光辉并存的真相。看完之后,那种被震撼后的空茫感久久不能散去,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洗礼,对“活着”这两个字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不是那种让人读完后轻松愉快的消遣之作,而是一部需要你全身心投入、与之共振的文学作品,后劲十足。
评分我很少读到如此具有生命力的文本,它简直就是一团燃烧的火焰,将所有世俗的、虚伪的东西都烧成了灰烬。作者的笔触极其老辣,他似乎对人性的弱点有着近乎病态的洞察力,却又在描绘这些弱点的同时,保留了一丝对人类精神的敬畏。这本书的节奏变化太精彩了,它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充满了爆发性的张力。有些章节短促有力,像急促的鼓点,直击心脏;有些则绵长而幽深,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暗河,积蓄着巨大的力量。我特别留意了那些女性角色的塑造,她们的坚韧与脆弱,她们在生活重压下展现出的那种惊人的韧性,让我印象极为深刻,这绝不是扁平化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阅读过程中,我时常需要停下来,不是因为内容太难懂,而是因为情感冲击太大,需要时间来消化那种直击灵魂的真实感。这本书无疑是那种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每次重读,都会有新的感悟浮现。
评分拿到这本书时,我原本以为会是一部沉闷的历史叙事,但很快就被它那种近乎野蛮的生命力所吸引住了。作者的叙事视角非常独特,他似乎能从极高的位置俯瞰众生,却又能在下一秒立刻潜入角色的最深层意识,这种切换异常流畅且自然。整本书的情绪张力就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弓弦,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微小的触发点而崩断。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关键情节时的克制,他从不滥用煽情的笔墨,而是让人物的行为、环境的变迁,以及那些沉默的对视来完成情感的传递。这种“少说多做”的写作手法,反而让最终的爆发显得更加真实和震撼。每一次翻页,都像是一次冒险,你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到惊喜还是惊吓,但你知道,无论如何,你都无法逃脱故事所构建的那个独特的精神世界。读完后,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去了解更多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上的故事,这本书成功地搭建起了一座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梁,结实而有力。
评分这部作品最让我惊艳的地方,在于它对“地方性”的深入挖掘和提炼。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像是一份详尽而充满情感的田野调查报告,只不过是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作者对特定地域的习俗、语言、乃至那种特有的生活哲学,掌握得炉火纯青,读起来丝毫没有隔阂感。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词汇和表达,非但没有降低作品的格调,反而为其增添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厚重感和历史感。我曾尝试去对比其他一些描绘底层生活的作品,但很少有能达到这种“在场感”的。仿佛我就是那个在烈日下劳作的人,皮肤被晒得黝黑,呼吸着混杂着尘土的气息。更难得的是,尽管背景设定如此鲜明,但它探讨的主题——关于生存、关于尊严、关于爱与被爱——却是永恒的,具有极强的普适性。这本书的格局很大,它在描绘个体命运的同时,也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其深刻性令人不寒而栗。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冷峻与热烈”的完美结合。开头几页我就被那种近乎残酷的写实主义风格给吸引住了,没有任何多余的渲染和矫饰,一切都以最直接、最原始的面貌呈现出来。但有趣的是,在这种极简的叙事背后,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能量。作者似乎精通于通过环境的描写来烘托人物的心境,那些关于土地、关于劳作的段落,读起来简直像一首厚重的史诗。我尤其喜欢它对群体心理的描摹,那种在共同困境下产生的微妙的依附与疏离,那种看不见的、却又真实存在的社会结构,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每次读到冲突爆发的关键时刻,我都感觉自己握紧了拳头,仿佛自己也身处那个特定的时空,感受着命运的无常和个体的渺小。这本书的结构看似松散,实则处处伏笔,前后照应,等到最后揭晓时,那种豁然开朗的震撼感,是其他小说难以比拟的。它迫使我不断地去思考,在极端环境下,什么是底线,什么是救赎。
评分不错~活动买的~
评分包装超级棒,真的好喜欢!
评分京东服务一流,书是正版,很满意
评分不错~活动买的~
评分赶上有券屯点书,期待更大力度,书是好东西,原价买不起
评分质量还可以吧,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好
评分此书印刷精美'插图精美'非常喜欢满意'支持京东
评分正版 质量好 送货快
评分买了很多书,书本炒鸡精致,真的很喜欢,还没有看,但很期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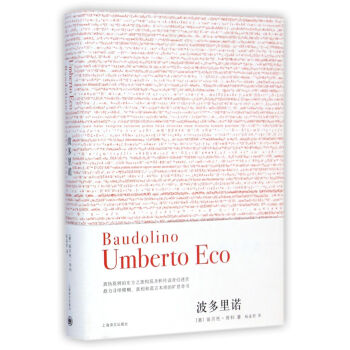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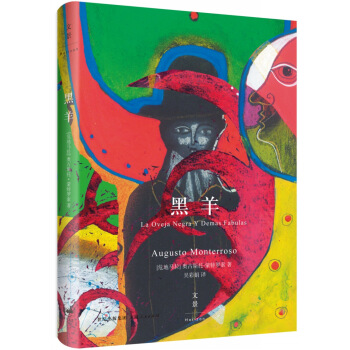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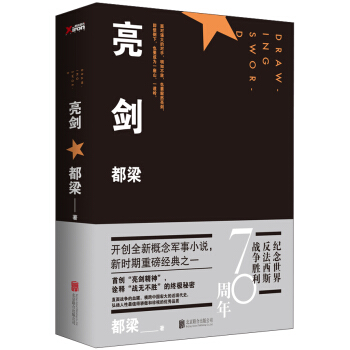


![金田一探案集(12):首 [首]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76144/rBEhVFHf294IAAAAAALSX9pMrRcAAA_6QBtaQsAAtJ384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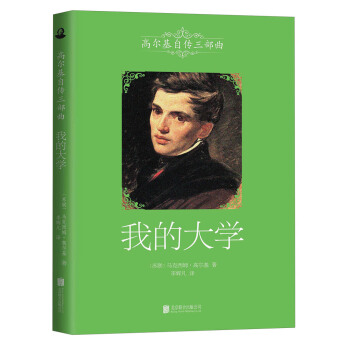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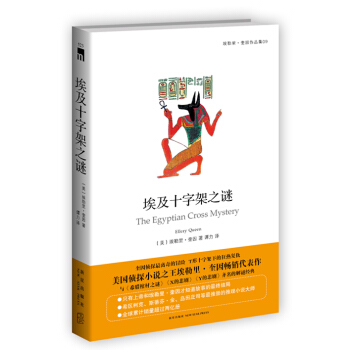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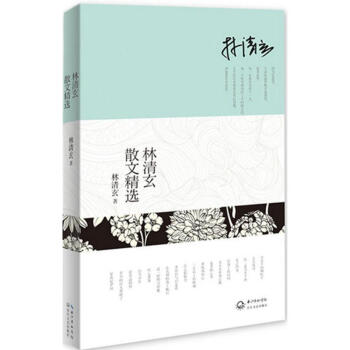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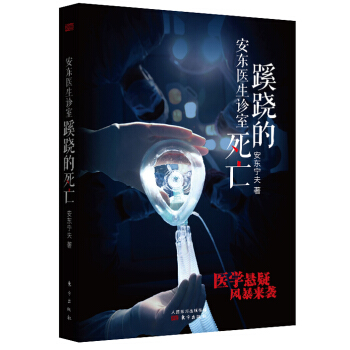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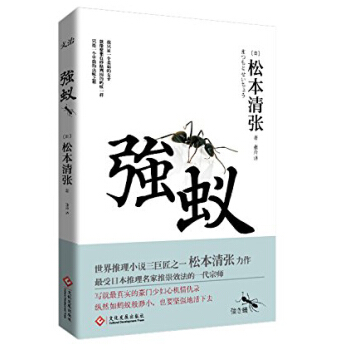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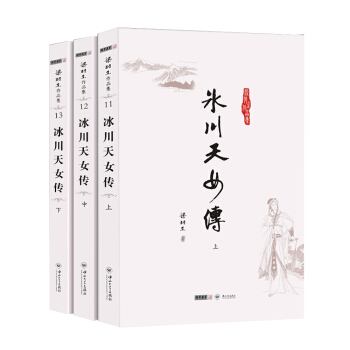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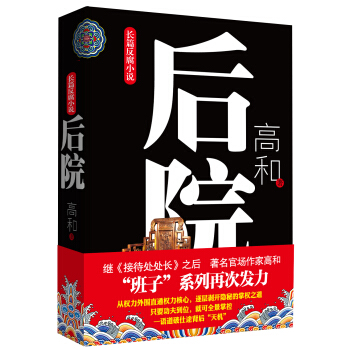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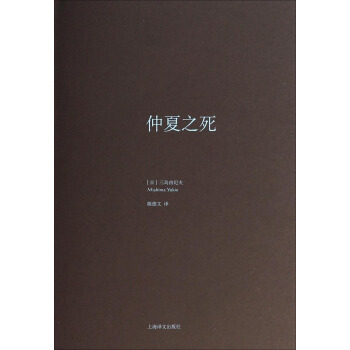
![寻羊冒险记 [羊をめぐる冒険]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43609/53a97d4fNf3574eb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