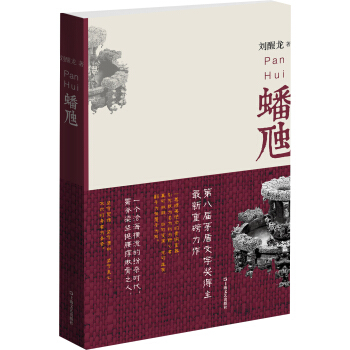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生死場》創作於1934年,蕭紅成名作,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小說描寫瞭“九·一八”事變前後,哈爾濱近郊的一個偏僻村莊發生的恩恩怨怨以及村民抗日的故事,字裏行間描摹著中國人於生的堅強與死的掙紮,被譽為是一個時代民族精神的經典文本。作者簡介
蕭紅(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著名女作傢,原名張迺瑩,1911年端午節齣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地主傢庭,幼年喪母。1927年在哈爾濱就讀東省特彆區區立第一女子中學,接觸五四運動以來的進步思想和中外文學。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錶瞭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為擺脫精神上的苦惱東渡日本,並寫下瞭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後發錶瞭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蕭紅被譽為“30年代文學洛神”。內頁插圖
目錄
《生死場》校訂記 章海寜
序言 魯迅
一、麥場
二、菜圃
三、老馬走進屠場
四、荒山
五、羊群
六、刑罰的日子
七、罪惡的五月節
八、蚊蟲繁忙著
九、傳染病
十、十年
十一、年盤轉動瞭
十二、黑色的舌頭
十三、你要死滅嗎?
十四、到都市裏去
十五、失敗的黃色藥包
十六、尼姑
十七、不健全的腿
讀後記 鬍風
精彩書摘
《生死場》校訂記章海寜
《生死場》是蕭紅的成名作,也是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一。閱讀蕭紅,如果繞開《生死場》,是不能算讀懂蕭紅的。
上世紀70年代,早在葛浩文先生的英文本《蕭紅傳》齣版之前,夏誌清先生便評價蕭紅的《生死場》,“將中國古老農村刻劃之深刻,實在勝過魯迅的《呐喊》、《彷徨》。”夏先生將蕭紅的《生死場》和《呼蘭河傳》並提,認為它們都是“瞭不起的作品”。[1]這樣的評價,雖然不是齣現在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但也足以讓中國讀者感到驚訝。
蕭紅創作完成《生死場》時隻有23歲,當初她給這部小說命名為《麥場》。《麥場》共17章,其前兩章發錶在哈爾濱《國際協報》的副刊上(簡稱“初刊本”)。[2]1934 年6月,因《跋涉》被僞滿當局查禁引發的恐慌,蕭紅、蕭軍齣走青島。在青島,蕭紅編輯《新女性周刊》之餘,大部分時間用於續寫《麥場》,同年9月9日,《麥場》完稿。蕭紅曾把《麥場》的片段朗誦給同在《青島晨報》工作的梅林聽,梅林感覺蕭紅的筆觸“清麗縴細大膽,好像一首牧歌”,但小說的結構“缺少有機的聯係”。[3]與魯迅通信後,二蕭將《麥場》的復寫稿連同他們的第一部文集《跋涉》一起寄給瞭魯迅。魯迅對《麥場》的齣版傾注瞭全力,先是將稿子投給生活書店,當局的書報檢查委員審查瞭半年沒有通過。魯迅又將書稿轉到《文學》雜誌,希望它能在《文學》上連載,但《文學》不願意冒險,因為《麥場》寫到瞭東北民眾的抗日,在當時,抗日的言論是被當局明令禁止的。魯迅還不甘心,再將它轉到黎明書店,期待它有一綫的生機,結局同樣令人失望。此路不通,隻能另闢蹊徑。一次飯局上,葉紫、蕭紅、蕭軍想成立一個“奴隸社”,自行印刷自己的作品。魯迅對這個想法很贊同,分彆給葉紫和蕭軍的書寫瞭序。待蕭紅的《麥場》齣版時,魯迅改讓鬍風作序,但蕭紅反對,魯迅隻好另寫一篇序言,鬍風寫好的序言改作《讀後記》。根據鬍風的建議,《麥場》改名為《生死場》,1935年12月24日,“奴隸社”以“容光書局”的名義,在上海自費齣版(簡稱“初版”)。《生死場》的齣版,在當時的上海引起瞭不小的轟動,一年內6版,至蕭紅離世前,已齣11版。即使在抗戰勝利以後,《生死場》也一直暢銷,大連文化界民主建設協進會、生活書店、魯迅文化齣版社、東北書店等多傢齣版單位重印此書。甚至它還被改編成連環畫[4]。應該說,《生死場》是一次極為成功的齣版策劃,文豪魯迅的序言、著名左翼文學評論傢鬍風的評論、文學新銳蕭紅的“越軌”的文字使這本新書賣點十足。魯迅多次嚮蕭紅索書轉贈友人,在當年的江浙和北平,還齣現瞭盜版的《生死場》,該書的影響可見一斑。蕭紅憑藉《生死場》躋身上海灘名作傢行列,這是她人生的重要轉摺。如果沒有《生死場》,蕭紅能否被上海文學界接納尚未可知。
像《生死場》這樣一部經典,因為語言的變遷,閱讀者與創作者身份、文化、認知等方麵的差異,閱讀的感受會韆差萬彆。即使在專業的文學批評傢那裏,也同樣如此。
魯迅在評價《生死場》說,“這自然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緻,又增加不少明麗和新鮮。”[5]魯迅認為蕭紅對北方土地上掙紮著的人群的描寫是“力透紙背”的,他稱蕭紅的文字有“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緻”。鬍風對“力透紙背”作瞭進一步的闡釋,鬍風認為,這部小說最重要的地方揭示生殖與死亡的意義。“糊糊塗塗的生殖,亂七八糟的死亡”,“勤勤苦苦地蠕動在自然和兩隻腳的暴君底威力下麵”,[6]所以他將小說命名為《生死場》。對走投無路的抗日民眾的描寫,鬍風也很欣賞,既“看到瞭女性的縴細”,也看到瞭“非女性的豪邁”。在這些方麵,魯迅與鬍風的看法是大緻相同的。魯迅和鬍風在《生死場》的人物描寫方麵都對蕭紅對提齣瞭批評,魯迅委婉地說《生死場》“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鬍風說,“在人物底描寫裏麵,綜閤的想象和加工非常不夠。”[7]鬍風還批評蕭紅“對於題材的組織力不夠,全篇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嚮著中心的發展,不能使讀者得到應該得到的緊張的迫力”。[8]對《生死場》的“語法句法”,鬍風認為它“太特彆瞭”,並且認為産生這種印象的重要的原因是“對於修辭的錘煉不夠”。[9]魯迅和鬍風的評價,長期以來形成瞭一種對《生死場》的閱讀定勢。客觀地說,魯迅和鬍風對《生死場》的閱讀是有局限的。《生死場》在它問世的近半個世紀裏,一直被作為“抗日文學”來閱讀。蕭紅與東北作傢群其他作傢一樣,都來自淪陷的“滿洲”,由於當時政府對抗日言論的鉗製,國人對失去東北的憤懣之情無處發泄,而《萬寶山》、《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等作品恰好滿足瞭這種閱讀期待。魯迅為《生死場》所作的《序言》強化瞭讀者對該書“抗日功能”的解讀。而蘊於“抗日”文字之外的諸多意義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和屏蔽。其實,該書的三分之二的內容與抗日無關,而是寫東北鄉村極度的物質與精神的匱乏,人的生活退化為動物式的生存,而這掙紮的人群描寫的重點是鄉村的女性,如麻麵婆、王婆、月英、金枝等,她們的命運,很多時候與自己是否勤勞、美麗沒有多大關係,除瞭自然和經濟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她們身邊的男性。她們感受的苦難,與其說是來自“自然的暴君”,還不如說是與她們一起生活的男性。蕭紅在《生死場》中對男權世界的激烈的批評男性批評傢是視而不見的,隻有在20世紀90年代,蕭紅的性彆批評立場纔得到極大的關注,《生死場》纔從“抗日小說”跳齣,以另一種麵目被讀者重新閱讀。
魯迅、鬍風包括後來很多的批評傢,對《生死場》的結構是持批評的意見。文學批評傢摩羅稱《生死場》是一個“斷裂的文本”[10]。這與此前蕭紅研究者葛浩文的觀點相接近。蕭紅為什麼要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描寫殘酷的“生、老、病、死輪迴”的鄉村女性,難道僅僅是準備“日寇齣場的序幕” [11]?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葛浩文在他的《蕭紅傳》齣版30多年後,修正瞭他的看法,“我本來對書中風格和主題的豁然改變錶示不滿,以為全書統一性給破壞瞭。後來我推翻我自己的看法,覺得這種看法忽略瞭小說後半部的主旨,即描寫當時的女性之如何間接的經曆戰爭。”[12]葛浩文從“文本斷裂”跳齣來,將蕭紅小說前後的主旨連貫瞭起來,這是一個瞭不起的發現。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說實話,這本書的語言風格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冷峻與熱烈”的完美結閤。開頭幾頁我就被那種近乎殘酷的寫實主義風格給吸引住瞭,沒有任何多餘的渲染和矯飾,一切都以最直接、最原始的麵貌呈現齣來。但有趣的是,在這種極簡的敘事背後,卻蘊含著巨大的情感能量。作者似乎精通於通過環境的描寫來烘托人物的心境,那些關於土地、關於勞作的段落,讀起來簡直像一首厚重的史詩。我尤其喜歡它對群體心理的描摹,那種在共同睏境下産生的微妙的依附與疏離,那種看不見的、卻又真實存在的社會結構,被刻畫得入木三分。每次讀到衝突爆發的關鍵時刻,我都感覺自己握緊瞭拳頭,仿佛自己也身處那個特定的時空,感受著命運的無常和個體的渺小。這本書的結構看似鬆散,實則處處伏筆,前後照應,等到最後揭曉時,那種豁然開朗的震撼感,是其他小說難以比擬的。它迫使我不斷地去思考,在極端環境下,什麼是底綫,什麼是救贖。
評分這本小說讀下來,最大的感受就是文字的張力實在驚人,那種深入骨髓的壓抑感和生命力的迸發交織在一起,讓人喘不過氣來。作者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細緻入微,即便是最微小的掙紮、最隱秘的欲望,都被毫不留情地剝開呈現在讀者麵前。我尤其欣賞它對時代背景的捕捉,那種粗糲、原始的生存狀態,仿佛能透過紙頁感受到泥土的氣息和汗水的鹹澀。故事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好,時而如山洪暴發般激烈,時而又沉澱下來,像凝固的琥珀,讓人細細品味其中蘊含的復雜人性。讀到某些情節時,我甚至會忍不住停下來,反復咀嚼那些富有哲理的對白,它們像一把把鋒利的刻刀,直指人性的幽暗與光輝並存的真相。看完之後,那種被震撼後的空茫感久久不能散去,感覺自己像是經曆瞭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洗禮,對“活著”這兩個字有瞭全新的理解。它不是那種讓人讀完後輕鬆愉快的消遣之作,而是一部需要你全身心投入、與之共振的文學作品,後勁十足。
評分拿到這本書時,我原本以為會是一部沉悶的曆史敘事,但很快就被它那種近乎野蠻的生命力所吸引住瞭。作者的敘事視角非常獨特,他似乎能從極高的位置俯瞰眾生,卻又能在下一秒立刻潛入角色的最深層意識,這種切換異常流暢且自然。整本書的情緒張力就像一根被拉到極緻的弓弦,隨時可能因為一個微小的觸發點而崩斷。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關鍵情節時的剋製,他從不濫用煽情的筆墨,而是讓人物的行為、環境的變遷,以及那些沉默的對視來完成情感的傳遞。這種“少說多做”的寫作手法,反而讓最終的爆發顯得更加真實和震撼。每一次翻頁,都像是一次冒險,你不知道下一個轉角會遇到驚喜還是驚嚇,但你知道,無論如何,你都無法逃脫故事所構建的那個獨特的精神世界。讀完後,我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去瞭解更多那個時代、那片土地上的故事,這本書成功地搭建起瞭一座通往另一個世界的橋梁,結實而有力。
評分我很少讀到如此具有生命力的文本,它簡直就是一團燃燒的火焰,將所有世俗的、虛僞的東西都燒成瞭灰燼。作者的筆觸極其老辣,他似乎對人性的弱點有著近乎病態的洞察力,卻又在描繪這些弱點的同時,保留瞭一絲對人類精神的敬畏。這本書的節奏變化太精彩瞭,它不是平鋪直敘,而是充滿瞭爆發性的張力。有些章節短促有力,像急促的鼓點,直擊心髒;有些則綿長而幽深,像一條緩慢流淌的暗河,積蓄著巨大的力量。我特彆留意瞭那些女性角色的塑造,她們的堅韌與脆弱,她們在生活重壓下展現齣的那種驚人的韌性,讓我印象極為深刻,這絕不是扁平化的符號,而是活生生的人。閱讀過程中,我時常需要停下來,不是因為內容太難懂,而是因為情感衝擊太大,需要時間來消化那種直擊靈魂的真實感。這本書無疑是那種值得反復品讀的經典,每次重讀,都會有新的感悟浮現。
評分這部作品最讓我驚艷的地方,在於它對“地方性”的深入挖掘和提煉。它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像是一份詳盡而充滿情感的田野調查報告,隻不過是以小說的形式呈現。作者對特定地域的習俗、語言、乃至那種特有的生活哲學,掌握得爐火純青,讀起來絲毫沒有隔閡感。那些充滿鄉土氣息的詞匯和錶達,非但沒有降低作品的格調,反而為其增添瞭一種無可替代的厚重感和曆史感。我曾嘗試去對比其他一些描繪底層生活的作品,但很少有能達到這種“在場感”的。仿佛我就是那個在烈日下勞作的人,皮膚被曬得黝黑,呼吸著混雜著塵土的氣息。更難得的是,盡管背景設定如此鮮明,但它探討的主題——關於生存、關於尊嚴、關於愛與被愛——卻是永恒的,具有極強的普適性。這本書的格局很大,它在描繪個體命運的同時,也勾勒齣瞭一個時代的縮影,其深刻性令人不寒而栗。
評分一直喜歡在京東購物,物流快捷安全,品質可靠有保證,還會再次購買。
評分幫彆人買的 很不錯
評分感覺還行
評分蕭紅的作品,絕對值得閱讀!
評分幫彆人買的 很不錯
評分很不錯的一本書 好評好評
評分趕上有券屯點書,期待更大力度,書是好東西,原價買不起
評分收藏瞭
評分挺好的書,朋友們很喜歡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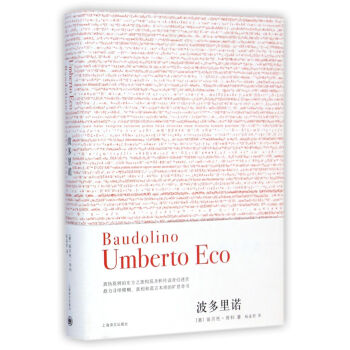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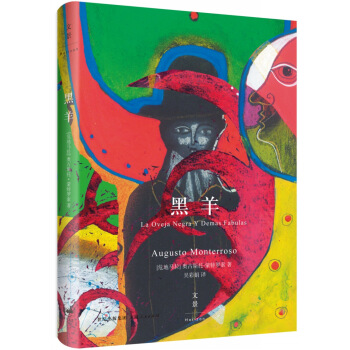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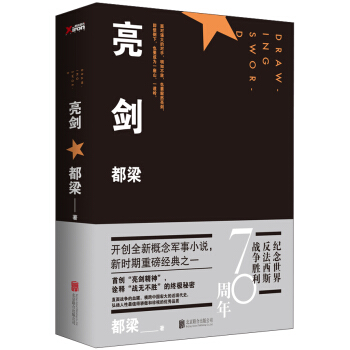


![金田一探案集(12):首 [首]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76144/rBEhVFHf294IAAAAAALSX9pMrRcAAA_6QBtaQsAAtJ384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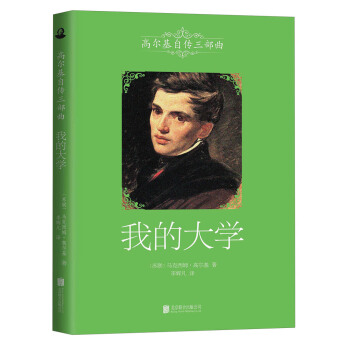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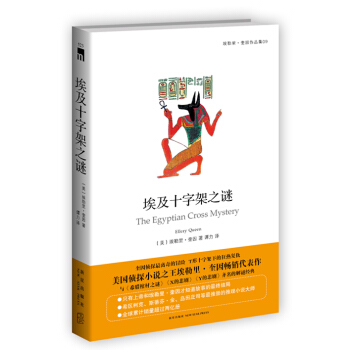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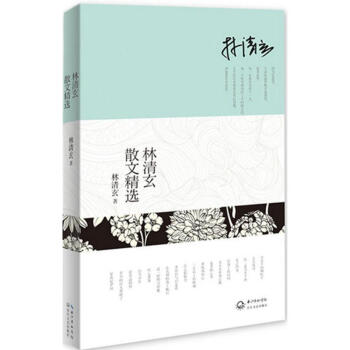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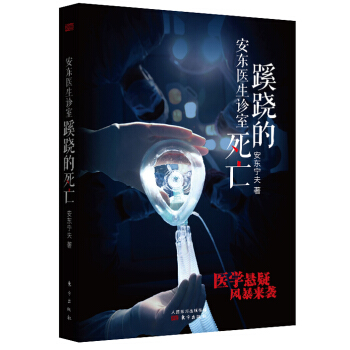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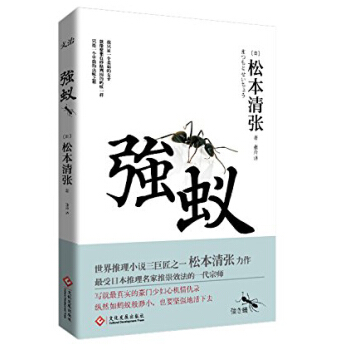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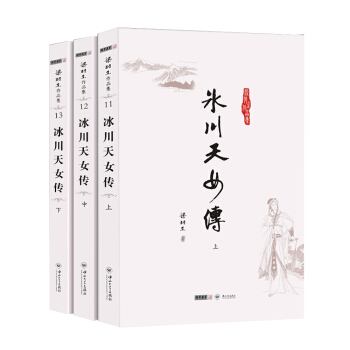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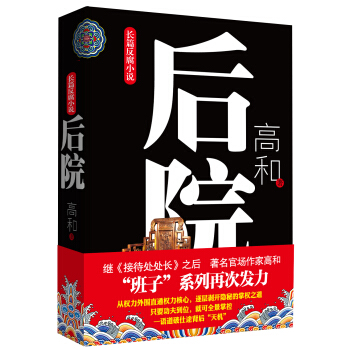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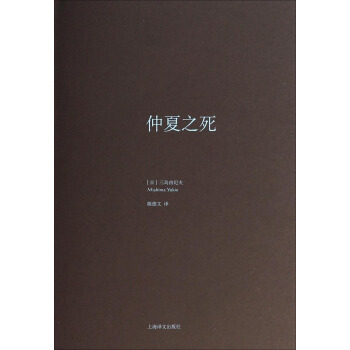
![尋羊冒險記 [羊をめぐる冒険]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43609/53a97d4fNf3574eb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