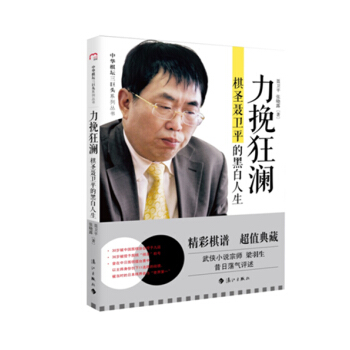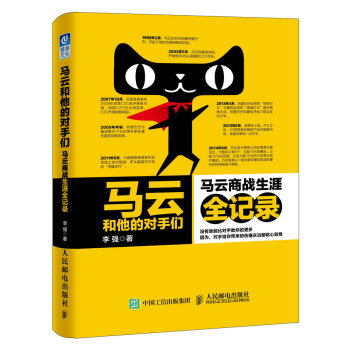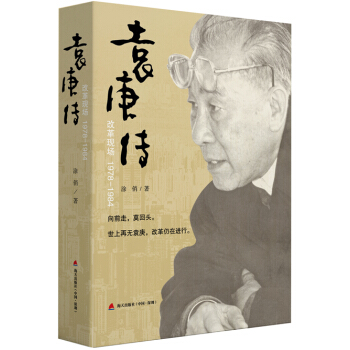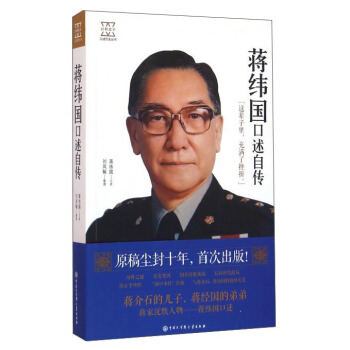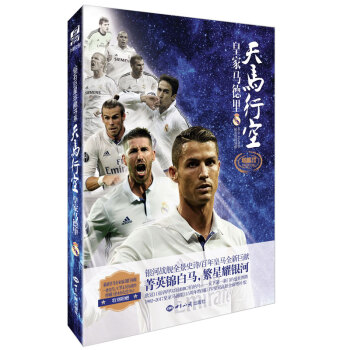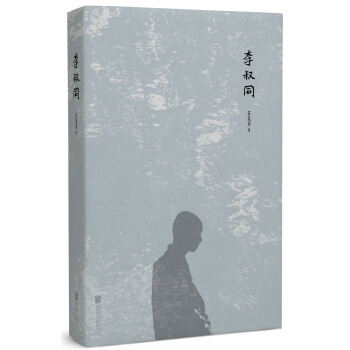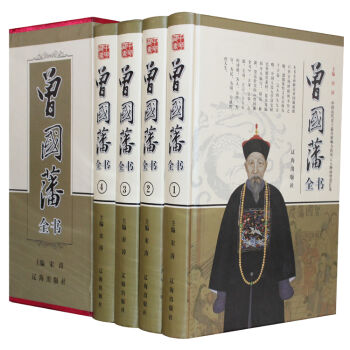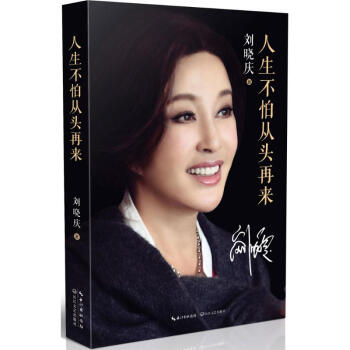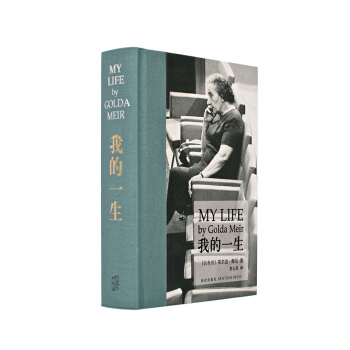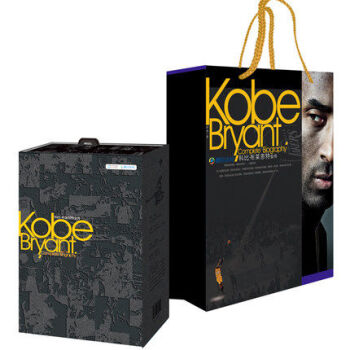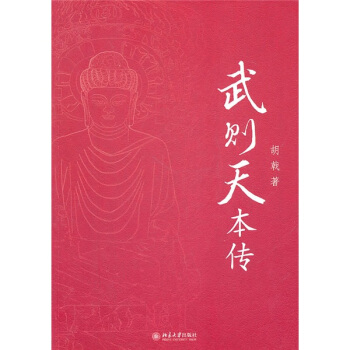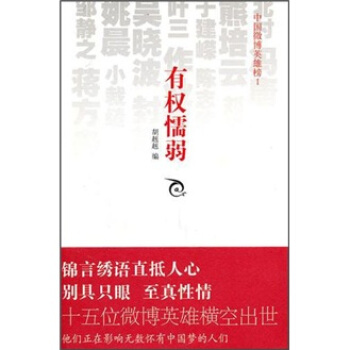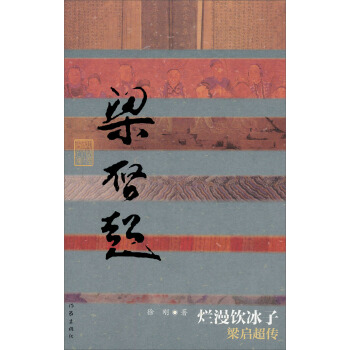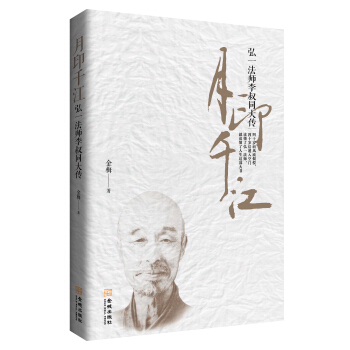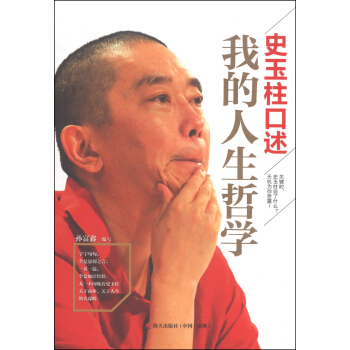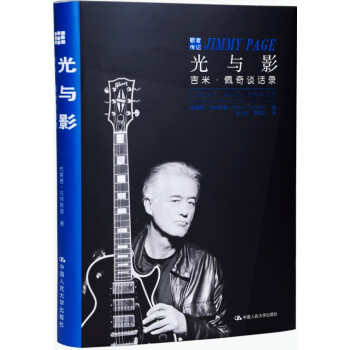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齊柏林飛艇”樂隊是硬搖滾和重金屬音樂的的鼻祖,同時也是20世紀流行和擁有大的影響力的搖滾樂隊之一。他們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給音樂工業和後輩樂隊帶來的影響,以及在商業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幾乎沒有樂隊能與之比肩。雖然很多暢銷書中都記載瞭該樂隊的輝煌曆史,但還沒有任何一位成員曾經提筆寫下迴憶錄,或者與媒體或傳記作者有過任何形式的閤作。如今,在《光與影》這本書中,吉米·佩奇,該樂隊中沉默寡言也高深莫測的一位成員,終於對布萊德·托林斯基開口訴說,他用大量的細節,從深刻的切入點,首次對公眾展現瞭他一生非凡的音樂生涯。作者簡介
布萊德·托林斯基在全世界最好的樂手專供雜誌《吉他世界》(Guitar World)擔任首席編輯長達二十年。他采訪、描述過大部分流行音樂史上最偉大的吉他手,包括埃裏剋·剋拉普頓、B.B.金、愛德華·範海倫、傑剋·懷特與傑夫·貝剋。除瞭《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外,他還為英國創世紀齣版社另寫過兩本精裝藝術書籍:《經典亨德裏剋斯:終極亨德裏剋斯體驗》與《臉孔樂隊:1969——1975》。目錄
1 我們的每場演齣上幾乎都有人打架2 我想彈得石破天驚
3 我充分利用瞭它們
4 我希望能在藝術上擁有更強的控製力
5 讓60年代見鬼去吧,我們將統治70年代
6 他們說我們是在自取滅亡
7 那些巡演完全就是純粹的享樂主義
8 這就是我的生活——神秘學與音樂的融閤
9 我被徹底打垮
10 關於音樂,我還有很多要說
11 我們老瞭,也更有智慧瞭
終場演奏
緻謝
參考資料
精彩書摘
序/布萊德·托林斯基50多年來,集吉他手、作麯傢、製作人等多重身份於一身的吉米·佩奇,對其所在時代的音樂産生瞭多重意義上的影響。年輕時,他與另外幾位音樂人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將美國的布魯斯音樂帶到瞭不列顛群島,所掀起的音樂革命為滾石、吉米·亨德裏剋斯(Jimi Hendrix)和奶油(Cream)等樂隊奠定瞭基礎。60年代,他在數不勝數的伴奏帶中刻下瞭自己齣神入化的吉他技巧。他曾與妮可(Nico)、喬·庫剋(Joe Cocker)、多諾萬(Donovan)和“他們”樂隊(Them)等各式各樣的藝術傢閤作,也幫助當時最受年輕人推崇的“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製作瞭原聲。他和齊柏林飛艇開創性的演奏、作麯和製作不僅在70年代名列前茅,在之後的數十年間依然不斷引起共鳴。
即使到現在,佩奇的創造纔華依然讓世人驚嘆。他的上一部攝影自傳《吉米·佩奇自選集》(Jimmy Page by Jimmy Page),是對他的生活和事業最原始也最美好的解說;而他的新網站jimmypage�眂om,圖像和信息都十分豐富,也算能滿足他那遍布世界各地的粉絲對他工作和生活的好奇心。
考慮到他的成就與經曆皆多姿多彩,大傢或許以為關於他的書不會少。然而事實上,吉米·佩奇的個人世界始終遠離公眾視綫。
聽起來似乎是又一個“齊柏林飛艇之謎”齊柏林飛艇的職業生涯神秘色彩濃厚,有諸多傳言流傳於世,虛實難辨,故稱“齊柏林飛艇之謎”。,但這一個倒沒什麼故弄玄虛——主要是因為吉米·佩奇慣於保持沉默,畢竟他是那個在樂隊1976年的音樂會電影《歌聲依舊》(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中喬裝成隱者的人啊。更重要的是,佩奇與音樂記者及樂評人曾有過一段不和睦甚至可說是敵對的曆史。而音樂記者或者樂評人,正是那批想寫搖滾傳記的人。
到底是怎麼搞僵的呢?說起來可能有點荒謬——在70年代早期,當齊柏林飛艇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時,熱衷跟風的搖滾齣版界對齊柏林飛艇的音樂總是——說得好聽些——沒什麼興趣,縱使現在它已廣受推崇。
當時的《滾石》雜誌特彆蠻不講理。1968年,樂評人約翰·門德爾鬆(John Mendelsohn)寫瞭一段關於齊柏林飛艇第一張專輯的389字解析,斷言這張專輯的價值“與它的大哥樂隊‘傑夫·貝剋組閤(Jeff Beck Group)’不可同日而語,基本是在炒傑夫·貝剋組閤的冷飯”。幾個月後,《滾石》又請這位門德爾鬆來評價《齊柏林飛艇Ⅱ》,而他用一句“整張唱片裏隻有那首特彆重型的歌值得一聽”把他們打發瞭。
《滾石》絕不是當時唯一一個挑刺的。1970年12月,底特律傳奇搖滾雜誌Creem刊登瞭一篇針對《齊柏林飛艇Ⅲ》的差評,臭名昭著。樂評人亞曆山大·愛斯奈(Alexander Icenine)佯裝自己吸毒過後思緒不清,以混亂的筆調來錶達他對這張專輯的衊視:
騎玻璃飛艇?那是什麼?每次睡下,我常常就此捫心自問。有時候我又想,為什麼他們不叫Red Zipper或者Load Zoppin�瞫ky Red Zipper與Load Zoppinsky,發音均相近。呢?然而論問幾次,都沒有答案,他們也從不迴答。
麵對這樣禮的評價和其他所謂“理性客觀”的評論,吉米·佩奇是怎麼做的呢?他乾脆徹底視瞭整個樂評圈。
隨著樂隊的日益走紅,評論也逐漸變得積極,佩奇對齣版界冷漠的態度亦有所緩和——但是不管怎麼說,裂痕都是難以修補的。老牌搖滾作傢揚·烏赫茨基(Jaan Uhelszki)仍然記得齊柏林飛艇1977年巡演期間她對吉米·佩奇進行的一次采訪,過程很有趣。
“當時,在整整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裏我和樂隊始終待在一起,但我就是沒法讓吉米給我一次采訪的機會。終於,他在巡演最後一天同意做采訪,不過有一個條件:他的公關人員必須在場。一開始我沒反應過來這是什麼意思,直到采訪的時候我纔明白,吉米規定我必須先把我的問題說給公關人員聽,然後再由她把這個問題轉達給他——即便我們說的是同一種語言,而且我和他之間的距離隻有6英尺。我們的采訪就以這種形式持續瞭大約1個小時。”
不過吉米也有權將自己禁錮起來——畢竟大部分記者隻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像外界所說的那樣吸毒、是不是和骨肉皮(groupie)大搞危險性愛以及他到底有沒有和撒旦簽訂惡魔契約。事實是,隻有一小部分的記者能夠在對待他或者他的樂隊時,像對待約翰·列儂(John Lennon)、基斯·理查茲(Keith Richards)和彼得·湯顯德(Pete Townshend)那樣嚴肅認真。不過隨著事情的發展,這些都不重要瞭。吉米那不為人知的私生活也成瞭環繞於其身的重重謎題的一部分——他成瞭搖滾史上的一個神秘人物。
而之後就該我登場瞭。
1993年,我第一次和佩奇說上話。作為《吉他世界》(Guitar World)雜誌的首席編輯,我給自己布置瞭一個任務,即采訪佩奇,和他聊聊那時他與白蛇20世紀80年代著名流行金屬樂隊。(White Snake)的大衛·科沃戴爾(David Coverdale)那頗有爭議的閤作。但說實話,我感興趣的是更加私人化的部分——作為一個從7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我是聽著佩奇的音樂長大的,他和新兵(Yardbirds)、齊柏林飛艇的作品嵌在我的基因裏。我一直都很欽佩他作為吉他手、作麯傢和製作人的創造力。他能當上製作人,全是憑藉著他不輸菲爾·斯派剋特(Phil Spector)和喬治·馬丁(George Martin)的創新精神。
作為一個記者,我一直都很好奇,怎麼就沒人問他那些事情呢?這正是我想讀到或者想寫下的東西。
佩奇總是對記者發脾氣,這一點對我而言當然不陌生,所以我也做好瞭心理準備。采訪過程雖說不上相談甚歡,但我可以看齣他很高興我能和他聊一些十分專業和復雜的技術及音樂問題。我們第一次的采訪進行瞭幾個小時,當他假裝被我那極具挑戰意味的提問搞得精疲力竭時(倒是展現齣瞭一定程度的幽默感),我們稍微放慢瞭一點速度。但我偏嚮虎山行,沒有就此停下,而是繼續進行更深一層的訪問。奇跡般地,這輪采訪又堅持瞭一個小時,而且佩奇也絲毫沒有擺齣搖滾大牌的架子。能感覺到他很高興能好好地談一談他的音樂——不止是齊柏林飛艇,還有他和科沃戴爾超過一年的閤作。
這也就是我寫《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的目的。其實這本書是我們初次會麵後極為自然的衍生品。我認為吉米·佩奇是上個世紀最重要、最受歡迎的吉他手之一。我想也沒想就把他和那些藝術奠基人,如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和查剋·貝裏(Chuck Berry)等在藝術和商業成功之間架起橋梁的夢想傢排在一起。他的音樂經受住瞭時間的考驗,而且仍在持續激勵著那些在齊柏林飛艇解散後齣生的年輕樂迷們。他的話和故事都很有曆史意義。
我盡力誘使這位以擅長保護隱私而聞名於世的大師盡量多談些他那綿延多年、豐富跌宕的事業經曆。感謝我在《吉他世界》的職務,使我在過去的20年間有不少機會能和吉米聊聊天。雖然我覺得我們算不上朋友,但至少我們的關係是很友好的,我們在彼此的專業性之上建立起瞭相互尊敬的橋梁。
“專業性”是指,他隨和親切、舉止禮貌、對我尊重——隻要我不故意觸碰禁忌。他希望我能把自己的功課做好,隻討論客觀事實。為瞭在最大程度上保證這一點,我們的話題都隻集中在音樂上。隻要我遵守這些規則(當然不能明說),他便會和藹可親,且很真誠地接受采訪。
讓他推測他人對他音樂的態度的開放性問題,或者試圖讓他對其他音樂人做齣消極的評價的問題,都是他所討厭的。隻要你問瞭其中一種,就會讓原本進行得十分順利的訪問唐突地停下來,並且難以重新開始。作為一個作傢,這些限製雖然會給我帶來束縛,但是麵對音樂這片肥沃的土壤,這算不上什麼大問題。
說到禁忌話題,繞不開的便是佩奇對神秘學的狂熱興趣(這也是人們一聽說我能和他見麵就立刻問我的問題)。與大眾的想象截然相反,他從來沒有隱藏自己對魔法(magick,英國神秘學傢阿雷斯特·剋勞利(Aleister Crowley)為將魔法與魔術區分開而選取的拼法)和玄學的癡迷,這種癡迷也錶現在瞭他的音樂裏。但他發現很難深入地談論這個話題,因為論他說什麼,最後都會被人故意麯解或者斷章取義得聳人聽聞——他覺得這樣不僅侮辱瞭對他而言重要的東西,也會顯得他是個神經病。這麼想也沒錯。
不過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在這方麵的學問,分明是他的藝術作品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希望在必要的時候,他能多談論一些他的興趣愛好。搞不好這些信息還能讓那些喜愛魔法儀式、玄學和占星術的人茅塞頓開呢。
除瞭魔法,《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這不是一本傳統意義上全盤揭秘型的傳記,而是(至少我希望是)一本清晰的、由搖滾天纔自己講述的音樂人生,而它能給予讀者些許啓發。在音樂紀錄片《吉他英雄》(It Might Get Loud)中,吉米簡單地提到瞭對他而言“光與影”是什麼:
“力量十足的……雷聲;讓你陶醉的聲音。吉他之所以如此讓我著迷,是因為它有其他物體沒有的特性。每個人彈吉他都具有自己的風格,這和他們的個性也有很大的關係。”
就把這本書想作是建築在此觀念的基礎之上,一次傾聽藝術大師講解他的音樂的難得機會吧。
你會發現佩奇雖然是這本書的主角,但他絕不是這本書裏唯一的聲音。本書中涉及的其他人,在佩奇的經曆和音樂方麵,作為旁觀者提供瞭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而且他們的話也可以為佩奇的敘述增添有趣的細節。比如,我之所以把約翰·瓦爾瓦托(John Varvato)關於佩奇對時尚的影響的看法也寫瞭進來,是因為我覺得他有資格談論這個話題,而這也是佩奇給世人留下的重要元素之一。
我想這些材料中所呈現的,即是一個復雜的男人身上如吉米所言的那種被稱為“光與影”的東西。
前言/序言
序/布萊德·托林斯基50多年來,集吉他手、作麯傢、製作人等多重身份於一身的吉米·佩奇,對其所在時代的音樂産生瞭多重意義上的影響。年輕時,他與另外幾位音樂人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將美國的布魯斯音樂帶到瞭不列顛群島,所掀起的音樂革命為滾石、吉米·亨德裏剋斯(Jimi Hendrix)和奶油(Cream)等樂隊奠定瞭基礎。60年代,他在數不勝數的伴奏帶中刻下瞭自己齣神入化的吉他技巧。他曾與妮可(Nico)、喬·庫剋(Joe Cocker)、多諾萬(Donovan)和“他們”樂隊(Them)等各式各樣的藝術傢閤作,也幫助當時最受年輕人推崇的“搖擺倫敦”(Swinging London)製作瞭原聲。他和齊柏林飛艇開創性的演奏、作麯和製作不僅在70年代名列前茅,在之後的數十年間依然不斷引起共鳴。
即使到現在,佩奇的創造纔華依然讓世人驚嘆。他的上一部攝影自傳《吉米·佩奇自選集》(Jimmy Page by Jimmy Page),是對他的生活和事業最原始也最美好的解說;而他的新網站jimmypage�眂om,圖像和信息都十分豐富,也算能滿足他那遍布世界各地的粉絲對他工作和生活的好奇心。
考慮到他的成就與經曆皆多姿多彩,大傢或許以為關於他的書不會少。然而事實上,吉米·佩奇的個人世界始終遠離公眾視綫。
聽起來似乎是又一個“齊柏林飛艇之謎”齊柏林飛艇的職業生涯神秘色彩濃厚,有諸多傳言流傳於世,虛實難辨,故稱“齊柏林飛艇之謎”。,但這一個倒沒什麼故弄玄虛——主要是因為吉米·佩奇慣於保持沉默,畢竟他是那個在樂隊1976年的音樂會電影《歌聲依舊》(The Song Remains the Same)中喬裝成隱者的人啊。更重要的是,佩奇與音樂記者及樂評人曾有過一段不和睦甚至可說是敵對的曆史。而音樂記者或者樂評人,正是那批想寫搖滾傳記的人。
到底是怎麼搞僵的呢?說起來可能有點荒謬——在70年代早期,當齊柏林飛艇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時,熱衷跟風的搖滾齣版界對齊柏林飛艇的音樂總是——說得好聽些——沒什麼興趣,縱使現在它已廣受推崇。
當時的《滾石》雜誌特彆蠻不講理。1968年,樂評人約翰·門德爾鬆(John Mendelsohn)寫瞭一段關於齊柏林飛艇第一張專輯的389字解析,斷言這張專輯的價值“與它的大哥樂隊‘傑夫·貝剋組閤(Jeff Beck Group)’不可同日而語,基本是在炒傑夫·貝剋組閤的冷飯”。幾個月後,《滾石》又請這位門德爾鬆來評價《齊柏林飛艇Ⅱ》,而他用一句“整張唱片裏隻有那首特彆重型的歌值得一聽”把他們打發瞭。
《滾石》絕不是當時唯一一個挑刺的。1970年12月,底特律傳奇搖滾雜誌Creem刊登瞭一篇針對《齊柏林飛艇Ⅲ》的差評,臭名昭著。樂評人亞曆山大·愛斯奈(Alexander Icenine)佯裝自己吸毒過後思緒不清,以混亂的筆調來錶達他對這張專輯的衊視:
騎玻璃飛艇?那是什麼?每次睡下,我常常就此捫心自問。有時候我又想,為什麼他們不叫Red Zipper或者Load Zoppin�瞫ky Red Zipper與Load Zoppinsky,發音均相近。呢?然而論問幾次,都沒有答案,他們也從不迴答。
麵對這樣禮的評價和其他所謂“理性客觀”的評論,吉米·佩奇是怎麼做的呢?他乾脆徹底視瞭整個樂評圈。
隨著樂隊的日益走紅,評論也逐漸變得積極,佩奇對齣版界冷漠的態度亦有所緩和——但是不管怎麼說,裂痕都是難以修補的。老牌搖滾作傢揚·烏赫茨基(Jaan Uhelszki)仍然記得齊柏林飛艇1977年巡演期間她對吉米·佩奇進行的一次采訪,過程很有趣。
“當時,在整整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裏我和樂隊始終待在一起,但我就是沒法讓吉米給我一次采訪的機會。終於,他在巡演最後一天同意做采訪,不過有一個條件:他的公關人員必須在場。一開始我沒反應過來這是什麼意思,直到采訪的時候我纔明白,吉米規定我必須先把我的問題說給公關人員聽,然後再由她把這個問題轉達給他——即便我們說的是同一種語言,而且我和他之間的距離隻有6英尺。我們的采訪就以這種形式持續瞭大約1個小時。”
不過吉米也有權將自己禁錮起來——畢竟大部分記者隻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像外界所說的那樣吸毒、是不是和骨肉皮(groupie)大搞危險性愛以及他到底有沒有和撒旦簽訂惡魔契約。事實是,隻有一小部分的記者能夠在對待他或者他的樂隊時,像對待約翰·列儂(John Lennon)、基斯·理查茲(Keith Richards)和彼得·湯顯德(Pete Townshend)那樣嚴肅認真。不過隨著事情的發展,這些都不重要瞭。吉米那不為人知的私生活也成瞭環繞於其身的重重謎題的一部分——他成瞭搖滾史上的一個神秘人物。
而之後就該我登場瞭。
1993年,我第一次和佩奇說上話。作為《吉他世界》(Guitar World)雜誌的首席編輯,我給自己布置瞭一個任務,即采訪佩奇,和他聊聊那時他與白蛇20世紀80年代著名流行金屬樂隊。(White Snake)的大衛·科沃戴爾(David Coverdale)那頗有爭議的閤作。但說實話,我感興趣的是更加私人化的部分——作為一個從70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我是聽著佩奇的音樂長大的,他和新兵(Yardbirds)、齊柏林飛艇的作品嵌在我的基因裏。我一直都很欽佩他作為吉他手、作麯傢和製作人的創造力。他能當上製作人,全是憑藉著他不輸菲爾·斯派剋特(Phil Spector)和喬治·馬丁(George Martin)的創新精神。
作為一個記者,我一直都很好奇,怎麼就沒人問他那些事情呢?這正是我想讀到或者想寫下的東西。
佩奇總是對記者發脾氣,這一點對我而言當然不陌生,所以我也做好瞭心理準備。采訪過程雖說不上相談甚歡,但我可以看齣他很高興我能和他聊一些十分專業和復雜的技術及音樂問題。我們第一次的采訪進行瞭幾個小時,當他假裝被我那極具挑戰意味的提問搞得精疲力竭時(倒是展現齣瞭一定程度的幽默感),我們稍微放慢瞭一點速度。但我偏嚮虎山行,沒有就此停下,而是繼續進行更深一層的訪問。奇跡般地,這輪采訪又堅持瞭一個小時,而且佩奇也絲毫沒有擺齣搖滾大牌的架子。能感覺到他很高興能好好地談一談他的音樂——不止是齊柏林飛艇,還有他和科沃戴爾超過一年的閤作。
這也就是我寫《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的目的。其實這本書是我們初次會麵後極為自然的衍生品。我認為吉米·佩奇是上個世紀最重要、最受歡迎的吉他手之一。我想也沒想就把他和那些藝術奠基人,如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和查剋·貝裏(Chuck Berry)等在藝術和商業成功之間架起橋梁的夢想傢排在一起。他的音樂經受住瞭時間的考驗,而且仍在持續激勵著那些在齊柏林飛艇解散後齣生的年輕樂迷們。他的話和故事都很有曆史意義。
我盡力誘使這位以擅長保護隱私而聞名於世的大師盡量多談些他那綿延多年、豐富跌宕的事業經曆。感謝我在《吉他世界》的職務,使我在過去的20年間有不少機會能和吉米聊聊天。雖然我覺得我們算不上朋友,但至少我們的關係是很友好的,我們在彼此的專業性之上建立起瞭相互尊敬的橋梁。
“專業性”是指,他隨和親切、舉止禮貌、對我尊重——隻要我不故意觸碰禁忌。他希望我能把自己的功課做好,隻討論客觀事實。為瞭在最大程度上保證這一點,我們的話題都隻集中在音樂上。隻要我遵守這些規則(當然不能明說),他便會和藹可親,且很真誠地接受采訪。
讓他推測他人對他音樂的態度的開放性問題,或者試圖讓他對其他音樂人做齣消極的評價的問題,都是他所討厭的。隻要你問瞭其中一種,就會讓原本進行得十分順利的訪問唐突地停下來,並且難以重新開始。作為一個作傢,這些限製雖然會給我帶來束縛,但是麵對音樂這片肥沃的土壤,這算不上什麼大問題。
說到禁忌話題,繞不開的便是佩奇對神秘學的狂熱興趣(這也是人們一聽說我能和他見麵就立刻問我的問題)。與大眾的想象截然相反,他從來沒有隱藏自己對魔法(magick,英國神秘學傢阿雷斯特·剋勞利(Aleister Crowley)為將魔法與魔術區分開而選取的拼法)和玄學的癡迷,這種癡迷也錶現在瞭他的音樂裏。但他發現很難深入地談論這個話題,因為論他說什麼,最後都會被人故意麯解或者斷章取義得聳人聽聞——他覺得這樣不僅侮辱瞭對他而言重要的東西,也會顯得他是個神經病。這麼想也沒錯。
不過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他在這方麵的學問,分明是他的藝術作品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希望在必要的時候,他能多談論一些他的興趣愛好。搞不好這些信息還能讓那些喜愛魔法儀式、玄學和占星術的人茅塞頓開呢。
除瞭魔法,《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這不是一本傳統意義上全盤揭秘型的傳記,而是(至少我希望是)一本清晰的、由搖滾天纔自己講述的音樂人生,而它能給予讀者些許啓發。在音樂紀錄片《吉他英雄》(It Might Get Loud)中,吉米簡單地提到瞭對他而言“光與影”是什麼:
“力量十足的……雷聲;讓你陶醉的聲音。吉他之所以如此讓我著迷,是因為它有其他物體沒有的特性。每個人彈吉他都具有自己的風格,這和他們的個性也有很大的關係。”
就把這本書想作是建築在此觀念的基礎之上,一次傾聽藝術大師講解他的音樂的難得機會吧。
你會發現佩奇雖然是這本書的主角,但他絕不是這本書裏唯一的聲音。本書中涉及的其他人,在佩奇的經曆和音樂方麵,作為旁觀者提供瞭一些很有價值的觀點。而且他們的話也可以為佩奇的敘述增添有趣的細節。比如,我之所以把約翰·瓦爾瓦托(John Varvato)關於佩奇對時尚的影響的看法也寫瞭進來,是因為我覺得他有資格談論這個話題,而這也是佩奇給世人留下的重要元素之一。
我想這些材料中所呈現的,即是一個復雜的男人身上如吉米所言的那種被稱為“光與影”的東西。
……
用戶評價
剛讀完《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整個人還沉浸在那種震撼人心的氛圍裏。這本書簡直是為那些渴望瞭解Led Zeppelin幕後故事的粉絲量身打造的。吉米·佩奇本人親口講述,這本身就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他從樂器選擇,到編麯技巧,再到現場演齣的能量爆發,幾乎是全方位的剖析。最讓我著迷的是他對於“光與影”這個概念在音樂創作中的運用。他不是簡單地談論鏇律和節奏,而是深入到聲音的質感,那種如何通過吉他音色來營造齣一種既黑暗又光明,既神秘又直接的張力,簡直是技驚四座。他分享瞭大量關於專輯製作的細節,比如《Physical Graffiti》的錄製過程,其中一些意想不到的睏難和巧妙的解決辦法,都讓我大開眼界。我一直覺得Led Zeppelin的音樂有一種魔力,能夠瞬間抓住人的靈魂,而這本書則揭示瞭這種魔力是如何被一點點雕琢齣來的。佩奇的訪談風格非常直接,不迴避問題,無論是成功的喜悅還是失落的思考,都坦誠相待。他對於音樂的純粹追求,對於創新的不懈探索,都深深地打動瞭我。這本書不僅僅是迴憶錄,更像是一本關於如何進行純粹音樂創作的教科書,隻不過它的作者是傳奇中的傳奇。
評分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 終於到手瞭,這本書簡直是一場遲來的盛宴!作為吉米·佩奇的樂迷,多年來我一直渴望能更深入地瞭解這位傳奇人物的內心世界,他的音樂理念,以及Led Zeppelin那段波瀾壯闊的曆程。這本書以訪談錄的形式,將佩奇本人最直接、最真實的思考娓娓道來,仿佛他坐在我麵前,用他特有的低沉嗓音,一點一點揭開那些縈繞心頭的謎團。我迫不及待地翻開瞭第一頁,就被他那些關於早期音樂經曆的描述所吸引。他談到自己是如何從一個普通的樂手,一步步走上吉他大師的巔峰,其中的艱辛、靈感迸發,以及那些改變他音樂道路的關鍵時刻,都寫得淋灕盡緻。尤其是一些關於錄音室中的細節,那些關於音效、關於鼓點、關於吉他失真的細緻入微的講解,讓我仿佛置身於那個輝煌的時代,親眼見證瞭《Stairway to Heaven》的誕生。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音樂,更是關於一個靈魂的探索,關於藝術的堅持與創新。佩奇的語言樸實而富有力量,沒有絲毫矯揉造作,完全是一種源自內心深處的袒露。我特彆喜歡他談到自己創作中的“意象”和“氛圍”時,那種充滿哲學意味的闡述。他不是那種隻會炫技的吉他手,他是一位真正的音樂藝術傢,懂得用聲音去描繪畫麵,去傳遞情感。這本書讓我對Led Zeppelin的音樂有瞭全新的認識,也對佩奇本人這個人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評分這本書《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我拿到手就愛不釋手瞭。一直以來,吉米·佩奇在我心中都是一個充滿神秘感的音樂符號,他的吉他演奏技巧爐火純青,他所創造的Led Zeppelin更是搖滾樂史上的不朽傳奇。這本書以一種非常坦誠的方式,讓這位傳奇人物親自為我們講述他的音樂故事。他並沒有故作高深,而是用一種非常接地氣的方式,分享瞭他對音樂的理解,對創作的思考,以及在漫長的音樂生涯中遇到的種種挑戰與感悟。我特彆喜歡他談論自己如何從一個Session Musician,一步步蛻變成Led Zeppelin的核心人物,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他所經曆的自我懷疑與堅持。他對於音樂的“直覺”和“能量”的強調,讓我對搖滾樂的本質有瞭更深的體會。他不是那種隻會套用公式的音樂人,他更注重音樂的情感錶達和靈魂的傳遞。書中關於他對於吉他音色和錄音技術的細節描述,讓我這個非專業人士也能感受到其中的精妙之處。這本書不隻是關於Led Zeppelin,更是關於一個藝術傢如何用一生去追尋音樂的真諦,這種精神力量,遠比任何炫技都更動人。
評分《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這本書,給我帶來的不隻是對Led Zeppelin音樂的更深層理解,更是一種對藝術創作的全新啓迪。佩奇以一種非常個人化、也非常真誠的口吻,迴顧瞭他的音樂生涯,從早期在倫敦的樂壇摸爬滾打,到Led Zeppelin的輝煌,再到之後的個人探索,每一個階段都充滿瞭令人著迷的故事。他對於吉他音色和錄音技術的鑽研,簡直到瞭癡迷的程度。我一直對Led Zeppelin那種原始的、充滿力量感的吉他音色著迷,而這本書則詳細地闡述瞭他在這方麵的精妙之處。他如何通過不同的吉他、不同的效果器、不同的拾音器組閤,來營造齣那種獨一無二的“佩奇之聲”,這簡直是一門科學與藝術的完美結閤。更重要的是,他不僅僅是在分享技術,更是在分享一種創作哲學。他如何看待音樂中的“空白”,如何理解“節奏的動態”,如何運用“鏇律的張力”,這些都為我打開瞭新的思路。這本書讓我意識到,偉大的音樂是多種元素的精妙融閤,而佩奇正是那個將這些元素完美駕馭的巨匠。
評分拿到《光與影:吉米·佩奇談話錄》時,我便知道這將是一次意義非凡的閱讀體驗。這本書以一種近乎朝聖的方式,讓我得以窺探吉米·佩奇這位吉他聖手的心靈殿堂。他不僅僅談論瞭Led Zeppelin的那些經典歌麯是如何誕生的,更重要的是,他分享瞭自己作為一個音樂人,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思考和感悟。那些關於他如何從一個session musician成長為一代宗師的經曆,那些關於他如何在音樂中尋找新的可能性,如何在壓力和贊譽中保持自我,都寫得極其深刻。我特彆欣賞他對於“即興”的理解,他認為即興不是隨意的發揮,而是基於深厚功底和對音樂直覺的精準捕捉。書中關於他如何通過聆聽和感受去塑造歌麯的段落,讓我對音樂創作的本質有瞭新的認知。他的一些觀點,比如對“完整性”的追求,對“真實情感”的錶達,都遠遠超齣瞭單純的音樂技巧討論。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不隻提供信息,更提供瞭一種思考方式。它讓我明白,偉大的音樂不僅僅是音符的組閤,更是藝術傢靈魂的投射。佩奇的語言樸實而充滿智慧,每一句話都值得反復咀嚼。
評分正在看
評分好書
評分不錯的書,不錯的書。。
評分喜歡搖滾的朋友必備。
評分很好,包裝很仔細,喜歡
評分書是正版,買瞭還沒看
評分買的京東自營的,第二天就到貨瞭 ,非常速度,非常好
評分東西不錯以後還會買的。
評分沒看完,比較滿意!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他是誰? 探尋真實的鮑勃·迪倫 [Who is That Man ? In Search of The Real Bob Dyla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14017/559c72d1N584eee4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