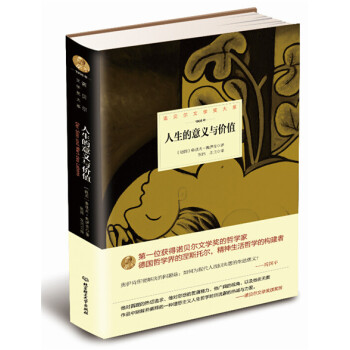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米沃什的辞世,令诗歌具有救赎力量这一古老的信念在世界中失去了一个可靠的见证。”——希尼《新共和》
★“关注衰老和死亡的问题,《第二空间》为九十三岁的诺贝尔奖得主米沃什进一步赢得了‘伟大的诗人’的称号。”
——爱德华·赫希《纽约时报》
★《第二空间》是诺贝尔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新诗集,它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诗歌朝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英文版推荐语
内容简介
《第二空间》是米沃什晚年最后一本诗集,在他去世那年出版,写作时诗人已逾九十岁。如同诸多伟大的作家高龄时一样,面临大限,此时他们往往从宗教的角度寻找“生死”这个永恒问题的答案,是一生寻遍之后的归宿吗?时间的意义、生命的真相,乃至神学的真伪,等等,一个老人的思考,远离了尘世的纷扰,而与最终世界更相接近,安静,广阔,深邃,悲悯。米沃什在国内已经享有深远的影响,有众多崇拜者,这本诗集是首席推出,当能引起读者关注。
作者简介
切斯瓦夫·米沃什,一九一一年生于立陶宛,二战时参加了华沙的抵抗纳粹的运动,战后作为波兰文化专员在纽约、华盛顿和巴黎工作。一九五一年出走巴黎,一九六〇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是美国人文艺术学院会员之一。一九八〇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二〇〇四年去世。米沃什的诗歌注重内容和感受,广阔而深邃地映射了二十世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动荡历史和命运。其主要著作除了诗歌外,还有《乌尔罗地》《路边狗》《被禁锢的头脑》等随笔和思想性著作,被视为二十世纪东欧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周伟驰,翻译家、诗人和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出版有译诗集《沃伦诗选》《梅利尔诗选》《英美十人诗选》,诗集《蜃景》《避雷针让闪电从身上经过》,诗歌评论集《旅人的良夜》和《小回答》。
目录
CONTENTS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高兴
米沃什晚期诗歌中的历史与形而上(中译本前言) 周伟驰
第一部分
第二空间
晚熟
假如没有上帝
在克拉科夫
框架
维尔基
优势
教我手艺的一个师傅
一次停留
一个老妇人
同学
房客
守护天使
美丽的陌生人
贬低本性
我现在应该
高地
不适
倾听我
科学家们
商贩
保险柜
我
退化
新时代
眼睛
笔记本
多层次的人
第二部分
塞维利奴斯神父
第三部分
关于神学的论文
第四部分
学徒
第五部分
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
精彩书摘
第一部分第二空间
天厅是何其地敞亮!
经天梯走近它们。
白云之上,便悬着极乐花园。
灵魂把自己从肉体撕开翱翔。
它记得有一个“向上”。
也有一个“向下”。
我们真的对那别一个空间失却了信心?
天堂和地狱,都永远地消逝了?
若无超凡的牧场,如何得到拯救?
被定罪的,到哪里找到合适的住所?
让我们哭泣罢,哀恸损失的浩大。
让我们用煤渣把脸擦脏,再蓬乱头发。
让我们哀求把它还给我们:
那第二空间。
……
前言/序言
米沃什晚期诗歌中的历史与形而上(中译本前言)
周伟驰
米沃什(1911—2004)是一位长寿的诗人,活了九十三岁,获得过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真正算得上“圆善”——德福合一了。天主教徒与长寿的关系,曾有搞宗教的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大概跟定期的告解有关——它有助于纡缓现代人常有的焦虑。是啊,既然把一切忧愁痛苦都交给天主了,一个人怎能不心情舒泰呢?米沃什晚年一首小诗《礼物》,颇有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逸趣,当是其身心惬洽的写照。
米沃什来自波兰(更准确点是立陶宛)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可是他跟天主教的关系如何,似乎未见专文写过。中国诗人译米沃什,大都对他的东欧经验感兴趣,这是情境相似引发的共鸣。可是翻译欧洲诗人,如果不了解他们背后的宗教传统,到底是隔靴搔痒,难有深契,只能看到一些政治、技艺类的形而下。这就好比一个外国译者翻陶渊明或杜甫,如果他对于儒道不了解,就只能做字句或意象的对译,却难以译出文字背后的精义。
米沃什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诗人兼思想家,空间上跨了东欧、西欧和美国,制度上跨了纳粹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时间上跨了整个“极端的年代”,他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纪西方史。他的诗多是直抒胸臆,行云流水,对内容的关注胜过了对语言的在乎(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尽管他的诗各体完备),因此在技法上他或许不如希姆博尔斯卡、赫贝特,但是在历史的沧桑感上,在文明视野的宽广上,在胸怀的博大上,却可说是略胜一筹。
《第二空间——米沃什诗选》(后简称为《第二空间》)是米沃什晚年——不,应该说是“高年”——时期的诗集,是他去世那年出版的,写作时诗人已逾九十岁。这无疑打破了叶芝、哈代、沃伦的纪录。
米沃什在诗里写了些什么呢?这跟一个高龄诗人面临的迫切的问题有关:他必然思考“生死”这个宗教核心问题,顺带牵出时间、生活的意义、写作的意义,乃至神学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奇怪,诗集大部分的诗都跟神学搅在一起,有一首就干脆以“关于神学的论文”作题。
诗集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二十八首短诗,哀叹老年已至,从前身边的同龄人和曾经爱慕过的美人都已消逝无踪,他们的事迹荡然无存,无人记忆,作者自己也垂垂老矣,身心不一(身体不听大脑指挥),唯有在回忆中度日,在记忆中穿梭。回顾一生,作者对于“自我”发生了疑问:镜中人到底是谁?一生的经历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到底是天使还是动物?上帝到底有没有,现代人不信上帝会导致何等后果?进化论的后果为何?人死之后到底有何归宿?《第二空间》这首标题诗,就点明了这整本诗集的主旨:
我们真的对那别一个空间失却了信心?
天堂和地狱,都永远地消逝了?
若无超凡的牧场,如何得到拯救?
被定罪的,到哪里找到合适的住所?
让我们哭泣罢,哀恸损失的浩大。
让我们用煤渣把脸擦脏,再蓬乱头发。
让我们哀求把它还给我们:
那第二空间。
用煤渣撒头发,这是《旧约》中犹太人表达哀恸绝望的方式。如《约伯记》第二章记载,约伯受上帝考验,浑身长满毒疮。他的三个朋友来看望他,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
米沃什这是在哀叹现代西方人渐趋于有形无形的无神论,有形的无神论好理解,无形的无神论指什么?指对宗教问题根本不关心、不在乎,它比有形的更具杀伤力——起码后者还关心这个议题!在另一首短诗《假如没有上帝》里,米沃什更道出了他对于上帝的态度:
假如没有上帝,
人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仍旧是他兄弟的照顾者,
他不能让他的兄弟忧愁,
说并没有上帝。
我们知道,对于欧洲人来说,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问,没有了上帝,人怎么办呢?岂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了?欧洲人没有宋明理学“天理”的概念,故有这样的问题提出。米沃什的态度看来跟孔子有点类似:即使上帝不存在,你也不能说,否则你显得多么残忍啊!还是遵照传统的仪式吧!祭神如神在就好了。在《不适》里他说:
我尊重宗教,因为在这个痛苦的地球上
它乃是一首送葬的、抚慰人心的歌。
对于进化论和现代科学,米沃什的态度跟上面这首短诗《假如没有上帝》一致。在《科学家们》一诗里,他写道:
查尔斯·达尔文
在公开他的——如其所说,恶魔式的理论时,
至少有良心的痛楚。
而他们呢?说到底,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的:
把老鼠隔离在不同的笼子里。
把人类隔离开来,把他们自己的同类
当作遗传学的浪费一笔画掉,毒死他们。
在别的地方他也反对进化论,认为它把人拉低到动物的水平,而忘记了人的神性来源和道德来源(人是上帝的形象),对于现代大屠杀一类的事终究是有责任的。对于欧洲现代人来说,既然传统的以上帝为依托的世界观不复存在了,便以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科学主义世界观来取而代之。纳粹之种族主义、优生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最终导致了将人视为物,单纯从进化得失去看问题和处理问题,而使得欧洲伦理堕落,发生了二战中“屠犹”这类惨无人道的种族大灭绝。
我相信米沃什对待上帝和基督教的态度是一种现代欧洲人的矛盾、尴尬和犹豫的态度:一方面他们的大脑告诉他们,上帝难以被证实存在;另一方面他们的意志告诉他们,不能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就什么都没有,只有虚无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发展出了一种神圣的悖论,用庄子《齐物论》中的话说,“吊诡”。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那里有突出表现,在米沃什这里也不例外。在《倾听我》这首诗里,诗人说:
倾听我,主啊,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这就是说除了祷告我什么也没有。
保护我远离江郎才尽和无能为力的日子。
当无论是燕子的飞行,还是花市上的牡丹花、水仙花和鸢尾花,都不再是你荣耀的象征。
当我将被嘲笑者包围,无力反驳他们的证据,记起你的任何一个奇迹。
当我将在自己看来成为一个冒名顶替者和骗子,因我参加宗教仪式。
当我将指责你创立了死亡普遍的规律。
当我最终准备向虚无低头,将尘世的生活称作一个恶魔的杂耍。
这就是一个眷恋着基督教传统的现代欧洲知识分子的心脑矛盾。它终归和纯粹的无神论人文主义者不同,也跟恪守信仰不做反思的基要派不同。这是一种“吊诡”的精神生活。
第二部分名为《塞维利奴斯神父》,是以一个自认为“没有信仰”的神父的眼光来看终极关怀和基督教的问题。在他看来——
人们不过是节日里的牵线木偶,在虚无的边缘跳舞。
十字架上强加给人子的折磨
之所以发生,不过是为了让世界显出它的冷漠。
在他看来,西方人满世界地传教,甚至乘着太空船向外星球传教,但到头来,“他(耶稣)的肉体,横伸在耻辱柱上,/遭受着真实的折磨,关于这我们每天都试着忘记”。很多人上教堂只是出于形式,是表面功夫:“说真的,他们又信又不信。/他们去教堂,免得有人以为他们不信神。/神父讲道时他们想着朱利娅的奶头,想着一头大象,/想着黄油的价格,想着新几内亚。”作为神父,塞维利奴斯虽然穿着法袍,却并没有底气——
我的长袍,属于神父和告解者,
恰好用来包裹我的忐忑和恐惧。
我们是不一贯的人。
我嫉妒群众在世界里的安定。
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孩子在教导成年人,
给出劝告像纸做的大坝对着狂暴的溪流。
作为天主教神父,神人之间的中介,他们的工作时时要遭到信众的怀疑(宗教改革派就取消了神父这一中介),饱受失业的威胁。对于神学中的难题,如三位一体、原罪,这位神父认为君士坦丁皇帝用权力干涉教义,使得后世的人代代都要受折磨,历史充满戏剧性的反讽。现代人再也不信地狱,但是来告解的人里面,如利奥尼亚,还是相信的(出于良心的公平潜意识?)。
我认为这首长诗中,最出色的要算这么一段:
假若所有这些都只是
人类关于自己的一场梦呢?
而我们基督徒
只是在一场梦里梦见了我们的梦?
诗人长期在加州工作和居住,对于东方哲学自不陌生(他编的世界诗选中选了大量的中国古诗),对于佛教、印度教乃至庄子的“庄周梦蝶”和“大圣梦”都不会陌生,它们所透现出的非实在论(佛教梦幻泡影喻不用多说了,以商羯罗为代表的不二论视世界为梦幻亦有传统)对于西方神哲学实在论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引起诗人的反思。现代西方对于尘世之“变”的关注,使得西方哲学开始摆脱“永恒”理念世界而领略到“幻”的滋味,叔本华直接从印度哲学获益,尼采则亦回到赫拉克利特“变”的哲学,这种潮流在诗人那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受柏格森影响的马查多,亦对于东方哲学有所体会。米沃什无疑对这种哲学有所意识。但他仍在摇摆之中,他的情感和意志仍旧使他感觉到需要一个实在论的上帝,以及实在论的天堂和地狱(“第二空间”),来保证在二十世纪西方备受摧残的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他才会借塞维利奴斯神父之口说:
主啊,你的临在是如此真实,比任何论证更有分量。
在我颈上和我肩上,我感到你温暖的呼吸。
我想要忘记神学家们创造出来的精巧的宫殿。
你不经营形而上学。
这里意志战胜了理性,虽然理性无法论证一个上帝,但是意志和情感体会到了并且极其需要一个上帝。这里“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更加剧烈了。我们感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和阿廖沙的矛盾。
第三部分是一首原文近五百行的长诗《关于神学的论文》。作者思考了恶的来源问题、神正论问题、原罪问题、进化论、神迹问题等。作者自认为是“一个信仰微弱的人”,“一天信,一天不信”。但是奇怪的是,他喜欢跟祷告的人们在一起,觉得温暖,“自然,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但我跟他们一起唱,/于是克服了存在于/我的私人宗教和仪式宗教之间的矛盾。”这首诗是米沃什晚年写的最长的诗之一,是对他在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心态、心脑冲突及解决办法的一个尝试。
第四部分《学徒》是写他的一个很有名的堂兄奥斯卡?米沃什(1877—1939),他生在波兰但在巴黎读完中学,后来成为一个诗人兼神秘主义哲学家,亦曾在一战后为争取立陶宛独立而出谋划策,并提出过“欧洲合众国”的构想。他曾经在二战发生十年之前(1929年)就预见到德国人将在波兰和东普鲁士之间的走廊地带发动战争,他
警告一场大战正骑在末日大劫的红马上
迫近,一场大战将从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开始。
这里“红马”的形象来自《启示录》6∶34,“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据米沃什的研究,奥斯卡之所以预见到德国将发动战争,是因为他认为德国人的民主只是肤浅的表面功夫(魏玛共和国),未深及精神,不是真正的民主。也许这背后奥斯卡有他的理路——比如,德国人做不到英美的民主制度也许跟他们的整体主义的世界观有关?或跟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太强大有关?——但是米沃什没有提及,这就有待将来的人们的研究了。
奥斯卡的一些思想(如神学异端思想,如世界有一个开端的想法,后者类似于今天的“大爆炸理论”)和作品(如关于唐璜原型、西班牙人米格尔?马纳拉的戏剧),对米沃什有很深的影响。米沃什年轻时钟爱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史维登堡,也与他有关。诗名《学徒》的意思来自于第八章中所说的“我不过是一个炼金术师父的学徒”,暗示作者以堂兄奥斯卡为师父,也像他的堂兄一样,继承了欧洲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派别的精神。这首长诗原文连诗带注,达三十页,占了《第二空间》这本集子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不只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奥斯卡的生平活动、传奇故事、创作与创见,以及米沃什本人跟奥斯卡的精神上的交织,更难得的是通过叙述米沃什家族的历史,折射出更为广阔的立陶宛、波兰乃至近代欧洲的历史变迁,米沃什作为一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诗人和思想家,夹叙夹议,融情感与理性于一炉,将历史沧桑感和个人命运糅合进同一景框(如第二章写作者跟威尼斯的关系,数行之内就提及在那里埋葬或待过的拜伦、布罗茨基、庞德、奥斯卡),起点就已迥异寻常诗人。
我常常想到威尼斯,它回旋着就像一个音乐主题,
从我战前第一次到访,
在丽多岛海滩上看到
以德国女孩面孔出现的女神戴安娜,
……
用户评价
我得说,这本书的结构设计简直是鬼斧神工。它不是那种线性叙事可以概括的,更像是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由无数个看似独立的线索构成,但当你深入阅读时,会发现这些线索是如何精妙地相互交织、互相印证,最终汇聚成一个宏大且逻辑严密的整体。这种叙事上的复杂性和精密度,让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强大的掌控力。有时候我甚至会停下来,拿出纸笔画出人物关系图谱,试图梳理清楚那些隐藏的联系。更厉害的是,尽管结构复杂,作者却能用一种非常清晰流畅的方式呈现出来,保证了读者在跟随故事发展时不至于迷失方向,反而会被这种层层剥茧的惊喜感所驱动着继续前行。它成功地在“烧脑”和“易读”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这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成就。
评分坦白讲,我过去对“文学性”的理解可能比较狭隘,总觉得它必须是晦涩难懂的。但这本书彻底地拓宽了我的视野。它的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韵律感和美感,读起来赏心悦目,充满了古典文学的底蕴,但在表达现代概念和处理当代情感时,却又显得无比前卫和大胆。作者在遣词造句上功力深厚,常常用一个不常见的词汇,却能瞬间精准地捕捉到那种难以言喻的心境,让人拍案叫绝。阅读它,就像是在欣赏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经过了深思熟虑,没有任何冗余。这种对语言本身力量的极致运用,使得故事的感染力倍增,即便是最平静的描述,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是一次对语言美学的极致探索,读完后,我感觉自己的词汇量和对语言的敏感度都有了质的提升。
评分说实话,我本来对这类题材的接受度不是特别高,但这部作品彻底颠覆了我的固有印象。它的语言风格非常鲜活、充满生命力,读起来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完全没有传统严肃文学那种高高在上的距离感。作者似乎很懂得如何与读者“对话”,那种平易近人却又充满智慧的表达方式,让我感觉就像是坐在老友身边听他娓娓道来一件惊心动魄的奇遇。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对话,简直可以单独拿出来分析研究。人物之间的化学反应极其真实自然,哪怕是立场对立的角色,他们的交锋也充满了张力,不是简单的正邪对抗,而是复杂人性光谱下的碰撞。每次读到高潮部分,我都要不自觉地放慢语速,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妙的措辞。这本书在情感层面的处理也相当到位,那些关于失去、关于寻找、关于成长的描绘,精准地击中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让人忍不住想落泪,但泪水里又带着一种释然和希望。
评分哇,这本书真是让人眼前一亮!从一开始翻开书页,我就被那种扑面而来的独特氛围给牢牢抓住了。作者的笔触极其细腻,仿佛能触摸到文字背后的真实质感。它构建的世界观宏大而又充满了细节,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角色的内心活动都描绘得入木三分。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叙事节奏上的把握,时而疾风骤雨般推进剧情,让人屏息凝神,时而又缓缓铺陈,让读者有足够的时间去品味那些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不仅仅是讲述了一个故事,更像是一次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邀请函。我读到一些关于人性和社会结构的反思,这些思考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巧妙地融入到情节发展中,让你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不知不觉间被引导着去审视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读完之后,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特别强烈,脑海里还会时不时地回想起那些令人震撼的转折点,并且开始主动去揣摩作者埋下的那些伏笔,真是一本值得反复咀嚼的佳作。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场沉浸式的感官之旅。作者对于场景的描绘,简直可以直接拿去拍电影级别的素材。我能清晰地“看到”那些光影的流动、空气中弥漫的气味,甚至能“听到”背景声效的细微变化。这种极强的画面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于细节的偏执。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丰富场景的元素,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摆设、一种特定的天气现象,都可能在后续的情节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读到后半部分,我已经完全脱离了“在阅读”的状态,而是真切地感觉自己“存在于”故事的那个世界之中,与角色一同呼吸、一同面对困境。这种深度的代入感,是许多作品梦寐以求却难以达到的高度,而这本书,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让人心驰神往,恨不得立刻钻进书页里去。
评分??????????????
评分活动很优惠,买了很多,慢慢看
评分大师代表作品,值得品读!
评分花城的米沃什诗选,值得收藏,又一珍本的节奏啊
评分快速反应能力机制创新
评分蓝色东欧都不错,喜欢
评分还可以,物流挺快,东西也好
评分因为那首小诗礼物才来的 喜欢zuozhe
评分因为那首小诗礼物才来的 喜欢zuozhe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尤利西斯.摩尔推理冒险系列(套装共6册)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38248/5672705cN3fb87277.jpg)

![彭绪洛科学探索书系(套装共8册) [7-11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44013/567bac52N6402dd8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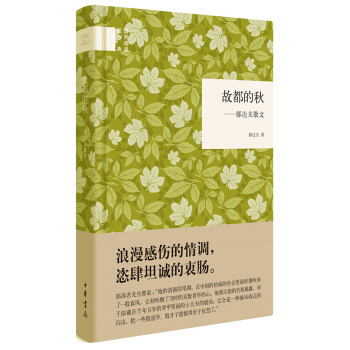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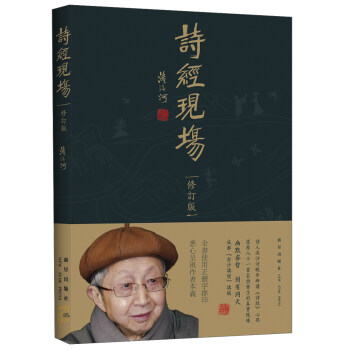
![少年幻兽师系列6:英雄学院的诞生 [8-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32975/58f5b705N9385791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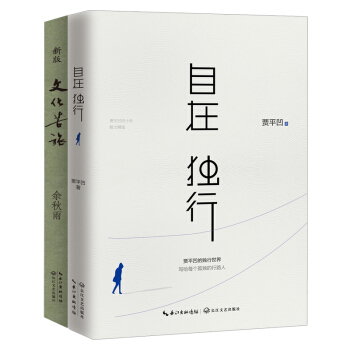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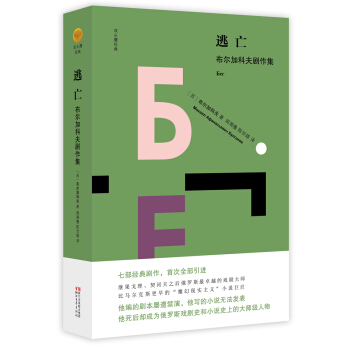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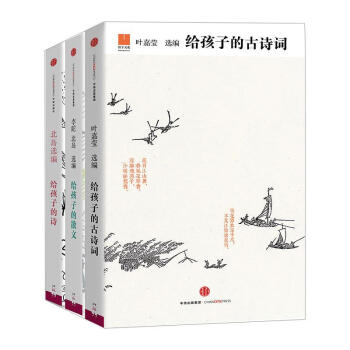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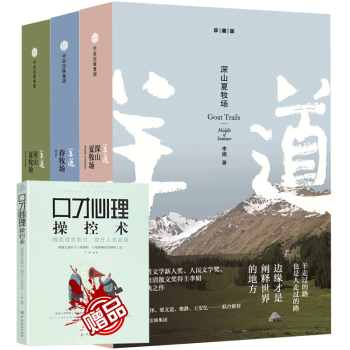


![越南小英雄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73809/rBEQWFEPUXgIAAAAAAhsg0DjIHIAAAjdQGaP24ACGyb918.jpg)
![丛林故事(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56260/577f3c46N1a45578e.jpg)
![夏洛书屋:穆尔克国的故事(第三辑)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43604/5397a7f4N0ae52ba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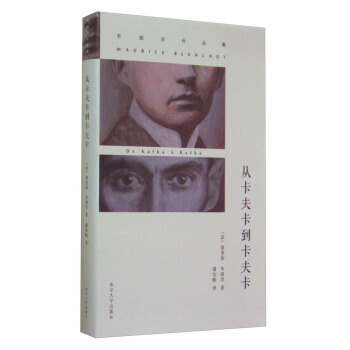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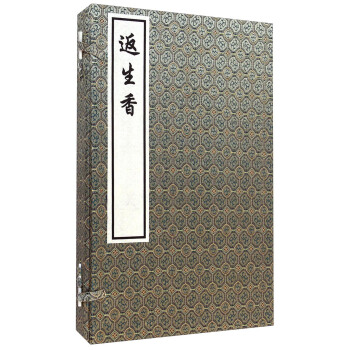
![曹文轩推荐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惜城的同桌日记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8299/55541667N0feb020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