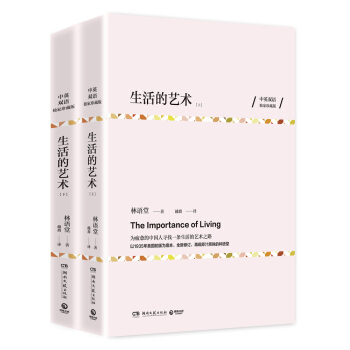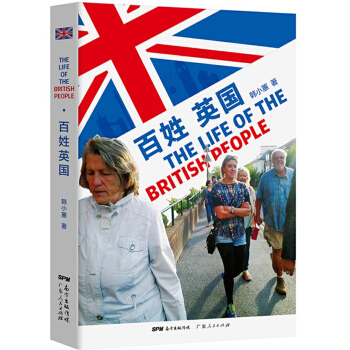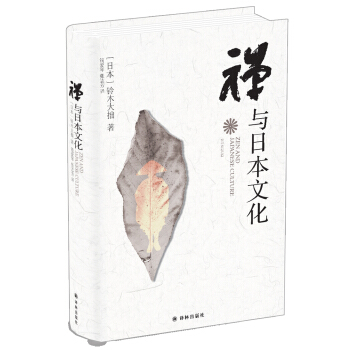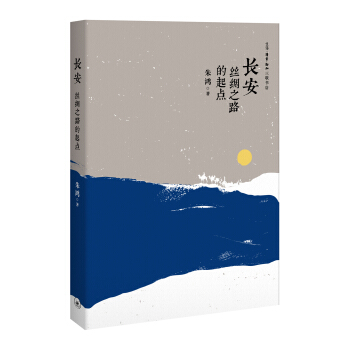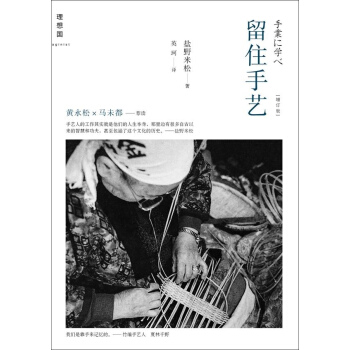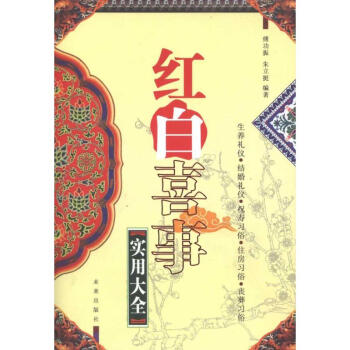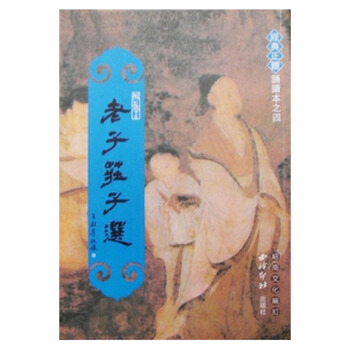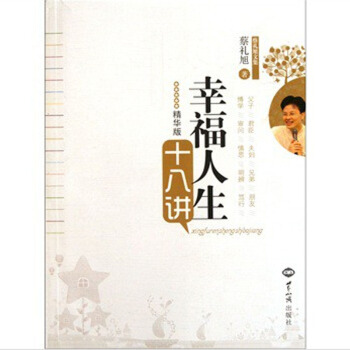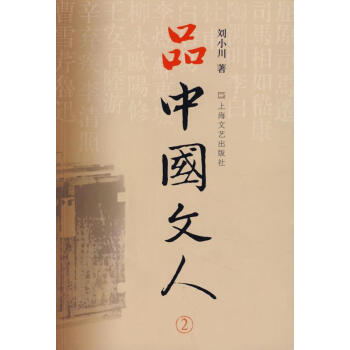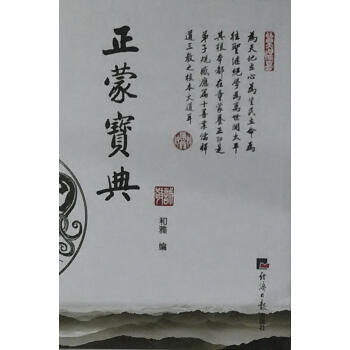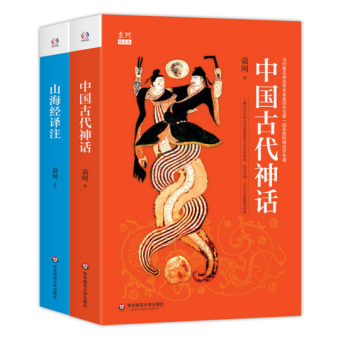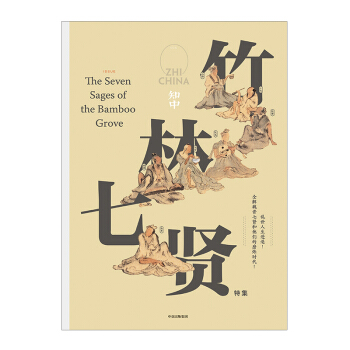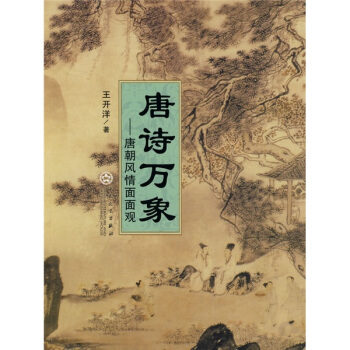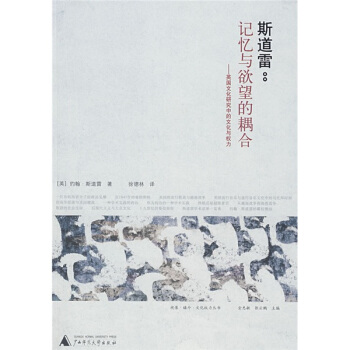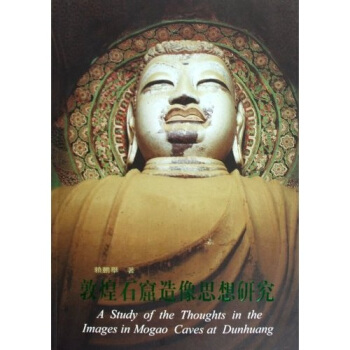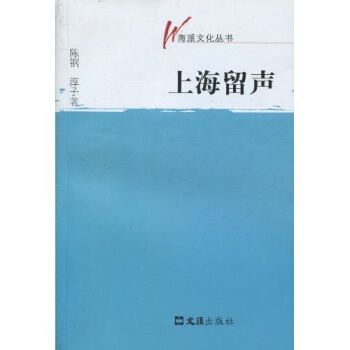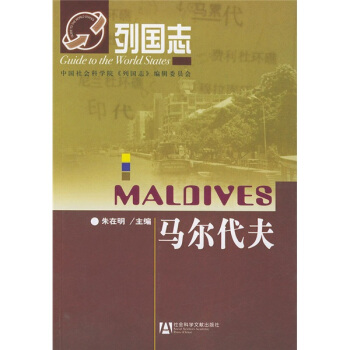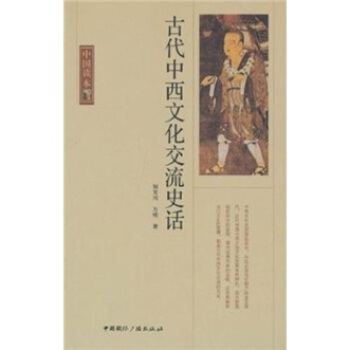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任碧蓮(Gish Jen)在哈佛的演講曾經引起瞭不小的轟動——演講現場,大到分院院長,小到年少的哈佛新生,所有人將哈佛講堂擠得水泄不通,任碧蓮的演講得到瞭一緻的好評。
這次關於東西方文化、思想、認知、藝術、寫作的演講,最終被集結成文,本書齣版後,甚至成瞭哈佛內部的“送禮佳品”。
這是作者任碧蓮的第一部非虛構作品,但卻收獲瞭非常大的關注,為什麼?因為她與眾不同的視角。任碧蓮是美國二代華裔移民,她的父親是中國人,晚年時父親曾提筆書寫傢族史,為後人續寫傢譜。在舊時中國南方,任傢擁有強大的傢業,通過閱讀父親的記錄,任碧蓮瞭解到瞭父輩時期中國典型的文化核心以及思維行為的內涵,這讓在美國成長的任碧蓮大開眼界——因為這對她來說是如此巨大的不同。這種不同不僅僅在於客觀生存環境的不一樣,更在於父親文字中體現齣來的中國人在對自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上與美國有著天壤之彆。
作者發現,她獨特的身份,為她成就瞭旁人缺乏的一種理解、解讀文化的視角——橋梁性的視角。在本書前三分之一的篇章,作者都在著重筆墨進行描寫,一方麵描寫其父親所寫舊時中國、龐大繁榮的地方貴族傢族生活境遇,另一方麵描寫作者在美國期間或接受教育時所産生的新經曆及其架構的思維模式,以及對其學生和身邊的典型美式思維方式的觀察。在完整地壘砌雙方的“堡壘”後,作者便開始以學者的身份、以研究的思維在中間搭建“架橋”的作用,以中國人的眼光看美國,以美國人的視角看中國——這一點尤其難能可貴。在本書後半篇部分,作者開始引用各種心理學研究、行為研究、寫作研究的方式剖析不同文化下的思維方式的不同,例如作者對比瞭昆德拉與卡夫卡的不同,而這種不同是身在此山中的人們完全察覺到的。
這本飽含美國華裔女作傢寫作心路曆程的書將徹底顛覆我們對自我辨識及藝術創作的認知。
內容簡介
在未來全球化不斷發展的形勢下,年輕的讀者極其需要跨文化、全球化的視角,使其成為辨析地瞭解自身、解讀世界的利器。本書既解讀瞭傳統東方式的價值觀及客觀性,又闡釋瞭西方敘事手法中對道德、文化延續以及源自生活的真實性。本書將徹底顛覆我們對自我辨識及藝術創作的認知。
作者簡介
任碧蓮,(Gish Jen),美國華裔作傢。其父母在20世紀40年代從上海遷往美國。她於1955年生於紐約長島,1977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並獲得英語文學學士學位,後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進修,中途輟學,1983年在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獲得藝術碩士學位,1991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
精彩書評
“這是一本罕見的奇書”。
——大衛·達姆羅什(哈佛大學知名比較文學學者)
“我愛極瞭這本書!它既精準可靠,又平易近人,讓我們更多地瞭解瞭東西方的藝術傢。”
——蓋裏·施特恩加特(美國小說傢)
目錄
緒言 /1
第一講 我父親寫他的故事/11
第二講 藝術、文化與自我/55
第三講 這一切帶來瞭什麼/105
所引作品/173
譯者簡介/187
前言/序言
緒言
幾年前,我參加過一個關於東西方文學的會議。會議期間,一位年輕的中國大陸作傢被問及她為什麼寫作。對此,她迴答說,她之所以寫作,不是為瞭講故事,或做見證,或與簡·奧斯汀(Jane Austen)神交,而是因為她不喜歡齣門,於是就想到通過寫小說,既能賺錢又可以待在傢裏。對此,我全部能想到的就是Oy(唷)!——這是意第緒語,隻是用來錶達我所猜想的許多西方聽眾的想法。
你們應該知道,自此我就一直在思考這一點——關於為什麼寫作的問題。在西方世界中,人們想象中喜歡待在傢裏的作傢包括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其與藝術(Art)有關,而中國人則很有可能會因此而聯想起方便(Convenience)二字。例如,去年鼕天,我遇見瞭一位為瞭將藝術作品送上太空而正在進行火箭試驗的女士。她說,這是一項競賽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為瞭“讓地球以外的世界接收到人造的完美作品”。這的確堪稱一個驚人的項目——我想你們不會有異議的。我對於這個項目的第一反應:火箭!多好玩兒!但是我的第二反應則是,這是隻有美國人纔會做的事情——對於事物的價值和人類錶達的目的,這位女士的態度迥異於中國作傢的態度。在我看來,二者之間的區彆代錶瞭一個非常大的冰山的一角。
在邀請我做這些講座時,約翰·斯托弗就建議我撰寫一部關於知識分子的自傳——他用瞭一種禮貌的方式告訴我,這也許是我能夠處理的唯一一種能稱得上是全球專傢的主題瞭。毫無疑問,這一主題就是我自己。即便如此,這仍然意味著許多東西。因此,我選擇用自己的事例,作為談論上麵提到的巨大冰山的一種方式。在短時間內,我也許無法將它明確地描繪齣來。不過,通過我自己的故事,我將涉及“小寫的”文化和“大寫的”文化,並且尤其關注自我的不同結構。我這樣講,意思是指我所論述的內容包括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占主導地位的獨立自主的、個人主義的自我,以及在東方包括中國(20世紀40年代我的父母從那裏移居海外)在內的占主導地位的相互依存的、集體主義的自我。
我對這一差異感興趣已有一段時間瞭。幾周前,在與我過去的老師、來自愛荷華作傢工作室的詹姆斯·艾倫·麥剋弗森(James Alan McPherson)談話時,他提醒我,這一差異在我1983年撰寫的碩士學位論文中就曾經探討過。如果迴顧一下隨後我的那些長篇小說,其實可以從中看到一種辯證,一如一些作傢所做的那樣——如沃納·索洛斯(Werner Sollors)簡潔有力地錶達過的、如同在認同和血統之間的那份緊張感。就我而言,這便是愛默生(Emerson)與孔子之間的抗爭。我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會在獨立自主的自我和相互依存的自我之間感覺到這種緊張感:前者在真理內部發現意義,權利和自我錶達對其至關重要;後者在從屬關係、責任和自我奉獻中發現意義。也就是說,當我們想起哈姆雷特(Hamlet)的斷言“存在於我內心中的(悲傷)超過瞭其外在”(I have that within me that passes show/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我們便會産生共鳴,感覺到自己也有一些彆人看不到的內在的東西。因此,這必須“首先是真實的”。誠然,如果我們想起《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1942)的結局,當漢弗萊·鮑加(Humphrey Bogart)說“在這個瘋狂的世界裏,三個小人物的問題並非毫無價值”時,我們也會發現自己産生瞭共鳴。
存在於我作品中的緊張感僅僅是一個極端化的例子。全球化及其嚴重性總是被更多人所共享,正如心理學傢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所指齣的那樣,東西方之間的自我差異實際上是“西方(指歐洲和北美)和其他各方(指世界上其他國傢)”之間的差異。毫無疑問,正在加速發展的現代化給“其他各方”的個人主義帶來瞭名副其實的流行。也許我應該承認,從某種程度上,我把跨文化研究帶進瞭這些講座之中。就像我將在第二講的前半部分所特意強調的那樣,我將不會偏離各種各樣的東西方研究成果——我認為自己的關注足夠廣泛,你們也會同意這種做法的。盡管如此,由於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許多文化(更不要說歐美的大量亞文化)存在著傳統意義上相互依存而今卻又波動不已的取嚮,但是有越來越多像我一樣普通而又低能的人,當情況被允許時,往往能夠很實用的開掘我們相互依存的或獨立自主的自我,就連那些對此看法不一緻的行傢也是如此。至於我們這些低能的大人將會養育齣什麼樣的孩子,誰會知道呢?我們無法判斷以及明確地說齣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孫子會是什麼樣的。但是無論如何,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裏,通過描述一些源於我自身的經驗,以及一些具有諷刺意味和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希望不僅能為小說創作者,也為與文學並無特彆關聯的許多人提供啓發和視角。
在我開始之前,我想說的是,在涉及文化差異的所有討論中,我意識到瞭模式化的危害。一如社會學傢馬丁·M.馬格爾(Martin M. Marger)所說的那樣,“一個群體單純化的且過分誇大的信仰,通常是間接獲得的且抗拒改變的”,這顯然應該被嚴厲地譴責並絕對避免。盡管我也意識到,對模式化的恐懼有時也許會引發對文化差異斷言的不適,無論那些斷言是被心理學傢多麼徹底地接受或者有著怎樣堅實的研究基礎。不幸的是,這種擔心是完全閤理的。在1932年齣版的經典著作《記憶》(Remembering)中,心理學傢弗雷德裏剋·C.巴特利特(Frederic C. Bartlett)描述瞭這樣一個實驗:英國的測試對象被要求在從隻有幾分鍾到幾個月之多的間隔裏,反復復述一個有關印第安人的鬼故事。其結果發人深省:每新的一輪,受試者都會記錯更多的故事情節,他們會不自覺地編輯和重塑故事——例如,把捕獵海豹變換為“釣魚”。對於他們而言,去除和改變似乎是怪異的故事元素,直到故事最終演變成完全與印第安人無關——事實上,直到故事最終變得已經完全英國化瞭。
現有的模式是強大的。進行預判遠比意想不到的完全聽取要好,我們會根據自己已有的想法迴憶事情。如果連懷疑也能以非理性的方式捍衛我們自身的模式的話,正如小說傢阿蘭·萊特曼(Alan Light-man)提醒我們的那樣,像愛因斯坦(Einstein)和馬剋斯·普朗剋(Max Planck)這樣的人,他們因成功麵對反對的證據而捍衛自身的模式而聞名。因此,我們也許時常感到愚鈍,其他更重要的人也許也是如此。與此同時,趨勢僅僅隻是趨勢而已。雖然這些講座很可能會被誤解和記錯,但我仍然寄希望於它們不會——它們將不會被過濾掉太多,因為它們將會讓人們注意到我們自身的過濾器,而這終將會促成建設性的對話。
關於術語的說明:我沒有像通常的用法那樣,用“獨立自主”(independent)這個詞去錶達自足或不受外界控製,我也沒有用“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這個詞來錶示相互聯係或相互依賴。相反,如同跨文化心理學傢所做的那樣,我一直以這些詞為一種方式,描述有關自我解釋的兩種非常不同的模型。第一種,“獨立自主”的、個人主義的自我,強調獨特性,通過諸如特點、能力、價值和偏好這些固有屬性來定義自身,往往孤立地看待事物。第二種,“相互依存”的、集體主義的自我,強調共性,通過地位、角色、忠誠和義務來定義自身,往往透過背景看待事物。當然,這兩種非常不同的自我解釋之間存在一個連續體,大多數人沿著它進行定位。在整個一生的過程乃至某一瞬間的過程中,他們也許會沿著它移動。文化不是一種宿命,它隻提供模闆,個體最終可以接受、拒絕或修改,並且執行它。例如,事實上,美國人的確喜歡汽車,但許多人選擇不開車、不經常開車,或者他們不喜歡開車對環境的破壞,以及他們會暈車。
毫無疑問,這彰顯齣的是一種汽車文化——事實上,汽車影響瞭從城市設計到外交政策的一切。因此,它處於相互依存/獨立自主的範圍之內。無論人們沿著其長度通常將自己定位於何處,也不管他們傾嚮於變動多麼寬的幅度,其端點仍然代錶著極具影響力的文化現實——這些現實,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帶來瞭感知、記憶以及敘述自我和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探索這一切時,我最終將關注點鎖定在這種差異對我寫作生涯的派生和支撐作用上。然而,正如我曾經說過的那樣,這種差異對於我們理解藝術與小說,對於我們理解我們自身,對於我們理解文化與文化變革遠遠超齣瞭其本身。這便是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至於我的計劃,我將以一個“根”的講座開始。這也是一個講述瞭相互依存的自我如何影響瞭一個人的一生的例子。也就是說,我們將細讀我父親在85歲時寫下的一本精彩的自傳的開頭部分。這一部分與他在中國的成長經曆有關——我希望這些文字能夠帶給大傢感動,並引起我們的興趣,同時也為我們打下一個基礎,為相互依存提供一種感覺,這是我們無法從單一的研究中所得到的。
我們並非不讓自己進行研究。在第二講的前半部分,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樣,事實上,我們將會把跨文化心理學的一些研究作為我們深入理解我父親故事的一種方式。這些研究也會使我們深入瞭解其對立麵——高度獨立自主的事業。在第二講的後半部分,我將聚焦西方敘事。在這裏,我將考察“小寫的”文化和“大寫的”文化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一切與我早期的作傢生涯有什麼關係。
隨後,在第三講中,我將會思考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會是什麼。當相互依存遇到獨立自主會發生什麼?我將把自己和我的工作置於變動不居的背景以及其他人的工作之中。此外,我們還會參觀一個非正式的工程講堂。
在這些講座結束之後,我將計劃在一個熱水浴池裏度過一天。但首先應該是: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
用戶評價
讀罷《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我腦海中迴蕩著的是一種既激昂又深沉的共鳴。它並非一本簡單的寫作指南,更像是一麵多棱鏡,摺射齣創作者內心世界的復雜光譜。作者對於“老虎”意象的運用,在我看來,恰如其分地捕捉到瞭寫作中最本真的力量——那種源自生命深處的原始衝動,那種不畏艱難、勇於探索的開拓精神,以及那種獨一無二、不容復製的個人風格。然而,寫作的道路並非總是一帆風順,它也充斥著對藝術的迷惘,對文化的睏惑,以及對自我的審視。《老虎寫作》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沒有迴避這些挑戰,反而將它們置於聚光燈下,尤其是“依賴型自我”這一概念的引入,無疑觸及瞭當代許多創作者的痛點。我們渴望被看見,渴望被肯定,卻又常常在這種渴望中迷失瞭自我,讓外部評價的聲音蓋過瞭內心最真實的聲音。這本書似乎在引導我們審視,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如何纔能不被“他人的眼睛”所綁架,如何纔能在汲取文化養分的同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創作的自覺。作者的論述,我感受到的,並非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對個體生命體驗與宏觀文化環境之間,以及個體創作衝動與社會評價機製之間微妙而深刻的互動關係的精妙解析。它讓我開始反思,我所理解的“老虎”式的寫作,是否隻是一個錶麵的標簽,而內在的自我,又在多大程度上被無形的力量所塑造和束縛。
評分初次翻開《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便被其直白而又引人深思的書名所吸引。我一直認為,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探索,它如同探險傢深入未知的叢林,試圖用文字勾勒齣隱藏在現實迷霧中的真相,亦或是將內心的幽暗角落照亮。而“老虎”這個意象,在我的腦海中總是與力量、野性、獨立以及一種難以馴服的生命力聯係在一起。當它與“寫作”這個需要耐心、技巧和深度思考的活動結閤時,不禁讓人好奇,作者究竟想描繪怎樣一種寫作姿態?它是在鼓勵一種原始的、不受束縛的創作衝動,還是在探討寫作過程中,我們如何與內心深處的“猛獸”共處,馴服它,又被它所滋養?而“藝術、文化”這兩個詞,則進一步拓展瞭這本書的維度,預示著它不僅僅是關於個人寫作技法的探討,更可能深入到寫作與更廣闊的社會、曆史、審美語境的互動之中。這讓我聯想到,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往往是藝術傢個體生命體驗與所屬時代文化精髓的交融,它既有“老虎”般的原創性和顛覆性,又承載著厚重的文化積澱。最後,“依賴型自我”這個概念,則像是為這一切濛上瞭一層復雜而微妙的麵紗。它指嚮的是我們在創作過程中,是否會過度依賴外部的認可,是否會在某種程度上將自我價值構建於他人的評價之上?這與“老虎”的獨立野性似乎形成瞭一種張力,讓人不禁想知道,作者將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或者說,如何揭示這種依賴性如何影響甚至扭麯瞭我們對藝術和自我的認知。我迫切地想知道,這本書將如何展開這三者之間的復雜關聯,是否會提供一種新的視角來理解我們作為創作者的存在狀態。
評分當我第一次看到《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這個書名時,內心深處湧起瞭一股莫名的好奇與一絲警惕。好奇的是“老虎”這個鮮活的意象如何與寫作這一相對內斂的活動相融閤,它是否預示著一種充滿力量、激情甚至野性的創作風格?而“藝術、文化”的加入,則讓我意識到這本書絕非止於個人技巧的傳授,而是將寫作置於更廣闊的社會和曆史語境中去審視。然而,“依賴型自我”的提法,卻讓我有些不安,它直指我們在創作過程中,是否會不自覺地尋求外部的肯定,是否會將自我價值的衡量標準,外化於他人的眼光和評價。這與我一直以來所推崇的“獨立思考”、“個性錶達”似乎存在著一種潛在的矛盾。讀這本書,我期待的是一種能夠幫助我理解並超越這種依賴性的指引。我希望能從中看到,如何在汲取藝術的養分、理解文化的內涵的同時,依然能夠保持創作的獨立性,不被外界的聲音所左右,不讓“自我”成為一個被他人塑造的影子。我希望這本書能為我揭示,真正的“老虎”式寫作,並非隻是外在的張揚,而是內在的強大與自洽,它來自於對自我最深刻的認知,以及對藝術最純粹的追求。
評分《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這本書,仿佛為我打開瞭一扇通往內心世界深處的窗戶。我一直認為,寫作不僅僅是文字的排列組閤,更是一種生命的吐息,一種靈魂的呐喊。作者用“老虎”來比喻寫作,在我看來,恰恰點齣瞭寫作中最寶貴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特質——那種原始的生命力,那種不受拘束的創造衝動,那種對世界充滿好奇和探索的野性。然而,我們身處的“文化”環境,以及社會對“藝術”的定義,往往會潛移默化地塑造我們的認知,甚至限製我們的錶達。更讓我警醒的是“依賴型自我”的論述。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似乎越來越習慣於從外部獲取認同,用點贊、評論來衡量自身的價值。這種依賴性,正如作者所揭示的,可能會扼殺我們內心的“老虎”,讓我們變成迎閤他人期待的“寵物”。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我理解,如何在與文化、藝術的互動中,保持自我的獨立性,如何纔能馴服內心的“老虎”,讓它成為我們創作的強大引擎,而不是失控的野獸。它讓我反思,所謂的“藝術”,究竟是服務於外部的評價體係,還是應該忠於內心的召喚?
評分《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這本書,仿佛是一場深入靈魂的對話,讓我不得不審視自己作為創作者的真實狀態。《老虎》這個意象,在我看來,是寫作中最具生命力、最不馴服的部分——那種源於生命本能的衝動,那種敢於冒險、勇於探索的姿態,以及那種不可復製的獨特氣質。然而,我們身處的“文化”環境,以及社會對“藝術”的普遍認知,往往會潛移默化地塑造我們的創作模式,甚至將我們納入既定的框架。而“依賴型自我”的提法,則直接觸及瞭當代許多創作者的核心睏境。我們渴望被看見,渴望被肯定,卻常常在不自覺中,將自己的價值寄托於他人的評價之上。這使得原本可能像“老虎”一樣自由奔放的創作,變得小心翼翼,甚至失去瞭原有的銳氣。我迫切地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揭示,如何在與藝術和文化的互動中,保持創作的獨立性,如何纔能馴服內心的“老虎”,讓它成為我們創作的強大驅動力,而不是一個被外部評價所左右的幻影。它讓我思考,真正的藝術價值,究竟在於贏得多少贊譽,還是在於忠於內心的真實錶達。
評分初次接觸《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的書名,我的腦海中立刻勾勒齣一種充滿力量和個性的創作圖景。作者以“老虎”為喻,我理解為是對寫作中最原始、最鮮活生命力的贊頌——那種不畏艱難、勇於開拓的進取精神,那種獨立思考、絕不隨波逐流的姿態。然而,寫作並非是孤立存在的行為,它必然會受到“藝術”和“文化”這兩個宏大概念的影響與塑造。“文化”既能給予我們豐富的養分,也可能成為一種無形的規訓,限製我們的視野。“藝術”的定義與流變,更會讓我們在追尋過程中産生迷茫。而“依賴型自我”的齣現,則為這一切濛上瞭一層更深的哲學色彩,它直指我們在創作中,是否會不自覺地將自我價值建立在他人的評價體係之上,是否會為瞭迎閤外部的期待而犧牲內心的聲音。我期望這本書能夠深入地剖析,這種依賴性如何悄悄地侵蝕我們創作的純粹性,如何讓我們在追求“藝術”的光環時,失去瞭“老虎”般的獨立與野性。它讓我思考,如何纔能在與藝術和文化的交融中,找迴並堅定那個不被外界定義,而是由內心力量所驅動的“自我”,讓每一次寫作,都如同“老虎”的奔跑,既充滿力量,又獨具風采。
評分在我翻閱《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的過程中,我反復思考著“老虎”這個詞所蘊含的多重意義。它既有力量,有野性,有獨立的氣質,又有潛藏的危險和不可預測性。當它與“寫作”結閤,我聯想到的是一種不羈的、充滿生命力的創作方式,一種敢於挑戰傳統,敢於探索未知邊界的藝術態度。而“藝術、文化”的加入,則將這種個體化的創作行為,置於瞭更宏大的背景之下,讓我開始思考,我們的寫作,如何與更廣闊的社會思潮、審美取嚮發生碰撞與融閤。然而,最讓我感到觸動和警醒的,是“依賴型自我”這一概念。在信息泛濫的時代,我們似乎越來越容易將自己的價值,建立在他人的評價之上,我們的創作,也可能因此而變得迎閤、妥協,失去瞭原有的鋒芒。“老虎”式的寫作,是否意味著一種徹底的獨立,一種不被外部所乾擾的創作?它又將如何麵對,當我們的“自我”,已經習慣於從他人的反饋中尋找定位時?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地解析,這種依賴性如何影響我們的創作決策,如何讓我們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不至於迷失瞭自我,成為他人期待的工具,而是能夠真正地釋放內心的“老虎”,展現齣最獨特、最真實的生命力。
評分《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這本書,如同一麵古老而又鋒利的鏡子,映照齣我作為一名創作者內心深處的隱憂與渴望。作者對“老虎”意象的運用,精準地捕捉到瞭寫作中最原始、最蓬勃的生命力。它代錶著不屈的意誌、獨立的思考,以及對世界永不枯竭的好奇心。然而,藝術的創作並非孤立存在,它始終與我們所處的“文化”環境息息相關。文化既是滋養我們靈感的土壤,也可能是一張無形的網,將我們的思想和錶達框定其中。“依賴型自我”的提法,則像一記重錘,敲擊在當代許多人心靈的軟肋上。我們似乎越來越渴望通過他人的認可來確認自己的價值,這種對外部評價的依賴,使得我們的“自我”,變得像一根風中的蘆葦,搖曳不定。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深刻地剖析,這種依賴性是如何悄悄地侵蝕我們的創作初衷,如何讓我們在追求“藝術”的錶象下,迷失瞭自我,甚至用他人的目光來定義自己的價值。它讓我思考,如何纔能在汲取藝術的精華、理解文化的脈絡時,依然能夠守護內心的“老虎”,保持創作的獨立與純粹,讓這份力量,源自內心深處,而非外在的喧囂。
評分當我翻開《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一種畫麵:一頭矯健的老虎,在廣袤的草原上奔跑,它的眼神中充滿瞭警覺與智慧,它的步伐中帶著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這種力量,我理解為寫作中最純粹的創造力,那種源自生命本能的衝動,那種對於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而“藝術、文化”這兩個詞,則像是為這頭“老虎”披上瞭精美的外衣,它既吸收著自然界的力量,也受到環境的影響,變得更加復雜而富有層次。然而,最讓我産生共鳴的,是“依賴型自我”這一概念。在當今社會,我們似乎越來越難以擺脫對他人的審視和評價,我們的價值感,常常建立在他人的反饋之上。這使得我們原本可能如“老虎”般獨立而強大的自我,變得脆弱而易碎。我期望這本書能夠深入探討,這種依賴性是如何影響我們的創作,如何讓我們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迷失瞭方嚮,甚至淪為他人的附庸。它讓我思考,如何纔能在汲取文化養分、融入藝術洪流的同時,不被這些外部因素所裹挾,從而保持創作的獨立與本真,讓內心的“老虎”能夠自由地奔騰,而不是蜷縮在他人期待的陰影之下。
評分《老虎寫作:藝術、文化與依賴型自我》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最深刻的感受,是一種剝離與重塑。作者在書中,仿佛一位經驗豐富的解剖師,細緻地剖析瞭寫作行為背後隱藏的種種動機與睏境。他用“老虎”來象徵那種純粹的、不受汙染的創作本能,那種對於未知世界的好奇與徵服的欲望,以及在藝術創作中必不可少的銳氣與野性。但與此同時,他也揭示瞭“文化”這層外衣,它既能滋養、豐富我們的創作,也可能成為一種無形的束縛,將我們納入既定的軌道。更值得深思的是“依賴型自我”的探討。在我看來,這正是當代社會文化語境下,個體身份構建和價值認同所麵臨的普遍睏境。我們習慣於通過他人的評價來錨定自己的存在感,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社交媒體無處不在的時代,這種依賴性似乎愈發根深蒂固。這本書並沒有給齣簡單的解決方案,而是通過深入的分析,引導讀者去認識到這種依賴性是如何悄無聲息地侵蝕我們創作的獨立性,如何讓我們在追求“藝術”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變成瞭“他人的代言人”。我感覺作者是在鼓勵一種“內在的獨立”,一種即使在外部缺乏支持,依然能夠堅持自己創作方嚮的力量,就像一隻真正的“老虎”,它不畏懼孤獨,也不隨波逐流。
評分不錯,值得一看
評分好
評分好
評分好
評分好
評分不錯,值得一看
評分不錯,值得一看
評分好
評分好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