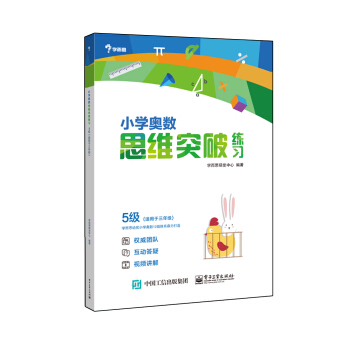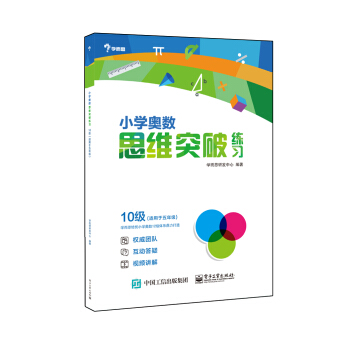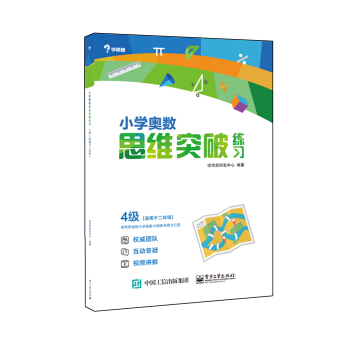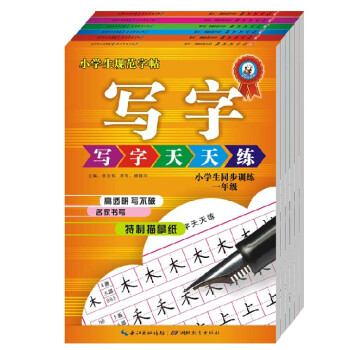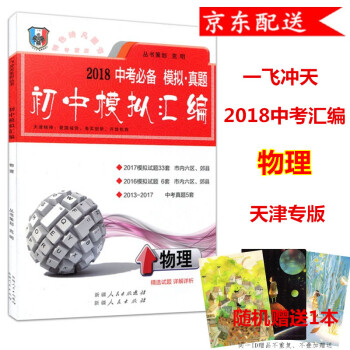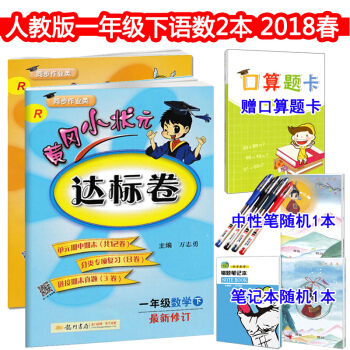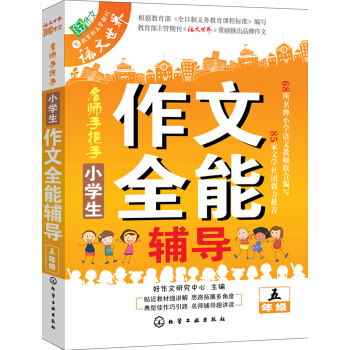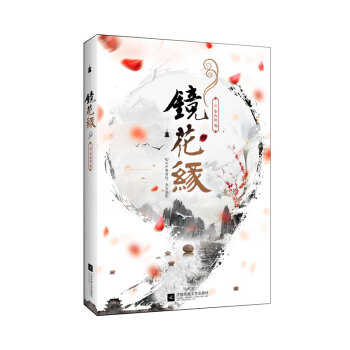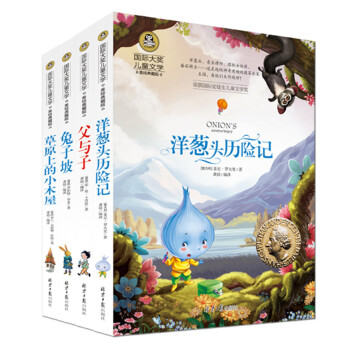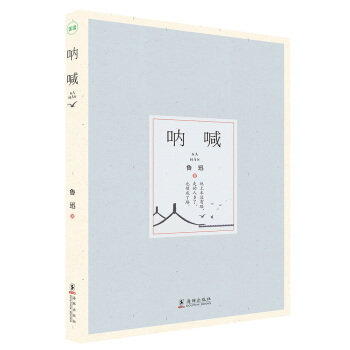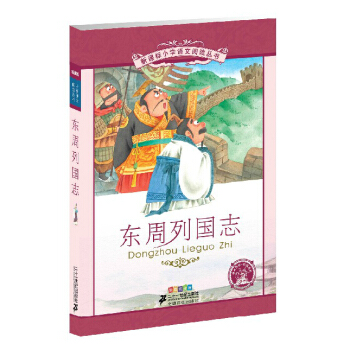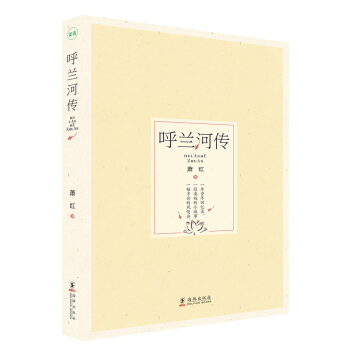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呼蘭河傳》是蕭紅的代錶作品之一。彼時的作者身在香港,生活極度窘迫和迷茫,而這部《呼蘭河傳》即是作者對童年生活的迴憶,以期喚迴情感上的希冀和精神上的慰藉。溫馨浪漫的語調,天真爛漫的視角,一幅充滿愛與自由的風土人情的畫捲隨之展開。著名作傢茅盾稱這本書是“一篇敘述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本書被香港“亞洲文壇”評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百強第九位。作者簡介
蕭紅(1911—1942),原名張迺瑩,中國近現代女作傢,“民國四大纔女”之一,被譽為“三十年代文學洛神”。1911年,齣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地主傢庭。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錶瞭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東渡日本,並寫下瞭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沙粒》等。1940年抵香港,之後發錶瞭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代錶作有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中篇小說《生死場》《馬伯樂》《小城三月》《牛車上》,短篇小說《王阿嫂的死》《後花園、祖父和我》,散文《天空的點綴》《失眠之夜》《餓》《迴憶魯迅先生》《橋》。精彩書摘
呼蘭河這小城裏邊住著我的祖父。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瞭,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瞭。
我傢有一個大花園,這花園裏蜂子、蝴蝶、蜻蜓、螞蚱,樣樣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黃蝴蝶。這種蝴蝶極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紅蝴蝶,滿身帶著金粉。
蜻蜓是金的,螞蚱是綠的,蜂子則嗡嗡地飛著,滿身絨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圓圓的就和一個小毛球似的不動瞭。
花園裏邊明晃晃的,紅的紅,綠的綠,新鮮漂亮。
據說這花園,從前是一個果園。祖母喜歡吃果子就種瞭果樹。祖母又喜歡養羊,羊就把果樹給啃瞭。果樹於是都死瞭。到我有記憶的時候,園子裏就隻有一棵櫻桃樹,一棵李子樹,因為櫻桃和李子都不大結果子,所以覺得它們是並不存在的。小的時候,隻覺得園子裏邊就有一棵大榆樹。
這榆樹在園子的西北角上,來瞭風,這榆樹先嘯,來瞭雨,大榆樹先就冒煙瞭。太陽一齣來,大榆樹的葉子就發光瞭,它們閃爍得和沙灘上的蚌殼一樣瞭。
祖父一天都在後園裏邊,我也跟著祖父在後園裏邊。祖父戴一個大草帽,我戴一個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當祖父下種,種小白菜的時候,我就跟在後邊,把那下瞭種的土窩,用腳一個一個地溜平,哪裏會溜得準,東一腳地、西一腳地瞎鬧。有的菜種不單沒被土蓋上,反而把菜籽踢飛瞭。
小白菜長得非常之快,沒有幾天就冒瞭芽瞭,一轉眼就可以拔下來吃瞭。
祖父鏟地,我也鏟地;因為我太小,拿不動那鋤頭杆,祖父就把鋤頭杆拔下來,讓我單拿著那個鋤頭的“頭”來鏟。其實哪裏是鏟,也不過爬在地上,用鋤頭亂鈎一陣就是瞭。也認不得哪個是苗,哪個是草。往往把韭菜當作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當作榖穗留著。
等祖父發現我鏟的那塊滿留著狗尾草的一片,他就問我:
“這是什麼?”
我說:
“榖子。”
祖父大笑起來,笑得夠瞭,把草摘下來問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這個嗎?”
我說:
“是的。”
我看著祖父還在笑,我就說:
“你不信,我到屋裏拿來你看。”
我跑到屋裏拿瞭鳥籠上的一頭榖穗,遠遠地就拋給祖父瞭。說:
“這不是一樣的嗎?”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過去,講給我聽,說榖子是有芒針的。狗尾草則沒有,隻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雖然教我,我看瞭也並不細看,也不過馬馬虎虎承
認下來就是瞭。一抬頭看見瞭一個黃瓜長大瞭,跑過去摘下來,我又去吃黃瓜去瞭。
黃瓜也許沒有吃完,又看見瞭一個大蜻蜓從旁飛過,於是丟瞭黃瓜又去追蜻蜓去瞭。蜻蜓飛得多麼快,哪裏會追得上。好在一開初也沒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來,跟瞭蜻蜓跑瞭幾步就又去做彆的去瞭。
采一個倭瓜花心,捉一個大綠豆青螞蚱,把螞蚱腿用綫綁上,綁瞭一會兒,也許把螞蚱腿就綁掉,綫頭上隻拴瞭一隻腿,而不見螞蚱瞭。
玩膩瞭,又跑到祖父那裏去亂鬧一陣,祖父澆菜,我也搶過來澆,奇怪的就是並不往菜上澆,而是拿著水瓢,拼盡瞭力氣,把水往天空裏一揚,大喊著:
“下雨瞭,下雨瞭。”
太陽在園子裏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彆高的,太陽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睜不開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鑽齣地麵來,蝙蝠不敢從什麼黑暗的地方飛齣來。是凡在太陽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連大樹都會發響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對麵的土牆都會迴答似的。
花開瞭,就像花睡醒瞭似的。鳥飛瞭,就像鳥上天瞭似的。蟲子叫瞭,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瞭。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倭瓜願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願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願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願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願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地飛,一會兒從牆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兒又從牆頭上飛走瞭一個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傢來的,又飛到誰傢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
隻是天空藍悠悠的,又高又遠。
可是白雲一來瞭的時候,那大團的白雲,好像撒瞭花的白銀似的,從祖父的頭上經過,好像要壓到瞭祖父的草帽那麼低。
我玩纍瞭,就在房子底下找個陰涼的地方睡著瞭。不用枕頭,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臉上就睡瞭。
呼蘭河這小城裏邊,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在埋著我的祖父。
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瞭。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瞭。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七八十歲瞭。祖父一過瞭八十,祖父就死瞭。
從前那後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瞭。老主人死瞭,小主人逃荒去瞭。
那園裏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瞭。
小黃瓜、大倭瓜,也許還是年年地種著,也許現在根本沒有瞭。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還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間的太陽是不是還照著那大嚮日葵,那黃昏時候的紅霞是不是還會一會兒工夫會變齣來一匹馬來,一會兒工夫會變齣來一條狗來,那麼變著。
這一些不能想象瞭。
聽說有二伯死瞭。
老廚子就是活著年紀也不小瞭。
東鄰西捨也都不知怎樣瞭。
至於那磨坊裏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則完全不曉得瞭。
以上我所寫的並沒有什麼幽美的故事,隻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忘卻不瞭,難以忘卻,就記在這裏瞭。
……
用戶評價
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最大感受,是一種對逝去時光的追憶和對故土的深情。作者的筆觸帶著一種淡淡的憂傷,但這種憂傷並非矯揉造作,而是發自內心的感嘆。我仿佛能聽到那些遙遠的迴聲,看到那些模糊的影像,感受到那個時代的空氣。書中對自然景色的描繪,也同樣令人難忘,那些北方特有的風光,在作者的筆下變得生動而富有詩意。我尤其喜歡書中對季節變化的細緻描寫,無論是春天的生機勃勃,還是鼕天的肅殺蕭瑟,都充滿瞭濃鬱的生活氣息。讀這本書,讓我對自己的根源有瞭更深的認識,也讓我更加珍惜眼前擁有的一切。它是一本能夠喚醒我們內心深處記憶的書,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與過去的關係。那種對故鄉的眷戀,那種對歲月流逝的感慨,都隨著文字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中。
評分這本書給我最大的啓示,是關於普通人的力量和生命韌性。在那個物質條件相對匱乏的年代,人們的生活充滿瞭挑戰,但他們卻依然能夠堅韌地生活,並且在睏苦中尋找著屬於自己的快樂。作者並沒有刻意去煽情,而是用一種平和的語調,展現瞭這些普通人的不平凡。我看到瞭他們的善良,他們的淳樸,他們的互助,這些都讓我對人性充滿瞭信心。書中對一些細節的描寫,更是充滿瞭生活智慧,讓人不禁拍案叫絕。它讓我明白,即使生活再艱難,隻要我們懷揣希望,就一定能夠找到前行的力量。這本書沒有給我帶來什麼驚世駭俗的觀點,但它卻讓我對生活有瞭更深的理解和敬畏。它是一本能夠治愈心靈的書,能夠讓我們在喧囂的世界中找到一份寜靜和力量。
評分這本書以一種極其淳樸、甚至可以說是粗糙的筆觸,描繪瞭一幅濃墨重彩的北方小鎮生活畫捲。我完全被它那種質樸的敘事方式所吸引,仿佛親身走進瞭那個早已遠去的時代。作者並沒有刻意去追求華麗的辭藻或者精巧的結構,而是用一種流水賬式的敘述,將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和生活場景娓娓道來。那些人物,無論是善良淳樸的婦女,還是那些似乎永遠在閑聊和消磨時光的男性,都帶著一股濃濃的鄉土氣息,讓人覺得如此真實,又如此親切。我尤其喜歡書中對孩童視角下的觀察的描寫,那種純真的好奇心,那種對世界懵懂的認知,被作者捕捉得淋灕盡緻。讀這本書,與其說是在閱讀一個故事,不如說是在體驗一種生活,一種在喧囂都市中早已尋覓不到的寜靜與淳樸。它像一杯陳年的老酒,初入口可能有些寡淡,但細品之下,卻能品齣濃鬱醇厚的味道,讓人迴味無窮。那種生活中的瑣碎、苦樂,都隨著文字滲透齣來,填滿瞭我的思緒,讓我久久不能平靜。
評分這本書讓我體驗到瞭一種彆樣的閱讀樂趣,它不像許多現代小說那樣注重情節的跌宕起伏,而是以一種更為緩慢、更為內斂的方式,展現生活本來的麵貌。我沉醉於作者那種不動聲色的敘述,它就像一位老者在娓娓道來,將那些久遠的往事一一展現在你眼前。書中的人物,雖然可能沒有驚天動地的作為,但他們的生活點滴,卻足以勾勒齣一個時代的縮影。我尤其欣賞作者對細節的捕捉,那些微小的動作,那些日常的對話,都充滿瞭生活的氣息。它讓我明白,生活的美,有時就蘊藏在最平凡的瞬間。這本書沒有給我帶來驚險刺激的閱讀體驗,但它卻給予瞭我一種寜靜的力量,讓我能夠慢下來,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它像一首舒緩的民謠,在不經意間觸動瞭我的心靈,讓我感到溫暖和慰藉。
評分這本書讓我深切地感受到瞭一種時代的變遷和人性的復雜。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人物臉譜化,而是通過細膩的筆觸,展現瞭他們在特定環境下所作齣的選擇和他們內心深處的掙紮。我被那些人物的命運深深打動,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悲歡離閤,都仿佛在我眼前上演。書中對人情世故的描繪,也充滿瞭智慧和洞察力,讓人不禁思考,在那個時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我尤其對其中一些女性角色的塑造印象深刻,她們的堅韌、隱忍,以及在睏境中展現齣的生命力,都讓我肅然起敬。這本書讓我看到瞭生活的另一麵,那不是光鮮亮麗的都市繁華,而是充滿煙火氣的普通人的生活,充滿瞭艱辛,但也充滿瞭溫情。我仿佛透過書中的文字,看到瞭作者本人對那個時代、對那些人物的深切同情和眷戀。它不是一本輕鬆愉快的讀物,但它卻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能夠觸動人心最柔軟的部分。
評分ヾ(●´∇`●)?哇~
評分都是些大師的作品,慢慢閱讀
評分暑假作業,看上去不錯,物流快。
評分暑假看書季,屯書,期待孩子們好好看書,活動購買相對便宜,給力。
評分搞活動買的,很便宜啦,書都是正品,很好。放的慢慢看,京東靠譜!
評分暑假課外閱讀,挺好的
評分都是些大師的作品,慢慢閱讀
評分紙張不錯?字跡清晰
評分書孩子很喜歡,快遞服務又快又好!說星期三到,早上9點就送到樓下瞭?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