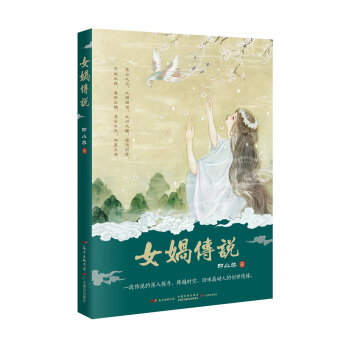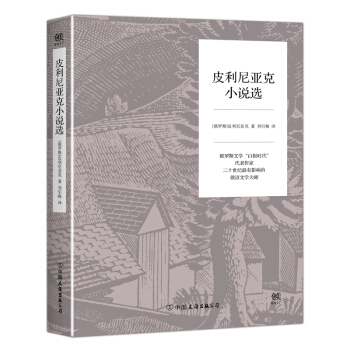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皮利尼亚克是文学技巧的实验者和大师,其作品有着魔术般的叙述手法。有时会突然找不到中心或主题,跟不上作者的跳跃式思维;有时会觉得故事荒诞不经,又逼真得如在眼前。皮利尼亚克通过一系列看似荒诞不经、古怪离奇的故事情节,以不拘一格的艺术技巧生动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对细节的描写生动逼真!
内容简介
《皮利尼亚克小说选》收录了皮利尼亚克的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中篇小说《红木》《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以及短篇小说《人的风》和《骗子手们》。皮利尼亚克的作品有着魔术般的叙述手法,有时会突然找不到中心或主题,跟不上作者的跳跃式思维;有时会觉得故事荒诞不经,又逼真得如在眼前。皮利尼亚克通过一系列看似荒诞不经、古怪离奇的故事情节,以不拘一格的艺术技巧生动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对细节的描写生动逼真。
作者简介
皮利尼亚克(1894—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作家,十月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1920年,皮利尼亚克出版了长篇小说《裸年》,这部作品使他一举成名,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国文字,同时也招致了严厉的批评。1929年,在柏林出版的中篇小说《红木》因“歪曲苏维埃现实”而遭批判。
目录
译者前言 /01红 木 /001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051
人 的 风 /095
骗子手们 /105
果实的成熟 /113
译后记 /343
精彩书摘
第一章乞讨者、有预见者、叫花子、要饭的、拉撒路、男男女女的朝圣者、赤贫者、伪善者、香客、先知、男男女女的愚人、疯修士——神圣罗斯生活习惯中这些意思相同的五花八门的称谓,正是神圣罗斯的这些乞讨者、朝圣者、赤贫者、疯修士——使自有罗斯以来,自伊万王朝以来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俄国数千年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所有俄国史学家、民族学家和作家都在记述这些曾经大行其道的故人。这些疯子或者骗子——叫花子、伪善者、先知——被认为是教会的精英、基督的同修、来世的祈福者,俄国正统的历史和古典文学中也正是这样称呼他们的。
十九世纪中叶,有一个住在莫斯科的疯修士伊万·雅科夫列维奇,一个未受完教育的神学院学生,死在了基督登山变容节医院。于是采访记者、诗人、史学家纷纷撰文记述他的葬礼。有位诗人作诗一首,登在《消息报》上:
疯人院里在举行什么庆典?
为什么车水马龙,人潮如涌,
满心忧惧,步履匆匆?
人群中不时响起
惶惶不安的哀叹,
充满诚挚而深切的悲痛:
伊万·雅科夫列维奇英年早逝了!
当之无愧的卓越先知归天了!
史学家斯卡夫隆斯基在《莫斯科特写》中说,在尸体安葬之前,连续为死者做了五天二百多场安灵弥撒,许多人就在教堂附近过夜。学术著作《二十六个莫斯科的伪先知、伪疯修士和愚人》的作者是巴尔科夫,他是葬礼的目击者,他说,伊万·雅科夫列维奇的葬礼原定礼拜天举行,消息就“公布在《警方公报》上。可是当天一大早,好多崇拜者纷至沓来,由于在究竟在何处安葬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出殡未能如期举行。他们差点儿动起手来,有恶言相向的,也有品行端正的。一些人要把他运往斯摩棱斯克,逝者的故乡;另一些人张罗着要把他葬在波克罗夫男修道院,墓穴都挖好了,就在教堂附近。还有一些人大为动情地恳求把他的遗骸交给阿列克谢耶夫女修道院;更有一些人紧紧拽住灵柩不撒手,硬要把它拖到切尔基佐沃村。”因为“他们担心伊万·雅科夫列维奇的遗体会被偷走。”史学家写道:“当时一直在下雨,地上泥泞不堪,灵柩从停尸间运往小礼拜堂,又从小礼拜堂运往教堂,然后再从教堂运往墓地,好一通折腾。但尽管如此,那些妇女、姑娘、穿着钟式裙子的千金小姐都俯首在地,在灵柩下边爬行。”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在弥留之际大便失禁,“污物从他身子底下流了一地”。
史学家这样写道,“吩咐守护人用沙子把污物掩埋起来。就是这种被伊万·雅科夫列维奇的粪便浸湿了的沙子,他的崇拜者们都收集起来,带回家去了。于是这小小的沙子便显示出灵丹妙药的神力。小孩儿闹肚子疼,妈妈便在他的稀粥里掺半小勺沙子,小孩儿喝下去肚子就不疼了。安魂弥撒之后,用来堵死者鼻孔和耳孔的棉球分成了许多小块,发给教徒。许多人来到灵柩跟前,收集从灵柩里流出来的尸水,因为死者是死于水肿的。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死的时候穿的衬衫也被撕成了碎片。出殡之前,那些赤贫者、疯修士、伪善者、男男女女的朝圣者纷纷聚集在教堂周围。由于拥挤,他们没有进到教堂里来,就在外面站着。这时他们或讲经布道,或装神弄鬼,或宣布神启,或破口大骂,或收罗钱财,或发出不祥的凶猛吼叫。”伊万·雅科夫列维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总是让他的崇拜者们喝他的洗脸水,他们就真的喝了。伊万·雅科夫列维奇不仅有口头预言,而且也留下了书面预言,它们都被保存了下来,以供历史研究之用。有人写信问他:“某某人可否婚配?”他叽里咕噜说了一句谁都听不懂的话,神乎其神的,像是天书。
莫斯科有个中国城,是一群装疯卖傻的乌合之众的麇集之地。这里有的人写诗;有的人学公鸡打鸣、学孔雀和红腹灰雀喳喳叫唤;有的人为了上帝而破口大骂;有的人只知道一句漂亮的空话,这句漂亮的空话被认为是先知的话,并赋予了先知以名望,譬如:“人生好比童话,棺材好比四轮马车,跑起来平平稳稳!”有的人癖好狗叫,因为上帝的吩咐是通过狗叫预言的。在乞讨者、有预见者、叫花子、拉撒路、伪善者——整个神圣罗斯的这一类赤贫者中,还有农民、小市民、贵族、商人;有儿童、老人;有膀大腰圆的庄稼汉、生育力旺盛的高大粗胖的蛮婆娘。他们统统都是酒鬼。所有他们,这些不幸的苦命人,都像干酪和葱头一样,被覆盖在野蛮落后的俄罗斯帝国葱头形的蔚蓝色的宁谧之下,因为教堂的葱头形尖顶当然就是葱头俄罗斯生活的象征。
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另一些俄罗斯的大城市,有另一些怪人。他们的家谱可追溯到帝国时期,而不是沙俄时期。俄罗斯的家具手艺始于彼得大帝时期,兴盛于伊丽莎白时期。这一农奴制时代的手艺历史上没有文字记载,而工匠们的名字也被时间的长河湮灭。这种手艺是一个人单干的活儿,是在城市的地下室里,在地主庄园下房的小屋里干的活儿。这种手艺是在伏特加酒和残酷环境中留存下来的。扎克布和布尔是师傅。奴隶制时代,那些半大男孩儿被送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被送到巴黎和维也纳,他们在那里学艺。学成后,他们便从巴黎回到圣彼得堡的地下室,回到下房的小屋里,进行制作。有的工匠制作一件催眠沙发,或梳妆台,或书柜,要花费数十年时间——他的一辈子就是干活、喝酒、死去,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侄甥,因为不允许他有自己的孩子。侄甥要么模仿叔辈的手艺,要么把这手艺继承下来。工匠死了,而东西却长久地摆放在地主庄园里和独家豪宅里,主人或在近旁欣赏,或在催眠沙发上死去,把那些秘密通信藏在活面写字台的暗匣里,待字闺中的姑娘们在盥洗间对镜端详自己的青春容颜,老太婆们对镜细看的则是年老色衰。从伊丽莎白时代到叶卡捷琳娜时代,盛行的是可可式、巴洛克式、青铜器、精巧的涡纹装饰、红木、紫檀、乌木、卡累利阿木、波斯胡桃木。保罗一世要求的风格非常苛刻,红木家具是抛光的,包面是绿色皮革,雕饰是黑色的狮子和狮身鹰翅鹰首怪兽。亚历山大一世要求的是后古典主义风格,古典主义,埃拉多斯。尼古拉一世又恢复了保罗一世的风格,不及他兄长亚历山大一世那样的豪华。那么,这三个时期红木家具都十分盛行。1861年,农奴制垮台了。农奴工匠被家具厂取代——列温松家具厂,托奈特家具厂,维也纳家具厂。但是那些工匠的侄辈们靠着喝酒活了下来。这些工匠现在什么都不制作,他们只修复古物,但他们把叔辈们的技艺与传统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他们都是单身汉,他们也都是沉默寡言的人。他们像哲学家一样,都为自己的行当而感到自豪,而且他们也热爱自己的行当,像诗人一样。他们依旧住在地下室。假如不把这样的工匠打发到家具厂,那么要想修好尼古拉一世以后的器物,就使唤不动他。他是古董鉴赏家,他是古董修复家。无论在莫斯科人家的阁楼上,还是在失过火的地主庄园的杂物棚里,他都能够找到桌子、三扇镜、长沙发——这些叶卡捷琳娜时代、保罗一世时代、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器物。于是他会一头扎进去,在自己的地下室里一连数月仔细琢磨,不停地抽烟,认真思考,用一只眼睛反复打量,他将会喜欢上这件器物,目的就是要还原这些死物件的鲜活生命。恐怕他还会在写字台的暗匣里找到一沓泛黄的书信。他是修复家,他的眼睛是向后看的,盯的是古物的年代。他一定是个古怪的人,他必将要按古怪的方式把修复好的器物卖给一个也是这样古怪的收藏家,交易时,他会跟这个收藏家一起喝白兰地,这瓶白兰地是当年摆放在叶卡捷琳娜橱柜里的,用的高脚玻璃杯是过去皇家的御用品,一套极其珍贵的酒具。
第二章
1928年。
这个小城就是俄国的布吕赫和俄国的镰仓。三百年前,留里克王朝的最后一位王子就是在这个小城镇里被杀害的。王子被害那天,贵族图奇科夫的孩子们还在跟王子一起戏耍游玩。图奇科夫家族在本城一直绵延至今,像修道院和许多其他名气较小的家族一
样……俄国古迹、俄国行政区、伏尔加河上游、森林、沼泽、村庄、修道院、地主庄园,——还有一连串城市——特维尔、乌格利奇、雅罗斯拉夫尔、大罗斯托夫。这座小城——犹如修道院一般寂静的布吕赫。这里有俄国皇室领地,交错的街巷里处处种着有益健康的洋甘菊,有记述历次谋杀的石碑。小城距离莫斯科两百俄里,而距离铁路线五十俄里。
这里留下了地主庄园的废墟和古旧的红木家具。这里的古物博物馆馆长戴着高筒礼帽,穿着披风式大衣和方格裤子,而且蓄起了络腮胡子,像普希金那样。他的披风式大衣口袋里装着博物馆和各修道院的钥匙。他在小饭馆里喝茶,孤独的时候在自家的贮藏室里拿酒自斟自饮。他家里胡乱堆放着《圣经》、圣像、修士大司祭的高筒帽和金冠、辅祭的法衣、圣带、锦缎套袖、教袍、神父的外衣、盖圣餐布、盖棺布、桌裙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十三世纪、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他的书房里摆着卡拉津的红木制品,写字台上放着一个烟灰缸,酷肖带有红帽箍和白帽身的贵族制帽。
维亚切斯拉夫·帕夫罗维奇·卡拉津老爷曾在近卫重骑兵团服役,由于生性耿介,大约在革命前二十五年,他退役了,原因是他的同僚长期盗窃的行为败露了,指派他去做侦查,结果他如实报告了长官,长官却包庇了窃贼。这让卡拉津老爷咽不下这口气。他打了第二份报告:请求退役。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庄园,定居下来。他每礼拜进一次城,采买日用品。他从庄园到城里来,总是乘坐一辆笨重的四轮轿式马车,带两名仆役,他用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指着店铺的伙计,让他给称半普特上等的黑鱼子酱,大半普特干咸鱼脊肉,一尾闪光鲟,一个仆役付钱,另一个仆役收货。一次,一个商人伸出手来想跟老爷握手,老爷没有伸手,只简短地说了一句:“不必啦!”
卡拉津老爷总是戴着贵族制帽,穿着尼古拉式大衣。革命迫使他搬出庄园,迁到了城里,但是大衣和制帽留给了他。现在卡拉津老爷排队购物时仍然戴着那顶贵族制帽,只是跟差的仆役换成了他的妻子。卡拉津老爷靠变卖古董维持生计。为此他常常去找博物馆馆长。他在博物馆馆长那里看见了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以革命的权力从他的庄园里没收来的。他并不看重这些东西。但是,有一次他在博物馆馆长的桌子上看见了那只贵族制帽式样的烟灰缸。“收起来吧。”他简短地说。“为什么?”博物馆馆长问。“俄国贵族的制帽不能当成痰盂。”卡拉津老爷回答说。两位古董行家争执起来。卡拉津老爷愤然离去。从此他再没有迈进过博物馆馆长的门槛。
城里住着一个皮匠,他感恩地回忆说,他小时候在卡拉津老爷的府上当侍童,由于干活慢慢腾腾,老爷用左手扇了他一记耳光,打掉了他七颗牙齿。
城里一片死寂,只有一昼夜两次响起的轮船汽笛声和教堂钟楼上陆续响起的古老钟声,才把这沉闷打破。钟声响到1928年之前。因为1928年许多教堂的钟都被摘下来送到冶金公司了。钟是用滑轮、原木和绳索从高高的钟楼上拉出来,悬在半空,然后缓缓地放下来。钟在绳索上慢慢往下滑动,发出忽高忽低的哭泣声。这哭泣声回荡在城里死寂的上空。钟发着嗡嗡的轰鸣声重重地坠落下来,把地砸出大约两俄尺的深坑。
摘钟还在继续。这些日子里,小城正像古钟那样发出呜咽。
城里最有用的是工会会员证。店铺里排着两队——一队是有工会会员证的,一队是没有工会会员证的。有工会会员证的租用伏尔加河上的游艇是一小时十戈比,其余的人是一小时四十戈比,电影票价是二十五、四十和六十戈比不等,有工会会员证的电影票价是五、十和十五戈比不等。在实行工会会员证的地方,其重要性是占首位的,同等重要的还有粮食供应卡,并且粮食供应卡,这么说,还有面包卡,只发给有选举权的人,定量为一天四百克。没有选举权的人及其子女,连面包也得不到。影院设在工会园地一间有防寒设备的板棚里,入场时不打铃。整个城镇的作息安排是根据发电厂发出的信号进行的:第一个信号——结束早茶;第二个信号——着装出门。发电厂通常工作到午夜,但是在命名日、十月嘉名会和其他一些突然的隆重庆典活动,如执委会主席、工业联合企业主席及其他领导人的喜庆日,发电厂才会通宵供电,这时居民们正好借光适时安排自己的庆祝会。有一次在电影院里,内贸贸易公司全权代表,不知是姓萨茨,还是姓卡茨,在完全没有醉酒的情况下,由于动作笨拙,偶然碰了一下执委会主席的夫人,后者则满怀蔑视地甩给他一句:“我是库瓦尔津娜。”全权代表以前不知道这个姓氏的权势,他惊诧莫名地道了歉,但最后他还是被打叉勾掉,走人了事。领导们在城里住得很集中,出于与生俱来的多疑,总是防范着其他居民,整天忙于勾心斗角,而放弃社会活动。根据割肉补疮的原则,受那些勾心斗角的人的派别所支配,自然每年都有领导人从这个县的领导岗位上落选,然后到另一个县的领导岗位上就任。经济也是根据割肉补疮的原则在运行。联合企业在管理经营(联合企业是在本篇主人公伊万·奥若戈夫变成呆傻人那一年出现的)。管委会成员有执委会主席库瓦尔津(库瓦尔津娜的丈夫)和工农监察机构全权代表普列斯努欣,涅多苏戈夫任会议主席。他们的经营管理就是慢慢地把革命前的资源严重浪费掉,就是敷衍塞责和营私舞弊。榨油厂亏损,锯木厂亏损,制革厂不亏损,但也没有利润。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动用了四十五匹马和全城半数居民,硬是把好大一口锅炉在雪地上拖了五十俄里,才拖到这个制革厂。锅炉拖回来了,也废弃了,因为不适用,其费用在盈亏的账上冲销了。当时为了粉碎树皮而购置了一台铡草机,结果也废弃了,因为树皮不是干草,其费用又是冲销了事。为了改善工人的生活,决定修建住房:购买了一座整体木房,几经周折运回了工厂,然后将其锯成一段一段的木柴,一共锯出五立方,因为木房已经腐烂了,能用的木料只有十三根。用这十三根木料,又加上九千卢布,房子总算盖起来了:恰好,这时工厂因建房而倒闭了,尽管这时候工厂不亏损,像其他企业那样,但也不赚钱。于是新房便闲置着。联合企业靠抛售革命以来停产企业的设备来掩盖亏损,甚至不惜采用这样的招数:执委会主席库瓦尔津把一批木材按固定价格的百分之五十卖给管委会成员库瓦尔津,即打一个对折,也就是说,库瓦尔津把定价为五万卢布的木材,以两万五千卢布买下来,然后管委会成员库瓦尔津再转手卖给居民,特别是,按原价卖出,不打折扣。这样一倒手,库瓦尔津主席所得到的就是五万多卢布。1927年来临之际,鉴于库瓦尔津取得的成就,提出要对库瓦尔津给予嘉奖:管委会赠给库瓦尔津一个皮包。购买皮包的钱是从备用金里支付的。为了把这笔钱归还给出纳,他们便四处奔走,让当地人签名认捐。由于受其他居民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兴趣和生活是闭塞的,他们不会对小说产生任何兴趣。城里出售的烧酒只有两种:伏特加酒和教堂用的红酒。其他酒一概没有。伏特加酒的需求量很大,教堂用的红酒需求量虽说少一些,但也很大——用于祝圣用的圣水和圣餐酒。城里也有香烟出售——“大炮牌”的,十一戈比一盒,“拳击牌”的,十四戈比一盒,其他牌子的一概没有。像买伏特加酒一样,买香烟也排两队:工会会员排一队,非工会会员排一队。一昼夜有两班轮船经过,在那里的小卖部可以买到“萨福牌”香烟、波尔图葡萄酒和花楸露酒,而且吸“萨福牌”香烟的人显然都是盗用公款者,因为城里没有私营商店,而买“萨福牌”香烟的人从来就没有结过账。就是为了让这座小城成为非行政中心的县辖城镇,靠菜园子和互助服务去生存。
斯库德林桥畔矗立着斯库德林家的房子,雅科夫·卡尔波维奇·斯库德林就居住在这栋房子里,他是农民事务的代理人,年龄大约八十五岁。除了雅科夫·卡尔波维奇·斯库德林,城里还单独居住着小他许多岁的两个妹妹卡皮托利娜和里玛,还有一个呆傻的弟弟伊万,后改名为奥若戈夫。下面将会谈到他们。
最近四十年来,雅科夫·卡尔波维奇患有疝气,走路时用右手从裤子的前开口处托住自己的疝突出,他的双手肿胀而发青。他从盐瓶里把盐撒在面包上,总是撒厚厚一层,吃的时候盐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然后把散落的盐粒十分节俭地收起来,重新放回盐瓶。最近三十年来,雅科夫·卡尔波维奇不再会正常睡觉了,常常是夜半醒来,精神勃勃地读《圣经》,直到天亮,然后睡到中午。但中午时,他一向都去阅览室看报:城里没有卖报的,订报又没有钱,所以只能在阅览室里看报。雅科夫·卡尔波维奇身体肥胖,头发全白了,谢顶了。他的眼睛总是流泪,当他准备开口说话时,也要喘好大一阵子,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斯库德林家的房子从前属于地主韦列伊斯基,后者随着农奴制的废除在选举调解法官的职位时破产了。雅科夫·卡尔波维奇在废除农奴制之前刚好服完兵役,于是在韦列伊斯基手下当了一名文书,学会了司法方面的一套东西。这时韦列伊斯基破产了,他就捷足先登把他的房子连同职位一起买下来了。自叶卡捷琳娜时代以来,这栋房子依然完好无损,在这一个半世纪当中,房子已经变得黯然失色,犹如房子里的红木家具一样,玻璃器皿上长出一层绿锈。雅科夫·卡尔波维奇记得农奴制。老头儿什么都记得:农奴制乡村的农奴主老爷,塞瓦斯托波尔的士兵招募;他记得最近五十年当中所有俄国大臣和苏联人民委员的名字和父名,所有帝俄宫廷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使、所有大国的外交部长、所有总理、国王、皇帝和教皇的名字。老头儿对久远的岁月已经记不清了,他说:
“我活得比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比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比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比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长久,我还要活过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呢!”
老头儿脸上总挂着那种非常讨厌的,同时又卑躬谄媚和阴险恶毒的笑容,他微笑时,他那双灰白的眼睛总是流泪。老头儿的脾气很倔,他的几个儿子也都随他。远在1905年之前,长子亚历山大被打发送一封急信到码头,结果迟到了,没赶上轮船,领受了父亲一记耳光和辱骂:“滚,你这坏蛋!”这一记耳光是父亲赏赐给儿子的最后一滴蜜酒,——小男孩当时只有十四岁,——小男孩扭身离家出走了。六年以后他回来了,已然是艺术学院一名大学生了。在这几年当中,父亲不断给儿子写信,信中命儿子回家,并永远诅咒他,使其失去父母的祝福。就在这封信中,在父亲落款的稍下方位置,儿子补写了一句:“见鬼去吧,去您的祝福。”于是把父亲的信退了回去。离家六年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亚历山大踏进了客厅,这时父亲迎上前去,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举起一只手,要打儿子;儿子带着快活的讥笑,一把抓住父亲的手腕,又微微一笑,在这微笑当中愉快地显示出儿子的强劲有力,父亲的两只手被牢牢地钳制住了。儿子稍稍一使腕力,让父亲坐到桌旁圈椅上,说道:“您好,老爸,何必费心呢,老爸?坐下吧,老爸!”
父亲开始发出嘶哑的声音,哧哧地笑起来,从鼻子里发出喘息声,脸上掠过一抹凶狠的善意。老头儿冲妻子喊道:“玛丽尤什卡,对啦,嘿嘿,伏特加,快给我们拿伏特加来,亲爱的,来一瓶酒窖里冰镇的,再来一个冷盘。长大了,儿子长大了——儿子给我们添痛苦来啦,狗崽子!”
他的几个儿子都发展起来了: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神父,一个是芭蕾舞演员,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工程师。两个最小的弟弟像大哥——艺术家,也像父亲,他们俩也像大哥一样是离家出走的,最小的一个成了共产党员,他就是工程师阿基姆·雅科夫列维奇,他再没有回过父亲的家,即使回到他的出生地,他也是短暂住在她的姑妈卡皮托利娜和里玛家里。1928年之前,雅科夫·卡尔波维奇的几个大孙子都要娶妻成家了,但他的小女儿才二十岁。这是他唯一的女儿,在革命的轰鸣中,她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有老头儿及其妻子玛丽亚·克利莫夫娜和女儿卡捷琳娜。有一半的房子和阁楼冬天都不生火。这房子像人们的生活一样——在叶卡捷琳娜时代之前很久,甚至在彼得大帝时代之前很久,这栋房子就像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红木家具那样沉默无语。老两口靠种菜园子维持生计。家里用的工业品只有火柴、煤油和盐,如何使用火柴、煤油和盐,都由父亲说了算。从春到秋,玛丽亚·克利莫夫娜、卡捷琳娜和老头儿都在忙活园子里种的白菜、甜菜、芜菁、黄瓜、胡萝卜和替代糖的甘草。夏天黎明时分总能遇见老头儿穿着睡衣,打着赤脚,右手插在裤子前开口处,左手拿一根细树条,踏露披雾地在户外放牛。冬天,只在老头儿不睡觉的时候点灯,而其他时候,母女俩只能黑灯瞎火地待着。中午,老头儿去阅览室看报,拼命往脑子里记人名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闻。这时卡捷琳娜坐在钢琴前弹唱科斯塔尔斯基的宗教赞美诗,她还参加教堂合唱团。老头儿天黑之前才回家,吃饭,然后倒头睡觉。整栋房子陷入两个女人的低声絮语和黑暗中。这时卡捷琳娜去教堂参加合唱排练。父亲半夜醒来,点上灯,吃东西,深入领会《圣经》,大声背诵。大约六点时,老头儿又躺下睡着了。老头儿把时间弄颠倒了,不再害怕死亡,也不再担心寿命的长短。当着老头儿,母女俩都不说话。母亲熬粥,做汤,烤馅饼,煮牛奶,做酸奶,把肉冻藏起来(甚至把羊拐子也藏起来留给孙子),也就是说,她的生活像十五世纪和十七世纪时俄罗斯人的生活一样,她做的食物也同十五世纪和十七世纪的食物一样。玛丽亚·克利莫夫娜,这个干瘦的老太婆,想当年曾是一位奇美的女子,是在俄罗斯乡村连同古老的圣母像一起保存下来的妇女之典型。她的丈夫是个残酷无情的人。五十年前举行婚礼后第二天,她穿了一件深红色的丝绒坎肩,丈夫问她:“这是干什么?”(她当时没明白问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干什么?”丈夫又问了一遍。“脱下来!不穿华服盛装我也认得你,用不着穿给别人看!”这时丈夫把大拇指蘸上唾沫,给妻子演示她应该怎样梳理鬓发,把她弄得生疼。丈夫强迫妻子把丝绒坎肩收进箱子里,永远不得再穿,只让她下厨房。是丈夫的残酷无情摧毁了妻子的意志,抑或用顺从锻炼了她的意志?妻子一辈子都是那么绝对服从、本分、沉默、忧郁、悲伤,从不口是心非。她的活动范围不出自家的栅墙,出了栅墙,她只有一条路,一条去教堂的路,如同去墓地的路一样。她和女儿一起唱科斯塔尔斯基谱曲的圣诗,她六十九岁了。彼得大帝前的罗斯在这栋房子里凝固了。老头儿每天夜里都背诵《圣经》,不再担心寿命。老头儿很少,甚至一连数月都不进妻子的卧房,偶尔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走到妻子床前,低声说:“玛丽尤什卡,是啊,咳咳,哼!……是啊,咳咳,玛丽尤什卡,这就是生活,玛丽尤什卡!”
他手里擎着蜡烛,他的眼睛在流泪,在发笑,他的双手在颤抖:“玛丽尤什卡,咳咳,是我呀,是啊,这就是生活,玛丽尤什卡,咳咳!”
“您真不害臊,雅科夫·卡尔波维奇!……”
玛丽亚·克利莫夫娜画了一个十字。
雅科夫·卡尔波维奇熄灭了烛光。
女儿卡捷琳娜有一双黄色的小眼睛,由于经常做梦而显得呆滞无神。她那肿胀的眼皮周围长出许多雀斑。她的胳膊和腿粗壮得犹如原木,乳房很大,活像瑞士母牛的乳房。
这个小城是俄罗斯的布吕赫和俄罗斯的镰仓。
……
前言/序言
译者前言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利尼亚克(原姓沃高),1894年出生在莫斯科省莫扎伊斯克市一个兽医家庭。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他小时候随父母生活过许多地方,如萨拉托夫、诺金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科洛姆纳等,对外省生活十分了解。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在许多方面都受到平民知识分子环境和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在他的作品中多有印证。
他很小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自己认为他真正开始以文学创作为职业是在1915年。那时,各种刊物上都出现了他用笔名发表的短篇小说。1915年夏,他住在乌克兰一个乡村,那里的村民从事伐木业,因此被称为皮利尼亚克,即伐木人或拉锯人。于是他的作品便开始署名为皮利尼亚克。
1919年皮利尼亚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2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裸年》。这部作品使他一举成名,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国文字,同时也招致了严厉的批评和诘难。
他在小说中把十月革命描写成了一种自发势力,认为革命就像肆虐的暴风雪,像某种要挣脱束缚的野兽。尽管小说中出现的布尔什维克形象——“穿皮夹克的人们”是果敢坚强的,尽管他们的意志使俄国改变了面貌,但由于他“思想动摇”,他真正的革命性遭到批评界的怀疑。
从1921年到1937年10月28日他被捕为止,在这17年间,他游历了许多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希腊、中国等,大大开阔了眼界,对革命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发表了大约20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特写集等,还出版了一套6卷本文集和一套8卷本文集。1936年,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问世,这是他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盐仓》是他1937年创作完成的,但由于他的被捕而未能出版。
1937年10月28日晚,皮利尼亚克在庆祝儿子三周岁生日时被捕。临行前,妻子让他带上一包衣物等,但他没有带,“他想以自由人,而非被捕者走出家门”。
一个月后,他的妻子,电影演员基拉·格奥尔基耶夫娜在电影制片厂被捕。1938年4月21日,皮利尼亚克被枪决。1988年5月5日,苏联最高法院裁定:1938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指控皮利尼亚克为“国事犯”的判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他的枪决是毫无根据的。至此,50年过去了,皮利尼亚克终于得到了平反。
通过以上介绍不难看出,皮利尼亚克是一位勤奋的、多产的、有才华的作家,是20世纪上半叶苏联文学进程中重要的作家。
1997年,我应约翻译皮利尼亚克的《果实的成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作者后期的重要作品,其中有对历史的观照,有对现实的思考,如红塔尔卡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夭折、农民选举农民当沙皇、帕列赫圣像画工们革命前后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修建铁路、集体农庄……作品起承转合,收放自如,气势如虹,将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相互映衬,所承载的内容丰富而凝重,体现出作者一贯的敏锐洞察力和表现力及其不拘一格的艺术技巧。
这次收入本书的还有中篇小说《红木》和《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短篇小说《人的风》和《骗子手们》等。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发表于1926年,描写一位红军指挥员的死,人们猜测这位指挥员可能是刚去世不久的卫国战争英雄和天才军事指挥官伏龙芝。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第一个人——腰板挺直的人:“我召你来,是因为你需要做手术。你是革命不可或缺的人……这是革命的需要……我已下达了命令……”第二个人——集团军司令:“……我的医生告诉我,说我不需要做手术……我觉得自己是健康的,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手术,我不想做手术。”
书中对集团军司令加夫里洛夫是这样描写的:他是一个革命的老兵,战士,集团军司令,大元帅;他身经百战,叱咤疆场,战功赫赫;他号令千军,调兵遣将;他是卫国战争的英雄,是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英雄,他的名字变成了战争传奇的代名词。但是他为了执行上边的旨意,为了服从党的纪律,被迫接受了手术,并死在手术刀下。
书中对第一个人的着墨并不多,也没有指名道姓,只说他是一个腰板挺直的人,有一张极其普通的脸,也许有点儿冷酷,但却非常专注。加夫里洛夫死后,他亲临医院告别,并在尸体旁坐了许久。
从两个人的特征描写来看,很难不使人产生猜测,而且作者在作品前面画蛇添足地加了一个前言:“这篇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会使人联想到米·瓦·伏龙芝的死成了其写作的由头和素材……他去世的真实细节我不知道……报道人民委员将领的逝世无论如何不是我这篇小说的目的。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交代清楚……”因此,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猛烈批判,作者不得不发表了悔过信,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小说的意义是广泛的、深远的、不可否认的,因为在作品中首先指出党的“意见一致”和“绝对服从”的危险性的人是皮利尼亚克,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位有敏锐洞察力的“社会诊断医师”。
1929年,皮利尼亚克的《红木》在柏林出版。于是他又一次成了思想毒草的残酷的批判对象。当时批判者们愤怒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在国外侨民出版社出版的事实本身,而主要是作者表露出来的那种可疑态度,即小说中有一定篇幅是描写一群对革命失望的英雄。作者认为这是对其作品的肆意歪曲。作为抗议,作者声明退出作家协会(他时任全俄作协主席)。高尔基曾不止一次批评过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但他不同意以抹杀皮利尼亚克在苏联文学方面的功绩这种激烈的方式对待作者。
《红木》主要是通过买卖红木家具和古董的两兄弟帕维尔和斯捷潘、农民事务代理人雅科夫·卡尔波维奇及其被革命摒弃的变成疯疯癫癫的弟弟伊万等,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官僚主义、敷衍塞责、弄虚作假、倒买倒卖、侵吞国家财产等。书中描写了三个收购红木家具的场景,每一个场景后面都折射出一个令人感到悲凉同时又引人沉思的故事。
场景一:寡妇梅什金娜,一个行将就木的七十岁老太婆。她的房子建成于彼得大帝时代之前,是曾祖辈留下来的,由于建筑工艺是榫卯结构,当时堪称王府,至今仍保留着瓷砖壁炉和瓷砖火炕,瓷砖上面绘有用赭石和釉烧制的祥云和王公大臣。可是现在穿着破毡靴的老太婆不得不违背先祖的遗言,把这些文物级的瓷砖揭下来,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以换取维持生计的资费。
场景二:地主图奇科夫曾是上校,1915年被打死。他的大儿子也曾是一位军官,因患病于1925年自杀了。小儿子因反革命被枪毙了。他家从前的庄园现在变成了乳品厂。现在住在半地下室里的是图奇科夫的遗孀老太婆和大儿子的遗孀奥莉加及六个孩子,其中两个是被枪毙的小儿子的孩子。他们家现在一贫如洗,仅靠奥莉加每晚在影院弹钢琴艰难度日。一个刚三十岁的女人,已然变成满脸皱纹的沧桑老太婆。古董商以极低的价格打劫式地收买了她家的红木写字台、微型精细画、瓷器等。
场景三:从前的贵族卡拉津老爷病了,躺在餐室长沙发上,身上盖一件磨光了毛的松鼠皮外衣。他一见古董商便怒骂他们是坏蛋,叫他们滚开,说难道“他们会懂得艺术的妙处吗?”古董商见状转身要走,可是妻子陪笑留住了他们,因为她实在需要卖几件东西。无论卡拉津多么不情愿变卖文物,但生活是现实的。
雅科夫·卡尔波维奇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具有鲜明的那种庸俗卑微、吝啬粗俗、冷酷狡黠等小市民特征。他老迈,肥胖,白发,谢顶,眼睛老是流泪,脸上总挂着那种非常讨厌的、卑躬谄媚的、阴险恶毒的笑容,开口说话时先要喘一阵子,走路时一只手托住自己的疝突出。他每天半夜起来朗读《圣经》,下午去阅览室读报,拼命往脑子里记共产主义的新闻。他害怕上帝,记得农奴制,不喜欢无产阶级。他对妻子残酷无情,妻子一辈子都只能对他绝对服从,活动范围不出自家的栅墙,出了栅墙,她只有一条去教堂的路,如同去坟墓的路一样。他的儿子们也都被他打跑了,与他没有往来。他积极为古董商物色古董并且亲自找人把古董商收来的古董打包托运,可谓不遗余力。而他自己的红木家具、青铜酒器等古物一件都不出手。他是农民事务代理人,经常帮农民写徒劳无用的证明材料或呈子,还经常写传单和哲学论文。总之,他简直可憎得令人厌恶。
他的弟弟伊万曾是这座小城的第一位共产党员,首任执委会主席。1921年,伊万和像他一样的一群共产党员被驱逐出党。他们是一群被革命摒弃,但又被革命造就的人,一群思想停顿的人,精神失常的人和醉汉。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了能在窑坑里取暖栖身,无偿地为砖厂烧砖卖命。他们有兄弟般的团结、平等和友谊。伊万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执着地到处奔走呼号,一次次在集市上演讲,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那套慷慨而荒诞的话落泪,并且都很尊敬他,像书中第一章所描写的旧时俄国对疯修士无限尊崇那样,认为伊万就是苏维埃罗斯的疯修士,他的话是有预言性的。伊万还坚定地认为,他的兄长雅科夫·卡尔波维奇是历史反革命,他的侄子阿基姆早晚会被开除出党。果然,阿基姆的情况的确不妙。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他的党派被清除了,“革命对于他既是生活的开端,又是生活的本身,亦是生活的终结”。
从作品看,作者对革命的认识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他对革命也是持欢迎态度的,也很高兴看到贵族的瓦解和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他在革命的进程中和革命后的现实中所看到的问题,令他深感不安。于是他把这些问题以他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和鲜明的态度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对于当局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同时应该看到的是,作家在对革命的艺术诠释中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独到眼光,以及真诚和勇气。
皮利尼亚克最熟悉、最擅长表现的是外省生活,是小城镇、小市民的生活。
《红木》描写的外省小城生活是沉闷、庸俗、落后、闭塞和孤独的。那里的人们整天躲在自己狭窄的小天地里瞎忙活,对外面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甚至博物馆馆长竟然跟一尊刻着凡人嘴的坐式裸体基督的木雕像一起喝酒!寂寞的荒唐!孤独的怪诞!
卡皮托利娜和里玛是姐妹俩,都是这个小城的裁缝,但她们的生活轨迹和晚景迥然不同:姐姐一生恪守本分,年轻时除了缝纫就是祷告,她是全城的道德楷模,赢得了小市民阶层的尊敬。可是她的贞洁使她的晚年收获了一杯自酿自饮的浓浓苦酒:凄凉与孤独。妹妹的生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年轻时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生下两个女儿——两个耻辱的证据,她成了耻辱本身。她在赤贫和羞辱中带大了两个女儿,并当上了外婆。她的耻辱使她的晚年收获了满满的幸福:生活充满活力和温馨。
《人的风》描写妻子产后产生幻觉,写下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丈夫醋意大发,对妻子大加羞辱,妻子不堪忍受,抱着襁褓中的儿子伊万,愤然离家出走,辗转来到莫斯科。三年后,妻子又生一子,取名尼古拉,跟了大儿子父亲的姓。因为尼古拉的生父连名字都没有给他起,便弃他们母子而去。后来母亲死了,大儿子由外省的姨妈抚养长大,成为一名军人;患有癫痫,腿有残疾的小儿子在孤儿院长大,上了技工学校。他们经常通信,信中充满对母亲的怀念。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兄弟俩约定从各自的地方出发去看望远在另一个城市的父亲。他们不知道他们并非同父兄弟。弟弟先期到达父亲家,结果遭遇了像母亲当年所遭遇的羞辱,这对于见父心切的他不啻五雷轰顶!哥哥知道了弟弟的遭遇,决定不去看望父亲。站在门口等亲生儿子归来的父亲,直到天黑也没有等到。第二天早上,父亲在火车站看到:一身戎装的哥哥挽着拄杖的弟弟从他身边走过去。他又一次吞咽着自己用怨恨酿成的苦果,经受着精神上的酷刑。他像一具散发着尸体气味的行尸走肉,在对妻子的怨怼中煎熬,在对儿子的思念中枯萎……
《骗子手们》是通过一位去莫斯科办离婚手续的女农艺师在河岸边看见一个穷困而有幸福感的村妇,在列车上听到两个大概是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对话,反映革命后苏联社会的现实:无论是经营服装鞋帽的合作社,还是经营肉食品的合作社,全都不成功,因为合作社的员工缺乏素质培训。无论是店员、收款员,还是经理,全都是骗子,是窃贼,他们卖什么就往自己家拿什么,不付钱,白拿。盗窃成风。
评论界认为,皮利尼亚克是文学技巧的实验者和大师,继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同时又积极运用了现代主义的经验。他通过一系列看似荒诞不经、古怪离奇的故事情节,或急剧变化,或人物群体,以不拘一格的艺术技巧生动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对细节的描写生动、逼真、可信。他对生活的观察是敏锐而细致的,对人的命运的思考是犀利而深刻的,对陋习、庸俗、落后和残酷的揭露与针砭是辛辣而不留情面的。
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皮利尼亚克的作品读起来并不轻松。有时会突然觉得找不到中心或主题,跟不上作者驾驭的三马车跳跃式地在忽而历史忽而现实的时空中穿越;有时觉得故事情节荒诞得不可思议,又逼真得如在眼前;有时觉得作者在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残酷的现实生活,从而使现实生活更增添了凄苦与无奈,或希望与光明;有时觉得作者在用象征主义手法赋予作品中的事件或人物某种寓意,觉得弦外有音,话中有话。总之,他的作品耐看耐品,有厚重感,有历史穿越感。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解读,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评判。但无论怎样,历史都不能假设,也不能按照假设重新来过。历史总是在曲曲折折中前行,在惨烈与辉煌中定格。
刘引梅
2017年4月
用户评价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那么这本书为我打开的那扇窗,展示的是一种饱含着时代烙印和地域色彩的复杂人性图景。故事里的那些个体,他们的挣扎和选择,都深深地嵌入了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和社会背景之中。我特别关注到作者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的,那些固守的旧有观念如何与新涌入的思潮发生碰撞,产生的火花既有毁灭性,也带来了一丝新生。这种对宏大背景下个体命运的关注,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思考的张力。我常常在想,如果我置身于那样一个环境,我会做出怎样的决定?这种自我投射和反思,是优秀文学作品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它不是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抛出深刻的问题,促使我们去审视自身的立场和选择的重量。那些看似朴素的故事情节,实则暗流涌动,直指人性的核心困境。
评分这本选集展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语言驾驭能力,用词的精准和句式的多变,简直像一位技艺高超的雕塑家在打磨他的作品。我不是文学科班出身,但能明显感受到那些句子本身就具有一种音乐性。有的段落如同急促的鼓点,将紧张的情绪一波推向一波;而另一些地方,文字则舒展、悠长,带着一种近乎古典的韵律感,读起来需要反复咀嚼才能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深层意象。特别是关于人物内心独白的刻画,作者似乎能直接探入角色的灵魂深处,捕捉那些连角色自己都难以言明的矛盾与挣扎。这种内在的挖掘深度,使得角色摆脱了脸谱化的窠臼,变得立体而复杂,让人既同情又保持着距离的审视。对于语言爱好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场盛宴,它证明了文学的力量不仅仅在于“说什么”,更在于“怎么说”。我甚至会特意摘录一些句子,仅仅是欣赏它们在结构和音韵上的完美契合。
评分我必须得说,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具有实验性,它似乎刻意避开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通过碎片化的记忆、穿插的独白以及不同时间点的跳跃,来构建一个整体的认知。初次接触时,这种跳跃感可能会让人有些措手不及,感觉信息点是分散的,需要读者主动去搭建逻辑的桥梁。但一旦适应了这种节奏,你会发现,这种非线性的手法恰恰最符合人类记忆和情感的运作方式——我们的感受往往是片段式的、非线上的。作者通过这种巧妙的编排,成功地营造了一种“记忆重构”的阅读体验。每一次回到某个场景,都有了新的理解,因为你已经掌握了后续的信息。这种阅读上的“主动参与性”,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耐读性和回味价值。比起一览无余的直白讲述,这种需要读者动脑筋去拼凑的艺术,更让人感到满足。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处理得实在是妙极了,初读时可能会觉得有些散漫,仿佛作者是在漫不经心地铺陈一幅乡村生活的画卷,然而仔细品味,便能察觉到那份看似随意的笔触下蕴含的深沉力量。每一个场景的转换,每一次人物对话的停顿,都精准地卡在了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想象力的位置。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环境氛围的渲染,那种泥土的芬芳、阳光穿过树叶的斑驳光影,都被描摹得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能切实体会到故事发生地的气息。这种细腻入微的观察力,使得即便是最平凡的日常片段,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情节的推进并非靠跌宕起伏的事件,而是更多地依赖于人物内心微妙的波澜和他们之间无声的张力。读完后,那些人物的形象久久不散,他们身上那种根植于土地的坚韧与无可奈何的宿命感,构成了阅读体验中最深刻的一部分。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的“慢”,它要求读者放慢呼吸,去感受生活本来的质地,而非仅仅追逐故事的走向。
评分从整体的情感基调来看,这本书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略带忧郁的诗意。这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悲观,而是一种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后所产生的一种平静的接受,甚至是带着一丝黑色幽默的自嘲。书中的人物常常在困境中展现出一种近乎荒谬的尊严,他们的悲剧性并非完全由外力造成,也源于他们自身的局限和无法逾越的人性弱点。作者处理悲剧的手法非常高明,他没有试图去美化痛苦,也没有让读者沉溺于感伤,而是用一种冷静、疏离的笔触,去描绘痛苦本身的样子。这种克制感使得情感的表达更有力量,如同冰面下涌动的暗流,看似平静,实则汹涌。读完之后,心中留下的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更清晰、更坦然地面对生活复杂性的勇气。这是一种成熟的、富有哲思的文学表达。
评分好书好书好书
评分皮利尼亚克,俄罗斯文学大师得罪作品,值得期待
评分尼亚克通过一系列看似荒诞不经、古怪离奇的故事情节,以不拘一格的艺术技巧生动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对细节的描写生动逼真!
评分包装好,送货快。
评分包装好,送货快。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不错,细细品读。
评分好书好书好书
评分白银时代的名作,很有个性的作品。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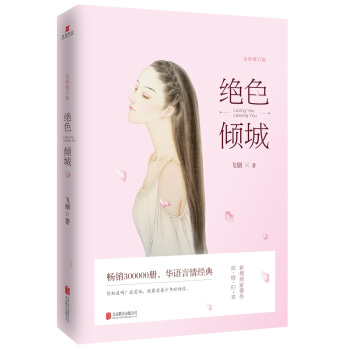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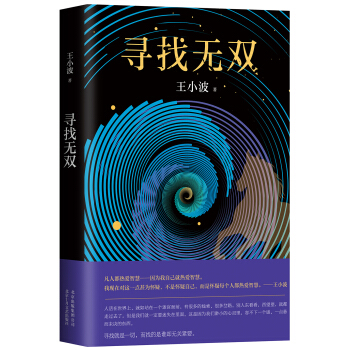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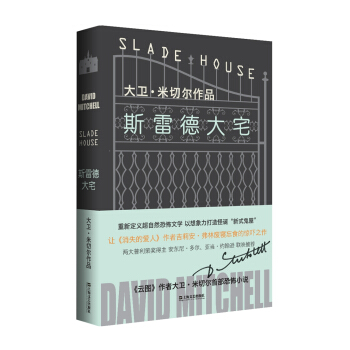











![险境生存(套装共4册) [The Worst-Case Scenario Ultimate Adventu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88615/57fdccebN918977d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