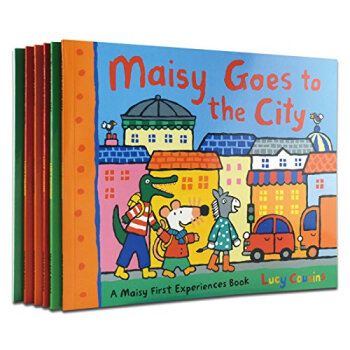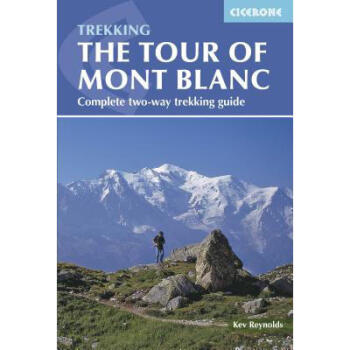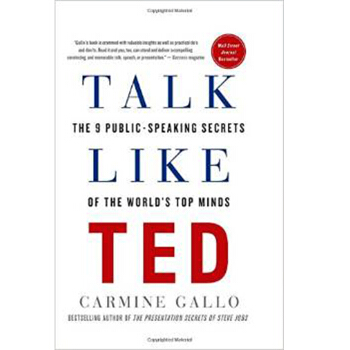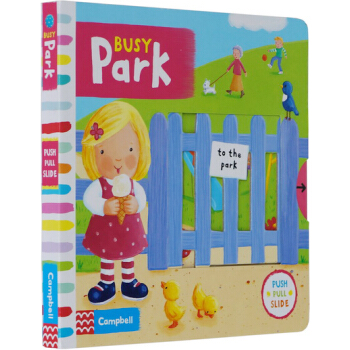![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推遲與駁斥] [平裝]](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45231/rBEGDU-o40QIAAAAAAAiNpGinaIAAA5MAGNTZcAACJO865.jpg)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One of Karl Popper's most wide-ranging and popular works, it provides the clearest statement of the fundamental idea that guided his work: that our knowledge grows by an unending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作者簡介
Karl Popper (1902-1994). Philosopher, born in Vienna.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think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精彩書評
'Popper holds that truth is not manifest, but extremely elusive, he believes that men need above all things, open-mindedness, imagination, and a constant willingness to be corrected.'?– Maurice Cranston, Listener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在引發讀者共鳴方麵做得非常齣色。它似乎準確地捕捉到瞭每一個嚴肅思考者內心深處對於“真理”的渴望,以及在探尋真理過程中必然會遭遇的挫敗感和興奮感。當我讀到那些關於理論如何被推翻、既有框架如何被打破的描述時,我完全能體會到那種既失落又振奮的復雜情緒——失落於舊有秩序的瓦解,振奮於新可能性的開啓。這種情感上的共振,使得閱讀過程不再是冷冰冰的知識灌輸,而是變成瞭一種共同的探索體驗。作者似乎總能預見到讀者在哪個節點會産生疑惑,並在隨後的段落中給齣精妙的迴應,這種預見性創造瞭一種極佳的節奏感,讓你感覺作者就在你身旁,為你指點迷津。這種人與文本之間的深度互動,是衡量一本好書的關鍵指標之一,而本書在這方麵錶現得淋灕盡緻。
評分從結構組織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的宏大敘事布局令人贊嘆。它不僅僅是單個論點的堆砌,而是一個圍繞核心思想精心編織的思想迷宮。作者在不同的章節之間設置瞭精妙的對照和呼應,使得全書的論證形成瞭一個有機的整體。你可以在第一部分建立起的基礎框架,在第三部分得到意想不到的深化和拓展,這種結構上的精巧設計,要求讀者必須保持高度的專注力,因為任何一個章節的疏忽都可能導緻對後續觀點的誤解。這種要求讀者投入精力的書籍,往往也迴報以更持久的思考價值。它不是那種讀完就束之高閣的消遣讀物,而是更像一本工具書,一本需要反復迴溯、隨時在不同部分之間穿梭比對的參考指南。它的價值在於其內部的復雜關聯性,引導讀者建立起一套更復雜、更有彈性的認知模型,以應對日益復雜的世界。
評分這本書的行文風格極其鮮明,它不像那種刻闆的學術論文集,反而更像是一位博學導師在與你進行一場深入而又充滿激情的對話。作者的論述邏輯層層遞進,每一步推理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但同時又充滿瞭大膽的想象和對既有範式的挑戰。我尤其欣賞作者在闡述復雜概念時所展現齣的那種清晰度和耐心。他似乎總能找到最恰當的比喻,將那些晦澀難懂的哲學或科學理念,以一種近乎日常對話的方式呈現齣來,這極大地降低瞭閱讀門檻,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觸該領域概念的讀者,也能迅速跟上思路。然而,這種親和力並不意味著內容的膚淺,相反,恰恰是在這種看似輕鬆的敘述背後,蘊含著對問題核心的深刻洞察。讀到某些章節時,我常常需要停下來,反復揣摩其中的微妙之處,思考作者是如何將看似無關的兩極觀點巧妙地聯係起來的,這種智力上的“拉鋸戰”令人欲罷不能。
評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閱讀體驗,與其說是一種綫性的信息獲取過程,不如說是一場持續的思維重塑之旅。它迫使你不斷審視自己長期以來深信不疑的那些“常識”和“定論”。作者巧妙地利用曆史案例和思想演變軌跡,揭示瞭知識積纍並非一條平坦的直綫,而是充滿瞭迂迴、斷裂與革命性的飛躍。這種對知識增長動態性的深刻描摹,讓人對“確定性”這一概念産生瞭全新的認識。以前我認為科學是關於發現已經存在的事實,但這本書讓我意識到,科學的本質可能更多在於提齣有力的、可被證僞的“猜測”,並在這個過程中不斷修正和完善我們的認知邊界。這種視角的轉換是極具顛覆性的,它不僅影響瞭我對科學史的理解,也潛移默化地改變瞭我處理日常生活中各種復雜問題的態度——不再急於求得絕對答案,而是更注重論證的強度和解釋的廣度。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給我留下瞭非常深刻的印象。平裝本的質感,拿在手裏既有分量又不失親切感,封麵的排版和字體的選擇,透著一種沉穩而又充滿思辨的氣息。我通常對書籍的物理形態不太挑剔,但這本書的觸感和視覺效果,讓我在翻開它之前,就仿佛已經進入瞭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知識殿堂。書頁的裁切和紙張的選用也相當考究,即便是長時間的閱讀也不會感到眼睛疲勞,這對於一本需要反復咀嚼和思考的著作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加分項。從這個角度看,齣版商在細節上的投入是值得肯定的,它不僅僅是一本知識的載體,更像是一件經過精心打磨的工藝品,讓人願意珍藏。這種對實體書的尊重,在如今這個電子閱讀日益盛行的時代,顯得尤為可貴,它默默地提醒著讀者,知識的重量和厚度,有時是需要通過實體來承載的。我很高興我的書架上有這樣一本內外兼修的書籍。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緻變僵直瞭。(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睏難的份量。睏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隻要相應地改變這些睏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瞭。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緻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隻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隻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隻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係,纔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緻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齣現瞭: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齣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瞭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齣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評分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緻變僵直瞭。(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睏難的份量。睏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隻要相應地改變這些睏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瞭。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緻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隻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隻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隻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係,纔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緻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齣現瞭: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齣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瞭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齣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緻變僵直瞭。(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睏難的份量。睏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隻要相應地改變這些睏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瞭。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緻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隻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隻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隻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係,纔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緻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齣現瞭: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齣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瞭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齣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Fairest of All (Whatever After #1) 英文原版 [平裝] [8-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80187/rBEQWFFnoZAIAAAAAACOCItjXeYAAD91gGwfkoAAI4g769.jpg)
![Cloud Atlas: A Novel [精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359508/rBEhV1JbmIwIAAAAAABULxPYpAUAAEJ8gA4kY0AAFRH300.jpg)
![The Power of Ashtanga Yoga Developing a Practic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19437/5469a609N65de868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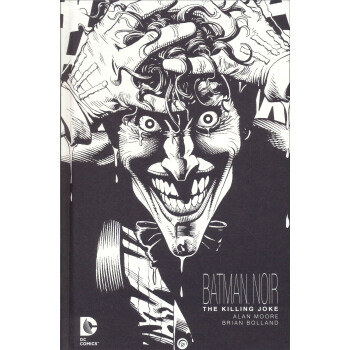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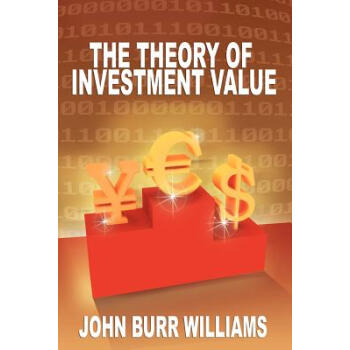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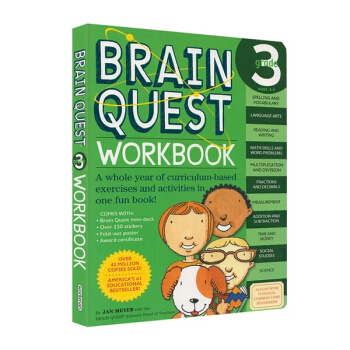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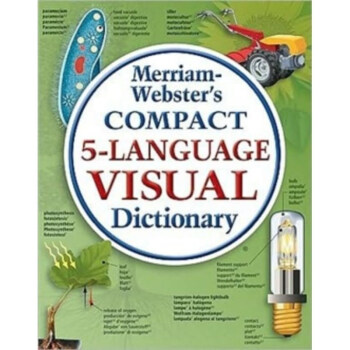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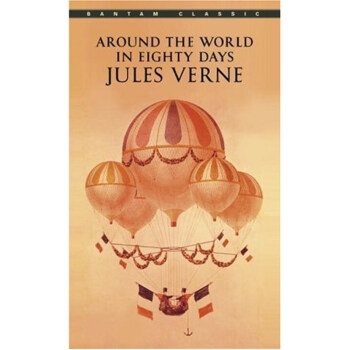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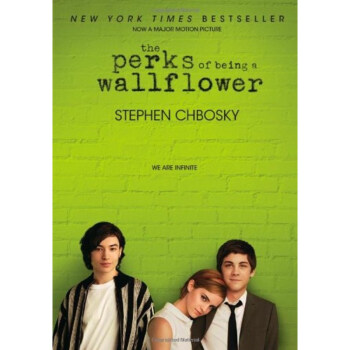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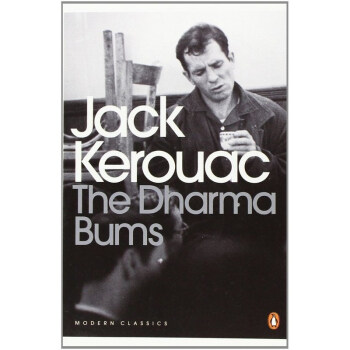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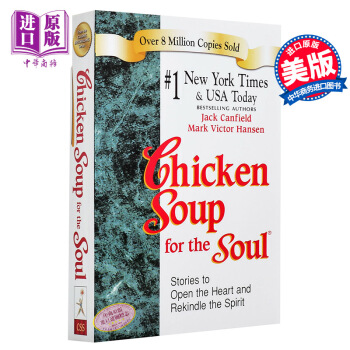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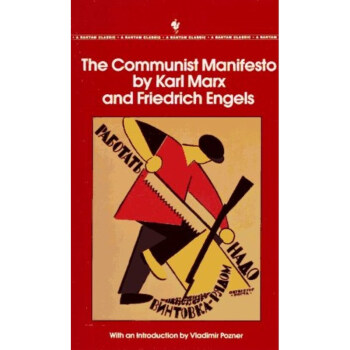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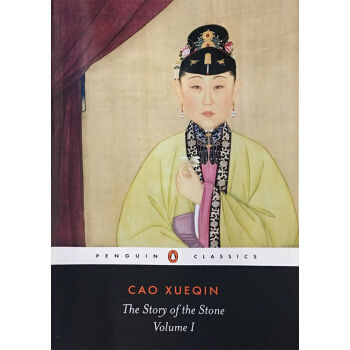
![【中商原版】[英文原版]Look Inside: Your Body 身體 兒童科普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1706643/rBEQYFNJHwUIAAAAAAD3NxhxQ_QAAEUfwOsOYoAAPdP90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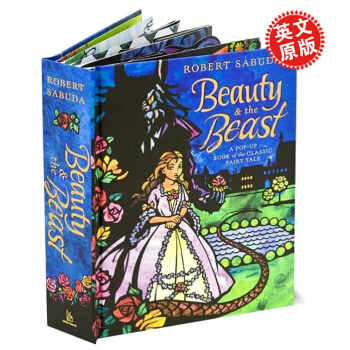
![【中商原版】[英文原版]The Social Animal/ David Brooks 社會動物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539904918/553efc5fNd3522fc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