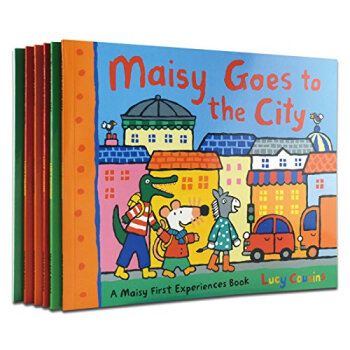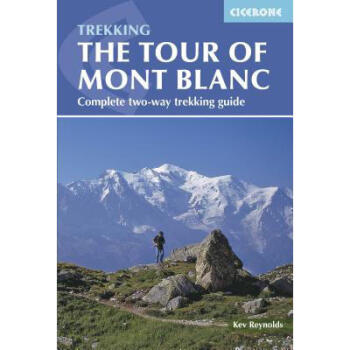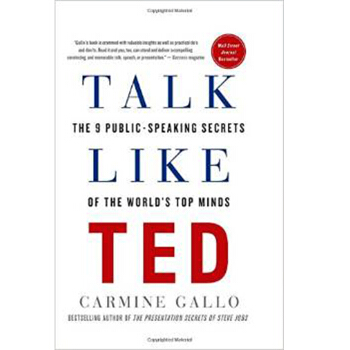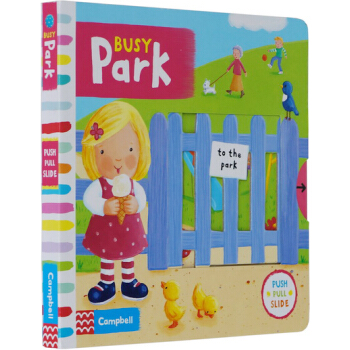![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推迟与驳斥] [平装]](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45231/rBEGDU-o40QIAAAAAAAiNpGinaIAAA5MAGNTZcAACJO865.jpg)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One of Karl Popper's most wide-ranging and popular works, it provides the clearest statement of the fundamental idea that guided his work: that our knowledge grows by an unending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作者简介
Karl Popper (1902-1994). Philosopher, born in Vienna.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think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精彩书评
'Popper holds that truth is not manifest, but extremely elusive, he believes that men need above all things, open-mindedness, imagination, and a constant willingness to be corrected.'?– Maurice Cranston, Listener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一种线性的信息获取过程,不如说是一场持续的思维重塑之旅。它迫使你不断审视自己长期以来深信不疑的那些“常识”和“定论”。作者巧妙地利用历史案例和思想演变轨迹,揭示了知识积累并非一条平坦的直线,而是充满了迂回、断裂与革命性的飞跃。这种对知识增长动态性的深刻描摹,让人对“确定性”这一概念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以前我认为科学是关于发现已经存在的事实,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科学的本质可能更多在于提出有力的、可被证伪的“猜测”,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我们的认知边界。这种视角的转换是极具颠覆性的,它不仅影响了我对科学史的理解,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我处理日常生活中各种复杂问题的态度——不再急于求得绝对答案,而是更注重论证的强度和解释的广度。
评分从结构组织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宏大叙事布局令人赞叹。它不仅仅是单个论点的堆砌,而是一个围绕核心思想精心编织的思想迷宫。作者在不同的章节之间设置了精妙的对照和呼应,使得全书的论证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你可以在第一部分建立起的基础框架,在第三部分得到意想不到的深化和拓展,这种结构上的精巧设计,要求读者必须保持高度的专注力,因为任何一个章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对后续观点的误解。这种要求读者投入精力的书籍,往往也回报以更持久的思考价值。它不是那种读完就束之高阁的消遣读物,而是更像一本工具书,一本需要反复回溯、随时在不同部分之间穿梭比对的参考指南。它的价值在于其内部的复杂关联性,引导读者建立起一套更复杂、更有弹性的认知模型,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世界。
评分这本书在引发读者共鸣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似乎准确地捕捉到了每一个严肃思考者内心深处对于“真理”的渴望,以及在探寻真理过程中必然会遭遇的挫败感和兴奋感。当我读到那些关于理论如何被推翻、既有框架如何被打破的描述时,我完全能体会到那种既失落又振奋的复杂情绪——失落于旧有秩序的瓦解,振奋于新可能性的开启。这种情感上的共振,使得阅读过程不再是冷冰冰的知识灌输,而是变成了一种共同的探索体验。作者似乎总能预见到读者在哪个节点会产生疑惑,并在随后的段落中给出精妙的回应,这种预见性创造了一种极佳的节奏感,让你感觉作者就在你身旁,为你指点迷津。这种人与文本之间的深度互动,是衡量一本好书的关键指标之一,而本书在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平装本的质感,拿在手里既有分量又不失亲切感,封面的排版和字体的选择,透着一种沉稳而又充满思辨的气息。我通常对书籍的物理形态不太挑剔,但这本书的触感和视觉效果,让我在翻开它之前,就仿佛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知识殿堂。书页的裁切和纸张的选用也相当考究,即便是长时间的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这对于一本需要反复咀嚼和思考的著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加分项。从这个角度看,出版商在细节上的投入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仅是一本知识的载体,更像是一件经过精心打磨的工艺品,让人愿意珍藏。这种对实体书的尊重,在如今这个电子阅读日益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它默默地提醒着读者,知识的重量和厚度,有时是需要通过实体来承载的。我很高兴我的书架上有这样一本内外兼修的书籍。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极其鲜明,它不像那种刻板的学术论文集,反而更像是一位博学导师在与你进行一场深入而又充满激情的对话。作者的论述逻辑层层递进,每一步推理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但同时又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和对既有范式的挑战。我尤其欣赏作者在阐述复杂概念时所展现出的那种清晰度和耐心。他似乎总能找到最恰当的比喻,将那些晦涩难懂的哲学或科学理念,以一种近乎日常对话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触该领域概念的读者,也能迅速跟上思路。然而,这种亲和力并不意味着内容的肤浅,相反,恰恰是在这种看似轻松的叙述背后,蕴含着对问题核心的深刻洞察。读到某些章节时,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反复揣摩其中的微妙之处,思考作者是如何将看似无关的两极观点巧妙地联系起来的,这种智力上的“拉锯战”令人欲罢不能。
评分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致變僵直了。(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困難的份量。困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只要相應地改變這些困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了。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致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只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只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只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系,才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致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出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了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评分首先,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购买的廉价原版书相比,纸张、装订、印刷的质量至少高出一筹。作者的论证非常深入且复杂,但结论又非常清晰简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合理懷疑余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里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家,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出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向導致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致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只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才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向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了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了)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制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出與精神分析學相一致的一點。精神分析家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向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向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向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制,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合,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致,傷害或刺激造成了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评分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致變僵直了。(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困難的份量。困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只要相應地改變這些困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了。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致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只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只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只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系,才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致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出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了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评分首先,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购买的廉价原版书相比,纸张、装订、印刷的质量至少高出一筹。作者的论证非常深入且复杂,但结论又非常清晰简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合理懷疑余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里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家,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出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向導致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致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只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才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向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了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了)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制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出與精神分析學相一致的一點。精神分析家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向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向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向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制,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合,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致,傷害或刺激造成了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评分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致變僵直了。(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困難的份量。困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只要相應地改變這些困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了。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致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只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只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只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系,才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致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出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了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评分首先,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购买的廉价原版书相比,纸张、装订、印刷的质量至少高出一筹。作者的论证非常深入且复杂,但结论又非常清晰简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合理懷疑余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里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家,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出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向導致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致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只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才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向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了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了)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制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出與精神分析學相一致的一點。精神分析家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向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向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向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制,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合,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致,傷害或刺激造成了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致變僵直了。(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困難的份量。困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只要相應地改變這些困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了。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致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只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只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只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系,才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致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出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了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评分首先,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购买的廉价原版书相比,纸张、装订、印刷的质量至少高出一筹。作者的论证非常深入且复杂,但结论又非常清晰简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合理懷疑余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里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家,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出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向導致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致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只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才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向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了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了)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制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出與精神分析學相一致的一點。精神分析家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向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向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向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制,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合,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致,傷害或刺激造成了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致變僵直了。(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困難的份量。困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只要相應地改變這些困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了。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致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只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只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只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系,才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致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出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了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评分首先,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购买的廉价原版书相比,纸张、装订、印刷的质量至少高出一筹。作者的论证非常深入且复杂,但结论又非常清晰简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合理懷疑余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里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家,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出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向導致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致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只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才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向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了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了)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制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出與精神分析學相一致的一點。精神分析家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向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向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向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制,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合,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致,傷害或刺激造成了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致變僵直了。(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困難的份量。困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只要相應地改變這些困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了。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致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只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只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只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系,才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致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出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了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评分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致變僵直了。(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困難的份量。困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只要相應地改變這些困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了。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致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只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只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只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系,才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致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出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了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Fairest of All (Whatever After #1) 英文原版 [平装] [8-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80187/rBEQWFFnoZAIAAAAAACOCItjXeYAAD91gGwfkoAAI4g769.jpg)
![Cloud Atlas: A Novel [精装]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359508/rBEhV1JbmIwIAAAAAABULxPYpAUAAEJ8gA4kY0AAFRH300.jpg)
![The Power of Ashtanga Yoga Developing a Practic [平装]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19437/5469a609N65de868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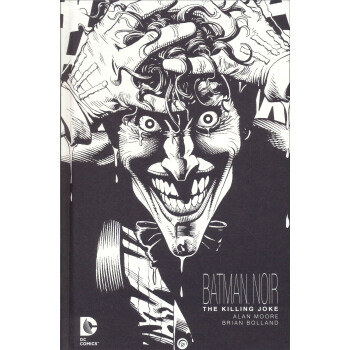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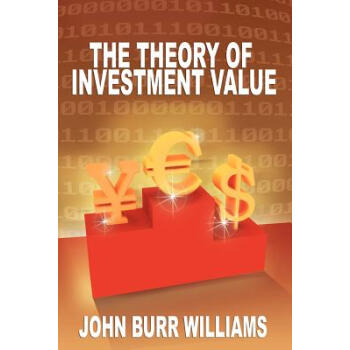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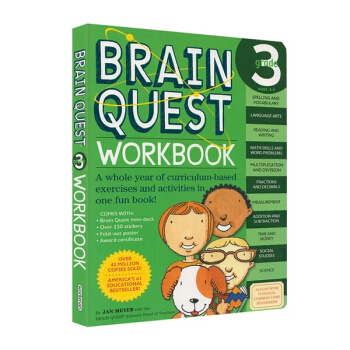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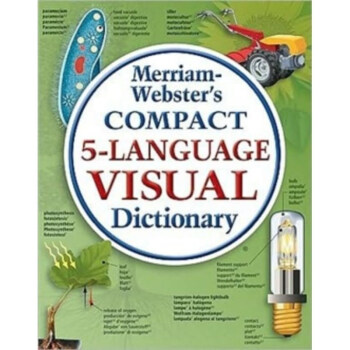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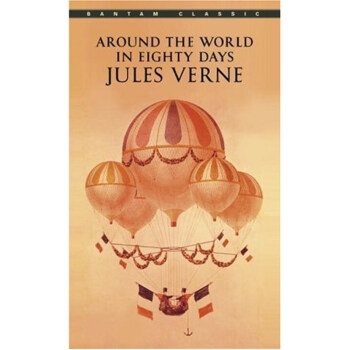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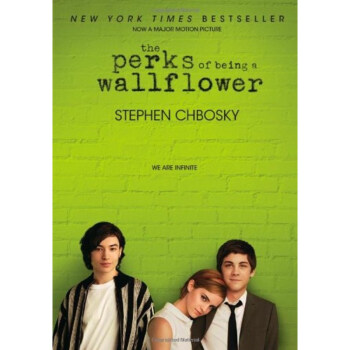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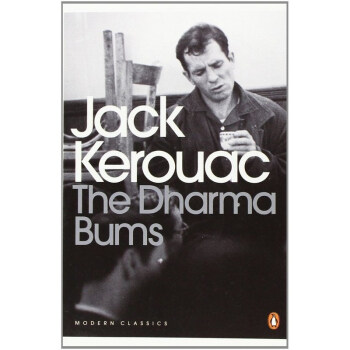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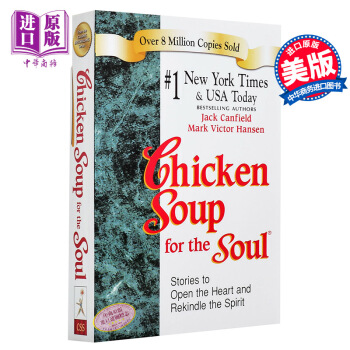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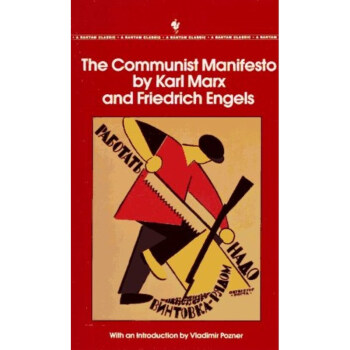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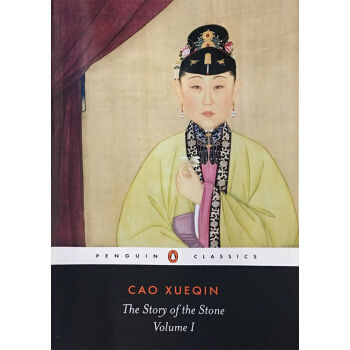
![【中商原版】[英文原版]Look Inside: Your Body 身体 儿童科普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1706643/rBEQYFNJHwUIAAAAAAD3NxhxQ_QAAEUfwOsOYoAAPdP90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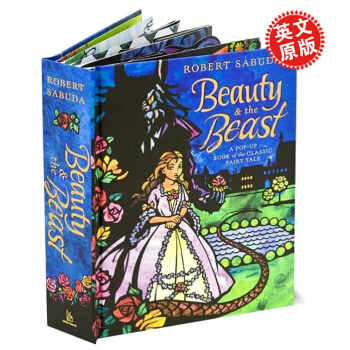
![【中商原版】[英文原版]The Social Animal/ David Brooks 社会动物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539904918/553efc5fNd3522fc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