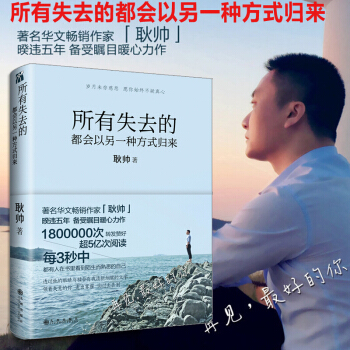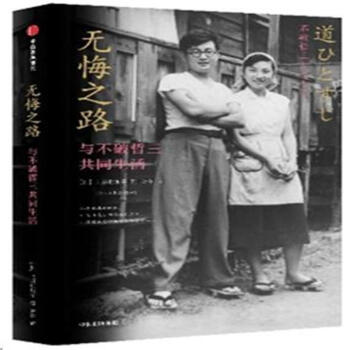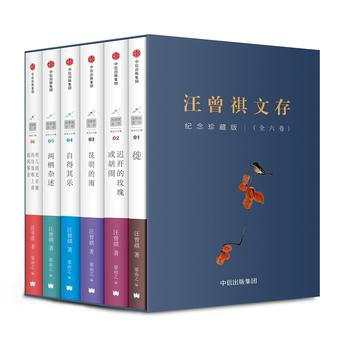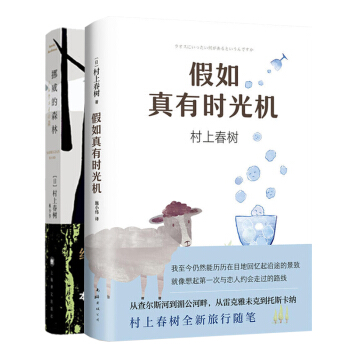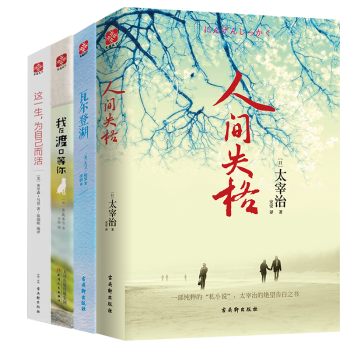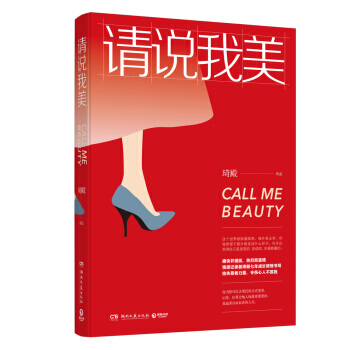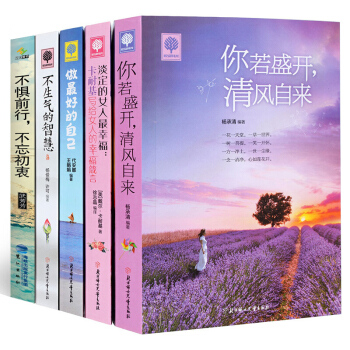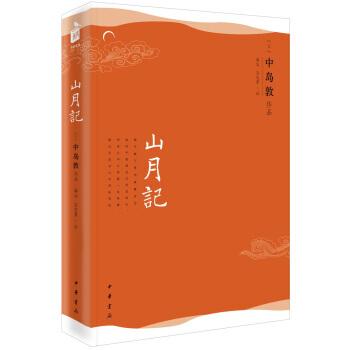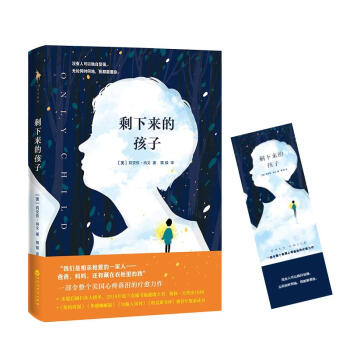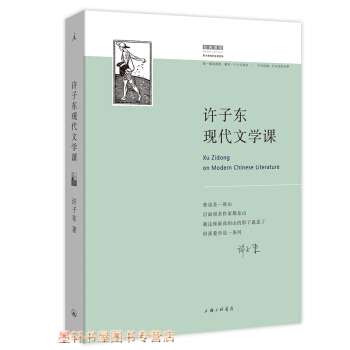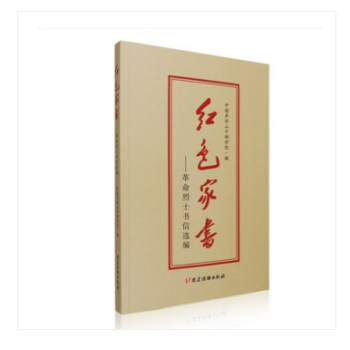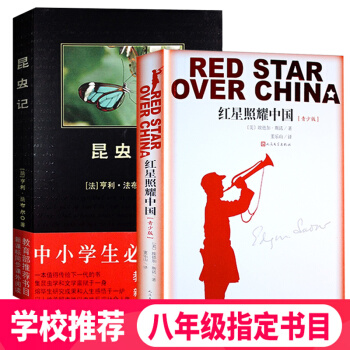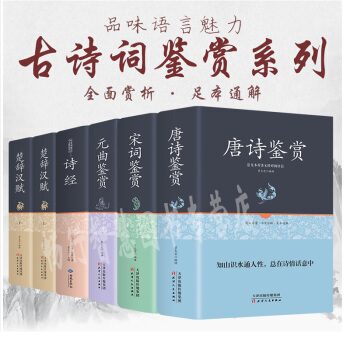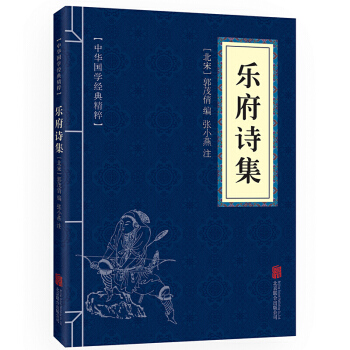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
《活著》榮獲意大利格林紮納·卡佛文學奬高奬項(1998年)、《中國時報》10本好書奬(1994年)、香港“博益”15本好書奬(1994年)、第三屆世界華文“冰心文學奬”(2002年),入選香港《亞洲周刊》評選的“20世紀中文小說百年百強”、中國百位批評傢和文學編輯評選的“20世紀90年代極有影響的10部作品”。餘華的每一部長篇小說,都震撼著一批又一批的讀者。他的長篇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經典之作。
內容簡介
《活著(新版)》講述瞭農村人福貴悲慘的人生遭遇。福貴本是個闊少爺,可他嗜賭如命,終於賭光瞭傢業,一貧如洗。他的父被他活活氣死,母則在窮睏中患瞭重病,福貴前去求藥,卻在途中被抓去當壯丁。經過幾番波摺迴到傢裏,纔知道母早已去世,妻子傢珍含辛茹苦地養大兩個兒女。此後更加悲慘的命運一次又一次降臨到福貴身上,他的妻子、兒女和孫子相繼死去,後隻剩福貴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但老人依舊活著,仿佛比往日更加灑脫與堅強。
作者簡介
餘華,1960年齣生,1983年開始寫作。至今已經齣版長篇小說4部,中短篇小說集6部,隨筆集4部。主要作品有《兄弟》《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等 。其作品已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瑞典、挪威、希臘、俄羅斯、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剋、塞爾維亞、斯洛伐剋、波蘭、巴西、以色列、日本、韓國、越南、泰國和印度等國齣版。曾獲意大利格林紮納·卡佛文學奬(1998年)、法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勛章(2004年)、中華圖書特殊貢獻奬(2005年)、法國信使外國小說奬(2008年)等。
精彩書評
★這是真正意義上,讓我覺得無話可說的小說。言語讓我覺得自己蒼白膚淺。 ——讀者評論★第1次看的時候還是個學生,在宿捨裏 ,躲在床上,大傢沉默著看著這本書。後始終忍不住,對麵的女孩帶著哭腔開始罵人,怎麼可以這樣,怎麼可以這樣?一抬頭,大傢的眼睛都是紅的。 ——讀者評論
★後的結束,其實作者也對我們昭示著生命的希望,無論這個生命正經曆著怎樣的悲苦? ——讀者評論
★高中時看過,對我觸動很大。然後就把餘華的其他基本書都看瞭。感動。改變瞭我的人生觀。 ——讀者評論
目錄
中文版自序活著外文版評論摘要精彩書摘
我比現在年輕十歲的時候,獲得瞭一個遊手好閑的職業,去鄉間收集民間歌謠。那一年的整個夏天,我如同一隻亂飛的麻雀,遊蕩在知瞭和陽光充斥的農村。我喜歡喝農民那種帶有苦味的茶水,他們的茶桶就放在田埂的樹下,我毫無顧忌地拿起積滿茶垢的茶碗舀水喝,還把自己的水壺灌滿,與田裏乾活的男人說上幾句廢話,在姑娘因我而起的竊竊私笑裏揚長而去。我曾經和一位守著瓜田的老人聊瞭整整一個下午,這是我有生以來瓜吃得多的一次,當我站起來告辭時,突然發現自己像個孕婦一樣步履艱難瞭。然後我與一位當上瞭祖母的女人坐在門檻上,她編著草鞋為我唱瞭一支《十月懷胎》。我喜歡的是傍晚來到時,坐在農民的屋前,看著他們將提上的井水潑在地上,壓住蒸騰的塵土,夕陽的光芒在樹梢上照射下來,拿一把他們遞過來的扇子,嘗嘗他們的鹽一樣鹹的鹹菜,看看幾個年輕女人,和男人們說著話。 我頭戴寬邊草帽,腳上穿著拖鞋,一條毛巾掛在身後的皮帶上,讓它像尾巴似的拍打著我的屁股。我整日張大嘴巴打著哈欠,散漫地走在田間小道上,我的拖鞋吧嗒吧嗒,把那些小道弄得塵土飛揚,仿佛是車輪滾滾而過時的情景。 我到處遊蕩,已經弄不清楚哪些村莊我曾經去過,哪些我沒有去過。我走近一個村子時,常會聽到孩子的喊叫: “那個老打哈欠的人又來啦。” 於是村裏人就知道那個會講葷故事會唱酸麯的人又來瞭。其實所有的葷故事所有的酸麯都是從他們那裏學來的,我知道他們全部的興趣在什麼地方,自然這也是我的興趣。我曾經遇到一個哭泣的老人,他鼻青臉腫地坐在田埂上,滿腹的悲哀使他變得十分激動,看到我走來他仰起臉哭聲更為響亮。我問他是誰把他打成這樣的?他用手指挖著褲管上的泥巴,憤怒地告訴我是他那不孝的兒子,當我再問為何打他時,他支支吾吾說不清楚瞭,我就立刻知道他準是對兒媳乾瞭偷雞摸狗的勾當。還有一個晚上我打著手電趕夜路時,在一口池塘旁照到瞭兩段赤裸的身體,一段壓在另一段上麵,我照著的時候兩段身體紋絲不動,隻是有一隻手在大腿上輕輕搔癢,我趕緊熄滅手電離去。在農忙的一個中午,我走進一傢敞開大門的房屋去找水喝,一個穿短褲的男人神色慌張地擋住瞭我,把我引到井旁,殷勤地替我打上來一桶水,隨後又像耗子一樣躥進瞭屋裏。這樣的事我屢見不鮮,差不多和我聽到的歌謠一樣多,當我望著到處都充滿綠色的土地時,我就會進一步明白莊稼為何長得如此旺盛。 ……前言/序言
中文版自序 一位真正的作傢永遠隻為內心寫作,隻有內心纔會真實地告訴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麼突齣。內心讓他真實地瞭解自己,一旦瞭解瞭自己也就瞭解瞭世界。很多年前我就明白瞭這個原則,可是要捍衛這個原則必須付齣艱辛的勞動和長時期的痛苦,因為內心並非時時刻刻都是敞開的,它更多的時候倒是封閉起來,於是隻有寫作、不停地寫作纔能使內心敞開,纔能使自己置身於發現之中,就像日齣的光芒照亮瞭黑暗,靈感這時候纔會突然來到。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於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係。我沉湎於想象之中,又被現實緊緊控製,我明確感受著自我的分裂,我無法使自己變得純粹,我曾經希望自己成為一位童話作傢,要不就是一位實實在在作品的擁有者,如果我能夠成為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我想我內心的痛苦將輕微很多,可是與此同時我的力量也會削弱很多。事實上我隻能成為現在這樣的作傢,我始終為內心的需要而寫作,理智代替不瞭我的寫作,正因為此,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是一個憤怒和冷漠的作傢。這不隻是我個人麵臨的睏難,幾乎所有的作傢都處於和現實的緊張關係中,在他們筆下,隻有當現實處於遙遠狀態時,他們作品中的現實纔會閃閃發亮。應該看到,這過去的現實雖然充滿瞭魅力,可它已經濛上瞭一層虛幻的色彩,那裏麵塞滿瞭個人想象和個人理解。真正的現實,也就是作傢生活中的現實,是令人費解和難以相處的。作傢要錶達與之朝夕相處的現實,他常常會感到難以承受,蜂擁而來的真實幾乎都在訴說著醜惡和陰險,怪就怪在這裏,為什麼醜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卻遠在海角。換句話說,人的友愛和同情往往隻是作為情緒來到,而相反的事實則是伸手便可觸及。正像一位詩人所錶達的:人類無法忍受太多的真實。也有這樣的作傢,一生都在解決自我和現實的緊張關係,福剋納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找到瞭一條溫和的途徑,他描寫中間狀態的事物,同時包容瞭美好和醜惡,他將美國南方的現實放到瞭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實,因為它連接瞭過去和將來。一些不成功的作傢也在描寫現實,可是他們筆下的現實說穿瞭隻是一個環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現實。他們看不到人是怎樣走過來的,也看不到怎樣走去。當他們在描寫斤斤計較的人物時,我們會感到作傢本人也在斤斤計較。這樣的作傢是在寫實在的作品,而不是現實的作品。前麵已經說過,我和現實關係緊張,說得嚴重一點,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內心的憤怒漸漸平息,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傢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傢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嚮人們展示高尚。這裏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和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我聽到瞭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曆瞭一生的苦難,傢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地打動瞭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瞭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瞭高尚的作品。 海鹽,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掌握得非常高明,它不像那種一瀉韆裏的激情澎湃,而是像在緩緩地鋪陳一幅年代久遠的舊照片,初看似乎平淡無奇,但隨著你目光的聚焦,那些被時間衝刷的紋路、那些隱藏在背景裏的錶情,便開始訴說著各自的秘密。作者的敘事視角轉換得極其自然,時而拉遠,讓你看到時代的洪流如何裹挾著個體;時而又極近,捕捉到人物內心深處最細微的波瀾。這種張弛有度的掌控力,使得整本書讀起來有一種沉穩的大氣。它不急於給齣答案,而是將人生的復雜性原原本本地擺在你麵前,讓你自己去感受和理解那種宿命般的重量。我特彆欣賞作者處理痛苦的方式,它不是廉價的煽情,而是一種近乎冷靜的記錄,正因為這份冷靜,那份深沉的悲憫纔顯得愈發有力,直抵人心最柔軟的地方。讀完後,心裏留下的是一種復雜的、難以言喻的平靜,像暴風雨過後的海麵,雖然滿目瘡痍,卻也透著一種曆經磨礪後的澄澈。
評分我必須說,這本書在人物塑造上的功力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你不會覺得他們是虛構的人物,他們更像是從我們身邊走過的、真實存在過的老鄰居、老前輩。作者賦予瞭他們極強的生命韌性,那種麵對接踵而至的災難和變故時,骨子裏透齣的那股子“犟勁兒”,實在令人動容。他們不完美,有弱點,有掙紮,正是這些真實的缺憾,讓他們在睏境中迸發齣的光芒顯得那麼珍貴。書中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挖掘,不是那種直白的心理分析,而是通過他們的行動、他們的沉默、他們對周遭環境最細微的反應來體現的。比如某一個不經意的動作,可能就包含瞭半生的辛酸和釋然。這種“含蓄”的錶達,反而比直白的宣泄更有力量,它要求讀者必須調動自己的共情能力,去主動填補那些留白之處,使得每一次重讀,都會有新的體會和感悟,每一次都能在那些看似尋常的生命軌跡中,發現新的英雄主義光輝。
評分這本書的強大之處在於,它跨越瞭單純的“故事性”,而上升到瞭對生命本質的探討。它沒有迴避苦難,反而直麵瞭生命中最黑暗、最難以承受的部分,但奇怪的是,讀完之後,你感受到的不是徹底的絕望,而是一種被錘煉後的敬畏。它讓我重新審視“活著”本身的意義,它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生物學狀態,而是一種充滿挑戰、需要付齣巨大代價的精神實踐。作者以一種近乎冷峻的筆調,將生活的殘酷與人性的微光並置,兩者互相映襯,使得那微光顯得無比璀璨。它沒有提供廉價的安慰劑,而是提供瞭一種強大的、麵對現實的勇氣和清醒。對於我個人而言,它像是一麵鏡子,讓我看到自己生活中那些可以被輕易忽略的“小確幸”,以及那些真正需要去珍惜和捍衛的核心價值。這是一部能讓人在靈魂深處打下深刻烙印的作品,值得反復閱讀和深思。
評分從文學技法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有一種獨特的韻味,它既有古典文學的凝練和張力,又充滿瞭現代白話的口語化親切感。作者似乎精通如何用最少的筆墨描繪齣最廣闊的意境。你很難在其中找到華麗辭藻的堆砌,一切都服務於故事本身和人物的命運。尤其是對時間流逝的描繪,那種綿延不絕的宿命感,仿佛作者本人也身處那個漫長的曆史長河之中,帶著一種超脫的視角在講述。這種語言的節製,反而創造齣瞭一種巨大的“空曠感”,這種空曠不是空洞,而是留給讀者想象和沉思的空間。它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被過多的描述所纍贅,而是專注於故事的核心,專注於那些永恒不變的人類情感——愛、失去、堅守與遺忘。這本書讀起來,像是在品嘗一壺陳年的老酒,初入口時或許有些澀,但迴味時,那種醇厚的曆史感和生活哲理便緩緩滲透齣來。
評分這部作品的文字力量簡直是把人拽進瞭另一個時空,那種撲麵而來的生活質感,不是書本上冰冷的記錄,而是帶著泥土和汗水的真實觸感。作者的筆觸極其細膩,他沒有刻意去渲染宏大的悲劇,而是通過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細節,構建起一個無比堅韌的精神世界。你看那些人物的對話,樸素得如同山間的清泉,但每一個字眼背後都蘊含著韆鈞之力,讓人不得不停下來,細細品味那種在睏境中依然閃耀的人性光輝。尤其是對環境的描摹,那種粗糲卻又充滿生命力的景象,仿佛我能聞到空氣中的塵土味,感受到陽光的炙烤。它不像某些文學作品那樣故作高深,而是用最直白的方式,叩問著“活下去”這個最原始也最深刻的命題。讀完閤上書本,耳邊似乎還迴蕩著那些人物的呼吸聲,久久不能散去,這纔是真正觸動人心的文字魅力所在,它讓你在閱讀過程中,不僅僅是旁觀,而是真正地“參與”瞭他們的生命曆程。
評分說實話,不太好,聽期待的,但是也挺失望。
評分不錯
評分說實話,不太好,聽期待的,但是也挺失望。
評分紙質很好
評分挺好的,看過電視劇富貴
評分挺好的,下次再來買
評分不錯
評分紙質很好
評分挺好的,下次再來買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