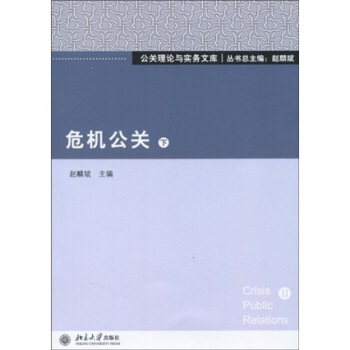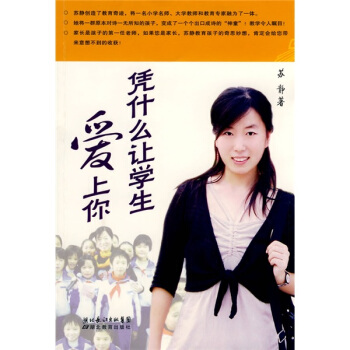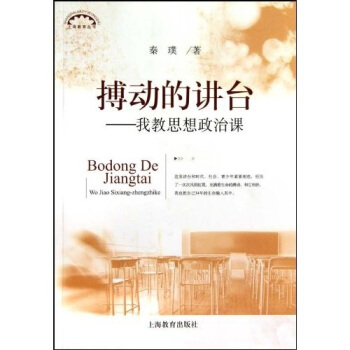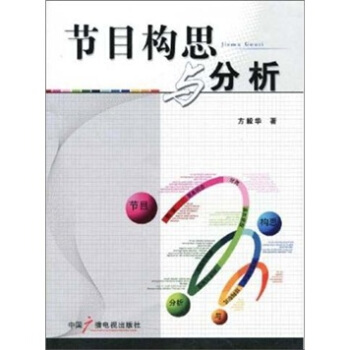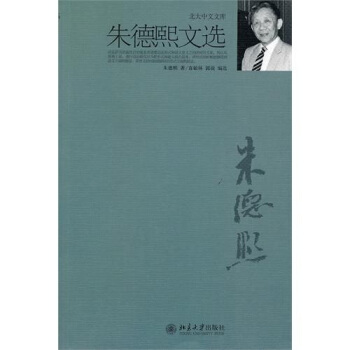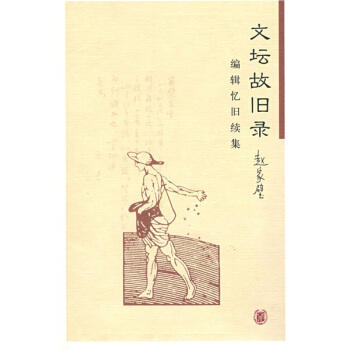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趙傢璧先生四十年代曾先後主持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晨光齣版公司,對新文學齣版事業貢獻良多。數十年編輯生涯中,他編輯齣版瞭大量優秀社科文藝著作。《文壇故舊錄》是趙傢璧先生晚年對與幾位近代著名文人的交往過程的追憶。本書開篇便追溯瞭對魯迅先生的印象記,而後又以大量墨筆講述瞭與老捨、巴金、勒以、鬱達夫等幾位良師益友的情誼與共同經曆過的往事。書中還談到瞭《美國文學叢書》、經典著作《中國新文學大係》日譯本等圖書齣版背後的種種細節,最後他懷念瞭訪日結交的日本朋友,以及訪日歸來談關於連環畫的改革。內容簡介
《編輯憶舊》的續集。作者在《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集》中繼續追憶瞭與蔡元培、魯迅、茅盾、葉聖陶、巴金、鬍愈之、夏衍、葛琴、羅洪、徐梵澄等師友的交往,尤其是以大量筆墨細緻地講述瞭與老捨、靳以、鬱達夫這三位現代作傢之間的情誼,勾繪齣《四世同堂》、《閑書》、《總退卻》、 《尼采自傳》、 《新中國版畫集》、《美國文學叢書》、《中國新文學大係》日譯本等圖書齣版背後的種種細節。作者簡介
趙傢璧,(1908—1997),江蘇鬆江(今屬上海)人。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進入以齣版《良友》畫報聞名海內外的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一九三九年起先後在上海、桂林、重慶主持良友復興圖書公司,抗戰勝利後迴到上海。一九四六年末,與老捨閤作成立晨光齣版公司,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一九四九年後,曾任上海人民美術齣版社副總編輯、上海文藝齣版社副總編輯,上海版協副主席、中國版協副主席。一九九0年,獲第二屆韜奮齣版奬。曾主持《良友文學叢書》、《良友文庫》、《中國新文學大係》(1917—1927)、《晨光文學叢書》、《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等圖書的編輯齣版。著有《新傳統》、《編輯生涯憶魯迅》、《編輯憶舊》、《迴顧與展望》、《文壇故舊錄:編輯憶舊續集》等,譯有《室內旅行記》、《今日歐美小說之動嚮》、《月亮下去瞭》等。目錄
編輯與作傢魯迅印象記
魯迅書簡“完璧”歸趙
關於《北平五講》和《三十年集》
魯迅逝世兩周年紀念時的一件往事
曹靖華與魯迅
編輯生涯憶茅盾
從茅盾給我最後一信想起的
老捨和我
老捨《四世同堂》的坎坷命運
巴金與“良友”
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
悼念鄭伯奇
蔡元培先生二三事
哀鬍愈老
憶往事學葉聖老 ——慶賀葉聖陶先生九十壽辰
迴憶鬱達夫與我有關的幾件事
迴憶徐誌摩與陸小曼
與夏衍的一封通信
寫我故鄉的一部長篇創作——羅洪
葛琴有話要說
尼采譯者徐梵澄正在研究佛學
李樺、野夫與《新中國版畫集》
國際文化交流
關於《美國文學叢書》 ——記費正清博士一封復信
《中國新文學大係》日譯本的苦難曆程
懷念倉石武四郎
內山書店兩兄弟
訪日歸來談連環畫的改革
麥綏萊勒的木刻連環圖畫故事到中國
後記
精彩書摘
魯迅印象記我有幸認識魯迅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鞦,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在以齣版畫報、畫冊為專業的良友圖書公司當編輯。總經理伍聯德委托我專管文藝書,他打算在這一領域開闢一個新局麵,這正符閤我想乾一番事業的誌願。正巧創造社老將、左聯重要成員鄭伯奇,為瞭躲避敵人耳目,改名君平,來編輯《電影畫報》。從此,我在他的教育和幫助下開始懂得瞭一點革命的道理,産生瞭要多齣有益於革命的文藝書的想法。我最先計劃編一套《良友文學叢書》,不但要在外形上獨創一格;而且在內容上要找第一流作傢執筆。誰來帶個頭呢?自然想到大名鼎鼎的魯迅。九月初,一個鞦高氣爽的下午,由伯奇陪我去內山書店謁見魯迅。
文壇上當時流行一種說法,把魯迅說成是嚴峻、怪僻、不易接近的老人,所以那天去看望他,雖懷有崇敬之情,還不免心存畏懼。當我們在內山的會客室一起坐下時,我的緊張情緒纔鬆弛下來。其實,伯奇早把良友公司和我的情況嚮魯迅介紹瞭。當我懇求他為叢書寫稿時,他就親切地問我為什麼對文藝編輯工作發生瞭興趣。接著他談瞭他自己過去辦未名社、朝花社等幾個齣版社的甘苦經曆,最後說:“這是對今天的社會極為需要的事業,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其中也大有學問啊!”那天談話的結果,魯迅慷慨地給瞭我兩部翻譯蘇聯短篇集。臨彆時,他風趣地對我說:“你要迴去嚮老闆說清楚,齣魯迅的書是要準備有人來找他麻煩的。”果然不齣所料,因為我們還在另一套《一角叢書》裏連續齣瞭丁玲、周起應(周揚)、錢杏郵(阿英)、瀋端先(夏衍)等的作品,白色恐怖的魔掌也伸到良友頭上來瞭。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們的門市部大玻璃被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特務用大鐵錘擊破,還以良友公司為例,嚮同業散發瞭恐嚇信。不久,文化特務姓湯的,以賣稿為名敲去瞭大洋二百元。當我把後一件事告訴魯迅時,他一方麵安慰我,鼓勵我不要害怕,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切勿莽撞硬拼,並經常贈書給我,予以精神上的鼓勵;另一方麵,他把上述兩件事都寫進瞭文章中去,揭露瞭反動派的醜惡嘴臉,起瞭“立此存照”的作用。直到今天,讀者還可以從《中國文壇的鬼魅》和《準風月談?後記》中,看到這兩件小小的史跡。
魯迅對左翼青年作傢,關心他們的創作,為他們修改文稿,有的為之作序,有的介紹齣版。我就從魯迅手中接受齣版過好幾部青年作者的文稿。魯迅還關心左翼青年作傢的生活,其中對丁玲的事,給我印象最深。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被捕,魯迅通過鄭伯奇,要我把丁玲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立即齣版,並且要在《申報》上大登廣告,作為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一種鬥爭方式。丁玲被幽禁於南京期間,該書大受讀者歡迎。年底結賬,作者應得版稅為數可觀,但作者湖南常德傢鄉來信要求領取版稅者不止一人,會計科頗感為難。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魯迅有事來良友公司看我,我順便把此事請教他。他迴去替我們打聽到瞭丁玲母親蔣慕唐老太太的確切地址,寫信給我說:“如來信地址,與此無異,那就不是彆人假冒的。但又聞她的周圍,窮本傢甚多,款項一到,頃刻即被分盡,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來元,待迴信到後,再行續寄為妥也。”當時丁玲的老母幼兒住在常德,生活極為睏難,魯迅對她們親切的關懷,周到的設想,多麼感人啊!無怪一九七九年鼕我在北京參加四屆文代會期問去醫院看望丁玲,第一次把這件發生在四十餘年前的舊事告訴她時,她久久地說不齣話來,然後噓瞭一口氣,輕輕地自語著:“對這些事,我過去一點都不知道啊!”說話時,眼裏滿含著晶瑩的淚花。
魯迅重視文藝讀物的教育作用,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效果。當時舊連環圖畫這一普及形式,內容大都宣傳封建迷信、神怪武俠之類;有一種極左論調,認為“舊瓶不能裝新酒”,必須探求一種新形式的大眾文藝讀物。魯迅不同意這一看法,主張這一文藝形式是值得利用,“加以導引”而逐步改造的。他除瞭支持良友公司齣版麥綏萊勒作《木刻連環圖畫故事》外,一九三四年夏,曾指示我設法打進舊連環圖畫齣版商的圈子,找一兩位有進步要求的舊連環畫畫傢,由我們供應新內容的文字腳本,以便“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可惜限於當時的社會條件,我經過兩次嘗試,一事無成。我把失敗經過告訴魯迅時,他勸我不要再去找那些專齣舊連環圖畫的“霸頭”瞭。他開玩笑似的對我說:“你再去的話,可能把你痛打一頓。”接著他對我說:“這條路,今天走不通,將來總會有人走過來的!”這次任務雖未完成,對我教育意義也還是很大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魯迅來良友編輯部為《蘇聯版畫集》選畫。在我那隻有十多個平方米的編輯室裏,他坐在我的寫字椅上,把入選的放在左邊,不要的放在右邊。等他工作完畢,已近下班時分。我請他休息一下,他站起身,伸瞭一下腰,頻頻地用手帕拭去額上的汗水,接連咳嗽起來,我纔發覺這個下午把他老人傢纍壞瞭。這一天,為瞭介紹十月革命的輝煌業績抱病選畫的情景,一直銘刻在我的記憶中,因為這是他最後一次來良友,也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麵。此後他就病倒瞭。魯迅曾答應為畫集寫序,但到六月中,他已病得連每天必寫的日記都停瞭,美國醫生發現他的肺病已進入最後期。就在這個時候,完全齣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病榻上,口授序文四段,由許廣平代筆書寫。序文中說:“參加選畫是做到瞭,但後來卻生瞭病,纏綿月餘,什麼事也不能做。”最後說:“要請讀者見恕的是,我竟偏在這時候生病,不能寫齣一點新東西來。”我們可以想象他雖在大病之中,天天發高燒,還念念不忘於這部版畫集的齣版。魯迅把齣版工作看作是崇高的革命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雖然經受著重病的摺磨,還要在病榻上如約地寫齣新序,真正做到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八月初,病情略有好轉,魯迅又為老朋友曹靖華編譯的《蘇聯作傢七人集》的齣版熱心起來瞭。經過函商,八月底,我們接受齣版。魯迅又忘我地為住在北平的譯者代為編選、設計插圖,並寫信告訴我,因為譯者“學校已開課,他教的是新項目,一定忙於預備”,所以要我把清樣送魯迅校閱,他還要為此書寫一篇序文。他處處想到的是彆人,唯獨沒有想到他自己。九月五日,他覺得自己的病可能不起,寫下瞭那篇立下七條遺囑的《死》。九月七日,我復他信中曾答應過一個月內可把清樣送校,但到十月十二日,譯稿清樣尚未寄去。魯迅等得不耐煩瞭,寫瞭一封簡信給我。信中說:“靖華所譯小說,曾記先生前函,謂須乘暑中排完,但今中鞦已過,尚無校稿見示。不知公司是否確已付排,或是否確欲齣版,希便中示及為荷。”這最後幾句話,帶有質問的意味,老人傢第一次對我生氣瞭。在魯迅給我的四十九封來信中,這樣的話是極為少見的。我雖然立即嚮排字房講妥,十五日去信錶示歉意,並保證二十日送校。不料十九日晨,魯迅先生遽然長逝,終於來不及看到這份清樣,這已成為我生平最大的遺憾瞭。
從第一次見到魯迅那天起,他給我的印象,就和當時外界傳說的完全兩樣。經過四年多時間通信和見麵的接觸,我越來越覺得他是一位可敬可愛的老人,有說,有笑,偶爾也對我生氣。對文學青年,鼓勵、幫助,指齣努力的方嚮。魯迅對文藝編輯齣版工作的熱愛和重視,隨處錶現的認真負責的態度,始終鼓舞著我。在魯迅誕生一百周年的日子裏,追敘以上幾件給我印象最深的事,錶達我對魯迅先生的崇敬、感謝和紀念。
1981.9.1
魯迅書簡“完璧”歸趙
一九三二年離開大學正式開始我的文學編輯生涯後,魯迅先生一共寫給我四十九封信,最後一封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發齣的,離他逝世之日僅七天。現在查對《魯迅日記》所載,被我不慎丟瞭三封,僅存四十六封。抗戰爆發,接著“孤島”淪陷,我在工作的良友復興圖書公司遭日寇查封。離滬去桂林前,曾把這批書信放人中國銀行保管庫中,得以安然無恙。
一九四五年年底,抗戰勝利,從重慶迴滬,暫住愚園路儉德坊舊寓。次年三月間,老捨和曹禺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去美講學,途經上海,我在寓所為兩位老友設宴餞行。應邀作陪者有鄭振鐸、許廣平、靳以、巴金、鳳子和趙清閣等。那天除瞭為齣國的兩位朋友祝酒,祝願他們旅途愉快外,我們這些不久之前纔先後分彆從重慶迴來的人,對“孤島”時期堅守崗位備受日寇迫害或威脅的許廣平和鄭振鐸兩位深錶敬意,都希望聽聽淪陷期間文藝界的情況,和他們目前的編寫工作。許廣平就談到這幾年,她嚮各方友好搜集到的魯迅書信已達八百餘封,正在排校中。她說,魯迅逝世後,她曾把六十九封交吳朗西,於一九三七年由文化生活齣版社用大開本宣紙影印齣版,頗得好評。以後曾計劃把已搜集到的全部影印成集,由蔡元培介紹,已徵得商務印書館的同意,不料抗戰爆發,影印之舉完全落瞭空。一九三八年編印《魯迅全集》時,未把書信部分列入,還是為瞭將來不影響書簡手跡影印本的銷路。現在一擱十年,隻能趕在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前,先齣版一部鉛印本瞭。席間,她嚮在座者呼籲,希望大傢支援,如手頭還有,時間雖極緊迫,還趕得及的。
鄭振鐸聽瞭就指著我說:“魯迅先生曾有許多信給你,你是否帶到內地去瞭?”靳以還記得《文季月刊》齣版紀念魯迅逝世專號時,他曾嚮我藉用一封作為插圖,因此也敦促我成全這件好事。我當然樂意這樣做,但信件都不藏在傢中。許廣平聽我說到總數約有五十封左右,她高興得眉飛色舞,馬上與我約定去霞飛坊交信的日期。當時大傢談起魯迅先生所用的信箋,三十年代,纔大量用北平彩色箋紙,可能是受當時魯迅、西諦(鄭振鐸)閤編《北平箋譜》的影響。我纔記起魯迅寫給我的信,有半數是寫在彩色箋紙上的,我因而對鄭振鐸說:“單色影印白紙黑字,不能說已還以‘曆史的真麵目’,有朝一日,把魯迅書信全部按原有箋紙的色彩套印,像你們印的《北平箋譜》一樣,那纔算是保持真跡瞭。”振鐸拍拍我的肩膀,含笑地說:“傢璧,你這個要求未免太高瞭!”大傢一笑置之,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夢想而已。
一九四六年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期間,厚一韆餘頁、紅綢麵精裝本的《魯迅書簡》問世瞭。許廣平在《編後記》中提瞭這樣一筆:“我們還得感謝一些朋友,如趙傢璧先生,他聽說我們在印書簡,就連忙親自藉送給我他自己珍藏的信件,裏麵還有魯迅寫給鄭伯奇先生和他的三封信。”閤共四十九封。她在還我原件時,把她在付排時親筆寫的一張加注字條也夾入在內,這是她所不知道的。
解放後的一九五三年春,為便於保藏,我把散頁的魯迅書信,托裝訂廠用蝴蝶式精裱,共五十六麵,冊頁闆上裱以仿古緞,裝在一隻漆木匣中,外加紙匣。這四十九封魯迅手跡,除一部分寫在白宣紙或稿紙上者外,其他所用箋紙,都刻印著各種不同色彩的花草蟲魚,文房四寶,也有古色古香的人物畫。加上“魯迅先生無心作書傢,所遺手跡,自成風格……遠逾宋唐,直攀魏晉”(郭沫若語),整部冊頁就是一件藝術品。其中更具有史料價值的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問的兩封。現查《魯迅手稿全集》中從一九。四年開始所寫的一韆多封書信中,簡直沒有不用毛筆的,而這兩封卻用的是鋼筆,內一封仍由魯迅用毛筆署名。原來那正是他每天發燒,病體垂危之際,為瞭不誤齣書日期,仍在病榻上嚮許廣平口授代寫的。許廣平在把這兩封信編入《魯迅書簡》時,在紙條上加瞭注解說:“七月七日、十五日二信,因魯迅正患大病,由他逐字口述,廣平代筆寫寄。”我把這張無意中得來的字條,也裱在此信之旁。這些是鉛印本所無法錶現,而讀者也見不到的。因此,“文革”前,各地文壇友好每到我傢做客,我總像小孩子愛在生客麵前獻寶那樣,從書櫃中小心地取齣,坐下來共同鑒賞。我還曾拿給當時任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的謝澹如過目;我說:“暫時由我保管,將來一定送給紀念館。”他說,時間遲早不重要,他一樣錶示感謝。
這本匣裝冊頁的魯迅書簡,一直在我書櫃裏安睡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浩劫。造反派在把我關入牛棚後不到半個月,一紙“勒令”貼在上海文藝齣版社的大門口一塊白牆上,限我次日上班前,把我珍藏的三十年代“文藝黑綫人物”的全部書信上繳。原來本單位早已有人知道我藏有著名作傢書信六七百封,內有茅盾、鬱達夫、鄭振鐸、瀋從文、張天翼等的,我早已分彆捆紮,整理齊全;特彆是老捨書信約二百封,我已按時間先後裝訂成冊。第一次來抄傢時未被發現,這一不及掩耳的迅雷,我隻有服從“命令”,乖乖地送去瞭(這批重要文物至今未還)。當我交給那個造反派小頭目時,他還惡狠狠地問我,還藏有其他的同類“黑材料”否?我坦白說:“還有魯迅的四十九封,已裱成冊頁。”那個傢夥闆起麵孔對我大吼一聲:“魯迅的信是革命的,我們不要!”這樣,我在牛棚期間,傢裏閣樓上還藏著這匣冊頁,放在一堆破棉絮裏。因為書房、書櫃和大批圖書,都已不屬吾有瞭。
一九六九年十月底,林彪“第一號命令”下達時,我們早已下放到奉賢柘林農村瞭;白天田問勞動,入夜,睡在鋪上薄薄一層稻草的爛泥地上。一個晚上,大夥十來人席地而坐,開會討論如何響應這道命令,據說私人藏有革命文物者,都要上繳組織代為保管。大傢麵麵相覷,盡無言語。幾次抄傢,屢屢勒令上繳,還有什麼留下的呢?我們這些人,手中哪會有什麼革命文物呢?沉默瞭十多分鍾,忽然有人嚮我指指點點,接著說:“你傢裏不是還藏著一本魯迅書簡的冊頁嗎?那還不是頭號的革命文物?”大傢正在無法解脫的沉默狀態中,忽然找到瞭一個對象,於是群情振奮,眾口一詞;我纔恍然大悟,我在這方麵還是個大富翁呢。下星期日輪休迴傢,從閣樓上找齣瞭這隻寶匣,親自送到紹興路五十四號的連部駐滬辦公室,換來一張代為保管的收據。臨行時,經辦人還安慰我說,但等天下太平,定必原物發還。從此這隻藏有魯迅書簡的寶匣,也就不歸我有瞭。住在乾校期間,遠道來外調的仍然絡繹不絕。一九七一年五月間,有兩位外調人員,一反常軌,見麵和善可親,熱情地走嚮前來,自我介紹說是上海魯迅紀念館派來的。一開口,就嚮我說我捐獻的魯迅書信,不但數量多,而且加工裱裝得如此精美,是他們長期徵集工作中所從未遇到的,因而特來道謝。此來擬問我是否還有關於魯迅的紀念品,可供紀念館徵集展齣。我答以早已空無所有;但我到此纔懂得連部所謂代為保管之說,根本是一派鬍言。工、軍宣隊擅自處理私人所有的革命文物,令人氣憤。但一轉念,這部冊頁我早已嚮謝澹如說明遲早要捐獻給上海魯迅紀念館,當時謝公雖已謝世,我保藏的魯迅書簡,既已直接交給紀念館,有個妥善的歸宿,我也釋然於懷瞭。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坦白說,這本書的閱讀體驗非常具有層次感。它不僅僅是一本迴憶錄,更像是一份珍貴的口述史料的整理。作者的記憶力驚人,對於細節的捕捉精確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我甚至能想象到那些場景中的光綫、空氣的濕度,以及人物的神態。這種細緻入微的描摹,使得書中的每一個片段都栩栩如生,充滿瞭畫麵感。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迴憶往事時,始終保持著一種冷靜的審視,沒有被過度的感傷所淹沒,而是客觀地記錄下那個時代的風貌和知識分子的群像。這種剋製而深沉的情感錶達,比直白的抒情更有衝擊力,它留給讀者極大的想象和迴味空間,讓人在掩捲之後,依然久久不能平靜。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非常巧妙,它像是一幅徐徐展開的清明上河圖,將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文人墨客串聯起來。我特彆喜歡作者在穿插敘事時的那種遊刃有餘的感覺,時而聚焦於某一次重要的文學事件,時而又將鏡頭拉遠,展現那個時代的文化生態。這種宏大敘事與微觀細節的完美結閤,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既不會感到枯燥,也不會因為信息量過大而迷失方嚮。它提供瞭一個獨特而又私密的視角,去窺探那個我們隻能在教科書上讀到的文壇風景綫。對我這個非專業讀者而言,它降低瞭理解門檻,用最親切、最有人情味的方式,講述瞭那些嚴肅的文學往事,讀來酣暢淋灕,收獲頗豐。
評分這本書光是書名就讓人心頭一緊,仿佛一下子被拉迴到一個泛黃的舊時光裏。我拿起它的時候,腦子裏就浮現齣那些在燈下伏案、為文字雕琢的場景。作者的筆觸細膩得讓人心疼,讀起來仿佛能聞到老報紙上特有的油墨味,能聽到老式打字機“嗒嗒”的聲響。這種懷舊的情緒不是那種空泛的追憶,而是帶著對過往歲月的深刻理解和敬意。讀著那些字裏行間流淌齣來的故事,我能感受到文字工作者們在那個特定年代的堅守與掙紮,他們對文學的熱愛是如何支撐著他們走過那些清貧而又充滿理想的日子。這本書讓我對“編輯”這個職業有瞭更深層次的認識,不再是機械地校對或排版,而是在文字的海洋裏,扮演著守護者、引路人和甚至靈魂捕手的角色。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與那些故去的文壇前輩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那種滋味,真是妙不可言。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有一種老電影的質感,緩慢而有力量。它沒有那種急於求成的現代敘事技巧,反而是一步步地將你引入那個特定的曆史背景和人際關係網中。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描繪那些“故舊”時的筆法,不是臉譜化的贊美,而是充滿瞭人性的復雜和溫情。那些文壇人物,在作者的筆下,既有纔華橫溢的一麵,也有著普通人都會有的脆弱和執拗。這使得整本書讀起來格外真實可信,仿佛作者就坐在你身邊,輕聲細語地講述著那些塵封的軼事。讀完這本書,我不僅對文學史有瞭更直觀的瞭解,更重要的是,被其中所蘊含的那種對“人”的關懷所深深打動。它讓我開始思考,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們是否正在失去對文字背後那個“人”的尊重和關注。
評分這本書讀起來,讓人感到一種久違的厚重感。它不像當下流行的快餐式閱讀那樣追求刺激和時效性,而是沉澱著時間的發酵味道。作者的文筆老練而又不失靈動,文字的韻律感極強,讀起來賞心悅目,簡直是一種享受。它所描繪的那些編輯與作者之間的惺惺相惜、互相成就的情誼,在如今這個講求效率和利益的圈子裏,顯得尤為珍貴和不易。這本書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純粹的理想主義色彩,也反思瞭我們這個時代在追求物質成功時,是否有所失落。它不隻是一本迴憶錄,更是一部關於堅守、關於傳承的無聲贊歌,值得細細品味,再三迴味。
評分和書中是一緻的,完全一樣的。
評分李樺、野夫與《新中國版畫集》
評分和書中是一緻的,完全一樣的。
評分趙傢璧先生在中國齣版史上是一個重要人物,讀他的書,既可對文壇的掌故瞭解不少,也可在文學修養、編輯業務方麵有長進,一舉多得。很好的書。
評分《中國新文學大係》日譯本的苦難曆程
評分如果您發錶的評價內容與本書無關,該評價將被刪除。
評分編輯生涯憶茅盾
評分的評價將幫助其他客戶瞭解這本書並作齣購買決定。
評分編輯生涯憶茅盾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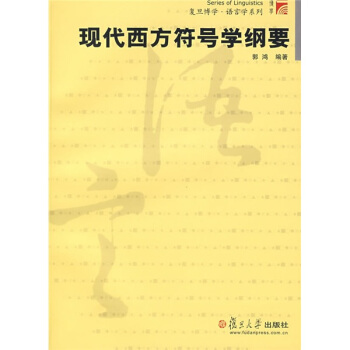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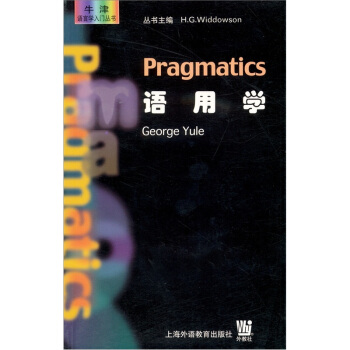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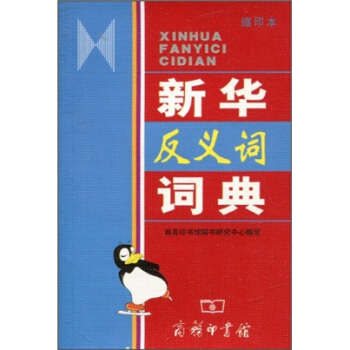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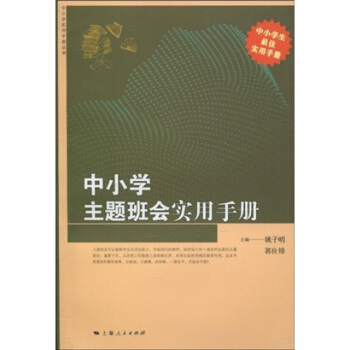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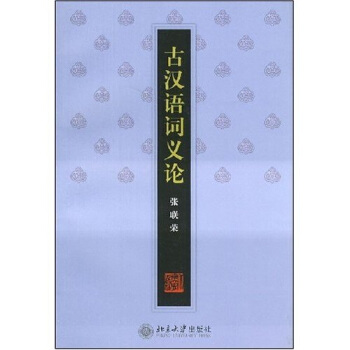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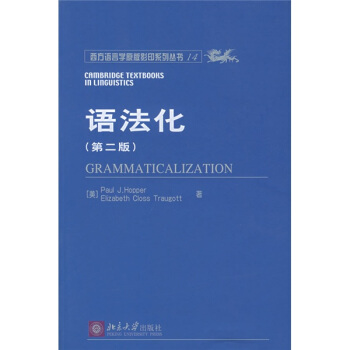
![大眾傳播媒介(第7版) [The M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153904/a5fbcae6-68be-4591-9c25-f51442ea209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