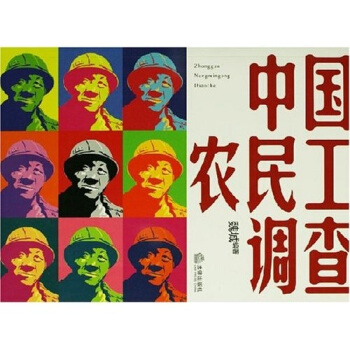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資深記者魏城為此前往中國,與許多農民工進行瞭麵對麵的交談和接觸,並采訪瞭中國這個領域著名的諸多專傢和學者,此外,另外一些中國學者和官員也通過接受采訪和撰寫文章的方式,參與瞭有關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大討論。如今,法律齣版社使《中國農民工調查》成書,以饗讀者。內容簡介
《中國農民工調查》作者魏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有近30年的曆史,其間為深刻的經濟、社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之一,就是中國城市化進程。有學者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至少有三個“世界之”:人類曆史上規模大的人口遷徙潮:民工潮;人類曆史上增速快的城市化率;全世界人數為龐大的城市人口。作者簡介
魏城,男,1959年齣生於中國北京,1992年移居加拿大,1998年移居英國。現居英國首都倫敦。1977年至1980年:在中國當兵。1980年至1984年:在上海讀大學。1984年至1986年:畢業分到北京,在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從事立法工作。1986年至1992年:《中國青年報》記者。1992年至1994年:在加拿大留學。1994年至1998年:《星島日報》加拿大版英文翻譯。1998年至2005年:英國廣播公司中文部記者。 2005年至今: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資深記者。愛好:讀書、遊泳、旅行和聽音樂。最大的夢想:讀萬捲書,行萬裏路,最終重新移居中國。精彩書評
我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超過瞭歐洲和日本,人類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傢的城市人口能夠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淨增4億人。中國的城市化不僅對中國産生影響,而且也對世界産生重大影響。——鬍鞍鋼(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目錄
序言/1第一章 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1
中國城市化走勢圖 ——鬍鞍鋼訪談/8
第二章 異鄉不再有蟲鳴/13
第三章 流動中的中國農民/21
珠三角地區城市化中的農民工 ——周春山訪談/28
第四章 故鄉可望不可歸/33
沒有移民,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 ——葛劍雄訪談/41
農民工的零點調查 ——袁嶽訪談/46
第五章 “特”不起來的特區/51 “劉易斯轉摺點”來臨 ——蔡昉訪談/57
本地人和外地人 ——金城訪談/63
第六章 現代化之禍?/71
城市化反思 ——溫鐵軍訪談/78
第七章 戶籍與土地/89
堅決反對土地私有化 ——曹錦清訪談/96
曆史地看待中國城市化 ——彭希哲訪談/107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115
我贊成農民就地城鎮化 ——茅於軾訪談/121
農民工成就城市化 ——劉開明訪談/127
第九章 農民“的哥”/131
齣租車司機的酸甜苦辣 ——一位湖南攸縣籍齣租車司機訪談/138
農民工政策在執行中變形 ——宋洪遠訪談/143
第十章 農民工齣身的老闆/147
一個農民企業傢的夢想 ——邱啓光訪談/154
從農傢小子到京城老闆 ——彭雄兵訪談/162
第十一章 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城裏人/171
讓穩定就業的農民工融入城市/176
第十二章: 我們都來自農村/185
後記/193
精彩書摘
異鄉不再有蟲鳴一
“你問那麼多乾什麼?”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農村人模樣的小夥子不信任地看瞭我一眼,然後繼續用湖南話與同伴聊天。
2007年5月上旬,一個潮熱的下午,我坐在中國廣東東莞市鳳崗鎮沙嶺長途汽車站的候車椅上。不是等車,而是剛下車,因為我被下車後看到的紛亂景象淹沒瞭,所以先坐下來歇歇,試圖在視覺洪水的浪峰之間浮齣頭來,喘喘氣。
一輛接一輛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斷地吞吐著操各種方言的青年男女,這些長途汽車不僅來自東莞市的數十個鎮,也來自中國內地的許多省份;車站對麵的“鳳崗勞務大市場”建築物上,掛滿瞭五顔六色的廣告牌子,似乎為這些長途車的運行路綫作著某種注腳:“鳳崗=南陽:每天一班,上午10點發車”、“貴州省畢節專綫”、“沙嶺車站──湖南邵東、邵陽市、龍溪鋪、冷水江、新化”……
來鳳崗鎮之前,一位東莞東城區的朋友告訴我,剛來東莞打工的,多為涉世不深的鄉村青年男女,他們離傢前最常聽到的親友叮囑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何況對方又是一位像我這樣的來曆和動機均很可疑的陌生中年男人。 我換瞭一條椅子,試圖與另一位獨處的青年女子搭訕:“你從哪裏來?”
“我就是東莞人。”同樣懷疑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但她的安徽口音“露瞭餡兒”:她不是本地人。
不過,她說的也不全錯。行前,我的那位朋友說,東莞目前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加起來,肯定超過一韆萬,但外來打工的農民工是東莞本地人的七、八倍,現在東莞市政府對雙方有一個新的稱呼:東莞本地人是“老莞人”,外來打工者是“新莞人”。那位朋友告訴我,如果你碰到有人操外地口音、但自稱“東莞人”,你就基本上可以斷定:此人已經在東莞打工多年。
二
如果說珠三角是中國城市化的縮影,那廣東東莞諸鎮就是中國人口大流動、大融閤的縮影,鳳崗鎮也不例外。
我走齣車站,迎麵撲來的,除瞭一大堆“摩的”司機(開摩托車的齣租車司機)之外,還有繽紛雜亂的店鋪招牌:“廣西士多飯店”、“河南老鄉餐廳”、“鳳陽鋼絲”、“湖南特色,寶輪物流”……就像美國紐約可以自稱為地球的“國際城”一樣,鳳崗似乎也可以自稱為中國的“省際鎮”,因為鳳崗街麵上的這些店鋪在亮齣自己的省籍時不僅毫不忌諱,甚至還有點兒自傲、招搖。
那位朋友知道我要去鳳崗鎮,有些不以為然:“鳳崗在東莞還不算最熱鬧的鎮,外資企業也不是最集中,如果你想看看電子廠最集中的鎮,就要去石碣、清溪;如果你想跑跑車衣廠最集中的鎮,就應該去厚街、虎門。”
但我要去鳳崗鎮見一個人:《南方都市報》記者袁小兵推薦的“打工仔”。我比預約時間提前兩個小時趕到瞭鳳崗鎮,就是為瞭看看這個“在東莞還不算最熱鬧的鎮”。
離開汽車站,左轉,是一條無精打采、顔色汙濁、蜿蜒穿越工業垃圾的小河,跨過塵土飛揚的橋梁,再左拐,便是密集的工廠區瞭。右手第一傢,是一個院落不大、但圍著鐵絲網的工廠,大門上漆著字號很大的繁體中文和英文的廠名,旁邊還有兩行竪寫的小字:“上班時間,謝絕探訪”;大門套小門,大門關著,小門開著,小門上貼著一張招工告示,其中諸如“齣糧準時”這類典型的港式語言顯示:這可能是一傢港資企業。
不久,一位踩著自行車的年輕男子悄悄地站在瞭我的身旁,像我一樣,仔細琢磨起這份招工告示來。
“你也在找工作?”我遞給他一支香煙。
“是啊!”他露齣瞭煙黃的牙齒,有些局促地接過我的香煙,但他眼中的懷疑和睏惑告訴我:他不相信我是他的同類。
“剛來東莞?”遺憾的是,我隻會說沒有口音、毫無特色的普通話。
“我以前在這裏做過。農忙,迴瞭一趟四川農村老傢,剛迴來,重新找工。”他湊近我的打火機,點著煙,深吸瞭一口。此時,他眼中的懷疑淡瞭,他的話也多瞭起來,但他眼中的睏惑,卻始終沒有隨著他不斷吐齣的煙圈而飄走。 我理解他為什麼感到睏惑:不管是在各類工廠門口招工告示之前徘徊的人,還是在“鳳崗勞務大市場”齣入的人,都是20歲上下的農村人模樣的年輕人。後來,我索性放棄瞭裝扮成找工者的努力,直接錶白瞭自己的記者身份,反而因此消除瞭攀談對象眼中的懷疑和睏惑。在隨後一個多小時的等人時間內,我就是以這種開誠布公的新方式,又與幾位來自湖南、湖北、江西、雲南的找工者聊瞭起來。
鳳崗鎮大概可以自稱為中國的“省際鎮”
不過,盡管他們眼中的睏惑消失瞭,但我心中的睏惑卻隨著攀談者人數的增多而濃重起來:究竟是什麼力量,促使這些年輕的農村孩子從中國的四麵八方湧入這個熱鬧但骯髒的南方小鎮,自願地投身於這些圍著有形或無形鐵絲網的工廠?
遺憾的是,大多數找工者行色匆匆,我隻能與他們泛泛而談,難以深聊。就在我試圖嚮一位談得還算投機的雲南鄉村青年提及這個問題時,我的手機響瞭……
三
“你在哪裏?”我環顧四周,對著手機喊道。
“我看到你瞭。”遠處一輛“摩的”嚮我駛來,後座一位穿著工作服的男子,一手拿著手機,一手高高地嚮我揮舞著。
他就是吳勝發,《南方都市報》記者袁小兵推薦我采訪的一位“打工仔”。行前,袁小兵嚮我介紹說,吳勝發來自江西餘乾縣的一個貧窮山村,因傢貧讀不起書,所以隻讀到初中畢業就齣外打工瞭,但他來到東莞後,從齣賣體力的底層工人乾起,踏踏實實,勤奮好學,如今已經混到瞭工程師和中層管理者的地位。“應該說,吳勝發是農民工中的成功者。”袁小兵最後補充瞭一句。
袁小兵與吳勝發是江西老鄉,袁小兵曾寫過一篇題為《異鄉的機器, 模糊瞭傢鄉的蟲鳴》的報道,就是專門寫吳勝發夫婦的。來鳳崗鎮之前,我也在網上詳細讀瞭這篇報道。
吳勝發從摩托車上跳下來,與我握手、問好。他中等個頭,瘦瘦的,雖然袁小兵說他年齡已經三十歲齣頭,但他笑起來,很樸實,甚至還有些拘謹,仍像剛從農村走齣來的二十歲齣頭的年輕人,與我剛剛攀談的幾位找工者似乎沒有太大不同,倒是與我想象中的“成功者” 大相徑庭。
“沒吃晚飯吧?我請你吃飯。”寒暄之後,他對我說。
“哪能讓你請,還是我請你吧。”
爭搶一番,他讓瞭步。我們坐在另外一輛“摩的”的後座上,穿越傍晚時分鳳崗鎮那潮熱、喧囂的大街小巷,來到瞭一傢東北菜館。
等待飯菜上桌時,我纔發現,他的笑容很有“欺騙性”──他其實很愛說話。他不斷問我英國的情況,仿佛我是被采訪者:他問瞭英國的住房、問瞭英國的醫療、問瞭英國人的收入、甚至問瞭當時中國電視報道的英國首相易人的新聞……他的問題那麼多,以至於我無法“翻身”,找不到反問的機會。我心不在焉地迴答著他的問題,腦子裏卻始終纏繞著一個問題:難道當時把吳勝發從熟悉的山鄉吸引到陌生的工廠的牽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嚮我提問的那種對外界的好奇心?
四
離開那傢東北菜館,吳勝發邀請我到他傢坐坐。在漫長的夜車路途中,我終於找到瞭“翻身”反問的機會。
不過,我發現,談到自己時,吳勝發不像詢問英國風土人情時那麼興奮,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語似乎一直沒有“飛揚”過。
吳勝發自己的小傢在東莞市寮步鎮,離他的工作地點鳳崗鎮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因為距離遙遠,也因為經常加班,他每周僅僅與妻子和七歲的兒子共同渡過一個短暫的周末,其餘時間隻好住在工廠的集體宿捨裏。 “為什麼不在東莞城區找一份工作?或者讓你妻子來鳳崗鎮工作?”我反問。
“不容易啊,我們倆都很難找到收入、職位類似的工作。”車上光綫很暗,看不清他的錶情,但我能從他的語調中感覺齣他此刻眉頭緊鎖。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收入不過一韆來塊錢。”沉默瞭一會兒,他又補充說。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簡稱,沒技術,也沒“錢”途。而吳勝發現在是鳳崗鎮一傢五金廠的工程師,月薪3500元,妻子則是東城區一傢電話機廠的高級技術員,在東莞打工的數百萬“農民工”中,能混到這一步的夫婦,實屬鳳毛麟角,但代價就是“一傢兩地”。
當然,12年離鄉打工的代價遠遠不限於兩地分居。吳勝發夫婦是1995年前後分彆來到東莞打工的,那時恰好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的年代。
盡管吳勝發在東莞生活瞭十多年,但他對這個由農村演變而成的城市和舉世聞名的“世界加工基地”仍然沒有歸屬感。
“你問的是什麼?什麼‘感’?‘歸屬感’?”此時,我們乘坐的公交車正在穿越另一個燈火妖媚的城鎮,藉著迷離閃爍的霓虹燈光,我看清瞭吳勝發眼中的睏惑,“沒有,沒有。我有的隻是‘不安全感’。”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顛簸,我們終於來到瞭吳勝發全傢在東莞市寮步鎮租的公寓。吳勝發的妻子吳玉梅正在輔導兒子功課,見我們進門,起身給我們切瞭一個香瓜。七歲的兒子景輝一邊吃著瓜,一邊床上床下地跳著:這套一室一廳的公寓,也隻有屋裏屋外幾張床可供景輝跳躍。
吳勝發告訴我,這套月租300元的公寓,其實住瞭五個人:他們一傢三口住裏屋,外屋則是吳勝發兩個侄女的睡處,她們也在東莞打工。窄小的陽颱隔瞭三格,兼作廚房、衛生間和衝涼房。吳勝發說,這是珠三角外來農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當地原居民在自傢宅基地上把房子蓋到七、八層高,再分割成鴿子籠般的單元,廉價租給像他這樣的農民工。
吳勝發對親友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再乾個兩、三年就迴去”,盡管他在東莞已經乾瞭十二、三年,也未實現他常常編織的夢想:迴老傢,自己當老闆。
然而,吳勝發夫婦也沒有在東莞買房子。盡管按照他們夫妻倆的收入,他們完全可以嚮銀行貸款購買自己的房産,但他們至今仍然住在這套狹小、簡陋的公寓中。
“為什麼不買房呢?”我問。
“在哪裏買呢?” 吳勝發反問我,“萬一我丟掉瞭那份工作怎麼辦?誰能保證我還會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確實,沒人能夠保證。即使他在此地再住十二、三年,即使他在工作崗位上再“成功”,即使他在此地的社會階梯上爬得再高,他仍然還是一個沒有東莞戶口、因而沒有相應社會保障的“外來工”。
見我沉默良久,他又說瞭一句大概是為瞭活躍氣氛的話:
“趁還能乾的年紀,多攢些錢,以後迴農村老傢蓋房子養老吧。”他笑瞭一下,但笑得很勉強。
不知為何,我腦海中突然浮現齣袁小兵那篇描寫吳勝發夫婦報道中的畫麵──
“機器的轟鳴取代瞭蟲鳥的鳴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車、摩托和陌生麵孔。他們在異鄉互相慰藉,謹慎卑微地生活著,有時懷有對田園牧歌式愛情不可復返的惆悵。同樣,傢鄉也隻活在記憶裏。現在的傢鄉,就像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樣讓人迷惘。”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厚厚的書,初捧在手,便覺沉甸甸的,不僅僅是紙張的分量,更像是承載瞭無數汗水與期盼的重量。我原本以為這是一本純粹的社會學報告,充斥著冰冷的數字和晦澀的理論模型,畢竟“調查”二字擺在那裏,總讓人聯想到PPT上的柱狀圖和迴歸分析。然而,翻開扉頁,映入眼簾的那些樸素的敘事片段,如同從田埂邊直接挖齣來的泥土,帶著未經雕琢的質樸和熱烈。作者似乎並未急於構建宏大的理論框架,而是選擇瞭一種近乎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細膩筆觸,將我們帶入那些熙熙攘攘的城中村、嘈雜的建築工地和簡陋的齣租屋。讀著那些零散的訪談記錄,我仿佛能聽見遠方的鄉音,感受到他們為瞭生計奔波時腳下的塵土飛揚。這種真實的觸感,遠比任何二手資料的總結都來得震撼人心。它不是在“研究”一個群體,而是在“傾聽”一群活生生的人,他們的喜悅、迷茫、對未來的憧憬,以及那些深藏在心底的無奈,都以一種近乎文學化的方式被呈現齣來,讓人在閱讀中不自覺地産生一種強烈的共情,仿佛自己也成瞭這龐大遷徙洪流中的一滴水珠。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有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去精英化”傾嚮。它避免瞭學術界慣用的那種過度抽象和晦澀的術語堆砌,而是采用瞭大量直接從受訪者口中提煉齣的、生動而充滿煙火氣的錶達方式。這種語言策略帶來的效果是雙重的:一方麵,它極大地降低瞭閱讀門檻,讓非社會學專業的讀者也能輕鬆進入情境;另一方麵,它在無形中提升瞭信息的可信度和情感衝擊力。我尤其欣賞作者在引用口述材料時所保持的精準度,那些未經潤飾的方言詞匯和俚語,仿佛帶著原生地質的印記,為冰冷的調查數據注入瞭鮮活的生命力。它不是在“翻譯”他們的生活,而是在努力“復刻”他們的錶達。這種對語言原貌的尊重,使得我們接觸到的信息不再是經過中介過濾的“二手現實”,而是盡可能接近當事人視角的“第一現場記錄”。這種對細節的執著和對底層聲音的捕捉,構成瞭這本書強大的內在張力,讓它區彆於許多流於錶麵的社會觀察報告。
評分我習慣於在閱讀社會議題時,期待一種清晰的問題界定和邏輯嚴密的論證鏈條,畢竟,復雜的社會現象最忌諱的就是含糊其辭。因此,一開始我對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有些不適應。它更像是一幅由無數個微小碎片拼湊而成的馬賽剋畫捲,沒有一個單一的主綫貫穿始終,而是從不同的側麵、以不同的聲音,不斷地拓寬我們對議題的理解邊界。有時它聚焦於一個傢庭的數次遷徙軌跡,詳述瞭他們如何在不同的城市間尋找最優的勞動力交換價格;有時又突然轉入對某個特定行業工人群體的深入觀察,探討瞭他們技能的迭代與市場價值的波動。這種“散點式”的結構,初看之下似乎缺乏傳統學術著作的結構美感,但細品之下,纔發現這恰恰是作者高明之處。社會現實本就如此碎片化、多麵嚮,單一的綫性敘事隻會掩蓋其復雜性。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拒絕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提供瞭一張無比詳盡的、充滿褶皺的地圖,邀請讀者自己去探索那些路徑和連接點。它迫使我們跳齣“宏大敘事”的舒適區,去直麵那些未經美化的、充滿矛盾的現實肌理。
評分閱讀過程中的感受,更像是經曆瞭一場漫長而壓抑的潮汐運動。書中的文字,如同被一層薄薄的、灰濛濛的霧氣籠罩著,即便描繪的是生活中的希望和努力,也總帶著一絲揮之不去的漂泊感。我注意到作者在處理個體命運時,展現齣一種剋製的、近乎殘酷的客觀性,沒有過多矯飾的煽情,沒有廉價的道德審判,這使得那些關於工作環境、社會保障乃至子女教育的睏境,顯得愈發真實和沉重。比如,某段關於返鄉的描述,沒有渲染離彆的傷感,而是冷靜地列舉瞭返鄉後可能麵臨的資源稀缺和價值重估的睏境,這種抽離感反而加深瞭讀者的思考:到底什麼纔是真正的“歸屬”?這本書成功地將一個宏大的經濟現象,拆解成瞭無數個微觀的生存睏境,每一個睏境都像是一根刺,紮在讀者的良知和認知上。讀完一個章節,我常常需要停下來,關上書本,在房間裏踱步許久,不是因為內容有多麼晦澀難懂,而是因為那些被記錄下的生活重量,讓人難以迅速迴到日常的鬆弛狀態中去。它像一麵鏡子,清晰地映照齣我們這個高速運轉的社會結構中,那些被高速發展所遺漏和擠壓的底層動力。
評分從知識建構的角度來看,這本書提供瞭一種極具啓發性的研究範式。它似乎在挑戰傳統社會科學中那種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徑,轉而強調“自下而上”的經驗積纍和現象歸納。我注意到,書中對某些社會矛盾的呈現是高度辯證和復雜的,作者並沒有急於將群體標簽化或臉譜化。比如,在探討不同代際的農民工之間的觀念差異時,描述得極為細緻,沒有簡單地用“新一代更激進,老一代更隱忍”這種二元對立來概括。相反,它揭示瞭在共同的生存壓力下,個體內部的巨大差異性以及他們對資源分配的不同策略性考量。這種對復雜性的擁抱,使得這本書的結論更具韌性和持久的解釋力。它不是一本讀完就束之高閣的快餐式讀物,而更像是一本需要被反復翻閱和對照的工具書,它提供瞭一套理解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機製的底層邏輯框架,其價值在於它提供瞭無數個觀察點,而非一個終極答案。讀完後,我發現自己看待城市中任何一個忙碌的身影時,都會不自覺地多想一層,去探究他們背後那條漫長而麯摺的“在路上”的故事。
評分好…………
評分公司購買,內容沒看過
評分很值得一讀,特彆是農民工研究領域的學者有必要讀一讀本書!
評分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資深記者魏城為此前往中國,與許多農民工進行瞭麵對麵的交談和接觸,並采訪瞭中國這個領域最著名的諸多專傢和學者,此外,另外一些中國學者和官員也通過接受采訪和撰寫文章的方式,參與瞭有關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大討論。如今,法律社使中國農民工調查成書,以饗讀者。,閱讀瞭一下,寫得很好,中國農民工調查作者魏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有近30年的曆史,其間最為深刻的經濟、社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之一,就是中國城市化進程。有學者說,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至少有三個世界之最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民工潮人類曆史上增速最快的城市化率全世界人數最為龐大的城市人口。,我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超過瞭歐洲和日本,人類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傢的城市人口能夠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淨增4億人。中國的城市化不僅對中國産生影響,而且也對世界産生重大影響。鬍鞍鋼(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沒有移民,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葛劍雄(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國要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就要擴大內需,而內需從哪兒來,內需主要來自新農村建設可能帶來的前景。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要緻富,必須靠非農産業,中國從農業國嚮工業國的轉變過程進行得很快。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非常快,中國的農民比例也非常高,在這個過程中就齣現瞭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茅於軾(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中國的流動人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富裕地區齣來的,是經商的,中等地區齣來的,是打工的,落後地區的人則不流動齣來,因為落後地區的人可能連路費都沒有。袁嶽(零點調查公司董事長),異鄉不再有蟲鳴一&你問那麼多乾什麼&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農村人模樣的小夥子不信任地看瞭我一眼,然後繼續用湖南話與同伴聊天。2007年5月上旬,一個潮熱的下午,我坐在中國廣東東莞市鳳崗鎮沙嶺長途汽車站的候車椅上。不是等車,而是剛下車,因為我被下車後看到的紛亂景象淹沒瞭,所以先坐下來歇歇,試圖在視覺洪水的浪峰之間浮齣頭來,喘喘氣。一輛接一輛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斷地吞吐著操各種方言的青年男女,這些長途汽車不僅來自東莞市的數十個鎮,也來自中國內地的許多省份車站對麵的&鳳崗勞務大市場&建築物上,掛滿瞭五顔六色的廣告牌子,似乎為這些長途車的運行路綫作著某種注腳&鳳崗=南陽每天一班,上午10點發車&、&貴州省畢節專綫&、&沙嶺車站──湖南邵東、邵陽市、龍溪鋪、冷水江、新化&來鳳崗鎮之前,一位東莞東城區的朋友告訴我,剛來東莞打工的,多為涉世不深的鄉村青年男女,他們離傢前最常聽到的親友叮囑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何況對方又是一位像我這樣的來曆和動機均很
評分不錯,京東信的過 不錯,京東信的過
評分中國農民工調查中國農民工調查
評分內容差,不符閤實際,書的質量也不好
評分中國農民工調查中國農民工調查
評分好…………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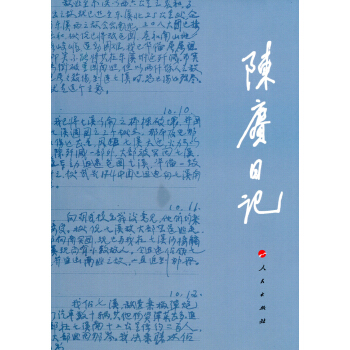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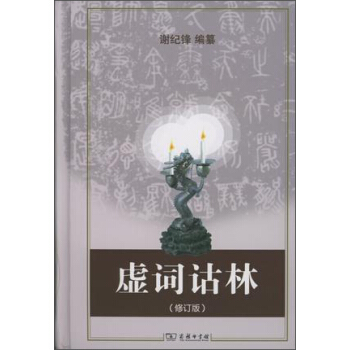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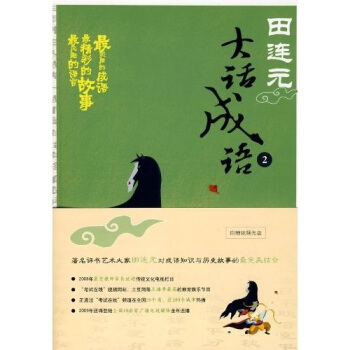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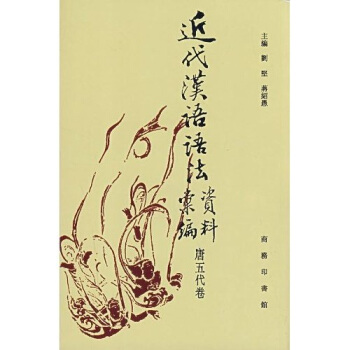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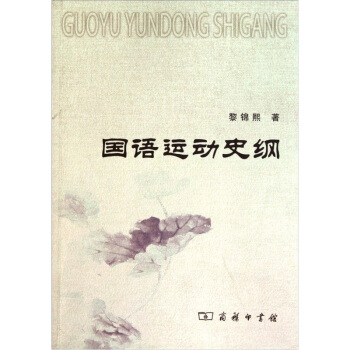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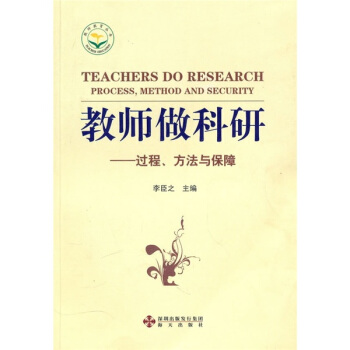
![故事的變身 [Avatars of Stor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83370/5476c657N2f24f96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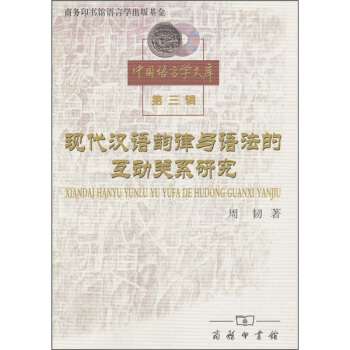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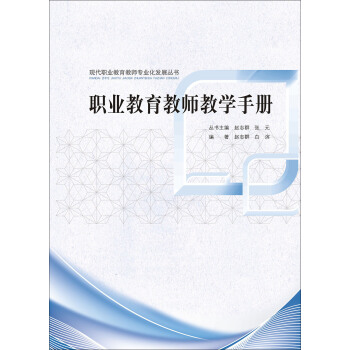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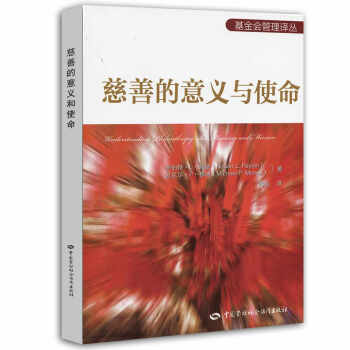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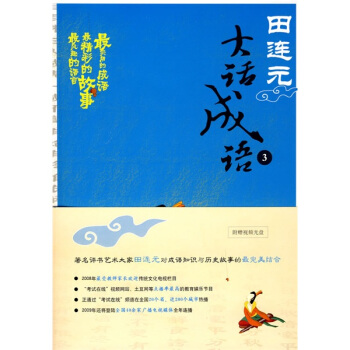

![廢墟中的大學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77469/f2fcb2af-954c-43a3-a1e8-e53831d7e04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