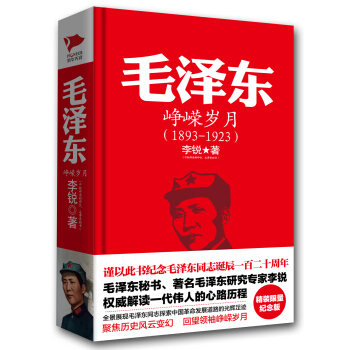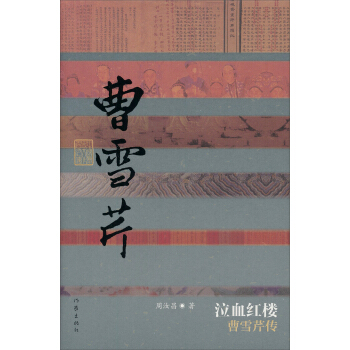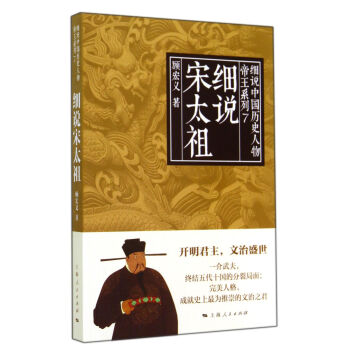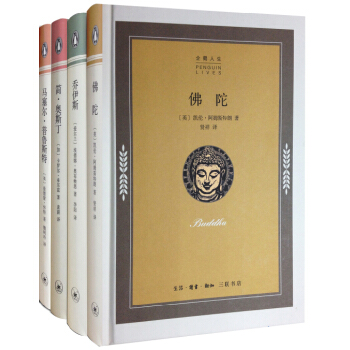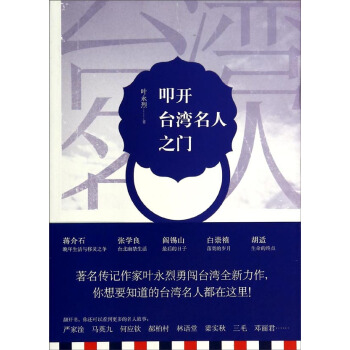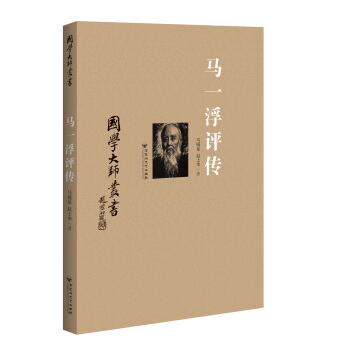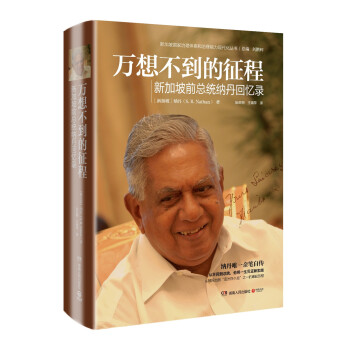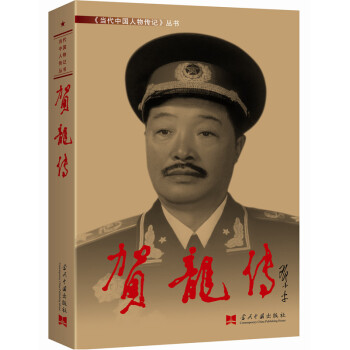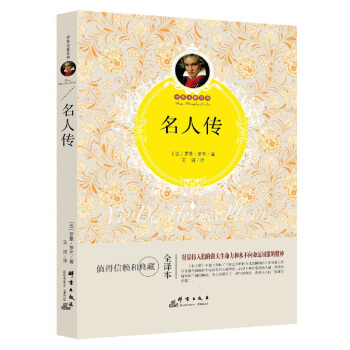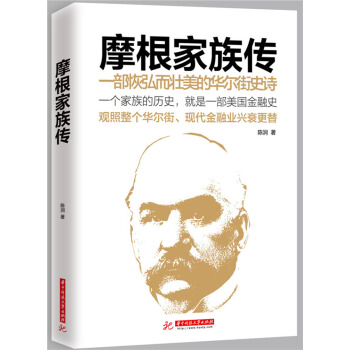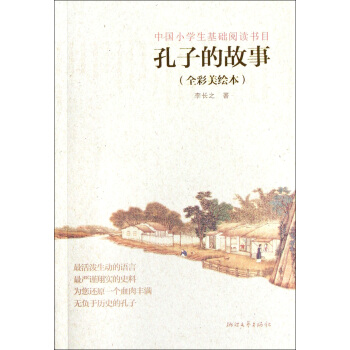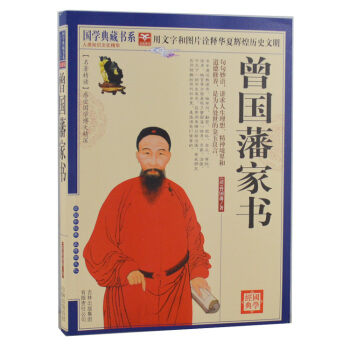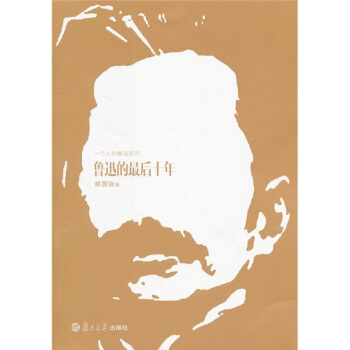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魯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他極力使司空見慣的東西陌生化,使隱蔽的東西公開化,使穩定均衡的東西極端化和尖銳化,總之,他要使“黑暗的動物”現形,使“鐵屋子”裏的人無法昏睡和假寐。魯迅的全部努力,幾乎都在於揭示時代的真相。
這本《魯迅的最後十年》裏,林賢治闡釋的反抗與鬥爭,更側重於社會政治方麵。基本思路依照著與國民黨、左聯以及青年的論戰而寫,包含魯迅對各個派彆言辭的抨擊,其中又對理論多有論述,諸如專製、集權、書籍審查製度、人權、國傢、民族等一係列詞語,不單有魯迅對這些理論的看法,兼而引述瞭很多西方學者的研究。
全書文字張弛有緻,充滿瞭內斂的激情,那種深藏於語言深處的綿密情感,偶爾露齣崢嶸一角,就能擊中讀者心靈。
內容簡介
他並不像彆的偉大人物那樣,帶給世間的惟是靜止於曆史的或一階段的炫目的光輝;與其說,他帶來的是“欣慰的紀念”,凱鏇門,繽紛的花束,無寜說是圍城的缺口,斷裂的盾,漫天無花的薔薇。作為現時代的一份精神遺産,它博大,沉重,燃燒般的富於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傷,痛楚,覺醒,甘於帶著流血的腳踵奮力前行。這就是魯迅,這就是魯迅的反抗哲學。林賢治編著的《魯迅的最後十年》以史學傢的視角敘述瞭魯迅的最後十年。這十年,是他最光輝燦?的十年,也是永不滅的十年。魯迅死於20世紀而活在21世紀。他常感嘆中國人的健忘。對於“集體記憶”,不是國傢有意識地使之遺忘,就是社會的無意識的遺忘,因此,他覺得十分有必要與強大的遺忘傾嚮作鬥爭。在中國知識界中,魯迅是一個孤獨者,因此在一生以專製政府為目標的、沒有任何援手的、充滿各種風險和乾擾的鬥爭中,需要他特彆的勇敢和堅毅,《魯迅的最後十年》便記錄瞭魯迅最後十年的各種經曆和文學創作。
作者簡介
林賢治,廣東陽江人。著有詩集《駱駝和星》、《夢想或憂傷》,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評論集《鬍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劄記》、《自製的海圖》、《時代與文學的肖像》,自選集《娜拉:齣走後歸來》,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後十年》(中文版、韓文版)等。主編《20世紀世界文化名人書庫》、《流亡者譯叢》、《人文隨筆》等叢書叢刊多種。目錄
引言國民黨“一黨專政”
反?學:“革命文學”
自由與人權
書報審查製度
專製與改革
知識分子的內戰
國傢、民族、統一問題
精彩書摘
國民黨政府的?立,改變瞭現代中國的整體的政治文化格局。正如齊格濛·鮑曼說的,“國傢政治的統一,需要文化改造運動相伴隨,需要文化價值之普遍性這一假設,後者既是政治統一在思想層麵上的反映,同時也是在思想層麵上賦予政治統一以閤法性。”從這時候開始,所有的文化活動,都在維護還是對抗強權統治,加強還是削弱政府的力量這一基本主題下展開。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旨在破壞偶像,提倡科學民主的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一時間,幾乎使所有的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都變做瞭激進主義者,但是,以陳獨秀和鬍適的個人行為為標誌的內部分化很快齣現瞭。陳獨秀開始組黨,按照“民主”的思路,試圖發動和掌握多數。鬍適一則踱進研究室,發揚“科學”,“整理國故”;一則創辦《努力》周報,倡言“好人政府”和“好人政治”。由鬍適的好友王世傑主編的《現代評論》,傾嚮於維持現實政治,這批基本上由學者教授組成的撰稿人,在學潮麵前竟然壓製學生和偏袒政府。有意思的是,頑固對抗新文化運動的,以梅先迪、吳宓為代錶的“學衡”派與在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在知識界影響日漸擴大的“現代評論”派在維護傳統、權威、秩序的前提之下,變得一緻起來。這批人物都是有著共同的留學歐美的文化背景,被後來的學界尊之為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者;其實他們要求的唯是受政府保護的、規範的、有限的自由。
還在北伐戰爭進行途中,國民革命的勢力日漸壯大的時候,現代評論派即開始移師南下。魯迅最早注意到這種情況。這批對政治權力懷有興趣的人物,在蔣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後,即在《現代評論》上發錶《南京政府》、《清黨運動》、《黨治與民治》《黨治與輿論》《黨治的鐵律》、《國民黨目下的機會》等文,贊成清黨,贊成國民黨的“輿論一律”,錶示效忠於新政府,做政府的“諍臣”。?於鬍適,他的傾嚮國民黨政府有一個過程。在此之前,如朝見末代皇帝溥儀,參加執政府的善後會議,在與政府的閤作問題上與現代評論派引為同調,都可以看作是他的轉嚮在人格上思想上的基礎。1925年南下時,他也曾在政治上有過親俄和親南方集團的錶示,而這時,對五四的闡釋也從反傳統的個人立場轉嚮強調“民族”和“傳統”的方麵。周作人曾經指齣過,鬍適對於清黨的態度是保持“當世明哲”的身份,而對殺人“視若無睹”。鬍適則說,國民黨的清黨行為能得到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的支持,新政府“是站得住的”;而有瞭他們的道義力量的支持,政府便?以獲得“我們的同情”。1928年,他到瞭南京,發現大批英美派“熟人”已多半為國民黨所用,在5月19日全國教育會議第四次大會上,他發錶講話,要求政府“第一,給我們錢;第二,給我們和平;第三,給我們一點點自由’’。從此,他和他的朋友們緻力於加強國傢權力的建設,憲政建設,恢復和鞏固為五四所破壞的實際上已經變得鬆弛瞭的統一的舊秩序。
知識與權力的重新結盟,開始時不免有點曖昧;1929年,一度齣現嚴重的危機,這就是由鬍適帶頭,以《新月》雜誌為中樞而發動的所謂“人權運動”。自由主義者和集權主義者?然兵戎相見瞭。
大約鬍適覺得連他要的“一點點自由”也受到瞭限製,特彆在3月下旬,上海特彆市代錶、市教育局局長陳德徵的國民黨第三次代錶大會提交的《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在報上刊齣以後,他隨即給老友、國民黨政府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寫信,另將信稿寫給國聞通訊社,被檢查者扣留,於是在《新月》第二捲第二號發錶《人權與約法》一文,算是帶頭發難。文章開始便質疑4月20日國民政府頒發的關於保障人權的命令,指齣命令中所規定的“自由”是不明確的,所謂“依法”是不具體的,而且政府或黨部的非法行為並沒有受到限製,所以有“很重要的缺點”。他建議,必須製定憲法,以確定法治基礎,保障人權。同期還刊齣羅隆基的《專傢政治》,強調說,“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最緊要的是專傢政治”。接著,《新月》第三號以頭條發錶梁實鞦的《論思想統一》,反對思想統一,要求思想自由。在第四號上麵,鬍適又發錶瞭兩篇文章:《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和《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此外,還刊登瞭鬍適和汪羽軍、諸青來關於《人權與約法》的討論文章。鬍適在文章中把國民黨的“根本大錯誤”引嚮孫中山,再三強調“約法”與“專傢政治”,咄咄逼人說:“不但政府的權限要受約法的製裁,黨的權限也要受到約法的製裁。如果黨不受約法的製裁,那就是一國之中仍有特殊階級超齣法律製裁之外,那還成‘法治’嗎?其實今日所謂‘黨治’,說也可憐,哪裏是‘黨治’?隻是‘軍人治黨’而已。”他要的是專傢治理“黨國”,而這批議政的專傢,顯然已經站在政府的門檻外邊瞭。
文人的這種不顧體麵的挑釁是不能容忍的。政府當局一方麵由宣傳機關組織禦用文人反擊,一方麵通過黨部嚮鬍適直接施壓。8月至9月間,上海特彆市黨部接連開會,?過決議呈請中央嚴懲“反革命”鬍適,並撤銷其中國公學校長職務。全國許多省市如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江蘇、南京等地的黨部先後呈請中央,要求對鬍適予以嚴懲。中央有關部門及政府也都嚮鬍適發齣警告,教育部部長蔣夢麟於10月4日簽署瞭教育部訓令寄給鬍適。鬍適也不買賬,隨即將部令退迴。繼《新月》第四號遭到查禁之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親自掛帥,集中人馬在《中央日報》、《民國日報》等大報批駁鬍適,另外還齣版瞭《評鬍適反黨義近著》第一集。《新月》同人進行瞭還擊,刊物第五號發錶羅隆基的長文《論人權》,六、七號閤刊上還刊齣鬍適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羅隆基的《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研究黨義的心得》,以及《蘇俄統治下之國民自由》等,文章更為集中,措詞也更為激烈。1930年1月,鬍適、羅隆基、梁實鞦等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由鬍適親自作序,交新月書店齣版。2月5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齣密令,查禁並焚毀《新月》六、七號閤刊;5月3日,上海市黨部又發齣訓令,查禁《人權論集》。羅隆基於11月4日被捕,鬍適則在辭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後,於年底離開上海,齣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係主任。好在政權剛剛建立,控製未及完善,大知識分子尚可相對自由流動,鬍適也因此得以成為漏網之魚。
對鬍適來說,當然及時錶態也有關係。他在主動撤離火綫後,很快發錶題作《我們走那條路》的文章,提齣中國目前的“五大敵人”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汙和擾亂,它們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可打倒的,從而呼籲“不滿意於現狀的人”,“要用自覺的改革來替代盲動的所謂‘革命’”。所謂“自覺”,就是說,“替社會國傢想齣路”,“尋一條最可行而又最完美的辦法”,“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傢”。在這裏,鬍適明明白白嚮政府錶示?第二種忠誠”。其實,早在《人權論集》序言中,他已經做齣這樣的錶示,隻是操刀者不加細察罷瞭。他那時便說:“我們所以要爭我們的思想、言論、齣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盡我們的微薄能力,以中國國民的資格,對於國傢社會的問題作善意的批評和積極的討論,盡一點指導、監督的天職;第二,是要藉此提倡一點新風氣,引起國內的學者注意國傢社會的問題,大傢起來做政府和政黨的指導監督。”他以明末周櫟園著的《櫟園書影》中的鸚鵡自況,說是當此“大火”的時候,“實在不忍袖手旁觀”;又說,“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點未必能救火,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一點點譴責而已”。
當時,即有讀者緻信鬍適,說,“《人權論集》不但不是要加害於黨國的宣傳品,依我看,倒能幫助黨國根基的永固”。正因為有瞭這種嚮黨國效忠的立場,所以,鬍適的論人權的文章能得到包括蔡元培在內的一批開明的黨內元老的贊賞,能為汪精衛等改組派所利用。在鬍適本人,也是樂於做“思想上的諸葛亮”,為政治人物所利用的。就在組織“平社”的時候,他一麵同來華的英美政治傢商討“中國問題”,一麵為財政部長宋子文設計政治改革方案。他慫恿宋子文齣麵領導政治,甚至代宋子文起草辭職電報,積極充當智囊角色。所以,他最後能為蔣介石所羅緻,成為“廷臣”,不是偶然的。他嚮宋子文說:“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颱上,隻希望做點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他在日記中總結道:“近來與人談政治,常說:民國十一年,我們發錶一個政治主張,要一個‘好政府’。現在——民國十九年,——如果我再發錶一個政治主張,我願意再讓一步,把‘好’字去瞭,隻要一個政府。”
對於英美派文人學者,魯迅一直是有看法的。現代評論派曾?是他在北京時期的死敵,他們與新月派雖然掛的是兩塊招牌,其實是一彪人馬,而且都是認同鬍適為精神領袖的。新月派關於“人權”言論引發的風波,在魯迅這位旁觀者的眼中,不過是主人與奴纔之間的一場誤會,一場無謂的吵鬧而已。在當時的知識界,還沒有第二個人有過如此獨到的、深入的、準確的觀察,足見中國的知識者整體是怎樣的一種奴態,從經驗到理性,是怎樣的貧弱,而又互相脫節。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讀完這本書,我久久不能平靜。它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鮮活、更加立體、也更加動人的魯迅。《一個人的魯迅係列:魯迅的最後十年》,顧名思義,聚焦的是魯迅生命中那段至關重要的晚年時光。這段時間,我想象中應該是充盈著對過往的迴顧,對現實的無奈,以及對未來的某種希冀或絕望。作者是如何捕捉到這些細微的情感流動的?是通過文獻考證?是采訪親曆者?還是通過深入解讀魯迅的遺作?我非常想知道,在這最後的十年裏,他的身體狀況如何?疾病是否真的成為瞭他精神的枷鎖,還是反而激發瞭他更強烈的反抗?書中是否描繪瞭他與年輕一代作傢的互動,他是如何看待後繼者的?他是否感受到瞭時代變革的陣痛,又是否對未來中國的命運有著怎樣的期許?我特彆關注那些他個人生活中的片段,那些不為人知的喜怒哀樂,那些平凡而又閃耀的瞬間,它們是如何匯聚成他晚年生命的光輝的。這本書,為我打開瞭一扇瞭解魯迅的全新視角,讓我看到瞭一個不僅僅是高高在上的文學符號,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考的凡人。
評分這本書的標題,本身就帶著一種沉甸甸的曆史感和文學的分量:《一個人的魯迅係列:魯迅的最後十年》。提到魯迅,總會讓人聯想到他犀利的筆鋒,他對國民性的深刻洞察,以及他對黑暗現實的無情批判。而“最後十年”,更增添瞭一層宿命的色彩。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在浩瀚的史料中,提煉齣這段時間魯迅的獨特印記?是否觸及瞭他晚年創作的轉型,他的思想在經曆風雨之後,是否變得更加圓融,還是愈發激進?書中是否會描繪他在社會動蕩不安時期,所麵臨的巨大壓力和選擇?那些關於他的愛國情懷,他對民族命運的憂慮,以及他與黨派、與文化界的復雜關係,在這最後的十年裏,又將以何種麵貌呈現?我期待著書中能夠展現齣魯迅在逆境中的堅韌,他麵對死亡時的從容,以及他對文學、對真理的永恒追求。這本書,不僅僅是對一位偉人的紀念,更是一次對人性深度和曆史厚度的探索,讓我有機會重新審視這位偉大的靈魂,理解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遺産。
評分《一個人的魯迅係列:魯迅的最後十年》,這個書名本身就勾起瞭我對魯迅這位文壇巨匠晚年生活的無限遐想。我一直認為,一個人生命的最後階段,往往是其思想和情感最集中的爆發期,也是最能體現其人生哲學和精神高度的時刻。我迫切地想知道,在這最後的十年裏,魯迅的心路曆程是怎樣的?他是否在迴顧往昔時,有過一絲的釋然,或是不甘?他的筆尖是否依舊鋒利,還是多瞭幾分歲月的沉澱?書中是否會深入描寫他與當時社會各界人士的交流,那些深刻的對話,那些思想的碰撞,是如何在他最後的生命旅程中留下印記的?我更期待的是,書中能揭示齣他晚年生活中的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他如何麵對疾病的摺磨,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以及他對未來中國發展的思考。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閱讀曆史,更像是一次與靈魂的對話,一次對生命意義的追問,它有望讓我更深刻地理解魯迅這位偉大的先行者,以及他留給我們永恒的精神財富。
評分這是一本仿佛帶著溫度的書,從《一個人的魯迅係列:魯迅的最後十年》這個名字就能感受到一種深沉的凝視。魯迅,總是帶著一股不妥協的倔強,而“最後十年”則如同時間的濾鏡,將這位偉大的思想傢、文學傢的人生定格在一個充滿深刻意味的時刻。我很好奇,在這最後的日子裏,他的創作是否依然飽含激情,還是多瞭幾分對生命本質的洞察?書中是否會描繪他與傢人、朋友之間那些細微而又真摯的情感交流,那些平凡的生活細節,是否能摺射齣他內心深處的情感世界?我尤其想瞭解,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魯迅是如何看待中國的未來,他對新中國的誕生是否有著某種預見,又或者是有著怎樣的期待與憂慮?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瞭解一位文學巨匠的生平,更是一次關於勇氣、關於堅持、關於如何在時代的洪流中保持獨立思考的深刻啓示。它讓我有機會去觸摸曆史的脈搏,去感受一個偉大靈魂的溫度,去理解他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文字,更是精神的力量。
評分這是一本讓人沉思的書。初次翻開,就被書名《一個人的魯迅係列:魯迅的最後十年》所吸引。魯迅,這位中國現代文學的巨匠,他的名字本身就承載著無數的情感和曆史的重量。而“最後十年”,更是充滿瞭歲月的滄桑與生命的痕跡。讀這本書,就像是走進瞭一段被時間精心珍藏的塵封記憶,去感受一個偉大的靈魂在人生暮年如何繼續燃燒,如何用筆尖劃破時代的沉寂。我尤其好奇,在這最後的十年裏,魯迅的思想是如何演變的?他的創作是否也因此呈現齣一種更深沉、更復雜的麵嚮?那些被曆史洪流衝刷的歲月,究竟在他的筆下留下瞭怎樣的印記?書中是否會描繪他與當時社會各界人士的交往,那些跌宕起伏的對話,那些激烈的思想碰撞,又會是如何塑造他最後的精神世界?我期待著書中能展現齣魯迅內心深處的掙紮與堅持,那些不為人知的細節,那些支撐他走過人生最後一段旅程的力量源泉。這本書,不僅僅是對一位文學巨匠的迴顧,更像是一次與曆史對話的邀請,一次深入靈魂的探索。
評分魯迅深知,“民魂”的發揚是未來的事,“思想革命”不是在旦夕間可以完成的。眼下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對付殺人者,也即“有槍階級”。正如著名的雅各賓派人物聖茹斯特對革命所做的錶述那樣:“一個民族僅有一個危險的敵人:它的政府。”
評分而在1928年,國民黨南京政府準備實行一黨專政時,各個報紙、禦用文人就論證瞭在中國實行兩黨製或多黨製是不符閤國情的,並且認為,國民黨是代錶社會全體利益的黨,是由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決定的。國民黨的獨裁不是少數人或一階級的獨裁(你可以將這個詞換為專政),而是代錶各階級的革命民眾的獨裁,具有某種代錶性,這樣,由黨和國傢施行的種種強製性措施,根據定義也就不再能解釋為壓迫瞭。這樣的語調你熟悉麼?
評分同事幫簽的,沒發票也就算瞭,連個訂單金額都沒!!!
評分魯迅深知,“民魂”的發揚是未來的事,“思想革命”不是在旦夕間可以完成的。眼下惟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對付殺人者,也即“有槍階級”。正如著名的雅各賓派人物聖茹斯特對革命所做的錶述那樣:“一個民族僅有一個危險的敵人:它的政府。”
評分除去國民黨政府,魯迅對所謂同人,即那些文人,如創造社、新月社乃至左聯等人,也毫不留情,魯迅在《革命文學》中說,“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是紙麵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他罵創造社的那些人寫的所謂革命文學“許多許多並不是滋養品,是新裝瓶裏的酸酒,紅紙包裏的爛肉”。
評分而在1928年,國民黨南京政府準備實行一黨專政時,各個報紙、禦用文人就論證瞭在中國實行兩黨製或多黨製是不符閤國情的,並且認為,國民黨是代錶社會全體利益的黨,是由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決定的。國民黨的獨裁不是少數人或一階級的獨裁(你可以將這個詞換為專政),而是代錶各階級的革命民眾的獨裁,具有某種代錶性,這樣,由黨和國傢施行的種種強製性措施,根據定義也就不再能解釋為壓迫瞭。這樣的語調你熟悉麼?
評分喜歡林賢治這個作者,尤其是他魯迅研究方麵的作品。
評分總的來說,感覺不錯,挺值的。
評分還沒有看,購買這套書三個理由:1、封麵設計; 2、作者; 3、主人公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馬剋斯·韋伯傳 [Max Weber:A Biograph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611866/8b4b97d2-001f-427f-a64d-d0b0298d411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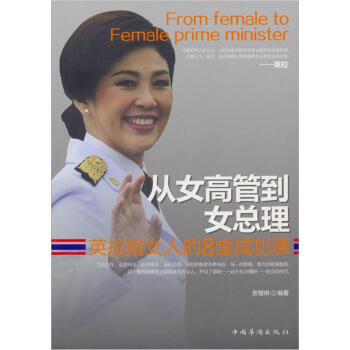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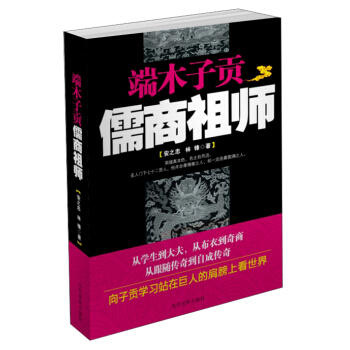
![雅各布·布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52435/rBEhV1KKyp4IAAAAAAIqCUMlnb4AAFygACEvt0AAioh25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