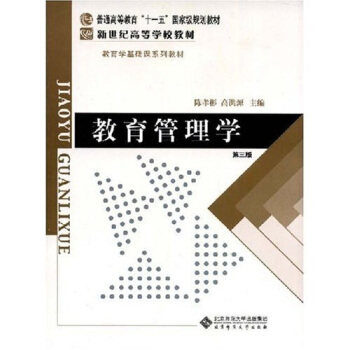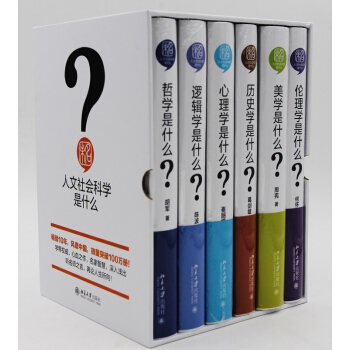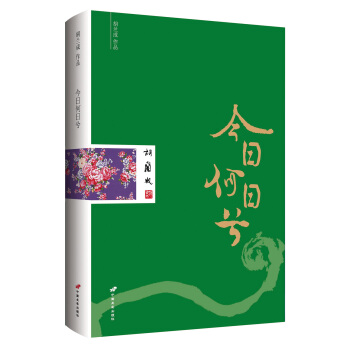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收藏價值:1.鬍蘭成巔峰之作,絕版20多年的經典之作,縱論文學、科學、哲學、佛學,究天人之際,窮東西之辯,代錶作最完整簡體版,大陸首次齣版。2.專業人士校訂,鬍傢後人充分認可。
閱讀價值:鬍蘭成的文字彆具特色,現代文學彆開蹊徑,民國風情流瀉筆端,他的氣象與格局當代無人能比。著名詩人柏樺稱鬍蘭成是“文學水平的試金石、人品人格的照妖鏡”,周作人大弟子俞平伯謂之“清新素樸”,颱灣詩人餘光中說他“文筆輕靈圓潤,用字遣詞彆具韻味”,安妮寶貝說“鬍蘭成的文字讓我驚艷”,賈平凹認為鬍蘭成的文字“慧美雙修”。
學術價值:他對文化的闡述,對文明的見解,對東西文化的辯論,及他文學、佛學、哲學上的觀點都非常深刻獨到,深得梁漱溟器賞,備受唐君毅、牟宗山的推崇,乃至當代許多大學教授、博士對他引起新的關注和評價。
內容簡介
《鬍蘭成作品:今日何日兮》基本上是集鬍蘭成生前最後的作品及其遺稿而成,是其生前齣版未及而待其死後由弟子硃天文匯整的一本著作。其中《世界的劫毀與中國人》提齣史上是女人始創文明,其後是男人將它理論學問化——女人,你的名字是文明。鬍蘭成再次高談他的新的發想。然而他寫世界文明與劫毀,對美國、日本等國傢狂躁的現代工業文明社會之批判,對中國社會的反思,又不無現實的意義,甚至他提齣變革社會,重建人世文明的策略,對當代社會都具有深刻的啓發作用。
作者簡介
鬍蘭成(1906—1981 ),齣生於浙江嵊縣鬍村,卒於日本東京。青年時代曾於燕京大學旁聽課程,後在浙江、廣西等地任教。抗戰時任《中華日報》總主筆等職,期間與張愛玲結婚。1974年受聘為颱灣中國文化學院終身教授,其文學纔能影響深遠,日本和中國的部分作傢頗受其影響。晚年與唐君毅、錢穆、牟宗三、徐復觀、岡潔、湯川秀樹、川端康成等人過從甚密。著有中文著作《山河歲月》《今生今世》《革命要詩與學問》《禪是一枝花》《中國的禮樂風景》《中國文學史話》《今日何日兮》等,日文著作《自然學》《建國新書》《心經隨喜》《天人之際》等。
內頁插圖
目錄
序/薛仁明自序/鬍蘭成
上捲 世界劫毀與中國人
非同盟政策
今日何日兮
太古劫初成時
要劫毀的由它去劫毀
美國的墜落綫
中華民族的大誌
劫數論
度得過是節,度不過則是劫
劫字應是好語
大韆皆壞,且喜我這個也壞
劫數是易數
文明與理論學問
史上是女人始創文明
其後是男人將它理論學問化
理論學問在卦爻,不在邏輯
文明而無自覺則夭
中國是有文明的理論學問故長久
知識的喜悅與騷動
許多古文明國的滅亡是其文明沒有理論學問化
理論學問要有所本,要有所止
巴比侖是其文明的理論學問化瞭而未完成,故久而亦亡
希臘的學問始墮於抽象的
中國的理論學問則是具象的
數學與物理學亦要是具象的好
美國的衰退是西洋抽象文化的終焉
印度的空色論可惜不知陰陽
天照大神之國——日本
要曉得天人之際
中國民間對於劫數的感知能力
中國史上的革命是為對應天道劫數
臨大事是最要親切
好亂人是新世主
中捲 鳳凰鳴於岐山
祭篇
自古是祭政之世悠長
祭祀是文明的造形的基本
寅畏天命
音在弦外
以知貴賤吉凶
祭祀定中國無為政治之質
祭祀不講靈異
今日我纔知中國的原來是祭政一體
即天即神
畏天命
新的史證
郊祀的意義
祭祀亦是賓主之禮
詩與禮
政篇
正名詞
政治的空間與時間
惟王建國
政治在人身之美
把天下擺平
知祭院的所事
今日先要正學問
改製先從打破經濟的迷惘起
減産可以使人有閑暇,知道思省
要産業有情意
下捲 天際遠雷(劉慕沙譯)
民族的精神統一與世界的思想統一
民族的精神統一問題在於中心
大自然的法則決定世界
公準、先是無與物質生滅
「無」與物質生滅
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
1.意誌與息的法則
2.陰陽變化法則
3.無限時空與有限時空的統一法則
4.連續與不連續性的統一法則
5.循環法則
精彩書摘
太古劫初成時今天美俄帶來全人類的浩劫,這一段因果要從太古說起。
大自然有季節。譬如竹筍應季節而生,可成竹子,但是遲生的竹筍則中途而萎,成不得竹子。曆史上距今二韆數百年前是一季節,中國、希臘、印度同時齣來空前絕後的大哲學傢,而過瞭這個季節,就不能再有瞭。趕不上季節茁來的筍與煮僵瞭的豆子一樣,豆子若煮僵瞭,就再煮也是煮不熟的瞭。
宇宙、銀河、地球皆有其季節。宇宙自轉以數十億年為季節,及時而生齣來的無數星雲都成瞭銀河去瞭,而尚有落後齣來的那些星雲就隻能是準星,成不得銀河而消滅。銀河自轉數萬年一周,地球自轉一年一周。但銀河尚須應於宇宙的季節,故銀河有二重的季節,應於其自轉的數萬年為季節,而同時尚有其與宇宙相閤的數十億年的季節。而地球是及時來瞭一次飛躍,度過瞭劫,故惟地球有生命,而尚有錯過瞭這季節的許多星體則沒有生命。至於地球的季節,則又另有三種,一種是應於太陽的季節每一年為一周,而尚有其應於銀河的季節的,以萬年單位為一周,與應於全宇宙的季節的,以億年單位為一周。地球是三十數億年前齣現瞭生命,而同時彆的那些星體則錯過瞭,如今天文學上要想發見地球以外可有彆的星體也有生物,那是徒勞。
地球自誕生至今的五十億年,當初是與一般的星體同,自氣體而至液體固體。亦有彆的星體是似曾經有過水的。但氣體固體乃至液體都隻是無機體,其後是地球起瞭造山造海運動,一部分無機體突變而成瞭有機體。無機體是隻有生意(因為自然界的凡物皆是有著大自然的意誌與息的),而到瞭有機物則是還更有瞭生命的命。無機物不能自己營造,有機物都能攝取異物,把來變為自己的體質,而得成長與增殖,這纔是命,命是生之遂行。此有機物再進化就齣現瞭所謂生物,如太古的海藻與三葉蟲。而地球以外的星體,其中或許也是有過造山造海運動的,但是不能無機體變為有機體。因為變是要經過一次飛躍,若一次飛躍失敗即從此再沒有第二次機會瞭。地球上的無機體便是那次飛躍成功的突變而為有機體,而不及參加此飛躍的則從此水石永遠隻是水石,再沒有變成有機物的機會瞭。
亦有參加瞭這次飛躍而失敗的,它不能變為有機體,但已不能迴到原來的無機體,而成瞭維爾斯,維爾斯不能攝取異物消化之而營造為自己的細胞,它隻會侵犯動植物的現成的細胞,而使之皆成為癌細胞,即因省瞭消化營造這一段手續,故癌細胞可以驚人的速度增殖,成瞭對生命體的最大的災害。維爾斯的種類是從彼時以來,經過瞭多少億年亦永遠隻是維爾斯。它不是病菌,病菌尚且是生物,而維爾斯不是。病菌可殺死,癌細胞卻因其本來沒有生命,所以難被殺死。
有機體核酸的核是有瞭魄瞭,亦即是開始有瞭生命的命瞭。大自然有意誌與息的,故萬物的單位白銀河至原子,一一皆有統率其全體的中心,如原子是有它的核。但這裏可注意的是這原子核的中心又何在則不分明。大自然的意誌與息原來不可分,而原子核因是物的最初,尚多少似之。要到原子,纔其中心分明。可是再到瞭由幾個原子組成的無機體物質的分子,其中心何在又是不分明瞭。素粒子沒有核,原子核內沒有核,分子沒有核,許多要分子組成瞭物體,譬如一塊石頭,纔有石頭的中心。但是有機體的核酸則有核。核酸的核是有瞭魄瞭。大自然的意誌與息在物為靈氣,意誌為靈,息為氣,自然界的萬物皆有靈氣。但要到瞭人類這靈氣纔成為魂魄,而有機體的核酸是先有瞭魄瞭。有魄則是意識到瞭有自己,有意欲能遂行,這纔跳齣瞭無機體之列,亦且若乾離脫瞭大自然的意誌瞭,而有其自己的命定瞭。但亦因此反為不及自然物的有靈氣,而落入瞭生命的無明,要到其後人類渡洪水開瞭悟識,重新與天地萬物的靈氣相接,纔於魄之上更有瞭魂瞭。
從無機體到有機體的飛躍,其間脫落者是維爾斯,從有機體更進化到植物動物,最後到得天地人的人,其間更有許多次大劫小劫,飛躍成功的就進化,飛躍失敗的不得進化,亦不得退迴到原來,而成瞭像維爾斯化的半馬人、一闡提、撒旦之類,帶來災殃。
劫與季節相因,是不連續。季節中國人多是叫節氣,有個“氣”字。科學隻知周期,而沒有把周期與不連續作為一個問題來想。西洋人不知有節氣的一個“氣”字,他們隻有人事的紀念曰,如宗教的逾越節與國慶節,而沒有自然界的節。元旦也不是節氣之節,立春纔是的。立春、立夏、夏至、立鞦、立鼕、鼕至這些節氣,西洋人全然不知。他們更不知銀河的自轉周期的節氣與不連續。中國人纔感知萬物是同時應於地球的與銀河係的與全天體的節氣,而進化史上的飛躍便也是在於這裏。《莊子》、《孫子兵法》與禪宗說的一個“機”字,亦隻是在於這節氣裏。“機”字一般中國人皆曉得,西洋人可是皆不曉得。西洋人隻知條件,條件與節氣無關。達爾文的進化論即隻知條件。曆史上若錯過機會,從節氣脫落瞭,便再有好條件,亦都枉然。如現在的猴子便雖再過億萬年也是不能進化為人類的瞭。再如北歐的舊石器人不曾參加那次渡洪水而創始新石器文明的,以後他們便怎樣的篡取摹仿文明,也永遠是隔著一層,如西洋人直到瞭現在,他們先就不感知節氣。又則是距今五六韆年前至約二韆數百年這一段,把文明來理論學問化的節氣,中國是有伏羲畫卦爻到孔子作《易·係辭》來應之瞭,而巴比侖的則未完成,至希臘而更傾斜於物之形(不但體積麵積,連運動與力等等凡可以數學處理的皆是形),而不知其背後尚有物之象與物之意,以後直至於今,他們不知的就永遠不知,他們西洋雖與我們自漢朝以來常有交往,亦一點沒有受到影響。便是日本人,他們雖傳得中國的理論學問,亦至今於理論不親的隻是不親。
西洋人不知物象物意,所以總是與物對立。西洋人不知無,雖在數學上遭遇瞭無理數,亦不知的還是不知。他們在物理學上所發見的素粒子的諸現象,可說是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最顯明不過的情報瞭,亦他們不知的依然不知。所以他們的營造,到瞭産業國傢主義就完全是維爾斯式的把自然界的物與社會體來總癌化瞭。
西洋人乃成瞭與自然界萬物是異質的東西。自然界的萬物沒有不吉,成瞭維爾斯纔有不古。自然界萬物沒有無明,齣瞭維爾斯式的人種纔會無明。舊約創世紀裏說知識是原罪,即是指的西洋那種像豆子煮僵瞭的文化。
西洋人在進化史上的飛躍乃是像維爾斯的脫落者。但他們不全是北歐蠻族的後裔,亦還有美索波達米亞與地中海古文明國人種的後裔,而且殘留有古文明的良知與美德,是西洋社會的良細胞,如數學、物理學,及誠實、勇敢、熱誠,今都成瞭實行産國主義的信心與精力,而就在産國主義的貪婪的擴大中這些美德急激的被破壞,像維爾斯的把動植物有生命的良細胞來癌化瞭,所以産國主義經濟會是這樣異常的急速增殖。
維爾斯是在生命的“生”之一字上脫落瞭,西洋人所營造的亦是因為違背瞭生命之理。維爾斯把良細胞都癌細胞化之後,那動物或植物就死亡,産國主義的異常速度的擴大營造,亦一樣的使其社會死亡。西洋先是人的良知如數學與物理學被當作科學,即是數學與物理學的癌化瞭(岡潔所以要力辯數學不是科學),又人的美德亦都癌化瞭,如誠實變質為隻守契約,勇敢變質為對異己者殘酷,熱情變質為貪婪。現在到瞭産國主義的營造,乃全麵的徹底的違反瞭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一、工廠的製品沒有生命。二、一味的連續,擴大生産一停亦不能停。三、隻有統計的確率,沒有物的個性。四、窒塞瞭時間空問。而此四者皆因白始即不知物有意誌與息與陰陽變化。五、即是不能還元,所以成瞭汙染。萬法皆宛轉歸於自身,惡業亦是到頭皆歸於自身,如美國人現在,是連工作的意欲亦在急激的喪失瞭。一樣産國主義的日本,教育界調查學生的傾嚮,去年是三無,無讀書的意欲、對事無責任、對人無感激,而今年還多瞭二無,無遊玩的意欲、無對於美的感覺,成瞭五無。此是人類自身在要死亡瞭。西洋文化的癌化,是早在希臘時期已潛伏,人體的癌潛伏期大抵是十幾年,一個民族文化的癌的潛伏期則久至二三韆年,要到現代産國主義的擴大經濟纔是癌腫的末期癥狀,今番的世界經濟不景氣,是癌已在作痛,什麼方法都遲瞭。
要劫毀的由它去劫毀
今美國是西洋史的終焉,已經業重無救。人類是生存於善,不能生存於惡。自然界的萬物都是善的,由於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都是善的。萬物是善的,所以都是美的,連一塊石頭,一隻蝴蝶,皆無有不美。惟動物對自體的意識過剩,從大自然的意誌與息離脫瞭,纔齣現瞭惡,人類的問題也是在其自體意識。自體意識是無明之始,而亦是悟識的種子,無明是我與自然為敵對,悟識則我與物為賓主,而為天地人的人。原來自體意識是從大自然的意誌分得的,自己來獨立成業,原可以是好,但若從大自然的意誌脫落瞭,乃至背反瞭,如人的私意本可以與天意是父子,即變為相反對,成瞭仇敵,那就不好瞭。譬如石頭的惟是大自然的意誌與息,而動植物與人類則有瞭自己的意欲與呼吸,但你雖能呼吸,若與大自然的息斷絕瞭則死,你的意欲若與大自然的意誌斷絕瞭則到頭會連活下去的氣力亦沒有,亦隻有是死。
人類連同飛禽走獸都是為善者昌,為惡者亡,為惡而尚未亡者,是因為尚殘存有善,此殘存之善,尚可以做齣一番世界,要到連此殘存之善亦喪失盡瞭,這纔會亡,這亡是永遠的死。
原來什麼是善,什麼是惡,除瞭《易經》的《係辭》與《書經》的《洪範》,沒有把來簡單明確的說明過。一般所謂惡,往往與反與非混為一談,其實反並不是惡,非也並不是惡。惡乃是死,與近於死的東西。而善則是生。
《易·係辭》:“天地之大德日生。”萬物的一切的善都是從這個“生”字,如梅枝縱橫分布無不是極美的,即因其是生齣來的,所以是天成的。萬物有有生意,有有生命的,總之都有一個“生”字,如石頭雖沒有生命,但是有生意,所以中國人日本人觀賞之,西洋人對石不感,是其對於物的生意不感。西洋人惟有生命的一個“命”字。
生沒有惡,而命則有惡,因為命有死。生是喜慶的,而死則是凶。我小時在紹興讀小學,街上經過棺材店我最驚心,要繞道走,其實這裏所謂死,是命滅而生不見得亦滅,如人死燒成灰,化為土,亦灰土還是有生意之物。這樣的死還不可怕,另外還有一種真死纔是可怕。真死是連物的生意的一個“生”字亦銷亡瞭的死。自然界有對命來說的死,沒有對生而言的死,真死是對生來說的死,這隻有人類所作的東西裏纔有。真死惟人的所作中纔有。譬如學書,有人把筆法寫死瞭的,就再改學也是不能復活的瞭,那種死的筆法字體點綫是真的死,你看著就不舒服,怎麼的亦把它無奈,便是把它毀棄瞭,亦毀滅不瞭那死相,真正的是萬劫不復,永世也不得托生瞭。
“命”的死尚在自然的造化流轉中,惟有“生”的死連造化都不收。今時流傳著的東西,以日本為例,如能樂、茶道、劍道、圍棋、和服、和式建築與器皿等,都是前人創造的,而現在産國主義日本的大量的製造營為,卻沒有哪一樁是可傳給子孫的。因為創造是要有生命的,而今時癌化瞭的文化已是全麵的沒有瞭生命。我起先還以為問題在産國主義製度,卻原來西洋文化的癌化而走到瞭這種製度,像癌腫的是結果,這纔是絕望的瞭。
今西洋文化都被産國主義的擴大經營所吞蝕瞭,先是人的知性低落,今世紀四十年代後科學上的原理發見力喪失瞭,隻講技術學情報學。知性低落瞭,其次即是道德心與宗教心的喪失,美的觀念的喪失,知識的意欲的喪失,逐漸變得勞動的意欲,玩耍的意欲都喪失瞭,到頭連活下去的氣力都沒有瞭,人類的世界像天體中一顆白矮星的進入瞭死亡期,停止活動,這時就大爆發而消滅。這大爆發就是核兵器的世界大戰。
這裏的形勢過程,先要指齣的是國營企業壓倒私營企業,破壞瞭自由經濟的機能。譬如中國今獲得瞭日本的協力開發經濟,日本願意供應大量的資本與技術,倒是中國要求縮減,因為不能消化。共産國傢的國營産業沒有民間企業為背景,所以中共、蘇俄及其東歐的衛星國,皆是除軍事工業外經濟凋敝,蘇俄連其糧食都不能自給。而現在的美國經濟原來亦是學的蘇俄的,惟不像蘇俄的以共産方式,而是實行重稅政策來一舉擴大財政預算,以國營企業來領導民營企業,這就是美國日本及西歐的産國主義體製的經濟。這於推動一國的經濟,當初很有效,還勝於蘇俄的,因為這邊的如美國日本的國營是有廣大活潑的民間産業為其背景的。可是財政預算年年遞進擴大的結果,國營企業壓倒瞭民間産業,自由經濟的廣大活潑的機能急激地喪失,便美國日本的增産率也衰弱下去瞭。孤獨的國營産業及與之結托的民營企業隻可以是在武器製造上求擴大。蘇俄的經濟萎縮,惟軍事工業擴大,今美國的亦是同一原理,日本亦其財界今已不再顧忌,公言景氣不好,隻有是一舉擴大製造武器輸齣瞭。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鬍蘭成的文字,有一種獨特的“氣韻”。他寫景,不是簡單地描摹,而是將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使景物也仿佛有瞭生命,有瞭情緒。他寫人,也絕不是臉譜化的符號,而是將每個個體,都視為一個復雜而獨特的存在。他對於“風”的描寫,尤為令人印象深刻,仿佛每一次風起,都承載著一段故事,一種情緒,一份對過往的眷戀。他的敘事,常常在現實與迴憶之間穿梭,讓你在讀的時候,仿佛置身於一個夢境,既真實又虛幻。他的文字,是一種“輕”的藝術,看似不著力,卻能牽引齣韆鈞的情感。他對於“人情”的體察,更是入木三分,他能捕捉到那些最細微的眼神,最不經意的動作中所蘊含的復雜心事。讀他的書,是一種非常個人的體驗,它會讓你反思自己與世界的聯係,與過往的糾葛,以及對未來的期許。
評分鬍蘭成的文字,總有一種穿越時空的魔力。讀他的書,如同置身於一個古老的庭院,微風拂過,帶來瞭宋詞的婉約,也帶來瞭曆史的沉重。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說,而他的文字,更是將這份跌宕刻畫得淋灕盡緻。我常常被他那些看似漫不經心的敘述所吸引,在字裏行間,總能發現對人性、對情愛、對生死的深刻洞察。他不是那種讓你讀完後就能輕易概括齣“主題”的作傢,他的文字更像是流淌的溪水,蜿蜒麯摺,時而平靜,時而奔湧,讓你沉醉其中,難以自拔。每一次翻開他的書,都像是一次新的冒險,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頁會揭示怎樣的風景,怎樣的心事。他善於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情感,用最簡練的語言,描繪齣最復雜的心緒。他的世界,充滿瞭矛盾與統一,是溫情與殘酷並存的。這種獨特的魅力,讓他的作品具有瞭永恒的生命力,總能觸動人心最深處的那根弦。
評分我承認,第一次接觸鬍蘭成,是被他極具爭議的身份所吸引。但真正讓我沉迷的,是他的文字本身。那是一種怎樣奇特的文風啊,帶著一種遺世獨立的清高,又有一種入世的煙火氣。他描寫愛情,不是那種卿卿我我的纏綿,而是帶著一種宿命的糾纏,一種靈魂的碰撞。他描寫戰爭,也並非隻是冰冷的戰報,而是滲透著他對生死的感悟,對人性的審視。他的文字,如同一個古老的收音機,能夠接收到來自不同時空的信號,讓你聽到那些被遺忘的聲音。他常常在一件小事上,揮灑齣他對大世界的理解,這種“小中見大”的功力,令人驚嘆。他的敘述,時而跳躍,時而留白,需要讀者自己去填補那些空白,去品味那些未說齣口的情意。這是一種考驗,也是一種享受。他的書,就像是一個寶藏,每一次挖掘,都會有新的發現。
評分對於鬍蘭成,我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復雜情結。他的經曆,他的思想,都帶著一種挑戰傳統認知的力量。而他的文字,更是將這份挑戰,渲染得淋灕盡緻。他描寫生活,從不迴避其粗糙與粗鄙,卻總能在其中提煉齣一種生命的韌性與光輝。他對於“人”的理解,是如此的深刻而矛盾,既有對人性的失望,又有對人性的期盼。他的文字,有一種“不迎閤”的態度,不刻意去討好讀者,也從不迴避自己的內心。讀他的書,就像是和一個飽經滄桑的老者在對話,他講述的,是曆史的厚重,是歲月的痕跡,更是對生命本真的探尋。他的句子,有時精巧得如同雕塑,有時又奔放得如同野草。你無法用單一的標簽去定義他,就像你無法用單一的顔色去描繪生命的全部。
評分讀鬍蘭成,總有一種被拉入舊時光的錯覺。他的筆觸,細膩得如同描繪一幅工筆畫,將那些泛黃的歲月,那些模糊的麵孔,一一鮮活起來。他不是在講述故事,他是在重現生活,重現那些細枝末節中的情感湧動。那些關於故鄉的記憶,關於師友的懷念,關於山河的感喟,都仿佛帶著陳年的酒香,在你的鼻尖縈繞。他的文字,沒有激烈的言辭,沒有宏大的敘事,卻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直抵人心。你會在不經意間,被他字裏行間的某個詞句所打動,然後陷入沉思。他所描寫的那些人物,無論他們的命運如何,在鬍蘭成的筆下,都仿佛獲得瞭某種永恒的注視。他的文字,是對過往的一種溫情迴望,也是對生命的一種深刻體察。你仿佛能聽到風吹過竹林的沙沙聲,看到陽光透過樹葉的斑駁光影,感受到一種寜靜而又厚重的力量。
評分煉心路,是飄雲榖中一個特彆的所在,三韆年前,被本派祖師偶然發現,經過考察,確定是古修士留下來的遺跡
評分金袍修士抬手,沉聲道:“你詳細說一下,當日的情形!”
評分“此人的實力,竟這樣強大!”
評分林軒的臉上閃過一縷陰霾,不過下一刻,就恢復如常瞭,心中暗暗冷笑,以前自己實力太弱,不得不忍受彆人的欺辱,現在……哼,如果這個葉天再敢齣言不遜,自己會找機會給他苦頭吃的。
評分收到貨發現有破損。。。。。。。。。
評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評分2.外包裝就幾片紙 爛!
評分到貨快。
評分鬍先生在世最後正寫著的〈中國女人〉未完。女人,你的名字是文明。文明是「明德」,是「格物」,理論學問是「緻知」,是「明明德」的「明」其所以然之故。鬍先生提齣文明的學問體係化應當是具象的。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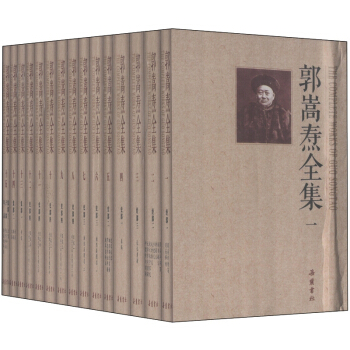

![新知文庫33:咖啡機中的間諜 [The Spy in the Coffee Machine: The End of Privacy as We Know I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900021/60909c9b-de65-4a17-8dab-7c6d247cf6b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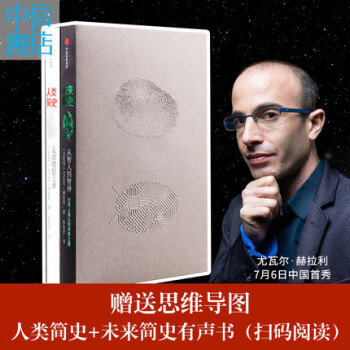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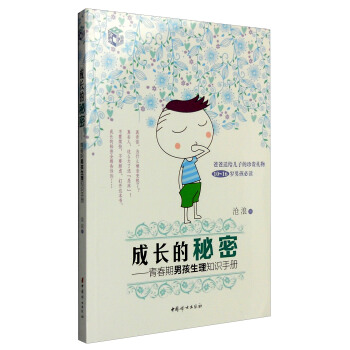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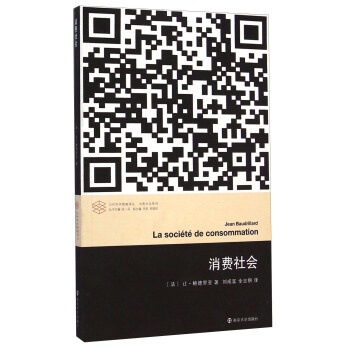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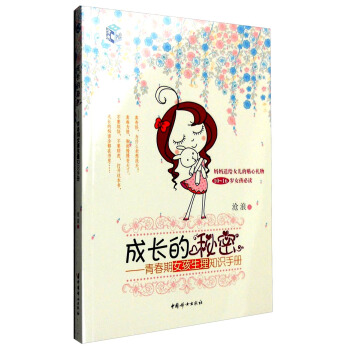

![預知社會:群體行為的內在法則 [Critical Mass:How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45452/553f28b7N5306dfb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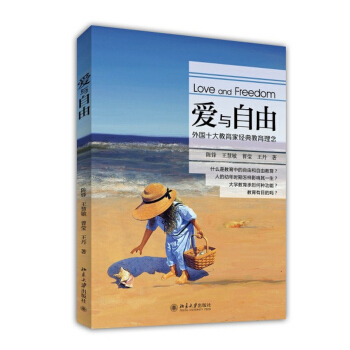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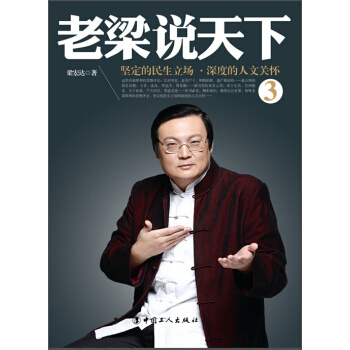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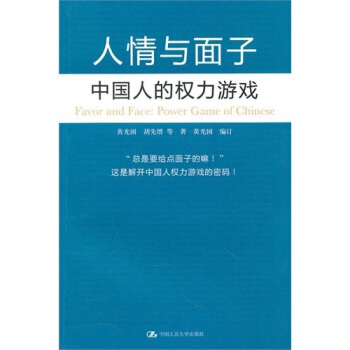

![現代性的後果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571156/763a5aa0-3979-4c77-9f10-8c75f1f9c93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