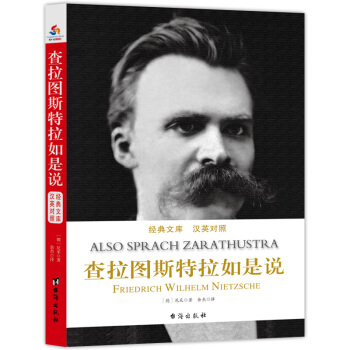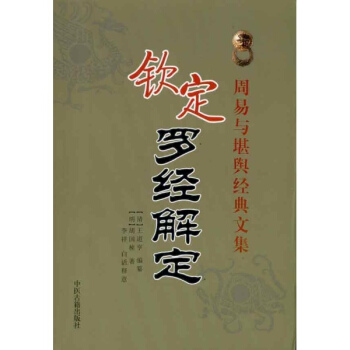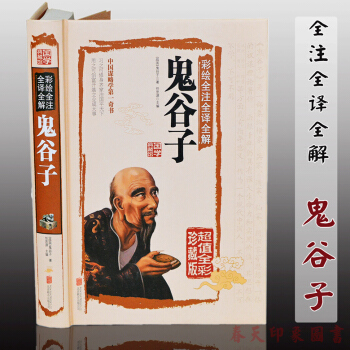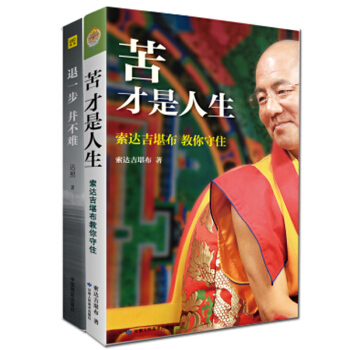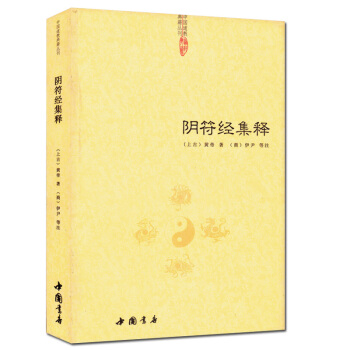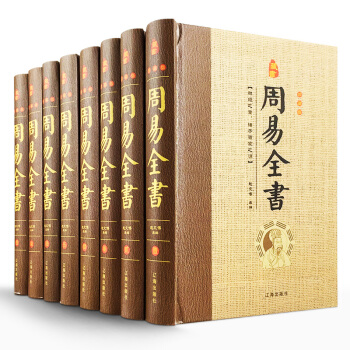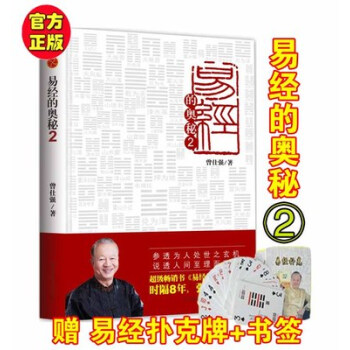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理”为义理之意,理学就是以阐述和发挥传统儒家典籍义理为主的学问,是相对汉唐的注疏之学而言的。理学的诞生经历了从唐代中期至北宋中期近300年的理论铺垫和发酵。理学家们大都出入佛老多年而后返回六经,不可避免有佛道的烙印。
内页插图
目录
引言 理学不是假道学一 时代背景:内忧外困
1 汉注唐疏遭厌弃
2 儒门淡泊归释氏
3 文人自由天下平
4 书院学风浓
二 理学的产生:“儒佛结婚的新学派”
1 理学的前奏:中唐儒学的复兴
2 理学的奠定:宋初三先生
3 理学初成:理学的第一个春天
三 理学的繁荣与发展:百舸争流,命运不
1 三足鼎立:理学的夏天
2 一统江湖:理学的冬天
3 破心中贼:理学的又一个春天
四 理学的式微:无可奈何花落去
1 理学遭清算
2 残酷文字狱
3 倾情考据学
……
精彩书摘
张九成率先以心为本体构建了心学体系,他的“心即天”与心学的标志“心即理”具有同等意义,但他一直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总让人觉得好像隔着什么。捅破窗户纸的是陆九渊。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自号存斋,江西抚州人。他少年老成,三四岁时就问父亲“天地何所穷际”,父亲见他年幼,便笑笑没有回答。谁知他竟为此废寝忘食,沉思不已。13岁时听了古人对“宇宙”的解释“四方上下日宇,往古来今日宙”之后,立刻大悟:“原来宇宙是无穷的!人和天地万物原来都生活在无穷之中。”于是写下了“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进而得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结论。这一结论成为他全部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乾道八年(1172年),他进士及第,主考官就是吕祖谦。陆九渊对吕祖谦的学问很佩服,二人可谓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京师,他与众人谈学论道,数日不休息,也不感到疲倦。他做过几任地方官,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学术上。因长期在象山讲学,故人称象山先生。卒谥文安。有《陆九渊集》传世。其兄陆九龄,号梭山先生,学问也很有名,与之并称“江西二陆”。既然“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那么宇宙之理(天理)就不是在我心之外独立的存在了,而就是我心,所谓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二者是一不是二。格物穷理其实就是格心。这里的心是指具足一切的道德本心,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只要发明本心就行了。就如孟子所说,人心本善,但欲望蒙蔽了一切。打个比方,人心好比一面镜子,光可照人,但是不幸蒙上了一层污垢。要想发挥镜子的作用,只要不停擦拭去掉污垢即可。发明本心也是这样。只要时时涵养省察,摒除各种贪欲,道德本心自然会呈现,陆九渊称这是“剥落”的功夫。因为人人都有这纯善的道德本心,所以人人皆可成为圣人,关键就看他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本心,即良心发现,并应用到行动中。
因为我心就是天理,天理就在我心,所以陆九渊反对像二程那样格物穷理,更反对读书时寻章摘句,他主张读书前要先认真思考:人生天地之间,该做一个怎样的人。想好了再去读书,就会读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读书时要抓住文章“血脉”,即大旨、纲要,不要被章句训诂这些细枝末节绊住。在给学生讲课时,他也反对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细究,而是要求学生从宏观把握。这就是他的“易简工夫”。他反对著述,他本人也述而不作,留下来的只有学生的听课记录。正因为他强调先学做人再读书明理,所以后人将其学说概括为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他直接以“心即理,理即心,至当归一,精一无二”立论,直截明快,在当时影响很大,与朱熹学说相抗衡,所以被学术界认为是心学的创始人。
陆九渊中进士后返回家乡,途经富阳,遇到了主簿杨简。二人本就熟识,因为杨简的父亲杨庭显学识渊博,在当时很有声望。陆九渊只比杨简大两岁,却与杨庭显成为忘年交。杨简(1141~1226年),字敬仲,慈溪人,人称慈湖先生。卒谥文元。有《易传》、《诗传》、《慈湖遗书》,《先圣大训》等传世。陆九渊在富阳住了半个月,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两人交谈至半夜,其间陆九渊多次谈到“本心”二字,杨简便问:“到底什么是本心?”陆九渊在白天正好旁听到杨简断了一个扇子纠纷案,便借此回答:“那起扇子纠纷案中的两个当事人,必有一是一非,你能断得是非分明,这就是本心啊。”杨简有如醍醐灌顶,忙接着问:“就只是这个吗?”陆九渊厉声反问:“难道还有别的吗?”杨简经一夜思考,第二天见到陆九渊俯身便拜,正式以师礼对待,成为陆九渊的入室弟子。
……
用户评价
说实话,我并不是科班出身,我阅读这类书籍更多是为了拓展自己的精神疆界,而非为了学术发表。因此,对我来说,作者的文笔是否流畅、叙事是否引人入胜,是决定阅读体验的关键。我发现这本书在保持学术深度的同时,在叙事节奏上把握得相当出色。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的教科书式堆砌文献,而是更像一位学识渊博的智者,循循善诱地引导你进入一个复杂的思想世界。他处理“式微”的部分也很有节制,没有一味地批判,而是着重分析了外部环境(如政治变动、西方思潮的冲击)对这套体系产生的结构性影响。这种客观而略带惋惜的口吻,使得整本书的情感基调非常成熟和沉稳,读起来有一种“大音希声”的韵味,让人回味悠长,而不是读完就忘。
评分这本书的体量相当可观,但阅读体验却出乎意料地充实。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心学”与“道学”之间张力关系的梳理。在我过去有限的认知中,这两派似乎总是在对立面,但通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一种更微妙的继承与分流。作者巧妙地利用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论述片段,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场域,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在继承孔孟老庄的基础上,为不同的人生困境提供应对方案的。特别是关于“良知”的探讨,不同学派的阐释差异,被描绘得犹如山涧的分岔,既相互关联,又各有独立的水源。这种对思想内部复杂性的精确描绘,极大地满足了我作为一个求知者的好奇心,让我明白,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流派,其内部都充满了活泼的争论与自我更新的动力。
评分这部书的标题里“华夏文库”和“儒学书系”的组合,立刻就给人一种庄重、严谨的学术气息。我原本是抱着一种研究者的心态去翻阅的,期待能看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脉络中儒家思想演变的宏观梳理。然而,当真正沉浸其中时,我发现作者的笔触远比我想象的要细腻和深入。他似乎没有满足于停留在对重要历史节点的简单罗列,而是力图去剖析那些看似抽象的哲学概念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的。特别是对于宋明理学的讨论,那种将“天理”与“人欲”的辩证关系置于时代背景下考察的视角,让人耳目一新。我特别留意了作者是如何处理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比如程颐和朱熹在某些细微之处的差异——他没有简单地裁决谁对谁错,而是展示了思想的动态演变过程,这比单纯的知识灌输要耐人寻味得多。那种穿透历史迷雾,试图把握思想本质的努力,让人感觉自己仿佛真的参与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哲学对话。
评分我是一个对明清思想史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最初被“理性的高扬”这个副标题所吸引。我总觉得,在传统儒学给人留下的印象中,似乎“情感”和“伦理规范”的权重更高一些,而“理性”的探讨往往被留给了后世的西方哲学。这本书,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正是试图修正这种片面的认知。它细致地勾勒出宋代士大夫们如何将内省和逻辑推理运用到对宇宙本源和道德实践的探求中去,那种对“格物致知”的孜孜不倦,简直可以媲美同期欧洲的科学探索精神。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描述那些复杂的思辨过程时,所采用的类比和实例,它们成功地将原本晦涩难懂的哲学思辨,转化成了可以被现代人理解的思维模型。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中国哲学并非只有道德训诫”这一点有了更坚实的依据,这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传统文化复杂性的认识。
评分作为一名对历史变迁颇有感触的读者,我更关注思想如何介入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这本书在论述理学如何从哲学思辨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实践时,展现了惊人的洞察力。它不仅仅是介绍了几条理论,而是深入剖析了这些理论是如何被“制度化”和“普及化”的。例如,作者对于理学在科举制度中的渗透,以及它如何重塑了士大夫阶层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感,有着非常精到的分析。这种将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使得“理性的高扬”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实实在在地塑造了数百年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读完后,我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为何会形成那种独特的权力结构和文化氛围,有了一种更坚实、更具逻辑性的解释框架。
评分中州古籍出版社编的这一套书不错,质量挺高。喜欢
评分中州古籍出版社编的这一套书不错,质量挺高。喜欢
评分中州古籍出版社编的这一套书不错,质量挺高。喜欢
评分中州古籍出版社编的这一套书不错,质量挺高。喜欢
评分中州古籍出版社编的这一套书不错,质量挺高。喜欢
评分中州古籍出版社编的这一套书不错,质量挺高。喜欢
评分好书,值得收藏。
评分中州古籍出版社编的这一套书不错,质量挺高。喜欢
评分中州古籍出版社编的这一套书不错,质量挺高。喜欢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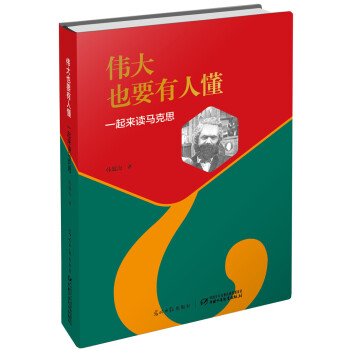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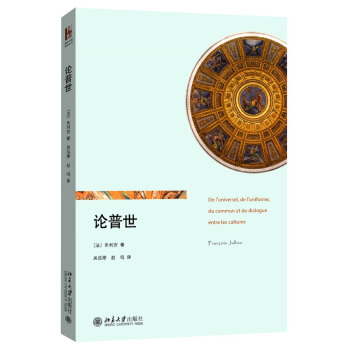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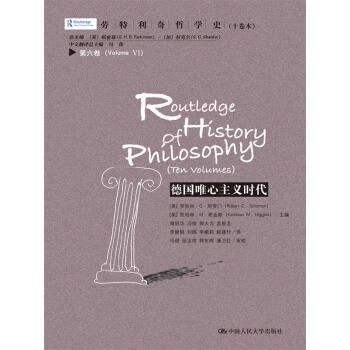


![柏拉图全集[增订版] 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37226/58c786e1Na1a35d7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