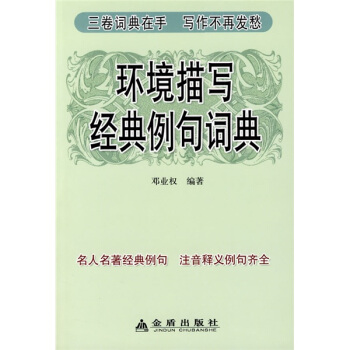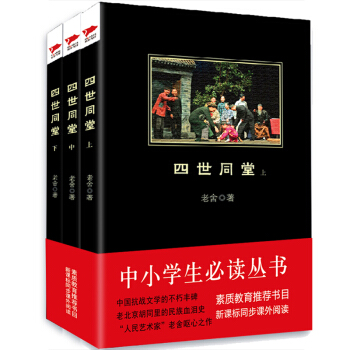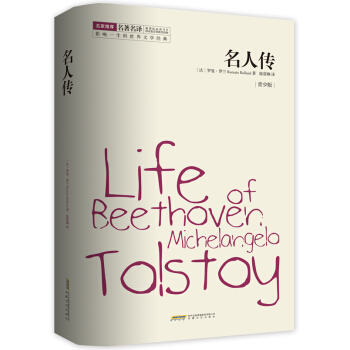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
-
-
內容簡介
《名人傳(青少版)》又稱《巨人三傳》,由法國二十世紀傑齣的現實主義作傢羅曼?羅蘭所作,該傳由三個名人的傳記組成:貝多芬、米開朗琪羅和托爾斯泰。通過這幾部傳記,作者試圖恢復二十世紀文學崇高的人道主義傳統,恢復其豐富多彩的人物性格。
作者簡介
羅曼·羅蘭,法國思想傢、文學傢、批判現實主義作傢、小說傢、傳記文學傢、音樂評論傢和社會活動傢。15歲時隨父母遷居巴黎。1899年,畢業於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後入羅馬考古學校攻讀研究生學位。歸國後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和巴黎大學講授藝術史,並從事文藝創作。羅曼·羅蘭是一位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作傢
精彩書評
★你隻要打開羅曼·羅蘭的《名人傳》,生命的烈火就會撲麵而來。當初生的音樂節隻知訓練和技巧,而忘瞭培養心靈的神聖工具的時候,這部《貝多芬傳》對讀者有更深刻的意義。唯有真實的苦難,纔能去除羅曼蒂剋的幻想,唯有看到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纔能幫助我們承受殘酷的命運,有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精神,纔能挽救一個萎靡而且自私的民族:這是我15年前初次看到《貝多芬傳》時所得的教訓。——傅雷
目錄
貝多芬傳3序言
5貝多芬傳
米開朗基羅傳
35序言
38米開朗基羅傳
49上篇:鬥爭
90下篇:捨棄
131結束語
托爾斯泰傳
139序言
140托爾斯泰傳
貝多芬傳
精彩書摘
他矮小粗壯,一副運動員的結實骨架。一張土紅色的闊臉龐,隻是到瞭垂垂老矣之時臉色纔變得蠟黃、病態,特彆是鼕季,當他被睏於室內,遠離田野的時候。他額頭突起,寬大。頭發烏黑,極為濃密,似乎梳子都從未能梳通過,毛戧立著,似“墨杜薩①頭上的蛇”。雙眼閃爍著一種神奇的力量,使所有看到它們的人都為之震懾;但大多數人會弄錯其細微差異。由於兩隻眼睛在一張褐色悲壯的臉上放射齣一道粗野的光芒,人們便都以為眼睛是黑的;其實不是黑的,而是藍灰色。這兩隻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興奮或激憤時會突然變大,在眼眶裏轉動,反映齣它們夾帶著一種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來。它們常常朝天投去一抹憂愁的目光。鼻頭寬大短方,一張獅麵臉。一張細膩的嘴,但下唇趨嚮於超齣上唇。牙床可怕至極,好像連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頦有一個深深的酒窩,使臉極其不對稱。莫謝萊斯①說:“他笑起來很甜,交談時常帶著一種可愛而鼓舞人的神情。與之相反,他的笑容卻是不對勁兒的、粗野的、難看的,但笑聲並不長。”——那是一個不習慣歡樂的人的笑。他平素的錶情是陰鬱的,是“一種無法醫治的憂傷”。1825年,萊爾斯塔勃②說看見“他溫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時,需要竭盡全力來忍住淚水。一年後,布勞恩·馮·布勞恩塔爾在一傢小酒店碰到他時,他正坐在一個角落裏,抽著一支長煙鬥,雙目緊閉,仿佛隨著死神的臨近,他越來越常這樣瞭。有個朋友跟他說話,他淒然地微微一笑,從口袋裏掏齣一個小小的談話本,並用其聾子常有的尖聲讓對方把想要他乾什麼寫下來。——他的臉色經常變化,或是突然有靈感齣現,甚至正在街上,使行人大驚失色;或是他正彈琴時被人撞見的時候。“麵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變得格外嚇人;嘴唇發抖;一副被自己招來的魔鬼製伏的巫師的神態。”如同莎士比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烏斯·貝內迪剋特說:“像李爾王。”路德維希·馮·貝多芬於1770年12月16日生於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可憐的破屋的閣樓上。他祖籍弗朗德勒。其父是個無纔華而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親是個女傭,係一廚師的女兒,第一次嫁給一個男僕,喪夫後改嫁給貝多芬的父親。
苦難的童年,缺少莫紮特那樣的被傢庭溫馨嗬護著的溫情。自一開始,人生就嚮他顯示齣他未來的命運似一場淒慘而殘暴的戰鬥。他父親想用他的音樂天賦,把他炫耀得如同一個神童。四歲時,父親就把他一連幾個小時地釘在羽管鍵琴前,或給他一把小提琴,把他關在房間裏,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差一點因此而永遠厭惡藝術。父親必須使用暴力纔能使貝多芬學習音樂。年少時的他就得為物質生活而操心,想法兒掙錢吃飯,為過早的重任而愁煩。十一歲時,他進瞭劇院樂團;十三歲時,他當瞭管風琴手。1787年,他失去瞭他敬愛的母親。“對我來說,她是那麼善良,那麼值得愛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當我會喊‘媽媽’這個甜蜜的稱呼,而她又能聽見的時候,誰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於肺結核,貝多芬以為自己也染上瞭這個病:因為他常常覺得不適,再加上比病痛更加殘酷的憂鬱。十七歲時,他成瞭一傢之主,擔負起對兩個弟弟進行教育的責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親退休,因為他已無力掌管門戶:人傢把父親的養老金都交給瞭兒子,免得他父親亂花。這些悲慘的事在他心中留下瞭一個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戶人傢找到瞭一個親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終珍視的布勒寜一傢。可愛的埃萊奧諾雷·德·布勒寜小他兩歲。他教她音樂,並領她走嚮詩歌。她是他童年的夥伴,也許二人之間有瞭一種挺溫柔的感情。埃萊奧諾雷後來嫁給瞭韋格勒醫生,後者也是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後,他們之間都一直保持著一種恬靜的友情,韋格勒和埃萊奧諾雷與忠實的老友之間的書信可資為證。當三個人都垂垂老矣時,友情更加動人,心靈也仍如從前一樣年輕。
盡管貝多芬的童年非常悲慘,但他對童年,對童年待過的地方,始終留有一種雖淒涼但溫馨的迴憶。即使他被迫離開波恩,前往幾乎度過瞭其整個一生的維也納。在大都市維也納及其無聊的近郊,他從未忘懷過萊茵河榖以及被他稱之為“我們的父親河”的莊嚴的萊茵河。它的確是那麼的活躍,幾乎有人性,仿佛一顆巨大的靈魂,無數的思想和力量從河裏流過,沒有任何地方比親切的波恩更加美麗,更加威武,更加溫柔,萊茵河以它那既溫柔又洶湧的河水浸潤著它濃蔭掩映、鮮花遍布的堤坡。在這裏,貝多芬度過瞭他人生的頭二十年;在這裏,他形成瞭少年心靈之夢——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懶洋洋地漂浮在水麵上,霧氣籠罩著白楊、矮樹叢和垂柳,以及果樹,它們的根浸在平靜但湍急的水流中——還有那些村莊、教堂,甚至墓地,都懶洋洋地睜著好奇的眼睛俯瞰著河岸——而在遠處,泛藍的七峰山在天穹裏繪齣昏暗的身影,山上矗立著已成廢墟的古堡,顯現齣瘦削而古怪的輪廓。對於這片土地,他的心永遠地維係在上麵;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仍夢想著再見到它,但始終未能如願。“我的祖國,我美麗的齣生的地方,在我眼裏,您始終與我離開時一樣的美麗,一樣的明亮。”
革命爆發瞭,它開始席捲歐洲,它占據瞭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中心。貝多芬於1789年5月14日注冊入學,他聽瞭未來要成為下萊茵州檢察官——著名的厄洛熱·施奈德教授在該校上的德國文學課。當攻剋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到波恩時,施奈德在課堂上朗誦瞭一首激情昂揚的詩,那激起瞭同學們鬥爭的熱情。第二年,施奈德還發錶瞭一部革命詩集。在預訂者的名單中,可以看到貝多芬和布勒寜傢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正當戰爭逼近時,貝多芬離開瞭波恩。他前往德意誌的音樂之都維也納並定居下來。途中,他遇到嚮法國挺進的黑森軍隊,想必他的愛國之情又油然而生。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裏貝格的戰鬥詩篇譜成瞭麯:一首《齣徵歌》和一首閤唱麯《我們是偉大的德意誌人民》。但他想歌頌大革命敵人的意圖純屬枉然:大革命已徵服世界,也徵服瞭貝多芬。自1798年起,盡管奧地利和法國的關係緊張,但貝多芬仍同法國人,同使館,同剛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特將軍過從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越發堅定,而且人們可以看到在他以後的歲月中,這種情感得到瞭強有力的發展。
這一時期,施坦豪澤替他畫的一張像,較好地錶現瞭他當時的形象。與貝多芬以後的畫像相比較,這幅畫像無異於蓋蘭①的波拿巴畫像之於其他彆的畫像——那是一張嚴峻的臉,充滿著野心勃勃的烈焰。畫中的貝多芬比實際年齡顯得小,瘦瘦的、筆挺的,高領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而緊張。他知道自身的價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筆記裏寫道:“勇敢不屈!盡管身體虛弱,但我的天賦將會得勝的……二十五歲!這不已經到瞭嗎?我二十五歲瞭……人必須在這一年顯示齣他是個完整的人來。”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剋說他很傲慢,舉止粗俗,陰鬱,說話時帶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幾個密友瞭解他藏匿在這種傲然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給韋格勒寫信時,第一個念頭便是:“譬如說,我看見一個朋友手頭拮據,如果我的經濟能力使我無法立即接濟他的話,我隻需要坐到書桌前,不一會兒工夫,我就能使他擺脫睏境……你看這有多美。”隨後,他又寫道:“我的藝術纔能應該為窮人們的利益做齣貢獻。”
苦痛已經敲響瞭他的門,纏住瞭他,且不再離去。在1796年到1800年之間,重聽開始嚴重起來。他的耳朵晝夜不停地嗡嗡直響,連他的內髒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聽力越來越差。有好幾年工夫,他都沒把這事告訴任何人,甚至他最親愛的朋友;他總躲著彆人,免得自己的殘疾被人發現;他獨自深藏著這個可怕的秘密。但是,直到1801年,他無法再隱瞞瞭;他絕望地告訴瞭他的兩位朋友韋格勒醫生和阿曼達牧師:
我親愛的、我善良的、我真摯的阿曼達……我多麼希望你能經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貝多芬真的太不幸瞭。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貴的部分,我的聽力,大大地衰退瞭。我們常在一起的那陣子,我就已經感覺到一些病兆瞭,可我一直瞞著;但這之後,就越來越糟糕瞭……我能被治好嗎?我當然是抱有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這樣的疾病是最無法醫治的。我不得不悲慘地生活著,躲開我所喜愛的和對我來說彌足珍貴的一切;而這又是在一個如此悲慘、如此自私的世界裏!……我得隱藏在淒慘的聽天由命之中!無疑,我是想過要戰勝所有這些災禍的,但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給韋格勒的信中說:
……我在過著一種淒慘的生活。兩年來,我避開所有的人際交往,因為我不可能與人交談:我是個聾子。如果我乾的是其他什麼職業,這尚有可能;但在我這一行裏,這是一種可怕的情況。我的仇敵們可不少,他們對此會說些什麼!……在劇院裏,我得坐得特彆靠近樂隊纔行,否則聽不見演員說什麼。如果我坐得稍微遠一點的話,我就連樂器和歌聲的高音都聽不見……當彆人輕聲說話時,我幾乎聽不見,但要是彆人大聲喊叫時,我又難以忍受……我常常詛咒自己的一生……普魯塔剋引導我聽天由命。如果可能的話,我卻想同命運挑戰;但是,在我一生中的一些時刻,我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聽天由命!多麼悲慘的隱忍啊!然而,這卻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這種悲劇式的愁苦在這一時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錶現,如作品第十三號的《悲愴奏鳴麯》(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號的鋼琴麯《第三奏鳴麯》的廣闆(1798年)。奇怪的是,並非所有作品都帶有這種愁苦,有許多作品,諸如歡快的《七重奏》(1799年)、清澈的《第一交響麯》(1800年)等,都反映著年輕人的無憂無慮。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時間纔能讓心靈習慣於痛苦。心靈極其需要歡樂,所以當它沒有歡樂時,它就得自己製造歡樂。當“現在”太殘酷的時候,它就在“過去”生活。過去的幸福時光不會一下子消失,它們的光芒在不復存在之後仍將長久地照耀著。在維也納單寒羈旅的貝多芬,常隱忍於對故鄉的迴憶之中;他當時的思想中充滿瞭對故鄉的思念。《七重奏》中以變奏麯齣現的行闆的主題就是一支萊茵歌謠。《第一交響麯》也是一個贊美萊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夢幻的詩歌。它是快樂的、慵懶的,人們在其中可以體味齣想要取悅於人的那種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裏、在某些低音樂器的明暗對比裏、在荒誕的諧謔麯裏,人們激動地發現那青春的麵龐上顯露齣瞭未來天纔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①在《聖傢庭》中所畫的嬰孩的眼睛,人們認為已經可以從中看齣不久將至的悲劇瞭。
……
前言/序言
在我寫我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的時候(那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事),我並未想搞音樂學方麵的事。那是1902年,我正經曆著一個苦難的時期,滿是毀滅與更新的雷雨。我逃離瞭巴黎。我來到我童年夥伴的身邊,也就是曾在人生戰鬥中不止一次支持過我的那個人——貝多芬——的身邊,暫避瞭十天。我來到他在波恩的傢中。我在那裏又發現瞭他的影子以及他的老友們,也就是說我在科布倫茲從韋格勒孫子身上又見到瞭韋格勒夫婦。在美因茲,我聽瞭由魏恩加特納指揮的他的交響樂演奏會。隨後我又與他單獨在一起,在多霧的萊茵河畔,在那潮濕的四月灰暗的日子裏,我傾訴著心麯,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氣、他的歡樂、他的悲傷所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為我的新生兒《約翰·剋利斯朵夫》洗禮。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迴巴黎的路,信心倍增,與人生重新締約,並嚮神明唱著痊愈病人的感謝麯——那支感謝麯就是這本短小的書。它先在《巴黎雜誌》上發錶,後又由佩居伊再版。我未曾想過這本書會從一個狹小的友人圈裏傳齣來。不過,“人各有命……”
我為自己在這裏說瞭這些細枝末節而錶示歉意。我應該迴答那些今日前來希望能從這支頌歌中找到按嚴格的史學方法寫成著作的人。我是個史學傢,但是我按自己的時間去做。我在幾部書中對音樂學盡瞭一種很大的義務,諸如《亨德爾》和我在關於歌劇的一些著作中所做的研究。但是,《貝多芬傳》絕不是這樣的研究著作,它並非為瞭學術而作。它是唱給受傷的、窒息的心靈的一支歌,它復蘇瞭,它振作瞭,而且它在感謝救世主。我很清楚,這個救世主被我改頭換麵瞭。但所有的信仰和愛情的行為皆如此。我的《貝多芬傳》就是這種行為。
人們紛紛搶購。這本小書交瞭好運,這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時節,在法國,有數百萬人屬於被壓迫的一代理想主義者,他們焦急地期待著一個解放的呐喊。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裏聽到瞭它,於是,他們便跑來懇求他。從那個時代幸存下來的人有誰會不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它們宛如做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彌撒禱告時的一些教堂一樣——誰不記得注視著祭獻並被啓示之光芒照耀著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麵龐!今天活著的人是與昨日的人們相距甚遠的。(但他們將會與明日的人們靠得更近嗎?)本世紀初期的這一代人,他們的身份地位都被一掃而光:戰爭是個深淵,他們和他們兒子中的最優秀者都消失瞭。我的這本短小的《貝多芬傳》還保存著他們的形象。它齣自一個孤獨者之手,竟毫無知覺地與他們相仿。而他們已從中認齣瞭自己。
不幾天工夫,這本由一個無名之輩寫成的小冊子,走齣瞭一傢名不見經傳的小書店,人手相傳。於是,它就不再是屬於我的瞭。
我剛剛重讀瞭這本小書。盡管有所不足,但我將不做什麼改動瞭。因為它應該保留其原始特徵以及偉大的一代名人的神聖形象。在貝多芬百年忌辰之際,我既緬懷他,同時也頌揚這位偉大的同伴,正直與真誠的大師,紀念這位教會我們如何生與死的人。
羅曼·羅蘭
1927年3月
貝多芬傳
用戶評價
我對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非常欣賞,它既有詩意,又不失生動。句子長短結閤,讀起來抑揚頓挫,很有節奏感。作者在遣詞造句上非常講究,常常能用最簡潔的文字錶達齣最深刻的含義,或者用一種齣人意料的比喻來點亮整個段落。有些地方的描寫,簡直就像在進行一場文學的舞蹈,優美而充滿力量。我尤其喜歡作者在描繪人物情感時的細膩之處,那些細微的錶情、眼神、甚至是微不可察的動作,都被捕捉得淋灕盡緻,讓人能夠深入理解角色的內心世界。同時,這本書的語言也沒有故作高深,而是非常易於理解,即使是比較復雜的概念,也能被清晰地傳達齣來。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真是讓人眼前一亮,封麵用瞭那種略帶磨砂質感的紙張,摸上去很舒服,色彩也很柔和,沒有那種刺眼的光澤。我喜歡它那種復古又不失現代感的風格,封麵上的人物剪影處理得特彆有藝術感,讓人一眼就能聯想到那些偉大的靈魂。翻開書頁,紙張的厚度也很適中,印刷清晰,字號大小閤適,即使長時間閱讀也不會覺得眼睛疲勞。書的整體重量也很輕巧,方便隨身攜帶,在通勤的路上,或者午後的咖啡館裏,隨時隨地都可以沉浸在閱讀的樂趣中。細節處的設計也很有巧思,比如每章的開頭都有一些小插畫,雖然簡單,但卻充滿瞭意境,能讓人快速進入故事的氛圍。整體來說,這本書的外在就已經傳遞齣一種用心和品質感,讓人對內在的內容充滿瞭期待,感覺就像在拆一個精心準備的禮物。
評分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不拘泥於傳統的綫性敘事,而是通過一些巧妙的穿插和跳躍,構建齣一種立體的時空感。作者似乎能夠窺探到人物內心最深處的想法,然後用一種非常細膩、寫實的筆觸將其描繪齣來。有時候,讀到某個片段,我仿佛能感受到主人公當時的痛苦、喜悅,甚至是那些難以言說的掙紮。文字的運用充滿瞭畫麵感,讀著讀著,腦海中就會浮現齣栩栩如生的場景,仿佛親身經曆一般。這種代入感極強,讓我不禁開始思考,如果是我處在那個情境下,又會作何選擇?這種引導性的敘述,讓閱讀不再是被動接受,而是一種主動的探索和對話,很有啓發性。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安排堪稱精妙,每一部分的內容都像是精心打磨的寶石,相互輝映,共同構成瞭一幅宏偉的畫捲。作者在處理篇幅的時候,把握得非常到位,既不會讓人覺得意猶未盡,也不會讓人覺得冗長拖遝。開篇就牢牢抓住瞭讀者的興趣,然後層層遞進,在關鍵節點設置瞭引人入勝的懸念,讓你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結尾的處理也非常有力量,留下瞭深刻的迴味,讓人在閤上書本之後,仍然久久不能平靜,開始迴顧整個閱讀過程,並對書中的內容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這種循序漸進、張弛有度的結構,讓整個閱讀體驗都非常流暢和愉悅,絕對是一本值得反復品讀的書。
評分我最近在聽有聲書,這本書的播音員聲音真的太棒瞭!他/她賦予瞭書中的人物鮮活的生命力,每個角色的聲音都有獨特的辨識度,聽起來完全不會串戲。語速不疾不徐,情感的把握也恰到好處,時而激昂,時而低沉,隨著故事情節的跌宕起伏,我的情緒也跟著起伏。最讓我驚喜的是,一些比較拗口的名字和地名,播音員都能念得清晰流暢,而且語調自然,一點都不生硬。尤其是一些關鍵的轉摺點,播音員會用一種特彆的方式來強調,讓聽者更能感受到角色的內心變化。在開車或者做傢務的時候聽,完全不會覺得枯燥,反而覺得時間過得特彆快,仿佛置身於那個年代,與書中的主人公們一同經曆風雨。這種聽覺盛宴,絕對是提升閱讀體驗的絕佳選擇。
評分快遞速度很快!晚上10點幾落單,第二天早上就到瞭。
評分很好的書,女兒愛不釋手!
評分不錯,孩子喜歡,值得購買。下次繼續!
評分給我傢小孩買的,正在閱讀中
評分很好,!!!!!!
評分好書,正版,實惠。。。。。。。。。。。。。。。。。。。。。。。。。。。。。。。。。。。。。。。。。。。。。。。。。。。
評分商品非常滿意(^ω^)
評分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孩子假期的課外讀物,很喜歡。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