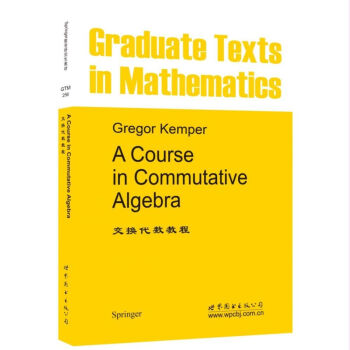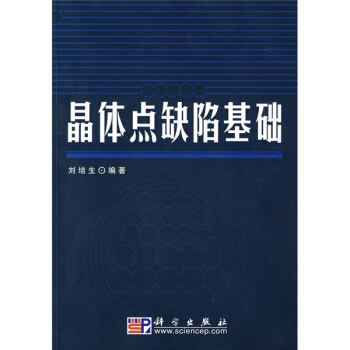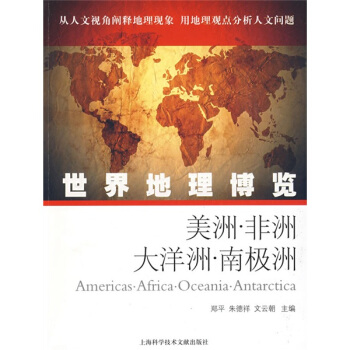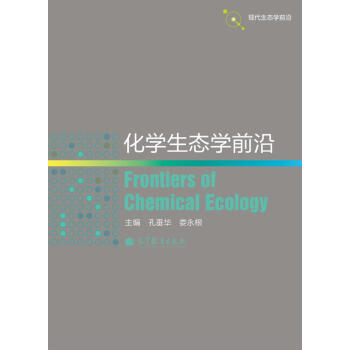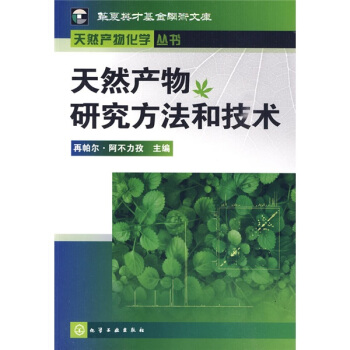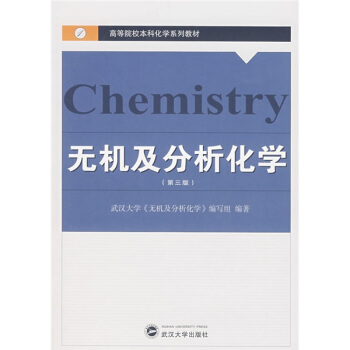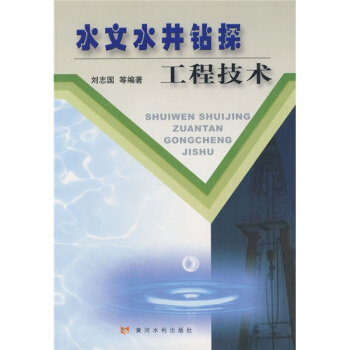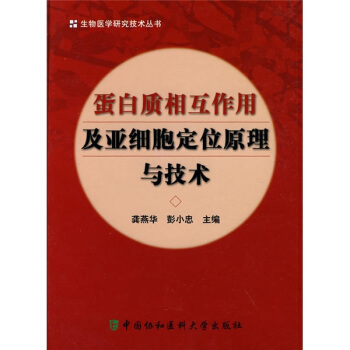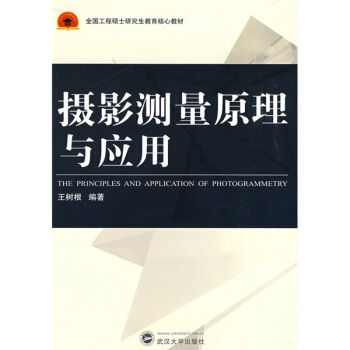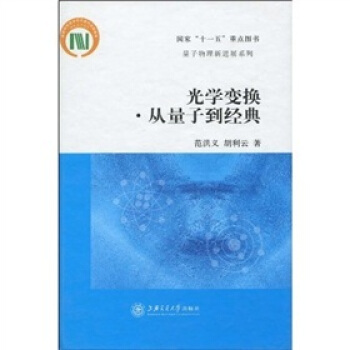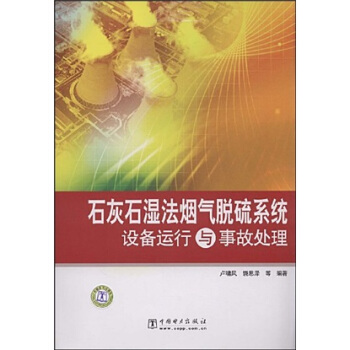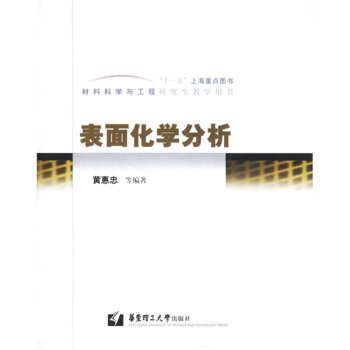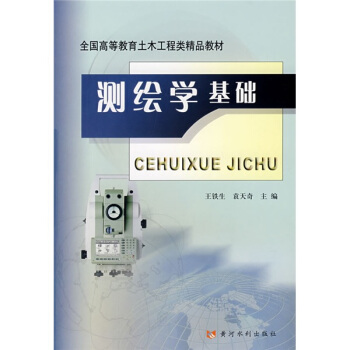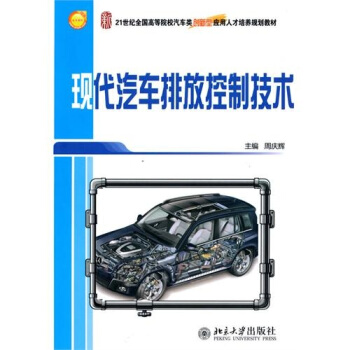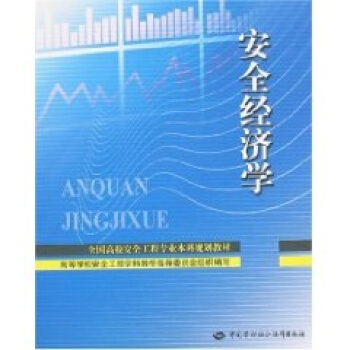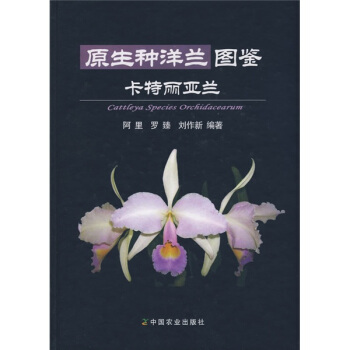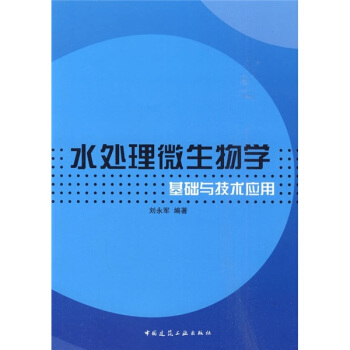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天文学因何而在古代中国出现?古代中国又是什么人在研究天文学?古代中国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天学外史》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多方面解读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外史的角度重新梳理了天学的兴起、发展、衰落。
内容简介
《天学外史》与以往介绍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著作迥然不同。书中多为前人所不欲言,或所不敢言者。作者在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天学置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和世界天文学发展两大背景之下展开论述,内容包括:古代中国帝王出于政治目的而需要天学;古代中国哪些人从事天学活动;官营天学作为王家禁脔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作者又以大量史实论证了:《周髀算经》与印度、希腊天文学的关系;印度、巴比伦天文学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中国与伊斯兰天文学的交流;近代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与思想冲突。作者还讨论了天文学史的方法论问题,讨论了古代中国的宇宙理论,介绍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现存“天学秘籍”,并借助三个引人入胜的个案论述应如何看待古代中国的天学遗产。
《天学外史》系久已被视为作者成名作的《天学真原》一书的姊妹篇,两书内容正可相互补充和印证,但本书适合的阅读对象更为广泛。
作者简介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等80余种,长期在京沪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科研成果及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新华社曾三次为他播发全球通稿。
目录
序
新版前言
引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古代中国什么人需要天学?
第三章 古代中国什么人从事天学?
第四章 官营天学:传统与例外
第五章 天象与天学秘籍(上)
第六章 天象与天学秘籍(下)
第七章 古代中国人的宇宙
第八章 古代天学之中外交流(上)
第九章 古代天学之中外交流(下)
第十章 近代西方天文学之东来(上)
第十一章 近代西方天文学之东来(下)
第十二章 明清之际的东西碰撞
第十三章 中国天学留下的遗产
索引
后记
前言/序言
序
刘兵
科学史理论家,科学传播研究学者,清华大学教授
7 年前,当晓原兄的大作《天学真原》完稿时,曾邀我撰写序言。当时,在斗胆撰写的那篇序言中,针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状况,我曾在很大程度上脱开原书,就有关科学史和历史的辉格解释问题作了一番议论,其实,这一问题与《天学真原》一书的立意倒也关系颇为密切。而《天学真原》一书出版后,确实引起了很好的反响,甚至直到7年后的今日,在众多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专著中,仍别具特色,仍有高度赞扬和激烈批判的书评在次第发表。当然,以晓原兄学问之功力,以及选题视角之新颖,史料之扎实丰富,《天学真原》一书能取得如此成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7 年后,当《天学真原》的姊妹篇《天学外史》写就,即将付梓之时,晓原兄再嘱我为之作序。一方面,虽然仍以为作序既非以我辈之资格宜作之事,亦非可用来畅所欲言之场合,但承晓原兄抬举,加之7 年前已“斗胆”唱过些“反调”,想来即使再撰序言,至多也不过使“罪行”加重一些而已。其次,虽然我于天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是外行,但对于这一领域近来的研究进展,倒是很有关注的兴趣,对于相关的科学编史学问题,也有些想法,于是正好借此作序之机会,再拉杂谈些感想,起码,是讲些实话——尽管“实话实说”现在也还往往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晓原兄这本书取名为《天学外史》。仅从此书名中,就可约略地看出作者的基本倾向:之所以称“天学”,而非“天文学”,不论在以前的《天学真原》一书中,还是在这本《天学外史》题为“ 古代中国什么人需要天学?”的第二章中,作者均有详细的论述,大致说来是为了将中国古代有关“天文”的种种理论,与目前通用的、由西方传入的现代天文学相区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区分,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至于“外史”一词,则明确地表达了作者研究方略的取向。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我曾对科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或者说科学编史学问题做过些研究,因而,对于来自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external history 一词,自各种文章和著作中,也不止一次地用到。国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通常将此词译作“外史”,以对应于internal history(即内史)的概念。记得几年前,在一次与物理学史老前辈戈革先生的交谈中,戈革先生曾提到,这种用法与中国历史上对内史一词原有的用法是不一致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外史”的概念本来是与“正史”相对应,其意义更接近于野史。类似的例子还有像我国科学史界常用的“通史”一词,在中国历史上,通史本是相对于断代史,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与科学史中“学科史”相对来指汇集了各门科学学科的历史,因而,如果考虑到已存在的用法,还是用“综合史”而非
“通史”来与“学科史”对应为好。当然,这已经涉及与科学史相关的近代西方概念在中译时,与中国历史上原有的用语的关系的问题。
正因为存在在概念的翻译和使用上的这种复杂局面,晓原兄在其新作《天学外史》第一章绪论中,专门讨论了他对“外史”这一重要概念的三重理解。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在从事具体科学史研究的科学史工作者中不常见的、结合本人研究实践来讨论科学编史学问题的一篇有特色的文章。
或许,也正是由于晓原兄勤于对有关科学史理论问题的思考,才使他的研究独具特色。《天学外史》一书,在继承了《天学真原》一书原有的良好倾向的基础上,对许多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新探索,提出了许多大胆但又言之有据的论点,包括对许多权威们的观点的挑战。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对于中国古代“天学”的本来性质、功能,以及与我们现在通常所谈的“天文学”,也即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差别的深入讨论。当然,这样的论点很可能会使那些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过分拔高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以极端辉格式的做法试图论证在所有科学学科和重要的科学问题上都是“中国第一”的人们,感到很不舒服。
我这样讲并非没有根据。虽然在本书的绪论中,晓原兄回忆了他1986 年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一次全国科学史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的大会报告,以及在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往事,并认为:“如果说我的上述观点当时还显得非常激进的话,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观点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早已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了。”但我以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就在最近,报刊上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热烈争论就很清楚地表明,像晓原兄的这类观点还是会有许多反对者,甚至激烈的反对者的。
在近来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讨论中,从历史研究的方法上来说,许多持中国古代确有科学者,实际上是对科学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意义视而不见。
科学,这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有不同的所指。在最常见的用法中,所指的就是诞生于欧洲的近代科学。而在其他用法中,或是把技术也包括在内,或者甚至还可以指正确、有效的方法、观念等等,等等。当我们讲比如说中国宋代科学史,或印度古代科学史,或古希腊科学史时,所用的“科学”一词的含义,显然也不是在其最常见的用法中所指的近代科学,尽管古希腊的传统与欧洲近代科学一脉相承,而中国或印度古代的“科学”,却完全是另一码事。而欧洲近代科学的
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种体系化了的对自然界的认识。正像我国早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没有物理学,只有物理学知识。这里之所以用物理学知识,正是指它们不是对自然界体系化了的系统认识。而这当然也并不妨碍我们仍然使用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的说法,来指对于中国古代物理学知识的认识和发展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情况自然也是一样。而《天学真原》以及《天学外史》在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如果我们仍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研究中,突出地使用
“天学”的概念,而不用“天文学”的概念,也正是为回避以相同术语指称不同对象而可能带来的概念混乱。
其实,在有关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的讨论中,许多人之所以极力地论证中国古代就有科学,其根本原因在于某种更深层的动机。例如,有人就曾明确地谈到:“当今相当多的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特别是青年一代,自幼深受科学技术‘欧洲中心论’的教育,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之不
多,甚至很不了解。当务之急是亟待提高认识,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问题,而不是‘大家陶醉’于祖先的成就的问题。”照此看来,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不要说大学的课本,恐怕中国从小学到中学的现行科学课本都得推倒重写,原因显而易见:其中有多少内容是来自中国自己的发现?有
多少内容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如今,我们都在谈论科教兴国,那么,是否依靠那些与近代科学并没有什么联系的中国古代的“科学”,以及建筑在此基础上的民族自信心,就真的可以兴国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对于有关的概念充分明确的话,可以说,中国古代究竟有无科学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至少,对于中国古代有无天文学的问题,《天学外史》(当然也包括以前的《天学真原》)给出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
这里所谈的,其实只是作序者在读了《天学外史》一书文稿后的一点随想而已。《天学外史》所涉及的问题自然远不止这些,在一篇序言中,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地论及所序之书的全部内容。更何况作序者的评价也只能代表本人,对一部作品,真正的评价,还应来自更广泛的读者。一部著作出版后,解读任务就留给了读者。不要说作序者,就连作者本人,也只能听任读者们的评判。但我相信,任何真正有见识的读者,肯定会在此书中发现有价值、有启发性的内容。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包装设计就颇具匠心,低调却不失质感,封面上的图案仿佛诉说着一段悠远的历史,让我对即将翻开的书页充满了好奇。拿到书的那一刻,我就被它沉甸甸的分量所吸引,这不仅仅是纸张的堆叠,更是一种沉甸甸的知识与思考的承载。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扉页,清晰的字体、考究的排版,无不透露出出版方的用心。我是一个对细节比较在意的人,所以书的整体质感,从纸张的触感,到墨水的浓度,再到装订的牢固程度,都是我评判一本好书的重要标准。这本书在这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捧在手里,就能感受到一种踏实的阅读体验,仿佛作者的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醇厚,值得细细品味。我习惯在阅读前先浏览一下目录,这本书的目录结构清晰,划分合理,让我对全书的脉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种条理分明的结构,预示着内容本身也可能同样严谨有序,让我对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有了初步的肯定。虽然我还没开始阅读,但光是这份前期的准备工作,就足以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之旅充满期待。这本书的出现,让我感觉像是邂逅了一位久违的老友,既熟悉又充满新鲜感,迫不及待地想与它展开一场深度的对话。
评分这本书拿在手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重量感,让人觉得沉甸甸的,仿佛捧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或是承载着深邃思想的宝藏。封面设计并非张扬炫目,而是带着一种内敛的光泽,仿佛古老壁画上斑驳的色彩,诉说着一段久远的故事。我是一个非常注重书籍“触感”的读者,纸张的质地、油墨的清晰度、装订的牢固程度,都是我衡量一本好书的重要指标。这款书在这几个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出色,翻动书页时的沙沙声,还有那温润细腻的纸张触感,都让阅读过程变得无比享受。它不像一些现代书籍那样追求视觉上的冲击力,而是更注重传递一种沉静、厚重的阅读体验。我喜欢那种能够让人心无旁骛地沉浸其中,与作者的思想进行一场心灵对话的书籍。这本书的整体风格,就给人一种这样的预感,它邀请我进入一个宁静的空间,在那里,我可以慢慢地咀嚼文字,品味其中的意味。
评分初次拿到这本书,便被它散发出的那股沉静而古朴的气质所吸引。封面设计简约大气,却蕴含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深邃感,仿佛历史的长河在此静静流淌。触感温润的纸张,搭配上清晰隽永的字体,每一次翻动都带来一种纯粹的阅读享受。我尤其欣赏它在细节之处的考究,从书脊的装帧到内页的留白,都透露出一种匠心独运的审美追求。拿到书后,我习惯性地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这里的重量并非指物理上的,更多的是指它所承载的思想分量。这本书的厚度适中,恰到好处,既不会让人望而却步,又足以承载丰富的内容。我喜欢那种能够让人沉浸其中,忘却时间流逝的阅读体验,而这本书,似乎就具备了这样的魔力。翻开扉页,作者的名字和书名跃然纸上,一种对未知知识的渴望油然而生。我通常不会在阅读前做过多的功课,而是更倾向于让书籍本身带领我进入它的世界。这本书,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散发着诱人的光芒,等待着我去探索它所蕴藏的奥秘。
评分这本书的第一眼,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它的封面设计,与其说是“设计”,不如说是“呈现”——一种恰到好处的、不加雕饰的真实感。那种沉静的色彩,搭配着若隐若现的纹理,仿佛是历史的沉淀,又像是深邃思想的具象化。当我拿起这本书时,那种恰到好处的重量感,让我立刻感觉到一种踏实,一种不容置疑的“内容”的厚重。我是一个对书籍细节要求很高的人,纸张的触感,油墨的色泽,字体的排版,甚至是装订的牢固度,都是我考量一本好书的重要标准。这本书在这些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那种能够让我完全沉浸其中,仿佛与作者进行一场灵魂对话的书籍。这本书,在还没有阅读之前,就已经散发出了这样的气质,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之旅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它不像一些书籍那样急于展示自己,而是静静地等待着,仿佛一位智者,邀请我去聆听它要讲述的故事。
评分这本书的包装就给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不是那种快时尚的华丽,而是带着一种沉淀下来的质感。拿到手里,能感觉到它分量很足,让人觉得里面装的东西肯定很实在,不会是那种轻飘飘的文字游戏。封面设计很有品味,不张扬,但仔细看又能发现不少细节,仿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艺术品,让人忍不住想要探究它背后的故事。我是一个比较“老派”的读者,喜欢书本拿在手里的那种真实感,而不是冰冷的电子屏幕。这款书的纸张触感就非常棒,细腻而有韧性,翻页的时候声音也很好听,墨水印在上面非常清晰,一点也不模糊,让人阅读起来眼睛很舒服。我特别喜欢这种印刷质量上乘的书,感觉作者和出版方都对作品倾注了心血。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有料”,而且是用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觉得物有所值,值得慢慢去品味。
评分好
评分很不错,很不错!值得购买!
评分朋友推荐的,一口气买了几本江晓原的书,留着慢慢看
评分朋友推荐的,一口气买了几本江晓原的书,留着慢慢看
评分书的内容还是很可以的,但是这些系列的书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做活动的时候还是值得收藏的!
评分dfhhhhhjjjjjjjjjjjkkkkkkkkkkkkkkk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哈哈
评分网购方便,京东送货真快~~~~~~
评分好书推荐大家有兴趣的看一下
评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