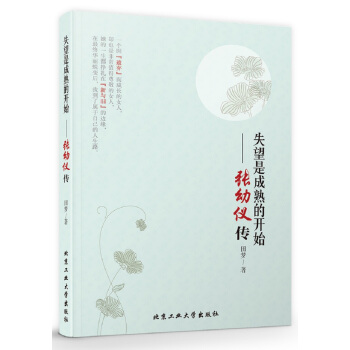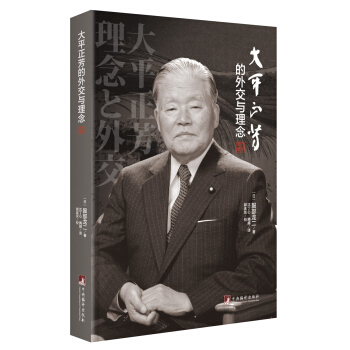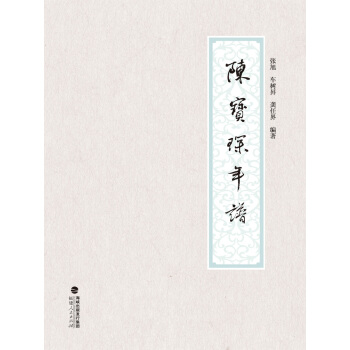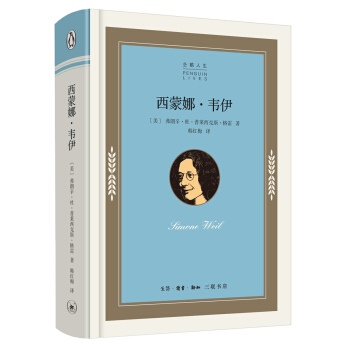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是难以归类的:爱国者,神秘主义者,社会活动家,笃信体力劳动救赎价值的知识分子,渴望感性美的禁欲主义者,向往进入天主教会的世俗犹太家庭的女儿。三十四岁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这本小传不仅追溯了西蒙娜?韦伊在宗教、哲学、政治、社会等方面复杂的思想演变历程,还追溯了她从享有特权的巴黎高师学生到工会组织者、社会活动家、哲学家的转变。她的思想尖锐、率直、坦诚,而作为读者,赞同还是拒斥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在于去碰触这个“有待成熟的”伟大灵魂。
作者简介
弗朗辛?杜?普莱西克斯?格雷(Francine du Plessix Gray),1930年出生,美国作家、批评家。母亲Tatiana Yakoleva是20世纪40年代纽约著名的帽子设计师,父亲Alexander Liberman是时尚杂志的缔造者之一(Liberman是她的继父,她的亲生父亲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二战”早期死于德国人手里)。这对夫妻是40年代纽约时尚界的风云人物。弗朗辛虽然天生丽质且系出名门,却不喜欢名流的生活,从小喜欢读书,研究宗教与哲学。她年轻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进入时尚圈,去过巴黎,为时尚杂志拍过照片,但很快就厌倦这种生活,26岁时嫁给艺术家Cleve Gray,婚后生育两子,并开始大量写书,著有《怒与火》(Rage and Fire)、《情人与暴君》)(Lovers and Tyrants)、《苏维埃妇女》(Soviet Women)、普利策奖入围作品《走近萨德侯爵》(At Home with the Marquis de Sade)等。其描述自己父母生活的传记《他们》(Them: A Memoir of Parents)为她赢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
精彩书评
【作家、批评家、哲学家、神学家眼里的韦伊】
西蒙娜·韦伊去世后的二十年时间里,T. S. 艾略特曾撰文,认为她尽管表现出“几乎超常的谦卑和近乎无礼的傲慢”,却具有“圣人般的天才”。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表示反对:“这位实际上已经去犹太化的犹太女人令人痛苦的声音”使人无法产生希望。
对于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西蒙娜·韦伊站在“深渊的边缘,双脚深陷进去,拒绝像普通民众那样跳过去(她以她自己的集体方式爱着这些民众),她屈从于搭在肩上的一只神圣的手,强烈要求被单独拣选出来”。
美国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写道,她象征着“一个异化时代里教会外的圣人”。
美国非神职神学家多里斯· 格伦巴赫(Doris Grumbach)因为她拒绝了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中介而批评她显示出一种“近于新教徒的骄傲”。
对于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一个狂热投身于我们这个时代zui危险体验的人”西蒙娜·韦伊给我们的zui伟大的礼物是:她保持着“对所有人类体验热情欢迎的态度,zui极端、zui无足轻重、zui连根拔起的体验……她寻求zui多的是使人类摆脱生存的自然孤独状态的一种对生活的世界深情的关注。”
肯尼思·雷克斯罗特(Kenneth Rexroth)谈到《扎根》时,说这是“一堆胡言乱语,只有盲目的爱国者佩吉(Péguy)那种精神错乱的幻想能超过它”,他指责西蒙娜·韦伊“拿印度教和比较神话故弄玄虚,比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虚构还糟”。
爱尔兰历史学家兼批评家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严厉批评西蒙娜·韦伊zui后的著作《扎根》,说这本书鼓励“一种严格、原始而又形式怪异的审查制度,这种制度会使雅克·马里坦因为说了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话误导了他人而受到惩罚”。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写道,韦伊是我们时代文化英雄的典范,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他们“重复、痴迷、无礼,以强迫取胜——不只是通过他们的个人权wei口吻和对知识的热情,还通过对个人困境和知识困境的敏锐意识”。通过韦伊,她继续说,现代读者能“对并非他们自己的,也不可能是他们自己的某种层次的精神事实表示敬意”。桑塔格提示,因为我们未能实现对美德和纯粹的本能追求,所以韦伊担当了代罪羔羊的角色:她比我们任何人都走得更远,站在了我们无人敢企及的高度,她替我们做到了。
阿尔贝·加缪在登上飞机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之前在西蒙娜·韦伊在巴黎的房间里沉思了一个小时。
据说教皇保罗六世把贝纳诺斯、西蒙娜·韦伊和帕斯卡视为影响他学术发展zui重要的三个人。
目录
一 家乡
天才制造厂
大师的弟子
巴黎高师
二 社会
斗争岁月
1931—1934
工厂经历
1934—1935
信仰萌芽
1935—1938
上帝与战争
1938—1939
三 他乡
困难重重
马赛
纽约
伦敦
神秘天父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西蒙娜·韦伊决定进工厂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困境,这对于20 世纪30 年代成年的一代人并不稀奇。就在几年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离开了他在伦敦舒适的家,到巴黎和伦敦体验穷困潦倒的生活。在美国,天主教活动家多丽丝·黛(Dorothy Day)经历了富足不羁的青年时代以后,在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窟永久定居,开始她对穷人的使命。到20 世纪60 年代,更多的美国活动家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实际上,美国人撰写的有关西蒙娜·韦伊的最好的一篇论文是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的那篇,林德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的领袖,他在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西蒙娜·韦伊对这场运动的重大影响。“西蒙娜·韦伊可以被视为……我称之为第一批新左翼的国际探索者中的一员,”他这样写道,“第一批新左翼,也是第三批。”“第一批新左翼由1930—1945 年间的激进主义者组成,这些人脱离了斯大林主义,也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而且,他们不仅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还部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本身……西蒙娜·韦伊预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批新左翼的每一项重大主题。”
西蒙娜· 韦伊在好友活动家苏瓦林的帮助下找到了第一份蓝领工作。工作单位是一家名叫阿尔斯通(Alsthom)的公司,这家公司很大、很有名,由阿尔萨蒂安(Alsatienne)和汤普森(Thompson)两家公司合并而成,生产大型电力机械。那个年代,很少有管理层的人能被说服雇用一个古怪、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兼劳工组织者到流水线工作。但阿尔斯通特别进步而开明的领导者奥古斯特·德特夫(Auguste Detoeuf)似乎对雇用西蒙娜·韦伊这样一位特立独行者的挑战很感兴趣。他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坚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可以融合,工业和古典文化可以融合”。他答应让西蒙娜·韦伊到巴黎一个比较大的工厂上班。工厂位于勒古布街(Rue Lecourbe),在第十五区。那里雇用了大约三百人,制造有轨电车和地铁的电气配件。为了找到一种更适合工厂工作的生活节奏,西蒙娜·韦伊搬出了父母的公寓,在工厂所在的那条街上租了一间很小的工人房,希望完全靠自己挣钱生活,不要父母任何帮助。实际上,随后的一年里,她星期日回家吃晚饭都会把估算的饭钱放到父母的餐桌上,而对于女儿这个习惯,善解人意的韦伊夫妇尽管感觉很痛苦,还是默默忍受了。
西蒙娜·韦伊从1934 年12 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开始到阿尔斯通上班。老板德特夫答应不把她的身份告知其他工人。很多人注意到她的手不是体力劳动者的手,以为她是一个考试不及格的穷学生,到阿尔斯通打工养活自己。他们还注意到她瘦骨嶙峋,而且是车间里唯一一个不带零食的人。他们经常主动把自己的面包或巧克力让给她吃,她通常都拒绝了。她每天写给苏瓦林的信本来是她工厂生活最真实的记录,却在纳粹占领巴黎期间被毁掉了。幸好她自己对后来八个月的生活留下了日记。她的“工厂日记”几乎每天都写,详细记载了她在三个不同工厂工作的悲惨经历:为了那点儿可怜的工资而被安排的任务、她对工人同事的印象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日记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计件工作的卑鄙本质:工厂计件付钱,不按工作时间付钱;完不成定额要从工资里扣钱;工作本身常常危险重重;时间安排不合理,除了十五分钟午餐时间,中间没有休息;只关心定额的工头经常羞辱工人。西蒙娜·韦伊在日记里谈到,她干体力活儿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笨。经常被她称为“雅克定额”(Jacquot)的一个仁慈的工头告诉她,她不像车间里某些工人那么笨,他们把自己弄伤残的时候比她多(应该承认,这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恭维。但鉴于快速生产的持续压力,又没有任何安全措施,西蒙娜·韦伊要避免身体遭殃就得费很大的劲。
……
1935 年,法国的失业率依然徘徊在20%,而她用几周时间就找到了第二份工厂工作,真是不简单。这是在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Billancourt)区的一个比较小的工厂,名叫卡尔诺(Carnaud),专门生产油壶和防毒面具。即使机器设备没那么大,工头也没那么凶,卡尔诺却跟阿尔斯通一样,使人心力交瘁。“一个刑罚机构,” 她这样描述那里,“一个烂机构,烂透了——疯狂加速,割破手指是家常便饭,不断有大批工人下岗……我一次也没见到哪位工人的眼睛离开过工作或与工友说句话。”她对车间里毫无人性的环境这样评价。第一天上班,她被安排到一台做金属零件的冲压机旁,全力以赴才在一小时内做出了四百个零件。但是,那天下午,工头——“一个外表帅气、样子和善的家伙”——过来告诉她,如果她不能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使数量翻番达到八百个,他就解雇她。“你要是能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做出八百个,我也许会同意你留下来。有工人做到一千二呢。”西蒙娜·韦伊怒火中烧,她强迫自己做了六百个,但到快下班时工头告诉她还不够。六点钟,就在打卡下班前,她问工厂经理是否希望她第二天回来。经理告诉她,只要她努力加快速度,就可以回来。
第一天在卡尔诺的工作结束,她走向塞纳河,渴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她坐在岸边,内心沮丧,精疲力竭,内心“充满无奈的愤怒”;假如注定要过这种生活,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每天过河而不跳河”。工厂里一位工友跟她说起自己十三岁的儿子,那些话使她深受触动:“他要是不上学,将来干什么?跟我们这些人一样受苦受难。”
第二天早晨,振作精神在同一台冲压机那里做了六百五十个零件后,西蒙娜·韦伊被安排了另一项任务:高速穿金属薄带,但要小心避免两条带子挨着穿过去。然而她出了错,把两条带子连着穿了。机器被卡住了。工头得修机器,他好像很不高兴。在这种颜面尽失的场合,她回忆道:“一个微笑、一句友好的话、人与人之间的瞬时接触,无不胜过特权圈子里的深情厚谊。”
确实如此,西蒙娜·韦伊在工厂工作的几个月里,她仅有的安慰就是工友们偶尔表达的善意与同情。她特别愿意接受这种表示。“每次我疼得龇牙咧嘴,坐在前面的电焊工都会对我凄然一笑,充满兄弟之爱,这对我胜过千言万语。”“在工厂里……最微不足道的善意,从微微一笑到帮个小忙,都能使你克服疲惫,克服工资的困扰,克服所有的压迫。”“碰上一个坦然微笑的火炉工,在更衣室听到大家讲比以往更有趣的笑话,我就知足……这些兄弟情谊的微小证明带给我极大的快乐,我一时竟忘了疲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人”是她对一个异常友善的工头的评语,那个工头曾关心地看着她赤手把巨大的铁螺栓搬到一个包装箱里。自始至终,她还不断意识到人们对女工表现出来的性别偏见。“男人对女人的不屑,”她在工厂日记里写道,“以及大家讲的黄色笑话在工厂工人中都比在其他人群里要显而易见得多。” “我处在一个双重卑微的地位,”她后来回忆,“消泯我尊严的不仅是那些工头,还有那些工人,只因为我是女人。”
西蒙娜·韦伊在卡尔诺只工作了一个月就下岗了。到目前为止,在两家工厂,她都发现流水线作业对人情感的摧残甚至超过了对其身体的压力。她还发现,这种劳动最令人沮丧的方面是“对工作目的一无所知”。工人们没办法把那些零部件生产与要装配这些零部件的大型机器联系到一起。而那些经常随心所欲的经理的反复无常又导致了一连串的屈辱经历。这种屈辱对西蒙娜·韦伊产生了深刻影响。她后来写下了那年的人生体验:
我几乎要崩溃了……我的勇气,我的自尊,在这段时间里都慢慢碎裂了……清晨,我在痛苦中起床,带着恐惧去工厂;我像奴隶一样工作;中午的短暂休息使我犹如撕裂般痛苦;5 :45回家,就想好好睡一觉……那种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的恐惧,那种焦虑,只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上午才没有。怕的是那种发号施令。此前在社会中形成的个人尊严感荡然无存。
前言/序言
【开篇诗】
那些死去的人们是幸福的,
他们重返苍茫大地,再次成为可塑的泥土。
那些死去的人们是幸福的,
假如他们死于一场正义的战争。
那些成熟的,捆扎起来的麦子,
是幸福的……
那些战死沙场的古人
是幸福的。
那些纯洁的圣器与加冕的国王
是幸福的。
——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
用户评价
这本《企鹅人生书系:西蒙娜·韦伊》简直是知识的宝库,我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才啃完第一遍,现在正准备开始第二轮的精读。这本书的叙事手法非常独特,它不像传统的传记那样平铺直叙地罗列生平事迹,而是更侧重于对韦伊思想核心的深挖和剖析。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那些晦涩难懂的哲学概念,用一种近乎诗意的语言重新组织起来,让一个对韦伊知之甚少的人也能迅速捕捉到她的核心关怀——那种对绝对真理和神圣性的不懈追求。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绘韦伊投身工厂劳动和战争前线的经历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近乎冷峻的客观性,既不过分渲染苦难,也不轻描淡写其对她精神世界的塑造。读到她描述自己如何在痛苦中寻求“失重”状态,我简直能感受到那种灵魂被撕裂又重塑的张力。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记录了一位伟大思想家的生平,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观察现代人精神困境的独特视角,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生活中的“重量”和“轻盈”究竟意味着什么。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和排版我必须单独提一下,作为“企鹅人生书系”的一部分,它保持了该系列一贯的高水准,拿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质感,非常适合反复翻阅。内容方面,这本书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试图将西蒙娜·韦伊“符号化”或“简化”,而是忠实地呈现了她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比如,她既是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持保留态度的知识分子;她对一切权力结构都抱有深刻的怀疑,却又对形而上的绝对秩序抱有近乎狂热的信仰。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手法,将她置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突显出她个人的选择是多么的艰难和不合时宜。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她对“工作尊严”的探讨,这远超出了当时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劳动的肤浅同情,而是一种基于本体论层面的理解和尊重。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思想不是坐在象牙塔里产生的,而是必须在最肮脏、最痛苦的现实中被锻造出来的。
评分说实话,我对西蒙娜·韦伊这个名字以前只停留在一些哲学史的脚注里,总觉得她是一个过于边缘化、难以触及的人物。然而,这本《企鹅人生书系》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这本书的笔触极其细腻,它没有沉溺于将韦伊塑造成一个神圣的圣人,而是非常坦诚地展现了她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挣扎、疾病以及她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疏离感。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她与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子保持距离的描写,那种近乎洁癖的精神追求,让她注定只能独自前行。书中的许多轶事都生动地描绘了她那种近乎偏执的道德自律,比如她坚持用与工人同等的报酬生活,甚至在病重时也拒绝任何形式的特权。这种近乎残酷的自我要求,与其说是哲学实践,不如说是一种生命燃烧的方式。读完后,我不再把她看作一个遥远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试图用生命来检验真理的斗士。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也很有巧思,它常常在回顾生平时插入她当时写下的笔记片段,使得文本的层次感非常丰富,读起来酣畅淋漓。
评分我通常对人物传记类的书籍保持警惕,总担心它们会变成作者的“自我投射”或者过于美化主人公。但《企鹅人生书系:西蒙娜·韦伊》却出乎意料地保持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距离感。作者似乎遵循着一种“呈现而非评判”的原则,将大量的原始材料——信件、日记摘录、访谈记录——精心编排,让韦伊本人通过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与读者进行直接对话。这种间接的叙事方式反而更具力量,因为它迫使读者必须主动去填补那些空白,去构建属于自己的韦伊形象。书中关于她晚年流亡瑞士,在贫病交加中仍坚持为法国抵抗运动撰写分析报告的情节,读来令人心酸却又无比震撼。这本书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它更像是一张地图,指引我们进入一个复杂、充满悖论的精神疆域。它真正做到的,是激发了我们对那个“真理的需要”的深刻共鸣,而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她是谁”。
评分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社会运动和伦理学的人,我一直试图在那些激烈的政治论述中寻找一种纯粹的、不被权力和意识形态污染的道德基石,而这本书仿佛就是一把钥匙,为我开启了那个寻找的过程。作者在阐述韦伊关于“注意力”和“等待”的理论时,采取了一种非常流畅的递进方式,先从她对古希腊悲剧的解读入手,逐步引申到她对政治体制的批判,最后汇聚到她对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探索。这种由表及里、由文化到信仰的梳理,使得原本复杂的话题变得清晰可辨。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描述了韦伊如何将“受苦”视为一种理解他者、抵达真理的必要途径,这与当代社会中普遍逃避痛苦、追求即时满足的主流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偏向于一种冷静的学术探讨,但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对韦伊人格魅力的深深敬意,不会让人感到枯燥,反而会激发读者不断地停下来,合上书本,进行长时间的沉思。
评分企鹅人生书系,值得推荐,传记就是一部个人史。
评分读书日买的,优惠力度还是不够。
评分读书日买的,优惠力度还是不够。
评分一本小册子,一直在收。
评分值得收藏!
评分西蒙娜薇依,我的最爱,必须买
评分一本小册子,一直在收。
评分一本小册子,一直在收。
评分西蒙娜薇依,我的最爱,必须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他缔造了哈佛:查尔斯·W.艾略特传 [Charles W. Eliot,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06319/59e5a268Nf275d01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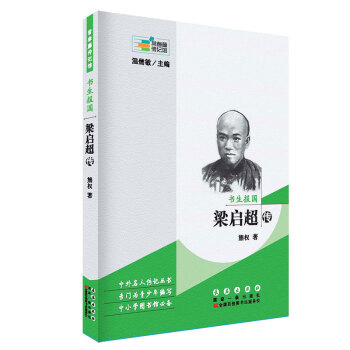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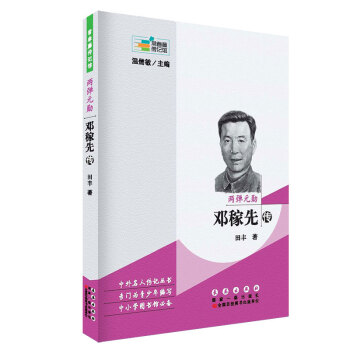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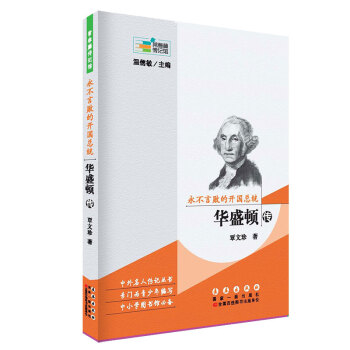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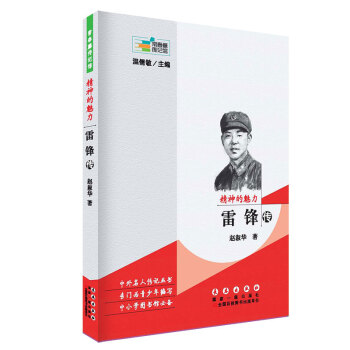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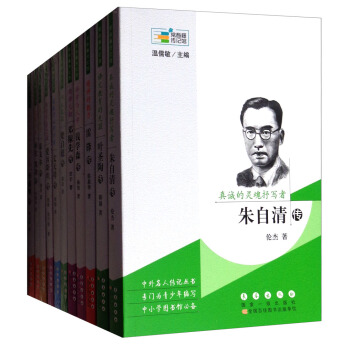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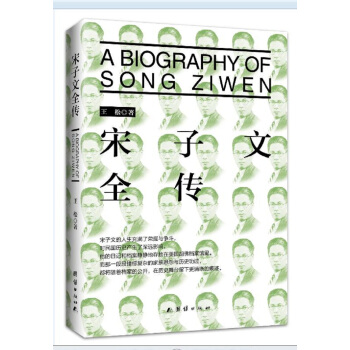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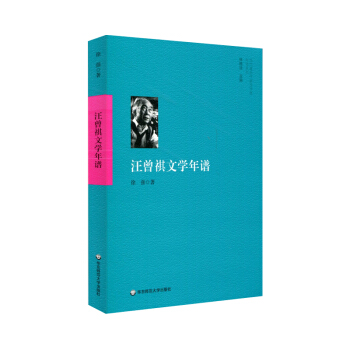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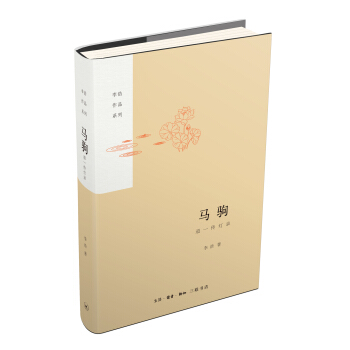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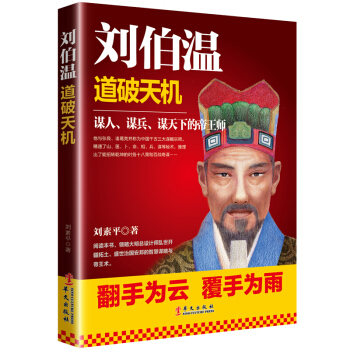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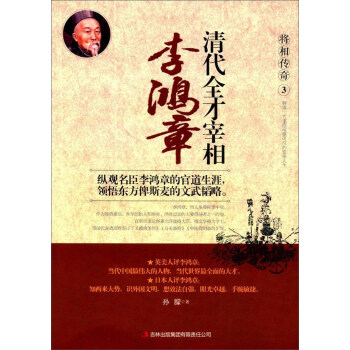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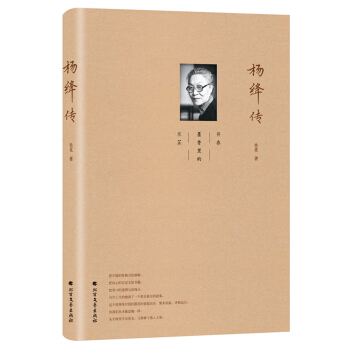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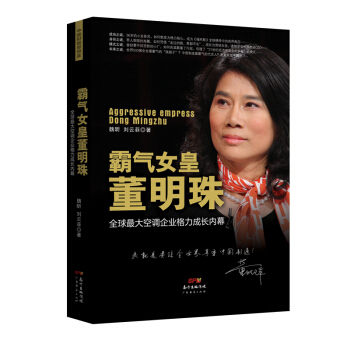
![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套装共2册) [Alan Turing—The Enigm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10115/59e95808N729047f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