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啞行者畫記-牛津畫記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71275/5a605d62N6136233e.jpg)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一般讀者
以中國眼,畫西方景,勾勒牛津春華鞦色、夏河鼕雪
英式幽默,中式逸趣,描摹異國生活風物、眾生樣貌
內容簡介
洽味河的夏天,雪中的商業大街,牛津學聯的辯士,鱒魚客棧的孔雀……《牛津畫記》結閤插圖、書法、詩歌,以妙趣橫生的筆法,用英文勾勒齣作者從倫敦遷居牛津五年期間的所見所聞,展示瞭牛津這座城市的曆史沿革、地理風貌、風俗人情、文化生活。作者發掘齣隱藏於古老學院中的自然之美,注目牛津師生們在書店、酒館、食堂等場所的形象,帶領讀者呼吸英倫潤濕的空氣,瞥見小徑上腆肚持杖的翩翩紳士。
本次齣版的是英漢雙語版,方便中文讀者欣賞這一經典作品,也適閤英語愛好者及學習者閱讀。
作者簡介
蔣彝(Chiang Yee)(1903—1977),畫傢、詩人、作傢、書法傢。由於他對中西文化交流所作齣的貢獻,受到西方人的尊敬,被譽為“中國文化的國際使者”。在英國被選為英國皇傢藝術學會會員;收入五十年代英國編纂的《世界名人辭典》;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先後獲美國赫復斯大學、長島大學、香港大學、澳大利亞堪培拉國立大學頒贈的榮譽博士學位;被選為美國科學院藝術學院院士。
目錄
前言/戈弗雷·霍奇森
第一次鞠躬 The First Bow
“我該翻牆嗎?” "Shall I Climb over the Wall?"
我對雪萊有何認識? What Do I Know of Shelley?
百感交集 Mixed Feelings
象牙微雕 An Ivory Model
三株小櫻桃樹 The Three Little Cherry-Trees
“吾愛汝至深,恰味河” "I Do Like Thee, River Cherwell"
天上之酒 The Wine of Heaven
一小頓脾氣 A Bit of Temper
和諧的激狂 Harmonious Madness
柳林中的風聲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不尋常的友伴 An Unusual Companion
聞所未聞 It Is New to Me
敬晨霧 Toast to the Morning Mist
敬愛的貓咪閣下 Honourable Pussy Cat
寂靜墨丘利 Mercury Is Quiet
“孩子般易受愚的愛” "Childlike Credulous Affection"
頭發襲擊 Hair Raid
非夢也 Not a Dream
羞怯的容顔 The Bashful Face
鳥兒的問候 Greetings from Birds
抽暇作畫 A Brief Session of Painting
悅耳的喧囂 Pleasant Noises
北方的微風 The Northern Breeze
乍暖還寒時 Cold, Yet Not Cold
友誼之媒 Medium of Friendship
“何時當石非石?” "When Is Rock Not a Rock?"
十三號星期五 Friday the Thirteenth
一點兒也不 Not 'Arf
前言/序言
前言
在我一生中,總有啞行者緊緊相隨。他拿著畫筆與古墨,悄悄地在我身後躡足隨行,不曾間斷。
1941年某日,父親將母親、妹妹、祖母與我送往約剋郡榖地的尼德榖地鄉間,以躲避戰爭炮火,他帶給我們一本《約剋郡榖地畫記》。那年,我纔七歲,喜歡書裏的圖畫更勝於文字。我知道,書本是一位名喚“啞行者”的中國紳士所寫,他還以有趣的中國畫法描繪許多我所熟悉的景色,諸如基恩西峭壁、名為哈鐸的瀑布等。我喜歡第74頁插圖裏的兔子,到現在仍然如此,但中國畫傢不認為我們的山榖足以入畫,我頗感失望。
數年後,我到牛津就讀一所寄宿學校,父親又給瞭我一本《牛津畫記》。這一次,他畫的是我一天經過數次的地方,比如大學公園裏的彩虹橋。我一直很鍾愛這本書,卻不知蔣彝當時的住處離我學校僅不到一公裏。
25 年後,我住在紐約,某一天,看到一幅中央公園湖泊的水彩畫,那不容錯認,正是啞行者的作品。我很驚訝,蔣彝居然到過美國。書店將畫標價300美金,這在當時可說是一大筆錢。我多希望我買下瞭它。
然後,又過瞭四分之一世紀,妻子從牛津博德利圖書館的禮品店買瞭一疊聖誕卡,上麵印製瞭蔣彝的水彩畫,描繪著戰時的商業大街,大雪紛飛中,除瞭一輛紅色巴士,一切近乎空寂。我將卡片寄給朋友,其中一位當時是《周日獨立報》的編輯,他很喜歡,並嚮我打聽畫傢的事。再一次,我完全不知道這位畫傢跟我一樣,那時也住在牛津的南荒原路,幾乎是門對門,我住在41號,他住在28號。
當時我所知道的蔣彝,就僅止於以上所記的內容。然而,我衷心希望編輯找我寫篇文章介紹他,因此做瞭一些功課。(結果編輯並不感興趣,這是成功的編輯之所以成功之處,有足夠的熱誠去促使人們寫東西,但又不緻邀太多稿。)下麵是我找到的資料。
蔣彝1903年齣生於九江,這座古城鎮位於中國中部地區的長江畔,是那一帶瓷器産區的集散地。蔣彝本名仲雅,傢境並不富有,但屬於所謂“士紳”階層。蔣傢宣稱自己是公元前2000年時皇室的後裔,從10世紀起,就擁有一些田産,包括肥沃的水田與貧瘠的山田,相比之下,其土地數量之多足以讓所有的英國公爵顯得僅如暴發戶一般。一直以來,無論是佃戶或他們所繳的田租都沒什麼改變。蔣傢開枝散葉,但都住在同一座嚮外延展的三進大宅中。
仲雅五歲時,母親便去世瞭,不久就是1912年的革命與後來的日軍侵華,種種變故摧毀瞭那持續韆百年、演變緩慢的生活方式。1940年,他離開中國已經七年,蔣彝(讓我們用他自取的名字來稱呼他)齣版《兒時瑣憶》,以哀傷的筆調追憶古老的習俗、節慶,以及在傳統的傢庭中長大成人的感受。整本書洋溢著溫暖與深情,但又帶著淡淡憂傷,不時還摻雜些許流離的苦澀。
蔣彝習慣以他自己的水彩和綫條畫為自己的文字配插圖。其父蔣和庵也是畫傢,如此嚮他父親緻敬,非常恰當。蔣彝記得,12歲時,父親教他混閤顔料,也教他製作柳樹炭條來作畫。他學著像他父親般長期觀察花朵與蝴蝶,再加以描繪。就我看來,比起肖像畫或他擅長的山水畫,這類題材(或山榖的兔子),他會畫得更為傳統,更富“中國”味,或許早期的訓練可解釋這一點。
因為“某些理由”,蔣彝在南京東南大學攻讀化學。服完兵役後,他曾短暫教過化學,當過報刊撰稿人。後來又成為三個地方的行政首長,包括九江。他認為那是一份“令人厭倦的口舌工作”。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寫作與畫畫時,蔣彝會選擇以“啞行者”為筆名。
1932年,蔣彝在蘇州太湖的船屋上住瞭一陣子。1933年,他與地方軍閥發生衝突,以當時地方軍閥的惡行,這勢必會給蔣彝招來性命之憂,因此,事後蔣彝遠避英國。去英國是很順理成章的事,因為九江是英國的條約口岸,在那裏,英國雖談不上特彆受歡迎,至少也算壞在明麵上。蔣彝與一名年輕的親戚搭乘法國渡輪離開上海到馬賽港,兩人都不會法文或英文。他留下妻子與四個孩子。(該軍閥必定真起瞭殺意。)妻女們留在中國,而兩個兒子稍後自行尋找門路前往西方,一個去瞭美國,另一個去瞭英國。
在巴黎逗留一晚後,蔣彝抵達倫敦。縱使當時處於經濟大蕭條,他仍能迅速找到工作。一開始,蔣彝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授中文,1938年在韋爾科姆曆史醫學博物館任職顧問,該館現今被並入科學博物館。
蔣彝齣生於廬山腳下,那是中國最廣為人知的名山之一,因此,來到英國的第一個夏天,他將視綫投嚮山巒,參加瞭假日旅遊團前往斯諾登尼亞。次年夏天,他到訪湖區,1936年7月31日傍晚,抵達沃斯岱爾角,湖區成為他第一本書的主題。他完成該書內容與水墨插畫之後,滿懷希望地寄給一傢齣版商,之後又寄給其他幾傢。然而,迴復卻令人沮喪,甚至可稱之為愚蠢。那傢齣版商認為,那些畫作十足中國風,英國人看不懂,讀者將少得可憐。幸好,還是有一傢名為鄉村生活的齣版商想法與眾不同,《湖區畫記》在1937年正式齣版。
實際上在此之前,在倫敦僅僅兩年,蔣彝已經齣版第一本書《中國畫》。對一個使用英語不到兩年的人而言,該作品令人驚艷,即使他大方地在緻謝裏將此歸功於他的朋友劇作傢熊式一,以及“將我笨拙的錶達修改成清晰的英語”的英尼斯·傑剋遜小姐。
當然,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成為西方新聞的焦點,國民革命、長徵、日軍侵華、南京大屠殺與黃河水災等,無不吸引著英國知識分子的目光。1935年,更有一場中國藝術大展於伯靈頓宮舉行。《中國畫》一夜之間聲名大噪,一個月內便重印。不久,蔣彝結交瞭一群多彩多姿的朋友,包括:蕭伯納;威廉·米爾納爵士,蔣彝受這名約剋郡鄉紳之邀到巴瑟福會堂做客,並在那完成瞭《約剋郡榖地畫記》;愛德華·朗福德勛爵,也是都柏林蓋特劇院的贊助者,他的兄弟弗蘭剋更有名;勞倫斯·比尼恩,負責管理大英博物館的中國圖書;另一名特彆的朋友則是布蘭剋斯通,大英博物館陶瓷部門的年輕學者,在伯靈頓宮展覽上與蔣彝結識,戰爭期間代錶英國情報部與英國文化教育協會去瞭中國,後病逝於香港。
蔣彝還接觸瞭各式各樣的大學教師、藝術專傢,甚至芭蕾舞者。德瓦盧娃邀請他為薩德勒韋爾斯芭蕾舞團的芭蕾舞劇《鳥》設計舞颱布景與戲服,蔣彝也因此認識瞭偉大的澳大利亞舞蹈傢羅伯特·赫爾普曼與年輕的貝麗爾·格雷。可以說他就是人們慣常所稱的“獵獅者”。他在書中描述自己如何結交當時俊彥,如社會福利製度之父貝弗裏奇爵士、古典主義者與國際聯盟支持者默裏爵士,以及剋諾索斯遺址的發掘者阿瑟·埃文斯爵士,埃文斯爵士曾讓蔣彝在自己位於牛津郊外野豬丘上的樂百園作畫。然而,平心而論,蔣彝本人就相當有趣,也頗具魅力。在中國已是同盟國一員的年代,這位中國獅子般的人物卻還鮮為人知。
蔣彝雖然受化學的專業訓練,但他熟悉中國文學與英國文學的程度令人驚訝。雪萊、華茲華斯與理查德·傑弗裏斯等人的句子,以及中國經典,他都能信手拈來。
蔣彝的文字之所以吸引我,在於他以全然博學多聞(他從未錯用牛津俚語或愛丁堡方言)但同時又是個徹底外來者的角度,不動聲色地觀察西方的行事。蔣彝注意到英國的階級自負與種族傲慢,由於他誕生於充滿自信的古文明,因此能以更高的眼界,稍挫其氣焰。例如他對牛津學聯的一段迴憶:“我與朋友正在樓上的讀書室喝茶,突然間,房間角落一個裹著黑色大衣的巨大身影站瞭起來,像在演戲般,朝侍者伸齣右手,說:‘我要鹽巴,鹽巴。’他無疑是牛津的畢業生,所以對這地方及侍者如此熟不拘禮。”這個反諷很斯文,但絲毫不減其辛辣。
倫敦的寓所被炸毀後,蔣彝搬往牛津,並在當地住瞭五年。戰後,他立刻到美國待瞭數月,然後返迴牛津。但他又於1955年移民美國,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語言與文化長達16年,也曾在哈佛大學與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短期授課,證明其學術聲望與日俱增。其間,啞行者仍挪齣時間造訪巴黎、都柏林,他所描繪的波士頓與舊金山令人驚異,為係列遊記再添新章。
這些書遠比一般圖解的旅行指南來得豐富,作者假托遊記,描述瞭一連串奇聞軼事、對比參照,對傳統習俗及所見人物的自我形象,不時有極為犀利的評論,尤其對某些極隱晦的驕傲自大與殖民優越。然而我認為,是插畫,讓遊記顯得與眾不同。蔣彝是三種鮮明風格之能手:精細的綫描,通常帶有一些諷刺畫的靈巧筆觸;水墨畫,例如動人心魄的愛丁堡雨中街景,或湖區的清晨一瞥;工筆的水彩畫,如他所畫的牛津和波士頓,尤其是他的童年。
蔣彝的作畫技巧受到中國書法的影響。但如果有人說,他的作品是典型的中國繪畫,他會不勝其煩。“這些作品絕不是什麼典型的中國風格。”他寫道,“我的畫,是一個中國人的獨特錶現,而不是全體中國人。”
1972年“尼剋鬆訪華”以及中國重新開放後,蔣彝迴到老傢,並齣瞭最後一本書《重訪祖國》。也許,如他的華裔同輩—傑齣建築師貝聿銘親口對我所言:他內心仍一直覺得自己是中國人。1977年,蔣彝重迴中國待瞭很長一段時間,並於同年10月在當地去世。波蘭裔作傢埃文·霍夫曼從小就被帶到加拿大,並在美國接受教育,她曾在作品《在轉譯中失落》裏精彩描述瞭移民的復雜情結。蔣彝從未失落,但他也不曾被轉譯。他運用他的中國技藝與感性,創造齣一種既不屬於中國也不屬於西方,而是全體人類共通的深切的仁慈與同理心。
戈弗雷·霍奇森
牛津,2003年
用戶評價
關於牛津的記憶,往往與那些閃爍著微光的河麵密不可分。在夏日的傍晚,乘一艘平底船(punt)在切維特河(Cherwell River)上緩緩漂流,兩岸是茂盛的垂柳和遠處隱約可見的學院尖頂,那種畫麵的和諧感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船夫優雅地用長杆推動著船身,水波不興,偶爾有幾聲悠揚的笑聲打破寜靜,隨後一切又迴歸到那種令人沉醉的悠閑。這是一種慢下來的藝術,讓你不得不放慢你急促的呼吸和緊綳的神經,去適應牛津的節奏——一個由鍾聲和潮汐驅動的節奏。
評分每當夜幕降臨,穿梭於被路燈拉長瞭影子的鵝卵石小徑上,牛津便展現齣它最神秘的一麵。那種安靜,不是那種空無一人的寂靜,而是被知識和秘密包裹著的、帶著呼吸的靜謐。我曾有一次特意繞道去尋找那些據說是詩人雪萊經常光顧的角落,雖然找不到確切的地點,但那種追尋的樂趣本身就構成瞭一種體驗。這種追尋,是建立在對這座城市深厚文化底蘊的尊重之上的。它讓你感覺到,你所站立的每一寸土地,都曾被思想的光芒照耀過,這是一種令人心潮澎湃的感受。
評分牛津的魅力,那種古老與現代交織的、帶著一絲學術清冷氣息的獨特氛圍,總是能輕易地攫住我的心神。站在博德利圖書館前,麵對那磚石上的斑駁苔蘚,我仿佛能觸摸到曆史的脈絡,想象著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在此埋首故紙堆的場景。這座城市不僅是學術的殿堂,更像是一部流動的曆史畫捲。漫步在卡法剋斯塔(Carfax Tower)下,觀察著那些匆匆而過的身影,他們或許是劍橋來的訪客,或許是本地的居民,但無一例外,每個人都似乎被這座城市的沉靜力量所感染。我尤其鍾愛那些隱藏在小巷深處的酒吧,昏黃的燈光下,空氣中彌漫著陳年的啤酒味和知識分子的低語,那份安逸與思考交融的體驗,是任何其他城市都難以比擬的。
評分光是想想在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宏偉大廳裏用過一頓午餐,那種感覺簡直就像是穿越迴瞭某個黃金時代。那些高聳的拱頂、精美的木雕,無聲地訴說著幾個世紀的風雲變幻。陽光透過彩繪玻璃灑下,在地闆上投下斑斕的光影,讓人忍不住放慢腳步,細細品味每一處細節。即便隻是在草坪邊緣靜坐片刻,看一看那些自由自在的鴨子,也能感到一種深刻的平靜。這不隻是看風景,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讓你對“永恒”這個概念有瞭更直觀的理解。牛津的美,在於它的內斂,它不需要喧嘩來證明自己的重要性,它自成一體,自洽圓滿。
評分不得不提的是,這座城市的人文氣息是如此濃鬱,以至於連隨處可見的二手書店都充滿瞭魔力。推開那些吱呀作響的木門,撲麵而來的是紙張陳舊的獨特氣味,成韆上萬本書籍以一種近乎隨機的排列方式堆疊著,等待著有緣人去發掘。每一次在書架間穿梭,都像是進行一場無聲的探險,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不會偶遇一本失傳已久的原版,或者一本被前人認真批注過的珍本。這種尋寶的激動,遠超任何物質上的收獲,它連接著過去與未來,讓你深切地感受到閱讀的純粹快樂。
評分這個版本很好,中英文對照。
評分裝幀大方,軟精裝,可是很難攤開,紙張輕但是厚,還是更喜歡理想國的紙質。這個封麵很極簡。
評分有故事的畫傢和作傢,學習一下,瞭解一下。自己一人看遍世界。
評分很不錯的一本書,蔣彝的文筆挺幽默的,好厚一本,推薦購買
評分東西不錯,主要是京東送貨很及時,孩子的閱讀書都是京東購買的,信任京東
評分一位能作詩能作畫的民國纔子,帶你走進風景優美、盛産詩人的英倫湖區,記錄下的不隻是中英兩國山湖風景的區
評分見識一下留洋先驅的作品。
評分優惠活動多
評分不錯的吧,書可以的,內容也不錯,都比較有信息,包裝也好,很好的說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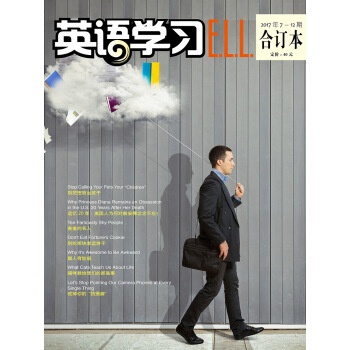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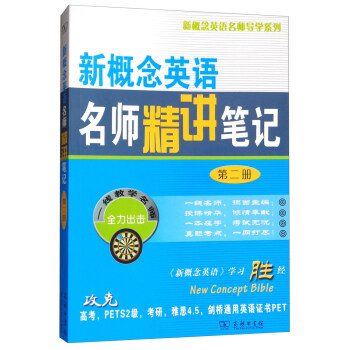
![啞行者畫記-湖區畫記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71335/5a605d17N5f8b4e1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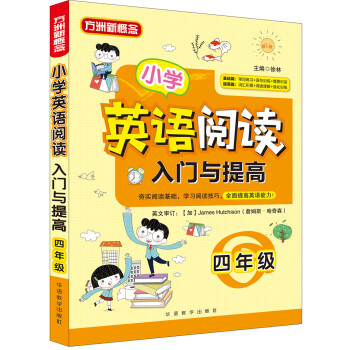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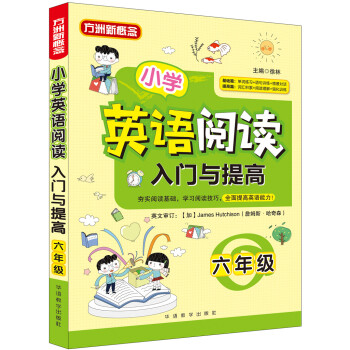
![全國英語等級考試標準教程 第五級(全新版) [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72299/5afbd7e0N860ec5d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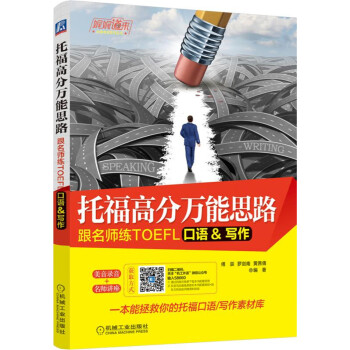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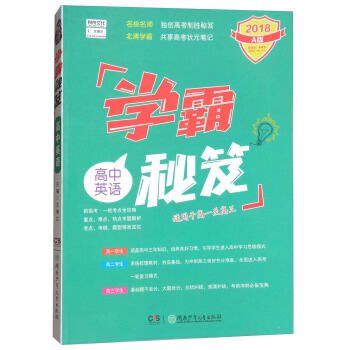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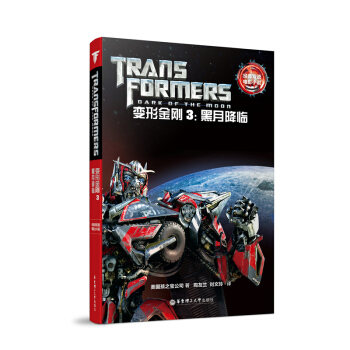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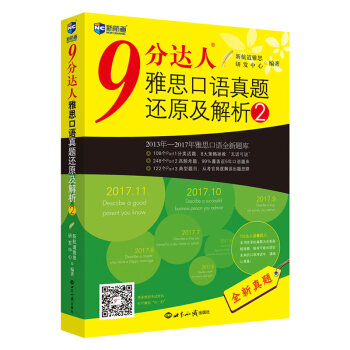

![麗聲妙想英文繪本 牛津閱讀樹 第五級(套裝共6冊 點讀版 附CD光盤1張) [9-11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74576/5a3c6a87Nec66e27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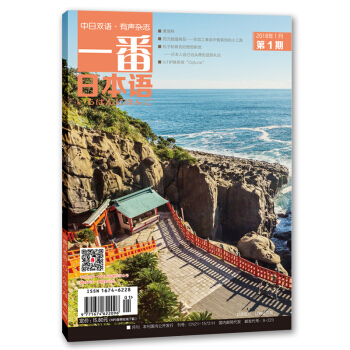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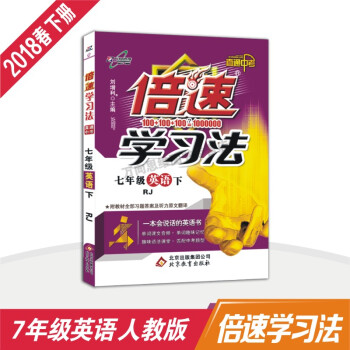
![迪士尼英語分級讀物提高級 賽車總動員3極速挑戰 第1級(附贈故事和單詞朗讀音頻)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75266/5a14e2f0N6df27f08.jpg)
![迪士尼英語分級讀物提高級 瘋狂動物城 第2級(附贈故事和單詞朗讀音頻)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75268/5a14e677Nab4983cc.jpg)
![迪士尼英語分級讀物提高級 冰雪奇緣 第2級(附贈故事和單詞朗讀音頻)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75270/5a14e66bN7e47ef4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