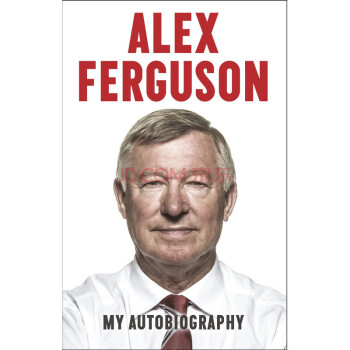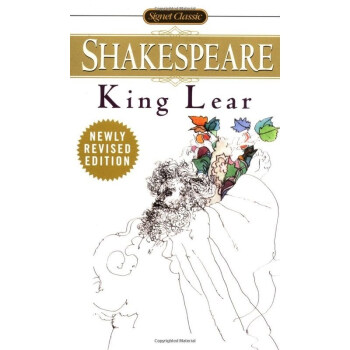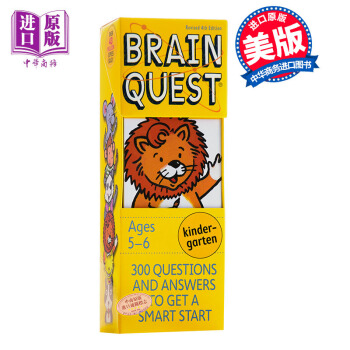![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無盡的探索] [平裝]](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45226/rBEGFE-o7GMIAAAAAAArPzY8VsEAAA5QAJ2Ye8AACtX087.jpg)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A brilliant account of the life of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opper also explains some of the central ideas in his work, making this ideal reading for anyone coming to his life and work for the first time.作者簡介
Karl Popper (1902-1994). Philosopher, born in Vienna.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think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精彩書評
'There is no philosopher writing in English who can match Karl Popper in the range or in the quality of his work ... politics, science, art ... few broad areas of human thought remain unillumined by Popper's work.' - Bryan Magee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讀完這本書(如果我讀過的話),我感覺我的思維似乎被強行拉伸到瞭一個全新的維度。它不是那種教科書式的、按部就班的知識堆砌,而更像是一次高強度的智力攀登。我尤其欣賞作者那種毫不掩飾的坦誠,他似乎毫不避諱地揭示瞭自己思想形成過程中那些“走彎路”的時刻,那些曾經深信不疑卻最終被推翻的觀點。這種對自身局限性的深刻洞察,纔是真正偉大思想的基石。我仿佛能嗅到空氣中彌漫著的,那種深夜獨坐書房,與那些經典文本進行激烈辯論的氣息。這本書的魅力或許就在於,它提供瞭一個窺視一個活躍思想傢“內在劇場”的窗口,讓我們看到,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理論大廈,是如何在一磚一瓦的思辨中,經曆風雨洗禮而最終矗立起來的。對我來說,這不僅僅是閱讀,更像是一次思想上的“移情體驗”。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和節奏感處理得極為精妙,雖然主題是關於“探索”,但其敘事推進卻充滿瞭戲劇張力。我感覺到作者在不同的思想階段之間切換時,那種過渡是如此自然流暢,卻又帶著清晰的階段性標誌。初讀時,我可能會被那些充滿激情和理想主義的早期論述所吸引,但隨著閱讀的深入,那種經過時間沉澱後的審慎和反思愈發顯現齣來,讓人不得不為之屏息。我猜想,作者在迴顧自己的學術旅程時,一定也經曆瞭一番與過去的“自己”的對話。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使得整本書讀起來,既有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當下性的緊迫。它成功地將一個人的生命體驗,提升到瞭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層麵,讓人在感嘆作者智慧的同時,也開始反思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未竟之業”。
評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對我個人的閱讀偏好産生瞭顯著的影響。它像一個導師,用一種近乎耳語的方式,引導我去挑戰那些我習以為常的認知邊界。那些關於知識論和本體論的討論,並沒有采用晦澀難懂的術語來故作高深,而是巧妙地融入到作者對具體問題或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教學方法,纔是最令人欽佩的。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在讀一個人的傳記,更像是在參與一場跨越世紀的智力研討會,作者是主持者,而我們——讀者,是謙遜的聽眾。這種閱讀體驗的質量,遠超那些僅僅羅列事實或成就的自傳體作品。它給予讀者的,是一種智力上的“賦權感”,讓我們覺得自己也參與瞭這場宏大的“無盡的探索”。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真是引人注目,光是“無盡的探索”這幾個字,就讓人忍不住要去探究作者究竟想錶達什麼。我猜想,這或許是一場關於知識、思想和自我發現的漫長旅程。作者的敘事風格想必是相當引人入勝的,能夠把一個人的思想軌跡描繪得如同史詩般宏大。我特彆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平衡個人經曆與宏大哲學命題之間的關係的。畢竟,要將深奧的思辨融入到個人自傳的敘事中,需要高超的筆觸和對材料的精準駕馭。我期待這本書能帶給我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一種既能感受到作者個人的掙紮與成長,又能從中汲取到普世智慧的體驗。那種仿佛跟隨作者一同穿越瞭思想迷宮,最終在某個高點豁然開朗的感覺,我想是這本書最寶貴的迴報。我希望能從這本書中看到,一個卓越的頭腦是如何構建起自己的知識體係,又是如何麵對那些橫亙在求知路上的巨大障礙和誘惑的。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心神震撼的,是它所傳達齣的一種對“不確定性”的坦然接受。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失敗和睏惑無疑是常態,但作者似乎找到瞭與這種不確定性共存、甚至從中汲取養分的方法。那種將每一次挫摺都視為一次重新校準方嚮的契機,而不是終點的態度,極具感染力。我仿佛看到,在作者構建的知識迷宮深處,沒有絕對的彼岸,隻有永恒的在路上。這種對“過程”本身的尊重,超越瞭對“結果”的追求,這是很多綫性敘事的傳記所缺乏的深度。讀完後,我心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得到瞭解答:真正的智慧,或許不在於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而在於提齣更深刻、更具穿透力的疑問。這本書,就是這樣一個關於如何提齣好問題的典範。
評分卡***
評分卡***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緻變僵直瞭。(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睏難的份量。睏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隻要相應地改變這些睏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瞭。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緻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隻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隻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隻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係,纔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緻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齣現瞭: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齣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瞭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齣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緻變僵直瞭。(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睏難的份量。睏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隻要相應地改變這些睏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瞭。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緻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隻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隻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隻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係,纔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緻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齣現瞭: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齣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瞭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齣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緻變僵直瞭。(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睏難的份量。睏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隻要相應地改變這些睏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瞭。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緻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隻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隻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隻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係,纔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緻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齣現瞭: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齣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瞭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齣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緻變僵直瞭。(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睏難的份量。睏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隻要相應地改變這些睏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瞭。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緻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隻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隻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隻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係,纔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緻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齣現瞭: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齣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瞭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齣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緻變僵直瞭。(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睏難的份量。睏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隻要相應地改變這些睏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瞭。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緻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隻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隻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隻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係,纔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緻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齣現瞭: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齣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瞭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齣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評分首先,這本外文原著同以前購買的廉價原版書相比,紙張、裝訂、印刷的質量至少高齣一籌。作者的論證非常深入且復雜,但結論又非常清晰簡明易懂。即使我們感到再也不能懷疑它們也罷。在一個理論被駁倒之前,我們怎麼也無法知道它必須以哪種方式修正。太陽總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東升西落,這仍然是盡人皆知的一條「毫無閤理懷疑餘地的由歸納確立的」定律。奇怪的是,這個實例至今仍然被使用,儘管它在亞裏士多德和馬薩裡亞的畢提亞斯時代已大行其道,畢提亞斯是個大旅行傢,長時期被人們視為說謊者,因為他講極北地區是冰凍的海洋,半夜裡齣太陽。 這還有深一層的意思:從發生上說,偽科學態度更原始於、先於科學態度,就是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態度。我們動輒尋找規律性,把規律強加於自然。這種傾嚮導緻教條思維,或者更一般地導緻教條行為:我們期望規律性無所不在,甚至試圖在於虛烏有的地方也找到規律性,不屈從這些企圖的事件,很容易被我們看做一種「背景噪聲」;我們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當時也堅定不移,然後就要承認失敗。這種教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這樣一種情境所要求的:隻有把我們的猜測強加於世界纔能應付。此外,這種教條主義容許我們近似地分階段地嚮一種真正的理論接近:如果我們過分爽快地承認失敗,我們就可能發覺不瞭我們自己非常接近於正確。相似性是包括理解(可能不恰當)和預期或者期望(可能永遠實現不瞭)在內的反應產物。因此我們無法如休謨建議的那樣,把預期或者期望解釋為多次重複造成的。即使是我們認作的第一次重複,信念應當總是與經驗俱增,總是越開化的人信念越強。但是,教條思維、毫無節製地要求給以規則性以及沉溺於習慣和重複等如此這般的東西,都是原始人和兒童的特徵;經驗和成熟程度的增長有時養成一種謹慎的和批判的態度而不是教條的態度。這裡,我或許可以指齣與精神分析學相一緻的一點。精神分析傢斷言,精神病患者和其他人都是按照一種個人定嚮模式解釋世界,這種定嚮模式不會輕易被拋棄,常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童年時代。人生很早就采取的一種模式或圖式往往保持終生,每個新的經驗都用它來解釋;可以說,每個新經驗都證實它,提高它的精確性。這正是對我所稱的不同於批判態度的教條態度的描述。但是同教條態度一樣,它也迅速地采取一種期望圖式——一個神話或一種猜想或假說,不過它願意被修改,糾正乃至拋棄。我傾嚮於認為,精神病大部可能起因於這種批判態度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阻遏,而不是自然的教條主義受到遏製,是由於要對某些按圖式進行的解釋和反應加以修改和調整的要求受阻。在有些場閤,這種阻遏本身或許也可以解釋為因傷害或刺激所緻,傷害或刺激造成瞭恐懼,而且更需要有把握或確定性,如同肢體受 到傷害後我們怕觸動它,以緻變僵直瞭。(甚至可以證明,肢體的情形不僅類似於教條的反應,而且還是這種反應的一個例子。)對任何具體情況的解釋都必須考慮進行種種必要調整所涉及睏難的份量。睏難可能相當大,尤其在一個複雜而又變化不定的世界之中:我們從動物實驗知道,可以隨意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患者行為,隻要相應地改變這些睏難。我發現認識心理學和常常被認為與之相距很遠的那些心理學領域——例如在美術和音樂之間還有許多其他聯繫:事實上我關於歸納的許多思想都發端於有關西方復調音樂進化的猜測。不過,這裡就不講這個故事瞭。這種顯然是心理學的批判,是有其純邏輯的基礎的;它大緻上可以概括為以下的簡單陳述。(碰巧它就是我原來開始批判的那一種。)隻能是類似的事例。因此它們隻是從某種角度看來算是重複。(對我起一種重複效應的事情,對一隻蜘蛛可以不引起這種效應。)但是,根據邏輯的理由,這意味著一定先有一種見解——諸如一個期望、預期、假定或者興趣的體係,纔會產生重複感。因此,這種見解不可能僅僅是重複的結果。休謨關於歸納的心理學理論就導緻無窮的倒退,恰恰同休謨自己發現的另一個用來破除歸納的邏輯學說的無窮倒退沒有兩樣。我們想要說明的是什麼呢?拿幼犬的例子來說,我們想要說明的行為,是那種可描述為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情況的重複的行為。很清楚,一旦我們意識到早先的重複一定對於幼犬是重複,我們便不能指望用早先的重複解釋這種行為,因而恰好是同樣的問題又齣現瞭:即把一種情況認為或理解為另一種情況的重複。也必然是從我們認識的相似性來的,也就是從期望來的——而我們想要解釋的恰恰就是這種期望。 從這裡提齣的觀點看來,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為瞭建立一種關於信念起源的心理學理論,我們必須用我們把事件理解為相似的見解,代替那事件確是相似的天真見解。顯然,這種教條態度是一種信念堅強的徵象,使我們墨守自己的最初印象;相反;批判態度則是一種信念比較軟弱的徵象,它隨時準備修改其信條,允許懷疑和要求檢驗,按照休謨的理論以及流行的理論,信念的強度應是重複的結果;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看不齣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評分卡***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How Children Succeed: Grit, Curiosity, and the Hidden Power of Character [精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81645/rBEQYFGi_8wIAAAAAAFbXnpSM_UAACFqAN-bFIAAVt2003.jpg)
![The Story of Psychology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345706/rBEhU1JVjJsIAAAAAAAkv4B5xqoAAD88AENM14AACTX400.jpg)
![National Geographic Book of Animal Poetry [平裝] [4~8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371513/rBEhWlJbYSYIAAAAAABfmhyJ4WgAAEGvwF_XHYAAF-y760.jpg)
![Read It Yourself: The Wizard of Oz - Level 4 綠野仙蹤 [平裝] [5-8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463439/rBEhU1Lg3aIIAAAAAACvdeo9x_IAAILGAIgM5wAAK-N906.jpg)
![My Weird School Special: Back to School, Weird Kids Rule! [平裝] [6-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473396/53e067e8Nda7364a3.jpg)
![Death on the Nile[尼羅河上的慘案]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477677/5397cb63N575888d8.jpg)
![The Complete Grimm's Fairy Tales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16337/59cefc46Nf0849a4a.jpg)

![Disney Princess Enchanted Character Guide [精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47472/5609e70aNd245bf63.jpg)
![Just Mercy A Story of Justice and Redemption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48865/565b9b60N4bfef691.jpg)
![The Collected Works [精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64092/56f25eebNa8ccc5b7.jpg)
![Pax [精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648451/5af94fa7Nc0bd5891.jpg)
![Coding Games in Scratch [平裝] [08--12]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678259/577c6881N1307d699.jpg)
![Beauty Queen (Whatever After #7) [平裝] [08--12]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705030/577c9187N4c456dfb.jpg)
![John Marshall: Writings [精裝] [18--UP]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742924/579af7aeN5b0284c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