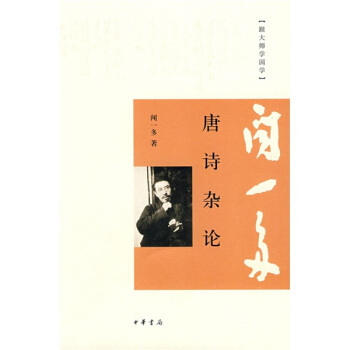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作家 学者 朱自清他的《唐诗杂论》……都是精彩逼入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作家 汪曾祺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
内容简介
《唐诗杂论》是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唐诗研究的经典之作,内容涉及唐代诗歌的多个方面,对唐代著名诗人,如“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评论与分析。全书论述精辟,行文优美流畅,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引人人胜。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略闻先生在唐诗领域的精彩创见,本次出版,增补了《陈子昂》、《唐诗要略》、《诗的唐朝》、《唐诗校读法举例》等数篇文字作为附录。另外,《闻一多先生说唐诗》是郑临川先生根据当年在西南联大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成,内容丰富,精义迭出,亦附录于书后。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他的《唐诗杂论》……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朱自清 作家 学者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
——汪曾祺 作家
目录
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
四杰
孟浩然(六八九——七四○)
贾岛(七七九——八四三)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岑嘉州系年考证
杜甫
英译李太白诗
附录一
陈子昂(六六一——七○二)
唐诗要略
诗的唐朝
唐诗校读法举例
附录二
闻一多先生说唐诗(郑临川笔录)
精彩书摘
类书与诗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六六○)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份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着格外分明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馀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未,潮水带星来。
甚至
马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
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两句诗,曾经谋害过两条性命。“枫落吴江冷”比起前面那两只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这不是说笑话。假如我们能回答这问题,那么太宗统治下的诗作的品质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归真地讲,崔信明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留给我们那样测验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机会。但这更足以证明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讲到这里,我们许要想到前面所引时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两句话。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拿虞世南、李百药来和崔信明、王绩、王梵志比,不简直是“事”与“意”的比照吗?我们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占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余地,也就太可怜了。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选家们搜出魏徵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药,以及当时成群的词臣,做了几十年的诗,到头还要靠这诗坛的局外人魏徵,来维持一点较清醒的诗的意识,这简直是他们的耻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领下的人们为诗干的多热闹,究竟他们所热闹的,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学术。关于修辞立诚四个字,即算他们做到了修辞(但这仍然是疑问),那立诚的观念,在他们的诗里可说整个不存在。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远,所以,我若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我所谓征集词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制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曾经说到太宗为堆砌式的文体张目过,不错,看他亲撰的《晋书·陆机传论》便知道。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初次接触唐诗,总是被那宏大的意象和优美的辞藻所吸引,但总觉得隔着一层薄纱,无法真正触及诗歌的灵魂。这本书的出现,如同一位博学的老友,娓娓道来,将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诗篇,用一种极其亲切而深刻的方式展现在我面前。它没有生硬的理论灌输,也没有枯燥的生僻字词考据,而是从一个读者的视角出发,引导我们去感受,去体悟。作者仿佛拥有穿越时空的慧眼,能洞察诗人创作时的心境,捕捉那些被历史洪流掩埋的细微情感。读这本书,就像是在与李白对饮,听杜甫在长安街头低语,和白居易一起在江南的烟雨中漫步。那些诗句不再是孤立的文字,而是有了鲜活的生命,有了温度,有了故事。它教会我如何去辨析诗歌的意境,如何去理解诗人的情感寄托,甚至如何从看似寻常的意象中挖掘出不凡的深意。这种学习方式,让我对唐诗的热爱,从最初的浅尝辄止,变成了如今的沉醉其中,欲罢不能。
评分对于我这样一个对传统文化怀有浓厚兴趣,却又苦于无从下手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及时雨。它以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将我引向了唐诗的海洋。作者并没有直接抛出各种学究式的定义和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将唐诗的精髓娓娓道来。读的时候,我常常会掩卷沉思,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与诗人们一同经历人生的悲欢离合。那些曾经读过的诗句,在经过作者的解读后,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我开始注意到诗歌中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感受到诗人心底最深处的呐喊与渴望。这种阅读体验,让我觉得自己在与历史对话,与伟大的灵魂交流。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唐朝。
评分我一直认为,国学经典虽然博大精深,但往往给人一种高高在上、难以企及的感觉。尤其是唐诗,虽然耳熟能详,但深入探究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背景,总让人感到力不从心。直到我翻开这本书,才发现原来国学也可以如此平易近人,唐诗的魅力也能如此生动地呈现在眼前。作者的笔触,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带着我们穿梭于大唐盛世,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讲述那些诗篇背后的故事,解析那些流传千古的佳句。他不仅关注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更挖掘了诗歌与历史、社会、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联系。读这本书,我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地参与到一场文化探索之中。我开始理解,为何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为何李白的诗歌飘逸豪放,为何王维的诗歌禅意盎然。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解读方式,让我对唐诗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深入学习国学的决心。
评分长期以来,我总觉得国学是一门需要“悟”的学问,很多时候,即使看懂了字面意思,也难以领会其背后的深意。这本书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我的这种迷思。它用一种极其接地气的方式,将唐诗的“杂论”化繁为简,化深奥为浅显。作者的文字,没有丝毫的故弄玄虚,而是充满了真诚和热情。他仿佛一位邻家大哥,用他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与我们分享他对唐诗的独到见解。读这本书,我不再感到学习国学的压力,反而觉得是一种享受。我开始发现,原来唐诗的魅力,并不在于那些艰涩的文字,而在于它所承载的丰富情感和深刻哲理。通过这本书,我不仅学会了欣赏唐诗的美,更学会了如何去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如何在诗歌中找到共鸣。这种学习方式,让我觉得国学不再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在与一位充满智慧的老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没有居高临下的教诲,而是以一种分享者的姿态,将自己对唐诗的理解和感悟娓娓道来。这本书最让我着迷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试图将唐诗进行生硬的分类和理论化的解读,而是从更宏观、更人性化的角度,去探讨唐诗的方方面面。作者的视角非常独特,他能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中,挖掘出诗歌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也能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阐释出诗人创作时的个体情感。这种处理方式,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它让我意识到,学习国学,尤其是像唐诗这样的经典,更重要的是去感受,去体悟,去将自己融入其中。这本书,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唐诗世界的大门,让我得以窥见其壮丽的风景,感受其磅礴的气势。
评分好书,老师的推荐,比想象的厚。
评分在京东你是上帝,在**你不是,卖家也不是,上帝是小二。 本来上帝是小二也很好,但前提必须是公平公正的。 问题是你经常会遇到受贿的上帝和弱 智的上帝。
评分网友推荐,拓展思路,留给女儿读的
评分一直读唐诗,然而我真的读懂过吗
评分购物选京东,物流快,东西好,购物体验超级棒。
评分跟大师学国学系列都买了
评分一直读唐诗,然而我真的读懂过吗
评分有时间一定好好拜读,摆书架上了
评分以前真不知道闻一多先生在诗歌方面的造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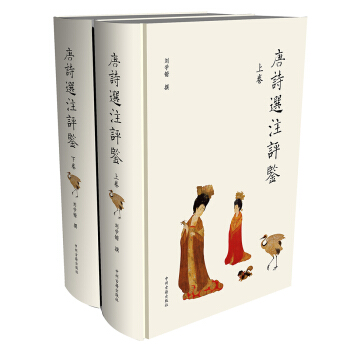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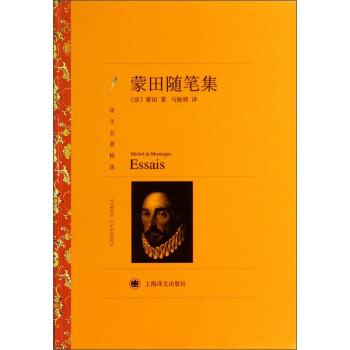
![意林小小姐幸福蔷薇系列5:蔷薇少女馆5·洛丽塔的新装(升级版) [8-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02342/53fa9199Nf71a5a5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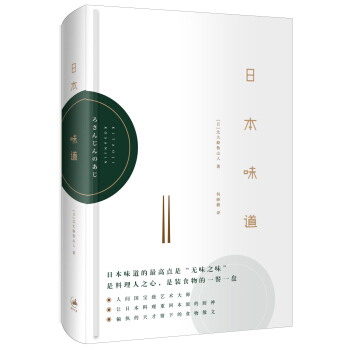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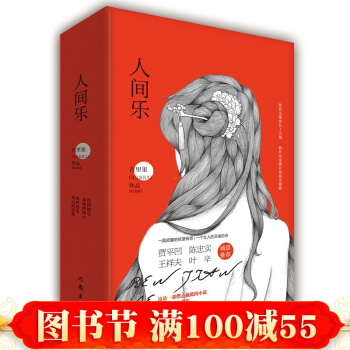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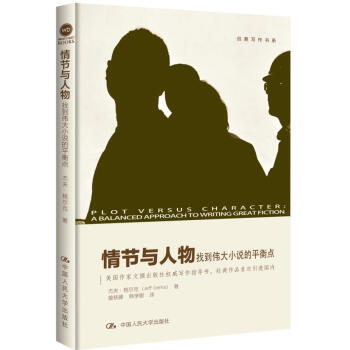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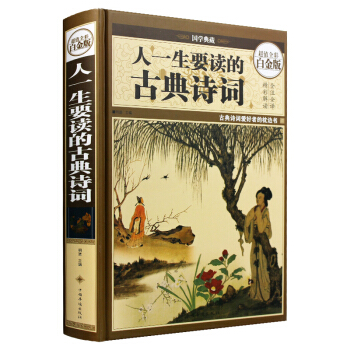
![汤汤精灵童话系列:美人树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61103/544a12f6N1382216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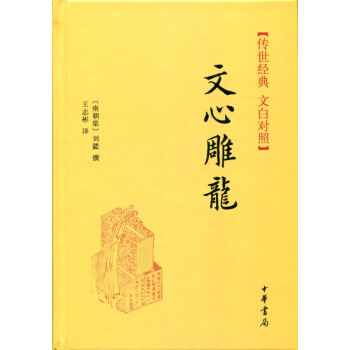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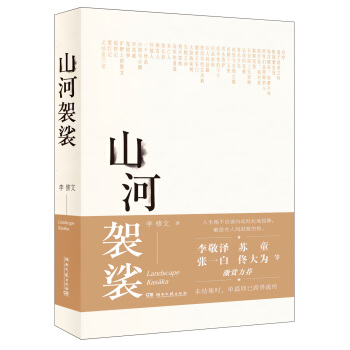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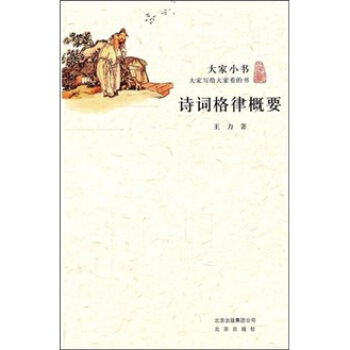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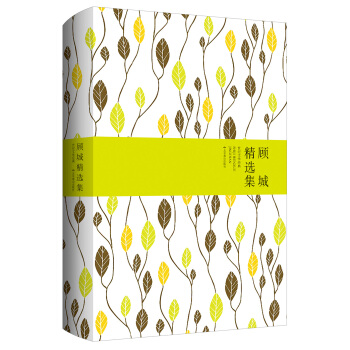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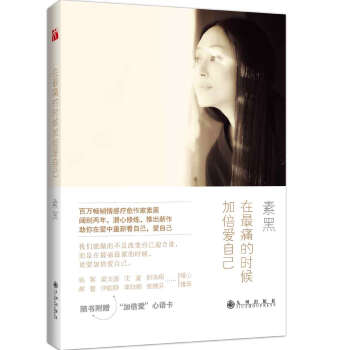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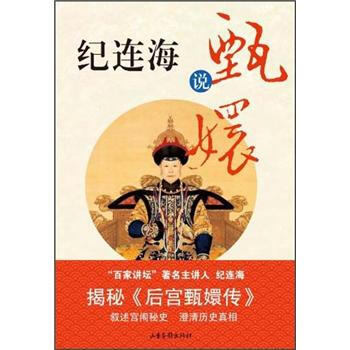
![小小姐合订本(2015年01期上-02期上总第35卷) [8-1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38185/54bf698aN9e1caee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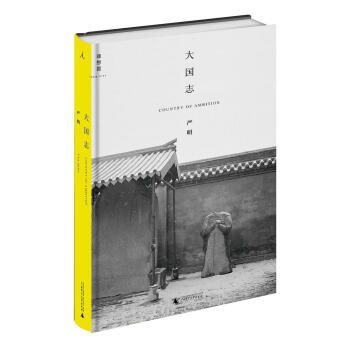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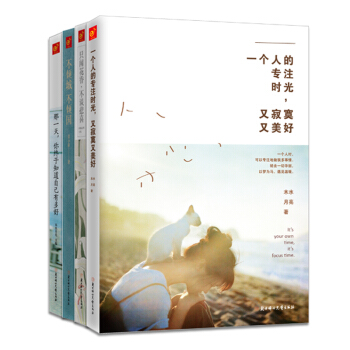
![童立方·儿歌小故事1:小狗和青蛙 [1-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18433/5739c28bNb737bd24.jpg)
![童立方·儿歌小故事2:小猫和小羊 [1-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32394/57345caeN431772e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