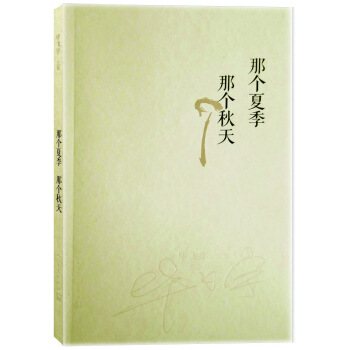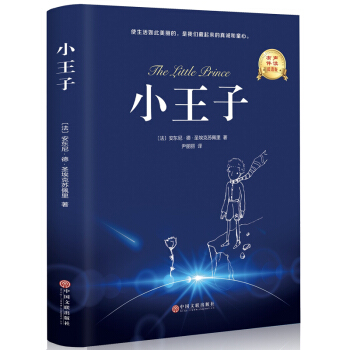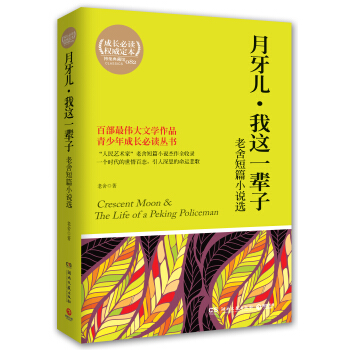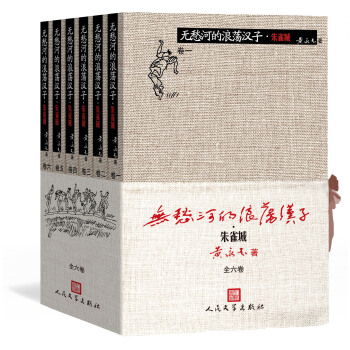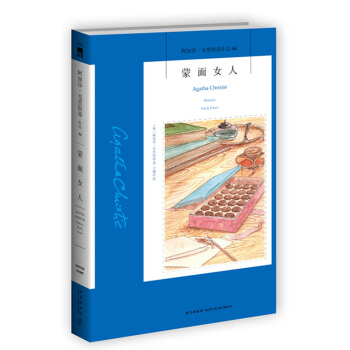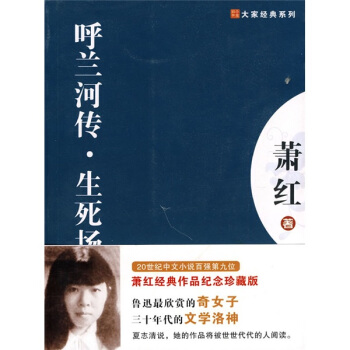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呼兰河传·生死场》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作者简介
.精彩书评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为生死场写的“序”
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夏志清
她的名声姗姗来迟。她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巨大分量只是在现在才清楚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批评的眼光却让那时代一些当时被Bq好的作品和强势作家不可挽回地没落下去。
——顾彬
张爱玲可以放在萧红的后面,丁玲的前面。《生死场》是比张爱玲所有的小说都好的东西……实际上,看看萧红的《生死场》,那种描写和叙述,现代中国的生存被表现得如此透彻。
——陈晓明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乌飞了,就像飞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呼兰河传》
目录
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生死场
旷野的呼喊
精彩书摘
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地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竞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
前言/序言
null
用户评价
这本被誉为“北方史诗”的作品,初读时那种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和凛冽的寒风,仿佛能透过纸页直抵人心最深处的角落。作者的笔触如同饱经风霜的老农,粗粝却又无比精妙地勾勒出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图景。我尤其被那些细微的生活片段所震撼,比如冬日里围炉烤火时,家人之间那种无需言语的心照不宣,又或是春耕时节,汗水滴落到干裂土地上的沉重回响。它不是那种追求华丽辞藻的文学作品,它的力量在于其质朴和真实,那种深入骨髓的对生命力的赞颂与叹息交织在一起,让人在为人物的坚韧而动容的同时,也不禁为命运的无常而感到一丝寒意。读完之后,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那些鲜活的面孔,他们身上带着的,是那个时代烙印下的,关于生存、关于尊严,最原始而又最深刻的哲学。这感觉,就像是亲眼目睹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迁徙,虽然过程充满了艰辛,但最终留下的,是关于人性光辉的深刻印记。
评分这本书最令人称奇的,是它在处理“苦难”这一宏大主题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近乎冷峻的客观性与内在的温情之间的精妙平衡。它没有进行过度煽情的渲染,也没有采取道德批判的姿态,它只是将那些难以想象的艰辛摆在了我们面前,任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重量。我总是在想,是怎样的经历,才能塑造出如此洞察世事却又不失悲悯的目光?那些人物的悲剧性,并非源于单一的外部压迫,而更多是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局限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读到某些情节时,我甚至会感到一种错愕,因为那份坦诚和直接,挑战了我对传统英雄叙事的刻板印象。它揭示了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光辉往往不是高歌猛进的,而是如同微弱却坚韧的烛火,在狂风中努力不灭,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伟大”。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对我来说,起初是一种挑战。它不像当下流行的那种情节紧凑、高潮迭起的作品,反而更像是一部缓慢流淌的、带着沉淀感的河流。它更注重环境的渲染和人物心理的细致剖析,而非事件的快速推进。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适应这种近乎散文化的叙事方式,但一旦沉浸其中,那种别样的韵味便开始显现。作者似乎并不急于将故事推向某个既定的终点,而是耐心地引导我们去观察、去感受,让时间本身成为叙事的主角。这种克制感,反而使得每一次情感的爆发都显得尤为珍贵和有力。读到某些段落时,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昏暗灯光下,默默缝补衣裳的旁观者,记录下这一切无声的抗争与和解。它要求读者放下浮躁的心态,用更接近“体悟”的方式去阅读,收获的自然也更为深厚。
评分我一直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世价值,而这本作品恰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但其中探讨的关于人与土地的关系,关于家族的延续与消亡,以及个体在集体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却是全人类共通的母题。我从中看到的,不仅是某一群人的历史,更是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出我们自身在面对生存压力时,最真实的反应和最深层次的渴望——对温暖、对意义、对不被遗忘的渴望。它没有给出任何简单的答案,也没有提供廉价的慰藉,它只是以一种近乎残酷的诚实,展现了生命的重量。这份厚重感,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恒久的生命力,值得被反复品读和沉思。
评分从文学技法的角度来看,作者对白描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那些精准而富有张力的场景描绘,构建了一个个立体可感的“世界”。比如对自然环境的刻画,风声、雪声、牲畜的低鸣,都不仅仅是背景,它们本身就是参与到人物命运中的重要力量。我特别欣赏那种用最简洁的词汇,捕捉住最复杂情绪的功力。有些句子读起来平淡无奇,但合上书本后细思,却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张力——那是生活本身在平静外表下翻滚的暗流。这种内敛的叙事风格,使得读者必须主动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去填补那些看似空白的地方。对我而言,这是一种高级的阅读体验,它考验的不是理解力,而是共鸣的深度和想象的广度。这种文学上的成熟度,使得作品的耐读性极高,每次重读都会有新的体会。
评分人生五十年,与天地长久相较,如梦又似幻;一度得生者,岂有不灭者乎?- 人间五十年,与天地相比 不过渺小一物 看世事,梦幻似水 任人生一度,入灭随即当前 此即为菩提之种,懊恼之情,满怀于心胸 汝此刻即上京都,若见敦盛卿之首级 放眼天下,海天之内,岂有长生不灭者? 日本的幕府时代,开始于两大武士氏族的殊死战争,史称“源平合战”。当时,平氏已经掌握朝政十数年,以太政大臣平清盛为首的平氏一门,遍布朝野,权倾天下。他们逐渐脱离了武士的生活,终日沉醉于音乐和诗歌之中,与平安朝以来奢糜浮华的公卿如出一辙。而源氏蛰居多年,一旦起事,在东国山野丛林中浴血奋战,心中只知仇恨,并无风雅。就此对比,胜负似乎就已经很明显了,两家仅对战了五年的时间,就以平氏彻底灭亡、源氏开创幕府时代而告终。 平敦盛是平氏的旁支,官至从四位下春宫大夫,平清盛弟修理大夫经盛之子,和清盛去世后的平氏领袖宗盛是堂兄弟。传说他容貌娇艳,多才多艺,尤其深通音乐,擅吹横笛。若能长在朝中,也许风雅一时无二,京城百姓也要为之倾心吧。但可惜源氏杀来,平氏西退。行军之中,烟尘扑面,发髻难梳;对阵之间,鼙鼓雷响,雅乐无用。到了元历二年(1185)二月,爆发了著名的一之谷合战,年仅十六岁的敦盛参加了这场战役,并且就此首身分离。 二月六日,两军对峙于一之谷,夜半时分,敦盛难以入眠,爬起身来。他随身携带着一支心爱的名笛,名为“小枝”,当下取出“小枝”,吹奏一曲,以平定澎湃起伏的心境。夜深月高,四野无声,优雅的笛声传得很远。不仅本方阵中,竟然连敌人也纷纷醒来,侧耳倾听,赞不绝口。 源氏阵中,有一猛将,名为熊谷直实,本是武藏国熊谷乡的土豪,力大无穷,武艺高强。熊谷虽是武人,倒也粗通音律,凝神细听,拍案叫好:“不想平氏阵中,有如此风雅之人,大战将发,坦然吹笛,而笛声清澈动人,没有丝毫浑浊紊乱的迹象。” 果然第二天清晨,战斗便即爆发。本来论起兵力,平氏略占上风,但是源氏名将九郎判官义经突然抄小路从后杀出,虽仅数十骑,但在腹背受敌的平家兵将看来,却以为敌人大军已到身后。心胆既怯,士气崩溃,平家兵将再无恋战之心,纷纷往停靠在海边的战船上逃去。源家军兵从后掩杀,斩首无数,血流成河。平家诸栋梁和公子——忠度、经正、经俊、通盛、业盛、知章,尽皆讨死,重衡被俘,押去镰仓。 且说敦盛,催动胯下马,急急奔逃,终于跃入水中,正准备登上战船,忽听身后有人呼唤道:“前面的武将,为何忙忙如丧家之犬?何不掉转马头,拿起武器,与某恶战一场,分个胜负。如何?”敦盛回头望去,一员白旗(平氏红旗,源氏白旗)将领立马于岸上叫阵。原来此人正是熊谷直实,一路追杀平家败兵到此,远远看见敦盛大铠华丽,气宇不凡,料想定是大将,因此喝骂挑战。 平氏虽已腐化,终是武士出身,有人喊阵,怎能不应。于是敦盛分开海水,驳马登岸,抽出刀来,就与直实战到了一处。两人马打盘旋,刀光相激,母衣(武将系在背上的装饰织品,四角固定,当风以后张开如鼓)鼓风,好不激烈。那直实本是关东有名的猛虎,敦盛不过初上战场的少年公子,不几回合,就被直实打落马下。直实也立刻跳下马来,拔出肋差,按住敦盛,掀起头盔,就欲取下敌将的首级。可是突然看到敦盛的容貌,呀,直实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僵在了那里,再难动手。 原来敌将非常的年幼,比较年龄,恰与直实的孙辈相近。且是眉清目秀,风朗俊雅,含羞忍辱,却并不呈现恐惧之色。直实再一低头,看到了插在敦盛腰间的“小枝”——呀,莫非昨夜吹笛,清澈悠扬,声感我阵的,就是眼前这个少年吗?直实缓缓放开敦盛,说道:“你还年青,何苦来到阵前厮杀,枉送性命。我今放汝归去,从此专研音律,再不要到血腥的战场上来了。” 直实想要放走敦盛,但是敦盛并不领情,他说道:“我是平家大将、春宫大夫敦盛,是平修理大夫之子,并非不懂事的少年人。我不上阵则罢,既然上阵,身为平家武士,岂能贪生怕死?你武艺高强,打败了我,就割了我的首级领功去吧。源平两家,世代为仇,何况战场之上,两阵之间,岂能对敌人存有怜悯之心?”直实反复劝说,年纪尚轻,何故寻死?但是敦盛死志已绝,偏偏不肯离去。身后喊杀之声渐响,源家大兵即将杀到。直实心道,我军已到,我不杀他,他也必被人杀,到时不知他会再受什么无端屈辱,岂不反是我的罪过?于是咬一咬牙,挥胁差割下了敦盛的首级。可怜一位年轻公子,优雅无双,却就因此魂归极乐去也。
评分字有点小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还没看,应该会不错。
评分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评分不错、品质有保证、希望坚持正品
评分优点是活动时入手,及其便宜,充实家中的书架!
评分好书,便宜
评分书封面有污渍,内容没问题。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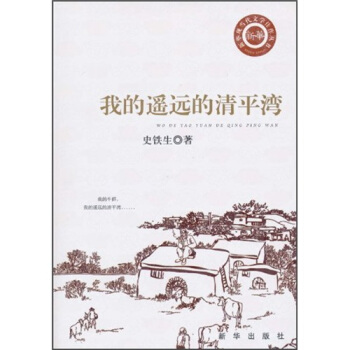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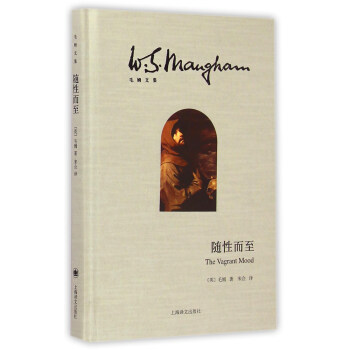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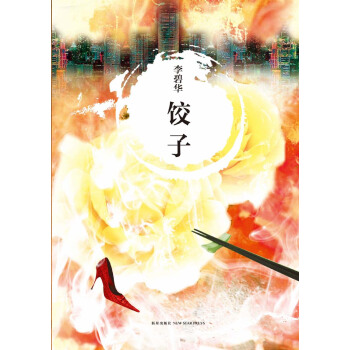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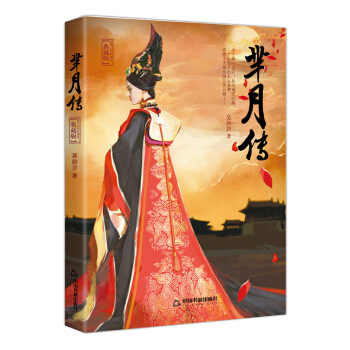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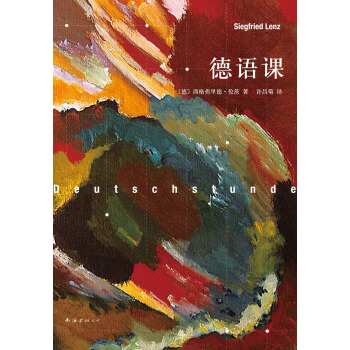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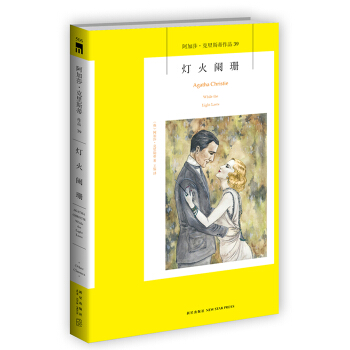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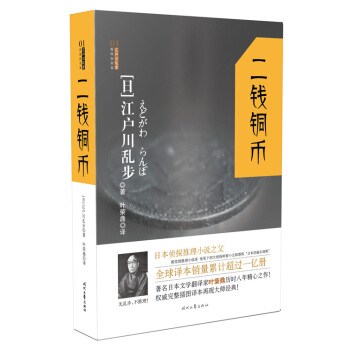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12:人性记录 [Agatha Christie Lord Edgware Di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05224/rBEhU1MKxXgIAAAAAADE2108rKAAAI97wFjSBoAAMTz8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