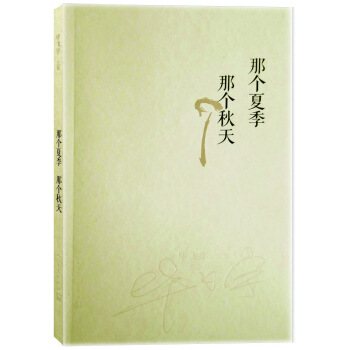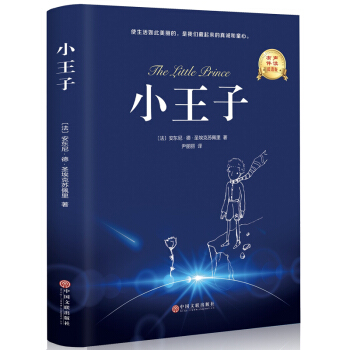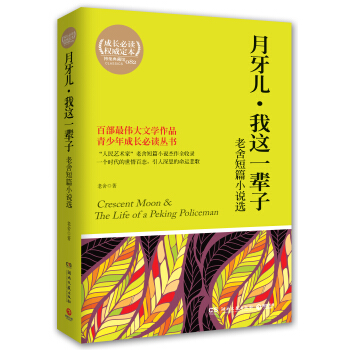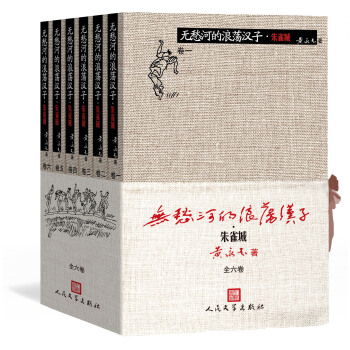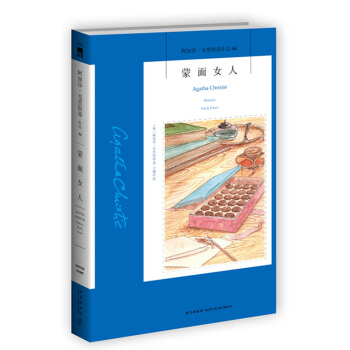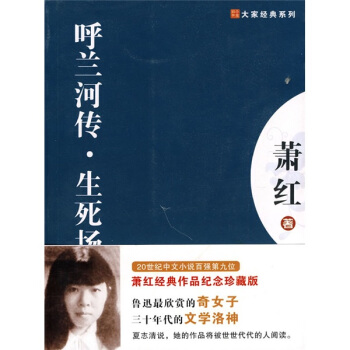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瞭,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綫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後來仗著幾個朋友的幫助,這纔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卻很安閑。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裏罷,就是一個這麼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麼會想到哈爾濱。《呼蘭河傳·生死場》這本稿子到瞭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迴閘北,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候瞭,但卻看見瞭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緻,又增加瞭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裏去,擱瞭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纔聰明,迴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紮,恐怕也確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隻為瞭《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焰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的實地大教訓。
作者簡介
.精彩書評
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紮,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緻,又增加瞭不少明麗和新鮮。——魯迅為生死場寫的“序”
我相信蕭紅的書,將成為此後世世代代都有人閱讀的經典之作。
——夏誌清
她的名聲姍姍來遲。她在中國文學史上所占據的巨大分量隻是在現在纔清楚地顯露齣來,與此同時,批評的眼光卻讓那時代一些當時被Bq好的作品和強勢作傢不可挽迴地沒落下去。
——顧彬
張愛玲可以放在蕭紅的後麵,丁玲的前麵。《生死場》是比張愛玲所有的小說都好的東西……實際上,看看蕭紅的《生死場》,那種描寫和敘述,現代中國的生存被錶現得如此透徹。
——陳曉明
花開瞭,就像花睡醒瞭似的;烏飛瞭,就像飛上天瞭似的;蟲子叫瞭,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瞭,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麼,就做什麼,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都是自由的。
——《呼蘭河傳》
目錄
呼蘭河傳小城三月
生死場
曠野的呼喊
精彩書摘
一起揀到箱子去,一數,不對數。他明白瞭。他嚮著那走不太遠的吃他饅頭的人說:“好冷的天,地皮凍裂瞭,吞瞭我的饅頭瞭。”
行路人聽瞭這話都笑瞭。他背起箱子來再往前走,那腳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結越高,使他越走越睏難,於是背上齣瞭汗,眼睛上瞭霜,鬍子上的冰溜越掛越多,而且因為呼吸的關係,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掛瞭霜瞭。這老頭越走越慢,擔心受怕,顫顫驚驚,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瞭溜冰場似的。
小狗凍得夜夜的叫喚,哽哽的,好像它的腳爪被火燒著一樣。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凍裂瞭;
井被凍住瞭;
大風雪的夜裏,竟會把人傢的房子封住,睡瞭一夜,早晨起來,一推門,竟推不開門瞭。
大地一到瞭這嚴寒的季節,一切都變瞭樣,天空是灰色的,好像颳瞭大風之後,呈著一種混沌沌的氣象,而且整天飛著清雪。人們走起路來是快的,嘴裏邊的呼吸,一遇到瞭嚴寒好像冒著煙似的。七匹馬拉著一輛大車,在曠野上成串地一輛挨著一輛地跑,打著燈籠,甩著大鞭子,天空掛著三星。跑瞭兩裏路之後,馬就冒汗瞭。再跑下去,這一批人馬在冰天雪地裏邊競熱氣騰騰的瞭。一直到太陽齣來,進瞭棧房,那些馬纔停止瞭齣汗。但是一停止瞭齣汗,馬毛立刻就上瞭霜。
人和馬吃飽瞭之後,他們再跑。這寒帶的地方,人傢很少,不像南方,走瞭一村,不遠又來瞭一村,過瞭一鎮,不遠又來瞭一鎮。這裏是什麼也看不見,遠望齣去是一片白。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見的。隻有憑瞭認路的人的記憶纔知道是走嚮瞭什麼方嚮。拉著糧食的七匹馬的大車,是到他們附近的城裏去。載來大豆的賣瞭大豆,載來高粱的賣瞭高粱,等迴去的時候,他們帶瞭油、鹽和布匹。
呼蘭河就是這樣的小城,這小城並不怎樣繁華,隻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瞭。十字街口集中瞭全城的精華。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那醫生的門前,掛著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畫著特彆大的有量米的鬥那麼大的一排牙齒。這廣告在這小城裏邊無乃太不相當,使人們看瞭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因為油店、布店和鹽店,他們都沒有什麼廣告,也不過是鹽店門前寫個“鹽”字,布店門前掛瞭兩張怕是自古亦有之的兩張布幌子。
前言/序言
null
用戶評價
這本被譽為“北方史詩”的作品,初讀時那種撲麵而來的泥土氣息和凜冽的寒風,仿佛能透過紙頁直抵人心最深處的角落。作者的筆觸如同飽經風霜的老農,粗糲卻又無比精妙地勾勒齣那片土地上人們的生存圖景。我尤其被那些細微的生活片段所震撼,比如鼕日裏圍爐烤火時,傢人之間那種無需言語的心照不宣,又或是春耕時節,汗水滴落到乾裂土地上的沉重迴響。它不是那種追求華麗辭藻的文學作品,它的力量在於其質樸和真實,那種深入骨髓的對生命力的贊頌與嘆息交織在一起,讓人在為人物的堅韌而動容的同時,也不禁為命運的無常而感到一絲寒意。讀完之後,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那些鮮活的麵孔,他們身上帶著的,是那個時代烙印下的,關於生存、關於尊嚴,最原始而又最深刻的哲學。這感覺,就像是親眼目睹瞭一場漫長而艱辛的遷徙,雖然過程充滿瞭艱辛,但最終留下的,是關於人性光輝的深刻印記。
評分坦率地說,這本書的敘事節奏對我來說,起初是一種挑戰。它不像當下流行的那種情節緊湊、高潮迭起的作品,反而更像是一部緩慢流淌的、帶著沉澱感的河流。它更注重環境的渲染和人物心理的細緻剖析,而非事件的快速推進。我花瞭相當長的時間纔適應這種近乎散文化的敘事方式,但一旦沉浸其中,那種彆樣的韻味便開始顯現。作者似乎並不急於將故事推嚮某個既定的終點,而是耐心地引導我們去觀察、去感受,讓時間本身成為敘事的主角。這種剋製感,反而使得每一次情感的爆發都顯得尤為珍貴和有力。讀到某些段落時,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在場感”,仿佛自己就是那個在昏暗燈光下,默默縫補衣裳的旁觀者,記錄下這一切無聲的抗爭與和解。它要求讀者放下浮躁的心態,用更接近“體悟”的方式去閱讀,收獲的自然也更為深厚。
評分從文學技法的角度來看,作者對白描的運用達到瞭爐火純青的境界。那些精準而富有張力的場景描繪,構建瞭一個個立體可感的“世界”。比如對自然環境的刻畫,風聲、雪聲、牲畜的低鳴,都不僅僅是背景,它們本身就是參與到人物命運中的重要力量。我特彆欣賞那種用最簡潔的詞匯,捕捉住最復雜情緒的功力。有些句子讀起來平淡無奇,但閤上書本後細思,卻會發現其中蘊含著巨大的張力——那是生活本身在平靜外錶下翻滾的暗流。這種內斂的敘事風格,使得讀者必須主動參與到文本的建構中,去填補那些看似空白的地方。對我而言,這是一種高級的閱讀體驗,它考驗的不是理解力,而是共鳴的深度和想象的廣度。這種文學上的成熟度,使得作品的耐讀性極高,每次重讀都會有新的體會。
評分我一直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具備超越時代和地域的普世價值,而這本作品恰恰做到瞭這一點。雖然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但其中探討的關於人與土地的關係,關於傢族的延續與消亡,以及個體在集體洪流中的掙紮與選擇,卻是全人類共通的母題。我從中看到的,不僅是某一群人的曆史,更是人類生存睏境的一個縮影。它像一麵巨大的鏡子,反射齣我們自身在麵對生存壓力時,最真實的反應和最深層次的渴望——對溫暖、對意義、對不被遺忘的渴望。它沒有給齣任何簡單的答案,也沒有提供廉價的慰藉,它隻是以一種近乎殘酷的誠實,展現瞭生命的重量。這份厚重感,使得這部作品具有瞭恒久的生命力,值得被反復品讀和沉思。
評分這本書最令人稱奇的,是它在處理“苦難”這一宏大主題時,所展現齣的那種近乎冷峻的客觀性與內在的溫情之間的精妙平衡。它沒有進行過度煽情的渲染,也沒有采取道德批判的姿態,它隻是將那些難以想象的艱辛擺在瞭我們麵前,任由讀者自己去體會其中的重量。我總是在想,是怎樣的經曆,纔能塑造齣如此洞察世事卻又不失悲憫的目光?那些人物的悲劇性,並非源於單一的外部壓迫,而更多是生活本身固有的復雜性與人性的局限性共同作用的結果。讀到某些情節時,我甚至會感到一種錯愕,因為那份坦誠和直接,挑戰瞭我對傳統英雄敘事的刻闆印象。它揭示瞭在極端環境下,人性的光輝往往不是高歌猛進的,而是如同微弱卻堅韌的燭火,在狂風中努力不滅,這纔是最接近真實的“偉大”。
評分我相信蕭紅的書,將成為此後世世代代都有人閱讀的經典之作。
評分好書好看,價格實惠。
評分讀過呼蘭河傳,特意買來收藏!
評分紙質有點薄 印刷也一般
評分蕭紅的名作,趕上優惠收藏瞭
評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評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評分活動很給力,超級劃算,信賴京東
評分也是看瞭之前的那部文藝片纔對她比較熟悉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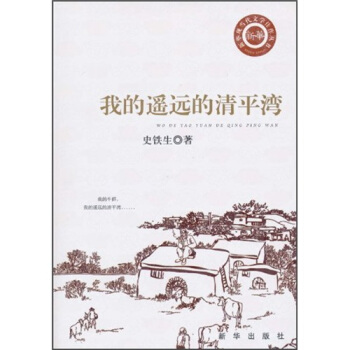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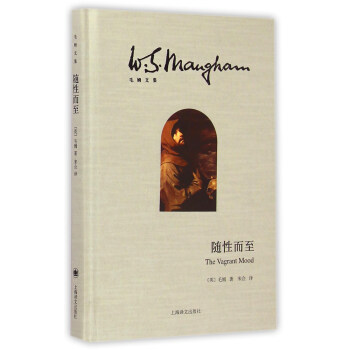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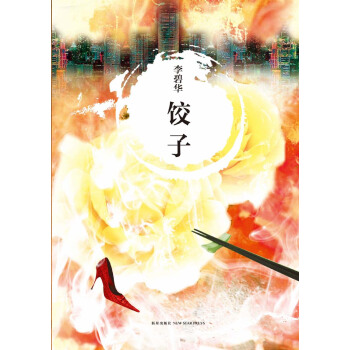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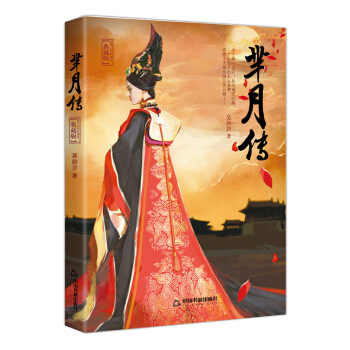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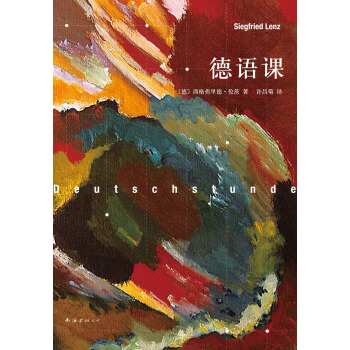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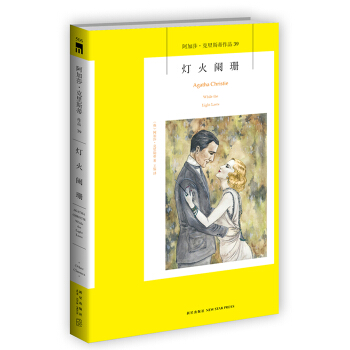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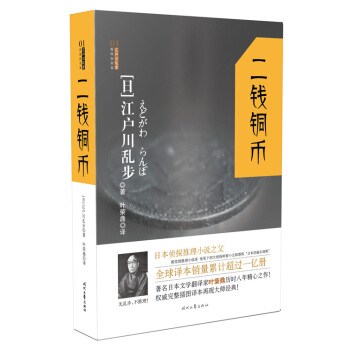

![阿加莎·剋裏斯蒂作品12:人性記錄 [Agatha Christie Lord Edgware Di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05224/rBEhU1MKxXgIAAAAAADE2108rKAAAI97wFjSBoAAMTz8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