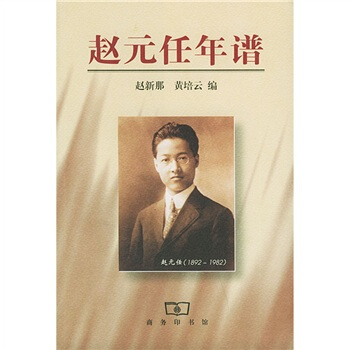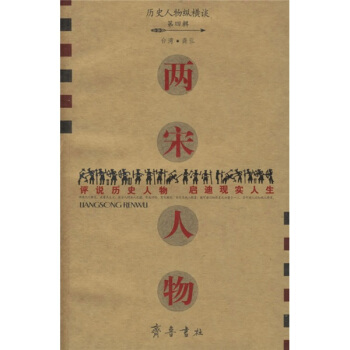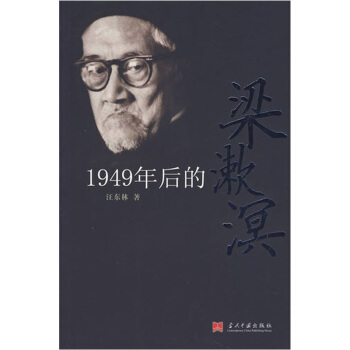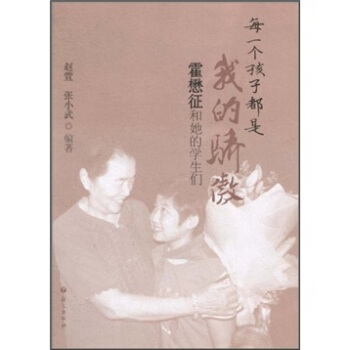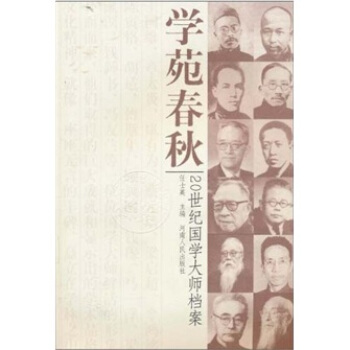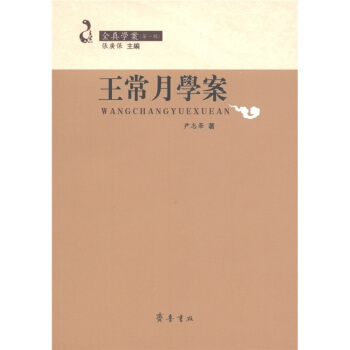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他是盛唐天子,在风诡云谲的宫廷斗争中杀出一条血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开元盛世;他是风流皇帝,曲折缠绵的爱情美丽得让人们忽视了所有伦理的束缚,一阕《长恨歌》成为多少恋人吟唱不尽的悠悠恋曲;
他是梨园祖师,羌笛羯鼓的清音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停息地吟唱着那永远溢彩流光的霓裳羽衣;他先明后暗,北地的战鼓惊碎了华清池里的绮梦,马嵬的哀歌宜告了那一段黄金岁月的终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翻开这本书。
倾听两位历史学家为你讲述,那段瑰丽、怆然、悠远的故事。
内容简介
唐玄宗并不是天生的皇帝,他的皂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得到的。在位期间,他任用贤相,整顿吏治,改善财政措施,进行军事体制变革,弘扬文学艺术,在唐太宗和武则天之后,使唐王朝再登高峰,开元天宝成为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然而,一系列措施导致的安史之乱成为这个时代的休止符,盛极而衰这样大喜大悲的历史场景都由玄宗导演而成,无论怎样的浓墨重彩和口诛笔伐也说不尽这个风流人物。作者简介
阎守诚,1942年6月出生于广西桂林,祖籍山西五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隋唐五代史。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口史》,《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主编)等。吴宗国,1934年出生于南京,祖籍江苏如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主要著作有《唐代科举制度研究》、《隋唐五代简史》、《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主编)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卷首语一 厄运中的王子
二 潞州别驾
三 诛灭韦党
四 铲除太平
五 开元天子与“救时之相”
六 巩固皇位,安定政局
七 整顿吏治
八 改善财政的措施
九 检括田户
十 军事体制的变革
十 张说的沉浮
十二 宫闱悲剧
十三 运粮关中,久住长安
十四 张九龄与李林甫
十五 忠诚的高力士
十六 广运潭盛会
十七 盛唐气象
十八 纳妃、佞道、游乐
十九 扬国忠其人
二十 文士境遇的逆转
二十一 开天边事
二十二 安禄山的崛起
二十三 鼙鼓声中
二十四 重返长安
精彩书摘
垂拱元年秋八月初五(685年9月8日),大唐新皇帝睿宗的德妃窦氏在东都洛阳生了个男孩子,取名隆基。这是睿宗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以后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唐玄宗(唐明皇)。当隆基降临人世时,唐王朝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时代,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一片升平景象。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却并不稳定,不时发生的政治事件酝酿着巨变,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隆基诞生前两年,弘道元年(683)十二月,他的祖父高宗皇帝李治病逝。长期以来,高宗身体状况欠佳,从显庆五年(660)开始,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隆基的祖母、高宗皇后武则天开始协助处理一些政务。武则天“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深得高宗信任。在高宗晚年,武则天逐渐掌握了唐廷实权,“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高宗去世之后,皇太子李哲继位,是为中宗。中宗尊奉武则天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
但是,中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就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赶下了皇位。武则天把皇冠授给了小儿子、李哲的弟弟睿宗李旦。
中宗被废,是因为他刚刚登上皇位,就急于树立自己的私党,想任命岳父韦玄贞为侍中,授乳母之子为五品官。不久前,韦玄贞由于女儿成为皇后而由普州参军晋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地再升为侍中显然不合适。这个提议受到当朝宰相裴炎的坚决反对。年轻的皇帝大为恼火,悻悻地说道:“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把这件事报告武则天,经过一番密谋,光宅元年(684)二月初六,武则天在乾元殿召集百官,裴炎和中书侍郎刘棉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昂率兵人宫,宣布太后命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当李哲被人从皇帝宝座上“扶”下来时,还问道:“我何罪?”武则天说:“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这样回答,既冠冕堂皇,也有些强词夺理。武则天抓住年轻皇帝在气愤时讲的一句过头话大做文章,其实是因为自从高宗死后,她已经大权在握,正积极而有步骤地把女皇梦变成现实,任何阻挠她达到目的的势力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摧毁,即使是温情脉脉的母子之情,也不例外。武则天的个性是坚毅严酷的,她对政敌的打击绝不心慈手软,惟其如此,她才能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存在发展并取得胜利。她把儿子放在皇位上,只是因为自己登上皇位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她并不希望儿子真正行使皇帝的权力,更不允许他滥用权力。中宗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对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对母亲的个性和思想,都缺乏正确的了解。他以为自己是皇帝,就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他自以为是的行为恰好触犯了严厉的母亲,刚刚戴上的皇冠很快就被摘下来了。
转瞬之间的皇位嬗递,使隆基得以诞生在大富大贵的皇帝之家。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随之也就笼罩在幼小的隆基头顶,预示着他前程坎坷,厄运重重。
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废掉中宗,扶立睿宗,显示了极大的权威,标志着她圣衷独断的时代开始了,“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以视朝”。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加快了称帝步伐。她改东都为神都,改易旗帜、服饰的颜色,改易政府各部门的名称和官名,任用侄儿武承嗣为宰相,追封武氏五代祖为王。这些咄咄逼人的措施,变更着唐廷的祖宗成法,造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中宗被废后数月,发生了以英国公徐敬业为首的扬州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虽然很快被平定,但它使武则天感到宫廷内外反对派的潜在势力依然强大。于是,她大开告密之门,重用酷吏,采取高压手段,打击反对派势力,屠杀持反对意见的官员。李唐宗室是反武势力的中坚,也是武则天称帝的主要障碍,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打击尤其沉重。诛杀李唐宗室的事件迭起,至武则天称帝之前,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除武则天自己生的李哲(中宗,又名显)和李旦(睿宗)以外,其余在世的全部被杀。“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
载初元年(690)九月九日,武则天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她自称“圣神皇帝”,降睿宗为皇嗣,赐姓武。这一年,隆基五岁。三岁时,他曾受封为楚王。隆基的童年时代,是在李唐宗室惨遭屠戮的恐怖气氛中度过的。幸运的是,由于父亲睿宗的聪明睿智,不仅使睿宗自己在险恶的环境中得以平安无恙,也使隆基兄弟姐妹处于较为安全的地位,可以享受一点童年的欢乐。睿宗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为人“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和哥哥们相比,睿宗对母后武则天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对宫廷斗争的形势和力量的对比也都有明确的认识。他即位后,垂拱二年(686)正月,“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太后复临朝称制”。睿宗不像哥哥中宗那样,以为当了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在太后临朝称制的情况下,甘心做一名无所作为的皇帝,不去干扰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所以,“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睿宗贵为皇帝,也仅仅是能免祸自保,“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可见隆基兄弟从小就过着幽禁宫中的生活,他们童年时代的欢乐是极其有限的。
历史上把改唐为周的事件称为“革命”。围绕着这场革命,大唐的政治生活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轩然大波,使这段历史显得格外惊心动魄,丰富多彩。一切事件的中心是武则天,她的光辉普照着这个时代。隆基正是在他雄才大略的祖母统治下,步入了青少年时期,开始了不平凡的经历。
在武周时期,隆基的父亲皇嗣李旦的处境一直是很窘迫的。武则天称帝那年,已经67岁了。她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斗争,才成为大周的神圣皇帝,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虽然她掌握着唐王朝的最高权力,宫廷斗争并没有因此而止息,只是斗争的焦点由称帝和反称帝转换为皇位由李氏、还是由武氏来继承。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双方,一方是以武承嗣、武三思为核心的武氏集团,另一方是忠于李唐王室的朝廷重臣,他们认为应由李氏继承皇位。武则天的态度并不明朗,犹豫于双方之间。作为皇嗣的李旦地位不很稳固。皇嗣是一个含义微妙的名称。它可以解释为皇位的继承人,可是又比“太子”这样的皇位继承人的传统名分和地位降了一格。武则天给李旦以“皇嗣”名位,表明她还没有下决心把他当成真正的皇位继承人。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武则天是重武轻李的,也许她更多地倾向于在武氏子弟中选择皇位继承人,因此,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在为谋求成为“太子”而大肆活动,他们当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皇嗣,欲取而代之。李旦既得不到武则天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只能处于被动挨整的地位。
如意元年(692)九月,武则天因齿落更生,宣布改元长寿。十月,睿宗诸子出阁,隆基兄弟可以开府置官属。这位严厉的祖母由于自己的健康长寿,心情愉快,放松了对子孙们的控制,让他们有一些独立活动的余地。隆基这时“年始七岁”,却做出了一件震动宫廷的事情:
朔望,车骑至朝堂,金吾将军武懿宗忌上严整,诃排仪杖,因欲折之。上叱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则天闻而特加宠异之。
这是武则天称帝后,李、武两姓间第一次正面冲突。武懿宗是武则天伯父仕逸的孙子,被封为河内郡王。这个武周新贵正在春风得意、趾高气扬的时候,看到隆基的车骑仪仗威严而整齐,心中老大的不快,便用金吾将军纠察风纪的权力横加阻挠,企图挫折隆基。然而隆基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责问:“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这针锋相对的回击,表明幼小的隆基个性倔强,已经有了权力斗争的意识。隆基政治上的早熟是和家庭教育、环境影响分不开的。他从小生活在宫廷斗争的旋涡之中,以李、武两姓的矛盾为焦点的权力之争,在耳濡目染间熏陶着他,使他很早就懂得了自己的地位和使命,激发了他为维护“吾家朝堂”而奋斗的精神,这也是他日后从事政治斗争的巨大动力。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厚度适中,拿在手里感觉很踏实,不像一些薄薄的书籍,读起来意犹未尽。我推测,这可能是一部内容非常充实的作品,作者在编撰过程中,一定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封面上的文字,包括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信息,都清晰地排列着,给人一种专业、严谨的印象。我喜欢这种简洁明快的排版风格,它让读者能够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书的内容本身。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深入剖析中国古代帝王心路历程和政治决策的书籍,而《唐玄宗的真相》这个名字,无疑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一类。我非常期待能够从这本书中,了解到唐玄宗这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真实的一面,以及那些影响深远的决策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动因和考量。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不是一本泛泛而谈的读物,而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读、反复琢磨的学术著作,充满了智慧的火花和历史的深度。
评分从书的整体风格来看,它似乎继承了某种古典叙事的精髓,但又融入了现代的审美视角。我猜想,作者在文字的运用上,一定花费了不少心思,力求在严谨的历史考据与生动的文学表达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封面上的字体选择也很有讲究,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现代的流畅性,与整体的视觉风格非常契合。我试着翻阅了几页,发现排版清晰,字间距适中,阅读起来非常舒适,不会有压迫感。这对于一部篇幅可能不短的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考量。我尤其注意到,书中的插图(如果存在的话)会不会也同样精美,能否有效地辅助读者理解书中的内容,让历史的画面感更加鲜活。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运用一些独到的笔触,将那些看似遥远的过往,描绘得生动立体,仿佛我能够穿越时空,亲临那个时代,感受历史的脉搏。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不仅仅是一本读物,更是一次沉浸式的体验,是对历史细节的深度挖掘和艺术化呈现。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质量实在是令人称道,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因为它直接影响到阅读的体验和书籍的收藏价值。封面的材质触感很好,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而且不易留下指纹,保持了书籍的整洁。内页的纸张厚实且不易透墨,这对于我这种喜欢用钢笔阅读的人来说,简直是福音,再也不用担心写下的笔记会影响下一页的清晰度了。书的整体设计有一种沉静而典雅的气质,没有过于花哨的装饰,但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流露出一种匠心独运的专业精神。我注意到书名《唐玄宗的真相》本身就带着一种探究和揭示的意味,让人联想到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真相,等待着被重新发掘和审视。我期待这本书不仅仅是简单地陈述史实,更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一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深入解读,引发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从这本书的外观,我就能感受到作者和出版方对内容的重视,以及对读者阅读体验的尊重。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非常有吸引力,深邃的背景色衬托着人物剪影,让人一眼就对书名产生了好奇。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书店的推荐区看到的,当时就被它沉甸甸的分量和精美的装帧所吸引。书页的纸质也相当不错,摸起来有质感,闻起来有淡淡的书香,这对于一个热爱阅读的人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体验。我尤其喜欢它的大小,既方便携带,又能在阅读时提供足够的空间感,不像有些小开本的书,字太密集会让人眼花缭乱。书脊的设计也很用心,采用了烫金工艺,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即使只是摆放在书架上,也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封底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本书的宏大叙事,让我对即将展开的旅程充满了期待。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又将带我走进一个怎样波澜壮阔的时代。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仪式感,仿佛捧在手中的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一份等待被发掘的宝藏。
评分当我第一次在书店看到这本书时,它的名字就牢牢抓住了我的眼球。《唐玄宗的真相》——这几个字瞬间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好奇。唐玄宗,这个名字本身就承载了无数的历史故事和传奇色彩,而“真相”二字,则暗示着这本书将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回顾,而是可能揭示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或者对已有的认知进行一次颠覆性的解读。我非常喜欢这种带有探讨性和思辨性的书名,它预示着一场智识的冒险即将展开。封面的设计也恰到好处地烘托了这种氛围,没有过于张扬,但隐约透露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故事的神秘感,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我喜欢这种“欲说还休”的设计,它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让人们在未读之前就充满了对书中内容的无限遐想。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对历史有着深刻洞察力和独到见解的学者,能够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复杂、也更加引人入胜的唐玄宗时代。
评分唐隆元年(710年)六月庚子日申时,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先天元年(712年)李旦禅位于李隆基,后赐死太平公主,取得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于长安太极宫登基称帝[1]。前期注意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他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极盛之世,在位后期宠爱杨贵妃,怠慢朝政,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塞外民族试图来稳定唐王朝的边疆,结果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为唐朝中衰埋下伏笔。天宝十五年(756年)太子李亨即位,尊其为太上皇。宝应元年(762年)病逝,终年78岁,葬于泰陵。庙号玄宗,又因其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清朝为避讳康熙帝之名玄烨,多称其为唐明皇。
评分不过看样子应该也是不错的了
评分京东的图书已经日趋强大,很好很不错
评分好书
评分京东不错,好评!
评分李隆基的功过一生,本书描写声情并茂,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唐玄宗
评分难得的好书啊难得的好书啊难得的好书啊难得的好书啊
评分京东的图书已经日趋强大,很好很不错
评分难得的好书啊难得的好书啊难得的好书啊难得的好书啊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