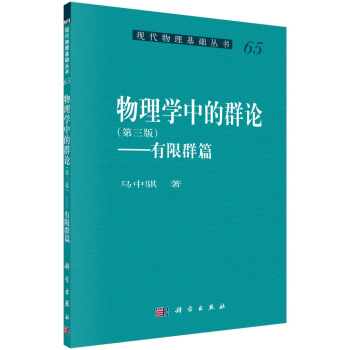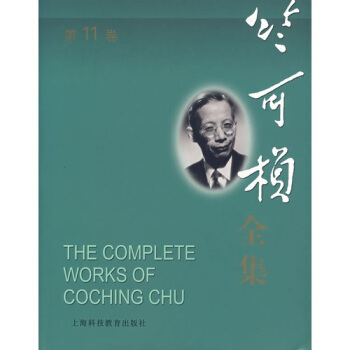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38年连续记述,1000余万字完整存世。一代宗匠竺可桢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在竺可桢生前,其日记是秘不示人的,作为史料宝库,如今以全貌公诸于世。
内容简介
在竺可桢生前,其日记是秘不示人的;作为史料宝库,如今以全貌公诸于世。
《竺可桢全集(第11卷)》收录1948-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
两年的时间,经历了民国和共和国两个时代,从杭州到上海,再迁至北京。为维持浙大运转而四处筹款,爱生护校。不去台湾,避居上海。告别旧朝,参与新政。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述科学与社会:纸与指南针中国知之甚早,何以近代科学不能产生于中国?
谈办大学之基本信仰:人人可以为圣人;教授治校。
论大学发展之关键:最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
勖勉学生: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
自强不息实为目前之急务。
校庆演讲:惟有每公民能公而忘私,恕人责己,国家才会太平,民族才会复兴。
反对保送办法:不经考试,又可保送,均属自私自利之举。
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有话: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
费正清论盛清人口猛增与玉米、红薯传入之关系,观点源自竺可桢。
章士钊述国共和议经过。
人才难得钱三强实科学院最初组织时之灵魂也。
力挺科学建议在《共同纲领》中设专门条款。
作者简介
竺可桢(1890—1974),气象学、地理学家,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早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年回国,先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南京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及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著有《竺可桢文集》。目录
前言关于竺可桢日记
日记编例
第11卷说明
1948年
日记
读书笔记
杂记
本年事要
子女成绩
通讯录
1949年
日记
本年事要
卅八年定西文杂志
收支账册
1950年国家预算草案
Elementary School(U.S.S.R.)
附录一 第11卷人名简释表
附录二 竺可桢家系人物表
附录三 张侠魂家系人物表
附录四 陈汲家系人物表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作为一名对科学史怀有浓厚兴趣的爱好者,《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中的许多篇章,都令我爱不释手。我一直对中国近代科学是如何从零开始,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感到着迷,而卷中关于竺先生个人经历和学术思想的论述,恰恰满足了我的这份好奇。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国内外求学、工作的点点滴滴,那些充满挑战的学术研究,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近代科学发展画卷。我尤其欣赏竺先生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不仅是科学的实践者,更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通过阅读这些文字,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科学工作者的不易与伟大,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坚持,如何为国家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不仅仅是阅读一本传记,更是一次对科学精神的洗礼。
评分作为一名对历史与自然科学都充满好奇心的读者,我有幸沉浸在《竺可桢全集》的世界里。我手上的这本,是全集中的第十一卷,翻开它,仿佛开启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卷中的篇章,不像我平时阅读的那些通俗读物,它们更像是一条条深邃的思想河流,需要我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反复咀嚼。我常常在深夜,伴着一盏孤灯,读到那些关于中国近代气象学发展筚路蓝缕的记述,深感竺先生当年是如何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才智,在一穷二白的环境下,为国家留下宝贵的科学遗产。那些详细的观测数据、严谨的分析方法,无不体现着科学的严谨与魅力。同时,书中对中国地理环境变化的长期关注,也让我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不仅仅是山川河流的堆叠,更是数千年人类活动与自然演变相互作用下的独特产物。阅读这些内容,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看到先辈们辛勤耕耘的身影,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给予的。
评分近期有幸研读《竺可桢全集》的第十一卷,其中一些关于自然灾害研究的章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界变化对社会的影响抱有关注,而卷中对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水旱灾害的深入剖析,让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竺先生并非仅是罗列史料,而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结合气象、水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对灾害的成因、过程、影响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更蕴含着对未来防灾减灾的宝贵启示。我从中看到了科学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巨大价值,也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人民在面对自然挑战时的智慧与韧性。阅读这些篇章,让我对“天灾”有了更科学、更辩证的理解,也更加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评分这本《竺可桢全集》(第11卷)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既有挑战又充满收获的阅读之旅。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农事节气与天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卷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无疑是一份宝藏。竺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将天文学、气象学、以及农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梳理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脉络,以及这些知识如何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对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尤其被那些关于古代气象观测仪器和方法的描述所吸引,它们展现了中国古人观察自然的智慧和细致。虽然有些专业术语需要反复查阅,但这种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极富乐趣。它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其实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而竺先生,无疑是其中一位伟大的巨人。阅读这些篇章,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对先人智慧的敬仰,一种对科学精神的传承。
评分我对《竺可桢全集》(第11卷)的阅读体验,可以用“豁然开朗”来形容,尤其是在接触到其中关于中国地理学与历史地理研究的部分。我一直对中国广袤的地理疆域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而卷中的论述,则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竺先生不仅仅是简单地描述地理特征,他更深入地探讨了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民族迁徙、文化发展乃至政治格局的塑造作用。那些关于中国季风气候的成因分析,以及它如何影响了中国南北方的差异,都让我对“中国”这个概念有了更具象、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卷中对历史上重大地理事件的考证,如黄河的改道,都让我惊叹于大自然的伟力与人类在其中的渺小与顽强。这部分内容,不仅满足了我对地理知识的渴求,更引发了我对人地关系、区域差异以及历史变迁的深刻反思,受益匪浅。
评分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尊重我们。就算不愿意买书,你也可以选择借阅朋友的,或者在图书馆,在书店看完。不要让作者们的心血,成为盗版商们赚钱的工具。应该获得劳动酬劳的,是辛苦写作的作者们,而不是等着靠网络电子版赚钱的流着口水不劳而获的盗版商人。 当然,也会有讨厌我的人恶意上传电子文档,我无可奈何,中国的法律还不健全。但是,至少,希望一直默默支持我的读者们,希望喜欢小时代的你们,可以保护这本书,可以让它凭借真实的销量,为这个系列划上一个我们都为之高兴,为之喝彩的句点。 最后,对于情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结局,但结局只有一种。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现实的生活,也是充满了悲欢离合,大团圆的结局一般都是在电影里,言情小说里,而我们真实的世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这个结局让你心痛,让你难过,让你愤怒,那么就证明,你依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你依然有一颗清澈的心,因为你对美好事物的逝去,会和我一样,感到心碎。那么,这本小说,也就值得了,至少,唤起了这个冷漠世界里更多的人,对友情的珍惜,对青春的留恋。 我有想过无数种结局,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结局是不是最多人想要的结局,我也不知道这个结局是不是最好,但是,它是我辗转反侧,在无数个不眠之夜过去后,最后的选择。 失望也好,愤怒也好,伤感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就是小时代的魅力,这就是属于我们一同走过的五年。谢谢你们,每一个遥远的我未曾蒙面的阅读者们,谢谢你们陪伴的这五年。 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啦。 在落笔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刚刚接到出版社宣传部的同事传来的消息:在一个全国性的媒体票选奖项中,我入围了。但微妙的地方在于,我并不是入围了最佳作品或者最佳作家的奖项,反而,我和几位中国出版界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前辈们,一起入围了“最佳出版人”的奖项。 从我第一次做出品人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过四年的时间。这四年里,确实有很多作者从《最小说》这个平台开始,迅速崛起,成为全国出版界的新锐,他们囊括了各大奖项的同时也收获了近几年来其他新生代作者无人能敌的市场销量。能够有幸作为他们的出版人,我为此感到骄傲。 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作为出版人有什么吸引力,值得你牺牲那么多自我创作的时间?要知道,你也是一个作者啊。 其实作家和出品人,前者的核心精神在于坚持自己的审美,用自己的独特征服别人;后者与之相反,出品人的核心精神在于放弃自己固有的狭窄审美,发现别人的独特,然后帮助他征服别人。 我作为出品人可能推出了很多的作品,应该已经过百部了,但是其中我作序推荐的,很少。之前有过的落落、笛安、安东尼、恒殊、hansey……每一个都几乎是百万码洋级别的新生代佼佼者,他们用耀眼的成绩来证明了自己,同时也证明了我作为出品人的职业素质,我很感谢他
评分章士钊述国共和议经过。
评分竺先生是浙江上虞人,还在清王朝覆灭之前,就与其他一些年轻人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留学生,出国学习自然与人文科学,他与胡适、赵元任就同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解放后,在思想改造时期的自我检讨中说,他一心想出国留学是因为自己有向上爬的思想。我们今天不能不感谢这样一批“向上爬”的俊彦,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现代史上就要失去一批世界有名的大学者与大科学家,学贯中西这样的帽子就只好给第二三流的人物去戴了。这些最早的一批海归,是一群令人肃然起敬的爱国者,在学成归国以后,把自己所学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而且还能在某些特定年代里忍辱负重,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做违心——也许在当时是真心——的自我批评。
评分Elementary School(U.S.S.R.)
评分附录四 陈汲家系人物表。
评分66666666666666666666
评分图书包装很好,内容也好
评分竺可桢全集书原计划出24册。中国发行古代科学家的纪念邮票四枚,这四位科学家是张衡、祖冲之、一行与李时珍。他们都是逝去已久的古人,今人又何以知道他们的相貌,并据以设计出邮票来呢?有人发现了一个秘密,是以今人作为模特儿,然后加上古代的衣冠。如果不信,请比照一下祖冲之的画像与竺可桢的照片,就可以发现二者宛如一人(这个发现是德国汉学家阿梅龙告诉我的),除去头巾与胡子,再戴上眼镜,祖冲之就是竺可桢。竺可桢是我国气象学的开山,是我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以他的形象来仿写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一点也不辱没先人。
评分杂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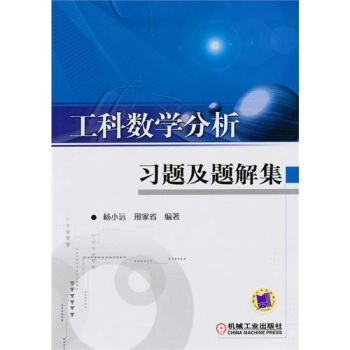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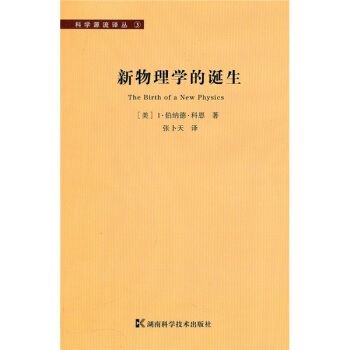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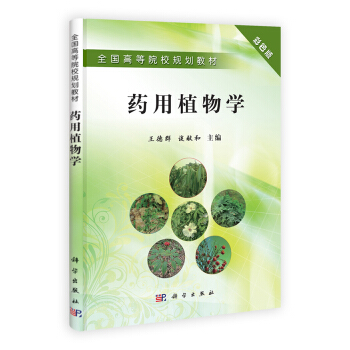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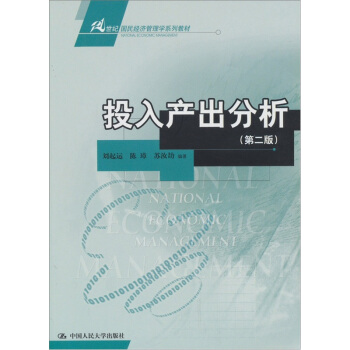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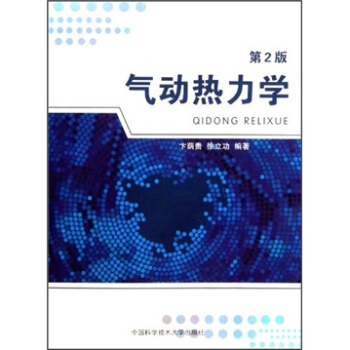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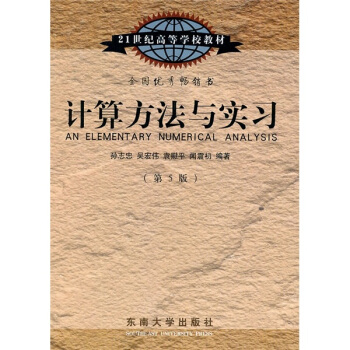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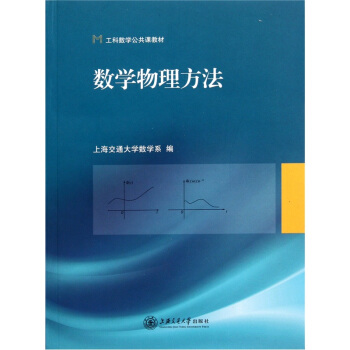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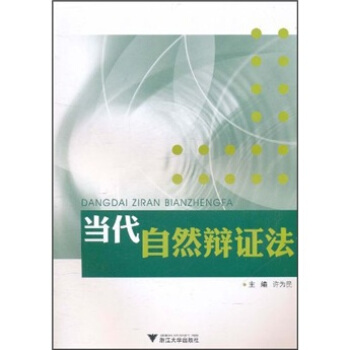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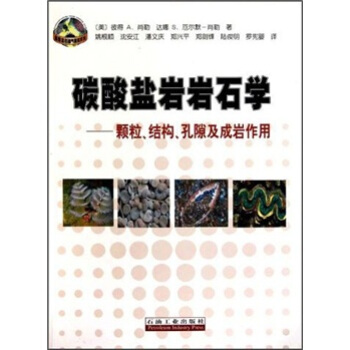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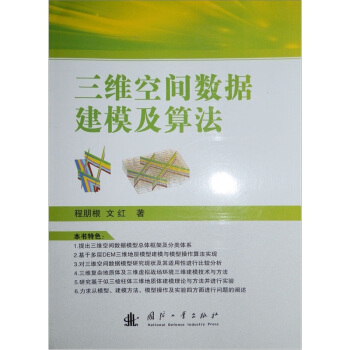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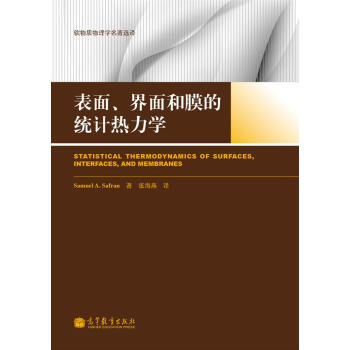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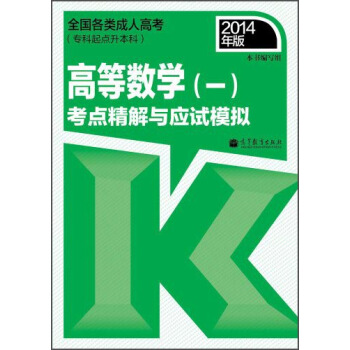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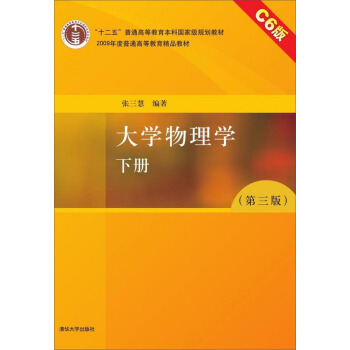

![牛津通识读本:进化(中英双语) [Evolu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64853/5a141c23N54ada9e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