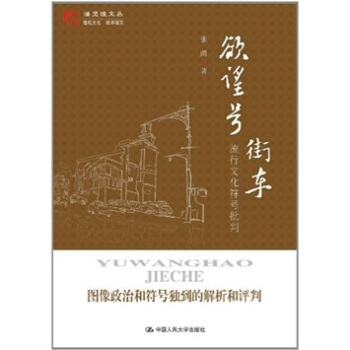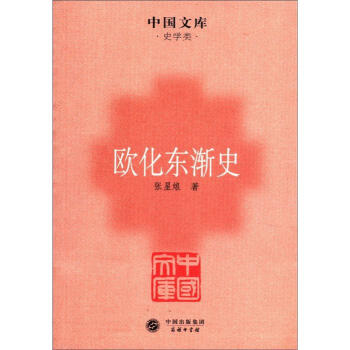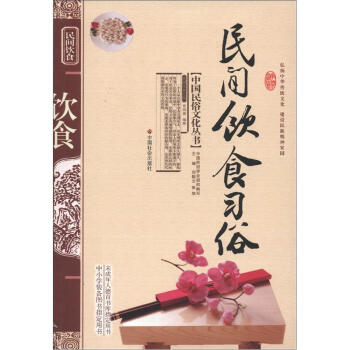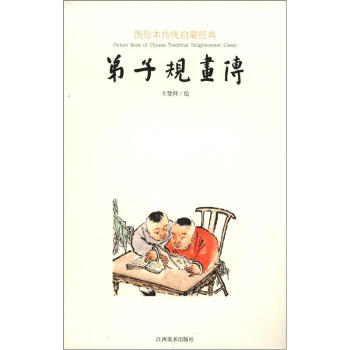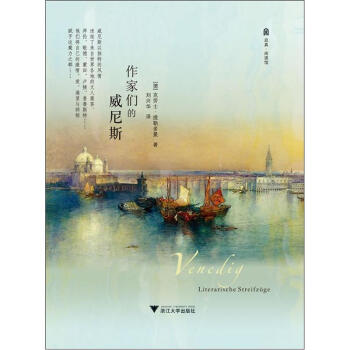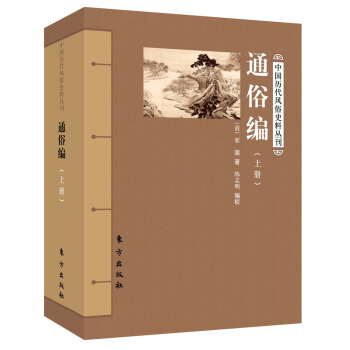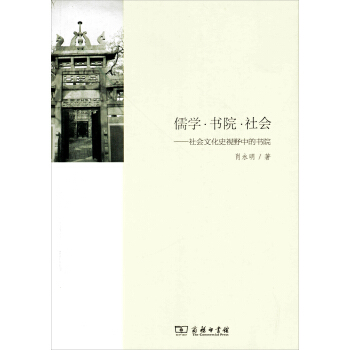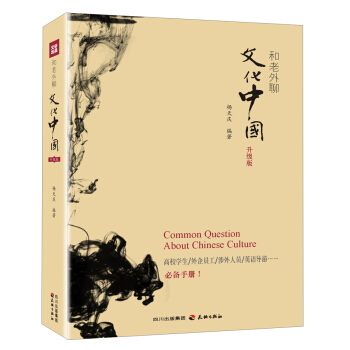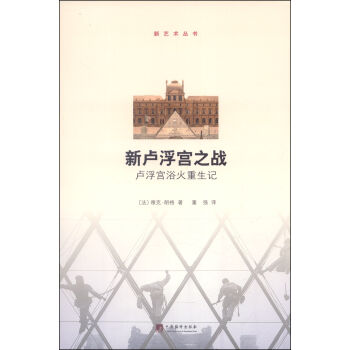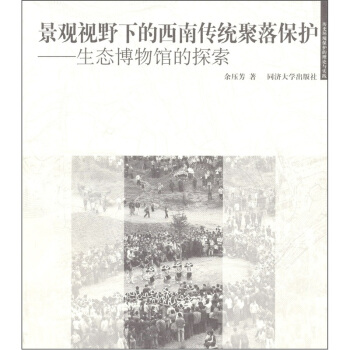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景观视野下的西南传统聚落保护:生态博物馆的探索》包括导言、生态博物馆思想体系与实践发展、西南传统聚落景观的成因、构成与价值取向等内容。目录
第一章 导言一、问题的缘起
1.困惑——传统聚落的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问题
2.限定——西南地域文化格局对传统聚落的影响
3.探索——生态博物馆理论与西南传统聚落景观保护实践的对接
二、基本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1.基本研究思路
2.分析框架
第二章 生态博物馆思想体系与实践发展
一、生态博物馆名称、定义与诠释
1.“生态博物馆(ecomuseum)”词义辨析
2.生态博物馆的定义与演变
二、生态博物馆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哲学渊源
1.博物馆与环境
2.博物馆与社区
3.新博物馆运动的发展
4.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产生
三、生态博物馆的成长历程及各国实践
1.法国生态博物馆:缘起
2.欧洲生态博物馆:新观念的继续成长
3.生态博物馆的世界范围传播
4.小结
第三章 西南传统聚落景观的成因、构成与价值取向
一、中国的乡村城市化与乡村景观化问题
1.乡村城市化
2.乡村景观化
3.乡村城市化与乡村景观化的关系
二、西南地域文化格局对当地传统聚落的影响及表象
1.自然地理环境
2.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
3.传统文化势位
4.后工业时期的现实处境分析
三、西南传统聚落的景观构成
1.固定特征景观因素
2.半固定特征景观因素
3.非固定特征因素
四、西南传统聚落景观的价值取向
1.西南传统聚落景观的价值取向构成
2.西南传统聚落景观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
第四章 西南村寨型生态博物馆景观历时性变迁的实例研究
一、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历时性比较结果与分析
1.梭戛“箐苗”社区的地理区位与历史沿革
2.梭戛苗寨景观的主要特征分析
3.梭戛箐苗社区的保护发展历程
4.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前后的景观变化(1995~2009)——以陇戛寨为例
5.景观的历时性变化与梭戛生态博物馆保护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二、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历时性比较结果与分析
1.镇山村的地理区位与历史沿革
2.镇山村景观的主要特征分析
3.镇山村的保护与发展历程
4.镇山生态博物馆建成前后的景观变化(1994~2009)
5.镇山村村寨保护、旅游发展与景观变化的相关分析结果
6.小结:景观变迁的综合分析
第五章 促进西南传统聚落型生态博物馆的景观保护途径探讨
一、由现象所引发的对几组关系的思考
1.生态博物馆与我国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体系的关系
2.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机制与我国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关系
3.生态博物馆的多元使用主体价值取向的主次关系
4.生态博物馆中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二、生态博物馆景观保护与利用的价值参考体系
1.以原住民为中心的多元主体价值取向的平衡
2.聚落景观的动态演变与景观功能的合理转换
三、促进生态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外力整合途径
1.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制度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国策
3.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
四、生态博物馆专有工作模式的推进途径
1.文化记忆和传承工程的成果巩固与转化利用
2.建立健全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运行机制
结束语:以过程为基础
参考文献
插图索引
表格索引
后记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从书名《景观视野下的西南传统聚落保护:生态博物馆的探索》本身,我首先联想到的是那些深藏在西南大地腹地的古老村落,它们不仅仅是历史的载体,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承载着千百年来的生活智慧与生态哲学。当“景观视野”与“传统聚落保护”并置,立刻勾勒出一种宏大的视角,不再仅仅聚焦于单体建筑的修复,而是将其置于广阔的自然环境、人文肌理之中,去理解其生存的逻辑与演变的脉络。这让我对书中如何阐述“景观”的内涵充满了期待,它是否会深入剖析那些蜿蜒的山峦、奔腾的河流、葱郁的森林,以及它们如何与聚落的形成、发展、甚至是衰落紧密相连?又或是,它会探讨那些象征性的景观元素,如风水树、神山圣水,在维系聚落文化认同中的关键作用?更进一步,我好奇书中是否会提及如何通过“景观视野”来识别和评估聚落的价值,比如,如何界定一个聚落的“生态性”?它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关系如何?是否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态习俗?这些疑问都驱使着我去翻阅这本书,渴望从中找到答案,去理解那些隐藏在寻常风景背后的深刻意义,以及如何在这种宏观的认知下,才能更有效地展开有效的保护工作。
评分“景观视野”让我联想到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它超越了对单个建筑或遗迹的关注,而是将聚落置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进行审视。那么,这种“景观视野”是如何具体应用于西南传统聚落的保护实践中的?书中是否会提供具体的案例,来展示如何通过分析聚落与周围山水、田野、森林等自然景观的关系,来理解聚落的形成机制、发展演变,以及其生态适应性?例如,一个依山而建的村落,其屋顶的坡度、院落的朝向、甚至是排水系统的设计,是否都与当地的地形地貌、降雨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这种“景观”的解读,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聚落的内在逻辑,从而制定出更符合当地实际、更具可持续性的保护策略。我期待书中能通过详实的图文资料,为我们展现“景观视野”下的聚落之美,以及这种视野如何为保护工作提供更深邃的洞察。
评分“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让我立刻联想到的是一种“活态的遗产”保护理念。它强调的不是将历史遗迹“封存”起来,而是让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呼吸”,继续发挥其文化和生态价值。在西南地区,如何让这些古老的聚落,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既能留住乡愁,又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书中是否会探讨,生态博物馆的模式如何能够为这些聚落的居民提供新的生计和发展方向,从而激发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例如,通过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业、农产品加工业,或是利用传统技艺开发文创产品等。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去破解“保护与发展”的难题,让西南的传统聚落,能够在“生态博物馆”的探索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评分从“景观视野”这个词,我立刻想到的是一种审美的维度,它不仅仅是关于聚落的布局和建筑,更关乎它们如何融入周围的山水、天空、光影之中,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西南地区素有“山水画廊”之称,其传统聚落更是这幅画卷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笔触。书中是否会运用摄影、绘画等艺术手段,去捕捉和呈现这些聚落的景观之美?或者,是否会探讨如何通过“景观设计”的理念,来优化聚落的保护和展示空间,使其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也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出一种将学术研究与艺术表达相结合的独特视角,用优美的语言和精美的图片,带领读者去感受西南传统聚落独特的视觉魅力,并从中体会到保护这些文化景观的重要性。
评分“保护”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挑战的议题,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全球化浪潮席卷的背景下。西南地区的传统聚落,往往面临着人口外流、传统技艺失传、生活方式改变等诸多困境。那么,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分析这些挑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策略?我尤其关注书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何与聚落的物质空间保护相结合。很多时候,一个聚落的灵魂在于其传承下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民俗信仰、节日庆典等,这些无形的东西与看得见的建筑、街道、广场共同构成了聚落的完整性。书中是否会探讨如何通过生态博物馆的模式, revitalise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例如,能否通过培训当地居民成为讲解员、传承人,或者组织相关的文化活动,来吸引年轻人回流,让他们重新认识和珍视自己的文化根源?我希望书中不仅仅停留在问题诊断,更能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为西南传统聚落的未来发展点亮一盏明灯。
评分我对书中对于“西南传统聚落”的定义和分类充满了好奇。西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由此孕育出的传统聚落形态必然也是千姿百态。书中是否会基于地理、民族、建筑风格、社会组织结构等多个维度,对这些聚落进行细致的划分和梳理?比如,我们会看到是像湘西的吊脚楼群落,还是川北的窑洞村寨,抑或是云南的白族民居?又或是,书中会着重探讨那些更具代表性的,比如那些依山傍水而建,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聚落,它们的选址智慧、空间布局、建筑材料的选择,是否都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学原理?我期待书中能够用翔实的图文资料,为我们呈现不同类型西南传统聚落的独特风貌,并且深入挖掘它们在历史长河中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深层机制。理解这些多样性,是展开有效保护的前提,否则,盲目套用某种模式,很可能适得其反。
评分“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其核心在于“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尤其是在西南地区,许多传统聚落的文化价值,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当地居民长期以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之中。书中是否会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生态博物馆的模式,去激活和传承这些古老的生存智慧?例如,那些依循自然节律耕作的农耕方式、利用当地物产制作的传统手工艺、或是与自然崇拜相关的民俗活动,这些是否都能成为生态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非常希望看到书中能够强调“在地性”和“参与性”的重要性,即生态博物馆的建设要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和需求,并且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保护和展示的过程中来。只有让当地居民成为生态博物馆的主体,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传承与活化,避免“外来者”主导的、可能脱离实际的保护模式。
评分“生态博物馆”这个概念的引入,无疑是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它跳出了传统博物馆“物”的陈列逻辑,转向了“活”的展示,强调的是在原地、在原环境中,通过参与式的互动,让人们去体验、去理解、去传承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那么,在西南地区,这样一个地域特色鲜明、民族文化多元的区域,如何构建和运作一个成功的“生态博物馆”?书中是否会提供具体的案例分析?我设想,书中可能会探讨如何将聚落的自然生态环境,如梯田、茶园、林地,与当地居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相结合,形成可展示、可体验的“展品”。例如,是否会介绍如何通过传统农耕体验、手工艺制作课程、民族歌舞表演等形式,让参观者深入其中,感受当地的文化魅力。更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书中是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是为了保护,但若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可持续的运营,也可能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旅游开发”,反而破坏了聚落原有的生态和文化。所以,我期待书中能详细阐述,如何在尊重当地居民意愿、维护其传统生计的前提下,通过生态博物馆的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生态保护的双赢。
评分书中“探索”二字,也让我联想到,在西南这样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地域,其传统聚落的保护工作,必然会面临许多未知的领域和挑战。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物质与非物质等一系列复杂的议题。那么,这本书是否会深入探讨,在这些复杂的背景下,生态博物馆的模式如何能够成为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在保护古老文化的同时,也为聚落的居民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发展?我期待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思考,不仅仅是对于现状的分析,更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引。它可能会触及到一些关于文化认同、身份建构、可持续发展等更宏大的命题,并试图在具体的聚落保护实践中找到答案。
评分“生态博物馆”的“探索”二字,暗示着这并非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西南这样一个人文地理复杂多样的地区,其“生态博物馆”的探索必然会遇到独特的困难和机遇。我好奇书中会如何讨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聚落,在构建生态博物馆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性。例如,对于那些位于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的聚落,其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思路可能与那些靠近旅游线路的聚落有所不同。又或者,对于那些保留着丰富民族习俗的聚落,其生态博物馆的重点可能更侧重于文化体验和互动。书中是否会分享一些成功的探索经验,也可能包括一些失败的教训,从而为未来的实践者提供宝贵的借鉴?我想看到书中能够展现出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同时又饱含着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敬意,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这些探索过程中的点滴,以及由此带来的启示。
评分安吉历史悠久,在溪龙乡上马坎出土的旧石器证明,距今8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该县是全国第一个生态县、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2008年起,安吉启动“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把安吉建设成“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美丽乡村,并在建设中力求保护和发掘自然与文化遗存。与此同时,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开始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实践,提出将县域范围内最具特色的人文、生态资源纳入展示范围,系统展示安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
评分安吉历史悠久,在溪龙乡上马坎出土的旧石器证明,距今8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该县是全国第一个生态县、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2008年起,安吉启动“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把安吉建设成“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美丽乡村,并在建设中力求保护和发掘自然与文化遗存。与此同时,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开始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实践,提出将县域范围内最具特色的人文、生态资源纳入展示范围,系统展示安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
评分内蒙古一个"敖伦苏木蒙古族生态博物馆
评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
评分安吉县文广新局局长彭忠心告诉记者,与所有博物馆不同,安吉生态博物馆建设最大的意义在于使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得到整体的、原真的、活态的保护,并使之不断延续和可持续发展。[1]
评分目前,我国已有7个生态博物馆:
评分内蒙古一个"敖伦苏木蒙古族生态博物馆
评分10月29日同时对外开放的安吉生态博物馆中心馆,承吴越遗风,镌苕溪历史,外形为城市方印,神隽味永,浑穆古朴,总建筑面积为15414平方米,总投资超过1亿元,馆内分为历史文化厅、生态文化厅、铜镜专题厅和临时展厅4个厅,馆藏文物2万多件。除了一个中心馆外,12个专题生态博物馆以原真、活态的形式散落于12个乡镇,26个文化展示馆则分布在各个村落,这些展示馆从书画文化、孝文化、手工造纸文化、桥文化等多方面,全面展示了安吉乡村的历史渊源和现代成就,呈现出各具特色的“一村一韵”、“一村一景”的乡村文化景观。[1]
评分在10月29日举行的开馆仪式上,文化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安吉县从传统博物馆的“馆舍天地”走向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面对多样化的文化资源,进入无限的发展空间,这种将自然生态资源与历史人文资源融于一体,将馆内宝贵的藏品与馆外原真、活态的陈列品紧密相连,突破了传统博物馆与环境之间、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物品之间、信息与实物之间的障碍,让全县人民成为博物馆管理的主人,是中国博物馆建设模式的重大创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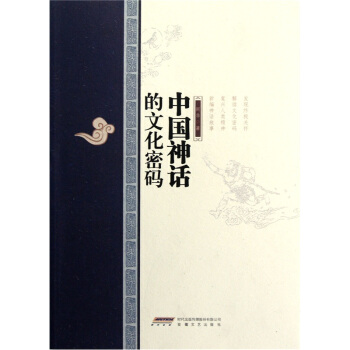
![中国史话·社会风俗系列:礼俗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Rituals and Customs in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85315/29909d27-4ec1-4455-bceb-4f0960e1267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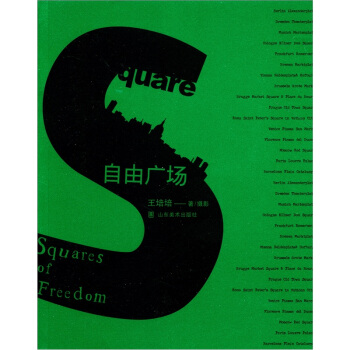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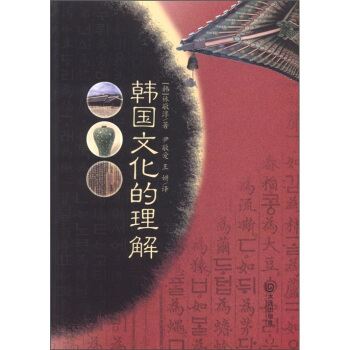
![中国史话·交通与交流系列:满汉文化交流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Manchus and Hans in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905495/75886ec6-d9fd-44a5-8024-f0bca9d2612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