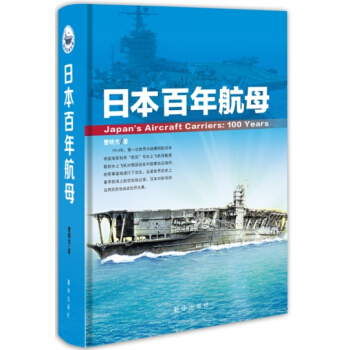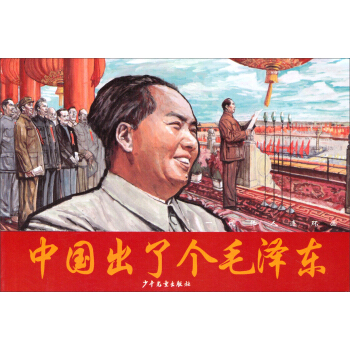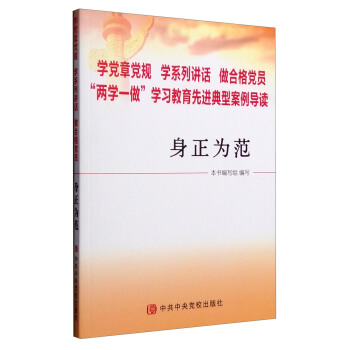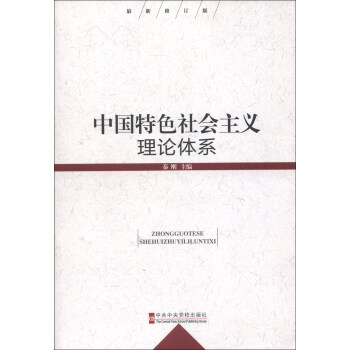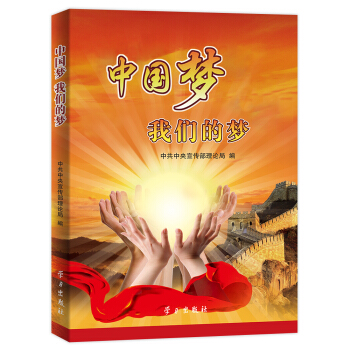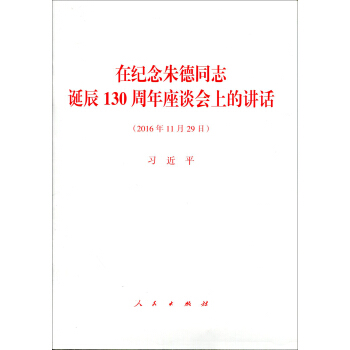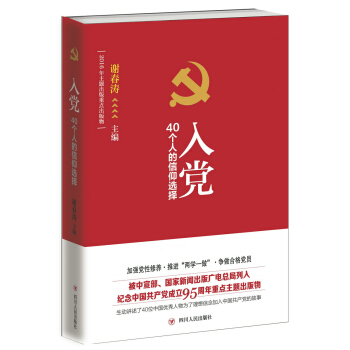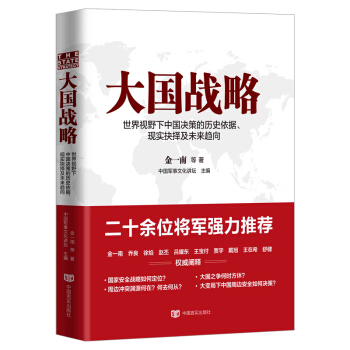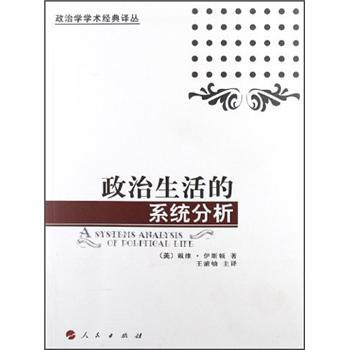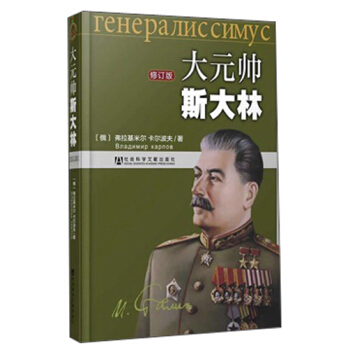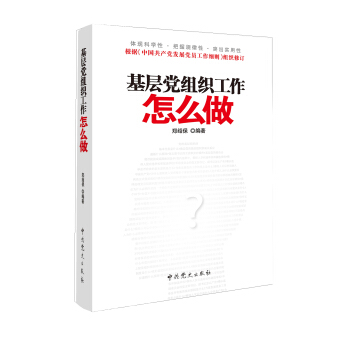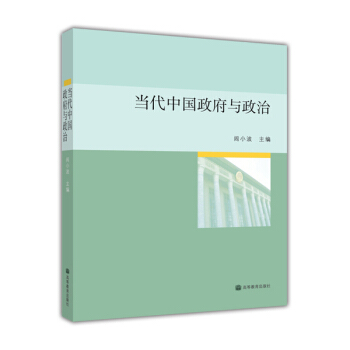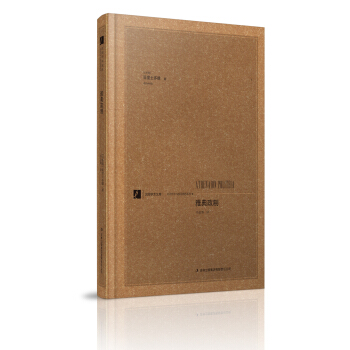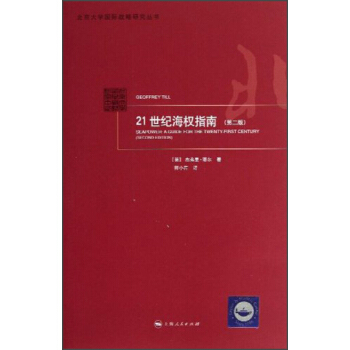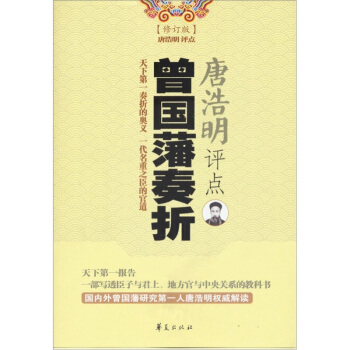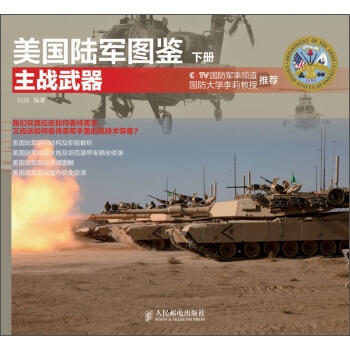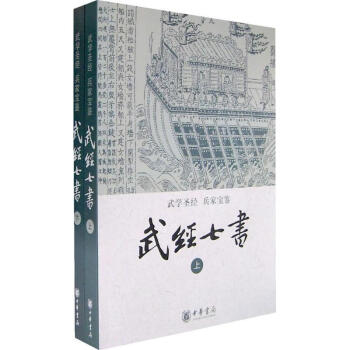![旧邦新造:1911-1917 [The Remaking of an Old Country]](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907681/1331fdeb-8a9b-4c7f-b4ed-e9a2b6c95963.jpg)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旧邦新造:1911-1917》是一本以中国1911-1917年间的政治大转型为研究对象的宪政史著作,探讨中国在多民族王朝国家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环峙、军事力量控制权高度分散化、政治精英高度分化的恶劣环境中艰难的共和建设历程,并试图重构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叙事。《旧邦新造:1911-1917》集中探讨了三大问题:(1)1911-1912年间以南北议和、清帝逊位和南北政府融合所构成的“大妥协”,突出其对于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意义,并阐发了其作为共和基础的薄弱;(2)1912-1914年在共和旗帜下的政治精英就政体选择进行的博弈和冲突,强调了国家建设的缺陷对于宪政建设的压力以及晚清以来的政治精英分化对政体选择所造成的消极影响;(3)1915-1917年两次不成功的向君主制的回归,重新审视导致共和革命之后的君宪运动成败的因素。本书熔宪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于一炉,观点新颖,内容丰富。作者简介
章永乐,常用笔名海裔,浙江乐清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2008年)、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年),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中国宪法与行政法。目录
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言)导言
第一章 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共和转型:四国比较
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清帝国这四个“老大帝国”在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过程之中都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唯有清帝国幸免于国家解体的命运。究其根本,“老大帝国”们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与复杂的制度多元主义实践,导致其始终难以达到可与西欧民族国家比肩的内部团结。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老大帝国”们被迫建构某种形式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塑造统一认同,对抗各种
离心势力,但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速度始终难于跟上国内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速
度;列强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扶持使得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帝国政府推动的改革也往
往导致鼓励地方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这一跨国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晚清政府的国家建设努力何以导致了更激烈的反满民族主义革命,以及中国的共和转型何以避免国家的全面解体。
第二章 1911-1912年的“大妥协”:过程、意义与局限
辛亥革命中,许多革命党人对于这场革命的想象打上了浓厚的美国革命的烙印——各地方单位脱离帝国政府控制,然后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家。但这一设想面对没有联合意愿的蒙藏分离主义势力时完全无能为力。民国政府之所以能从法理上实现对清朝全部疆土的继承,离不开清皇室、南方革命派与袁世凯集团之间的“大妥
协”。在这场妥协中,清帝下诏,将统治权“公诸全国”,要求建立以五大民族完全领土为基础的民国,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随后,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从法统上说,北方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尽管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来看,南方政府被北方政府吸收。《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从法理上限制了以“效忠大清不效忠中国”为理据的边疆分离主义的空间,为袁世凯政府处理边疆危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然而,在这场“大妥协”中,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派并来就民国的法理基础以及未来的政体安排达成真正的共识,这为以后的宪政危机埋
下了伏笔。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主权在国论”: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构
1913年,在围绕民国正式宪法起草的大讨论中,出现了“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国民党力主“主权在民”,试图建立一个以议会为中心的政体;而以康梁为代表的“主权在国论”的主张者认识到不成熟的政党一议会政治无法克服中国面临的深重的国家整合危机,试图以普鲁士一德国为楷模,赋予总统及其行政体系以更大的权力,通过后者来实现政治整合。梁启超对德国宪法学家伯伦知理与波伦哈克的引介,为中国的“主权在国论”提供了最为高端的理论支持。德国的“主权在国论”通过将“主权”赋予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为君主立宪国家中的君主提
供了一个强势而又不同于专制君主的地位。康梁试图借用此理论,加强民初孱弱的行政权力,实现国家重建。“主权在国论”者对于当时不成熟的议会一政党政治有着相当犀利的批评,但他们自身的理论却缺乏恰当的历史行动者载体——与普鲁士王室不同的是,北洋集团既缺乏足够理性化的军政组织,也缺乏对中国新旧政治精英进行全面整合的能力。
第四章 共和的诤友: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注
立宪派领袖康有为于1913年深度介入了立宪大讨论,其所作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其多年信奉的君宪原理在共和立宪上的运用。康有为认为在君宪政体中,君主占据最高荣誉位置但不行使实权,其他政治精英仅争夺实权而无法获得最高荣耀,可以降低党派斗争的激烈度;君主亦有助于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礼乐的完整性。中国皇帝退位之后,释放出来的是各路政治精英的夺权野心,政治稳定成为值得担忧的问题。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声称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政模式为基本参照,结合中国国情,创设中国自身的宪政模式,但其宪法方案实际上暗中参考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宪法模式,期望通过适度加强总统及其行政体系的权力来推进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同时,康有为主张保持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以孔教为国教,凝聚精英共识,塑造政治权威。
……
第五章 首届国会的解散与总统集权的诞生
第六章 渐行渐远的君主立宪制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由此引出康有为所列举的共和模式之第四种,英国的“虚君共和”。英国宪法设一虚君,但只有君主之礼,而无实际统治权,议会中各党派竞争首相位置,政争不至于动摇国本。在康有为看来,英国表面上有君主,但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国。他称之为“共和爵国”。君主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前面所分析过的“无用之用”,但这只是“道之以政”的层面。在“齐之以礼”的层面,这一被英国宪法学家白哲特称为宪法的“尊荣部分”的王室还能起到保存礼法纲纪,正风俗人心的作用。与法国相比,英国的政治和风俗都居于上风。“英国虽为国会万能,民权至盛,而保守其纪纲礼俗,道揆法守,以成其整齐严肃。博大昌明之政俗美化良矣,比于法之俪纲错纪、恣睢自由者,其政俗皆远过之。”②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君主不仅是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环节。保持君主在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能够支持政治制度的运作,也能保持一国伦理生活的完整性。对以上四种模式,康有为是怎么评价的呢?英国有虚君,但今日中国已推翻君主,英国模式虽好,但已不能学;美国模式“易生祸变”,不可学;瑞士模式“至公”,但在中国这样的广土众民的大国中难以推行。③因而,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他不太赞赏的法国模式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创设宪法。这就是康有为经过复杂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在这则交代宪法宗旨的“发凡”中,康有为既不是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宣示固有权利,也不是历数作为“我们人民”对立面的专制统治的种种罪恶,而是将革命者们自豪的推翻帝制的成果表述为一种困境,这显然不是一种能够令主流共和派激动得起来的写法。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读到“旧邦新造:1911-1917”这个书名,我立刻被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变革的紧迫感所吸引。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而1917年,又是一个充满了世界性动荡的年份。这两端之间,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好奇的是,作者会如何梳理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物、事件和思潮?是会像一些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一样,以帝王将相、政治博弈为主线,还是会更深入地挖掘普通民众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起伏?“旧邦”二字,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遗绪,如何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得以保留或升华?“新造”又意味着什么?是全新的制度、全新的思想,还是全新的国家认同?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视角,让我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段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堆砌。这或许是一次关于民族复兴、关于国家重塑的深刻反思,我迫不及待想要翻开它,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让我联想到了一段风起云涌的变革时期,1911年到1917年,这短短的六年,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惊涛骇浪,旧秩序被颠覆,新思潮涌动,社会面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很好奇作者将如何描绘这场“旧邦新造”的宏伟画卷,是侧重于政治制度的革新,还是着眼于思想文化的碰撞?亦或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剖析转型期的阵痛与机遇?“旧邦”二字,预示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与历史积淀,而“新造”则充满了新生、重塑的勃勃生机。我期待作者能够带领我穿越回那个充满矛盾与希望的年代,去感受那份变革的激昂,去理解那份探索的艰难。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张力,仿佛一场史诗般的叙事即将展开,我渴望从中窥见那个时代人们的挣扎、奋斗与梦想,以及这些努力最终将国家引向何方。
评分当我的目光落在“旧邦新造:1911-1917”这个书名上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的是那个充满动荡与希望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的巨响,犹如一声惊雷,劈开了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又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在这六年间,中国究竟是如何在旧有的躯壳里,孕育出新的生命?“旧邦”二字,仿佛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而“新造”,则象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探索。我非常好奇,作者将如何描绘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着重于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还是深入到社会肌理中的细微之处?是聚焦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还是关注个体的命运沉浮?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提供一个观察和理解那个关键时期的全新视角,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古老的中国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进行着一次艰难而又伟大的“新造”之旅。
评分“旧邦新造:1911-1917”这个书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那个波澜壮阔年代的无限遐想。1911年,一个王朝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端;1917年,一个世界格局重塑的节点,也预示着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场深刻变动。我猜想,这本书可能会深入探讨,在推翻了旧的统治之后,如何才能真正地“新造”一个国家。这其中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更包括了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文化观念等方方面面的革新。作者是否会聚焦于那些在这场变革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还是会着墨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旧邦”所象征的传统如何在“新造”的过程中被继承与扬弃,又或者被彻底打破?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希望它能带我走进那个充满挑战、机遇与未知的时代,去理解那个民族如何在迷茫中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评分“旧邦新造:1911-1917”——仅仅是书名,就足以让人心潮澎湃。1911年的巨变,推翻了帝制,开启了共和的艰难探索;而1917年,世界格局的重塑,又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这六年的时间,中国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新造”过程?我很好奇,作者会如何解读“旧邦”与“新造”之间的张力。是强调革命的彻底性,还是关注改革的渐进性?是探讨新思想的涌入如何挑战传统观念,还是分析经济发展如何重塑社会结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领我深入那个时代,去感受当时人们的迷茫与奋斗,去理解那些重大的历史抉择是如何被做出的,以及这些抉择最终将中国引向了何方。这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回顾,更可能是一次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跟随作者的笔触,去探索其中的每一个细节。
评分书很好!价格便宜!送货也很快!
评分听说很好,读读看看。就是印书不怎么好
评分非常好 书本内容不错 值得购买
评分作者的新观点还是非常好的
评分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作为一本由一系列主题相关的论文集结而成的专著,本书的整体感仍有相当的提升余地,具体表现在本书前半部分对“大妥协”的一系列有力分析并未贯彻到后面对“主权在国论”以及君主制重建运动的分析之中。另外,史学界一直缺乏对清末民初源于日本的“国体”理论的详细梳理,本书有专章探讨清末民初的“主权在国论”,但并未对当时的“国体论”作专门处理,对于该章的历史深度有一定影响。
评分听说很好,读读看看。就是印书不怎么好
评分挺好的一本书,法学院同学可以读读
评分很扎实的研究,新颖的视角
评分本书试图突破传统以文本分析为主的宪政史思路,是一部迈向政治与历史视野的新宪政史,也是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的新史学的可贵尝试。作者对清末宪政史的重述蕴含着他对目前中国宪政转型的关注与思考,同时“大妥协”塑造的主权连续性是对海外“新清史”研究将辛亥革命定性为中国从清帝国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说法的有力回应。汪晖为本书撰写的长篇序言提炼与升华了本书的一些理论命题,并有一些批评性回应,亦是本书看点之一。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Comparative Politics:Theory & Methodolog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18655/rBEhV1MfqugIAAAAAAIYsI5kpCQAAKAVgEO0WEAAhjI4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