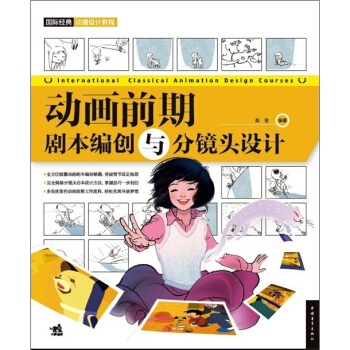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艰难中不失优雅风度,平淡中尽显大家气质。阅读张允和文集,让时光在优雅和美丽中回旋。内容简介
《昆曲日记(修订版)(套装上下册)》不仅记录了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日常活动,还记录了自1956年以来文化部、文化局以及各剧院团对昆曲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也记录了海内外曲友对于昆曲事业的执著。《昆曲日记(修订版)(套装上下册)》以丰富而翔实的史料,补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于抢救、继承昆曲事业而不断做出努力的历史记录,弥足珍贵。在《昆曲日记(修订版)(套装上下册)》出版之际,北京昆曲研习社迎来了第三次大变革,继俞平伯先生、张允和先生、楼宇烈先生之后,主任委员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深知,我和我的社委会成员,都是曲社的孩子,虽然刚刚走过蹒跚学步的阶段,毕竟未及弱冠、涉世不深,尚需要家长引路,前辈指点。但我们年轻的一代有信心把北京昆曲研习社的工作继续下去,不辜负前辈们的希望。这也是张允和老师的心愿,她希望昆曲事业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作者简介
张允和(1909-2002),安徽合肥人,长于苏州。当代著名昆曲研究家,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合肥四姊妹”)中的“二姐”,中国语言文字专家、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周有光先生的夫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56年参加俞平伯主持的北京昆曲研习社,1980年至1987年间任北京昆曲研习社主任委员,著有《多情人不老》、《最后的闺秀》、《张家旧事》、《昆曲日记》、《曲终人不散》等,并主办家庭刊物《水》杂志。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曲子是那般悦耳动听,身段是那般美妙婀娜,使我过去十年铅样重的心,一下变得轻松了。我抛却了十年的悲惨世界,像插上翅膀飞入了童话中的神仙世界。我飘飘然,心口又甜又酸又有点苦。我偷偷摘下眼镜,揩试腮边的眼泪,是苦水,也是蜜水。——张允和
昆曲的文词是集中历代中国韵文的大成,留下的剧本既事富,又精美,是其他剧种望尘莫及的,昆曲的舞蹈(动的叫身段静的叫亮相)怒中国话的雕塑艺术,尤其在亮相中表现更为突出。
(演戏中)眼神最重要,要“目中无人,目中有物”。“目中无入”就是看不见台下的人实在的脸,并不是心中无观众。“目中有物”是似乎看见台上的虚构的实物。如《小宴》中,眼巾看天空的雁儿、池麟中的柳树、桂花(似乎有清香)、池中的莲花和鸳鸯等,眼睛由上而中而下(天淡云闲)而且唱出情调、香味、色彩来……只要心中有戏,喜怒哀乐七情就会从眼光中流露。
——张允和
目录
《昆曲日记》序朱家溍一份珍贵的当代昆曲史料
——读《昆曲日记》楼宇烈
待等时来风便
——写在《昆曲日记》即将出版之际 胡忌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曲人名录
北京昆曲研习社大事记
永远不落的彩虹许宜春
奇人奇书金家昆余心正
后记欧阳启名
跋周有光
张家世系图
周家世系图
精彩书摘
11月17日南北昆曲老艺人座谈会,在北京第一招待所召开。(以下由王浞华记录)
金紫光:(1)成立昆曲学会,参加文联。(2)办刊物,由俞琳等同志负责,印刷经费等问题设法解决,中国戏剧出版社很快恢复。(3)昆曲繁荣还必得靠舞台表演。专业昆曲、业余昆曲相辅相成,业余的也很重要,也培养不少人。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传瑛同志,你为昆曲恢复立了大功——《十五贯》。
周传瑛:完全同意紫光同志的意见。昆曲这一艺术,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但为什么还半死不活?当时,碰到了“四人帮”,但全国还只有五个团体,也出了不少的演员。不光演戏,还要发掘整理,如汤显祖的四梦。整理出来不一定有票房价值,对老演员总要有点照顾,侯玉山已经80多岁了。我在传字辈中较年青,也已68岁了。明年会演很好,可以促进一下。去年我在南京,提了不少意见。他们想搞一个研究室,至少要60人,但力量不够,没办成。
浙江钱法成:完全赞成。戏曲研究,抓了昆曲,就是抓了牛鼻子。希望昆曲前辈健康,都上台献一献。继承是当务之急,创新当然也要。争取多多录像,北京、上海都有条件。昆曲向世界舞台演出,日本就希望昆曲去演出。经济补贴问题,不能与一般剧种一样看待,应像对文物那样。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就等于消灭它。
郑传鉴:录像,可要片断,还可用连环画。(傅雪漪插话:“还要教学用的。”)昆曲有400年历史,如是对的,就借过来。根茎都有用,不能连根拔。朝鲜人看了我们的《三打白骨精》,说我们是把唱和舞结合起来,而且还结合了杂技。
宋铁铮:温州想恢复昆剧团,还有50多个演员。昆曲也可用简谱,工尺也得懂。
王传淞:我从来不爱讲话,同意紫光意见。昆曲为什么弱下来,文字太高雅。简谱也好,我们需要。我们要找对象,现在对象太少了。艺术好看多看才懂。根据我们的情况,演小丑,有五毒形象,如壁虎、蜘蛛、……演戏要向观众靠拢,要懂得观众,才能演好戏。戏全是假的,只有脑子是真的。要通过动作来表现生活,戏要夸大,要美化。要繁荣昆曲,要找根源。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梨园寻踪:百年昆曲艺脉的沉思》 最近读完了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文学作品,它带我走进了一个光影交错的艺术殿堂,那种对传统文化深入骨髓的眷恋和探寻,实在让人动容。作者的笔触细腻得如同苏绣的针脚,将那些在舞台上转瞬即逝的唱念做打,一一用文字精准地捕捉并加以阐释。我尤其欣赏书中对几位已故艺术大师的追忆,那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扑面而来,仿佛他们就在耳边轻声诉说着当年的艰辛与辉煌。书中对昆曲声腔体系的剖析,并非枯燥的理论堆砌,而是结合了具体的剧目片段进行分析,使得即便是初窥门径的读者,也能领略到那“一字一腔,皆成境界”的绝妙之处。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艺术技法的书,更像是一部饱含深情的人生哲学书,探讨了艺术生命力的延续和传承的重量。书中引用的历史文献和手稿资料翔实可靠,可见作者下了极大的功夫去挖掘和考证,这种对“真”的执着追求,让整部作品的厚重感油然而生。读完之后,我仿佛能听见那悠远婉转的吴侬软语,在心底久久回荡,对这种“百花不争,独具韵味”的古典美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敬畏。
评分《泥土与星光:昆曲在地域文化土壤中的生长轨迹》 这本书的格局更为宏大,它跳出了纯粹的舞台艺术范畴,将昆曲的生命力置于更广阔的地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作者关注的重点在于“在地性”,探讨了昆曲如何与特定地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乃至市井语言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过程。书中关于昆曲在民间的“变体”和“非正式演出”的描述,尤其精彩,揭示了艺术从庙堂走向街巷的生命张力。文风严谨又不失文学性,大量运用了田野调查的素材和口述史的记录,使得文字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历史的尘埃感。我欣赏作者对“非主流”昆曲表演形态的重视,这打破了传统上只关注科班和官方演出的狭隘视角,展现了艺术生命力的顽强和多元面貌。它提供了一个理解昆曲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遗产的全新维度,让人意识到,这项艺术并非高悬于顶的孤立符号,而是深深扎根于我们脚下的泥土之中。
评分《浮生半梦:在现代喧嚣中聆听雅音的穿透力》 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没有沉湎于对往昔辉煌的单纯赞美,而是将古典的昆曲艺术放置于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之中进行审视和对话。作者的思辨性极强,尤其是在探讨如何让这项“活着的遗产”在当代语境下焕发新生这一点上,提出的观点发人深省。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节奏的张力”那一部分的论述,作者将现代人的焦虑感与昆曲慢板中的“不疾不徐”形成鲜明对比,探讨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慢下来”的可能。文字风格上,它摆脱了传统研究的板正,更像是与一位学识渊博的朋友在深夜里的推心置腹,时而引用哲学思辨,时而穿插个人体悟,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智力上的愉悦。书中对当代昆曲传播中的商业化与艺术纯粹性之间矛盾的剖析,更是切中了当下文化产业的痛点,让人不得不反思,在追求“流量”的时代,我们如何守护住那份难以量化的“雅”与“韵”。这本书无疑拓宽了昆曲研究的边界,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评分《镜台回顾:一个戏迷的自我修养与情感投射》 这本书读起来,最直接的感受是情感的真挚和强烈的代入感。它更像是一本深入个人情感世界的日记体随笔,记录了一个资深戏迷从懵懂到痴迷的整个心路历程。作者对特定剧目的喜爱,绝非蜻蜓点水,而是达到了与角色命运同呼吸、共悲欢的境界。比如,他对《牡丹亭》中杜丽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体悟,细致到可以拆解到每一个眼神和指法的层次,这种由表及里的沉浸式体验,感染力极强。书中的段落组织非常自由,有时会突然跳跃到某个剧场的瞬间,有时又会沉入对某段唱词背后历史典故的考据,这种跳跃感非但没有打乱阅读的节奏,反而模拟了记忆和思绪的自然流动,非常迷人。读着它,我感觉自己像是坐在作者的身边,听他娓娓道来那些年在剧院角落里捕捉到的每一个珍贵瞬间,那种专属于戏迷群体的“在场感”被完美地复现了。
评分《韵律之谜:探寻昆曲美学形式的数学结构与哲学意涵》 这是一本极具思辨色彩的学术随笔,它试图用一种近乎解构的方式来拆解昆曲表演的内在逻辑和美学密码。作者的文字风格非常冷静和精确,大量运用了类比和逻辑推理,去探寻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韵味究竟是由哪些结构性的元素构成的。尤其精彩的是对“板式”和“过门”的结构性分析,作者将其比作某种音乐的“算法”,展示了在看似随性的唱腔背后,隐藏着的严密而精巧的艺术规律。这本书的阅读门槛稍高,因为它要求读者不仅要有艺术感受力,还要对形式美学有所思考,但一旦进入作者构建的逻辑体系,便会产生豁然开朗的感觉。它揭示了昆曲表演中时间、空间、声音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哲学意义,让我们明白,那些看似重复的动作和唱段,实则是在对有限的结构进行无限的演绎和深化。读完后,我对昆曲的敬畏感更添了一层——那是对人类智慧在特定文化土壤中提炼出的极致形式美的赞叹。
评分趁着特价时候买进的。慢慢看
评分浙江钱法成:完全赞成。戏曲研究,抓了昆曲,就是抓了牛鼻子。希望昆曲前辈健康,都上台献一献。继承是当务之急,创新当然也要。争取多多录像,北京、上海都有条件。昆曲向世界舞台演出,日本就希望昆曲去演出。经济补贴问题,不能与一般剧种一样看待,应像对文物那样。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就等于消灭它。
评分送货及时,性价比高。
评分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评分印刷好,内容更好。喜欢张家姐妹张家事。
评分包装很好,昆曲的参考书,值得购买
评分保存了一脉神髓。合肥四姊妹之一作品。
评分周传瑛:完全同意紫光同志的意见。昆曲这一艺术,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但为什么还半死不活?当时,碰到了“四人帮”,但全国还只有五个团体,也出了不少的演员。不光演戏,还要发掘整理,如汤显祖的四梦。整理出来不一定有票房价值,对老演员总要有点照顾,侯玉山已经80多岁了。我在传字辈中较年青,也已68岁了。明年会演很好,可以促进一下。去年我在南京,提了不少意见。他们想搞一个研究室,至少要60人,但力量不够,没办成。
评分苏州一个名叫张吉友的富商,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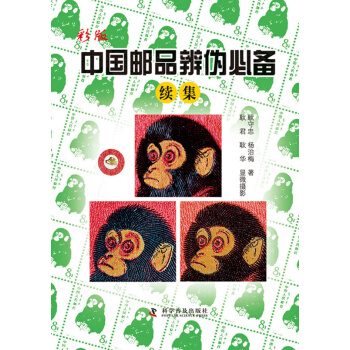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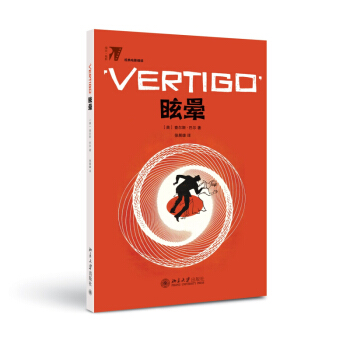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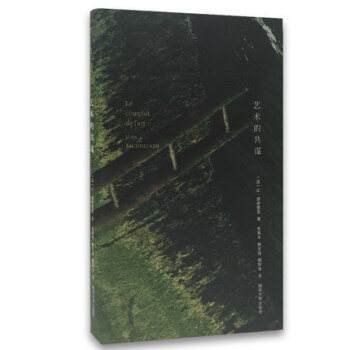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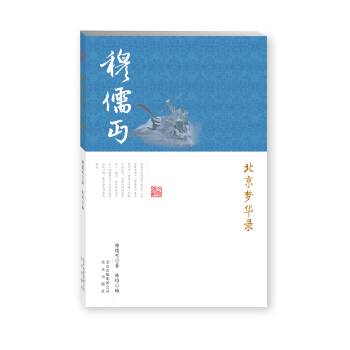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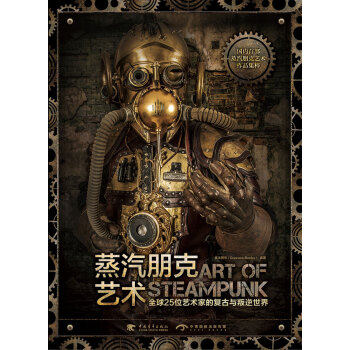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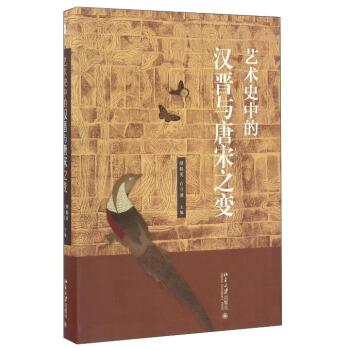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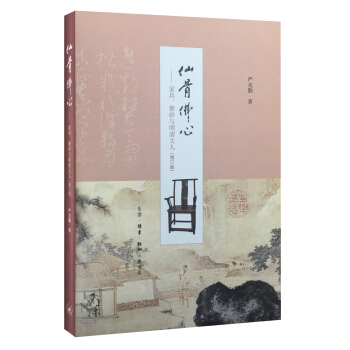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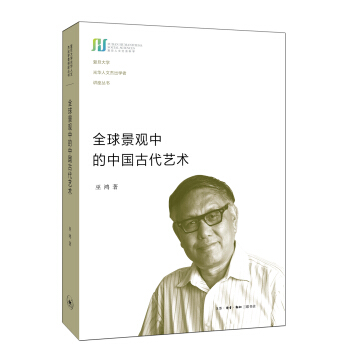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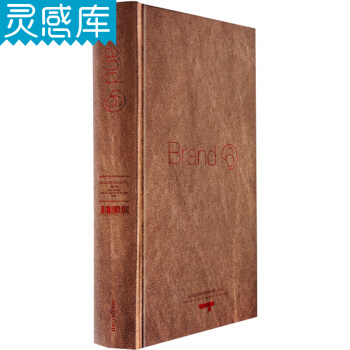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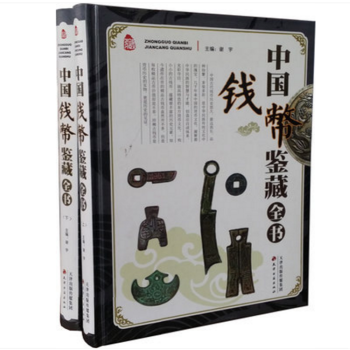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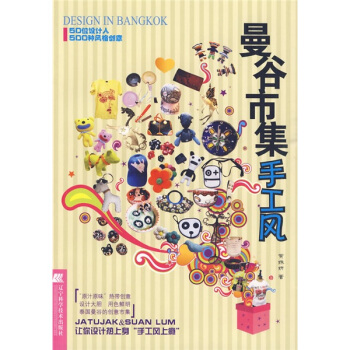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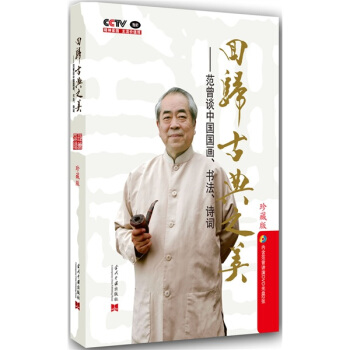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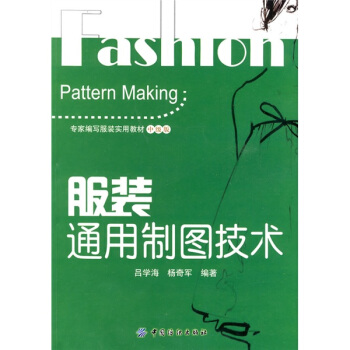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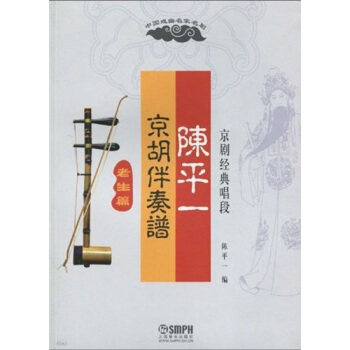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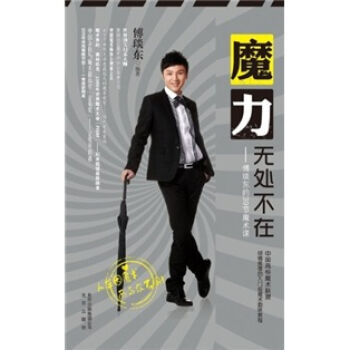
![国际环境艺术设计基础教程:商业空间设计 [Retail Desig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77025/60637875-62a1-4124-b0a4-37537459c42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