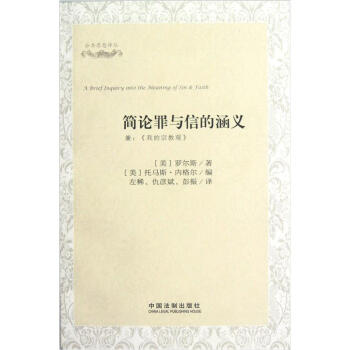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罗尔斯是美国乃至西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其主要的思想贡献是有关社会正义、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国际法的哲学理论。他的思想看来并没有因世纪的转折而过时,甚至我们可以说,对于在经济上已然飞速崛起,而国内体制与国际环境的问题却显得越来越突出的中国来说,现在或是需要更深入和全面研究他的时候。因此,左稀等就编译了《简论罪与信的涵义:兼我的宗教观》。内容简介
《简论罪与信的涵义:兼我的宗教观》中收集了作者两篇自己撰写的文字:主要的一篇是他194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简论罪与信的涵义》;还有一篇是他去世之后人们在他电脑中发现的一篇创建于1997年的文章:《我的宗教观》。前一篇文章是尘封多年之后,前几年才发现并受到重视的,后一篇文章则不仅罗尔斯生前没有发表,甚至他的亲友也不很清楚此文。目录
人、共同体与上帝——中文版代序(何怀宏)导言(乔舒亚科恩、托马斯内格尔)
青年罗尔斯的神学伦理学及其背景(罗伯特马里修亚当斯)
简论罪与信的涵义
文本说明
前 言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为自然宇宙辩护
第三章 被扩展的自然宇宙
第四章 罪的涵义
第五章 信的涵义
参考文献
我的宗教观
普通索引
《圣经》篇目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那么,罗尔斯会如何评论一种本质上并不包含任何人格关系的、对于另一个人所经历的一个过程(比如从疾病中痊愈)的利他主义关切呢?罗尔斯会否认任何人都有这种利他主义的关切吗?或者,他会同意利昂把它们归类为利己主义的或“为他主义的”动机吗?或者,他会仅凭这类关切关系到另一个人的福利便声称它们实际上归属于人格关系领域吗,即便一个人并不想要与另一个人相处或与她建立任何关系,除了希望她好以外?所有这些看来都是成问题的,而且罗尔斯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中任何一个。恰如上文所言,在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中,罗尔斯倾向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共同体的珍视:即我们应该珍视它(作为目的自身),而非根据它客观上拥有的价值来珍视它(作为善自身)。与他对共同体的最高评价相比,他把“善”这个词与他对“自然”嗜欲之对象的附属性评价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这并不是说他从未暗示共同体是善的,并且实际上是最善的。毋宁说,在考虑“善”的用法时,他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这鲜明地体现在这样一个单句中,他在那儿既反对‘好生活’这个短语,同时他又用‘好生活’来表示:他对人格关系的评价是超出“任何对象”之上的。他说,“我们认为,所谓的‘好生活’(一种令人嫌恶的表述)并不在于寻求任何对象,毋宁说它是涉及人格关系的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罗尔斯说,“完满意义上的共同体——天国共同体其自身就是目的,它是上帝造物的目标。”这个提示是很清楚的,作为“造物的目标”,共同体是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寻找的最重要和最终的目的。在这个文本中,同样有一个很强的提示:共同体是我们最高的目的,因为“拯救”或者我们人格本性的实现只有在共同体当中才有可能。罗尔斯暗示着,共同体必须要被作为目的自身来期盼——严格地讲,它不可能存在,除非这些参与其中的参与者都把它当做目的自身来期盼。“没有任何共同体可以建立在利己主义之上”。如果(就像青年罗尔斯、而非后来的罗尔斯所设想的)社会契约是“一个把社会仅仅当作手段来利用的互利计划”,一个基于社会契约的社会“就根本不是一个共同体”。
罗尔斯坚持认为,共同体就是目的自身。另一方面,尼格伦似乎要在涉及圣爱的讨论中完全把有关目的的分析排除掉。他宣称,“不能对[上帝之]爱持有目的论的解释或动机”。并且,他把路德当做是维护圣爱的伦理学家(agape-ethicist)的典型,他说“路德伦理学的整个构建并不是目的论式的,而是因果关系式的”。这些声明可能和尼格伦对于幸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拒斥有所关联。然而,我认为它们是误导性的,因为有一些重要的区别还没给出。尼格伦所追随的观点似乎可以说得更加详细些,而且,这个观点也是相对狭窄的。即,圣爱在某些方面没有最终的目的(ulterior end)。特别是,“上帝并非为了获得任何利益而去爱,而仅仅是因为爱就是袍的本性”。并且,在指向某个邻人的圣爱中,上帝的角色是作为圣爱的原因,而非邻人被当做手段来用时的奖赏。在这些观点中,没有哪一个能够保证圣爱的结构不能按照为圣爱所追求的目的来进行分析。事实上,我认为,除了把友谊和邻人的善当做是目的自身之外,理解尼格伦对于圣爱的说明也是不容易的。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读这本书的过程,更像是一场与作者思想的深度对话。他并没有急于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通过一系列层层递进的追问,引导读者一同去审视自己的内心。关于“信”的论述,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它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教条的遵循,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种在不确定中寻求意义的勇气,一种对超越性的渴望。作者将信看作是生命中一股强大的驱动力,它能支撑人在困境中前行,能在绝望中寻找到希望。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这种“信”的细腻描绘,它包含着对真理的追求,对良善的期盼,以及对未来的某种承诺。这种关于信的理解,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自己生命中的信仰。
评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个人的宗教观融入了对罪与信的哲学探讨之中。作者并没有刻意宣扬某种特定的教派或教义,而是以一种更为普适的、更具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分享他的信仰体悟。这种“兼我的宗教观”的副标题,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反而让整本书充满了真诚和个人魅力。通过阅读,我仿佛能感受到作者在思想探索过程中的每一次顿悟与挣扎,他的文字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温暖。他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于人类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于回归本真的呼唤,都深深打动了我。这本书让我反思,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是否已经迷失了最初的方向。
评分这本书初读之下,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哲学与信仰深处的大门。作者以一种极其个人化却又颇具洞察力的笔触,探讨了“罪”与“信”这两个古老而又深刻的概念。我尤其被他对于“罪”的解读所吸引,它并非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败坏或违背教义,而是更进一步触及了人类存在中那种根深蒂固的疏离感、迷失感,甚至是对自身有限性的无力感。作者没有选择用生硬的宗教术语来构建他的论证,反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在人性的弱点与挣扎中,挖掘出罪的真实面貌。这种解读方式,让身处现代社会,即便对宗教理论并不十分了解的读者,也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评分这本书并非一本简单的说教读物,而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作者的文字,时而如潺潺流水,细腻地描绘内心的感受;时而又如惊涛骇浪,激荡着读者的思想。他对“罪”的理解,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那些不愿承认的阴暗面,但同时,他对“信”的阐释,又给了我们走向光明的希望。他所提出的宗教观,虽然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其内核却充满了普世的价值。它鼓励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质疑,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坚定。读这本书,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净化和升华,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段旅程,一段通往内心深处的旅程。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内容之深邃,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智慧,以及他那种严谨而又充满诗意的表达方式,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反复咀嚼。他对“罪”与“信”的关联性的阐述,更是精辟入里。他并没有将它们割裂开来,而是展示了它们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正是对罪的深刻认识,才更能激发我们对信的渴望,而真正的信,又能帮助我们超越罪的束缚。这种辩证的思考,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哲学功底和对人性深刻的洞察。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被极大地拓宽了,也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深圳律师实务丛书:律师参与调解的技巧与艺术 [The Review of Shenzhen Lawyers:Art and Skill of the Lawyers Involved in Medi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94756/rBEHalBeugAIAAAAAAEWxD-r4b8AABehwKcBskAARbc26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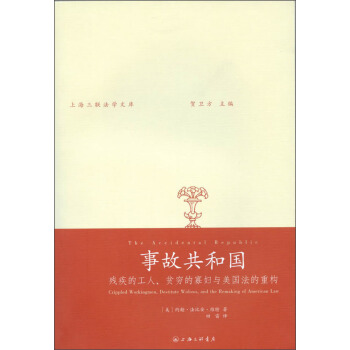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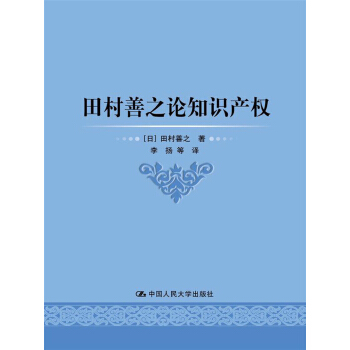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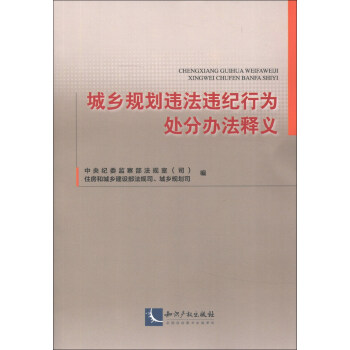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国际法哲学导论 [Fundamentals on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52392/rBEhUlGyyJ8IAAAAAAMhnaGttKkAAAFcwNnz4QAAyG149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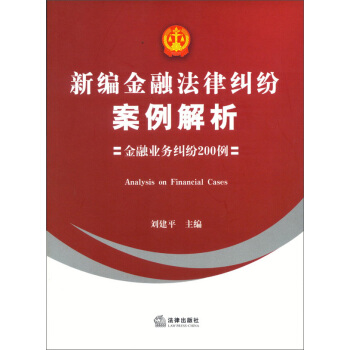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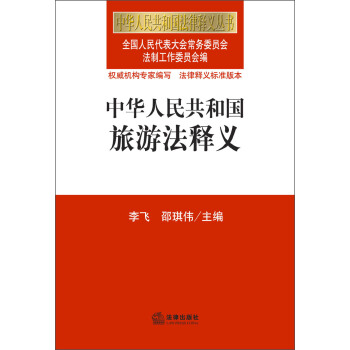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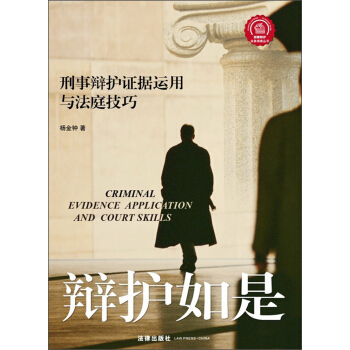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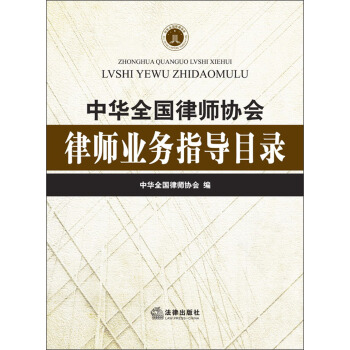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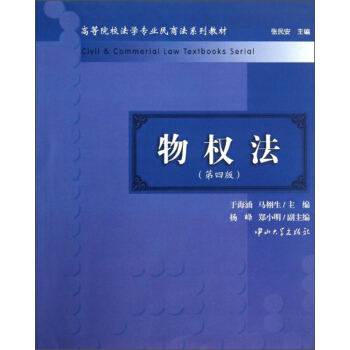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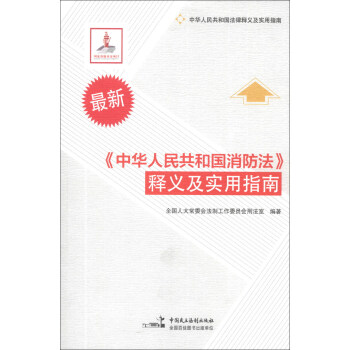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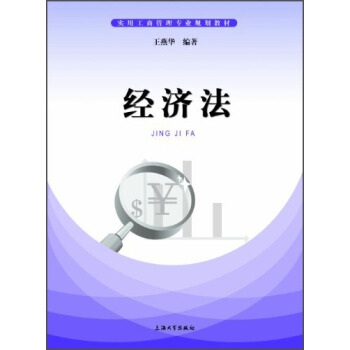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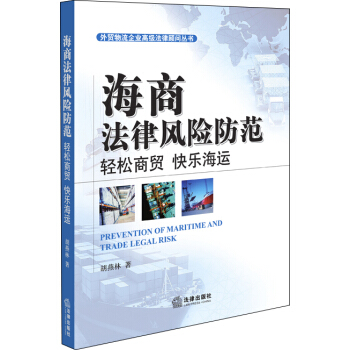
![法官博士文库:公司章程效力研究 [Study on the Validity of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16918/rBEhVFMdNfcIAAAAAA97or-PxW0AAJxoAAAAAAAD3u68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