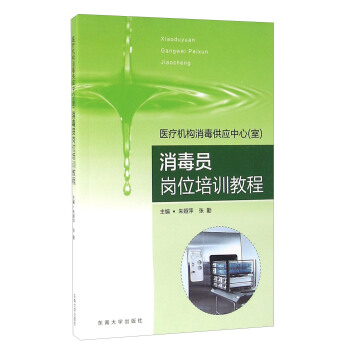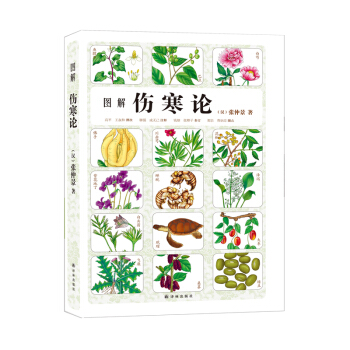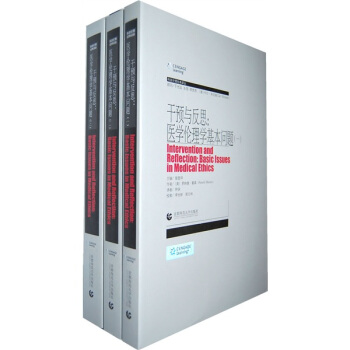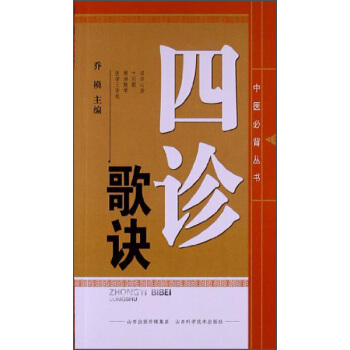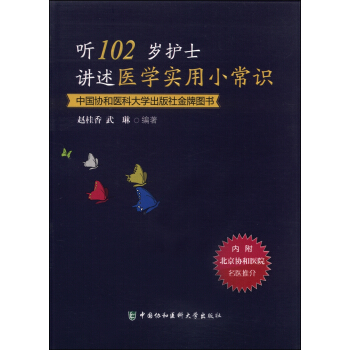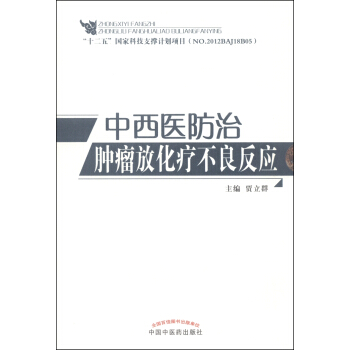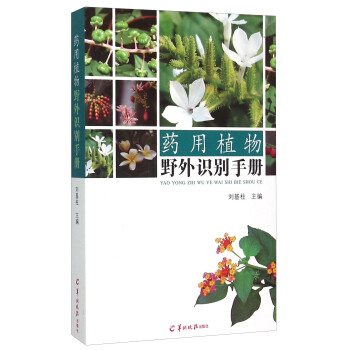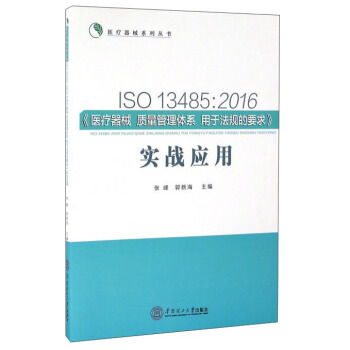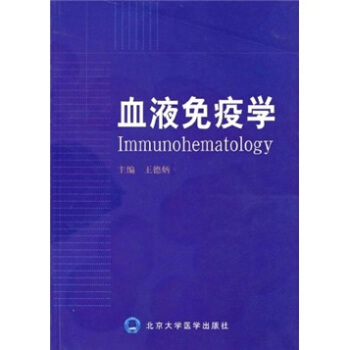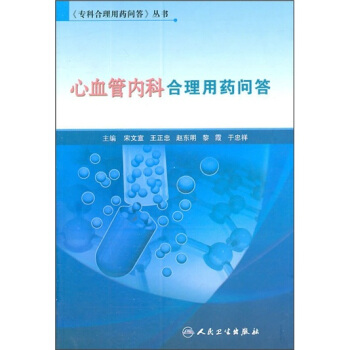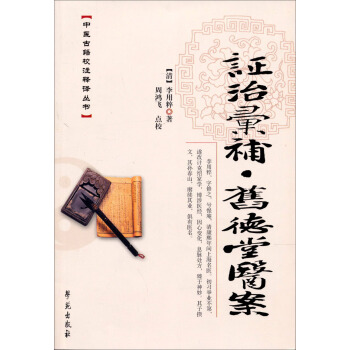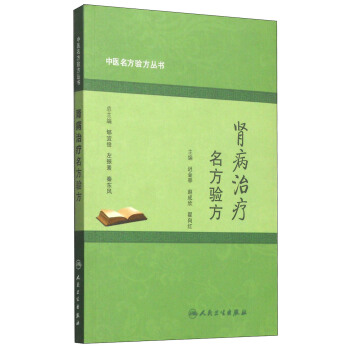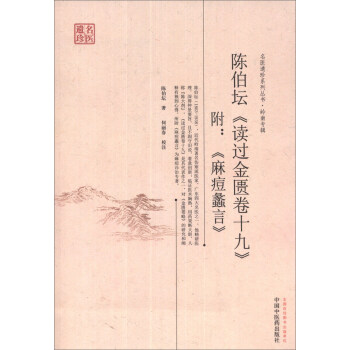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陈伯坛(1863-1938),近代岭南著名伤寒派医家,广东四大名医之一。他精研医理,深得仲景要旨,且不固守旧说,着意创新:临证医术娴熟,用药果断大胆,人称“陈大剂”。《名医遗珍系列丛书·领南专辑:陈伯坛<读过金匮卷十九>》是其代表作之一,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和阐释有独到心得,提出探讨《金匮》当与《伤寒》合观,治卒病注重风邪,读《金匮》当参透“传”字,讲传变当求五行等观点。尤其重视肝脾在发病和治疗中的重要性,深得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妙”,足见其对整体观及治未病思想的认识。所附《麻瘦蠡言》是其麻痘诊治专著,重视营卫之气,提倡去繁就简,诊治方法简便实用,反对用苦寒之品,体现了岭南医学的实用性特色。
此次这两《名医遗珍系列丛书·领南专辑:陈伯坛<读过金匮卷十九>》作为《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岭南专辑》之一,由从事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近30年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何丽春教授遴选底本,并在参阅大量史料文献,专访陈氏后人的基础之上,精心点校、注释,力求充分尊重陈氏之原意,最大限度保持其史料价值,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可靠研读文本。
作者简介
陈伯坛(1863-1938),近代岭南著名伤寒派医家,广东四大名医之一。他精研医理,深得仲景要旨,且不固守旧说,着意创新;临证医术娴熟,用药果断大胆,人称「陈大剂」。《读过金匮卷十九》是其代表作之一,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和阐释有独到心得。所附《麻痘蠡言》为麻痘诊治专著。内页插图
目录
序说起
汉张仲景卒病论卷一
原文之首第
痉湿喝病脉证治第二
栝楼桂枝汤方
葛根汤方
大承气汤方
麻黄加术汤方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
防己黄芪汤方
桂枝附子汤方
白术附子汤方
甘草附子汤方
白虎加人参汤方
瓜蒂汤方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
百合知母汤方
百合滑石代赭汤方
百合鸡子汤方
百合地黄汤方
百合洗方
栝楼牡蛎散方
百合滑石散方
甘草泻心汤方
苦参汤方
雄黄熏法
赤小豆当归散方
升麻鳖甲汤方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鳖甲煎丸方
白虎加桂枝汤方
蜀漆散方
附《外台秘要》三方
牡蛎汤方
柴胡去半夏加栝楼根汤
柴胡桂枝干姜汤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侯氏黑散方
风引汤方
防己地黄汤方
头风摩散方
桂枝芍药知母汤方
乌头汤方
矾石汤方
……
汉张仲景卒病论卷二
汉张仲景卒病论卷三
汉张仲景卒病论卷四
汉张仲景卒病论卷五
精彩书摘
乱发非为功于小便,实为功于白鱼。盖有乱发在,则白鱼尤活动故也。仍以滑石为舟楫者,沉而利滑之品,孰有神于滑石者乎?何以茯苓戎盐汤,又不参加白鱼耶?停小便于溺管之中,小便必凝滞而不行,苟无一物以解化之,则不利如故矣。妙哉戎盐,咸饴合杂,谓之饴盐,生于西戎之鄙,即今陕甘之盐者是,凡盐着水便化水,匪特戎盐始然,究以饴盐为甘美也。何以不用散耶?汤之为言荡也,假令三物杵为散,则味味如弹丸,又聚而不散矣。与滑石合作果何如?戎盐必留中久之而始效,滑石走精锐者也,同行则相左,不观其纳戎盐于煎成之中,再煎之乎?日煎不日煮,缓行苓术可知,白术取其轻,茯苓取其重,徐以俟其清肃之下行又可知。三方皆非亟亟于利小便也,有小便在,不患无小便。《伤寒》赤石脂禹余粮汤证,日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湿痹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日但当利其小便,正与本证同消息。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条下,曰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彼岂始终无小便哉?能于小便不利时,预决其小便利者,亦不患无利小便法也,三方其例焉者也。[1]半分:邓珍刊本、吴迁钞本作“七分”。
[2]方寸匕:邓珍刊本、吴迁钞本作“半钱匕”。
[3]茶:为“茯”的误字。
[4]分温三服:“先将茶苓”至此,邓珍刊本无。吴迁钞本作“叹咀,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渴欲饮水,口干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伤寒》《金匮》本方凡七见,白虎证不渴,加人参则为其渴,本证亦跟上渴字连类而及耳。得毋小便之利不利可勿计耶?所有白虎汤证、白虎加人参汤证无小便不利四字,然则小便必利耶?非也。渴饮证具,非热则烦,是里证成立,仲师亦明言无表证矣,与热不在里,仍在表不同论,从无小便必利之理。何以不日小便不利耶?小便即津液之符,与气化互为其盈虚,假令白虎尚未尝试,而津液先竭,以何物布水精于毫毛乎?白虎下行清肃者也,必令服之者如被甘霖,诸药遂洞开其腠理而不觉。苟因小便不利之故,津液自封其热邪,是州都之地如陷阱,虎威一衰,则震动坎泉,将有灭顶之凶矣。师谓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汗溺皆与膀胱之气化有关系,未有水道通调,而汗源壅塞者,太阳中热日其人汗出,得汗且如此,况小便乎!不然,阳明篇亦有白虎猪苓二证在也,小便不利主猪苓,何尝以白虎越俎乎?在阳明日口干舌燥,本证日口干燥,干燥形上不形下,便与下窍无涉,宜乎无小便不利之端倪,仲师特举多数白虎证,与上文渴欲饮水不止之文蛤散证异而同。造次与文蛤散祸犹小,造次行白虎加人参,则祸实大也。又不能以数少律小便也,例如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毫无窒碍者,小便虽少亦为利,非必小便数多才算利也。不利二字,当从小便难上看出也。汤见上,方注从省。
[1]口干燥:邓珍刊本、吴迁钞本作“口干舌燥”。
[2]白虎加人参汤主之:邓珍刊本下有小注“方见中喝中”。吴迁钞本下有小注“方见喝病中”。
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本条在《伤寒》既见于阳明,再见于少阴,上文师又言渴者与猪苓汤矣,其为泛应不穷可知。胡不留为下文水气用耶?师谓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本方非利小便乎哉?阳明汗出多而渴,本方有复利其小便之嫌,是猪苓汤最长于利小便矣。何以反为水气病之禁剂耶?匪特禁猪苓也,自痰饮咳嗽苓桂术甘汤以下,共二十七方,皆置而不用,独蒲灰散则厥而皮水者得与有其功,其余一路诸方,则与水气无涉也。仲师为前此去水诸药作大结束,进中工与言治五水之难,见得猪苓汤不能滥予,亦与爱惜阳明之津液同一例,白虎更宜谭(谈)之色变矣。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拿到这套《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岭南专辑》,尤其是陈伯坛先生的《读过金匮卷十九》(附《麻痘蠡言》),真的让我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厚重和传承的力量。陈老先生的文字,充满了大家风范,既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又不失温文尔雅的学者气质。他对《金匮要略》的理解,可以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挖掘出了其临床应用价值。我特别喜欢他对于“审证求因”的强调,他反复提醒读者,治疗的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病机,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辨病或者症状层面。书中对于一些经典方剂的讲解,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深入分析了该方剂适用的病机特点,以及在不同证候下的变化。他常常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复杂的医学概念,使得即使是初学者,也能从中获得启发。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金匮要略》的理解更加立体和深刻,不再是被动地记忆条文,而是能够主动地去思考和应用。
评分作为一名对中医理论颇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这次阅读陈伯坛先生的《读过金匮卷十九》(附《麻痘蠡言》),体验到的是一种沉浸式的学习过程。书中的内容并非是枯燥的学术论述,更多的是一种引人入胜的探索。陈老先生的文字流畅而富有逻辑性,他通过对《金匮要略》卷十九的精读,展现了他如何从经典的字里行间提炼出临床辨证施治的精髓。我特别欣赏他对于一些疑难病症的剖析,那种严谨的思维方式,如同侦探破案般,层层剥茧,最终指向疾病的根源。他对于方证的把握,往往能触及病之“枢机”,让我明白了为何某些方剂在特定情况下如此奏效。书中还穿插了一些他自己的临证体会,这些“锦上添花”的案例,让原本就精彩的理论阐述更加接地气,充满了人文关怀。阅读过程中,我时不时会停下来,对照自己的临床经验或者书本上的知识进行思考,这种主动学习的方式,让知识的吸收更加深刻。这本书不仅仅是学习《金匮要略》的辅助读物,更是一本启发思维、提升临床思维能力的上佳之作。
评分这次有幸接触到这套《名医遗珍系列丛书·岭南专辑》,尤其是陈伯坛老先生的《读过金匮卷十九》(附《麻痘蠡言》),实在是让我受益匪浅。首先,整套丛书的编排和装帧就体现出一种对经典传承的尊重,纸张的质感、印刷的清晰度都属上乘。翻开《读过金匮卷十九》,立刻被陈老先生那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辟的见解所折服。他并非简单地照搬《金匮要略》原文,而是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对经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和阐发。那些看似晦涩难懂的古文,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形象,仿佛一位慈祥的长者在娓娓道来。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陈老先生在阐释方剂组成时,不仅仅停留在药味和剂量上,更深入地挖掘了药物的配伍原理、君臣佐使的搭配逻辑,以及方剂在不同病机下的变化和应用。他对于病机演变的分析,常常能触及问题的本质,让我恍然大悟,对《金匮要略》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是古籍的解读,但通篇没有古板的生硬感,而是充满了鲜活的临床智慧,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
评分这次能读到陈伯坛老先生的《读过金匮卷十九》(附《麻痘蠡言》),感觉像是开启了一扇通往中医智慧殿堂的大门。陈老先生的学识渊博,对《金匮要略》的钻研可谓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是对原文的解读,更是对经典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我尤其被他在解读篇幅较少的条文时,所展现出的深刻洞察力所吸引。他能从寥寥数语中,挖掘出丰富的病机信息和治疗思路,这需要长年累月的临床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作为支撑。书中对于一些方剂的演变和加减,他都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明白了中医治疗的灵活性和个体化。那些看似微小的调整,却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治疗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此外,附带的《麻痘蠡言》也让我对陈老先生在儿科方面的造诣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在治疗麻疹和痘疹方面的经验,对于当下的儿科临床仍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总而言之,这本书是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之作,对于想要深入理解《金匮要略》的读者来说,绝对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评分这一次阅读陈伯坛先生的《读过金匮卷十九》(附《麻痘蠡言》),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严谨治学态度和深厚的临床智慧。陈老先生在解读《金匮要略》时,展现了他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同时也敢于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他不仅仅是对文字的梳理,更是对背后蕴含的医学思想的挖掘和阐释。我尤其欣赏他对于方证关系的处理,他能够清晰地勾勒出方剂所对应的病机特点,以及在临床上如何辨别和运用。那些看似简单的方剂,在他的解读下,充满了精妙的配伍智慧和治疗变化。书中附带的《麻痘蠡言》更是让我看到了陈老先生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在那个时代,能够总结出如此系统有效的治疗经验,实属不易。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对经典文献的解读,更在于它传递了一种治学精神和临床态度,这对于我们后辈学习中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评分嗯,挺好的
评分不错!!!
评分看图作文。刊行时间的确很早,也不知是库存亦或是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整体比较老旧,体验很一般了,书的内容值得一看
评分不错!!!
评分不错!!!
评分嗯,挺好的
评分嗯,挺好的
评分看图作文。刊行时间的确很早,也不知是库存亦或是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整体比较老旧,体验很一般了,书的内容值得一看
评分看图作文。刊行时间的确很早,也不知是库存亦或是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整体比较老旧,体验很一般了,书的内容值得一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磁共振成像设备技术学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34114/567d207dN3666632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