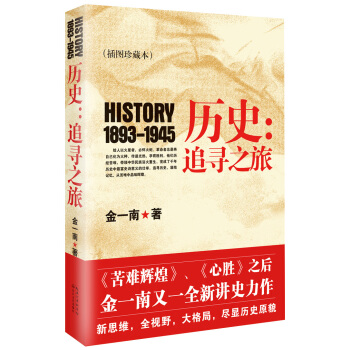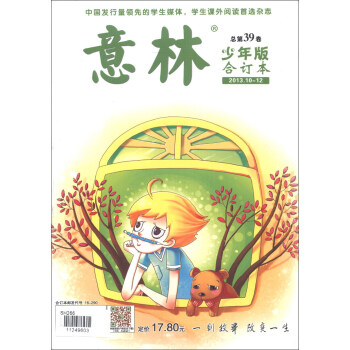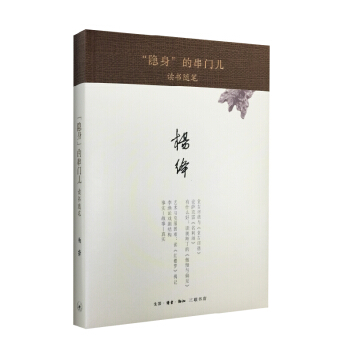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出版说明
杨绛先生于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期间,由清华大学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做研究工作,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少量必要的论文” (《杨绛文集·作者自序》)。本书收入的四篇: 《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 (一九五七)、 《论萨克雷〈名利场〉》 (一九五九)、 《艺术与克服困难》 (一九五九)和《李渔论戏剧结构》 (一九五九),即写于这一时期。其中《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一文曾在一九五八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被树为文学研究所的四面“白旗”之一;《论萨克雷〈名利场〉》一文也因全文欠“红线贯穿”,而受批判。
“文革”结束后,杨绛先生不仅写散文、写小说、做翻译,也重新开始写“论文”,即收入本书的《事实—故事—真实》 (一九八○)、 《旧书新解》 (一九八一)、 《有什么好?》 (一九八二)等,这几篇文章都与小说的理论、阅读与阐释有关,因而于一九八五年以《关于小说》之名结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以上七篇“论文”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另有两篇译者前言(《〈吉尔·布拉斯〉译者前言》)或序言(《〈小癞子〉译本序》)因属文本导读性质,故一并纳入,还有一篇《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 (一九八五)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杨绛先生对她翻译的这部名著的理解,后来该文在一头一尾分别增加了对作者塞万提斯和翻译版本情况的简要介绍之后,作为《堂吉诃德》中译本的“译者序”刊行。
但愿这十篇文章会在作为翻译家与作家身份的杨绛之外,为我们还原一个作为优秀学者的杨绛。
征得作者同意,书名取自其一九八九年的一篇随笔《读书苦乐》,其中提道: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杨绛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读书钻研学问”有形象的描绘,有独到的理解,因而她的“学术论文”一如她的散文随笔,洗练精审、亲切自然,犹如拜望鸿儒之后的兴会随感,闲话般娓娓道来,而没有时下的八股气、学究腔——当然这也是她极力避免的。
本次结集,除少量排印错讹外,一般不做更动,如译名和注释体例等,不强求统一,以保留作者不同时期的行文原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二○一四年十月
内容简介
《“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精装)》收录了杨绛先生的论文七篇:《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论萨克雷<名利场>》《艺术与克服困难》《李渔论戏剧结构》《事实-故事-真实》《旧书新解》《有什么好》,另有两篇译者前言《<吉尔·布拉斯>译者前言》或序言《<小癞子>译本序》,还有一篇《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杨绛先生对她翻译的这部名著的理解,后来该文在一头一尾为别增加了对作者塞万提斯和翻译版本情况的简要介绍之后,作为《堂吉诃德》中译本的“译者序”刊行。
作者简介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目录
代前言读书苦乐一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
二论萨克雷《名利场》
三艺术与克服困难
——读《红楼梦》偶记
四李渔论戏剧结构
五事实—故事—真实
六旧书新解
——读《薛蕾丝蒂娜》
七有什么好?
——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
八《吉尔·布拉斯》译者前言
九《小癞子》译本序
十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
出版说明
精彩书摘
一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隐身”的串门儿
一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
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菲尔丁说自己的小说是英国语言中从来未有的体裁,文学史家也公认他是英国小说的鼻祖。马克思对他的爱好,小说家像司各特、萨克雷、高尔基等对他的推崇高尔基对菲尔丁的推崇,见叶利斯特拉托娃著《菲尔丁论》——《译文》一九五四年九月号136页。,斯汤达(Stendhal)对他的刻意摹仿参看安贝尔(H�盕�盜mbert) 《斯汤达和〈汤姆·琼斯〉》 (Stendhal et“Tom Jones”)——《比较文学杂志》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九月号351—370页。,都使我们想探讨一下,究竟他有什么独到之处,在小说的领域里有什么贡献。好在菲尔丁不但创了一种小说体裁,还附带在小说里提供一些理论,说明他那种小说的性质、宗旨、题材、作法等等;他不但立下理论,还在叙事中加上评语按语之类。他在小说里搀入这些理论和按语,无意中给我们以学习和研究的线索。我们凭他的理论,对他的作品可以了解得更深切。这里综合他的小说理论,作一个试探的介绍。
菲尔丁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分散在他小说的献词、序文和《汤姆·琼斯》每卷第一章里。最提纲挈领的是他第一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序,这里他替自己别开生面的小说体裁下了界说,又加以说明;在这部小说头三卷的第一章里又有些补充。《汤姆·琼斯》的献词和每卷的第一章、 《阿米丽亚》和《江奈生·魏尔德》二书的首卷第一章以及各部小说的叙事正文里还有补充或说明。
菲尔丁的读者往往嫌那些议论阻滞了故事的进展,或者草草带过,或者竟略去不看。《汤姆·琼斯》最早的法文译本庇艾尔·安德华纳·德·拉·普拉斯(Pierre�睞ntoine de la Place)的译本一七五○年出版。,老实不客气地把卷首的理论文章几乎全部删去。但也有读者如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司各特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对这几章十分赞赏。司各特说,这些议论初看似乎阻滞故事的进展,但是看到第二三遍,就觉得这是全书最有趣味的几章。见《小说家列传》 (Lives of the Novelists)——世界经典丛书版22页。艾略特很喜欢《汤姆·琼斯》里节外生枝的议论,尤其每卷的第一章;她说菲尔丁好像搬了个扶手椅子坐在舞台上和我们闲谈,那一口好英文讲来又有劲道,又极自在。见《米德尔马契》 (Middlemarch)第15章——世界经典丛书版147页。可是称赞的尽管称赞,并没有把他的理论当正经。近代法国学者狄容(Aurélien Digeon)说,菲尔丁把他的小说解释为“滑稽史诗”,而历来文学史家似乎忽视了他这个观念。见《菲尔丁的小说》 (Les Romans de Fielding)一九二三年版284—285页。这话实在中肯。最近英国学者德登(F�盚omes Dudden)著《菲尔丁》两大册见《亨利·菲尔丁:他的生平、著作和时代》 (Henry Fielding,his Life,Works,and Times),一九五二年版。,对菲尔丁作了详细的研究。可是他只说, “散文体的滑稽史诗”不是什么新的观念。他并没说出这个观念包含什么重要意义,只把“滑稽史诗”和史诗、悲剧、喜剧、传记、传奇等略微分别一下,又把菲尔丁的理论略微叙述几点,并没有指出菲尔丁理论的根据,也没有说明他理论的体系见德登著《菲尔丁》第1册328—334页,又第2册666—671页。,因而也不能指出菲尔丁根据了传统的理论有什么新的发明。
菲尔丁写这些理论很认真。他自己说, 《汤姆·琼斯》每卷的第一章,读者看来也许最乏味,作者写来也最吃力见《汤姆·琼斯》 (以下简称《汤》)第5卷第1章。本文翻译原文,都加引号;没有引号的只是撮述大意。;又说,每卷的第一章写来比整卷的小说还费事。见《汤》第16卷第1章。他把这些第一章和戏剧的序幕相比,因为都和正戏无关,甲戏的序,不妨移到乙戏;他第一卷的第一章,也不妨移入第二卷;他也并不是每卷挨次先写第一章,有几卷的第一章大概是小说写完之后补写的。见德登《菲尔丁》第2册591—592页。他为什么定要吃力不讨好地写这几章呢?菲尔丁开玩笑说,一来给批评家叫骂的机会,二来可充他们的磨刀石,三来让懒惰的读者节省时间,略过不读。见《汤》第16卷第1章。他又含讥带讽说,他每卷的第一章,好比戏院里正戏前面的滑稽戏,可作陪衬之用;正经得索然无味,才见得滑稽的有趣。见《汤》第5卷第1章。又说,这第一章是个标志,显得他和一般小说家不同,好比当时风行的《旁观者》 (Spectator)见斯狄尔(R�盨teele)和艾迪生(Addison)一七一一年编辑的报纸。开篇引些希腊拉丁的成语,叫无才无学的人无法摹仿。见《汤》第9卷第1章。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菲尔丁觉得自己的小说和一般小说不同,怕人家不识货,所以要在他的创作里插进那些理论的成分。他在《约瑟夫·安德鲁斯》里说,他这种小说在英文里还没人尝试过,只怕一般读者对小说另有要求,看了下文会觉得不满意见《约瑟夫·安德鲁斯》 (以下简称《约》)序。;又在《汤姆·琼斯》里说,他不受别人裁制,他是这种小说的创始人,得由他自定规律。见《汤》第2卷第1章。这几句话才是他的真心实话。
二论萨克雷《名利场》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是英国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 《名利场》 (Vanity Fair)是他的成名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赞他观察细微,对人生和人类的心灵了解深刻,富有幽默,刻画人物非常精确,叙述故事非常动人。他认为当代欧洲作家里萨克雷是第一流的大天才。见《俄罗斯作家论文学著作》
《名利场》描写的是什么呢?马克思论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时说: “他们用逼真而动人的文笔,揭露出政治和社会上的真相;一切政治家、政论家、道德家所揭露的加在一起,还不如他们揭露的多。他们描写了中等阶级的每个阶层:从鄙视一切商业的十足绅士气派的大股东、直到小本经营的店掌柜以及律师手下的小书记。”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 (�aber Kunst und Literatur),一九五三年柏林版254—255页。《名利场》这部小说正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英国在十九世纪前期成了强大的工业国,扩大了殖民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讲究的是放任主义和自由竞赛莫登(A.L.Morton) 《人民的英国史》 (A People�餾 History of England)劳伦斯·惠沙特(Lawrence & Wishart)版380页。,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分裂成贫富悬殊的两个阶层。新兴资产阶级靠金钱的势力,渐渐挨近贵族的边缘;无产阶级越来越穷,困苦不堪。萨克雷说,看到穷人的生活,会对慈悲的上天发生怀疑。见《萨克雷全集》 (The Work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纽约柯列(Collier)公司版(以下简称《全集》)第22册108—109页;又第21册245—246页。他对他们有深切的同情萨克雷说,富人瞧不起穷人是罪恶。——见戈登·瑞(Gordon N�盧ay)编《萨克雷书信集》 (以下简称《书信集》)哈佛大学版第2册364页;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智慧一点也不输于他们的统治者,而且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为什么让那样有钱的腐朽的统治者压在头上(《全集》第15册425—428页)。,而且觉得描写矿工和工厂劳工的生活可以唤起普遍的注意,这是个伟大的、还没有开垦的领域,可是他认为一定要在这个环境里生长的人才描写得好。他希望工人队伍里出个把像狄更斯那样的天才,把他们的工作、娱乐、感情、兴趣,以及个人和集体的生活细细描写。见戈登·瑞编《萨克雷在〈晨报〉发表的文章汇辑》 (Thackeray�餾 Contributions to the Morning Chronicle)一九五五年版77—78页。他自己限于出身和环境,没有做这番尝试。萨克雷看到富人和穷人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彼此不相来往,有钱的人对穷人生活竟是一无所知(见《全集》第15册391—393页;第22册108页)。他说只有狄更斯描写过在人口里占大多数的穷人的生活(《全集》第22册103页)。
萨克雷不仅描写“名利场”上种种丑恶的现象,还想指出这些现象的根源。他看到败坏人类品性的根源是笼罩着整个社会的自私自利。萨克雷认为自私自利的心是这个世界的推动力(《书信集》第2册357页)。他在下一部小说《潘丹尼斯》 (Pendennis)里尤其着力阐明这点:人人都自私、推动一切的是自私心(《全集》第4册232,336,352,381,425页;又见第9册111页)。他说,这部小说里人人都愚昧自私,一心追慕荣利。见《书信集》第2册423页。他把表面上看来很美好的行为也剖析一下,抉出隐藏在底里的自私心。他以为我们热心关怀别人的时候,难保没有私心;我们的爱也混杂着许多自私的成分。见《全集》第1册448页。老奥斯本爱他的儿子,可是他更爱的是自己,他要把自己那种鄙俗的心愿在儿子身上完偿。爱米丽亚忠于战死的丈夫,只肯和都宾做朋友;其实她要占有都宾的爱,而不肯把自己的爱情答报他。一般小说家在这种地方往往笔下留情,萨克雷却不肯放过。他并非无情,但是他要描写真实。有人说他一面挖掘人情的丑恶,一面又同情人的苦恼;可是他忍住眼泪,还做他冷静的分析。参看拉斯·维格那斯(Las Vergnas)著《萨克雷——他的生平、思想和小说》 (W�盡�盩hackeray:L′Homme,le Penseur,le Romancier),巴黎一九三二年版84页。萨克雷写出了自私心的丑恶,更进一步,描写一切个人打算的烦恼和苦痛,到头来却又毫无价值,只落得一场空。爱米丽亚一心想和她所崇拜的英雄结婚,可是她遂心如愿以后只觉得失望和后悔。都宾和他十八年来魂思梦想的爱米丽亚结婚了,可是他已经看破她是个浅狭而且愚昧的女人,觉得自己对她那般痴心很不值得。利蓓加为了金钱和地位费尽心机,可是她钻营了一辈子也没有称愿;就算她称了愿,她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萨克雷看了这一群可怜人烦忧苦恼得无谓,满怀悲悯地慨叹说: “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乐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见《全集》第2册428页。这段话使我们联想到《镜花缘》里的话: “世上名利场中,原是一座迷魂阵。此人正在场中吐气扬眉,洋洋得意,哪个还把他们拗得过……一经把眼闭了,这才晓得从前各事都是枉费心机,不过做了一场春梦。人若识透此义,那争名夺利之心固然一时不能打断,倘诸事略为看破,退后一步,忍耐三分,也就免了许多烦恼,少了无限风波。如此行去,不独算得处世良方,亦是一生快活不尽的秘诀。”见《镜花缘》第16回。萨克雷也识透“名利场”里的人是在“迷魂阵”里枉费心机,但是他绝不宣扬“退后一步,忍耐三分”,把这个作为“处世良方,快活秘诀”。
《名利场》描摹真实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尝试。萨克雷觉得时俗所欣赏的许多小说里,人物、故事和情感都不够真实。所以他曾把当时风行的几部小说摹仿取笑。参看《名作家的小说》 (Novels by Eminent Hands),见《全集》第19册。《名利场》的写法不同一般,他刻意求真实,在许多地方打破了写小说的常规滥调。
《名利场》里没有“英雄”,这部小说的副题是《没有英雄的小说》 (A Novel Without a Hero),这也是最初的书名。见《书信集》第2册233页。对于这个副题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没有主角的小说”,因为不以一个主角为中心参看西昔尔(D�盋ecil) 《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小说家》 (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 《企鹅丛书》版66页。;这部小说在《笨拙周报》上发表时,副题是“英国社会的速写”,也表明了这一点。另一说是“没有英雄的小说”;英雄是超群绝伦的人物,能改换社会环境,这部小说的角色都是受环境和时代宰制的普通人。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著《萨克雷评传》一八九二年版91页;普拉兹(M�盤raz) 《英雄的消灭》牛津版213页;凯丝琳·铁洛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229页;西昔尔《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小说家》66页也提到这一点。两说并不矛盾,可以统一。萨克雷在《名利场》里不拿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做主角。他在开卷第一章就说,这部小说写的是琐碎庸俗的事,如果读者只钦慕伟大的英雄事迹,奉劝他趁早别看这部书。见《全集》第1册6—7页。萨克雷以为理想的人物和崇高的情感属于悲剧和诗歌的领域,小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尽力写出真实的情感。见《书信集》第2册772页。萨克雷反对小说里写英雄,参看《全集》第12册74、76、177页。最近有人凭主角左右环境的能力把作品分别种类,说:主角能任意操纵环境的是神话里的神道;主角超群绝伦,能制伏环境的是传奇里的英雄;主角略比常人胜几筹、但受环境束缚的是史诗和悲剧的英雄;主角是我们一般的人,也不能左右环境,他就称不得“英雄”,因此萨克雷只好把他的《名利场》称为“没有英雄的小说”;主角能力不如我们,那是讽刺作品里的人物。——见傅赖(N�盕rye) 《批评的解剖》 (Anatomy of Criticism),普林斯登(Princeton)版33—34页。他写的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一群小人物,像破产的赛特笠,发财的奥斯本,战死的乔治等;甚至像利蓓加,尽管她不肯向环境屈服,但又始终没有克服她的环境。他们悲苦的命运不是悲剧,只是人生的讽刺。
一般小说里总有些令人向往的人物, 《名利场》里不仅没有英雄,连正面人物也很少,而且都有很大的缺点。萨克雷说都宾是傻瓜,爱米丽亚很自私。他说,他不准备写完美的人或近乎完美的人,这部小说里除了都宾以外,各个人的面貌都很丑恶。见《书信集》第2册309页。传统小说里往往有个令人惬意的公道:好人有好报,恶人自食恶果。萨克雷以为这又不合事实,这个世界上何尝有这等公道。荣辱成败好比打彩票的中奖和不中奖,全是偶然,全靠运气。同上书,402页;《全集》第2册272页;又参看第12册60页,第13册105,112页。温和、善良、聪明的人往往穷困不得志,自私、愚笨、凶恶的人倒常常一帆风顺。见《全集》第2册273页,又参看《全集》第4册448—450页。这样看来,成功得意有什么价值呢同上书,32页。;况且也只是过眼云烟,几年之后,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上难道还留下什么痕迹吗?同上书,第15册351—352页。因此他反对小说家把成功得意来酬报他的英雄。同上书,第12册177页。《名利场》里的都宾和爱米丽亚等驯良的人在社会上并不得意,并不成功;丑恶的斯丹恩勋爵到死有钱有势;利蓓加不择手段,终于捞到一笔钱,冒充体面人物。萨克雷给朋友的信上安排了《名利场》结束时利蓓加怎样下场。信尾说,利蓓加存款的银行倒闭,把她的存款一卷而空。可是他没有把这点写到小说里去(参看《书信集》第2册377页)。《名利场》上的名位利禄并不是按着每个人的才能品德来分配的。一般小说又往往把主角结婚作为故事的收场。萨克雷也不以为然。他批评这种写法,好像人生的忧虑和苦恼到结婚就都结束了,这也不合真实,人生的忧患到结婚方才开始。见《全集》第1册320页。所以我们两位女角都在故事前半部就结婚了。
萨克雷刻意描写真实,却难免当时社会的限制。维多利亚社会所不容正视的一切,他不能明写,只好暗示。所以他叹恨不能像菲尔丁写《汤姆·琼斯》那样真实。见《全集》第3册导言6页。他在这部小说里写到男女私情,只隐隐约约,让读者会意。见《全集》第2册359页。譬如利蓓加和乔治的关系只说相约私奔,利蓓加和斯丹恩勋爵的关系只写到斯丹恩吻利蓓加的手。如果把萨克雷和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福楼拜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描写真实的程度上、选择细节的标准上有极大的区别。
萨克雷和菲尔丁一样,喜欢夹叙夹议,像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时时现身说法对人物和故事做一番批评。作家露面发议论会打断故事,引起读者嫌厌。不过这也看发议论的艺术如何。《名利场》这部小说是作者以说书先生的姿态向读者叙述的;他以《名利场》里的个中人身份讲他本人熟悉的事,口吻亲切随便,所以叙事里搀入议论也很自然。萨克雷在序文里说: “这场表演……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他的议论就是台上点的蜡烛。他那批判的目光照明了台上的把戏,他的同情和悲悯笼罩着整个舞台。因此很有人为他的夹叙夹议作辩护。见《小说家萨克雷》71—114页;《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251—256页。但是萨克雷的议论有时流于平凡啰嗦,在他的小说里就仿佛“光滑的明镜上着了些霉暗的斑点”见奥列弗·艾尔登(Oliver Elton)著《一八三○—一八八○年英国文学概观》 (A Surve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2册231页。。还有一层,他穿插进去的议论有时和他正文里的描写并不协调。他对爱米丽亚口口声声的赞美,就在批评她没头脑、虚荣、自私的时候,口吻间还含蕴着爱怜袒护。我们从他的自白里知道,爱米丽亚这个人物大部分代表他那位“可怜”的妻子依莎贝拉见《书信集》第3册468页。,在爱米丽亚身上寄托着他的悲哀和怜悯;他在议论的时候抒写这种情感原是极自然的事,但是他议论里的空言赞美和他故事里的具体刻画不大融洽,弄得读者摸不透他对爱米丽亚究竟是爱、是憎、是赞扬、是讽刺。譬如凯丝琳·铁洛生就以为萨克雷是在讽刺爱米丽亚这种类型的女角(见《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246页)。有的读者以为作者这般赞美的人物准是他的理想人物,可是按他的描写,这个人物只是个平庸脆弱的女人。是作者的理想不高呢?还是没把理想体现成功呢?读者对爱米丽亚的不满就变为对作者的不满了。见《萨克雷生平索隐》36页。萨克雷的女友——萨克雷认为有“一部分”和爱米丽亚相似的那一位——也很不满意爱米丽亚这个人物(见《书信集》第2册335页又395页)。
萨克雷善于叙事,写来生动有趣,富于幽默。他的对话口角宛然,恰配身份。他文笔轻快,好像写来全不费劲,其实却经过细心琢磨。因此即使在小说不甚精警的部分,读者也能很流利地阅读下去。《名利场》很能引人入胜。但是读毕这部小说,读者往往觉得郁闷、失望。这恰是作者的意图。他说: “我要故事在结束时叫每个人都不满意、不快活——我们对于自己的故事以及一切故事都应当这样感觉。”见《书信集》第2册423页。他要我们正视真实的情况而感到不满,这样来启人深思、促人改善。
《名利场》在英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萨克雷用许许多多真实的细节,具体描摹出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断,在那时候只有法国的斯汤达和巴尔扎克用过这种笔法,英国小说史上他还是个草创者。见《忧患的锻炼》394—395页。他为了描写真实,在写《名利场》时打破了许多写小说的常规。这部小说,可以说在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的境地。
一九五九年
前言/序言
代前言读书苦乐“隐身”的串门儿
代前言读书苦乐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 “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伙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 “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塞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捡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
可惜我们“串门儿”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
用户评价
《隐身》的串门儿,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诗意与想象。我好奇这“串门儿”究竟是串起了怎样的思想,又“隐身”在怎样的角落。它是否是一本关于阅读的阅读?亦或是,作者通过“串门儿”的方式,串联起不同主题、不同作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思想网络?“隐身”的意象,让我猜测,作者或许善于从那些不显眼的地方发掘价值,从那些被忽视的细节中提炼智慧。我期待这本书能打破常规的解读方式,为我打开一扇全新的看待文学、看待世界的大门。精装的质感,也让我对这本书的内容有了更高的期望。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一本纸质的书,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思想馈赠,一份能够滋养灵魂的甘泉。我渴望在这本书中,遇到那些我曾忽略的闪光点,听到那些被低语的智慧之声。
评分翻开这本《隐身》的串门儿,我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进入了一个由文字构筑的奇妙世界。这本书的精装质感就已经让人爱不释手,厚重而典雅,仿佛每一页都承载着作者对阅读的敬意。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的是,那些隐藏在日常琐碎中的深刻洞察,那些不为人知的精神角落。作者笔下的“串门儿”并非简单的走访,而更像是一种灵魂的交流,一种思想的碰撞。我期待着,通过这些“串门儿”,能窥见作者内心深处那些不曾显露的思考,那些在喧嚣世界中悄然生长的感悟。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也十分别致,那若隐若现的书名,恰如其分地呼应了“隐身”的主题,让人在好奇中,对内文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我喜欢这种留白的艺术,它给了读者足够的空间去想象,去构建属于自己的阅读体验。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我进入一种全新的阅读状态,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与作者一同探寻,一同发现。
评分读到《隐身》的串门儿,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许多画面。我设想着,作者或许是以一种极其放松、随性的姿态,在某个午后,一杯清茶,一本好书,然后将自己沉浸其中,再将这份沉浸的感悟,以一种近乎私语的方式,分享给我们。这种“串门儿”的意象,让我感受到一种亲近感,仿佛作者并非高高在上的智者,而是一位与我们并肩同行的旅人。我渴望在这本书中,看到那些对生活细微之处的敏锐捕捉,对人情冷暖的深刻体悟。它可能涉及的“隐身”,或许是一种不被察觉的观察,一种不动声色的思考,而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足以撼动人心的力量。这本书的精装本,本身就带有一种仪式感,它提醒着我,这是一次值得郑重对待的精神之旅,一次与作者、与思想的深度对话。我期待在这段旅程中,能够涤荡心灵,获得新的启迪。
评分这本《隐身》的串门儿,初见时便被那份沉甸甸的质感所吸引。精装的扉页,细腻的纸张,无不透露出一种对文字本身的尊重,也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期待。我好奇的是,作者笔下的“串门儿”究竟是怎样的形式?是关于某本经典著作的解读,还是对某个文学流派的探索?抑或是,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跨越时空的精神漫游?“隐身”二字,更是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暗示着一种不张扬,一种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的力量。我期待在这本书中,找到那些不喧哗、自鸣惊人的思想火花,那些在平凡生活表象之下,涌动的生命力。我希望它能像一位默不作声的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递过来一句点醒你的话语,或者一个让你豁然开朗的视角。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单而富有深意,仿佛在邀请读者一同潜入文字的深海,去发掘那些被隐藏的宝藏。
评分这本《隐身》的串门儿,在我拿到它的一瞬间,就被它的分量和精美的装帧所打动。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艺术品。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作者的“串门儿”是怎样的形式?是像一位隐士,在某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观察着世事变迁,然后将他的感悟娓娓道来?“隐身”这个词,让我感觉这本书可能并非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一种含蓄、内敛的方式,传递深刻的思想。我期待在其中找到那些不动声色的观察,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智慧,那些能够让你在某个瞬间,突然顿悟的句子。它可能不会给你明确的答案,但会引导你去思考,去探索,去发掘属于自己的真理。这本书的精装,仿佛在暗示着,内容同样是厚重而值得珍藏的,我期待着它能成为我书架上,一本常读常新的精神伴侣。
评分挖绩脚
评分好书,超赞,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包装用了纸箱,很不错?搞活动价格也很给力!
评分感谢京东 活动很给力 谢谢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不错不能,书非常好吃看!!!
评分好书,超赞,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现在习惯在京东购物,速度已没话说,书籍的纸质、包装都很好。忙碌的人,近来书读得少了点,趁着搞活动多订了些,有了这么多书的陪伴也暂且可以歇歇脚了……
评分书本里的字清晰,一看就是正版,小孩上初一学校里的老师建议买的,一共买了7本,本来是想去新华书店里买的,但是不打折,所以上京东上来买了,超实惠,比书店里便宜一半都不止。晚上下的单,另—天上午就到了速度真快!下次有需要再來。?????
评分物流很快,当天收到货,包装严实,活动期间买的,很划算。钦佩杨先生,相信京东自营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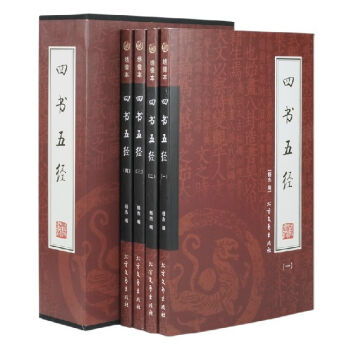
![巴巴爸爸新故事系列 智慧生活故事(套装全6册) [3-6岁]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11022/555aadd2N04b8796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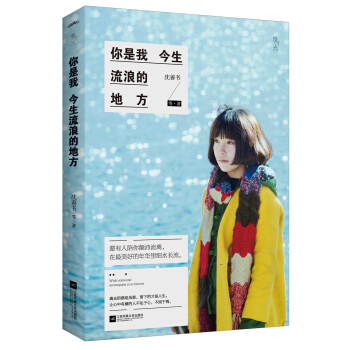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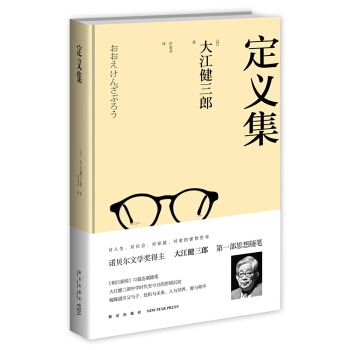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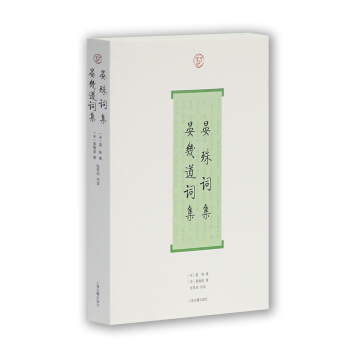
![莎士比亚书店 [Shakespeare&Compan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24918/rBEhWFM7bEEIAAAAAAaxRwgo_yMAALDlALGIlAABrFf14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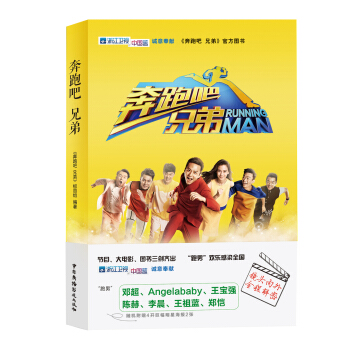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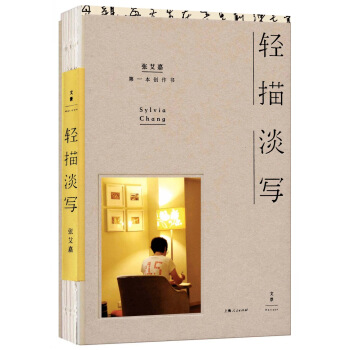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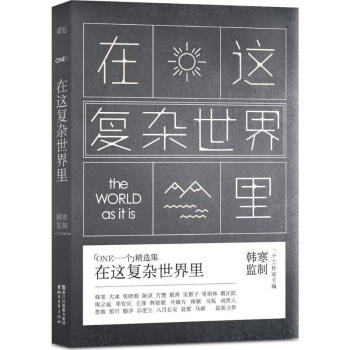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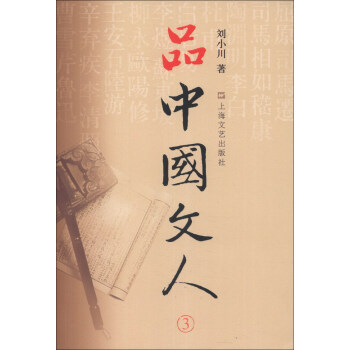
![汤素兰主编 第1辑 彩图注音版:笨狼的故事(套装全5册)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28902/5608bb6fNc36bc32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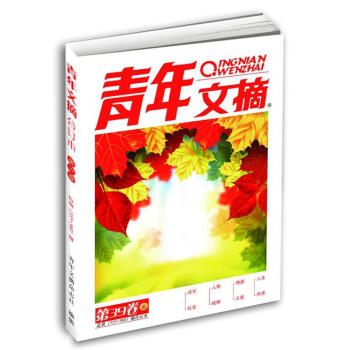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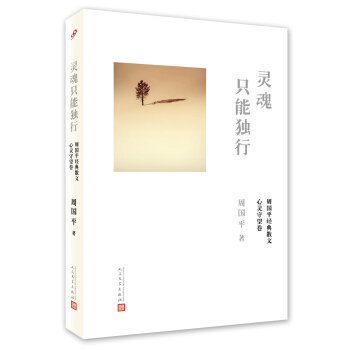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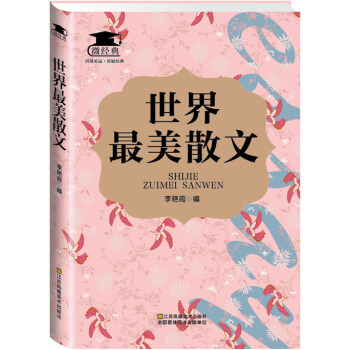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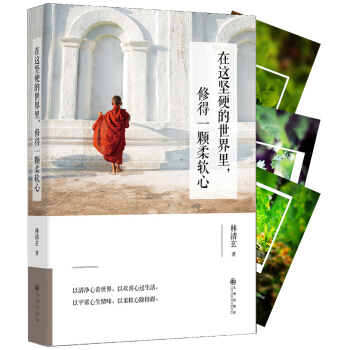
![汤素兰主编 第2辑 彩图注音版:笨狼的故事(套装全5册)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28903/5722b51dN1a814494.jpg)
![中外动物小说精品(升级版):雪国狼王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3933/54f43770Nd7be289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