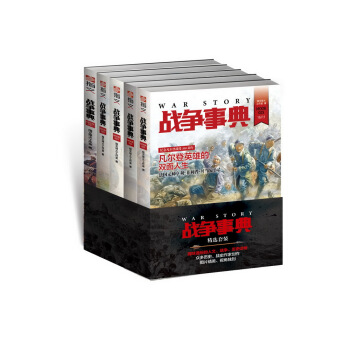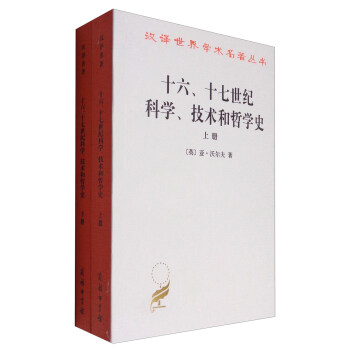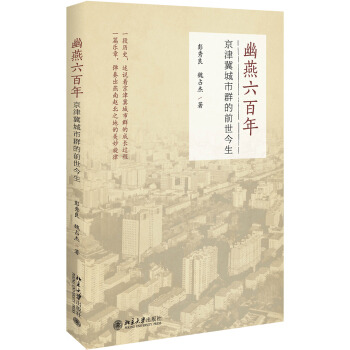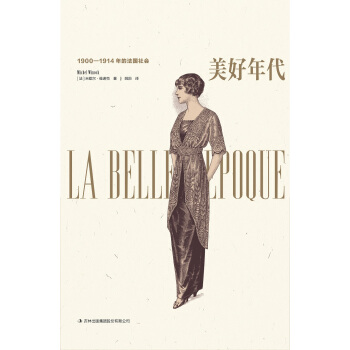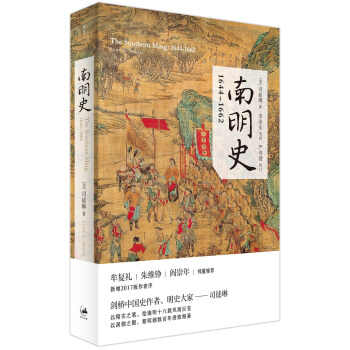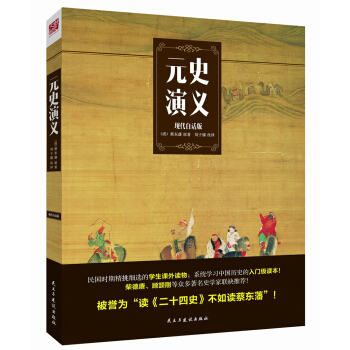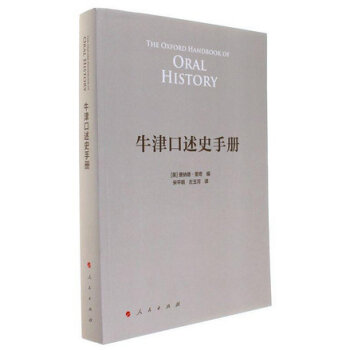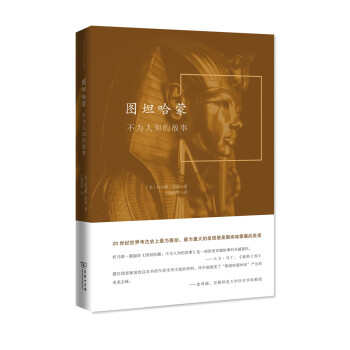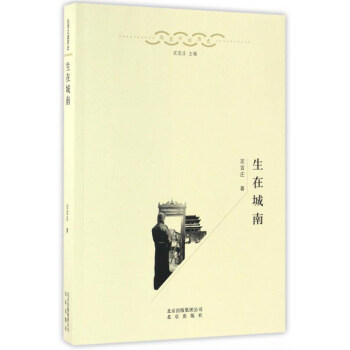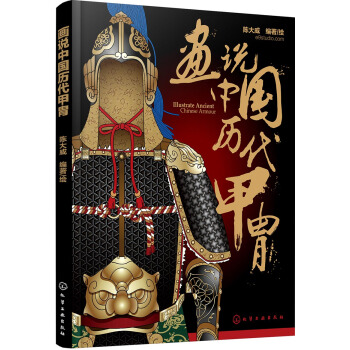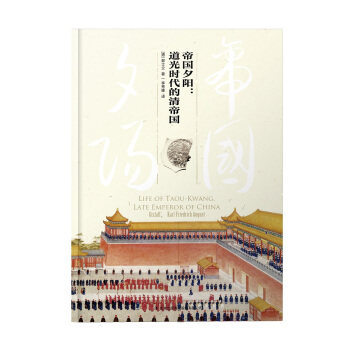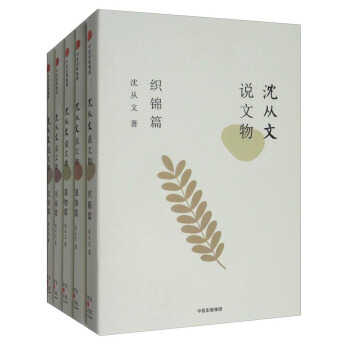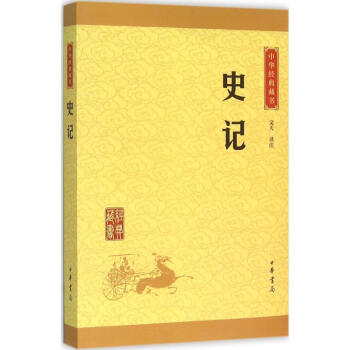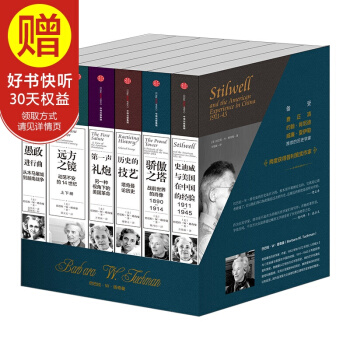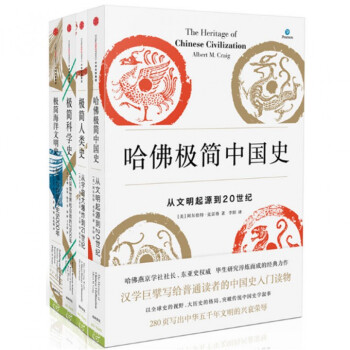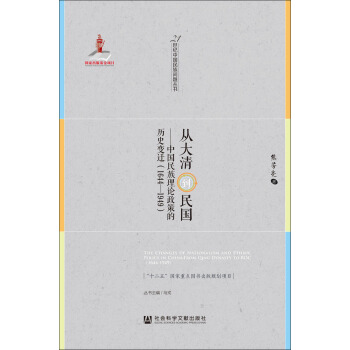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所关注的主题,并不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要往何处去”,而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是由何处来”,对“五族共和”“国民党一大宣言”“民族自决”“国族主义”“国族一宗族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等引领和影响民国时期民族政治基本走向的主要理论政策和重大历史事件,做了深入、系统的解读和阐述,在理论和史实上有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对更加客观、准确、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有启发和参考意义。作者简介
熊芳亮,男,1980年生,湖南省桑植县人。2004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社会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司权益保障处处长。曾参与筹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及筹备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IUAES l6th Congress,2009年,中国昆明)的相关工作。目录
前 言第一章“皇权一统”与“族类隔离”:清朝政府的族类政治及其历史遗产
一 “族类隔离”:清朝族类政治的基础和前提
二 “分其势而众建之”:清朝实行族类隔离政策的原因
三 清末新政:皇权体制的穷途末路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二章 “五族共和”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局限
一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改良”与“革命”的思想分歧与政治论争
二 “规复旧制”的奢望:“五族共和”的贡献、局限与影响三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三章 “民族自决”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
一 孙中山为什么反对“民族自决”
二 “民族自决权”:违背还是贯彻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 “民族自决权”:代表国际主义,还是谋求国家利益
四 “庞杂”而“革命”的思想体系: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灵魂与精髓
五 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四章 从戴季陶到蒋介石(上):伪篡“三民主义”的歪理邪说
一 国民党“右派”与“戴季陶主义”的崛起
二 “戴季陶主义”与蒋介石的政治学说
三 戴季陶与蒋介石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五章 从戴季陶到蒋介石(下):“国族—宗族论”的政治谎言
一 蒋介石集团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危害
二 蒋介石集团的政治困境与“国族—宗族论”的提出
三 “国族—宗族论”的理论路径与历史误会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六章 “国族主义”的起源与异变(上):“美国模式”的影响
一 “以美国为榜样”:孙中山“国族主义”学说的早期构建
二 “美国梦”的破灭与“国族主义”的异变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七章 “国族主义”的起源与异变(下):“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渊源
一 顾颉刚的“救国理想”及其“边疆/民族”研究
二 顾颉刚与孙中山
三 顾颉刚的政治宿命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八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上):共产国际与“民族自决”
一 被忽略的转变:“民族自决”的提出、调整与放弃
二 从“国际革命”到“国内联合”:决定“民族自决”政治命运的历史因素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九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下):
中苏同盟与新民主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
一 从“联邦”到“自治”:令人困惑的“转变”
二 “斯大林式”的“道歉”:苏共中央的秘密建议
三 “自治”与“联邦”,孰为中共策略
四 几点思考和结论
第十章 走向人民共和:逾越“国族主义”的缺陷与藩篱
一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分歧与论争
二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对比分析
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
附论1 现代“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基本迈向
——英国宪政革命、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统一的历史遗产
附论2 近代中国的“民族”概念及其衍化——皇权、天下、革命与“民族”建构
附论3 西方自由主义天平之上的“民族”与“国家”
参考文献
后 记
前言/序言
序一 溯源辨流求本探真宋人有诗云:“谁擘岩扉石窦开,中流玉水潄苍苔。有时卷雪从天下,端是源头蓄得来。”流水飞瀑,自有其源;理论政策,亦是如此。以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而言,她本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评估、评析理论政策的优劣、得失,显然需要在特定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之下,探究其生发的本源、思想的渊源、实践的效果和未来的走向,然后才能得出科学、客观、准确的结论和判断。
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一百余年间,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历了昏暗腐朽的晚清和民国时代。这个时代,不单单记录着全体中国人的屈辱和苦难,同时也记录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奋斗和牺牲。可以说,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都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孕育、生长出来的。最早接触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并介绍、传播这门学科进入中国的学者,大多也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家,从康有为“平满汉、去种界”的上书,到梁启超“合汉满蒙回藏”的主张,再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判断,都是对一代又一代学人忧国之心、救国之志的历史写照。而处于同一时代的政治家或革命家,同样高度关注民族问题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从兴中会的“驱除鞑虏”到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从北洋军阀的“规复旧制”到孙中山的“国族融合”,再到蒋介石集团的“国族—宗族论”,各派、各系政治力量曾经先后提出了多种试图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方案和政策措施,但最后都未能也不可能结出现实的果实。只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充分汲取了同时代学人的理论智慧和政治家的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理论政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道路。
熊芳亮同志的这本书,对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民族政策的转化、变迁的过程,做了一个较为体系性的梳理,是一本严肃而又严谨的著作。作为一名在机关工作的年轻人,能够在工作之余,耗数年光阴执着于一事,实属不易。更为难得的是,这本书稿在方法上“朝”“野”兼顾、“史”“理”兼修,在内容上“内”“外”兼具、“正”“反”兼容。虽然错漏、不当之处可能在所难免,但对于进一步加深读者对于民国时期民族政治和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了解而言,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探索和尝试。做学问,不急于近利、不希图捷径,更不管中窥豹、不坐井观天,只是踏踏实实读书,认认真真思考,占有和掌握大量甚至第一手的基础性资料,再进行深入、严谨的梳理和辨析,溯源辨流,正本求真,这很难能可贵。也只有这样才会有所见、有所得、有所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梦。广泛地凝聚力量、汇集智慧,更全面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深入地研究和发展创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当代民族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肩负的伟大使命。祈愿更多青年学者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领域,潜心用力,发挥所长,奉献光热,共筑中国梦。
吴仕民
2015年12月30日
序 二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开启了亚洲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一直位于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国从此陷入一个在帝国主义列强持续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极尽屈辱的恶性循环之中。几千年来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俯视“蛮夷”的中华文明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相遇后,在只懂“丛林法则”并且“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体系无情攻击下,这个“天下帝国”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故李鸿章惊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一再败绩,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这是与儒家传统、道家理念、佛教伦理等中国人熟悉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生存与发展之道。甲午战争再次让中国人通过切肤之痛真正地认清了自己是“弱者”。眼见中国人即刻面临“亡国灭种”的万古劫难,谭嗣同悲怆地感叹:“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人应当如何想、如何做才能做到“救亡图存”呢?
这是清朝后期、民国初年中国各族无数官员、学者、军人们都在苦苦思考、反复探索的问题。中国从东亚“天下帝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这个过程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过程。上至朝廷中的重臣督抚,下至民间的文人志士,凡是有爱国心和关心时事的人,无不参与到这一事关国家命运和亿万民众生存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特殊时代。郑观应建议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战”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康有为提出了一个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主张改良维新;梁启超力主变法,构建“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章太炎、邹容鼓吹“种族革命”,主张通过排满建立汉人新国家;孙中山则首先主张学习美国模式进行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对美国失望后又转向苏俄道路。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李大钊、陈独秀则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介绍进中国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各界人士提出的政治主张,大多是以上种种学术理念、政治光谱的延续。
应对大变局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大思路。反思历史足迹,对比国际经验,这是当年这些思想家们拓展视野和思路、寻求更新政治理念、充实分析工具的基本方法。总之,系统了解清末和民国时期围绕“中国应当选择何种道路”这个大议题所发生的理论争辩,包括“武器的批判”的种种实践,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认识并理解这段重要历史的切入点,也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根源的思想基础。中国的近代历史是那么厚重!几代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绞尽了多少脑汁、付出了多少血泪!我们真是不应淡忘了这段历史。
转眼之间,新中国已经成立60多年了。近些年来,边疆一些地区的民族问题有所凸显,推动了学术界对于“民族”定义、中国“民族构建”模式的大讨论,并引发对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这些讨论和反思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把一些对核心问题的讨论追溯到民国年代。例如对于“民族”定义的讨论,使人们重新审视1939年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所引发的争论;对孙中山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变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后是否仍然坚持“大汉族主义”,也出现一些评议;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最初提倡联邦制转变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对于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委,人们也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要回答这些理解近代中国“民族构建”过程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学者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对这段历史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细致的梳理,以史料文献为证据,揭示这些文献背后的那些当事者的真实思想和思维逻辑。
在改革开放前,这一文献研究工作是难以预想和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国民党政府的许多文件档案今天仍未公开或难以看到,但是近些年不知不觉间已经有大量历史文献正式出版,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1989—1992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1卷),1997—2013年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91—2000年出版;荣孟源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1985年出版。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文稿自80年代以来也陆续出版。这些看似枯燥的历史文献其实蕴藏了许多值得发掘的重要信息。同时,一些民国时期重要学者的论著也在近些年编撰出版,如《傅斯年全集》,2003年出版;《顾颉刚全集》,2010—2011年出版。这些史料与文献的出版为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和政策演变史提供了条件。
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需要面对的是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上面提到的,研究者是否能够看到各种重要和核心的档案史料文献,缺乏这个基本条件,一切无从谈起。二是在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些“禁区”,这些禁区让研究者无从下笔,动辄得咎,甚至令人对一些敏感题目望而却步、退避三舍。从我这些年的经验看,现在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许多历史文献和材料已经公开出版或能够查找到,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期望在这些方面主管部门的思想可以进一步解放,使民国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一些重要历史档案材料可以正式出版,这无疑将推动民国史的研究。另外,我感到有些传统的“敏感”话题也能够讨论了,比如我写的关于“民族”定义和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文章,有些杂志不能登,但在另外一些杂志还是能够刊出的。总体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包容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研究者自身了,就看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意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去查找资料、阅读文献和认真思考。
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负担很重。所在单位的各种指标性考核逼着他们不得不去申报一些“政治口号式”的研究课题,不得不去写一些“短平快”的文章,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质量却难以提高。但是,我也读到一些精彩的好文章,作者踏踏实实地讨论问题,引证了许多别人很少注意但十分重要的史料。我以前不认识熊芳亮,是从《中国民族报》上读到他写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等文章,感到他对文献和史料的发掘和独立思考超过我以前读过的相关文章。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读过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更不了解孙中山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之间的争论,读后觉得很受启发。熊芳亮是国家民委的年轻公务员,并不是大学的专业教师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这就更为难得。从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踏踏实实读书、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一代年轻学者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我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编辑《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已经先后出版了十几本。当熊芳亮提出希望我为他的《从大清到民国》这部书稿写一篇序时,我不仅欣然同意,而且建议他把这部书稿放到这个丛书里。我认为这是一本在历史文献方面认真下了功夫的研究成果。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持续动荡,这部书稿特别注意以形势变化为历史背景来分析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概念、民族理论、民族制度设想的演变历程,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当然,这部书稿中应用的一些概念和从文字解读中引出的一些因果关系是否适当,对一些历史人物“民族主义”思想的概括是否准确,这些都是可以在今后进行讨论的。我想任何研究成果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是我们需要对年轻人认真做学问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民国时期的国家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决定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和政治冲突中,各政党和重要学者的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纲领如何演变?这些历史的梳理更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关注的研究专题。我相信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人在阅读这本书时一定会感到有所收获。
上面写的这些话,就作为这本书稿的序言。
马 戎
2015年9月11日
于茉莉园
前 言
一
公元1644—1949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不过是弹指一瞬,却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波谲云诡的恢宏篇章。在这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所缔造的伟业、所经历的变局、所遭受的屈辱、所忍受的苦难、所激发的奋斗,无不堪称“三千年之未有”。
毫无疑问,这“三千年之未有”的历史,不仅曾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命运的汇聚与总和,而且现在也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二
历史就是曾经的现实,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大千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地方、每一刻时间,无不是历史的延续、未来的过往、偶然的相遇。
数学家说,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就会引发太平洋上的巨大风暴;历史学家说,古代埃及一个女人的鼻尖,就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和面貌。
先哲曾言,“六经皆史”,故“学者最紧要者,乃通知史事”。笔者虽难妄称“学者”,却凭借这一点朴素的认知,在数年前发下宏愿,幻想着一定要穷己之力,弄明白公元1644—1949年这三百余年间,中国的民族政策经历了哪些变迁,它又对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三
坦率说,关于新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与解读成果,不可谓不丰;投身其中、造诣非凡的学人,亦不可谓不众。作为后学之辈,恬不知耻地许下如此宏誓大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近年来“反思”“质疑”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言论及相关争论的影响。
毋庸讳言,笔者并没有民族学的专业背景,也没有在民族院校求学的教育经历,因工作需要才比较系统地学习、认知、践行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政策,学界的“反思”“质疑”及其论辩,确实曾给笔者在思想和认识上带来极大的困扰与困惑。
当然,引发笔者困惑与困扰的并不是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正确性”“正当性”的争议,抑或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应该“政治化”还是“文化化”的道路选择与方向分歧——作为一名公务员,首先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认知——而是出于对“反思”“质疑”从何而来、因何而起的学术追问。在笔者看来,“反思”“质疑”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客观、公正、深入地探究引发这种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才不会人云亦云、莫衷一是。
四
“历史”,也许正是探究和窥视这一社会现象的最佳途径之一。
从参加工作时开始接触、学习民族学的著作和文章起,笔者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中国民族学史的理论构建有一点“异样”。这个“异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史”在某种程度上的模糊与缺席。在某些关乎史实的表述中,有的时候“欲言又止”,有的时候“语焉不详”,有的时候“旁顾左右而言他”……同时,一些明显悖于历史常理、违反历史常识、缺乏历史根据的观点与看法,却一直在“以讹传讹”,而且“似是而非”。
有观点认为,外蒙古“独立”是孙中山“驱除鞑虏”的结果。但实际情况是,外蒙古有其自身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其“独立”是清政府分崩离析的大势使然,八世哲布尊丹巴可能连孙中山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有观点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但实际情况是,孙中山的“旧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赋予了“民族”以“国民”“公民”的意义。他的“新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学说——中也饱含着极具政治创造力和理论包容性的“人民”内涵,更遑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团结”“共同奋斗”的思想和主张一直延续至今。
有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国族—宗族论”继承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但实际情况是,蒋介石集团打着继承“总理”遗志的旗号肆无忌惮地歪曲、伪篡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
有观点认为,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与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提出存在理论关联。但实际情况是,顾颉刚对蒋介石集团的边疆/民族政策一直持批评、批判的态度,两者可谓泾渭分明、水火不容。
有观点认为,国民党的主张是“民族团结”“国族融合”。但实际情况是,蒋介石的“民族分治”思想深入骨髓,在“民族自决”的道路上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彻底。
有观点认为,共产国际的“民族自决”政策符合“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但实际情况是,“民族自决”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大国沙文主义”的支配和影响,不过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矫诏”,其目的就是要让国、共两党放弃对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有观点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自始至终都坚持把“民族自决”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但实际情况是,“民族自决”也曾经历提出、调整直至最终放弃的历史过程,斯大林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直接建议中共“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否则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形成,还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与阻力。
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但实际情况是,毛泽东思想才是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灵魂与核心,它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升华,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新民主主义化”的理论升华。
……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五
为了大致梳理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理论政策演化、嬗变历史的一个基本轮廓,笔者自2008年起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著,同时收集、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先后撰写了十余篇论文。应该承认,笔者最初并没有预想到这些论文最终会形成现在的数量和规模,更没有预想到原本以为只需要用一两篇文章、一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任务,竟然一直拖延到现在。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x,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历史何尝不也是这样?当你接触的资料越丰富、掌握的信息越全面,你就越能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还原和回归历史场景,收获的认知往往出乎意料,得到的结论也会让你充满惊喜和惊奇。
也许这就是总有那么多人迷恋历史的原因吧!
六
本书共分为十章,另有附论三篇。
第一章的主题是清朝政府的“族类政治”。按照最初预想的写作计划,笔者原本是要从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开始的,但在阅读清末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文献时,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如果不对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有大致的了解和基本的判断的话,就不可能正确、科学、客观地认知和评判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的功过得失,更难以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治。另外,学界对于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认识和评价的确有失公允。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清朝政府视为“民族压迫的牢狱”的观点当然不对,但片面放大其族类政治的历史功绩、视其为“古代中国族类政治的集大成者”显然也与实情不符。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清朝政府无处不在的隔离、封禁政策,隔绝了各族群众在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政治上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导致各族相异、相疑、相轻、相恨、相离,难以凝聚、汇聚、团结成统一的整体和力量进而抵御外侮、振兴国家,难以共同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换言之,清朝政府给近现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打下了一个“结”,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五族共和”,还是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族主义”,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都是在试图解开这个“结”。就此而言,我们显然需要从“隔离”“封禁”的角度,重新解读、批判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历史遗产。
当然,仅以一章的篇幅解读清朝政府施行二百多年的民族政策,难免会显得单薄和平面。清朝政府的族类政治远比“隔离”“封禁”这样的标签复杂和饱满。例如,在姚念慈所著之《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以及国外史学家史景迁所著之《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中,关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清朝皇帝政治理念和政治心态的独到分析,对于深入开展清朝政府族类政治的研究就极具启发意义。众所周知,在诸多武侠小说、戏剧、电影中,包括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在内,乾隆皇帝是一个有着汉人血统的皇帝,是天地会等反叛组织“光复汉室”的唯一希望,而史实中的乾隆皇帝却查禁了雍正皇帝旨在重构“华夷之辨”的《大义觉迷录》。也许,清朝政府变革其“族类政治”的唯一机会,正是在乾隆皇帝手里断送的;等到“清末新政”的时候,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了。
第二章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五族共和”。关于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的研究文章比较多,笔者所关注的不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而是重在探寻和分析二者分歧存在的理论基础,因之剖析“五族共和”走向失败的深层原因。通过第二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合族而治”还是“分族而治”问题上的分歧,背后还包含着极具思想史意义的理论冲突。无论是革命派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观点,还是改良派所秉持的“国家主义”立场,其实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政情,都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与缺点,在此基础之上仓促而成的“五族共和”最终失败,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对于国民党一大宣言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学界多持肯定和积极的评价,但其中暗藏的玄机和危害却鲜有人论及。笔者在第三章还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以及鲍罗廷依据该决议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背景,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和国民党一大宣言所宣示的“民族自决”,将中国各民族“各自斗争、相互斗争”的民族主义路线强加给国、共两党,不仅违背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论述,而且违背孙中山先生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的“国族主义”路线。
第四、五章主要分析和研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民族主义思想。长期以来,民族学界一直有一个“以讹传讹”的印象,即蒋介石集团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似乎孙中山先生就是“国族—宗族论”的始作俑者。通过文献分析,笔者认为,不仅这种“继承遗志”的印象并不准确,而且“国族—宗族论”也并非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的真实面貌。在发动反革命政变、窃取革命政权之后,蒋介石集团不仅没有继承孙中山先生“国族主义”的“遗训”,反而继续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史称“戴季陶主义”)为名背叛、歪曲、伪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其“国族主义”学说。在戴季陶、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划族而治”“民族分治”才是其深入骨髓的政治理念。虽然蒋介石在抗战压力之下炮制了所谓的“国族—宗族论”,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分裂、分治主义的本来面目。
第六章主要分析和研究所谓“美国模式”对孙中山“国族主义”构建和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影响。近年来,屡有学者提出借鉴“美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模式”来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争议。其实借鉴“美国模式”,并算不上“创见”。早在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就已经在借鉴“美国模式”构建其“国族主义”学说了。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主要有二:一是孙中山先生所理解的“美国模式”与现在学者所理解的“美国模式”大相径庭——孙中山认为“美国模式”就是一种基于“民意”“民主”的“政治化”模式,而现在的学者基本上认为“美国模式”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化化”模式;二是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政府的步步紧逼之下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借鉴“美国模式”构建其“国族主义”的路径和做法,转而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进而为戴季陶及蒋介石集团以儒家圣哲和道统学说伪篡、歪曲其“三民主义”学说开启了方便之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孙中山先生及其“国族主义”的境遇,很值得后人警醒和深思。
第七章以顾颉刚“边疆/民族”思想为主题。对于顾颉刚,学界大多关注其史学成就和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而忽略了对顾颉刚本人“边疆/民族”思想演化进程及其思想渊源的关注和剖析。根据笔者的分析,顾颉刚的“救国理想”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影响,其“边疆/民族”思想更是如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从本质上看就是对孙中山先生“国族主义”的重申和阐述。换言之,孙中山先生才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真正首倡者。顾颉刚的贡献在于,他戳破了蒋介石集团依附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上的“道统说”“圣哲说”的政治谎言,让“国族主义”再次回归到依托“民意”与“民主”的“政治化”的路径。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的观点,直至今日仍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八、九章主要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影响。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的“显学”。借助苏联解体后逐步解密的档案文献,近年来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档案解密的“春风”,似乎并没有刮到民族学领域。通过这两章的分析,可以发现“民族自决”并非共产国际一以贯之的政策导向,经历了制定、调整然后实际上放弃的阶段;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民族自决”政策,显然也很难与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画上等号。
关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制定过程,现在学界大致上采用下述说法,即由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建议,毛泽东和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放弃了“联邦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俄罗斯学者根据最新的解密档案,指称斯大林曾在1949年2月初通过访问西柏坡的米高扬,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议“不要让少数民族独立”,且毛泽东的反应让米高扬感觉到这样的建议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因为毛泽东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让少数民族独立”。2007年,有党史专家在公开出版物上正式披露,在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等文献中,原本有“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内容,只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被删除了。2008年,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联合出版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公开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历次草稿及其起草过程的相关文献。从中可以发现,直至1949年8月,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仍包含着“组成中华各民族联邦”的内容。很显然,单纯从“李维汉建议—中央采纳建议—放弃联邦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角度,很难解释上述档案文献的价值和意义。第九章的研究主题,就是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考察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确立过程。通过该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表明,关于“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共档案文献中确实存在不同的表述和摇摆反复,但对这种不同表述和摇摆反复需要在中共、苏共两党关系变化的大背景之下,从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的高度进行理解、分析和把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持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政治道路的根本立场和基本原则并未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动摇和改变。而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并没有导致中国共产党“照搬”和“照抄”所谓“苏联模式”,反而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政治道路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政治条件。
接下来的问题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什么会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放弃“联邦制”的主张呢?其理论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对比分析孙中山“三民主义”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十章旨在阐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政策,不仅需要且妥善处理了与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之间的理论关系,而且还需要且妥善处理了与孙中山“三民主义”尤其是“国族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是对马列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继承、发展和升华。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将“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理论政策”构建在“人民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基础之上,弥补了“国族主义”学说的缺陷,是一次重大的理论飞跃。在强化“国族构建”和“民族国家”思想有所抬头的今天,重新阅读“新民主主义”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附论共计三篇,是笔者分别于2008年和2009年完成的论文,对近代西方国家、近代中国、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民族”概念的形成、衍化和演变历程做了简要梳理和分析,虽然现在看起来文章略显稚嫩,但实际上奠定了本书对于“民族”概念的一些认识基础,故附录在书后,供读者参考。
七
历史总是比你知道的更复杂,比你想象的更丰满,比你揣度的更诡秘。
笔者实不敢妄言这本小书的文字已经给读者提供了唯一的、正确的、清晰的答案,但它确是笔者数年来的心血所寄,是笔者在困惑中探索、思考的成果。如果能够对读者有一点启发、有一点助益,笔者就以为善莫大焉,能够心满意足了。
诗曰:“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和书名就透着一股厚重的历史感,让人忍不住想翻开一探究竟。我最近读完这本书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作者对那个时代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它并非简单地罗列事件,而是深入挖掘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思潮的碰撞与交融。尤其是关于民族主义如何从一种边缘的知识分子思潮,逐渐演变成影响国家命运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写得尤为精彩。作者没有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视角去解读历史,而是呈现了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转型期。比如,书中对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差异的分析,非常细腻。这让我对当时社会结构的瓦解与重构有了更立体和鲜活的认识。那种在传统与现代、内部与外部多重压力下的挣扎,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读后深思。
评分这本书的学术功底是毋庸置疑的,大量引用的原始资料和清晰的逻辑推演,让整个论述体系显得非常扎实。但最让我惊喜的是,它并没有陷入纯粹的学术术语堆砌,而是用非常流畅的笔触将复杂的历史进程讲述了出来。尤其是关于不同族群关系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微妙变化,作者提供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以往的很多历史著作往往将这段时期视为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而这本书则成功地揭示了其中潜藏的断裂、反复和潜流。读完后,我对如何理解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有了一个更具批判性和深度的理解框架。这种知识的增量感,是阅读一本优秀历史著作最令人满足的体验。
评分坦白说,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是一次对自身历史认知的不断校准和修正。作者在梳理1644到1949年间的历史脉络时,所展现出的对“变”与“不变”的深刻洞察力,令人印象深刻。它清晰地展示了,看似一脉相承的“民族”概念,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内涵变化。我尤其关注到书中对清代“天下”观念向现代“国家”观念过渡的阐释,这部分内容极富启发性。它不仅关乎政治结构的变化,更触及到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层动摇。读这本书,你仿佛能听到那个旧王朝的挽歌,以及新思潮涌动时的巨大声响,这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感非常强烈。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既有宏观的历史脉络梳理,又不乏对具体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微观剖析,读起来张弛有度。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敏感议题时的审慎和严谨,没有被意识形态的刻板框架所束缚。在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被一些历史细节所触动,这些细节往往是理解大时代走向的关键。例如,书中对不同派系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政策转向的梳理,展现了决策层在内忧外患下的艰难抉择。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政策演变的历史书,更像是一幅描绘转型期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力量群像的画卷。它促使读者去思考,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何为“民族”的内涵,以及这种内涵是如何被不同力量所塑造和利用的。
评分这本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它对“政策”背后逻辑的穿透力。它不仅仅停留在描述“发生了什么”,而是深入剖析了“为什么会那样发生”。在处理从帝制瓦解到共和初建这一关键转折期时,作者对不同政治团体在“民族认同”上的诉求和博弈,进行了细致的还原。你会发现,许多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民族政策,在当时都是充满了摸索、妥协乃至激烈冲突的结果。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坦诚呈现,避免了后见之明式的简单评判。它提供了一种更具同理心的视角去理解先驱者们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所做出的抉择,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深度研究。
评分现在的书,价格优点离谱了
评分纸张也就那样
评分物流快 快递小哥赞 下次还会买的。
评分纸张也就那样
评分商品不错,物流够快,货真价实,值得拥有!
评分现在的书,价格优点离谱了
评分物流快 快递小哥赞 下次还会买的。
评分物流快 快递小哥赞 下次还会买的。
评分又好又快 赞?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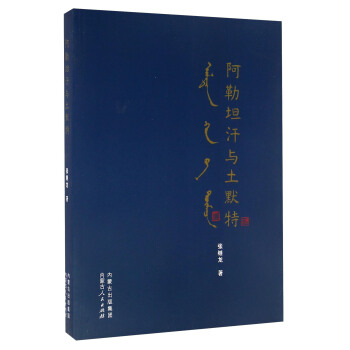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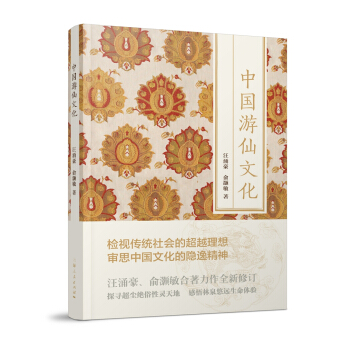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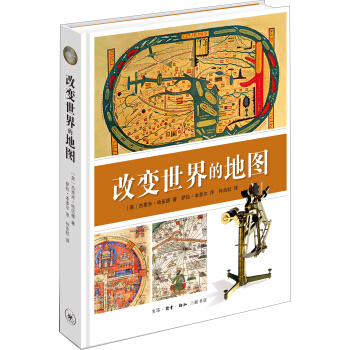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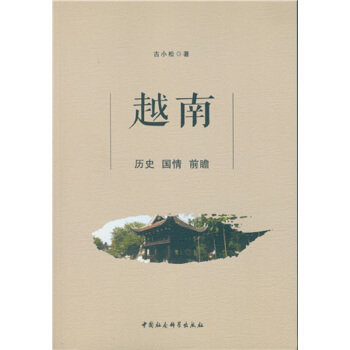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阿富汗史 [A Brief History of Afghanista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26340/57c02b3cNc776661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