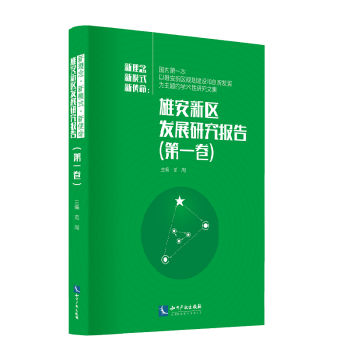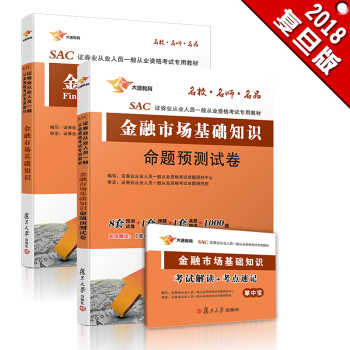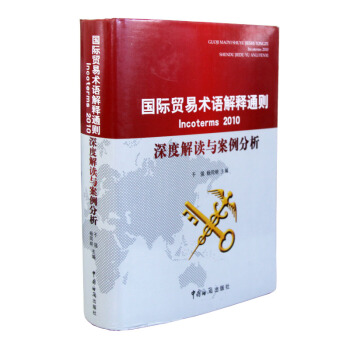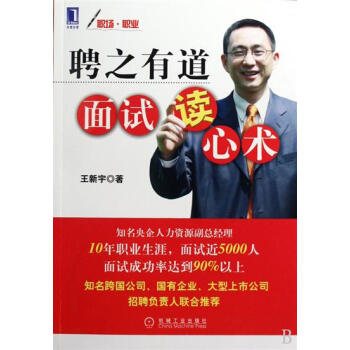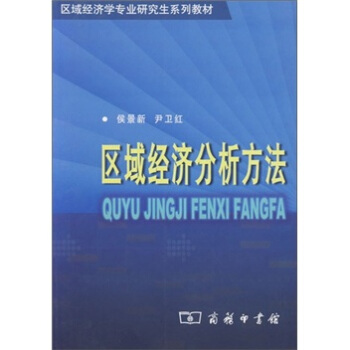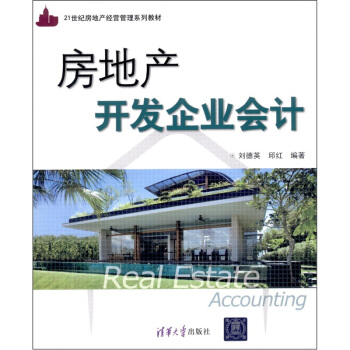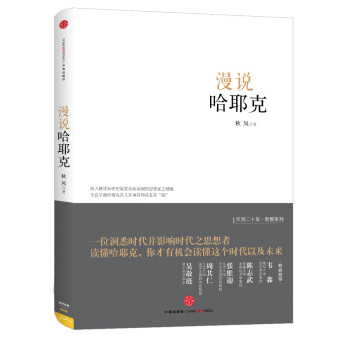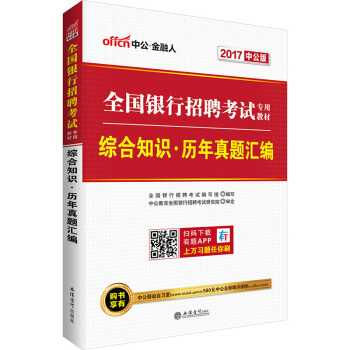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经济学的危机。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欧洲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都在挑战着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信条。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已经出了问题。基于对主流经济学基础假设的质疑,经济学家陶永谊重新梳理和审视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假设和基本原理,提出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建立在互利交换基础上的,并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展开了条分缕析的解读。
作者简介
陶永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硕士。之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攻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先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参加中国外贸经济体制改革、中国2000年国际经济环境等重大课题研究,并获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一等奖。出版专著《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互利:经济的逻辑》《互利:政治的智慧》,影响力至今不衰。后期任深圳国际经营战略研究中心证券咨询部主任、深圳新兰德证券投资培训中心主任、深圳巨澜投资分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全天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光大证券证券投资分析师。当过兵,下过乡,经过商,也做过学者。现为独立投资人。
精彩书评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过程中,对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前提的批评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在最近30年中,我国的经济学界过于急切地要从西方全盘引进其主流的经济理论,以致忽视了主流经济理论在解释许多经济现象上的无能为力,忽略了引进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根本性批评,更缺乏本国经济学者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恰当的根本性批评。对主流经济理论的迷信和根本性批评的缺乏,导致了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缺乏思想准备。在这样的环境下,由纯粹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者写出的这样一本书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它象征着中国经济学界分析和思考能力的提高,象征着中国经济学界正在走向成熟。——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学流派,只有西方经济学的跟从者,但陶永谊先生是例外。陶永谊先生力图从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原点出发,构建现实经济运行规律的假说与体系,具有开拓与创造性的经济学思想。希望这一创新的思想与假说,不会埋没在世俗功利的尘埃中,而能在今天和未来更久远的岁月里像宝石般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但斌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这本书分为十五章,每一章都针对流行经济学教科书中某个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并提供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全书的主要内容力图告诉读者,流行经济学教科书的许多观点和推理是不对的,现代经济学借以自豪的分析方法有着重大缺陷。
——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经济学的应用更不能基于脱离现实的种种假设。教条式地理解和应用西方经济学ABC,在过去很多年已经影响了中国经济决策的质量。陶永谊先生的这本著作对传统经济学的各种假设条件提出全面质疑,相信他的研究能够推动经济学在中国更好地应用。
——滕泰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著有《财富的觉醒》
目录
第1章 选错地基的经济学大厦/ 0011.1 个体本位的方法论谬误 / 003
1.2 交换的准则 / 006
1.3 群体的共生现象 / 015
1.4 互利的底线 / 019
1.5 交换比率的形成 / 022
1.6 交换模型中的制胜策略 / 027
第2章 我们在和谁交换/ 033
2.1 完全竞争的定价模型 / 035
2.2 垄断模式的价格曲线 / 039
2.3 寡头垄断的博弈模式 / 048
2.4 商人的加入 / 052
2.5 用货币实现的交换 / 055
2.6 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 / 058
第3章 需求与效用的误区/ 063
3.1 效用的冲突 / 064
3.2 效用的换算 / 070
3.3 需求的伪命题 / 076
3.4 需求的层级 / 080
第4章 供给的缺陷/ 087
4.1 我们忽略了什么? / 088
4.2 要素匹配的难题 / 092
4.3 要素的跨部门转移 / 096
4.4 要素的特征 / 100
第5章 价格如何决定/ 109
5.1 价格决定机制 / 110
5.2 价格的波动特性 / 114
5.3 价格函数 / 117
5.4 二元交换模型中的价格决定 / 120
第6章 不确定性与测不准效应/ 125
6.1 完全预期的尴尬 / 126
6.2 不确定性与凯恩斯革命 / 130
6.3 “两个剑桥之争”的方法论分歧 / 134
6.4 测不准效应 / 139
6.5 不确定背景下的决策模型 / 144
第7章 最难以实现的经济理性/ 147
7.1 被美化的偏好 / 148
7.2 非理性的心理特征 / 152
7.3 人类选择的行为模式 / 160
第8章 我们应该追求哪种最大化/ 165
8.1 人类并非天生勤奋 / 167
8.2 上下求索而不可得的路径 / 171
8.3 活下来不是标准 / 175
8.4 最大化原则的悖论 / 179
8.5 螳螂背后的危险 / 183
第9章 均衡还是转折/ 187
9.1 一般均衡实现的条件 / 188
9.2 虚幻的均衡点决策:产品出清 / 193
9.3 市场崩溃的前奏 / 197
9.4 充分就业的幻想 / 203
9.5 南辕北辙的帕累托最优 / 206
第10章 博弈论对经济学的挑战/ 213
10.1 假定对方不会还手? / 215
10.2 假如对方选择背叛 / 217
10.3 两种不同的均衡 / 222
10.4 合作的效率 / 225
第11章 增长的陷阱/ 233
11.1 总量概念之殇 / 234
11.2 增长模型的缺憾 / 238
11.3 储蓄=投资? / 241
11.4 并不神奇的乘数效应 / 244
11.5 创新对传统理论的挑战 / 248
第12章 危机是否可以避免/ 253
12.1 有关经济周期的争议 / 255
12.2 消除危机的前提 / 261
12.3 技术更新的周期 / 269
12.4 反周期措施 / 273
第13章 看得见的手可以做什么/ 277
13.1 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能互补 / 278
13.2 主权债务危机与“凯恩斯死结” / 284
13.3 政府职能的国别差异 / 288
13.4 公共管理职能的历史差异 / 295
第14章 印钞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 299
14.1 货币催生的幻觉 / 300
14.2 货币是否是中性的? / 307
14.3 都是货币惹的祸? / 312
14.4 以纸代金的悲剧 / 316
精彩书摘
笔者自学习西方经济学以来,始终有一个困惑难以释怀: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学习如何发财致富吗?经济学给出的回答有点令人气馁:经济人是自私且理性的,他们天生就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无须别人的教诲,个人只要按照自利本能的指引,就知道应该如何从事经营活动,企图通过学习经济学去赚钱,似乎是在走不必要的弯路。那么,经济学是否可以用来经世济民、富国兴邦呢?好像也不行。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主流经济学都义正词严地告诉我们,市场上交易当事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自动导致市场供求趋于均衡,并使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实现。政府干预市场运行只能扭曲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既然如此,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何在?难道仅仅是用来证明经济学是无用的?如果经济学只能拿来自娱自乐,学习经济学与效用最大化原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笔者认为,一个好的经济理论,至少应该具备三项基本特征:一、良好的解释功能;二、有效的解决方法;三、平和的解脱路径。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主流经济学在这三个方面均乏善可陈。
以200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为例。主流经济学家对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是将其归咎于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缺失,抑或是美联储“错误的”低利率政策。笔者手头有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次贷危机真相的书,书名就是《贪婪、欺诈和无知》。这倒有点奇怪了,哪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不是在讲,自利原则和最大化原则是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哪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引用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那段名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以自动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政府监管怎么又成了市场稳定的必要条件?如果贪婪真的是次贷危机的原因,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华尔街不是今天才变得贪婪的。至于欺诈和无知,则与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和完全信息的假定相矛盾,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被假定为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当然也包括对政府的错误政策做出理性的预期,他们是不可能被欺骗的。如果对次贷危机这样重大的经济事件都要借助经济学以外的概念去解释,我们有理由怀疑,经济理论本身是否存在着根本的缺陷。
承认政府监管的缺失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就等于承认,那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仅靠它的调节,市场并不会自动走向均衡,弄不好还会出大乱子。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重新拾起曾经备受质疑的财政和金融手段来干预经济,而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却不幸地发现,政府本身早已债台高筑,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经济体还没有从衰退的陷阱中脱身,政府却出现了债务违约的危险。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这次沦落到自身难保,也要被别人来救的地步。这又如何是好呢?
至于认定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为次贷危机的原因,就更加难以自圆其说了。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说法,交易当事人可以对市场的所有信息做理性预期,其中也包括对政府政策的效用预期。这种预期不仅会使政府政策失效,还会对政策引起的市场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认定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为危机爆发的原因,岂不是对市场调节能力的自我否定?况且,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救市方式,不过是一连串的QE。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政策来拯救危机。如果低利率是引起次贷危机的原因,零利率和负利率又会引起什么危机呢?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病因的诊断是吸食鸦片过多,结果开出的药方却是让病人吸食更多的鸦片。还有比这更为滑稽的解释吗?
经济的危机其实反映的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出了问题。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而我们现有的主流意识,对此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的时候,有必要对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理论信条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审视。
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个体本位的方法论传统演变的。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以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以个人追求财富的动机作为经济行为的动机,并以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原则。根据几个由内省方式得出的“自明”假定,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整个市场的运行模式,如供求法则和市场均衡,等等。即便是“凯恩斯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这一传统。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逻辑演绎的前提假设是否可以成立。以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为例,笔者以为,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交换,中间至少要涉及两个行为主体、两种不同的商品。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最原始的单元应该是一个二元结构的交换单元,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一个厂商和一种商品的一元结构。从交换的二元结构,我们还能推导出商品经济的基础是互利,而不是自利。没有利他成分的自利行为只能导致交换无法完成,或对交换形成破坏。经济学家鼓吹的自利原则其实是对商品经济的一种误导。被称为经济学中心原则的最大化原则,在广泛推演的过程中,会导致无法解释的悖论。而理性原则和完全预期原则由于缺乏现实性的基础,不仅与心理学的测试不相符合,而且也不能产生与现实相一致的预测。通过对经济学所有基本假设的重新审核,本书得出了一个结论:经济学很可能在根基上就出现了偏差。
正是由于前提假设上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主流经济学一方面承认各种投资类别在收益上的差异,如利息、利润和地租,同时又假定未来收益可以预期。我们知道,不同投资类别的不同收益率,正是基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如果未来收益可以预期,理性经济人的正确决策肯定是进行收益最高的直接投资,而那些低收益的间接投资,如借贷及土地出租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同的投资收益与未来收益可预期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假定,它们不可能同时成立。类似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会重复出现,笔者在正文中对此逐一进行了分析。
对于曾经一度占据过统治地位,并且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凯恩斯经济学,笔者也同样持保留态度。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是由于市场自发调节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不足又起因于三大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但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普遍出现负储蓄率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产能过剩危机。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政府在救助经济的同时,会出现笔者称之为“凯恩斯死结”的结果——主权债务危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各国政府还在执行的经济措施完全以这些有重大缺陷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当所有的招数都已经用尽,比如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政策,政府负担难以为继的巨额债务,经济依然无法摆脱困局,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各种极端主义在各国抬头,可以视为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讲,都到了对经济学进行全面梳理并重新构建的时刻了。
本书共分十五个章节,前十章涉及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后五章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内容,每一章都针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进行论辩,并提出替代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可以应用的科学,无论对于企业、个人还是政府,都是如此。人类进入21世纪,正面临着一个全新发展时期的前夜,中国经济学家如果以书本到书本的方式将主流经济学理论当作指导中国经济的圣经,很有可能使我们错失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百年之后,我们将无颜面对历史和后人。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个引领性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新经济理论的诞生,一个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前沿的大国,不可能是他人思想的模仿者和追随者,没有思想的领先,任何一个国家充其量都只能是二三流角色。时代呼唤经济学领域中国学派的诞生。创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的经济理论,是中国知识精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本书仅仅是为此所做的粗浅尝试,若能为这一旷世盛举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也算是不辱使命,问心无愧了。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互利经济学》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不如说是一本关于如何实现个体与集体共赢的“生活哲学”。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者在书中并没有使用过于学术化的语言,而是以一种更加生活化、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引导读者去思考经济活动与我们自身的关系。他反复强调,经济学并非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图表,而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交换、合作,来实现自身价值,并最终促进社会整体福祉的学问。书中很多关于“非理性行为”的解读,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所谓的“不经济”的选择,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心理和行为动因。作者通过对这些行为的洞察,提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互利”策略,能够帮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读这本书,就像是在进行一场心灵的洗礼,它让我看到了经济学在改善人类生活、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巨大潜力。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对生活充满好奇,渴望追求更好自己和更美好社会的人。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逻辑的严谨与论证的充分。作者在《互利经济学》中,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互利”概念的浅层描述,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并通过大量的数据和案例进行支撑。比如,在探讨市场失灵问题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而是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角度,阐述了市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并提出了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互利”机制来弥补这些不足。我特别喜欢作者对“公共物品”的分析,它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纯粹的市场机制下,公共物品往往会被供给不足,以及如何通过集体协作和互惠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书中关于“创新”与“互利”之间关系的论述也极具启发性。作者认为,创新并非是少数天才的灵光一闪,而是在一个鼓励分享、回报公平的“互利”生态系统中,更容易迸发出来的集体智慧。读完这本书,我仿佛经历了一场头脑风暴,对经济学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更加坚信,一个真正繁荣的经济体,必然是建立在广泛的互利共赢基础之上的。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本书的期待值并不高,毕竟市面上的经济学书籍大多晦涩难懂,充斥着各种专业术语,读起来让人望而生畏。然而,《互利经济学》却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它并没有像传统的经济学教材那样,上来就抛出各种复杂的模型和公式,而是从一个更加宏观、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出发,探讨经济活动的核心驱动力——“互利”。作者的文笔非常细腻,他对每一个概念的阐释都充满了智慧和洞察力,他善于从细微之处着眼,发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经济规律。例如,书中对“信任”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论述,就让我印象深刻。它不仅仅是社会学的范畴,更是经济运行的基石。没有信任,契约精神无从谈起,交易成本将呈指数级增长。我特别欣赏作者提出的“共享价值”的理念,它强调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为社会创造积极的价值。这不仅是对企业道德的呼唤,更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思考。这本书无疑是一股清流,它让我重新审视了经济学的意义,也让我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
评分这本书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直以来,我对经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总觉得很多理论都过于抽象,离我们的生活太远。直到我翻开《互利经济学》,才真正体会到经济学原来可以如此生动、如此贴近人心。作者用一种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那些复杂的经济概念娓娓道来,仿佛在与一位老朋友聊天,轻松而愉快。书中充满了各种各样贴近生活的例子,从家庭的日常开销到社区的志愿服务,再到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每一个案例都深刻地揭示了“互利”这一核心理念如何贯穿其中。我尤其喜欢作者对“合作”与“竞争”之间关系的剖析,它颠覆了我以往对竞争的单一理解,让我看到了在合作中竞争的更高境界,以及如何通过互惠互利来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本书不仅让我对经济学有了全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如何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如何去构建更加和谐、高效的人际关系和商业模式。读完之后,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豁然开朗,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更美好世界的大门。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独特,它颠覆了我以往对经济学书籍的刻板印象。作者并没有选择一个循序渐进的讲述方式,而是直接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互利”思维的宏大叙事中。从开篇的几个引人入胜的案例,到中间对各种经济现象的深入剖析,再到结尾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整个过程都充满了智性的挑战和思想的启发。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探讨“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所提出的“信号博弈”理论,它非常形象地解释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个体如何通过各种“信号”来传递自己的意图,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加透明、更加互利的交易环境。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提供了理论上的框架,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一套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工具。它让我看到了,在复杂的经济世界中,通过理解和运用“互利”的原则,我们能够规避风险,抓住机遇,并最终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共同成长。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的著作。
评分奔着作者买的,也想了解一下经济学
评分非常快,一直信赖京东。
评分比旧版好,花点时间看~
评分正版好书!!!
评分正版好书!!!
评分非常快,一直信赖京东。
评分非常好。。。。。。。。。
评分非常好
评分比旧版好,花点时间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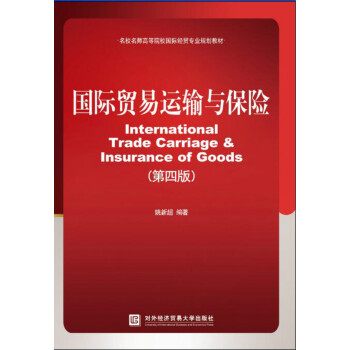
![设计幸福 [Happiness by Desig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51152/582019bfN535a43a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