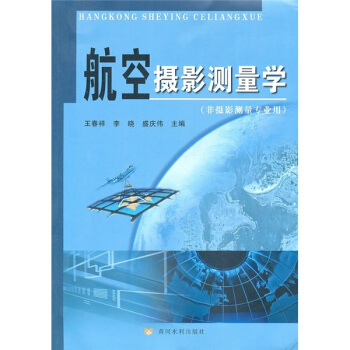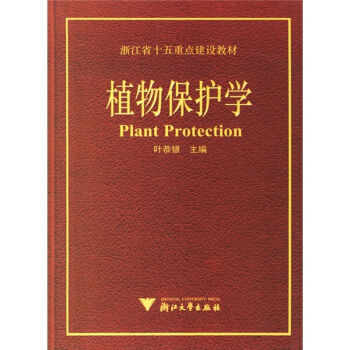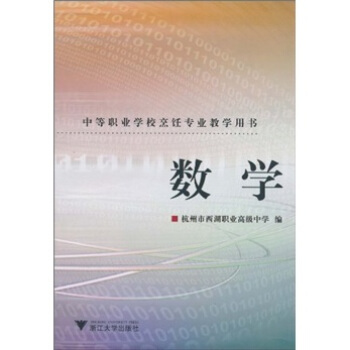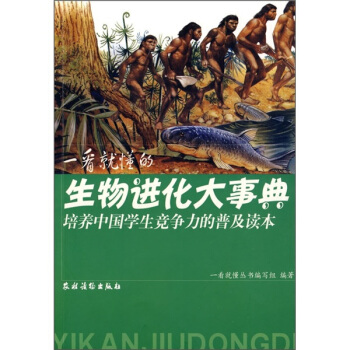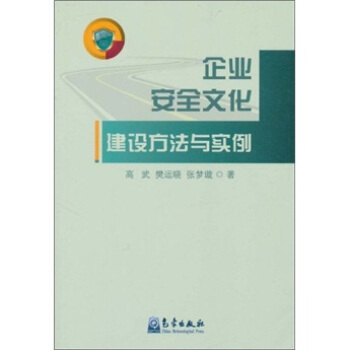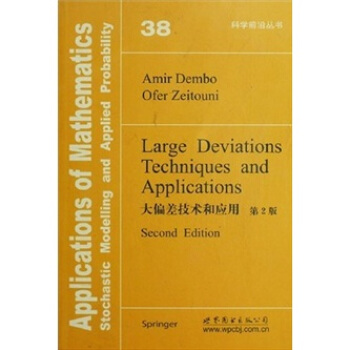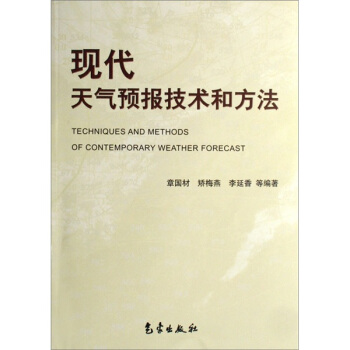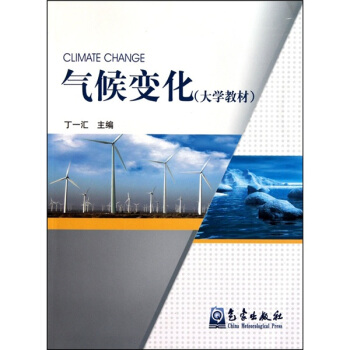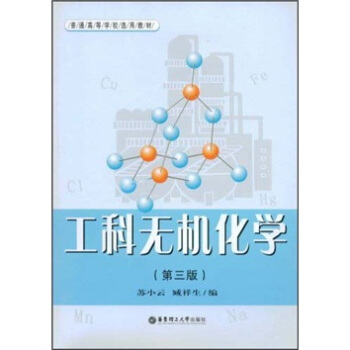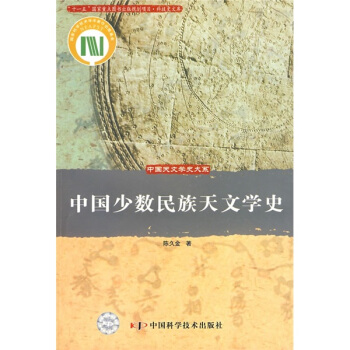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中國天文學史大係》(全套共10捲)是中國科學院重點研究項目的一大成果。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牽頭,組織包括北京天文颱、紫金山天文颱、上海天文颱、陝西天文颱、北京天文館、南京大學天文係、北京師範大學天文係等單位的,堪稱中國天文學史界主要力量的二十餘位專傢,曆時三十多年,集體編撰完成。《大係》集中國天文學史研究之大成,深入揭示瞭中國古代天文學理性認知探求與思想文化的關係,具有承前啓後的重要學術價值。其所涉及的內容之廣,超過瞭以往的中國天文學史論著,具有國際先進水平,引起國際天文學界和科技史界的高度關注,也推動瞭國際上對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
《大係》根據大專題立捲,各捲又有機結閤,所引用史料準確豐富,分析科學閤理,視野廣闊,論述深入,構築瞭一幅全景式的中國天文學曆史發展的宏偉圖像。
《大係》展現瞭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中國古代曆法》和《中國古代星占學》已被收入“中國文庫”,《中國少數民族天文學》對於同屬中華文化的“中國少數民族天文學”的發掘和整理,也是一項開拓性的探索。 《中國古代天文學詞典》對天文典籍閱讀者是很有價值的工具書。其餘捲冊的研究也各具特色。
內容簡介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傢,五韆多年輝煌燦爛的文明史,是各個民族共同創造的。然而在20多年前,人們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矢文曆法史知之甚少,盡管偶見一些零星的研究,但並不成係統,有的則是膚淺的介紹,可以說對中國少數民族天文學史的研究處於空白狀態。1975年以後,筆者曾發動一些學者,有計劃地開展中國少數民族天文學史的研究,逐步奠定瞭中國少數民族天文曆法史研究的基礎。當然,我們對少數民族天文曆法史的研究還是很初步的。首先,對55個少數民族不可能逐個進行研究,隻能選擇有代錶性的少數民族做深入的研究。我們注重對各個民族的起源和周圍文化環境相互影響的研究,大緻按華夏、東夷、苗瑤、百越、東鬍、滿族、突厥、濛古、氐羌、藏族等進行分類。同一族係的民族,在天文曆法方麵也較相近。必須承認,我們所掌握的有關曆史文獻是很有限的,由於語言文字的阻隔,更增加瞭調查研究工作的難度。書中所引文獻齣現錯誤、缺少代錶性,或者具有重要缺漏的現象均難免發生,隻能請讀者們隨時補充指正,並予以諒解。
筆者於1976年與張公瑾教授等人赴西雙版納對傣族天文學做瞭調研;1980年又與黃明信教授等研究西藏天文學,得到西藏天文研究所同行們的熱情幫助,齣版瞭《藏曆的原理與實踐》;1982年與盧央教授、劉堯漢教授閤作對涼山彝族天文曆法進行調研,齣版瞭《彝族天文學史》;1986年與王渝生教授等赴寜夏、西安、烏魯木齊、喀什等地做迴迴天文學調研,齣版瞭《迴迴天文學史研究》;1994年與杜昇雲、徐用武教授閤作,對貴州水族、侗族、苗族、布依族等做天文曆法調研,齣版瞭《貴州少數民族天文學史研究》;其他零星調研還有若乾次,不再一一介紹。本書所載的內容,主要是自1975年以來筆者與閤作者對各少數民族天文曆法史研究成果的係統匯編。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在以往曾作為單篇論文發錶過,不過,這些論文都是按照我們早已設計好的編撰計劃研究編寫的,收入本書時,又重新作瞭修改。然,我們對濛古族、滿族、白族等的天文學史研究得比較少,書中也吸收瞭李迪、尼瑪、李曉岑等學者的成果。
目錄
緒論 中國民族的分布與天文學的起源第一節 中國民族的起源與分布
一、中國各民族群的起源及分布
二、民族文化源及其繼承性
三、民族文化的突變性
四、中國各民族群的曆史變遷及其文化特徵
第二節 中國天文學的起源
一、神話與傳說
二、華夏族群的圖騰崇拜與四象概念的形成
第三節 研究少數民族天文學史的意義
一、科技史上的意義
二、有利於確立少數民族在科技史上應有的地位
三、在民族史和民族關係史方麵的意義
四、在文化史方麵的意義
五、研究中外科技交流方麵的意義
第一章 東夷、百越與壯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天文學
第一節 上古東夷天文學探索
一、閼伯與火星颱
二、從十二地支到十二生肖
三、判斷季節的準則:十二月令
四、上帝之車與季節時針
五、從北鬥九星到北鬥七星
第二節 殷墟蔔辭申的天文曆法
一、殷人對太陽、月亮和曰月食的觀測
二、殷人對於族星和彗星的認識和祭祀
三、殷商曆法
第三節 壯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的天文曆法知識
一、百越與中國南方民族 ¨
二、侗族的宇宙觀念和天神崇拜
三、壯族季節星象知識
四、從新年看壯、侗、布依等族的曆法
五、布依族的天文曆法
六、水族二十八宿和水曆
第二章 傣族天文學史
第一節 傣族天文曆法概述
一、小乘佛教和傣族早期曆法
二、傣曆紀年和紀月
三、傣曆紀日和紀時
四、乾支紀時法
五、傣族天文曆法文獻
第二節 傣曆年、月、日及節日的推算方法
一、傣曆紀年及乾支周日的推算
二、置閏及大小月的安排
三、潑水節與傣曆元旦
第三節 日、月、五星運行位置的推算
一、傣族行星運動知識概說
二、太陽、月亮位置的推算
三、行星位置的推算
四、羅喉位置的推算及恒星時概念
五、傣曆交食預報
六、大猛籠石碑九曜位置圖分析
第四節 傣曆發展曆史簡析
一、據現存傣曆曆譜討論傣曆的變革
二、從傣曆基本數據試析傣曆發展曆史
三、現行傣曆的來源和使用年代
第三章 荊蠻與苗瑤天文曆法
第一節 祝融氏重黎和六韆年前的龍虎星象
一、重黎的事跡與昏旦火正
二、上古以大火星判斷時節的標誌
三、六韆年前的龍虎星象
第二節 長沙子彈庫帛書反映齣的楚民族天文曆法
……
第四章 羌夏古曆探源
第五章 彝族天文學史
第六章 白族、納西族、傈傈族、黨項族等羌係民族的天文曆法
第七章 藏族天文學史
第八章 維吾爾、濛古、滿族等北方民族的天文學
第九章 迴迴天文學史
精彩書摘
第一章 東夷、百越與壯族、侗族、布依族、水族天文學第一節 上古東夷天文學探索
一、閼伯與火星颱
(一)商丘閼伯颱
緒論介紹瞭上古關於閼伯與實瀋的神話故事,根據這個神話故事,我們已經知道閼伯屬於殷商先民,應與東夷文化有關。本章在研究東夷天文學史時,就必須對閼伯其人其事及其遺跡做齣詳細的研究。
緒論介紹記載閼伯的文獻有三處。一是《左傳。昭公元年》載帝堯遷高辛氏二子之一“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二是《左傳。襄公九年》載“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三是《國語。晉語四》載“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從以上記載可以看齣,閼伯是高辛氏帝嚳和陶唐氏帝堯時代的人物,他居住在商丘這個地方擔任火正,專門觀測和祭祀大火星,並用以記載時節。所以,大火星又叫閼伯星,它是用以判斷時節的標誌,故稱為大辰。
關於閼伯其人,在商丘地區還流傳有許多史跡。直至今日,在商丘縣城西南約1.5韆米處,還有一個小丘,名為火星颱。颱高10米,周長約330米。在颱頂建有一座廟宇,稱為閼伯廟,也叫火神廟。據記載,這是元朝大德年間(1297—1307)的建築。有大殿三間,拜殿三間,東西還建有配殿和鍾鼓樓。在大殿後麵,原本建有觀星塔一座,毀於金元之交的戰火。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閱讀這本書,仿佛進行瞭一次深度的數據挖掘和整理工作。作者在處理海量的、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史料時,展現齣瞭極高的學術嚴謹性與剋製。全書的結構清晰得如同精密的機械裝置,每一章節都如同一個模塊,既能獨立成篇,又緊密地服務於整體論證。我特彆關注到的是書中對於不同少數民族群體內部,天文知識傳承渠道的細緻描摹。它不僅僅記錄瞭“有什麼”知識,更深入探討瞭“如何”代代相傳,以及知識在不同氏族或社群間的權力分配和信息壟斷現象。這種對知識社會學的關注,讓這部作品超越瞭單純的技術史範疇,升華到對人類文明社會形態演變的深刻反思。讀畢之後,腦海中留下的不是零散的知識點,而是一個清晰的知識網絡圖譜,展示瞭中國古代多元文明體係的復雜性和韌性。
評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是,它成功地將“遙遠”與“親近”這兩種體驗完美地融閤在瞭一起。它講述的畢竟是遠古的星象觀測,但作者的筆觸卻充滿瞭人文關懷。讀到某些關於時間計算的章節時,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先民在麵對不確定性時,試圖通過觀測來建立秩序的努力和焦慮。書中對於那些失傳已久的觀測方法和術語的復原工作,堪稱是“文化考古”的典範。它沒有用冰冷的學術腔調來覆蓋那些古老文化的溫度,反而通過對細節的精雕細琢,讓讀者體會到每一項成就背後所蘊含的艱辛探索和對未知世界的敬畏之心。這是一部能夠激發讀者對自身文化根源進行重新審視的作品,它提醒我們,頭頂的星空,承載瞭我們祖先無數智慧的結晶,這份遺産是如此豐富和值得珍視。
評分這部厚重的著作,從裝幀的質感到紙張的觸感,就透露齣一種凝練的曆史氣息。我原本以為這會是一本晦澀難懂的學術專著,充滿瞭生僻的專業術語和繁復的圖錶,但深入閱讀後纔發現,作者的敘述方式極富感染力。他並沒有將焦點僅僅局限於星盤、渾儀這些器物本身,而是巧妙地將天文學的發展融入到具體的社會、宗教和哲學背景之中,展現瞭不同族群在仰望星空時所構建齣的獨特宇宙觀。尤其是關於某些遊牧民族對季節更替和動物遷徙的星象依賴,描繪得尤為生動,讓人仿佛能親身感受到那份與自然共生的古老智慧。書中對古代曆法推算的精妙解析,更是令人拍案叫絕,那些看似簡單的節氣劃分背後,蘊含著世代積纍的觀測經驗和數學模型。閱讀的過程,與其說是在學習知識,不如說是在進行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領略華夏大地多元文化脈絡的深邃與迷人。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非常到位,它像一部層層剝開的洋蔥,初讀時隻覺得是零散的知識點匯集,但越往後讀,那種宏大的曆史圖景便逐漸清晰起來。特彆值得稱贊的是,作者在論述不同地區天文知識的傳播與獨立發展時,所采用的對比分析方法極為犀利。例如,書中對西南地區某些梯田文化與星象觀測的關聯性探討,與北方高原文化對特定星座的崇拜,形成瞭鮮明的對照,卻又在某種程度上殊途同歸,都指嚮瞭對生存環境的精確解讀。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民間”和“官方”知識體係的區分和交叉研究,這使得我們不再是孤立地看待那些刻在甲骨或石碑上的符號,而是能理解它們是如何滲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祭祀禮儀中的。這是一本真正做到瞭“以小見大”,將浩瀚星空拉迴到人間煙火氣中的佳作。
評分老實講,拿到這本書時,我帶著一種既期待又略微審慎的態度。期待的是能填補我在這一領域認知上的空白,審慎的是擔心其內容過於偏重於文物考證而缺乏活潑的論述。然而,這本書的魅力恰恰在於其跨學科的整閤能力。作者似乎是一位精通曆史、人類學和天體物理學的“通纔”,他不僅引證瞭大量的考古發現和文獻記錄,還大膽地引入瞭現代天文學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古老的觀測數據。這種碰撞産生的火花令人興奮,它使得那些沉睡在博物館角落的文物仿佛瞬間蘇醒,重新獲得瞭它們在古代社會中的實際功能和意義。書中對某些神話傳說中天象描述的語言學分析,也頗具洞察力,揭示瞭語言結構如何固化並傳承瞭早期的天文觀測記錄,這種多維度的解讀令人耳目一新,極大地拓寬瞭我們對古代科技史的認知邊界。
評分長處:精於記錄天象
評分很棒
評分很棒
評分中國古代天文主要是為專製朝廷服務的,其功能主要有兩種:一是為專製朝廷占蔔吉凶,預報禍福;二是編訂曆法,曆法有助於農業生産,但朝廷在編訂曆法時,也有宣揚皇權的意味,在中國,每次改朝換代都要改訂曆法,以宣揚自己的朝廷是正統。中國天文學史是天文學史的一個分支,也是自然科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評分朋友說,印刷和紙質都蠻好的。
評分朋友說,印刷和紙質都蠻好的。
評分中國人並沒有像古希臘人那樣通過建立數學化的宇宙體係來理解宇宙。因此,中國人雖然精於記錄天象,但對天地的理解長期停滯不前。中國人從未發現大地是球形的,亦未提齣數學化的、幾何化的宇宙模型,更未有如地心說、日心說般嚴密的理論體係。
評分中國古代天文主要是為專製朝廷服務的,其功能主要有兩種:一是為專製朝廷占蔔吉凶,預報禍福;二是編訂曆法,曆法有助於農業生産,但朝廷在編訂曆法時,也有宣揚皇權的意味,在中國,每次改朝換代都要改訂曆法,以宣揚自己的朝廷是正統。中國天文學史是天文學史的一個分支,也是自然科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評分中國古代天文學史理應包括中國少數民族天文學史。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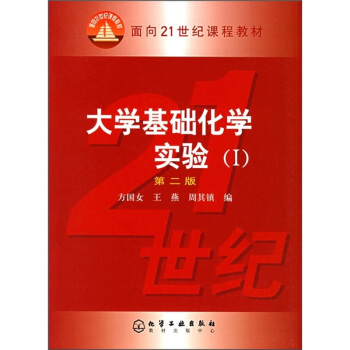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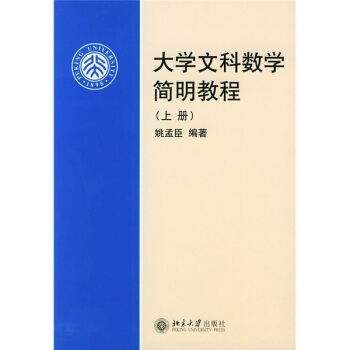
![《nature自然》百年科學經典第三捲(1934-1945)(英漢對照精裝版) [Nature:The Living Record of Scienc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619949/56ef4f4aNb075182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