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结合在了一起,他用自己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史铁生散文选集》荟萃了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32篇,包括:“合欢树”、“秋天的怀念”、““安乐死”断想”、“三月留念”、“复杂的必要”、“一个人和一只牛”、“喜欢与爱”、“乐观的根据”、“信仰是自己的精神描述”等。内容简介
“新百花散文书系”将中国的散文传统视为一个不断更新的开放体系。 “新百花散文书系”力求把当代散文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作品不断纳入自身。 “新百花散文书系”展示的,即是这样一条有着自新能力的中国散文之河。 藉此,您将充分感受与领略中国文学的巅峰笔意与思想之美。 《史铁生散文选集》是该书系中的一本。 《史铁生散文选集》主要收录了史铁生的32篇作品,包括:秋天的怀念”、““安乐死”断想”、“三月留念”、“复杂的必要”、“一个人和一只牛”、“喜欢与爱”、“乐观的根据”、“游戏·平等·墓地”、“二姥姥”、“庙的回忆”等。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精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具有较高的可读性,非常值得欣赏。作者简介
史铁生(1951-2010),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4年始在某街道工厂做工,七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从1986年起,即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一级作家职称。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命若琴弦》、《往事》等;散文随笔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以及《史铁生作品集》。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2002年,史铁生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内页插图
目录
合欢树
我二十一岁那年
秋天的怀念
我与地坛
想念地坛
笔墨良心
“安乐死”断想
好运设计
随笔十三
减灾四想
游戏·平等·墓地
三月留念
“嘎巴儿死”和“杂种”
神位·官位·心位
爱情问题
无病之病
复杂的必要
外国及其他
在家者说
在北京友谊医院“友谊之友”座谈会上的发言
病隙碎笔·之一
一个人和一只牛
二姥姥
老家
庙的回忆
庄子
喜欢与爱
种子与果实
乐观的根据
“足球”内外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信仰是自己的精神描述
精彩书摘
二十九说白了,作恶者更倾向于灵魂的无。死即是一切的结束,恶行便告轻松。于此他们倒似乎勇敢,宁可承担起死后的虚无,但其实这里面掩藏着潜逃的颤栗,即对其所作所为不敢负责。这很像是蒙骗了裁判的犯规者,事后会宽慰有加地告诉你:比赛已经结束,录像并不算数。
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是人类高贵的猜想,就像艺术,在科学无言以对的时候,在神秘难以洞穿的方向,以及在法律照顾不周的地方,为自己填写下美的志愿,为自己提出善的要求,为自己许下诚的诺言。
但是恶行出现了。恶行警觉地发现,若让那高贵的猜想包围,形势明显不妙。幸亏灵魂不死难于证实,这不是个好消息么?恶行于是看中“证实”二字,慌不择路地拉扯上科学——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向那高贵的猜想发难。但是匆忙中它听差了,灵魂不死的难于证实并不见得对它是个好消息,那只是说,科学在这个问题上持弃权态度。科学明白:灵魂的问题从来就在信仰的领域,“证实”与“证伪”都是外行话。
三十
可什么是恶呢?有时候善意会做成坏事,歹念碰巧了竟符合义举。这样的时候善恶可怎么评断,灵魂又据何奖惩?以效果论吗,有法律在,其他标准最好都别插嘴。以动机论吗,可是除了自己,谁又吃得准谁一定是怎么想的?所以,良心的审判,注定的,审判者和被审判者都只能是自己。这就难了,自我的审判以什么作标准呢?除非是信仰!或者你心里早有着一种善恶标准,或者你就得费些思索去寻找它。这标准的高低姑且不论,但必超乎于法律之外,必非他人可以代劳,那是你自己的事,是灵魂独对神的倾诉、忏悔和讨教。这标准碰巧了也可能符合科学,但若不巧,你的烦忧恰恰是科学的盲区呢?便只好在思之所极的空茫处,为自己选择一种正义,树立一份信心。这选择与树立的发生,便可视为神的显现。这便是信仰了,无需实证却可以坚守。
善恶的标准,可以永久地增补、修正,可以像对待幸福那样,做永久的追寻。怕只怕人的心里不设这样的标准,拆除这样的信守,没有这样的法庭也不打算去寻找它,同时快乐地宣扬这才是人性的复归。
……
前言/序言
写作(这里主要指小说和散文)成为少数人的职业,我总感觉有点荒唐。因而我想“专业作家”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世界上那么多人,凭什么单要听你们几个人叨唠?人间那么多幸福快乐困苦忧伤,为什么单单你们几个人有诉说的机会?几十亿种生活,几十亿种智慧和迷惑。为什么单单选取你们的那一点点儿向大家公布?我觉得这事太离谱儿。 小说或散文若仅仅是一处商业性的娱乐场所倒也罢了,总归不能人人都开办游乐场。但文学更要紧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观赏,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有人说得干脆那甚至是情爱般的,袒露、切近、以命相许、海誓山盟。这可是少数几个人承担得起的么? 作家都自信道出了世事众生的真相,即便夸张、变形、想象、虚构、拼接、间离……但他们必说那是真或是本质的真。虽对真的检查见仁见智,但有一条肯定:自命虚假的作品绝无。然而人间浩翰复杂瞬息万变,几位职业作家能看见多少真呢?有一副旧对子:百行孝当先/万恶淫为首。据说有位闲人给上下联各添了十三个字:百行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迹可察,但心可度么?我还听一位“文革”中遭拷打而英勇未屈者说过:要是他们再打我一会儿我可能就叛变了,我已经受不住了正要招认,偏这时他们打累了。我有时候猜测:那个打手一定是累了么?还是因为譬如说他与某个女人约会的时间到了?当然还可能是其他原因,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只要当事人不说,真相便永无大白之日。还是那句话,要是成千上万的人只听几个人说(且是小!说,是散!文),能听见多少真呢?充其量能听见他们几个人自己的真也就难能可贵。 扬言写尽人间真相,其实能看全自己的面目已属不易。其实敢于背地里毫不规避地看看自己,差不多就能算得圣人。记得某位先哲有话:“语言,与其认为是在说明什么,不如说是在掩盖什么。”形单影只流落于千差万别的人山人海中,暴露着肉身尚且招来羞辱,还敢赤裸起心魂么?自亚当、夏娃走出伊句园人类社会于是开始之日,衣服的作用便有两种:御寒和遮羞;语言的作用也便有两种:交流和欺瞒。孤独拓展开漫漫岁月,同时亲近与沟通成为永远的理想。在我想来,爱情与写作必也是自那时始,从繁衍种类和谋求温饱的活动中脱颖而出——单单脱去遮身的衣服还不够,还得脱去语言的甲胄让心魂融合让差别在那一瞬间熄灭,让危险的世界上存一处和平的场所。可能是罗兰·巴特说过,写作者即恋人。所以有人问我,你理想中的小说(或散文)是什么?我想了又想,发现我的理想中并没有具体的作品,只有一种姑妄名之的小说环境或日创作气氛,就像年轻恋人的眼前还没有出现具体的情人却早有了焦撩着的爱的期待。于是我说,在我的理想,中甚至是思念里,写小说(或写散文)应该是所有人的事,不是职业尤其不是几个人的职业,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地是每一个人的心愿,是所有人自,由真诚的诉说和倾听。所有人,如果不能一同到一个地方去,就一同到一种时间里去,在那儿,让心魂直接说话,在那儿没有指责和攻击当然也就无需防范和欺瞒。在那儿只立一个规矩:心魂有袒露的权利,有被了解的权利,唯欺瞒该受轻蔑。 所以我希望“职业作家”是暂时现象。我希望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么多技巧,几十亿种自由坦荡的声音是无论什么技巧也无法比拟的真实、深刻、新鲜。我希望写作是一块梦境般自由的时间,有限的技巧在那儿死去,无限的心思从那儿流露无限的欣赏角度在那儿生长。当然当然,良辰一过我们还得及时醒来,去种地,去打铁,上下班的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 (引自《随笔十三》第四节。文题系本集出版时所拟)用户评价
史铁生先生的文字,总能触碰到灵魂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初读《我与地坛》,就被那种绝望中的生命力深深震撼。他描绘的那个古老的地坛,不仅是一个空间,更是他内心世界的缩影。在那里,他与命运搏斗,与孤独对话,最终找到了生命的意义。那种挣扎、那种不甘、那种对生的眷恋,在字里行间流淌,仿佛能感受到他指尖划过粗糙石板的温度。他对人生苦难的坦然,对生命渺小的认知,却又在渺小中发掘出尊严与光辉,这种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他作品独特的魅力。读他的散文,常常会让人停下笔来,陷入沉思,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生命的本质。他笔下的苦难并非令人绝望,反而像一剂苦涩的良药,涤荡心灵,让人更加珍惜当下,更加懂得感恩。地坛的那个身影,不仅仅是一个残疾人的背影,更是那个时代无数追寻生命意义的灵魂的写照。他用文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窥见了一个深邃而又充满希望的内心世界。
评分我一直认为,文字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史铁生先生的散文,正是如此。他笔下的《病隙随笔》,与其说是记录疾病,不如说是记录生命在病痛中的坚韧与升华。他用一种超然的姿态,描绘着身体的限制,却又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翱翔。那种对生命的热爱,那种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从未消退。他对于“活着”这件事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概念,而是一种对生命状态的深刻体悟。他能够在病痛中看到风景,在苦难中发现乐趣,这种豁达与乐观,是多么难能可贵。他的文字,像一股清流,洗涤着我们被世俗尘埃蒙蔽的心灵,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可贵。读他的书,总能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真正地“活着”,是否懂得珍惜生命中的点滴幸福。
评分翻开《记忆与可能性》,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斑驳陆离的记忆迷宫。史铁生先生的文字,不像某些作家那样追求华丽辞藻,却自有其朴素而深沉的力量。他笔下的过往,并非简单的流水账,而是带着一种对时间流逝的独特感知。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孔,那些消逝的岁月,在他的笔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却又带着一丝物是人非的苍凉。他谈论记忆,也谈论记忆的不可靠性,这种对认知本身的探讨,让人不禁反思我们所认为的“真实”。他对于“可能性”的思考,更是拓展了生命的维度,让我们明白,即使身处困境,也并非没有选择。这种对命运的辩证思考,既有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又有对未来的开放心态。读他的文字,总有一种被温暖包裹的感觉,即使谈论的是悲伤和失落,也总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坚韧和力量。他没有给人鸡汤式的慰藉,而是以一种平和而又洞彻的姿态,引领我们去审视自己的生命。
评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本书,让我想起了那些已经远去的故乡和童年。史铁生先生的文字,总有一种独特的怀旧情怀,却又不是简单的伤感。他描绘的清平湾,仿佛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承载了他最纯真的回忆。那些关于土地、关于自然、关于质朴的人们的描绘,都带着一种令人动容的亲切感。他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那些纯粹的情感,那些简单的快乐,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他对于“故乡”的解读,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的归属,一种对根的追寻。读这本书,仿佛也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他的文字,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能够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去感受那些被遗忘的美好。它让我们意识到,即使岁月流转,那些曾经的情感和记忆,依然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
评分《扶轮问答》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是难以言喻的。史铁生先生以一种近乎哲学的思辨,探讨着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爱、死亡、自由。他的文字,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充满了真切的体验和深刻的反思。他对于“存在”的追问,对于“意义”的探索,总是能够触及我们内心最隐秘的角落。他将个人的苦难经历,升华为对人类共同困境的体悟,这种广阔的胸怀和深邃的智慧,让人由衷地敬佩。他关于“爱”的论述,并非流于表面,而是深入到爱的本质,爱的付出与获得,以及爱在生命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于“死亡”的探讨,更是带着一种超越恐惧的平静,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这本书,不仅仅是阅读,更像是一场心灵的对话,一场关于生命真谛的探索之旅。它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失落中拾回勇气。
评分老师要求买的,正品满意。
评分可以的,很好,搞活动买的,特别优惠,过二天再买一个
评分东西超级好,价格非常便宜,物流非常快,给京东点赞!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的
评分非常棒
评分没有封套,不宜保存和打理
评分很好
评分这本书非常好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
评分以前看过他的一些小文章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忧伤悲天悯人的感觉。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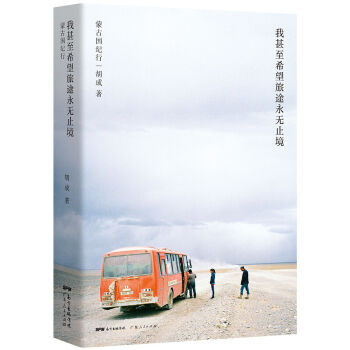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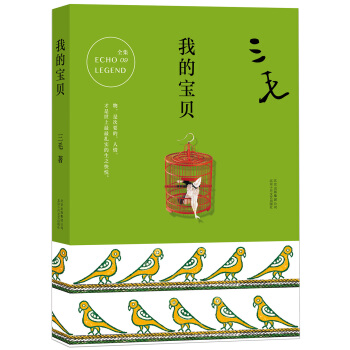
![意林·小小姐首创果味杂志书MOOK纯美小说系列:焦糖布丁号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84874/55473b6dN963448e4.jpg)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绿野仙踪(青少版 新版)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9314/rBEbRVN0EkUIAAAAAAsBa1__OrgAABHNwFGz34ACwGD728.jpg)
![曹文轩小说集(套装6册)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37887/5703dc46N3862b6a4.jpg)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青少版:洋葱头历险记(新版)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1971/rBEbRVNrVx0IAAAAAAmNg2eSZY0AAAWngDifdkACY2b50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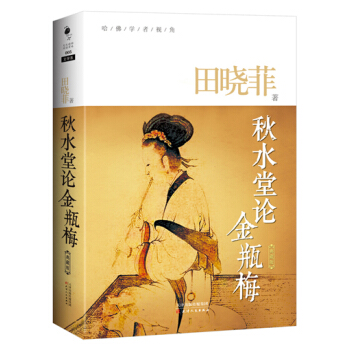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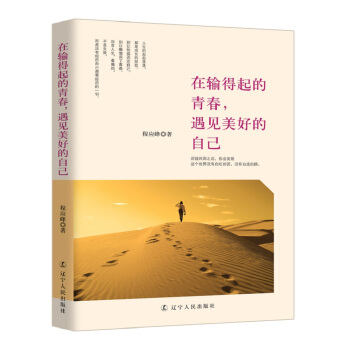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水浒传(青少版 新版)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9312/rBEbRVN0EkUIAAAAAArt1LNM-msAABHNwEhZPAACu3s58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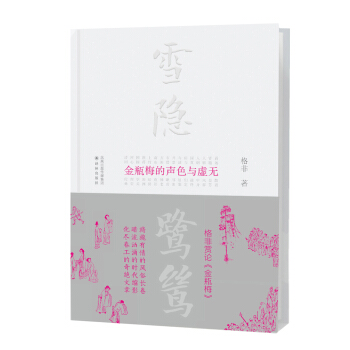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青少版:木偶奇遇记(新版)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1967/rBEbRVNrVx0IAAAAAAi2-vegt_UAAAWngCSuq8ACLcS452.jpg)

![小小姐首创果味杂志书:甜心草莓号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04624/554ffdebN9ee9a6e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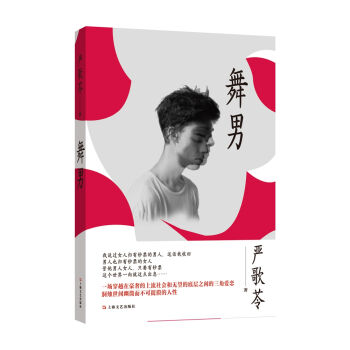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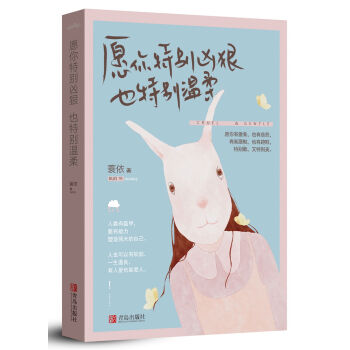
![意林最佳少女文学读本4·小小姐:踮脚跳支圆舞曲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74682/rBEHaVBEcowIAAAAAAFquMYSOlgAAA_3AFHJ5kAAWrQ794.jpg)
![曹文轩新作·冰项链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37888/540930d3Nb713ba10.jpg)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Confieso que he vivido]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69523/5513c930Na3a92b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