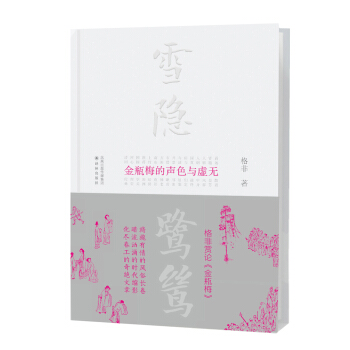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被列为禁书、奇书、才子之书的古典名著《金瓶梅》,究竟有多少可能的读法?为什么说它启发甚至胜过了《红楼梦》?书中一百回故事,如何暗藏着“雪隐鹭鸶”般深险幽微的人情世态?明清之际的市民生活与世风转变,又与今天的中国现实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你可以没有读过《金瓶梅》,但你不可错过格非“解毒”《金瓶梅》。
二十载精读之心血倾注,阅尽四百年未变之世相人心 学者之识、作家之笔相映生辉 不拘一格的经典解读,填补空白的妙趣新知,深言警世的智者之书
书名取自《金瓶梅》第二十五回中的诗句:“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 白色的鹭鸶藏在雪地里,也许只在它飞起的一刹那,人们才会猛然察觉它的存在。“雪隐鹭鸶”的意象可喻指《金瓶梅》中深远幽微的人情世态和历史文化讯息,也令人联想起《红楼梦》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劲悲凉。作者认为,《金瓶梅》所呈现的人情世态和当今中国现实存在着内在关联,或许,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并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 格非《雪隐鹭鸶》对《金瓶梅》的解读,正是要鼓励读者穿透偏见和曲解,去索解隐秘、探幽访胜。
“最美的书”多次获奖者朱赢椿用心设计 附《金瓶梅》绣像图百处精美细节
内容简介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首先将《金瓶梅》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细考察,探索小说情节背后的社会史和思想史渊源;进而,46则优美隽永的“修辞例话”将全书关窍一一勾连,为读者剖析《金瓶梅》写作的精妙处。格非对《金瓶梅》的解读承续了前辈学者“以诗证史”的努力,以小说观照时代,建立文学文本与“历史事实”间的复杂关联。修辞例话部分的细绎深解,亦堪称文本精读的典范。
作者简介
格非,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著有《迷舟》、《相遇》等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长篇小说六部,以及《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博尔赫斯的面孔》等论著和随笔集多部。内页插图
目录
卷一 经济与法律清河
清河国
临清
钞关
淮上
南方
南北方社会风习之别
书名之寓意
市井与田园
人人皆商
开中
西门庆的“经济型”人格
新信仰的出现
金钱崇拜
白银货币
同心圆
礼与法
蒋竹山的借票
“契约社会”的脆弱
法律与政治
法律的实质
法律之外
卷二 思想与道德
阳明学的投影
佛道世界观
参禅与念佛
禅、净之辨
无善无恶
真妄
《红楼梦》的真妄观
“诚”与“真”
恶人之死
佛眼
色情问题
伦理学的暗夜
自然、本然与虚无
倒影
卷三 修辞例话
老虎
十兄弟
邻居们
薛嫂
孙歪头
回前诗的删改
撞了个满怀
李瓶儿
邸报
囫囵语
夫妻交恶
越界
邈远
冰鉴定终身
两个太监
“青刀马”与“寒鸦儿”
白赉光
价值观之混乱
道佛之别
方巾客
改文书
贲四嫂宴客
苗青案
紫薇花与紫薇郎
桂姐唱曲
故事
水秀才
郑爱月因何不说话
半截门子
病急乱投医
李瓶儿之死
二十七盏本命灯
埋伏
途中风景
文嫂的驴子
幽明之分
重名问题
瞎子申二姐
群芳谱
蔡御史祭灵
散
荷尽已无擎雨盖
燕还旧巢
芍药花
陆沉
韩爱姐
精彩书摘
李瓶儿之死 不一时,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都进来看他。李瓶儿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落后待的李娇儿、玉楼、金莲众人都出去了,独月娘在屋里守着他。李瓶儿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 ——第六十二回在《金瓶梅》众多人物的死亡谱系中,李瓶儿之死描述最详。自她得病至下葬,前后文字竟达十余回之多,尤以第六十二回叙写最为详尽。此回文字超长,叙事剧繁,面面俱到,就连后文核心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之死,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小说中的各色人等,如亲人家眷、仆役小厮、地方官员、趁趣帮闲、妓家戏子、和尚道士和医家法师无不出场亮相。透过李瓶儿之死,作者不仅写出了各色人等对李瓶儿之死的态度,反过来也通过李瓶儿这个临终人之眼,来打量周遭的人情世态。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如此繁盛的篇幅,正面描述一个普通人的死亡,严格地说来,还是第一次。若要了解《金瓶梅》人情世界的亲疏深浅、德恨恩怨及种种世态炎凉,观此回文字足矣。 医家诊病,但为酬银,前文已有详述。王姑子来探望,关注的不是李瓶儿的生死,而是为了与薛姑子争夺从李瓶儿处骗得的印经钱。李瓶儿的大伯花大舅来探病,瓶儿只说了声“多有起动”,就将脸别过一边。这倒不是说瓶儿对大伯有多大的仇恨。花大舅的到来,让她想起了花子虚。正是花子虚的强拉硬拽,才弄得李瓶儿在通往阴曹地府的路上飞奔向前。当然,花大舅也是第一个断定李瓶儿无望,并直接让西门庆为她准备棺材的人。 冯妈妈本来是李瓶儿身边唯一可以依靠的旧人。自从西门庆看中王六儿之后,老冯开始对瓶儿日渐冷淡,成天在王六儿家厮混,把李瓶儿忘在了九霄云外。瓶儿将死,好不容易让人把她叫了来,老冯居然一味地耍贫嘴、撒风。当李瓶儿在死前给了她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一条黄绫裙、一根银掠儿,让她日后老了做个棺材本儿时,冯妈妈这才假惺惺地哭着说:“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我)那里归着?”绣像本的批评者此时很不客气地批道:“王六儿家去。”可谓一语道破禅机。 西门庆、吴月娘倒是时常来看她。一个居着官,公务繁忙,款接甚频;另一个管着这么一大家子,也不能朝夕相陪。西门庆眼看着李瓶儿临死,身边居然没有一个懂事且贴心的人,想了半天,他还终于想起一个人来。她就是李瓶儿的干女儿吴银儿。他向李瓶儿建议,将吴银儿接来家中陪她几天,可李瓶儿摇头拒绝了。前文写官哥死,吴银儿到家里打了个晃就走了。李瓶儿心里清楚,这个干女儿实在指望不上。事实上,在李瓶儿自病重至亡故的漫长日子里,吴银儿竟然没有来过一次。难怪张竹坡挖苦说:“娘死而女不知,方是干女。” 不过,李瓶儿身边倒是有两个丫鬟,对主人情深意笃。迎春似乎还懂点儿事,那绣春还只是个孩子,正处在懵懂无知的年龄。瓶儿临死前嘱咐绣春,将来寻个好人家嫁了,不可任性撒娇,绣春便跪在地上大哭:“我就死也不出这个门。”瓶儿道:“我死了,你在这屋里伏侍谁?”这一断肠之语,可以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红楼梦》中黛玉将死时对紫鹃所说的那番话。绣春的回答完全是孩童的口吻:“我和迎春都答应大娘。”李瓶儿一愣,淡淡说道:“这个也罢了。” “这个也罢了”五个字,可谓字字珠玑。其中既有对绣春不懂事的失望与沉痛——绣春对瓶儿与吴月娘之间的恩怨,恍然不知——或许还有对绣春日后境况的担忧,但更多的,是自己的满腹心事无人交托的无奈。此中的深意,通过迎春闻听此言后“哭的言语都说不出来”一句补写出来,令人伤叹不已。绣像本的批评者认为,此段文字,足以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媲美。瓶儿将死,孑然一身。而官哥死亡在前,总算是让她省掉了托孤的麻烦。她惟有将自己的一腔怜爱,都寄托在这两个丫鬟身上,由此反衬出李瓶儿的孤绝无依,在西门大院中并无半个亲人。其凄绝伤感,令人鼻酸。 对于迎春、绣春将来的安排,小说于同一回中,居然一连写了三次:第一次是李瓶儿当面对迎春、绣春的交代和嘱托,第二次是向吴月娘郑重交托,第三次则是对西门庆再度叮嘱一遍。每一次都言之甚详,不惮其烦。作者如此安排,其非无意? 李瓶儿直到临死,还在利用手中的钱财,最后一次成就她慷慨大方的美德。她知道这些钱物如不送人,最后也只能落在吴月娘、潘金莲手里。她多次劝西门庆,不要因为她的病重而耽搁公事,不要买太贵的寿材,日后家人还要过日子。她似乎对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真情假意概不计较,专心致志地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这是李瓶儿的愚妄之处,也是她的聪明所在——她不如此,又能怎样呢? 李瓶儿死后的第二天,她的干女儿吴银儿才“闻讯赶来”,还责怪吴月娘不通知她。吴月娘倒也没有心思与她计较,只是说:“你不来看你娘,他倒还挂牵着你,留下件东西儿,与你做一念儿,我替你收着哩。”这些东西放在预先打好的包袱里,计有一套缎子衣服、两根金头簪儿、一枝金花。睹物思人,吴银儿这才泪奔不止。一番人情至此,可谓凄婉哀恸之至。 虽说李瓶儿对众人不计前嫌,一概示好,但只有一个人除外,此人就是潘金莲。在此回中,潘金莲很少抛头露面。也许她知道李瓶儿之死与自己脱不了干系,不便出来“摇摆”了吧。可如果潘金莲幻想通过刻意回避,李瓶儿就会把她忘了,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李瓶儿对潘金莲铭心刻骨的仇恨,未曾一旦或忘。 引文中,吴月娘领着众姐妹最后一次来看她。李瓶儿对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和孙雪娥等人,“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无非是些虚与委蛇的应酬和客套,这里没有写出,但亦可想见。等到李、孟、潘诸人先行告退之后,她单独对吴月娘做出的一番交代,却字字见血。她提醒吴月娘,日后有了孩子要小心看护,不可“吃人暗算”。这里的“人”,当知是潘金莲无疑。这番话除了替月娘设身处地着想的表面文章之外,还流露出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官哥死于潘金莲之手;二是李瓶儿之死实源于官哥之亡。而吴月娘的答语“姐姐,我知道”几个字,虽然平常,但却说得斩钉截铁,表明吴月娘不仅接受了临终人的一番好意,同时也认可了李瓶儿的结论。 柔弱如李瓶儿者,于待死之时,万事无所争,却在关键处以寥寥数语预伏下潘金莲日后的悲惨结局,用绣像本批评者的话来说:“岂可欺不言人之无口哉!”后来西门庆一死,金莲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很快被吴月娘赶出家门,命丧武松之刀下。可见月娘对于瓶儿的临终赠言之重视程度。 当然,西门庆死后,有“道学种子”之称的吴月娘,首先要做的事还不是驱赶潘金莲,而是清除李瓶儿残存的最后一丝遗迹——她将李瓶儿的灵位和灵床以及西门庆煞费苦心让人传写的李瓶儿画像,一把火都烧了个精光。同时,月娘将李瓶儿屋内的金银衣物和首饰箱笼,通通搬到自己的房中,将李瓶儿的奶妈和丫鬟收为己用,最后将李瓶儿的房门一把锁锁了个严实,任由它房中长草,蜘蛛结网。李瓶儿若灵泉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我们再细细玩味引文中李瓶儿对绣春所说的“这个也罢了”,其无限的痛楚与怅惘,又有多少内心的暗波潜流激荡其中? 倒影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说法。它所强调的是《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承续关系,在《金瓶梅》的研究界,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了口头禅。可惜的是,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大多停留在对于结构、手法等叙事修辞的比较层面,较少注意到两者在思想和文化观念方面的复杂关系,更无法说明《红楼梦》对《金瓶梅》的重要改造与超越。其实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清代后期至民国一直流行着另外一个观点,即认为《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苏曼殊亦主此说)。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倒影说”显然更能切中肯綮,言简而意深。 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红楼梦》之继承《金瓶梅》,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吴月娘之变身为贾政,这是男女易位;潘金莲之于林黛玉,这是脱胎换骨;李瓶儿之于秦可卿,这是由实入虚;西门庆之于贾宝玉、薛蟠和贾琏(西门庆的孩子气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继承,而他的贪欲、蛮横和轻狂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这是一而多,多而一。同样,从孟玉楼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薛宝钗、探春或熙凤的影子。 就“真妄”与“善恶”观而言,《金瓶梅》是用真妄取代善恶,因而是“无善无恶”,最终落入了空寂与虚境;而《红楼梦》则是两者兼有,彼此照应,并行不悖。因为有了“真妄”,善恶之分被放置到了一个更严格的系统中加以观察而见出真伪。但曹雪芹只是将“善恶”放在引号中,并未最终取消它。除了真妄与善恶之辨外,《红楼梦》的作者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即“清浊之分”。 从情与欲的关系上看,《红楼梦》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则是一个无情或无善的世界。用“尊情”这样的概念来指称《红楼梦》则可,来描述《金瓶梅》则不可,因为《金瓶梅》中几乎是无情可尊。《红楼梦》让它最重要的男性形象贾宝玉始终处于未成年状态,是极富深意的。西门庆遍揽美色入其彀中的无休止纵欲,到了贾宝玉身上,则被抽象为一种对“美人”的倾慕与博爱,我们姑且称之为“贾宝玉主义”。不是说贾宝玉没有情欲,而是这种情欲必须以对女性的“利他性”尊重与崇拜为前提;不是说贾宝玉对待女性没有亲疏之别,但这种亲疏之别,必须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悯作为其基础。《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功利性“成人世界”,《红楼梦》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流溢着青春、幻想与诗意色彩的少年世界——大观园为抵抗世俗社会的风刀霜剑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作者一方面对她的娇媚、柔美、纤弱和聪慧的美人特质大书特书,同时也赋予她刚直不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君子品格。她孑然一身,遗世独立而高标自守,拒绝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黛玉身上也有世俗女性(如潘金莲)的善妒、小心眼儿、自高和争强好胜,说起话来,也像潘金莲那样机趣刻薄。但在《红楼梦》中,这种对境遇的不安和落落寡合,一变为君子不见容于当世的卓尔不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香草美人”比拟君子的传统。从《离骚》的“草木零落、美人迟暮”,至李商隐的“芳草怨王孙,美人喻君子”,可以说这一传统在诗词歌赋中一直连绵不绝。而明确地将君子之品格寄托于女性之身,与以男性世界为象征的污浊、功利和肮脏相抗衡,在小说史上,《红楼梦》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我们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宝黛之恋”,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两情相悦和男女私情,甚至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津津乐道的“爱情”。在宝黛关系中,最让人感动的,不是相恋而是相知。换句话说,“宝黛之恋”的隐秘核心,不是“有情人成了眷属”的恋人关系,而是知己关系。林黛玉对爱情的渴望,不是对举案齐眉的婚姻的渴望,而是对知己的渴望,是对“真”和“洁”的非同一般的追求。作者将往往只有在描述友朋关系时才会出现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主题,融入到了爱情关系中,这就使得《红楼梦》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了严格的切割和区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两部作品都涉及的“绝望”问题。《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佛道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瓶梅》的相对主义,将出家或对世俗世界的逃离,作为其基本归宿(虽说后四十回为续作,但原作的这一意图可以从“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一类的提前叙事中,看出端倪)。也就是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否定乃至绝望,但《红楼梦》的佛道结构是寓言性的,并非实指,这与《金瓶梅》有着根本的不同。《金瓶梅》中的佛道归宿,是世俗个体的唯一出路,而在《红楼梦》中则是象征性出路。在佛与道的俯瞰之下,在世俗世界的内部,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虽不免悲观,但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对绝望本身发出挑战。 《红楼梦》的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云,置大观园摇摇欲坠、“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现实于不顾,在水边联诗觅句,不顾今夕何夕,不管今世何世,充满了激越的旷达、忘我和喜悦。小说的叙述语调,也随之变得欢快、高亢起来。直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一联在不经意中被说出,冰冷而残酷的现实世界才再一次抓住了她们。
用户评价
我一直在寻找能够深入挖掘《金瓶梅》背后更深层意义的读物,而“雪隐鹭鸶”这个书名,瞬间就抓住了我的眼球。《金瓶梅》的声色之繁复,以及其隐含的虚无主义色彩,一直是我着迷的地方。书名中的“雪隐”,给我一种宁静、纯粹的感受,与《金瓶梅》中那些喧嚣、放纵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我不禁猜测,作者是否试图在这纸醉金迷的现实图景中,寻找到一种精神上的超脱,一种对世俗欲望的“隐”去?而“鹭鸶”,这种洁白而又独立的水鸟,是否象征着某种不染尘埃的意境,或是一种对人生虚幻本质的洞察?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将如何构建这种“声色”与“虚无”之间的张力,如何用“雪隐鹭鸶”的比喻,为我们揭示《金瓶梅》中那些被掩盖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本书,听起来就像是为我这样渴望深度解读的读者量身定做的。
评分我对《金瓶梅》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对其“淫书”的刻板印象和“世情百态”的浅层认识上。这次偶然看到《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的书名,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尤其是“雪隐”二字,它给我一种意想不到的静谧和距离感,与《金瓶梅》那种直白、露骨的描写似乎格格不谋。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在这种繁复浓烈的故事肌理中,找到那一份“雪隐”般的澄澈与超脱。难道说,在这声色犬马、欲望横流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更深沉的哲学思考,某种足以将这一切都“隐”去的虚无?我总觉得,《金瓶梅》并非只是一个关于男女情欲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映照出世事的无常与变幻。而“鹭鸶”的形象,又带有一种孤傲与疏离,这是否暗示着作者将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一种冷静而又带着一丝悲悯的眼光,审视那些沉溺于声色之中的生命?这本书,或许能为我解答这些困惑,让我重新认识这部伟大的作品。
评分初见“雪隐鹭鸶”,便被这意象所吸引,好似一幅泼墨山水,又似一段低回婉转的吴侬软语。我对《金瓶梅》素来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敬畏其“世情小说”的巅峰地位,又因其中赤裸裸的人性描绘而有所回避。这本书名,恰似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能以一种更超然、更审美的视角去窥探那繁华背后的落寞,那声色犬马中的虚无。我忍不住想要去探寻,作者是如何将“雪隐”的清冷与“鹭鸶”的孤寂,与《金瓶梅》那炽热而又注定消散的尘世欢愉相结合的。这是一种怎样的炼金术,能将如此世俗的作品,提炼出禅意般的哲思?我期待着,作者的笔触是否能如同薄雪一般,轻轻覆盖住西门庆宅院里的奢靡,却又在阳光下折射出点点晶莹,透示出那藏匿在声色背后的,无尽的空寂与无奈。我深信,这本书不仅仅是对《金瓶梅》的解读,更可能是一次对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全新观照,一次对人生百态的深刻冥想。
评分《金瓶梅》对我而言,是一部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我曾因其露骨的描写而却步,也曾因其深刻的人性刻画而赞叹。然而,关于其“声色”与“虚无”的二元论,我似乎尚未有清晰的认识。当看到“雪隐鹭鸶”这个书名时,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心头。它似乎预示着一种全新的解读视角,一种将繁华落尽后的寂寥、喧嚣过后的沉寂,巧妙地融入其中的方式。“雪隐”二字,带着一种隐匿的美感,一种在纷繁事物中保持清净的姿态;而“鹭鸶”,又带着几分孤高与淡雅。我想象着,作者的笔,是否能如同一位隐士,悄然穿梭于西门庆那奢靡的府邸,却又能超然物外,洞察到那些声色背后的空洞与无意义。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我拨开《金瓶梅》表面那层令人眼花缭乱的“声色”,去触碰到其灵魂深处那份更具穿透力的“虚无”,让我能够以更成熟、更具洞察力的眼光,去品味这部不朽的经典。
评分我一直对《金瓶梅》中那份极致的繁华与转瞬即逝的虚无感着迷,而“雪隐鹭鸶”这个书名,无疑精准地捕捉到了我心中对这部巨著的某种期待。它并非直白地宣扬其声色,而是以一种更为含蓄、更具诗意的方式,暗示着某种在喧嚣中隐藏的静谧,在繁华背后潜藏的空寂。“雪隐”二字,就仿佛在诉说着一种与世隔绝的清冷,一种不着痕迹的消融;而“鹭鸶”,又带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孤寂感,仿佛是站在世俗的岸边,静观潮起潮落。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将这样一种清逸的意境,与《金瓶梅》那浓墨重彩、充满了欲望纠葛的现实世界巧妙地联系起来的。这本书,听起来就像是在探索,在那声色犬马的盛宴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种令人深思的虚无,又该如何去理解那种“隐”在其中的、或许是更深刻的人生哲学。我期待着,它能为我开启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金瓶梅》那永恒的魅力。
评分书很好、价格也很实惠!
评分感觉不错的书。读得懂!喜欢读,就是快递太不在意了,扔在地上。
评分还没拆,但表面不错。格非老师的书内容上有保证的。
评分格非对《金瓶梅》的解读承续了前辈学者“以诗证史”的努力,以小说观照时代,建立文学文本与“历史事实”间的复杂关联。修辞例话部分的细绎深解,亦堪称文本精读的典范。
评分很好~~~~~~~~~
评分感谢京东,常见买书。
评分大家的作品,同时在看江南三部曲
评分自营商品品质都比较有保证,送货也还是很快,家里的储藏间又被我塞的满满的了!
评分格非品评《金瓶梅》:集二十载精读之所成,阅四百年未变之世相;繁华奢靡的明朝故事,深言醒世的智者之书。附《金瓶梅》绣像图百处细节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青少版:木偶奇遇记(新版)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51967/rBEbRVNrVx0IAAAAAAi2-vegt_UAAAWngCSuq8ACLcS452.jpg)

![小小姐首创果味杂志书:甜心草莓号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04624/554ffdebN9ee9a6e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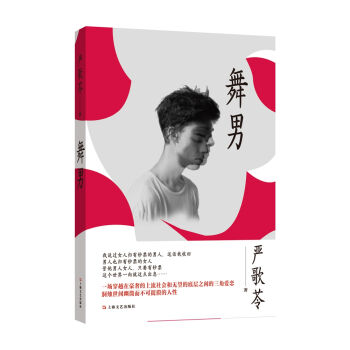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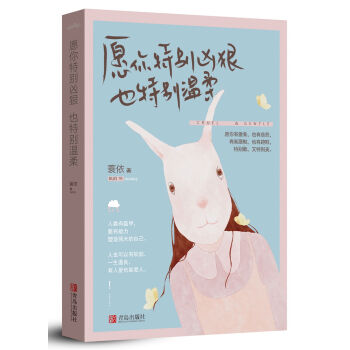
![意林最佳少女文学读本4·小小姐:踮脚跳支圆舞曲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74682/rBEHaVBEcowIAAAAAAFquMYSOlgAAA_3AFHJ5kAAWrQ794.jpg)
![曹文轩新作·冰项链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37888/540930d3Nb713ba10.jpg)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Confieso que he vivido]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69523/5513c930Na3a92b91.jpg)


![曹文轩新作·黑魂灵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37893/540e5f1fN99cc2cf2.jpg)
![荒野求生少年生存小说系列:狂鲨深海的复仇行动 [10-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34623/58f87570N653ea9e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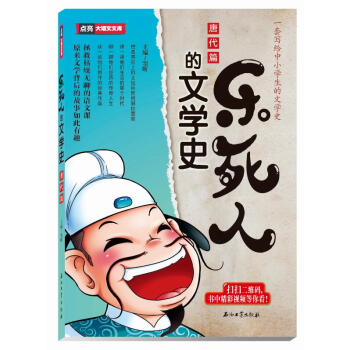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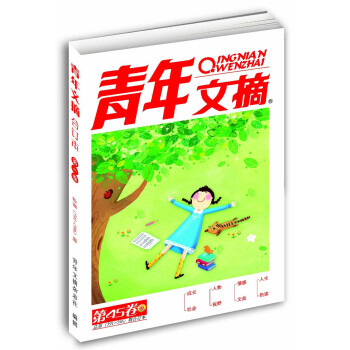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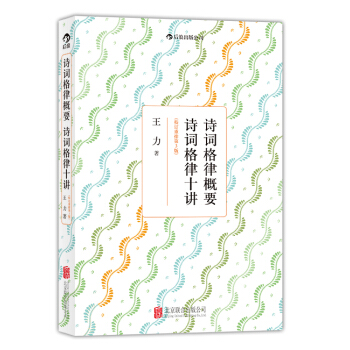
![曹文轩新作·红瓦片 [7-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37894/540934c0N05cc32e5.jpg)
![曹文轩新作·蓝花泪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37889/540e5f6eNdbf6f53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