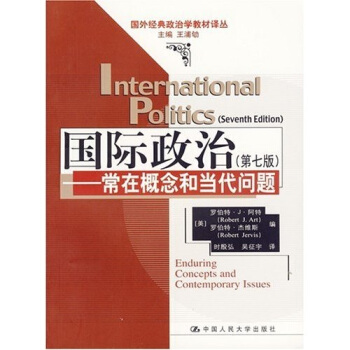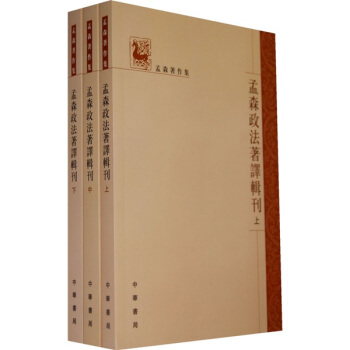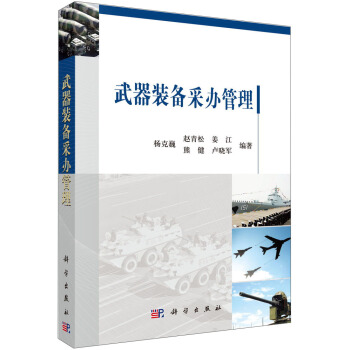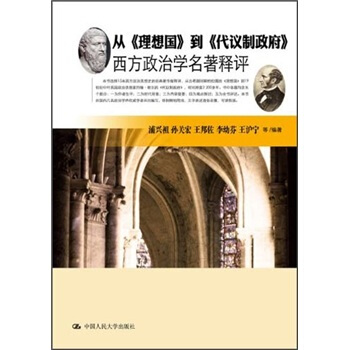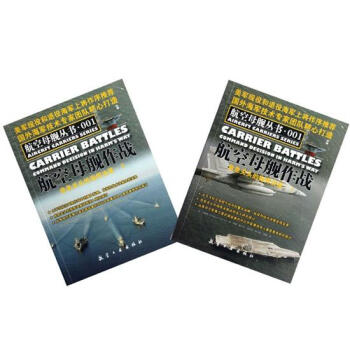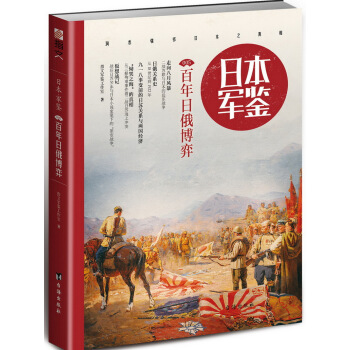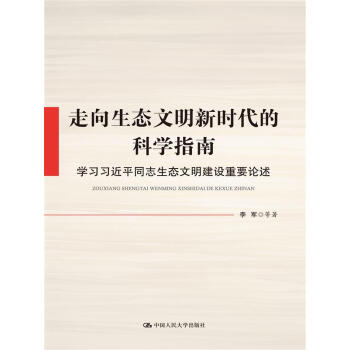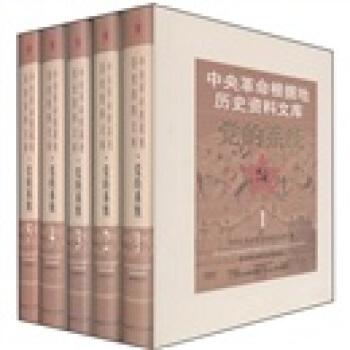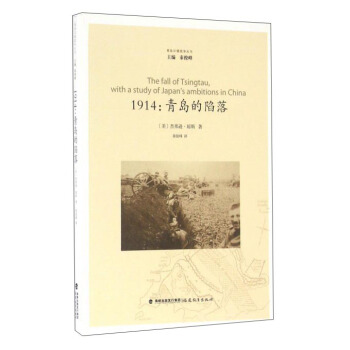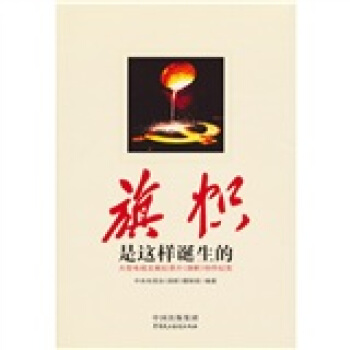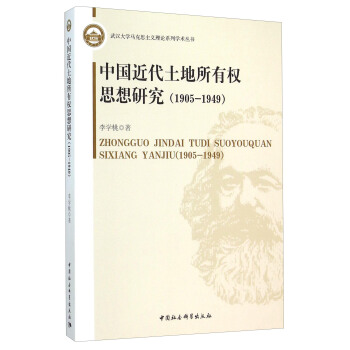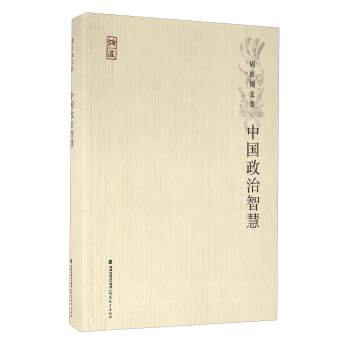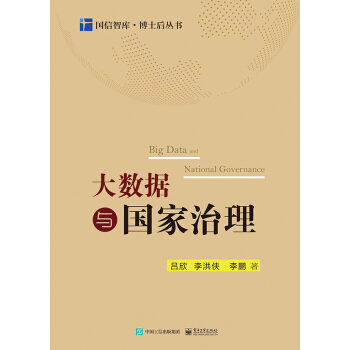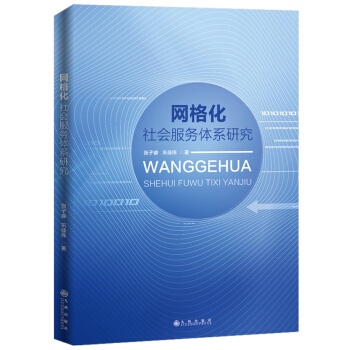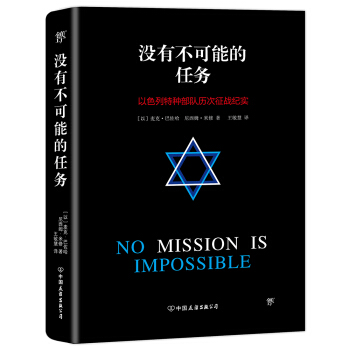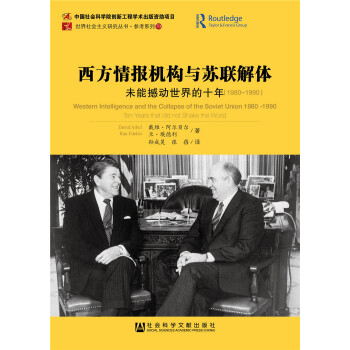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通过向政府官员、情报工作人员、学者、记者等作的大量的采访,细致描述了冷战期间情报机构与决策者的关系,内容引人入胜。书中对冷战双方执政者的思维理念与政策、核武器与高科技的作用、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情报机构的边缘化等问题的讨论,有助于读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其翔实的分析不仅具备学术性,而且极富故事性,可以使普通读者知晓行业内幕以及一些人为操纵的、涉及多国的政治“阴谋”。作者简介
戴维·阿尔贝尔,是一名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情报人员,曾经担任驻美国华盛顿事务部主管,对于情报机构的内部运作十分熟悉。兰·埃德利,既是记者又是作家。
目录
前 言/1惊 讶/1致 谢/2引 言/1第一章 威 胁/5核恐惧对情报机构的影响/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核力量/13核竞赛的开端:朝鲜战争/18古 巴/24越 南/31生化武器的军备竞赛和其他形式的疯狂/38欧洲、北约和中东:核战争的危险?/43“吉林现象”体现病态的疯狂世界/47阿富汗Ⅰ:转折点/54第二章 迷 思/62红军的传统行动能力/62欧洲:华约档案中的西方威胁/70能否打赢核战争/73冷战时期的国际恐怖主义:虚构和现实凯西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75列昂诺夫和克格勃定义的国际恐怖活动/81第三世界:关于斗争/94中东:以色列、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96推 回/100将他们赶出阿富汗/103尼加拉瓜/109伊朗/110格林纳达/111萨尔瓦多/116古 巴/118非 洲/123安哥拉/124非洲之角/126第三世界:概述/131
第三章 观念一致性/139美国的战略目标/139美国的“理念”在欧洲也有市场/147无休止的威胁/167政客、情报机构、媒体和当选官员/169美苏缓和/172里根政府有组织的行动/176凯西和中情局/179凯西vs.苏联/181军工业复合体;或“巨龙”、隐秘轰炸机及F-22战斗机/186星球大战/193
第四章 出人意料/206我很惊讶/206欧洲也很吃惊/209
第五章 不祥之兆/212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危机信号/212内部虚弱和外交政策/215东欧的解放/217苏联内部的民族问题/221军事威胁和红军的表现/224苏联:第三世界经济体?/230崩 溃/233
第六章 为什么西方没能看到不祥之兆/240恐惧、残暴和创伤/240失败的情报搜集、情报评估——或者二者兼有/246阿富汗Ⅱ:数据评估和情报行动的界限/249“理 念”/251国情评估:不是国情也不是评估/254中情局的失败/260对苏联经济状况的过高估计/264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政变/268夸大的军事力量——苏联威胁/271基本的情况怎么样?/276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未来/278情报机构是否出现失误/280其他西方情报机构/283
第七章 政治和情报/286报告的流动/286总统文件/290其他文件/291对情报机构及其作品的态度/293克里姆林宫也不相信情报/294情报的政治化/299情报与政治/305欧洲的情况/310美国政府内部就苏联意图的分歧和斗争/313里根“变心”/318乔治·布什在莫斯科和白宫/322
第八章 战略情报的实用性/326情报评估/326苏联崩溃之后:战略政治情报地位的贬值?/332情报机构失败?中情局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333苏联解体之后的情报机构/335
后 记 从战略盲点到行动失误/338新恐怖主义/338“9·11”事件之后的情报机构/354受访者名单/357参考文献/361中英文词汇对照表/366
前言/序言
前 言 2001年9月11日,当在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惨烈的恐怖暴行之时,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都为之震惊。同样是这些机构,1991年以前在情报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在全球范围发起针对苏联的运动,但是等到苏联崩溃时,它们依然惊愕不已。 本书试图解释为何在有众多明显征状的情况下,西方情报机构还是没能诊断出苏联已病入膏肓,更糟糕的是,为何情报机构甚至没能准确地向政治阶层传达它们已知的信息及做出的评估。 尽管1991年苏联的崩溃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即便简单地分析为何情报机构未能预测和预判“这一场针对美国的宣战”(乔治·W.布什语),也会对我们大有裨益。本书最后一章将着墨于此。 在为撰写本书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有数十个人接受了采访,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以及情报人员。大多数采访对象来自美国和俄罗斯,其他则来自英国、德国、法国和以色列。受访者包括外交部部长、情报机构负责人和研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专家。撰写过程中也用到了书面材料,其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国务卿的自传,以及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负责国情评估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秘密文件。 虽然材料来源丰富,但是本书并非学术专著。这本书更想用平实易懂的语言与读者一方面分享那些受访者——他们大多在冷战的最后十年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感受,另一方面则想共同分析中情局有关问题的文件所显现出的趋势。 每一个受访者都毫不犹豫地承认苏联崩溃让他们吃了一惊,只是每个人对于这种毫无察觉给出的缘由却都互有不同。当历史处于转折点时,运转的情报收集机制再复杂精巧,洞察转折点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此外,政治家似乎常常不把评估接收到的情报当回事。在任何情况下,只有那些能强化他们已有观点的情报才会被接受,如果情报与政治家的世界观和政治计划不符,那么他们就会心生疑窦或者置之不理。情报机构屡屡出错,照理说政治家对情报机构的使用和资助都会慢慢减少,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政治家并非总愿意把情报机构的话听进去,他们似乎也没有准备好抛弃情报机构。 情报机构在1991年的失败基本上要归咎于中情局负责国情评估任务的情报处。而2001年未能阻止恐怖袭击的失误则更为糟糕。1991年的失败所造成的惊讶可以说是“积极的”——对于调查委员会来说,西方情报机构未能洞察苏联的崩溃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没能发现和阻止针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则引发了严重后果。这一事件已经给人们造成精神上的创伤,因此必须全面审视情报机构。 惊 讶 “我很惊讶,”曾于1992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劳伦斯·伊格尔伯格表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知道苏联正发生剧变,但是我当时没想到它即将崩溃。” “我很惊讶,”伊格尔伯格的前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表示,“主要是苏联崩溃的速度让我们大吃一惊。不仅是我们的情报机构吃了一惊,戈尔巴乔夫也很惊讶,我们都很惊讶。” “我很惊讶,”贝克的前任乔治·舒尔茨表示,“虽然在里根总统任期的最后我们觉得冷战实质上已经结束,但是苏联的崩溃还是令人大吃一惊。” “我很惊讶,”20世纪80年代国家情报委员会资深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在中情局工作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表示,“我们没想到苏联会崩溃。” “我很惊讶,”华盛顿尼克松中心主席迪米特里·西梅斯教授表示,“当意识到苏联已经崩溃的时候。” “我很惊讶,”詹姆斯敦基金会主席、苏联民族问题专家、美国政府前高官保罗·戈布尔表示,“我们都没想到,苏联就那样停止存在了。” “我很惊讶,”20世纪80年代《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谢尔盖·施梅曼表示,“我和美国使馆的人都没料到苏联即将崩溃。我们还以为到2000年后都得与苏联共存。” “我很惊讶,”哈佛大学俄国历史教授理查德·派普斯表示,“我们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了若指掌,我们知道变化是巨大的,但是没想到它们会导致苏联的崩溃。” 致 谢 首先,我想感谢所有出现在这本书中的受访者。大多数受访者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和以色列的政界、学界和情报机构。感谢他们愿意抽时间与我们分享在世界政治方面的丰富知识和经验。他们所有人的贡献成就了这本书。 我们还想感谢一些朋友:感谢以色列外交部前总司长鲁文·默拉夫,他为本书的希伯来语版本提供了很多宝贵建议;感谢优秀的记者、编辑拉米·塔尔,他提出了许多编辑方面的意见;感谢莱斯利·苏瑟,他专业的翻译传神地还原了希伯来语原作的文字意思与内在精神。 引 言 1991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瞬间烟消云散,从战略、地缘政治和社会变革角度看,都算得上是20世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来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大事之一。苏联解体发生之突然,过程之迅速让政治家、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和媒体都大吃一惊,也让世界上最强大的两家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和克格勃措手不及。 上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并不平等的世界,生存之争会引发战争,包括部落、宗教及国家间战争,等等。在文明初创时期,由于害怕遭到攻击,一批早期预警系统得以建立,它们也成为现代情报机构的鼻祖。如今,这些情报组织享有特殊的地位、威信及大量预算资金。即使失误被曝光(有时已成为家常便饭),它们似乎也依然掌握着神秘的经验和知识。情报组织周围萦绕的神秘感创造出一种权力氛围,显示其通晓和塑造政治、战略变化的特殊能力。 尽管情报机构应为没有预见苏联解体而承担主要责任,政治家也有部分责任。他们被成见和政策所牵累,即便熟知相关情况,也没能洞悉苏联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决策者选择性地使用情报信息和采信评估,有时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一般认为情报机构不会受个人、小集团或者政治影响,但事实证明它们同样难逃其累。 西方国家都没能预见苏联即将解体。然而,没有人公开提出要将情报机构负责人撤职,也没有调查,认为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西方国家国会和媒体集体哑火,只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或者想当然地妄下结论。在美国,情报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弄清苏联的现实状况与未来走向,虽然美国每年在情报机构身上投入约300亿美元,但它们还是没完成任务。当时西德关注的焦点是苏联的动态及其卫星国的情况,不过,德国联邦情报局没能在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前让政府和公众做好准备,后者却没有要求其解释原因,而这一失败导致的历史欠债至今仍由德国公众承担。世界顶尖的英国情报机构采纳了美国对苏联形势的评估,而没有依靠自己的能力做出分析,使其国家领导人和其他人一样被蒙在鼓里。 在20世纪最后一段时间,其他声名显赫的情报机构也遭遇尴尬的意外情况。20世纪80年代初期,克格勃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没能正确评估阿富汗对苏联入侵的反应;以色列受人吹捧的情报机构没有及时洞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英国的军情六处未能预见阿根廷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都没想到萨达姆?侯赛因会进军科威特。 间谍机构的首要职责就是充当其效力国家的警犬。它们负责收集信息,提供评估,促使政治家做出理智周密的决策。多年来,许多情报机构变得强势而复杂,垄断了信息收集、评估以及秘密行动等业务。国家的命运,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的命运,似乎常常都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情报机制的质量。 然而,所有的情报机构都没能预见苏联解体,大到中情局、克格勃、以色列的摩萨德、英国的军情六处、法国的对外安全局、意大利的军事情报局,小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日本的情报机构。各国情报机构包含了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本来掌握的信息就不多,竞争关系更是成功地阻碍了信息共享。 与好莱坞电影中难兄难弟的情节不一样,那些所谓的“好人”编造出惊天阴谋,只为打倒苏联。他们带着十字军的热情,发起这场战斗。为了打倒苏联共产主义者的极权信仰,西方也用相同的热忱武装自己。而中情局也参加了这支“上帝”的部队。和任何宗教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有自己的“圣经”,即情报分析;另外还有“信仰”,即他们自己构建的事实。任何与上述“信仰”矛盾的报告,都会被视作“渎神”。 事后一想,这些情报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所掌握的情报就足以使他们得出结论:苏联不再具有战略威胁性,并处在迅速衰落的过程中;这创造了新的国际现实,呼唤着新的世界秩序。然而,即使一些美国情报官员偶尔察觉这个“邪恶帝国”不再是个帝国,而且并不那么“邪恶”,他们也没能将这一信息传达给美国政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发现预示着苏联行将崩溃,或者觉得最容易的事就是相信传统认识——苏联仍然是,并将一直是敌人。 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失误不仅蒙蔽了依靠它的其他西方情报机构,还蒙蔽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苏联问题专家及媒体。苏联本身的神秘,加上西方情报机构有计划的“爆料”,制造了整个西方的反苏阵线。这造成人们判断力的瘫痪,对近在眼前的变化毫无察觉,也排除了制定任何新政策的可能。 1991年10月,中情局负责苏联情报的前高级分析师梅尔文·A.古德曼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他宣称,对苏联的情报分析在经过中央情报局管理层时受到了“篡改”。美国很多情报工作人员和委员会成员当即否认了这一指控。然而,无论“篡改”与否,中情局的海外联系机构最终获得了这些情报,并据此得出一致的分析结论。而这最后又到了政客手上,他们利用这种分析打造对苏联的政策,尤其是在该分析佐证了他们自己的观念和政治议程的时候。 在整个冷战期间,对苏联的无情讨伐陷入了无休止的循环,在最后一段时间甚至发展到了太空。对苏联变化的忽视和误读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第三世界受到的影响尤其深刻。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曾说第三世界是“抵抗共产主义的主战场”,而就在那片饱受苦难的土地上,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苏联式共产主义模式水火不容。 整个世界都是角斗场。欧洲沦为核武器人质,而第三世界是主战场。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都努力不让战火烧到自己境内,而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展开大练兵。在这场所谓的“冷战”中,2000万人成为受害者。战火在世界各地燃起,远东的朝鲜、越南、柬埔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安哥拉、莫桑比克,拉丁美洲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格林纳达以及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都受到战争荼毒。 二战以后,并非所有的所谓“小战争”都由美苏直接挑起,但是每一场战争都会被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而且每一次都抱着针对对方的态度。一切行为都基于“非友即敌”的原则。 情报机构本应该向决策者解释,并非每一个发生在某个偏僻非洲角落的部族摩擦都是全球冲突的一部分,苏联在具体国家的一些政治、经济活动可能只是暂时的偶然行为,并非企图引发连锁效应的大阴谋。 有关情报机构支出的准确数字很难获得,而其中专门用于对付苏联的部分就更无从得知。同样,人们难以估计这些活动中有多少真正有必要,又有多少只是为了政治宣传或满足政客需求。1991年西方情报机构的总预算是400亿美元左右。其中美国所占的280亿美元中又有30亿美元是对中情局的专项拨款。而中情局的对头克格勃第一总局则在1991年花了49亿卢布,按照那年的官方汇率,相当于74亿美元。然而,第一总局的权力界定有不清晰之处,因此不能简单将两个机构的开支加以对比。大部分国家并不会公布情报机构支出在国防预算中的比重。因此,人们很难知道有多少钱纯粹是浪费公共资金,这些机构挫败的计划到底有多少威胁性,花出去的钱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没有预见到苏联的崩溃主要是情报评估者的责任。情报机构内部个人、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纷争,及其与政治人物、决策者和其他情报机构的复杂关系是产生这一失误的主要原因。那些亲眼见证苏联崩溃的人反应大多一致:“我们当时不知道。”“我们当时没弄明白。”“我们当时不知道,即使知道,还是会那样做。”用户评价
对于一个长期关注国际关系的业余爱好者来说,这本书提供的分析视角是相当新颖和富有启发性的。它没有流于表面地将苏联的解体归结为经济衰退或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失误,而是深入挖掘了信息战和心理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特别是关于西方情报机构如何通过非传统渠道渗透和影响东欧舆论的那些章节,资料的丰富度和论证的逻辑性令人叹服。我特别欣赏作者没有采取一种简单的“西方胜利”的论调,而是客观地探讨了这些干预行为的道德灰色地带,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加速了既有体系的瓦解,而不是仅仅搭了顺风车。这种批判性的平衡视角,使得整本书的厚重感和可信度大大提升,远超市面上那些偏颇的断论。
评分阅读完这部作品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关于“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重新审视。它让我意识到,在那些看似宏大叙事的背后,无数次微小的、几乎无人察觉的决策和信息传递,才是真正推动历史车轮滚动的力量。书中对于特定时间节点上,情报部门内部对于“是否要采取更激进手段”的辩论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历史决策的复杂性,它不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而是充满了内部的犹豫、误判和偶然的机遇。这种对“过程”的细致捕捉,远比只看“结果”要有价值得多。读完后,我对1991年夏天的剧变有了一种全新的、更加立体和人性化的理解,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能俯瞰历史全貌的制高点上,看到了那些平时隐藏在历史云雾之下的齿轮是如何咬合转动的。
评分这本书的引文和参考资料部分,绝对是学术界的一座宝库,这方面的工作量之大,简直令人咋舌。我特意翻阅了脚注和尾注,发现作者的引证来源非常广泛,涵盖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背景下的解密档案、前特工的回忆录,甚至是当时主流媒体的社论对比分析。这种跨越不同语种和不同信息源的交叉验证,使得书中每一个关键论点都有坚实的文献基础支撑。对于我这样的深度阅读者而言,那些详细的脚注本身就是一张延伸阅读的路线图,它指引我去探究那些未被完全展开的侧面历史。这表明作者对待历史事实的态度是极其严谨和负责任的,而不是简单地进行二手资料的拼凑和转述,这是高质量历史著作不可或缺的灵魂所在。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硬壳封面那种略带磨砂质感的深蓝色调,与书脊上烫金的标题形成了一种既沉稳又不失力量的对比。初次翻阅时,我注意到纸张的选取非常考究,米白色的内页不仅护眼,更重要的是,它很好地承载了那些厚重的历史细节和复杂的地图插图。在阅读过程中,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种八十年代末期冷战氛围的压抑感,设计者显然在视觉语言上花了大量心思去重现那个“铁幕”尚未完全倒塌的时代感。尤其是内页排版,大量的注释和旁边的空白留白处理得恰到好处,这让信息量巨大的文本在视觉上得到了有效的疏导,阅读体验相当流畅,没有一般学术著作那种令人望而却步的枯燥感。这不仅仅是一本书的包装,更像是一件精心制作的历史档案复制品,让人在拿起它的那一刻,就仿佛被拉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十年之中,为接下来的阅读做好了一种心理准备,这份对细节的执着,已经超越了普通商业出版物的范畴。
评分我必须得提一下作者对叙事节奏的把握,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示范。尽管主题是关于情报工作的博弈,听起来会是枯燥的档案整理,但作者巧妙地将宏大的地缘政治变动,穿插进具体的、充满人性的微观事件中。比如,书中对某些外交密会场景的描绘,那种在雾气弥漫的柏林街头,特工们如何通过眼神、手势传递信息的细节刻画,其紧张程度不亚于最精彩的谍战小说。然而,它又不是纯粹的虚构,每一次紧张的描摹之后,紧接着就是对相关政策文件或者解密电报的冷静分析,这种张弛有度的叙述方式,让读者既能感受到历史的戏剧性,又不会迷失在纯粹的感官刺激中。这种叙事技巧的成熟,显示出作者在处理复杂史料时所具备的非凡功力,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一口气读完了好几个章节而浑然不觉时间的流逝。
评分东西真不错 价格也还算公道 不错不错
评分好书
评分666666666666666666
评分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好喝
评分好很好,非常好
评分好书好价,送货快,质量优,喜欢京东
评分详细介绍了西方情报机构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对今天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评分书脊稍有瑕疵,看着像是出厂时就有的,暂时忍着不换,其他还好,期待内容。
评分速度够快,优惠更多,非常方便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